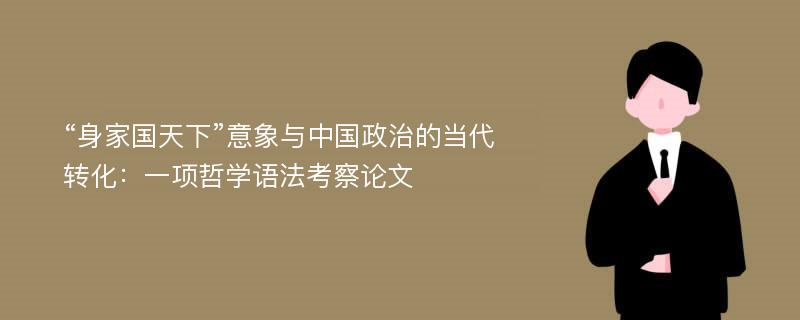
“身家国天下”意象与中国政治的当代转化:一项哲学语法考察
□ 刘梁剑
摘要: 自先秦以降,“身家国天下”乃是中国人理解世界和指导个体生命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的最基本意象之一。“身家国天下”意象是中国文化赖以生存的一个隐喻性概念或概念性隐喻。本文探讨“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内在结构、利弊得失及现当代转型,同时通过“身家国天下”意象体察隐喻和意象思维的一般特点和中西之异。“身家国天下”意象隐含内-外图式、本-末图式、涟漪图式。内-外结构突显了中心对于外围的结构性优势,与之相应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外围对于中心的内在建构意义,忽视外围自身的独特性,及其有别于中心(家区别于身,国区别于家,天下区别于国)的独特性。本-末图式、涟漪图式分别将植物生长与活水的经验用隐喻的方式投射到由身、家、国、天下所构成的社会生活之域,构成了中国思想的一个特色。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身家国天下”意象的缺陷以及由此意象所引导社会政治实践层面的缺陷不容忽视。异者别之、弱者强之(将国区别于家,改变家强国弱的状况;将天下区别于国,改变国强天下弱的状况),“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当代转化亟待实现。在方法论的层面,本文尝试在意象考察的层面进行哲学语法考察。
关键词: 身家国天下; 隐喻; 意象; 意象图式; 哲学语法
一、“身家国天下”,我们赖以生存的意象
我们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国家,然则,何谓“国家”?按照习见的做法,我们需要给国家下一个定义,找到比“国家”外延更大的属概念(比如,“政治团体”),同时刻画出国家在这个属概念之下有别于其他种概念的特性(比如,兼具领土、人民、主权和政府四要素),如此方能在抽象的层面深入国家的普遍本质,达到思想的超越性和纯粹性。
然而,中国人对“国家”似乎有一种更为素朴的、顾名思义的理解:国家国家,以国为家,国是“大”家。我们似乎很自然地将对于家的切近而具体的有感之知投射到国之上,因了这种投射,国不再是抽象遥远的概念。不妨说,“国”是意(概念),“家”是象,“国家”则是意象,即有象之意,或曰,栖居于象之上的概念。
“国家”意象也从一个方面例证了莱考夫、约翰逊等西方当代学者关于隐喻的若干说法。“不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我们思想和行动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1] 1“国家”中的家之象,正不妨说是一种隐喻(metaphor)。我们祝福朋友“事业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或祝福他“事业蒸蒸日上”,或祝福他“事业发达”。从修辞学的角度看,“芝麻开花节节高”是明喻,“蒸蒸日上”是隐喻,而“发达”则是抽象概念。细究起来,“发”“达”原初何尝没有隐喻之象:“发”(發)字从“弓”,箭之发射,舒扬开展;“达”字从“辶”,通也,畅也。只是它们如今在“发达”这个概念中似乎已经是衰竭的死隐喻。相较而言,“国家”中的家之象,依然是活的隐喻,依然作为“国家”意象(conceptual metaphor)的有机部分对当下中国人的“国”概念造成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发生的家庭革命、国民塑造等运动曾试图以极其激进的方式消灭这一“国家”意象,但它经种种变异,至今还是顽强(抑或顽固)地存活着。福兮?祸兮?
“国家”意象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身家国天下”意象。最有名的莫过于《大学》第一章(朱熹尊之为《大学》中“经”的部分,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直接标举为“圣经”[2] 394)所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子·离娄上》也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类似的提法不限于儒家。如《老子》五十四章:“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自先秦以降,“身家国天下”乃是中国人理解世界和指导个体生命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的最基本意象之一。这里的“意象”(conceptual metaphor,概念性隐喻)相当于隐喻性概念(metaphorical concept),象(隐喻)与意(概念)一体两面故。
按照通常的理解,隐喻是一种修辞学策略,一种语言文字层面的诗意点缀。莱考夫、约翰逊则提醒我们注意,有一些隐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的生存本身就依赖这些隐喻,我们就靠这些隐喻构建了理解世界并据之行动的概念系统。莱考夫、约翰逊把这些隐喻称为隐喻性概念(metaphorical concept)[1] 1-3。语言并非外在于人或世界的工具,而是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一种样态。我们的概念是隐喻性的,与之相应的实情则是:“我们的许多活动(争辩、解决问题、预算时间,等等)在本质上是隐喻。刻画我们日常活动的隐喻概念建构了我们眼前的现实。新隐喻有创造一个新现实的力量。当我们按照隐喻开始理解我们的经验时,这种力量开始起作用;当我们按照它开始活动时,它就会变成一个更深刻的现实。如果新隐喻进入我们赖以活动的概念系统,它将改变由这个系统所产生的概念系统、知觉、活动。许多文化变革起因于新隐喻概念的引入和旧隐喻概念的消亡。例如,全世界的文化西化其实部分就是把‘时间就是金钱’隐喻引入这些文化的这么一回事[1] 134。”“身家国天下”意象在中国文化的变革中易而不易。基于此,我们可以说,“身家国天下”意象是中国文化赖以生存的一个隐喻性概念或概念性隐喻。
我们且探讨“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内在结构、利弊得失及现当代转型,同时通过“身家国天下”意象体察隐喻和意象思维的一般特点和中西之异。
做哲学,哲学语法考察不失为一种有用的途径。所谓哲学语法考察,乃是细致勘察语言的线索,从中捕捉思想的蛛丝马迹。哲学首先要穷理,穷理不仅要考察概念,还应研究观念(史),留心语言的间隙(虚词)与语言的展布(句式)。哲学固然涉及概念创作,但也应当考察观念(史)、注目虚词与句式、创作意象与隐喻[3]。本文尝试在意象考察的层面进行哲学语法考察。
二、内-外,本-末,涟漪:“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内在结构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考察了“上-下”这一空间化隐喻如何将一些概念加以系统组织。快乐为上,悲伤为下;有意识为上,无意识为下;健康和生命为上,疾病和死亡为下;控制为上,被控制为下;多为上,少为下;尊为上,卑为下;优为上,劣为下;善为上,恶为下;理性化为上,情绪化为下。其中任何一个空间化隐喻(如“快乐为上”)内部具备系统性,而上述种种空间化隐喻分享了“上-下”结构,因而构成连贯的隐喻系统。基于此,莱考夫、约翰逊进而得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其中包括:大多数基本概念依赖一个或多个空间化隐喻;空间化隐喻不是任意的,它们扎根于我们的身体经验,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影响[1] 11-19 。
3.3 食葵地红蜘蛛的防治:用2.0%阿维菌素3000倍液~800倍液,或多虫螨丁2500倍液~3000倍液均匀喷雾。
莱考夫在《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范畴显示的心智》一书中深化了相关研究。尽管莱考夫的表述不无混乱之处,其大意似可概括如下:上述的“身体经验”被描述为人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层次,它表现为格式榙感知、心理意象和肌动运动等前概念结构,而上述的“空间化隐喻”则被解释为由身体经验而来的前概念“结构”激发了空间化的基本意象图式,人们通过隐喻方式将基本意象图式投射到抽象领域,形成抽象概念,但抽象概念仍保持意象图式的基本逻辑[4] 277-311。
然则,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莱考夫对中心-外围(内-外)意象图式的如上论述在相当大程度上与“身家国天下”意象中的中心-外围(内-外)结构颇为相契,中心对于外围的结构性优势显而易见。从中国思想史上看,这一点构成了“身家国天下”意象的一个内在缺陷。意象乃名言之一种。诚如杨国荣所言:“名言具有敞开存在的作用……但从另一角度看,名言往往又有遮蔽对象的一面。”[6] 164名言总是幽明并作,既开显又遮蔽。任何意象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它在突显某一面向的同时总是遮蔽了另一些面向。莱考夫、约翰逊分析了争论的战斗隐喻,同时指出,这一隐喻概念妨碍我们注意到争论还有合作的面向[1] 7。“身家国天下”意象中的中心-外围(内-外)结构突显了中心对于外围的结构性优势,与之相应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外围对于中心的内在建构意义,忽视了外围自身的独特性,及其有别于中心(家区别于身,国区别于家,天下区别于国)的独特性。这是“身家国天下”意象的一个不尽人意之处,也是“身家国天下”意象主导下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不尽人意之处。《论语》“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固然通过“以”将“人”“百姓”作为目的收摄为己的内在意图,但这只是在价值目标上突显了社会价值(群体的安定)和群体价值[注] 杨国荣从价值层面细致论述了修己与安人、安百姓的关系:“修己即道德上的自我涵养,安人、安百姓,则是指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后者显然已超出了单纯的道德关系,而与广义的社会进步相联系。这样,我们便不难看到,道德关系上的自我完善(为己),最终乃是为了实现广义的社会价值(群体的安定与进步)。孔子的如上看法既不同于无视个体价值的极端的整体主义,也不同于排斥群体的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表现了将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自我实现与社会安定统一起来的致思趋向。”(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并没有把“安人”“安百姓”作为独立的领域加以关注和专题探讨。《大学》第一章的本末先后厚薄叙事强化了这一点:“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氨甲环酸组患者术中失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术前术后血红蛋白差值也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2)。术后情况:虽然氨甲环酸组输血患者比例较对照组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术后引流量、凝血功能、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3)。两组术后均未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及肺栓塞。
基本逻辑:外围依赖于中心,而不是相反。
身体经验:我们的体验是人体具有中心(躯干和内部器官)和外围(手指、脚趾、头发)。同样,树木和其他植物也有中心的主干和外围的枝叶。中心在两方面比外围更加重要:①中心部分的毁坏,要比外围部分的毁坏更为严重(如无法恢复整体,并常有生命之虞);②同样,中心以外围部分不具备的方式界定个体的身份,一棵树没有树叶同样是一棵树,一个剃光头发或失去手指的人还是一个人。因此,外围被认为依赖于中心,而不是相反。血液循环不良可以影响头发的健康,但失去头发并不影响血液循环系统。
结构成分:实体、中心和外围。
莱考夫例举的基本意象图式包括容器图式、源头-路径-目标图式、链环图式、部分-整体图式、中心-外围(内-外)图式、上-下图式、前-后图式等。不难看到,“身家国天下”意象隐含着中心-边缘(内-外)图式。“身家国天下”意象首先呈现为多重中心-外围(内-外)结构:身是中心(内),家是外围(外);家是中心,国是外围;国是中心,天下是外围。进一步看,在先秦思想中,中心-边缘(内-外)结构之为基本意象图式,还被用来组织其他一些基本概念:典籍的“内篇”“外篇”;夷夏之辨,华夏居中心,四夷居外围;内圣外王的政教理想。诚如陈赟所言:“以教为里,则治为表;以圣为内,则以王为外,这就是《天下》所谓的‘内圣外王’,它代表了中国思想对治教结构的终极回答”[5] 25;人在天地间的位置:人者天地之心(《礼记·礼运》),天、人、地三才之道(《易传》)[注] 以人为中心、以天地为外围的意象也见于宋儒张载的《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如此等等。
莱考夫探讨了中心-外围(内-外)意象图式的身体经验基础、结构成分、基本逻辑与样本隐喻:
旱育秧3叶内以旱为主,促其根系发达、长成壮秧,尽量做到床土不开裂不浇水、秧苗不卷叶不浇水。3叶以后要适当提高床土水分含量,保持土壤湿润,切忌用大水漫灌。阴雨天要盖膜挡水,并及时排干畦沟水,达到最大限度地控水。
虽然当前乡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队伍的管理工作仍面临诸多问题,但要不惧困难迎难而上,积极面对压力与挑战,采取多种有效方法全面打造教师队伍。从上级部门到乡镇幼儿园本身等多层面、多角度落实与开展教师队伍管理工作,及时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为乡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队伍的良好建设与管理做不断的努力与尝试。
首先可以注意到,莱考夫的观察与三才之道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经验并不完全相契。“顶天立地”的身体基础不是被经验为唯我独尊,而是被经验为亲密的共在。人处天地之间,意味着人是万物之灵,需要自觉承担起以成己万物的方式参赞天地之化育的责任,但这并非人主宰、征服、利用万物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之相应的基本逻辑,不是外围依赖于中心,而是外围与中心相互依赖、相互成就。在此我们看到,三才之道所体现的中国思想传统对于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有着另一种不同的经验方式和理解方式。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上文提及的莱考夫、约翰逊的一个观点:空间化隐喻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影响。
(2)货币供应量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一般认为M2与不良贷款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当货币供应量下降,利率上升,企业利润随之下降,选择向银行贷款维持资金流通,商业银行风险增加;当货币供应量增加,利率下降,企业融资成本下降,利润增加,企业财务状况也得到改善,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
育苗营养块营养面积较小,定植时间要比普通营养钵育苗适当提前,只要根系布满营养块,白尖嫩根稍外露,就要及时定植,防止根系老化。定植前5~7天开始进行逐渐降温,增强光照,适当控制水分锻炼秧苗,接近定植地环境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以修身为本”,《大学》同时用本-末图式说明身家国天下。易言之,“身家国天下”意象除了隐含中心-边缘(内-外)图式之外,还隐含本-末图式。本为木之根,末为木之梢;本相对于末不仅逻辑在先、时间在先,而且还是源源不断提供生长活力的源头。本-末图式将植物生长的经验用隐喻的方式投射到由身、家、国、天下所构成的社会生活之域,由此却很自然地对应于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自然和人类社会分享共同的“道”,人道应合乎天道,而推天道可明人事。这也是“天人合一”的一层含义。我们之所以讲“本-末图式”,那是因为它是中国思想的基本意象图式之一。后世由“本”发展出“本体”,而本体之学颇不同于ontology意义上的本体论,恰恰因为本体之学栖居在“本”的植物生长隐喻之中[7] 1-8。人性论讨论人之本性,同样受到“本”喻的牵引。在汉学家艾兰(Sarah Allan)看来,“植物生长的原则从植物自身扩展到对所有生命的理解,其中包括人类。因此,人不是所谓‘理性的动物’,而是恰当培养后使可生长成熟的具有特定潜质的生物。”[8] 109本-末图式是植物生长隐喻而非空间化隐喻,而莱考夫所讨论的基本意象图式都是空间性的。这里或许透露出中西思想的某种根本差异:植物生长隐喻存在于中国思想的基本意象图式之中,但并不存在于西方思想的基本意象图式之中[注]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思想中没有植物生长的隐喻(如海格格尔对古希腊思想中的“physis”的自然生长义做了精彩的阐释)。 。
上文的“身家国天下”意象中的中心-外围(内-外)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外围自身有别于中心,如国区别于家的独特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完全忽视了家国之别。实际上,儒家曾将“门”喻引入内-外结构,形成复合的“门内”“门外”意象。由于“门”的间隔作用,门之内外不是中心与外围意义上的内外,而是不同领域的内外,与之相应的则是不同领域的治理原则:“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礼记·丧服四制》)陈乔见对此论之甚详。在他看来,门内门外之分类似于西方公域和私域的区分,门内是家庭内部的人物事及其关系,门外是家庭以外的政治公共领域。儒家主张公域和私域的区分,主张治国以公义为主导原则,齐家以私恩、私情为主导原则[9] 257-309。他进而强调:“所谓‘齐家’与‘治国’不分的说法,只有在个人‘修身’的意义上才是成立的,也就是《大学》所谓‘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若是认为儒家‘齐家’与‘治国’的原则毫无分别,那是非常荒谬的。前文关于‘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的论述已有充分证明。”[9] 376不过,依笔者之见,儒家思想中固然有重视家国之别的面向,但是,由于“门内”“门外”意象的影响力远不如“身家国天下”意象,重家国一体而忽家国之别仍然是儒家思想的主要面向。时至今日,孟德斯鸠在18世纪中叶所做的远距离观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不失为洞见:“中华帝国构建在治家的理念之上。”[10] 368
我们曾说,“身家国天下”意象首先呈现为多重中心-外围(内-外)结构。上文分析了内-外结构,但尚未触及它的多重性。因其多重性,中心-外围(内-外)结构拓展为涟漪结构[注] 费孝通先生曾用涟漪意象说明中国的差序格局:中国的社会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5页)。 。这一结构除了中心-外围的静态空间性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心影响外围的动态意蕴。与本-末图式的植物生长性类似,涟漪图式可以说是一种基于活水的本喻。《孟子·离娄下》下面这段话则巧妙地将植物与水、本与源绾合在一起: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很显然,个人-家庭-团体-天下继承了“身家国天下”意象。不过,其中诸项的意涵已经发生古今之变。现代人习惯于从权利主体、理性主体等角度理解的个人,显然与先秦的“身”所指向的关系性德性主体有所不同[注] 当然,这是相当粗略的说法。另一方面,身相对于家国天下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范式,有待进一步考察。 。周初分封诸侯,建立封建制。周天子富有天下,诸侯有其国,大夫有其家。《大学》所讲的“身家国天下”与此对应。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封建制走向瓦解,终究在秦朝为郡县制所取代。与之相应,家变为家族,国变为一姓之朝廷,天下则变为国之外的广大空间,有时也指天下百姓,以及民心天道这样更为抽象的价值。近代以降,家变为家庭,国变为民族国家,天下或变为现实政治形态的世界,或由天下百姓衍为人民、(民间)社会,或由民心天道衍为价值理想形态的文明价值。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
就水喻而言,这里虽为由源而流的线性意象,但也未尝不可说明由源头发动而向外围流溢的涟漪意象。道家乐水,儒家亦观水有术。艾兰所著《水之道与德之端》揭示先秦哲学家的许多基本概念根植于水与植物的意象,并且认为二者具有内在的相关性:水滋养植物。“涟漪”亦未见于莱考夫所列举的诸种基本意象图式。如果说,本-末图式将植物生长的经验用隐喻的方式投射到由身、家、国、天下所构成的社会生活之域,那么,涟漪图式则将活水的经验投射到由身、家、国、天下所构成的社会生活之域。
2.1 S1P对血管内皮屏障功能的调节作用 血管内皮细胞和基底膜构成的血管内皮屏障是维持毛细血管正常通透性的关键[9]。脓毒症时,在各种炎症和凝血因子的作用下毛细血管内皮屏障功能受损,毛细血管通透性异常增加,体液渗漏至组织间隙,造成组织水肿和细胞缺氧损伤,严重时可导致器官功能障碍。研究[10-12]表明,内皮屏障功能损伤程度与脓毒症的病情严重程度正相关。
人们常常把身家国天下同构称为几何学上的“同心圆”,但“同心圆”依然是静态的,未能表达出“涟漪”以中心点为源头,影响力逐渐向外传递的动态。影响力从中心向外传递的动态机制,儒道二家不约而同地归之为德化。当然,二家所理解的德化不尽相同。加拿大学者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对先秦典籍中的“无为”意象进行了精彩的研究。他在诠解《老子》五十四章时已指出,在老子那里,圣人之德影响天下的方式迥异乎儒家。《论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相反,老子的圣人通过“处众人之所恶”“知其白,守其黑”而为“天下式”。老子的圣王放低身段,让自己的德性以微妙的方式发挥影响,从而让老百姓涤除不自然的欲望和不自然的行为,让天下回归理想的自然之境[11] 5。简言之,老子的德化是处下守弱,无为而化;儒家的德化则是居上用强,有为而化。森舸澜的诠解不无所见。在儒家那里,德化的源头居上而可见,如泉涌之水;在老子那里,德化的源头处下而不可见,如漩涡之渊。进而言之,老子的德化是做减法,通过圣王德性的感化消除众人不自然的欲望与行为;儒家的德化是做加法,通过圣王德性的感化扩充众人本有的道德良知与道德行为。
另一方面,儒家的德化也主张无为而化,而不像森舸澜在此处所讲的有为而化。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这是讲德性由不可见之内心施于可见之四体,形成后来宋儒所讲的气象,或曰气场。进一步,则是德性气场在其场域中由己施于人。德性的主体,可为无位之君子,亦可为有位之君王。《论语·卫灵公》如此描述作为君王典范的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艾兰解释说:“尽管此段文字未及水这个词,但其意义最适宜于依据水的隐喻来解读:舜(像水)没有任何精心策划的行动,但他的仁德从他那里自然扩展开来,像泉涌之水流溢延展。”[8] 88“扩展”“流溢延展”,正是德性气场在其场域中由己施于人。陈赟考察儒门庄子的政治哲学,试图以这种德化方式对治现代政治之弊:“‘化’的生命政治学被概括为‘无为而无不为’,与当代政治生活中将一个中心点贯彻落实到世界的一切角落与细节中的强力的有为性相比,‘化’的政治并不营造一个作为中心点的最高目的,而是在人民的性命之中以其自正性命为目的,这样的政治行为便不再是强硬的植入,因而也不需要全民动员与深广的宣传。”[5] 5-6这里对现代政治的弊病极富洞见,但对儒家德治的论述似乎显得过于理想化了。儒家德治以圣王一人为政治生活的中枢,这样的圣王未曾有过,将来也不可能有。儒家德化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君如何形成有效的影响力,而不在于民如何成为自正性命的主体,因为民只是消极被动的追随者。再者,面对家国结构的古今之变,德化的有效作用场域乃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三、异者别之,弱者强之:“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当代转化
任何意象都是有缺陷的,由此引导的行动也是有缺陷的。“身家国天下”意象亦然,“身家国天下”意象引导的个体实践与社会政治实践亦然。近现代以来,在“古今中西”互镜的语境下,很多思想家对此深有洞见。梁漱溟曾标举个人-家庭-团体-天下四级关系。其中,家庭本于夫妇父子等亲缘关系,兼家族亲戚等,团体包括国家,以及宗教、种族或阶级等意义上的团体,天下则泛指社会、世界人类或国际等[12] 162-169。梁漱溟进而指出,中西之别表现为,“在西洋人的意识中生活中,最占位置者为个人与团体两极,而在中国人则为家庭与天下两极。”[12] 169“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12] 77-78
通过测试发现,用户操作软件能够完成自动检测、水下运动和实时监控等功能,软件的操作效率和人机交互水平也得到提高。
样本隐喻:这些理论具有中心原则和外围原则,重要的东西就被理解为中心。[4] 283
梁漱溟讲家庭在西方几若为虚位,这一点可证之以《理想国》。《理想国》考察正义,认为身之正义与国之正义相类,身(确切地说,灵魂)之正义在于理智、激情、欲望三者达到和谐,而国(确切地说,城邦)之正义在于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三者各司其职和谐统一[注] 这里表达的国身相同似乎只是逻辑同构的、静态的。实则不然。杜威概述《理想国》教育观:“当社会中每个人都能按照他的自然禀赋做有益于别人的事情时(或对他所属的整体有所贡献的事情),社会就能稳固地组织起来;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一个人的禀赋,循序渐进地加以训练,应用于社会。”(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98页)这就从特定的角度指出如何通过身之正义实现国之正义。但同时杜威又指出,“只有在一个公正的国家,它的制度、习俗和法律才能给人正确的教育”(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第99页)。易言之,身之正义的实现离不开国之正义。从身到国,复由国到身,二者是双向的。相形之下,“身家国天下”则呈现为由中心到边缘的单向逻辑。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固然也提到家庭,但他的主导观点在于,城邦与个人相同,应各修四德(智、勇、礼、义)庶几可得真正的快乐。身与国直接关联,家似乎是可以缺席的。何以如此?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城邦为最高级的社会团体,虽由家庭组成而较家庭为更能自给自足。城邦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13] 8-9。“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13] 7亚里士多德由此以目的论的方式论证人依其本性是城邦的动物。人成就自身只宜成之于城邦之中而非家庭之中。同样是修身,古希腊人首先修之于城邦,中国人则首先修之于家——这里的“城邦”或“家”,首先要在目的论的意义上而非具体场所的意义上加以理解。
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同,《老子》《大学》讲国身相同,都以家为中介。当然,细察之,家在《老子》《大学》中的价值又不尽相同。《老子》那里,家似乎只是修辞上的虚设。《老子》的修身是离“家”弃“家”的修身(绝仁弃义,遑论孝悌)。而在《大学》那里,家则是修身得以展开的内在场域(孝悌为仁之本)。
但另一方面,《老子》固然不重视家,他的治国主张却仿佛是从齐家化来。在他看来,圣王治民应如慈母待赤子。《老子》从不同的角度涉及母子意象[注] 莱考夫考察了英语中的“母亲”(mother)概念,认为它是根据群集模式(cluster model)形成的,其群集模式中包含多种单一的认知模式:生育模式、遗传模式、养育模式、婚姻模式、家系模式。不同的模式可以重合,但也可能分离。在现代社会,这几种模式出现分离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参见莱考夫:《女人、火与危险事物》,第79-82页)。 。 其一,母生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其二,母育子。“大道汎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二十四章)“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五十一章)其三,复归赤子在母亲怀抱的经验[注] 《老子》中的“赤子”似以男婴为原型:“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老子》五十五章) 。“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二十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五十二章)在治国的语境中,《老子》主要以养育模式理解母子关系。“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老子》四十九章)
儒家之“慈”不限于母,有慈母,亦可有慈父。如云“父慈子孝,姑慈妇听”(《左传·昭二十六年》)。不过,儒家同样主张,圣王应如慈父或慈母,治国使民“如保赤子”。《大学》传第九章引《康诰》“如保赤子”说明“慈者,所以使众也”:“心或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四书大全》引朱子说:“保赤子,慈于家也。如保赤子,慈于国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众。心诚求赤子所欲,于民亦当求其不能自达者,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众也。”宋儒吴季子推衍其义甚详:“人之赤子之当慈也,虽暴戾之夫,顽狠之人,一见赤子,则慈爱之心油然而生,盖不待教而能者。”“夫赤子之在襁褓,寒则欲衣,饥则欲食,疾痛则欲抚摩,痒疴则欲抑搔,盖与成人等耳。然其所欲了然于心而未能宣之以言,则夫为之保抱携持者,莫难于求其中心之所向。是故察之乳哺焉,察之卧起焉,察之声音笑貌焉,不待赤子之言,而自然合乎赤子之意,此父母之心最真实而无妄者。”[14] 62-63
“赤子”意象蕴含、激发民本思想,有其历史及逻辑合理性,同时在当代仍有其生发的潜能。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母子之喻和民本思想的限度不容忽视。“赤子”意象所突显的是,赤子有饮食等基本生理欲求而不能言,父母慈爱之心存乎天然,自然心知其欲。若以如此这般的“赤子”意象视“民”,可注意者有二。其一,往往注意民的基本生理欲求,温饱问题,物质需求(如俗话说“把群众的冷暖放心上”),而忽视其精神需求(在现代社会中,包括人身安全、财产安全、言论自由等基本政治诉求;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则是尚待觉醒为国民或公民的前现代之子民或臣民[注] “子民”“国民”之辨,可参见刘梁剑:《国民意识的觉与梦》,载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十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其二,“民”是需要被照料的婴儿(巨婴)。法家曾以蔑视的口吻说道:“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韩非子·显学》)尽管在对待民的态度上有呵护照料与蔑视驱使之别,但儒家还是与法家共享了相同的看法:民无知无能。在现代社会,这意味着,民不是独立的人格主体、社会公民、主权所在之民,而与“民”相应的“(父母)官”则是不成熟之民的看护者,在德、智、才诸方面优于民,在权力、社会地位诸方面高于民,而不是在德、智、才诸方面成熟之民所委托的管家,其权力、社会地位诸方面源于民而“低”于民。另一方面,国与国民的相互缔造,只要国民没有真正成为政治权利的主体,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或公民,国家也仍然没有从传统的家国同构意义的国的形态走出来,国与民之间的法权关系便没有真正建立。
因此,“身家国天下”意象的改良首先需要异者别之、弱者强之:将国区别于家,改变家强国弱的状况,克服家的僭越,避免以齐家原则代替治国原则的危险。梁漱溟已指出: “旧日中国之政治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所以说‘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慈者所以使众’,而为政则在乎‘如保赤子’。自古相传,二三千年一直是这样。这样,就但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间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之团体关系。”[12] 83旧日中国之政治构造根深蒂固,依然影响着今日中国之政治构造。是深可忧者。
存在于我国大部分企业中的,阻碍其基层党建政工工作开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企业不论是管理人员还是员工,都没有从源头上给予党建政工工作足够的重视度,这就导致了企业上下对党建政工工作从思想上的漠视。现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形式更加多样化,存在于我国企业中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而企业内部基层党建政工工作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开展,也是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其中一部分,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高速公路桥梁桥墩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地质条件、地形地貌以及墩高尺寸来选择最佳的结构形式,通常情况下会选择使用薄壁墩、圆柱墩等形式:
相较于家强的国弱,乃是因为以家代国,以家法代国法,未成立当代意义上的国家。但另一方面,似乎又是国(政府,政党)强而天下(人民、民间社会)弱。就此而言,弱者强之意味着以天下限国。国的合法性基础之一,在于天下(自主的民间社会;人民,不仅有腹有目而已,而且有心,是权利主体,是生命实践的主体)。
如前所述,天下兼有三层意涵:人民、(民间)社会,现实政治形态的世界,价值理想形态的文明价值。以天下限国,在后两个层次也是必要的。就现状而言,世界并非像国家那样是一有机体,而是不同民族国家以离散的方式置身其中展开生存竞争的丛林。这样,从国到世界是一种断裂,而非连续。身家国连续体以国为界,没有延伸到世界。作为政治单位的世界尚未形成。然而,居今之世,人类后经学时代已经来临。国的合法性基础之一,将在于能否把世界历史、人类整体作为自己的思考单元纳入国家意志[15]。另一方面,需要作为文明价值的天下约束国家。诚如许纪霖所言:“国家理性总是有一种内在的冲动,试图挣脱和凌驾于一切宗教和人文的规约,权势成为其唯一的目的,国家成为超道德的利维坦。……倘若国家理性缺乏宗教、人文和启蒙价值的制约,任凭其内在的权势扩张蔓延,便会从霍布斯式的功利主义走向保守的浪漫主义,蜕变为缺乏道德取向的价值虚无主义,而最后催生出反人文、反人性的国家主义怪胎。国家能力愈强大,国家理性便愈自以为是,其坠落悬崖的危险性也就愈大[注] 这里提到了宗教之于国家的意义。这或许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近现代康有为等人对儒“教”的渴望。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在国家层面,儒教追求现代版的神道设教,以制衡国家按其(利维坦)内在本性及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惯性所导致的惟富强、利力是求的国家理性。这样的国家理性缺乏终极意义上的价值维度,似乎并不能真正以个体的良好生活为追求目标。 。”[16] 12近二十年来,赵汀阳“天下体系”、许纪霖“新天下主义”等设想,都表现出将身家国连续体延伸到世界的某种努力,亦表现为整合作为现实政治形态的世界与作为价值理想形态的文明价值。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如果文明、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仁等价值形态被富强、力与利所压倒,“天下”等就会从一个超越中国的概念蜕变为一个证成中国的权宜概念。
如此,异者别之、弱者强之意味着:将国区别于家,改变家强国弱的状况;将天下区别于国,改变国强天下弱的状况。如此,我们能否实现“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当代转化?鉴于意象与世界的密切关系,变革意象即是变革世界。
参考文献:
[1](美)莱考夫、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载《船山全书》(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
[3] 刘梁剑:《天人共同体视域下的正义观:一项哲学语法考察》,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
[4](美)莱考夫:《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范畴显示的心智》,李葆嘉、章婷、邱雪玫译,李炯英审订,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
[5] 陈赟:《庄子哲学的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6] 杨国荣:《史与思》,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杨国荣:《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 (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张海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 陈乔见:《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
[10](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11] Edward Slingerland. Effortless Action .Wu -wei as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Spiritual Ideal in Early China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14](明)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刘梁剑:《人类后经学时代的中国哲学运思》,载邓辉、郭美华主编:《东方哲学》第十辑,2017年版。
[16]刘梁剑:《能否跳出“现代”的掌心?》, 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4期。
[17]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of Self-family-state-tianx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Today: An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Grammar
LIU Liang-jia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Self-family-state-tianxia ” has functioned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onceptual metaphors that lead Chines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perform personal and social practice. In this sense, it is a metaphor that Chinese culture lives by. Analyzing its internal structure at the levels of inter-outer scheme, root-branch scheme and ripple scheme, this thesis discuss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thinking and consequ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as well as its possible transformation today. In this process, some features of Chinese metaphorical thinking as well as metaphorical thinking in general are also explored. Methodologically speaking, this thesis illustrates a way to philosophize by examining a conceptual metaphor as an aspect of philosophical grammar.
Key words: self-family-state-tianxia ; metaphor; conceptual metaphor; scheme of a conceptual metaphor
中图分类号: B21;D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2019)04-0001-07
作者简介: 刘剑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8JZD014)
收稿日期: 2019-04-10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4.01
责任编辑 吴兰丽
标签:身家国天下论文; 隐喻论文; 意象论文; 意象图式论文; 哲学语法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论文; 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