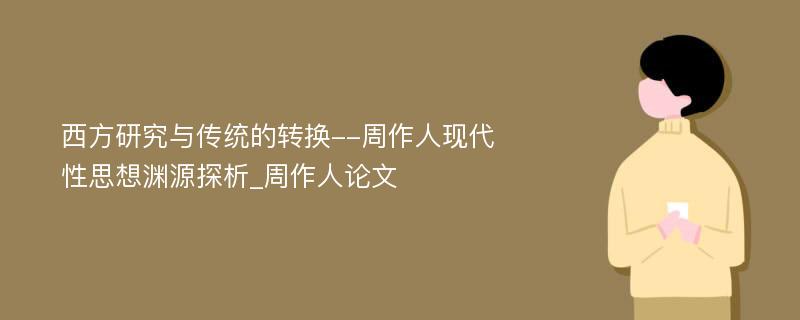
西学与传统之间的转换——周作人现代性爱思想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思想论文,周作人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性爱思想是周作人思想革命的利器。当年,周作人被称为“中国蔼利斯”,致力于提倡健全的性道德。①周作人的性爱思想来源复杂,其形成、发展又处于现代中国这样一个急速变动着的时代。鉴于周作人的工作几乎跨越了现代中国数个决定性的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现代性爱思想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标本,对构成这一思想的资源进行解析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身处传统与现代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周作人现代性爱思想最初来自于西学。在中国传统中,儒家朴素的、带有生殖崇拜色彩的性思想经过宋明理学的淘洗已经变异成了以男女大防为代表的压抑人性的道德教条;道家的采补说把性交看作争夺“阴精”的两性战争;佛家则以宣扬性的不净观来根绝人们的性欲念。这三股力量糅合在一起,构成了明清以来日益严苛的禁欲主义观。作为这样一种禁欲主义道德观念的受害者,祖母不幸的经历曾给周作人留下了关于性的极其不快的记忆。另一方面,从1890年代开始,在“自强保种”的观念影响下,进化论几乎成为整个新思想界的圣经,大量的西学资源以“先进”的姿态涌入中国。在周作人价值观形成的时候,禁欲主义道德观念越来越被与积弱的民族种性联系起来,成为不满于现状的改革者所猛烈抨击的对象。这些因素导致周作人性爱思想主要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中寻找资源。1940年代周作人在《往昔》中承认了这一点:“往昔务杂学,吾爱性心理,中国有淫书,少时曾染指。有如图秘戏,都是云如此。莫怪不自然,纲维在男子。后读西儒书,一新目与耳。”②周作人最早接触这些“一新目与耳”的西儒大约在1898年前后。查周作人日记,1898年5月(农历四月初十)周作人试图购买《寰宇锁记》(《四溟琐记》)未果。之后于1900年2月(农历正月二十)购得《寰瀛画报》、《点石斋画报》,1901年购阅《海上文社日报》、《游戏报》、《觉民报》、《新闻报》、《谈瀛八种》、《菘隐漫录》等书报。进入江南水师学堂读书之后,周作人开始大量阅读西学书籍,尤以1902年为甚。粗略检视周作人的日记,我们发现他是年读了约有40余种西学及介绍西学的书报。从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周作人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生理学、心理学知识,如《心灵学》(今译《心理学》)、《卫生学答问》、《传种改良问答》等。在这些书籍中应该包含有性学知识。由于接受能力和视野所限,周作人此时对西学的接受大多通过维新运动鼓吹者的文章完成。严复、梁启超、谭嗣同都曾经对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周作人于1902年初(1902年2月2日)从鲁迅那里得到严复译述的《天演论》。这本著作在随后的几年中一直是周作人案头书,1902年到1903年间他读过多遍。梁启超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饮冰室自由书》也给予周作人巨大的影响。读后,他赞叹道:“美不胜收”。③谭嗣同的《仁学》更是直接、深刻地影响了周作人早期性爱思想的形成。谭嗣同在《仁学》中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他所谓的“通”包括“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④从这一理论基础出发,谭嗣同猛烈地抨击了三纲五常:“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⑤同时,他从性的自然主义出发,反对以禁、耻、讳为手段的禁欲主义道德规范,反对缠足,反对男女不平等,提出通过正当的性满足、坦然的性教育来消除淫(过当的性行为)。他的性教育观念恐怕也是中国最早的以现代解剖学、生理学为基础的:“若更得西医之精化学者,详考交媾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肖人形体,可拆卸谛辨,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⑥可以说,谭嗣同《仁学》中建立在“通”的基础上的性爱思想在中国现代性爱思想史上有开天辟地之功。从1902年3月得到《仁学》始到1903年4月,周作人日记里记载了他读该书共八次。在他早期的性爱思想里,《仁学》的性爱观如影随形,如《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1904)、《女娲传》(1905)中对女性解放宣扬;《防淫奇策》(1907)中对性欲望的正视以及“人人各遂其饮食男女之欲,则淫盗之恶息”的观点等,都可以看到《仁学》的影子。⑦ 在周作人性爱思想的形成期,影响其性爱思想的西方思想资源十分驳杂。这一点从周作人1902-1904年所阅读的书目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这些著作中有《卫生学问答》(1902年)、《心灵学》(1902年,今译《心理学》)、《传种改良问答》(1902)、《生理学粹》(1904年);也有《男女交际论》(1903年)、《世界十女杰》(1903)、《东欧女豪杰》(1903)、《自由结婚》(1904);还有《权利竞争论》(伊耶陵,1903)、《民约论》(卢梭,今译《社会契约论》,1903)等,涉及了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在《周作人日记》1912-1934年的购读书目中,他购阅的性书籍的数量和学科种类更加繁多,包括了诸如哲学、文学、性心理学、性生理学、性病理学、伦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几乎所有与性有关的学科。它们从不同层面构成了周作人性爱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一点,《知堂回想录》提供了佐证:“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这于甲辰乙巳最为显著。”⑧“杂乱”一词恰当地说明了周作人性爱思想形成的多源性。这种“杂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现代性爱思想本身就是由自由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性心理学、性生理学等诸多内涵构成的复杂的混合体。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来自于那个激烈变动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各种各样的思想资源蜂拥而入,都可能成为正在饥渴地寻找人生根基的青年周作人的人生观的价值要素。因此,周作人性爱思想的多源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现代性爱思想形成期的复杂情形。 当然,这种“杂乱”中也有其统一性。科学、自由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和当时绝大多数的思想者一致,周作人信仰“唯科学主义”。⑨因此,包括性心理学、性生理学、性病理学在内的性科学成为他现代性爱思想的基础之一。从他日记中记录的书目中可以看出,周作人搜罗了大量性科学的书籍。仅举其在教育界里做“桃偶”的1913年为例,他购读的性科学书籍有:Kesth:The Human Body,C.Howard:Sex Worship,Thomson and Gedder:Evolution of Sex,《妇人卫生》(作者未知),《教育与善种》(Gorst),《遗传研究》(作者未知)等数种。1913年,他还把戈斯德的《教育与善种》(发表时名为《民种改良之教育》)节译发表在他主持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提倡儿童的性教育。性科学知识被周作人视为人生的根本:“我相信人们去求全面美善的生活,首在自知一切,生物学的性知识于儿童实为必要”,⑩“我们的理想是人人都有适当的性知识,理解,对于性行为只视为一种自然要求的表现,没有什么神秘或污秽”。(11)在唯科学主义的时代风气影响下,性的科学知识不仅为周作人对性的重新认识提供了一套崭新的标准,还为周作人的性道德革命提供了理论的自信。不过,周作人也认识到性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他试图以人情、人性来淘洗性科学知识的抽象、冰冷:“大家似乎忘记了一件事,便是最通行的性交方式大抵也难以称为美的(Aesthetic)罢。他们不知道,在两性的关系上,那些科学的或是美学的冰冷的抽象的看法是全不适合的,假如没有调和以人情。”(12)在周作人的性爱思想中,科学之光、艺术之美与人情、人性之善是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的。 周作人性爱思想中的人情、人性之善最初也是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是周作人理解的人情、人性之善的核心之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是周作人思想的主要理论资源,学术界早有定论。同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周作人的性爱思想中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资源。周作人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接受与其现代性爱思想的形成几乎同步。在接受《仁学》中性爱思想的同时,上文中提及的《天演论》、《饮冰室自由书》等所传达出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周作人。1902年,他开始阅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译为《民约论》),虽然周作人此时并不一定完全读得懂《民约论》,但并不影响他接受自由主义的思想。(13)在这一年,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慕英国自由主义者克林威尔(今译克伦威尔),改号克郎。(14)在8月31日(农历七月廿八日)日记中,周作人指斥《劝学篇》(张之洞):“剽窃唾余,毫无所取,且其立意甚主专制,斥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生成奴隶根性。此书一出,独夫之心益骄固,可恨也!”(15)与此同时,他开始对他曾经引以自得的策论充满厌恶,常常塞责了事。他欣喜地认为,自己的这种变化为“今是昨非”,决心“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拼与八股尊神绝交”。(16)很显然,周作人此时已经摈弃了科举思想,初步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随后,在周作人的思想革命活动中,现代性爱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二者始终相伴出现。这种伴随现象并不是偶然,其原因之一在于现代性爱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性权利的争夺常常是个人自由与权力斗争的前沿。(17)周作人也有把性爱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的理论自觉。他对现代性爱思想的接受始终以自由主义为价值标准。周作人虽然购阅过大量的性科学书籍,但对他性爱思想形成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同时以自由主义者姿态在性道德、性伦理领域发言的西方思想家,例如日本的与谢野晶子(1878-1942)和英国的性心理学家亨利·海弗劳克·埃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 1859-1939)。在谈到周作人的性爱思想的时候,研究者多注意到埃利斯的影响,而对于与谢野晶子的影响常常并不太注意。实际上,与谢野晶子对周作人的性爱思想影响非常大。周作人从1918年3月开始购阅与谢野晶子的文章,十数年间几乎遍览可以读到的与谢野晶子的文章。(18)周作人以现代性爱思想为利器参与思想革命,首先借助的就是与谢野晶子。1918年周作人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原名《贞操ハ道德以上ニ尊贵デアル》。译文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随即引起了一场“贞操问题讨论”。这篇文章与周作人翻译动机的契合就源于自由主义。与谢野晶子在她文章中既反对偏于男性的贞操观念,也反对普遍性的贞操道德,主张一种道德的“新的自制律”:“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既然是趣味信仰洁癖,所以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我所以绝对的爱重我的贞操,便是同爱艺术的美,爱学问的真一样,当作一种道德以上的高尚优美的物事看待。”这种道德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之一。它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振聋发聩的。周作人在《贞操论》的译前记中把它视为“阳光和空气”来看待。他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性道德的多元主义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虽然,在译前记中他不无反讽地提到这样的“阳光和空气”可能并不适宜于中国这一被禁欲主义道德统治着的老大帝国,但他执意要介绍这“阳光和空气”进入中国的意图是为了使懂得它的中国人有享受它的机会。(19)在随后的“贞操问题讨论”中,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何体现在贞操观念中,是周作人、胡适、蓝志先等围绕贞操问题争论的一个焦点。周作人与胡适都秉承着自由主义理念,反对任何外在权威对于贞操的规定,鼓吹出于自由意志的贞操观。周作人甚至肯定那些出于自由意志的守节。(20)除了自由意志之外,这场讨论还涉及性道德的多元主义、男女平等、个人主义等自由主义原则。可以说,贞操问题讨论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次现代性爱思想与自由主义的交融。这次交融使得自由主义思想经由性爱问题在中国扎下了根。在此,我们不应该忘记与谢野晶子的贡献。 周作人至晚在1918年开始阅读亨利·海弗劳克·埃利斯(周作人当时译为蔼理斯)的《性的进化》(Evolution of Sex)、《新精神》(The New Spirit)等书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周作人几乎读过他所能得到的几乎所有的埃利斯的作品。(21)周作人一再谈到埃利斯对他思想的决定性影响。1934年,他在自述中提到:“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斯的著作。”(22)埃利斯被“后来的崇拜者视为‘性圣贤’,爱德华时代性革命的预言者。第一个对性‘持肯定态度的人’。换言之,他是当代性问题的态度的创始人”,是“20世纪性启蒙的开拓者之一”。(23)作为埃利斯的中国传人,周作人从埃利斯那里接受来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性的心理学。在性问题上,作为“达尔文时代的孩子”,埃利斯对于性、人的本质的理解基于人的生物构造,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和生物决定论者。周作人性爱思想体系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显然是受他的影响。周作人称埃利斯“实在是一个科学家,性的心理学之建设者”,坦承自己的性心理学知识来自埃利斯。(24)二是以性心理学为基础的价值观。周作人曾经赞美过埃利斯的人生观是“根据自然的科学的看法”,“参透了人情物理,知识变了智慧,成就一种明净的观照”(25)。周作人的价值观显然与埃利斯的相通,他多次提到性心理学是他价值观的最重要来源,甚至不无调侃地认为自己的悟道就是从“妖精打架”而来的。(26)第三,思想革命中强烈的批判性。作为性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埃利斯是一个道德的斗士,他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禁忌和性道德观。同样,周作人也是性革命的积极鼓吹者,这使他在五四那一代新文化先驱者中十分特异,也使其社会文化批判具有独特而犀利的判断特质。这一取向也主要来自埃利斯。他在《答张嵩年先生书》中提到了这一点。(27)另外,周作人曾提到埃利斯的道德使者的身份意识对他的影响:他的思想革命的目的就是以道德使者的身份做“性的心理研究的工作”,“从性心理养成一点好的精神”。(28)当然,作为一个身处激烈变动的时世中的思想家,周作人曾经自诩为叛徒与隐士,这也是从埃利斯那里得来的。(29) 关于埃利斯对周作人性爱思想的影响,许多研究者都曾经注意到。但是,研究者常常并不严格区分埃利斯与其他性学家对周作人性爱思想影响的不同。例如,赵京华认为:“周作人对两性道德的态度主要是接受十九世纪末西方现代性学家特别是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福洛赫、福勒耳、鲍耶尔、凡特威耳和弗洛伊德的观念。”(30)研究者的这一结论与周作人1936年的一段自述有直接联系,(31)但是在1944年带有其一生思想总结性的《性的心理》中谈到其性爱思想时,周作人特意把蔼理斯与上述性学家对其的影响区分开来,其理由就是埃利斯著作中有着由性学知识而来的人生智慧。(32)这种区分对于我们认识周作人的性爱思想是有意义的:同样是性学家,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埃利斯成为周作人性爱思想最重要的源泉,凸显出现代性爱思想的自由主义向度在周作人以及在中国现代思想革命中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反证,周作人对于现代性爱思想其他派别的态度很能说明他对性自由主义的基本态度。实际上,自由主义思想并不是周作人性爱思想的唯一西方源泉。就如同西方现代性爱思想本身的芜杂一样,周作人在接受西方现代性爱思想的时候也同样是芜杂的。社会主义的性爱思想也曾经给周作人以重要影响。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也热衷于探讨性的问题。与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更关注经济制度对性问题的影响。虽然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与女权主义思潮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英美的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是合流的,他们强调反抗阶级压迫与女性解放的关联。周作人对社会主义性爱思想接受的一个来源是英国的凯本德。1918年周作人介绍了凯本德的《爱的成年》(Edward Carpenter,Love's Coming-of-age)。他赞同凯本德把女性解放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他认为在这一点上,凯本德比惠特曼、勃来克等“更说得明白,又注重实际的一面”(33)。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直接影响到了周作人对妇女解放及大革命的理解。在一段时期内,周作人甚至对共产主义抱有极大的好感。他曾经说过:“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这一阶级即使不争斗过去,那一阶级早已争斗过来,这个情形随处都可以看出,不容我们有什么赞成或反对的余地。”(34)“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35)但是,周作人现代性爱思想中的社会主义色彩并不是其主要的方面。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相比较,周作人显然更倾向于后者。他与社会主义的相交主要是缘于其对两性问题中的女性地位,或曰男女平等的关注。在周作人看来,社会主义能够通过制度变革,改变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压迫,即如凯本德在《爱的成年》中所说:“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1950-1951年间,周作人在《亦报》上发表的关于两性问题的随笔几乎全是注目于新政权所带来男女平等。虽然,此时周作人的写作是一种以谋生为目的的“政治性的商业写作”,(36)但是,如此频繁地就两性问题发言,还是应该有宿根的吧?除了对于男女平等的关注,他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即使在周作人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蜜月期”,他受法国吕滂的《群众心理》影响,对群众运动抱有深深的忧虑。因此,周作人与社会主义者之间只是同路人的关系。(37)从这一点上看来,他与他的精神导师埃利斯仍然是共通的。埃利斯早期的世界观是“社会主义的和女权主义的”,不过,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更倾向于费边主义。周作人的情形也类似于此,弄清楚了周作人的性爱思想与社会主义性爱思想的相交点在哪里,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性爱思想的构成有相当大的意义。 周作人现代性爱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二者共同成为其思想革命的重要武器。现代性爱思想本身也可以算作自由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因此,实际上我们无法确切地指出,到底是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了周作人的现代性爱思想,还是现代性爱思想本身所具有的自由主义特质使得周作人具有了自由主义倾向。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理性、个人主义、权利、道德多元主义、平等等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构成了周作人现代性爱思想的核心内容,并成为其针对假道学进行思想革命的主要武器。关于此点,拙文曾有论及,不赘。(38) 综上所述,“西儒”给予周作人性爱思想以科学的依据、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批判性的道德取向,这些也构成了周作人早期思想活动的底色。 除了西方思想资源的影响之外,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周作人主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性爱思想的依据。 周作人参与思想革命之初,传统文化被认为是压抑个性的罪魁祸首而受到他猛烈地抨击,尤其是那些道学家,更是他毫不留情地抨击的对象,就如他自己所说:“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39)他之抨击道学家,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虚伪,脑子里有“淫逸不净的思想”(40),“不近人情”(41)。当时的中国,在周作人看来,“假道学的空气浓厚极了,官僚和老头子不必说,就是青年也这样”。他对自己工作的期许主要是“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道德的见地,提倡(性的)净观,反抗这假道学的教育”(42)。此时,他的主要思想武器是上述的西学资源。也许是批判策略的需要吧,在这一阶段,周作人很少借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来阐述其性爱思想。 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周作人一方面仍然不遗余力地批判现实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性迷信和性专制,另一方面,他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爱思想的依据。1924年他开始追慕千年前的中国文化“一时有臻于灵肉一致之象”,追求一种“禁欲与纵欲的调和”的“生活之艺术”。周作人认为,现在要做的就是复兴中国千年前的“礼”,“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即“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43)他承认“儒家的现世主义”是对的。他甚至设想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把性的迷信和假道学中的淫逸思想驱除干净,使中国人在传统的基础上获得新生。(44)不过,周作人此时对中国“本来的礼”的肯定,只是“空想中以为应当如此的礼”,并不是真正存在过的历史真实。周作人此时的文化态度显然还是受着思想革命的批判性取向的影响,其所谓的“中庸”仍然是“激进的”。(45)他此时还警惕着“老祖宗的遗产”——那些关于性迷信的“蛮性的遗留”——要求以“科学之光与艺术之空气”来“造成一种新的两性观念”(46);赞赏着废姓外骨与拉伯雷等人以“猥亵的趣味”所体现出的“对于礼教的反抗态度”(47);或者直接把中国的礼教思想看作“萨满教的”(48);甚至疾呼:“青年必须打破什么东方文明的观念”(49)。这种现实斗争与文化评判之矛盾显示出周作人此时价值观的转型。在这种转型中,他提倡现代性爱思想的目光开始日渐偏向中国传统文化。他曾经有过自我认识:他的文章中“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50)。这种淡薄到1930年代初期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转向”。(51) 周作人对俞正燮的接受、阐扬历程可以显示出这种转向的基本轮廓。王充、李贽、俞正燮这三位被正统视为异端的思想家在周作人看来,是“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他把他们的“疾虚妄”与“通达人情物理”,视为“我们的理想”。(52)这三位思想家中,最早见诸周作人日记的是俞正燮。1902年,周作人阅读了俞正燮的《癸巳类稿》。(53)《癸巳类稿》卷十三中的《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人恶德论》等文深为周作人所激赏。(54)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周作人并没有援引俞正燮来阐明自己的现代性爱思想。直到1933年,周作人才在《画蛇闲话》中称引俞正燮,称之为“嘉道时豪杰之士,其《癸巳存稿》《类稿》都值得阅读”(55)。其后,周作人多次引用其《癸巳类稿》中关于女性的观点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通物理、顺人情”的标志。(56) 周作人对俞正燮的接受、阐扬显示出其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的“人情物理”与西方现代性爱思想进行对接的努力。这种对接一方面试图给予传统文化新的符合现代思想的意义阐释,另一方面则极力以中国的传统哲学符码阐述现代思想。前者表现为尽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性爱思想相通之处并加以阐扬。在周作人看来“本来中国的思想在这方面(性心理——引者注)是健全的……为圣王之所用心,气象很足博大”,只不过,到了“后来文人堕落,渐益不成话”。(57)周作人试图重新回到元典意义上去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其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想的相通之处:“中国思想向来很注重人事……中国的伦理根本在于做人”(58),“我总觉得大公出于至私,或用讲学家的话,天理出于人欲”(59)。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思想包含着对于人的欲望(包括性欲望)的肯定,“礼”原本就是与合理地满足欲望联系在一起,它可以以“情理”或“通物理,顺人情”概括:“我觉得中国有顶好的事情,便是讲情理,其极坏的地方便是不讲情理。随处皆是物理人情,只要人去细心考察,能知者即可渐进为贤人,不知者终为愚人,恶人。《礼记》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都是千古不变的名言,因为合情理”。(60)周作人在1939年以后多次引用、称扬圣王的“嘉孺子而哀妇人”的思想,认为这就是“顺人情”的最好体现,也是他文化工作的旨归:“鄙人执笔为文已阅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著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61)在《汉文学的传统》中他引述了焦里堂(循)《易馀侖录》卷十二中的一段话:“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随后,他又引刘继庄著《广阳杂记》卷二中的一段话:“……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他认为“人生不过饮食男女”一说,“真是粹然儒者之言,意思至浅近,却亦以是就极深远,是我所谓常识,故亦即真理也”。通过对这一传统的重新阐释,周作人似乎找到了现代性爱思想的中国土壤。从这一逻辑出发,我们倒推周作人早年的民俗学、人类学研究,似乎也带有这种接通中西文化的意味。他从西方借来的民俗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武器,“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在1920年代前后,他主要是从批判假道学、“解消”“威严的压迫”、寻找“化中人位”的角度来寻找中国民间的思想革命要素(62)。 因之,他从原儒、异端、小传统中剔抉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物理,来作为接通中西方性爱思想的桥梁。通过这一桥梁,西学与中国传统有了交通的可能。他所谓的“通物理”就是试图为中国儒家文化接上现代性科学的血脉;而“顺人情”则是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伦理价值尺度与现代思想中的人性维度沟通起来。周作人认为,“中国儒家重伦理,此原是很好的事,然持之太过,以至小羊乌鸦皆明礼教,其意虽甚佳,事乃近诬,可谓自然之伦理化,今宜通物理,顺人情,本天地生物之心,推知人类生存之道,自更坚定足据,平实可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此时,周作人在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思想革命资源时显得更为通达。 另外,他也试图为早期所服膺的现代性爱思想换上中国的古衣冠。1934年,他在介绍埃利斯的《性的心理》时指出,该书中埃利斯“根据自然的科学的看法还是仍旧,但是参透了人情物理,知识变了智慧,成就一种明净的观照”。他的性爱思想在周作人看来“极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能算怎么激烈,据我看来还是很中庸的罢”。(63)1936年,他明确宣称埃利斯等人的性书使他“懂得了人情物理”。到了1940年代,周作人更加自觉地希望把西方的性心理学、性生理学与中国的伦理学嫁接起来。在《性的心理学》中,他一方面期望中国的士人能够“知哀妇人而为之代言”,一方面庆幸:“我辈生在现代的民国,得以自由接受性心理的新知识,好像是拿来一节新树枝接在原有的老干上去,希望能够使他强化,自然发达起来。”(64)基于这种逻辑,他早期性爱思想中“利己又利人”的取向被置换成中国儒家文化的“饥寒由己”思想。(65)这样,中西两种资源就有了融合的可能,现代性爱思想似乎正在获得了中国化的土壤。 周作人之所以从1930年代开始,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现代性爱思想的理据,原因有二:一是,其“文化本位的民族主义”使然;(66)二是,其“思想历程的自然归结”。关于周作人在附逆时期的民族主义表达,学术界已有阐发。木山英雄曾经把抗日战争中周作人提倡的“儒家人文主义”既看做是“其思想历程的自然归结”,也看做是“被迫作出的政治性拟态”。(67)董炳月从“国家”的国土、政权、文化三个不同层面的内涵出发,剔抉出周作人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否定爱国与主张民族主义——这二者的统一构成了周作人思想中一个具有稳定性的模式。”他认为,在附逆期间,“对于周作人来说,在政治组织的层面上与入侵者妥协未必意味着民族意识的彻底沦丧。”周作人通过提倡“儒家文化中心论”确立了“精神中国人”身份,表现出自觉的民族意识。(68)如果我们从其为现代性爱思想中国化所做的努力看来,周作人的文化本位的民族主义在1930年代就已经成形了。只不过,在1930年代,这种“文化本位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被时代所凸显出来而已。 不过,如果把它当作是周作人“思想历程的自然归结”来看的话,他这一沟通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在文化建设上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价开始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先有1935年1月王新定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的本位文化建设宣言》,要求重新估价中国的文化,后有以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基点的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在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就是以理性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沟通中西文化资源。张申府所提倡的“文化综合主义”是其中的代表:“在文化上,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综合的。……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辨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69)后来,他又把这种文化综合明确表述为:“仁、科学法(即实验与算数的结合)、数理逻辑(包括几何及其他算学以及逻辑解析法)、辩证唯物论,既是历来以至未来文化中最好的东西,而且也缺一不可,当就应合而一之,也可以说,应将其代表人,孔子、罗素、列宁合而一之。尤其没有孔子所代表的仁,不但文化将不成其文化,人也将不成人。”(70)周作人作为一个文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思潮。1936年冬周作人及其弟子也曾“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71)。联系到从1934年前后周作人开始有意识地以儒家学说解释现代性爱思想这一事件,那么周作人使现代性爱思想中国化的努力就与1930年代这股试图接通中国传统与西学资源的思潮接上了榫卯。 周作人中西文化融合的思想,早在1921年其提倡乡土文学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72)。这种思想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的分化则日趋鲜明。1928年北伐逐渐迫近北京,周作人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宣称:“我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这里的“中庸主义者”不是儒家正统意义上的中庸,而是指思想不定于一尊,混合各种思想资源的意思:“我不是这一教派那一学派的门徒,没有一家之言可守。”(73)此时周作人选择中庸主义多是对现实失望的一种应激反应,其目的还并不一定真是要冶中西文化于一炉。1930年代,他的中西文化融合的思想开始成为一种自觉的、理性的选择。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曾对这种选择做过如下评述:“周作人终于在30年代,形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杂糅中见调和’的思想统一体。他以蔼理斯调节‘纵欲’与‘禁欲’的思想,儒家的‘仁’、‘恕’、‘礼’、‘中庸’,希腊文化的‘中庸之德’为基础,糅合了道家的‘通达’,日本文化中的‘人情之美’,构成了新的思想体系。其主要特点是以‘得体地活着’为中心,在顺乎人情物理的自然发展与自我节制中求得平衡的中庸主义。”(74)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周作人的中西文化融合思想就已经成形了。这与1930年代中国思想界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机恰好重合。 到1940年代,北京沦于异族治下时,他试图冶中西文化于一炉,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重塑中国现代文化的民族主义意图就更明确地凸显出来了:“总而言之,中国现今还是革命尚未成功,思想界也依然还是旧秩序,那是当然的事。要打破这个混沌情形,靠外来思想的新势力是不行的,一则传统与现状各异,不能适合,二则喧宾夺主,反动必多,所以可能的方法还是自发的修正与整理。”(75)显然,周作人认识到,西方的思想资源如果不能够与中国的传统融合,就不会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这与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激进文化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他《生活之艺术》、《谈虎集·后记》中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我们不宜把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修正与整理”看作复古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因为,周作人的这一方案并不是着眼于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君师的正统思想”,而是试图回溯原儒、发掘异端或者从小传统那里去寻找现代思想的本土化根源。这首先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清理与判别。他认为,儒家思想本身存在着“饥寒由己,民以奉君这两样不同的观念”。这两种观念“亦即是儒者自居的地位不同,前后有主奴之别也”。他进而把这一发现推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中有为人民与君父的两派,后者后来独占势力,统制了国民的道德观念,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在周作人看来,“……先贤制礼定法全是为人,不但推己及人,还体贴人家的意思,故能通达人情物理,恕而且忠,此其所以为一贯之道欤。……恕是用主观,忠是用客观的,忠恕两举则人己皆尽,诚可称之曰圣,为儒家之理想矣。此种精神正是世界共通文化的基本分子”。周作人宣扬对传统进行“自发的修正与整理”的理论依据就是缘于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符合现代思想原则的要素。因此,在对待儒家传统的问题上,他主张区别对待,对于那些成为统治术的“民以奉君”的思想应该加以抨击,对于“饥寒由己”的思想则应加以发扬。他提出:“中国道德标准宜加改正,应以爱人亲民为主,知己之外有人,而己亦在人中,利他利己即是一事。”(76)实际上,这种对于传统文化利人利己观的阐扬与其早期启蒙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另一方面,周作人更重视的是古今、中西的融合。他在《杂文的路》(1944)中谈道:“假如我们现今的思想里有一点杨墨分子,加上老庄申韩的分子,贯串起来就是儒家人生观的基本,再加些佛教的大乘精神,这也是很好的,此外又有现代科学的知识,因了新教育而注入,本是当然的事,而且借他来搅拌一下,使全盘滋味调匀,更有很好的影响,讲人文科学的人如有兴趣来收入些希腊、亚刺伯、日本的成分,尤其有意思,此外别的自然也都很多。我自己是喜欢杂学的,所以这样的想,思想杂可以对治执一的病,杂里边却自有其统一,与思想的乱全是两回事。”(77)这种融合儒道法、古今、中西的文化态度是他数十年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深入思考。周作人曾自称“非正统的儒家”:“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自定,内容的解说恐怕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78)这些“不同的地方”,我想,主要是指其从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资源中寻找出来的,符合其思想革命的那些思想资源吧。而他自称为“儒家”还是自认为是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吧。(79)通过这种中西思想资源的“搅拌”,周作人曾经投身的思想革命有可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和适宜的土壤。虽然后来的历史发展并没有给周作人这种“搅拌”以真正实施的机遇,但他性爱思想资源的变迁也会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带来深刻的启示。 ①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程光炜编《周作人评说8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②《往昔》,《周作人自编文集·老虎桥杂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③《周作人日记(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④加润国选注:《中国启蒙思想文库仁学——谭嗣同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⑤《中国启蒙思想文库仁学——谭嗣同集》,第17页。 ⑥《中国启蒙思想文库仁学——谭嗣同集》,第25页。 ⑦《防淫奇策》,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⑧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67页。 ⑨郭颖颐认为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科学精神取代了儒学精神,科学被认为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哲学”。[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⑩《考试二(夏夜梦之七)》,《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13页。 (11)《答张嵩年先生书》,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750页。 (12)《〈性的心理〉》,《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164页。 (13)周作人于1903年4月3日得到《民约论》,1903年4月8日日记记载有阅读该书的情形:“夜看《民约论》,不尽解。……视之,且索解无从,何能领会?岂义之奥耶?抑予之钝顽不足以语此耶?是未可知。尽半卷即不阅。”见《周作人日记(上)》,第380—381页。 (14)《周作人日记(上)》,第349页。 (15)《周作人日记(上)》,第348页。 (16)《周作人日记(上)》,第361—362页。 (17)李银河:《性的问题·福柯与性》,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8)《女及ビ人トトシテ》(1918)、《爱理性及勇气》(1918)、《襍记账》(1918)、《歌ノ作リヤワ》(1918)、《我等何キ求ムルカ》(1918)、《若キ友人》(1918)、《心头襍草》(1919)、《激动ノ中チ行ク》(1919)、《晶子歌话》(1920)、《女人创造》(1920)、《爱の创作》(1923)、《新译源氏物语下卷》(1926)。 (19)与谢野晶子:《贞操论》,《新青年》第4卷第5号。 (20)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 (21)据《蔼理斯的时代》一文,至1935年周作人藏有26册埃利斯的著作。《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169页。 (22)《周作人自述》,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八十心情》,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23)[英]杰弗瑞·威克斯:《20世纪的性理论和性观念》,宋文伟、侯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67页 (24)《文艺与道德》,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本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25)《〈性的心理〉》,《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164页。 (26)《自己的文章》,《周作人文类编·本色》,第328页。 (27)《答张嵩年先生书》,《周作人集外文(上)》,第750页。 (28)《蔼理斯的思想》,《周作人文类·上下身》,第141—142页。 (29)《泽泻集·序》,《周作人自编文集·泽泻集、过去的生命》,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30)赵京华:《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 (31)《鬼怒川事件》:“……半生所读书中,性学书给我影响最大,蔼理斯,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佛耳台,希耳须弗耳特之流,皆我师也。”见《周作人文类·上下身》,第137页。 (32)“我学了英文,既不读莎士比亚,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是可以读蔼理斯的原著,这时候我才觉得,当时在南京那几年洋文讲堂的功课可以算是并不白费了。性的心理给予我们许多事实与理论,这在别的性学大家如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特戚耳特诸人的书里也可以得到,可是那从明净的观照出来的意见与论断,却不是别处所有,我所特别心服者就在于此。”见《周作人文类·上下身》,第2页。 (33)《爱的成年》,《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8页。 (34)《外行的按语》,《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第531—532页。 (35)《北沟沿通信》,《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101—102页。 (36)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37)周作人认为,吕滂的《群众心理》“把群众这偶像的面幕和衣服都揭去了”。他对当时的国民革命有这样的看法:“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妇女问题的解决”也“不能脱了群众运动的范围,所以我实在有点茫然了”。《北沟沿通信》,《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102页。 (38)徐仲佳:《思想革命的利器——论周作人的性爱思想》,《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5期。 (39)《与友人论性道德书》,《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55页。 (40)《关于假道学》,《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88页。 (41)《古南馀话》,《周作人文类编·千百年眼》,第262页。 (42)《净观》,《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49—50页。 (43)开明:《生活之艺术》,《语丝》第一期,1924年11月17日。 (44)《关于假道学》,《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87页。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还写道:“从假道学里抽去淫逸不净的思想,古衣冠便噗的一声掉在地上,只剩了赤裸裸的人,那就是真的活人;只可惜这个法术是几乎不可能地不容易罢了。我们的时代比较好一点,有机会得到些科学的知识,破除些道德上的迷信,自然不会再中毒了。” (45)周作人的这种复兴中国旧文明的提议(《生活之艺术》)受到了时人的质疑,江绍原在《礼的问题》(《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1日)中认为,周作人“太把礼理想化了”,周作人所说的“中国本来的礼”和其他古老的野蛮的礼一样都包含着“法术(Magic)的分子,宗教的分子,道德的分子,卫生的分子,还有艺术(狭义)的分子”,“只怕无论怎样古的礼,若不用我们的科学智识,道德标准,和艺术兴趣,好好的提炼一番改造一番,决不能合我们今人的用”。周作人在回信中也承认自己“所谓的‘本来的礼’,实在只是我空想中以为应当如此的礼。……我同你一样相信今日的生活法非由我们今人自己制定不能适用,不过这名目——‘生活之艺术’(The Art of Living)大意与‘礼’字相近,所以那样的说,这原是‘礼论’上的而非事实上的话。……我的意思只是对宋以来的道学家动了感情,想声明中国现在的生活法之不适当而已。我说‘中庸’也只是我理想中的‘中庸’,即大胆而微妙地混和禁欲与纵欲,从信奉了《了凡功过格》和《安士全书》的中国人看来,这乃是过激的思想”。 (46)《狗抓地毯》,《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33页。 (47)《净观》,《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49页。 (48)《萨满教的礼教思想》,《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59页。 (49)《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344页。 (50)《艺术与生活·自序》,《周作人文类编·本色》,第334页。 (51)《艺术与生活·自序二》(1930):“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客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近几年来却有了进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了。” (52)《非正统的儒家》,《周作人文类编·千百年眼》,第6页。 (53)《周作人日记(上)》,1902年(正月卅日),第317页。 (54)“……《类稿》的文章确实不十分容易读,却于学问无碍,至于好为妇人出脱……在我以为这正是他的一特色,没有别人及得的地方。”《关于俞理初》,《周作人文类编·千百年眼》,第175页。 (55)《画蛇闲话》,《周作人文类编·千百年眼》,第127页。 (56)《女人骂街》(1939)、《俞理初的诙谐》(1939)、《钱竹汀论轮回》(1939)、《读〈列女传〉》(1940)、《观世音与周姥》(1940)、《药味集·序》(1942)、《〈一蒉轩笔记〉序》(1943)、《俞理初论莠书》(1943)、《非正统的儒家》(1944)、《性的心理学》(1944)、《关于教子法》(1944)、《俞理初的著书》(1944)《焦里堂的笔记》(1945)、《道义之事功化》(1945)、《弓足》(1950)。 (57)《性的心理学》,《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1页。 (58)《汉文学的前途》,《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第825—826页。 (59)《凡人的信仰》,《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第312页。 (60)《情理》,《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第736页。 (61)《秉烛后谈·序》,《周作人文类编·本色》,第353页。 (62)《我的杂学》·七、八、九。 (63)《性的心理》,《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164—165页。 (64)《性的心理学》,《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第2—3页。 (65)在《道德漫谈》中,周作人认为,《庄子天道篇》中的引述的尧的“嘉孺子而哀妇人”一语“显得出儒家广大的精神,总是以利他为宗,与饥寒由己的思想一致”。《道德漫谈》,《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第787页。 (66)钱理群:《面对我们共同的困惑——在木山英雄著〈北京苦住庵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书城》2009年7月号。 (67)[日]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2页。木山英雄这样评价周作人在《汉文学的传统》(1940)、《中国的思想问题》(1942)、《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1943)、《汉文学的前途》(1943)四篇文章中的思想:“所选择的是重视人事而建立在人之生物性自然基础上的‘合理’、实际的‘儒家人文主义’,且将此追溯到政治道德上为后世君权主义所压抑、仅勉强保留在少数异端和民间中的‘一切为了天下人民’的‘禹稷精神’这一源头并将其理想化。”(第151页)……“在‘禹稷精神’之上,又配合有近代世界‘对于人本身的认识’或者‘人的发现’特别是‘儿童研究与妇女问题’的附论,但论述的方式则十分的古腔古调。”(第152页) (68)董炳月:《周作人的“国家”与“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69)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70)张申府:《论纪念孔诞》,《张申府文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2页。 (71)转引自袁一丹:《知堂表彰禹稷臆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 (72)《〈旧梦〉序》、《〈希腊岛小说集〉序》(1921)。 (73)《谈虎集·后记》,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 (74)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页。 (75)《论小说教育》,《周作人文类编·本色》,第537—538页。 (76)《道德漫谈》,《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第786—788页。 (77)《杂文的路》,《周作人文类编·本色》,第685—686页。 (78)《非正统的儒家》,《周作人文类编·千百年眼》,第6页。 (79)美国学者艾恺(Guy S.Alitto)曾经这样说过:“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艾恺教授序》,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3页)标签:周作人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爱思论文; 性爱论文; 现代性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俞正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