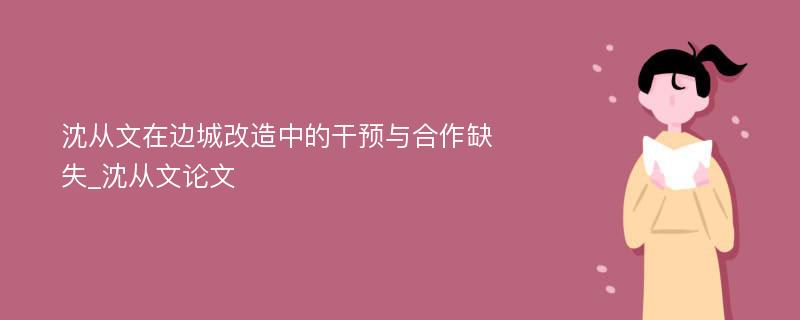
沈从文对《边城》改编的介入与不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城论文,不合作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文学中有不少名著被改编成电影搬上屏幕,在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同时,也扩大了名著自身的影响力。文学与电影在此实现了良性互动。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同样被改编成电影,并且是反复改编。
《边城》首次成功改编为电影的时间是1953年。这一年,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的导演严俊根据《边城》拍摄了电影《翠翠》,并邀请了当时的著名影后林黛出演女主角。影片在原作情节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动。譬如,片中侧重渲染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翠翠不再是小说中那个情感朦朦胧胧的含羞少女,摇身一变成了大胆追求爱情的成熟女子;为了凸显故事的诗意氛围,加入了较多插曲,如《热烘烘的太阳》《月下山歌》《不讲理的姑娘》《你真美》等。影片颇受当时观众的喜爱。作为原作者,沈从文却对该片极为失望,认为片中“尽管女主角是当时第一等名角,处理方法不对头,所以由我从照片看来,只觉得十分好笑。从扮相看,年纪大了些。主要错误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错了。”①
二十多年后,海外兴起的“沈从文热”波及国内,沈从文文学作品的价值逐渐被世人认可。在此情境下,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徐昌霖于“文革”结束不久,便抢先提出改编《边城》,但因改编意见未能与沈从文达成一致,导致后者无法认同电影剧本。因此,“文革”后《边城》的初次改编以失败告终。
198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凌子风再次提出将《边城》改编为同名电影,并尽可能忠于原作,他得到了沈从文的大力支持。沈从文本人还亲自审阅了电影剧本,并写下了不少建议②。不久,《边城》又被搬上屏幕,广受好评。
从以上对《边城》改编简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即沈从文对改编的频频“介入”——从最初对影片《翠翠》的臧否,到“文革”后拒与观点不合的改编者合作,再到亲自审阅《边城》剧本提出拍摄建议。出于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兴趣,本文不拟在小说与电影文本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具体改编实践进行细致的把握,而是侧重研究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对《边城》改编的上述“介入”。具体而言,涵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沈从文的改编心态,改编设想,以及与其文学观念的内在关联。
一、复杂的改编心态
沈从文向来喜欢写信。煌煌三十二卷作品全集中,有书信集九卷。沈从文“文革”后的不少书信中言及电影改编,这为我们探究他的改编心态提供了较为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在1979年10月回复好友徐盈的信中,沈从文首提《边城》改编一事:
……得信,并转徐昌霖先生一信,谢谢厚意。你听来的传说,恐不可信。事实或许正好相反,不免心中深怀杞忧也……
昌霖先生好意,拟为《边城》拍个电影,在上海方面看来,恐易出意外危险,也说不定。此事过些日子有机会见面时,再较详细来谈谈吧。从那边得来的消息,也可谓相当离奇,照朋友来信,不久前,我还居然被一个有权有势的什么长当作一个靶子,当着大几百文化人公开批评(附件看看即寄还)!……我所得于社会的,早已超过我应得的远甚。虚名过实,必易招致意外灾殃,不详之至。某某首长点名举例,正是一种必然反应。③
信中言及的徐昌霖,时为资深电影导演。他一直想改编《边城》。“文革”后,也是他最先向沈从文提出改编设想。④不过,沈从文“心中深怀杞忧”,因当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国内某些官员依然对他心存偏见。他不愿意此时过于招摇,认为“虚名过实,必易招致意外灾殃,不祥之至”。
两个多月后,沈从文致徐盈信中再次谈及《边城》改编:
转致徐昌霖先生信已见到。承昌霖先生厚意,拟把我四十五六年前早已过时旧作,试改成电影打算,好意可感。诚如你说的,如果能事先看看《湘西》中《常德的船》一章和《凤凰》一章,会得到些新的启发和理解。⑤
从信中可以得知,沈从文此时的担忧有所好转。他已经默许了徐昌霖的改编,并颇为热心地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然而,好景不长,《边城》后来被有关部门审查时认为只宜当作“历史作品”看待,不赞同改编成电影。在此境遇中,沈从文认为不拍或许是幸事,表现出了一种乐天达观的精神。他在1980年4月致徐盈的信中写道:
徐昌霖来信,事不出所料,电影稿有搁浅可能。这其实倒也省事。因据说只宜当作“历史作品”看待,定下的历史作品已过多,势将继续砍去一些。若作为新的,则内中人物似过旧。……《边城》若拍演不成,是意中事,非意外也。我早就觉得“虚名过实,易致奇灾异祸”,卅年“韬光隐遁,与世无争”还不成,老兄或当为指点迷途,如何一来,不至于让人以为我还算什么“作家”就好。《边城》即能拍,而不拍,也许对我正是幸运。⑥
除了当时不利的社会环境,沈从文更担心改编者误读原作,因为早有前科。前述的香港电影《翠翠》,虽有名角出演,但因导演根本未吃透小说文本,故影片与原作相去甚远。这一点招致了他的不满。
虽然,小说的电影改编本身意味着是以原作为基础的“再创作”,但如果加入过多莫须有的,乃至相悖的情节,影片将会同原作“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这无异于“买椟还珠”。“文革”后,《边城》的初次改编,“命运”可谓多舛——不仅要经受不利环境的考验,还因小说的“不合时宜”同样遭遇了“篡改”。前文已谈到,《边城》改编在最初审查时被拒。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提出要增加一些原文根本没有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情节。或许,在改编者看来,这是弥补原作“极端缺少思想性”缺陷的有力手段,但它完全背离了作家的创作本意。沈从文无法接受。在1981年10月致徐盈的信中,他写下如许文字:
……若电影剧本必须加些原作根本没有的矛盾才能通过,我私意认为不如放弃好。因为《边城》在国内外得到认可,正是当成个抒情诗画卷般处理,改成电影,希望在国外有观众,能接受,也需要把这个作品所反映的种种去忠实处理,一加上原书并没有的什么“阶级矛盾”和“斗争”,肯定是不会得到成功的。……我的作品照例是目前人习惯说的极端缺少思想性的,只能当成一种“历史”性作品看待……在生前看不到的重现于电影上,也认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其实这也极不现实,倒不如待我死后再拍好些。最好是不拍!⑦
以上所论,集中为“文革”后《边城》失败的初次改编。事实上,在1983年,《边城》再次改编时,尽管导演凌子风强调贴合原作,但沈从文依然担心会出现“误差”。这从他详细审阅电影剧本,并提出大量修改意见可以见出。
综上,沈从文对《边城》的电影改编,尤其是“文革”后的初次改编持复杂心态。一方面,他颇为热心,并提出拍摄建议。另一方面,他又“深怀杞忧”——其一,“文革”结束后,社会大环境对其不利,改编或导致灾殃;其二,改编者误读他的作品,甚至在影片中加入莫须有的离奇情节,最终与原作相去甚远。
二、系统的改编设想
尽管内心不乏隐忧,沈从文依然就如何改编进行了细致的思考。其中的核心理念便是“绝对尊重原作”⑧,强调“原文所有尽可能用上,原文如没有尽可能不用。”⑨基于这一核心理念,他对改编提出了系统的设想:
第一,关于电影的拍摄理念,他反对纯粹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并借用汪曾祺的意见,认为“或许应照伊文思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⑩简言之,便是一种贴合原著的“抒情诗画卷”式的处理方法。
第二,关于拍摄场景的选择,因小说写于半个世纪前,在此期间,湘西的地理、人文环境变化大,影片拍摄难以找寻适合的场景。为此,他提出了多个与原作相近的地点以供选择:
照最近新闻报道,王村下面的“凤滩”已改成发电廿五万千瓦大水电站,那里上面两岸最美的景物,大致已全部淹在水中了。……就我廿年前记忆,具有相同或更好看渡口背景的,还不少。同样山城却待找寻。一是沅陵附近马蹄驿村子,若值秋冬之际,四围山色红紫烂漫,简直是一种人间奇迹。即宋人最高画迹中亦不及万一。另一是距自治州仅廿三十里的“张八砦”,同样是一泓清水,四围远近山色红紫烂漫,最难得处,是一个渡口和小船,简直还保留千年不变。……若兼用故事中的划龙船景象,却必在旧五月初五到十五一段时间。酉水和辰河至今还保留竞渡习惯,以辰河为壮观。(11)
第三,关于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沈从文特别强调应忠实原作。他在1983年审校姚云、李隽改编的《边城》电影文学剧本(导演为凌子风)时,便指出“翠翠应是个尚未成年女孩,对恋爱只是感觉到,其实朦朦胧胧的,因此处理上盼处处注意到”(12)。并建议挑选主角时,“如编导心目中还无事先指定主角打算,或许到州上时,和州文化局各处商调十来个中学生(十五岁左右)或文工团员,就中挑选挑选,必不太费事,就可望得到较合理想角色”(13)。
第四,关于电影中的音乐编排,他认为应忠实原著中独具特色的湘西地方音乐和自然声响:
至于主题歌,我怕写不出,也不好写,甚至于不必写。依我主观设想,全部故事进展中,人实生活在极其静止寂寞情境中,但表现情感的动,似乎得用四种乐律加以反映:一为各种山鸟歌呼声;二为沅水流域放下水船时,弄船人摇橹,时而悠扬时而迫紧的号子声;三为酉水流域上行船,一组组纤夫拉船屈身前奔,气喘吁吁的短促号子声;四为上急流时,照例有二船夫,屈身在船板上用肩头顶着六尺长短篙,在船板上一步一步打“滴篙”爬行,使船慢慢上行的辛苦酸凄的喊号子声。内中不断有时隐时显,时轻时重的沅水流域麻阳佬放下水船摇橹号子快乐急促声音,和酉水流域上行船特别辛苦,船夫之一在舱板上打“滴篙”,充满辛苦的缓慢沉重号子声相间运用,形成的效果,比任何具体歌词还好听得多。此外则在平潭静寂的环境下,两山夹岸,三种不同劳动号子,相互交叠形成的音乐效果,如运用得法,将比任何高级音乐还更动人。(14)
沈从文深知在忠于小说的前提下改编《边城》难度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湘西巨变,场景选择颇为不易。此外,小说本身故事性不强,是当成抒情诗画卷来处理的。改编时,需突破一般重情节性的电影拍摄模式,难度可谓不小。但不管怎样,沈从文依然坚持应贴合原作,这是他的底线。
三、隐伏的文学观念
众所周知,电影改编小说的方式多种多样,或紧贴原作、或与原作保持一定距离、或完全背离,等等。可见,“绝对尊重原作”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然对于沈从文而言,这却是改编其小说的唯一选择——不仅指向《边城》,还涵括之后潇湘电影制片厂想改编的《贵生》《萧萧》和《丈夫》(15)。沈从文为何执拗于此?这一不乏偏执的改编理念背后是否隐伏着某种文学观念?(16)这些问题值得追问。
其实,沈从文强调贴近小说并非指改编者只能照搬原文。事实上,因文学、电影在艺术媒介上的本质差异,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他只是担忧电影工作者会因种种外在因素误读小说文本,以致改编时出现政治化、商业化的不良倾向,最终导致艺术创作上的失败。事实上,“文革”后《边城》的初次改编便出现了这般恶果。他对此提出了批评——如前所述,沈从文早在改编之初便对剧本中加入莫须有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十分不满。他曾在致友人信中特别强调小说中并无“军民矛盾”和“特权阶级”:
……作品(指《边城》,引者注)的时间性极重要,是在辛亥后袁世凯称帝前,大小军阀还未形成,地方比较安定的总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不会有什么(绝不宜加入什么)军民矛盾打闹噱头发生。即涉及所谓土娼和商人关系,也是比较古典的。商人也是平民,长年驿路上奔走,只是手边多有几个活用钱,此外和船夫通相差不多。决不会是什么吃得胖胖的都市大老板形象。掌码头的船总,在当地得人信仰敬重,身份职务一切居于调解地位,绝不是什么把头或特权阶级,这一点也值得注意。(17)
相对于改编的“政治化”,沈从文对“商业化”的批判更加不留情面。尽管他深知“电影和商品关系密切,必须考虑当时能否赚钱,所以不能不注意到目前观众兴趣,甚至于以‘吸引观众’成为中心目标。内容安排,也不能不到这问题上发生麻烦”(18)。但他丝毫不能容许改编《边城》时出现商业化倾向:
我绝对不同意把我作品来作上海流行什么补药一般商品处理,在剧本中故弄噱头逗笑,这样作为电影,若送到我家乡电影院放映,说不定当场就会为同乡青年起哄,把片子焚毁。(19)
为何沈从文会对改编中的政治化、商业化倾向如此反感?究其根源,正是他一贯坚持的文学观念使然。
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颇为特立独行的作家,他强调文学的本体地位,宣称“我为了把文学当成一种个人的抒写,不拘于主义,时代,与事物论理的东西……为图清静起见,我愿意别人莫把我巴列在什么系什么派或什么主义之下”(20)。“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21)基于这一独特的文学本位观,其创作一直游离于革命文学之外。在作品中,他极少刻意表现人物的阶级性,其好友胡也频曾劝他加入“左联”,但他认为“政治更多地需要目前;而文学,在注重目前外,似乎更值得向人类的远景凝眸。何况,人生的宽泛似乎不能全部被政治所涵盖。文学对于政治,既有其互相错综的一面,又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如果文学与政治完全结缘,文学的独立性就会遭到破坏”(22)。
沈从文同样反对文学的商业化。1933年10月,他在天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对作家“玩票白相”的写作态度提出批评。1934年1月,他又发表《论“海派”》一文,在肯定北京作家所具有的严肃创作态度的同时,对一些在上海赋闲的作家迎合文学的商业化提出批评,从而引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派”与“海派”之争。
沈从文反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的主张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中更是得到了系统的阐述。他说:“作品成为商品之一种,用同一意义分布,投资者当然即不免从生意经上着眼,趣味日益低下,影响再坏也不以为意……至于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治工具后,很明显的变动是:表面上作品能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事实上不过是政客从此可以畜养作家,来作打手,这种打手产生的文学作品,可作政治点缀物罢了。”(23)正是出于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的失望,他希望重建文学运动,“把文运从‘商场’与‘官场’中解放出来,再度与‘学术’‘教育’携手,一面可防止作品过度商业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家奴化,一面且防止学校中保守退化腐败现象的扩大。”同时还强调“一个作家在写作观念上,能得到应有的自由,作品中浸透着人生的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批判态度,方能可望将真正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24)。
通过以上爬梳,我们不难发现,在沈从文的电影改编理念背后隐伏的正是其文学观念。换言之,沈从文的电影改编理念与文学观念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即都强调艺术的本体地位,强调艺术不可沦落为政治和商业的附庸。
注释:
①⑤⑥⑦⑧⑩(11)(13)(14)(17)(18)(1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第3页,第78-80页,第288页,第433页,第149页,第3-4页,第372页,第150页,第149-150页,第149页,第457页。
②参见《沈从文全集》第八卷中沈从文对《边城》剧本的批注。
③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420页。
④徐昌霖曾就《边城》改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沈从文·〈边城〉·翠翠》。文中言及抗战胜利后,他就想将《边城》搬上屏幕,不过一直没有机会。“文革”后,其宗兄(疑为徐盈)向沈从文提及改编一事,后者默许,并推荐了几篇有助于改编的文章。参看《徐昌霖文集:一个电影工作者的手记》,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第88-91页。
⑨(1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第154页。
(15)参见1982年5月7日沈从文写给谢方一的书信(《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第403页)。沈从文在信中强调:“……至于设想把《贵生》、《萧萧》、《丈夫》合而为一试作一电影处理,怕不大会得到应有效果,因为三者性质少共同处。据这里熟人内行意见,其实还不如每一文试作一电影,或长或短,不必一致,尽可能忠于原作,或许效果比估计的还好。因为意大利就有这种成组故事电影,据看过的友好说,由于背景好,音乐好,成绩十分出色。若有可能这么作,我同意试试。”
(16)张新颖先生曾敏锐地指出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相通,参见《“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一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6期。其实沈从文的电影改编理念与其文学观念同样相通,都强调艺术的本体地位。
(2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三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146页。
(2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2)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23)(2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8页,第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