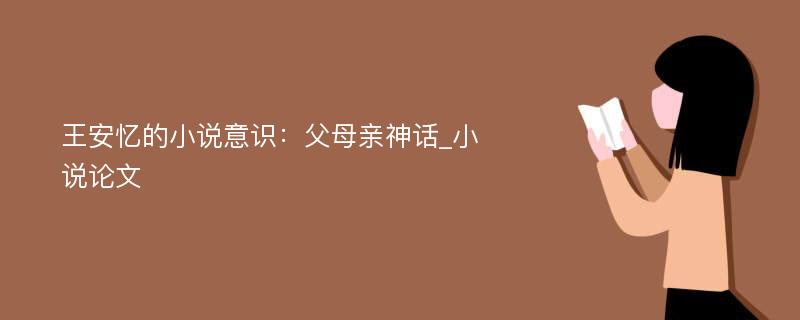
王安忆的小说意识——评《父系和母系的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父系论文,母系论文,意识论文,神话论文,王安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安忆是从写诗转向小说的,她起初的小说集《雨,沙沙沙》还明显地拖着诗的尾巴,因为这些小说是抒发性的,局限于个人经验和个人情感。《小鲍庄》是一个突变,一个飞跃,对此,王安忆说:“我想讲一个不是我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里看到的,它仅仅是发生了,发生在那里,也许谁都看见了,也许谁都没看见。”①像《大刘庄》、《小鲍庄》一样,她以后推出的小说几乎都是成组的,如“三恋”,如三部“三十岁”长篇,每一组都开拓出不同的艺术境界,探索着不同的小说意识,而从《叔叔的故事》起,她的视线又转向“自己的家族”,紧接着就是《伤心太平洋》写父系家族,《纪实和虚构》写母系家族。总的说来,尽管王安忆所写的题材多与自己的经历有关,如学生,知青,文工团,编辑,作家,家族等,实际上却不断地摆脱个人经验的羁绊,冲破个人情感的樊篱,执著地追求小说本身,即小说到底是什么?具体说,小说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情感的抒发,还是独立地创造出来的世界?如果是独立创造出来的世界,那么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尤其是它的动力是什么?是激情?是灵感?是想象力?是情节?是性格冲突?是逻辑推论?它们在小说创作中是兼而有之、不分主次,还是根据短篇、中篇、长篇的不同特点有主有次?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从她的小说阶段性发展脉胳中,分明地感受到衍进着的小说意识。
近作《父系和母系的神话》(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由一个中篇即《伤心太平洋》和一个长篇即《纪实和虚构》组成。这里凝结着王安忆探索小说意识的最新成果。仅从《纪实和虚构》的题目看,也很特别,它不像小说,倒像论文(其实,《叔叔的故事》所写的的确类似一篇新时期小说流变的形象化论文)。有人对这部长篇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它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对于正在离去的一个世纪的告别献礼,它标志着中国小说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次辉煌!而且,它事实上也为正在崛起的新潮长篇小说再次擂响了战鼓,从而预示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必将到来。”②可惜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未作具体的论述,不免包含着评论家个人的偏爱偏激,不足为训。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纪实和虚构》与《伤心太平洋》一起,再次显示了王安忆对现实人生体验之深刻,对新时代之魂把握之准确,特别是在小说意识的独创性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
1
倘若依据《叔叔的故事》来判定《父系和母系的神话》也是纯然虚构的小说,那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显然,《父系和母系的神话》的纪实性是极其触目极其明白无误的。“我”就是王安忆,父亲就是王×,曾祖父开创了我家的出洋史,同乡王木根说他还保留一本福建同安王氏家谱;母亲就是茹×,她是个浪子的女儿,“集孤儿与被抛弃于一身”,解放后以“同志”身份重返上海,等等,都说得有根有据,无庸置疑。那些寻根究底地追溯的家族历史,或有真名实姓,或有亲属称谓,或据之于史籍记载,或亲身实地寻访,也言之凿凿;至于虚拟的地方则直言不讳地表明“我想”、“我猜想”、“我设想”等字眼。所有这些,与自传体小说几乎毫无二致。然而,倘若真的把它当作自传体纪实小说,那又犯了常识性错误,实际上,它又是虚构的。纪实和虚构的对立统一,正是这本小说的特别之处,这问题留待下边详细讨论。在此,先从它的内容说起。
这本貌似描述逼真、背景确实、时空具体的小说,所表现的实质上并不是一个可视的行动世界,而是一个不可视的内心世界。在这里的所有实写,仅仅是露在表层的形态,而字里行间渗透着的情绪、观念、意识才是实质所在,简言之,就是孤独感和飘浮感。在《伤心太平洋》中,曾祖父从福建同安飘洋过海定居到新加坡,从此,一家几代人经历了动荡不停的年代,浮躁不安,变动不居,“我爷爷无休止地骂人”,叔叔是浪荡子,父亲和小叔叔投身革命,“他们必须做点什么,才可消除他们毫无二致的深入骨髓的飘浮之感”,而“革命者和浪荡子全是飘流的岛屿性格”。在《纪实和虚构》中,“我”是坐着痰盂进上海的,给人的感觉有点类似曾祖父坐着孤舟飘流到海岛上。“我家”是从外面飘流来的“外来户”,在上海没有根基,因而“我”从童年起就深深地陷于孤独之中。后来“我”竭力拓宽生活领域,但“这世界生气勃勃,我却参加不进去”,“我总是在追随这城市的潮流,这更说明我的无根无基,随风而去的本质”。直至处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编故事写小说,“热切地渴望建立新关系”,但也不过是“一座又一座纸做的房子,我自己似乎也成了纸人儿”了。至于母亲,她本来就是个无牵无挂的孤儿,到上海后仍保留孤儿的天性,“所有的人将她抛弃,她也将所有的人抛弃”;而母系家族,从茹姓找到远古的柔然族,逶迤起落,直到绍兴的“堕民”,始终飘忽不定,踏破铁鞋寻访,最后连祖坟也“无影无踪”。由此可见,这两个作品自始至终贯串着孤独的飘浮。倘若把它们看作自传和家族史,显然是经不起检验的,与客观实际并不存在同构关系、参照关系。
孤独和飘浮是互为因果的,而症结在于无根,正像浮云和浮萍,由于是无根的,所以才孤独,才飘浮。有人把《纪实和虚构》的主旨概括为“反抗孤独”,很有见地,只是把飘浮忽略了。其实,这种孤独,并不是加缪的《局外人》那种荒诞境况的孤独,也不是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那种无聊的孤独,或者残雪的《苍老的浮云》那种人性恶的孤独,而是无根飘浮的孤独。“我”之所以不遗余力去寻找家族的根,与其说是为了摆脱孤独,不如说是为了摆脱飘浮。耐人寻味的是,“我”苦苦寻找血缘的历史,发现家族祖先也同样经受着这种飘浮的命运(尽管他们有时曾显赫一时),最后仍然获得了一个飘浮感。实际上,王安忆的立意正在此,“我”在面对博大无边且汹涌澎湃的太平洋时,觉得“岛屿像一个孤儿,没爹没妈,没有家园。太平洋上的岛屿,全有一种飘浮的形态,它们好像海水的泡沫似的,随着波涛涌动”。而且,“从地图上看,大陆也是飘浮的岛屿。地球上的所有陆地,全是海洋中的礁石,供人类栖身。人类其实是一个飘流的群体,飘浮是永恒的命运。”这样,作品就超越了所有形而下的东西,凸现出形而上的意味。
寻家族的根,使我们想到“寻根文学”,其实两者是背道而行的。如果说“寻根文学”是试图为当下的生存方式寻出历史的证据,那末,《父系和母系的神话》则从探求历史的精神依托中缓解消解了当下的生存困境。因为这场貌似徒劳的寻根,其意义恰恰在于表明:人生、人类本来就是孤独的飘浮的,从而打开了现实和历史的存在的秘密。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因为那些小说抓住了存在的一种可能(人与他的世界的可能),并因此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够干什么。”③王安忆写的是“父系和母系的神话”,其中的现实和历史的具体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却是透过它们看到的那种人类存在的境遇,其中的孤独和飘浮,是每个人都可能碰到的感到的经受到的,而这种境遇一旦被揭示出来,一切都照亮了,似乎人与世界的关系顿时澄清了什么。这里,我们发现王安忆的一种小说意识,用她的话来说是:“经验性传说性故事和小说构成性故事是两个范畴。”④在这本小说集里,作者没有把个人的经验性和家族传说性的故事截取片段独立成章,走诗化、散文化的道路,所谓“走小道而取成”,而是抓住人类存在的疑问本质,进行漫长艰苦的探索,使小说构成性故事开合跌宕纵横捭阖,具有撞击心灵的力量。
2
当读着《父系和母系的神话》时,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在叙述方式上似乎可了然分明地划分出纪实部分和虚构部分,因为一方面有着“我”的现实生活的切身经历和感受,另一方面在叙述历史生活时又明确地标出是“我”的推论。其实这不过是作者的一种“策略”,在这里,纪实和虚构是难分难解的,貌似纪实的地方恰恰施展了虚构的天地,貌似虚构的地方恰恰运用了纪实的笔法。在这本书的《跋》中,王安忆明白地说过:“我以交叉的形式轮番叙述这两个虚构世界。我虚构了我的家族,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我还虚构了我的社会,将此视作我的横向关系”。可见,她说的是“两个虚构世界”,就是说整部小说都是虚构的。同时,她又说:“我在虚构时候往往有一种奇妙的逆反心理,越是抽象的虚构,我越是要求有具体的景观作基础。”这就是说并不因虚构而排斥纪实,而且越是抽象的虚构越要纪实。那末,她是怎样使纪实和虚构并存共处的呢?
严格地说,纪实和虚构是对立的两极,是水火不相容的。所谓纪实小说,虽然不无虚构的成分,但必须明显地偏重于“史实”并在文体风格上有着纪实性,而《父系和母系的神话》则是不偏不倚地将纪实和虚构交融起来,作为创造纵向和横向两个世界并使之“合围”的一种途径。在这里,纪实推动着虚构,虚构推动着纪实,纪实和虚构已不再是一种艺术技巧或文体色彩,而是一种创造小说世界的原动力,它们互相制动,谁也离不开谁。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景观,实者似实而虚,虚者似虚而实,读者苦心孤诣地去区分何者为实何者为虚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不可能。
比较而言,《伤心太平洋》重点是写纵向世界,纪实和虚构的界线不那么表面化,而《纪实和虚构》就不同了,很容易被误读。一篇评论文章中有这样两个小标题:“纪实:经验和往事对于世界的敞开”,“虚构:神话的寻找和家园的重建”。前者论述的是“我”的横向的社会关系,后者论述的是“我”的纵向的家族历史,这样是把纪实和虚构截然分割开来了,并把它们仅仅看作写作手法,显然有悖于王安忆的真正用意。这部小说交叉地写了现实生活(横向)和历史生活(纵向),但并不等于交叉地使用纪实和虚构的手法,而那篇评论文章是把貌实者当作实、貌虚者当作虚了。然而,这还不是症结所在。我们固然应知道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而且更在于理解纪实和虚构之间的逻辑关系。王安忆在谈到自己创作历程时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将生活与小说关系中的思想的部分与物质的部分视为一体”,但到着手写长篇时却碰到了困难,终于发现,“小说是有科学性的、机械性的、物质的部分。一些美丽的故事和完满的经验,足以走完一个短篇的行程,甚至勉力走到中篇的终点。然而,一部长篇,则要有故事与故事之间,经验与经验之间,逻辑的联络与推动。”⑤她又从亚洲华语大学生辩论会上得到启发,当时双方的辩论中有两种武器的较量,一种是思想内容的,另一种是形式逻辑的。“处于论题不利的一方,便更多地使用逻辑的力量,竟可使其反败为胜。这使我相信,逻辑是一种相对独立于思想内容的存在,那么,这是否也正是小说构成的那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呢?”这说明,王安忆在走完小说诗化道路以后,在创作中尤其在长篇创作中认真探求小说的物质性存在,其中就包括逻辑力量。而《纪实和虚构》(自然也包括《伤心太平洋》)正是把纪实和虚构之间的逻辑力量发挥到极致。
“我们在上海这个城市里,就像是个外来户。”这部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整部作品逻辑力量的起动点。“外来户”在上海是没有血缘之根的,社会关系也只是单一的式“同志”的,由此与日俱增着孤独感和飘浮感,并产生摆脱它们的要求和努力,纪实和虚构就从这矛盾中得到动力。这里的纪实和虚构是沿着两条路线进行的:(1)纪实——虚构——纪实。例如写保姆昔日的东家、邻居、同学、老师、知青、情人、查找史籍、寻访故地等,都充斥着具体的景观,但其中却包含着虚构的成分;又如写祖先的生存方式、战争、英雄、堕民等,都尽情发挥着虚构,但其中却包含着具体的景观。这就是说,从纪实引发虚构,也从虚构引发纪实,而且经常是相互引发,连锁反应,很难在某个地方把它们一刀切开。(2)整体的纪实负载着整体的虚构,整体的虚构带领着整体的纪实。从小说呈现的画面看,全是纪实性的,即使表明“我想”“我猜想”“我设想”之类其实也是纪实风格,然而它却负载着一个虚构的世界,这个虚构世界与现实和历史不存在着对应关系,是不依附于客观的自在自为的存在。而且,正是这个虚构的世界指引着纪实的方向和路线,使散漫的兴之所至的纪实凝聚一体。以上两点,实际上是充分调动了纪实和虚构之间的逻辑合力和张力。
把虚构和纪实统一起来的写法,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是别树一帜的,这种小说意识的产生,其实也是有生活根据的。王安忆曾写过一篇《城市无故事》的论文,说:“在乡村里,人们一代一代相传着祖先的事迹,那事迹总是有关于迁徙和定居,人们又一代一代演绎着传宗与发家的历史。”而在城市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也从不知道,别人从哪里来。人们互相都不知根底,只知道某些人的某些阶段与某些方面。他们在某一处作工,又在另一处住宿;他们和某一些人谈工作的事,又和另一些人谈情爱的事。”⑥既然城市既无现实的故事又无历史的故事,有的只是现实的片段生活和历史的断简残篇,那末只得依赖纪实和虚构的相互推动相互补充了。而一旦把故事写出来,“无故事”的城市就与“有故事”的农村一致了。因而,《父系和母系的神话》所写的故事,既概括了城市,也概括了农村。王安忆在这本书的封底上有个题词:“倘若难以知道我们向哪里去,也当知道我们从哪里来!”面对支离破碎的互不知根底的大上海,要表现“我们从哪里来”,除了纪实和虚构,几乎是别无选择的。
3
杜夫海纳说:“存在就是被叙述”。就是说,小说的叙述话语创造了一种存在,创造出了一种世界。《父系和母系的神话》作为一种存在,是用纪实和虚构的叙述话语创造出来的。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本小说创造了怎样的世界,它与现实和历史是怎样的关系,作者是用怎样的小说意识来指导自己创作的等。
不妨承接纪实和虚构的话题说起。王安忆在小说中写道:“这个坐在痰盂上进入上海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具体的事物,善于推论,没有想象力。”所谓“喜欢具体的事物”,就是具备了纪实的基础;所谓“善于推论,没有想象力”,就是虚构的方法靠的是推论,而不是想象。想象可以无风三尺浪,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到哪里是哪里,而推论必须始终扎在“具体的事物”的根上,根越多越深,推论也越有力越放得开,“像是风筝的线拉得越牢,风筝就飞得越高”,其中有一种反作用力。同时,推论又必须落实在“具体事物”上,从而又引发出新的推论,于是就构造出一幅幅丰富复杂五光十色的图景。在社会层面上,有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同志关系,同伴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情人关系,以及路人关系等等;在历史层次上,有上古的牧民,奴隶、奴隶主、汗(国王)、英雄、俘虏、叛徒、堕民、状元,以及农民、商人、浪子、革命者,等等。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每个人的命运千变万化,其中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无奇不有,这里有眼花缭乱的色彩,有令人迷惑令人陶醉的境界,也有人生真谛的思考,有豁达自信的精神指向,其情调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所说的孤独和飘浮只是就主要方面而言的,其实还有壮烈、荣耀、悲怆、屈辱、执著等等。这是个五彩缤纷的“神话”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横向的社会和纵向的历史之间还起着联系、映衬、背反等作用。现实的生活是那么偏狭、单调、小心眼、缺乏生气和光彩,好不容易迸发出真情、情欲、希望,也往往好景不长,但“我”毕竟一步步扎实地走向成熟;而家族的历史却是那么广阔、灿烂、大开大合,充满着生命力和创造力,但家族神话毕竟是变异了堕落了溃散了,并与现实的处境“合二为一”了。尽管辉煌的家族神话最终被拆散了,然而,“家族神话是一种壮丽的遗产,是一个家庭的文化与精神的财富,记录了家族的起源。起源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我们至少看见一端的光亮,而不至于陷入彻底的迷惑。”不是吗?我找到了推论出了家族的神话,就有了可以站稳脚跟的安身的“故乡”——“精神家园”;“我”甚至想,“我所以干上写东西这一行,是不是承继了祖是茹棻的某些遗传”,“我的遗传其实带有热带的痕迹”。有人说,回忆过去是一个人“老化”的表现;但“老化”也有成熟的含意。“我”回头探寻家族的神话,正与“我”走向成熟“合围”了。
王安忆说:“我甚至以推理和考古的方式去进行虚构,悬念迭起,连自己都被吸引住了。”这是指母系家族历史的创造,从发生在两千年前的拓跋部战争起,木骨闾做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奴隶主,社会创建了游牧国家,成了“我们柔然最后一名英雄,也是我们柔然最伟大的英雄”,到后来突厥崛起,柔然被灭族灭宗,柔然的另一部分则充当蒙古人的“堕民”南移至浙东绍兴。这段以推理和考古的方式虚构出来的漫长历史,确是奇妙无比,正如一篇评论文章所概述的:这里有辽阔的草原和沙漠风光,也有金戈铁马的战争;有忍辱负重的逃亡,也有血腥的残凶和背叛;有攻城掠地的豪迈,也有亡国灭种的悲哀;有生命降生的愉悦,也有死亡来临的恐惧;甚至还有苍色狼和白色鹿的美丽传说和动人景观……显然,这部家族史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对此,一位评论家引出了一个理论命题:“在我看来,王安忆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的目的,不过是想,显示一点,即‘小说可以创造历史’,或者反过来说,‘历史可以用小说的方法来创造’。”这里说的历史当然不是像《妻妾成群》之类的只有往昔生活和情景的历史,而是指有着真实的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然而这样一来,矛盾就来了。既然是有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作根据,就不能说是用小说的方法创造出来的;而既然是用小说的方法创造出来的,那就根本否定了真实的历史。事实上,《纪实和虚构》中的人物和事件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王安忆说得很清楚:“我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翻看二十五史,从中寻找蛛丝马迹。”问题的要害在于:不是历史可以用小说来创造,而是历史可以用逻辑推论来创造。不仅如此,现实也可以用逻辑推论来创造,这才是王安忆所说的“两个虚构世界”的奥妙所在。因为无论是历史部分还是现实部分,都有实有虚,都是纪实和虚构交织交融的,只是历史部分用了较多的“我设想”,而“我设想”之类不过是逻辑推论的明显标记而已。
王安忆曾为这部小说的取名颇费斟酌,其中曾想用“创造世界”,“最后我决定,干脆将我创造这纸上世界的方法,也就是所谓‘创世’的方法公诸于众,那就是‘纪实和虚构”——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我们已经说过,推动纪实和虚构互相动作的力量就是逻辑推理、逻辑推论。这,实际上是王安忆在自己的理论著作《故事和讲故事》中反复申明的一个观点,也是指导她创作《父系和母系的神话》的实践的小说观念小说意识,当然,这仅仅是“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
1995年3月4日杭州鼓楼
注释:
①《故事和讲故事》,第233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②吴义勤:《反抗孤独:由敞开到重建——王安忆〈纪实和虚构〉解读》,《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
③《小说的艺术》,第42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④《故事与讲故事》,第14页。
⑤《故事和讲故事》,第8、20页。
⑥《故事和讲故事》,第170-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