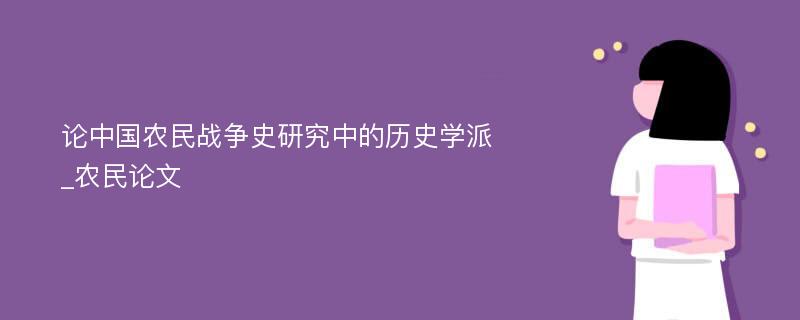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战争论文,历史主义论文,学派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以来,史学界在大部分时间内存在着若干种倾向不同、与一定的社会政治思潮息息相关的史学思潮,而有思潮一般说来就有学派;同时,由于每个研究者所使用的理论架构不同,对史料、史实的诠释不同,自然而然地也会使一批史学家对某些问题持有共同见解,从而形成学派。当然,衡量一批史学家是否构成为一个学派,主要是看他们是否有一种共同遵奉的史学主张,是否有一套体现这种主张的论点系统。由此看来,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的主张者确实构成了一个学派。
在承认和肯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的同时,随时批判和清算农民意识,以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历史理论划清界限,是这一学派几十年来的突出特点。但由于我们的社会现实长期受制于民粹主义的影响,所以这一学派一直遭受压抑和打击。现在已经到了给这一学派以应有地位的时候了。
一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始于抗战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关于农民战争性质和地位的判定成为这种研究的经典理论。一段时间内,史学界内部对这种判定的认识和诠释并无分歧。但1955年后,分歧、尤其是深刻的分歧产生了,另外的认识和诠释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产生。
封建社会里的农民不能建立非封建性的“农民政权”,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首先是在论证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1955年8月,孙祚民的《关于“农民政权”问题》一文的发表,是这一学派开始出现的标志。
关于“农民政权”的性质问题,早在1950年吕振羽就提出来了。①但最早判定农民政权依然是封建政权的,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学科的开拓者之一赵俪生。②继他之后,稽文甫和漆侠也都承认和强调了这一点。③正是在他们已有认识的基础上,孙祚民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农民政权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农民起义和战争,可以成功地推翻旧的封建王朝,“但他们是不可能组织‘农民政权’的。”“假如农民起义能够得到胜利,在顺利的条件下,他们自己便会、也不能不泰然自若地做起封建皇帝来。朱元璋的一生事业,正是体现了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典型范例。”而且,“他从一个农民领袖变成封建皇帝,乃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朱元璋在统一后所建立起来的,依然只能是封建专制的统治。”这一点容易为、而且也早已为人们所普遍认可。但张鲁、黄巢、李自成所建立的、与封建专制政权相对抗的短期性政权是什么性质的呢?是为农民自己谋利益的政权吗?这是农民政权问题讨论中的关键问题。孙祚民对此是坚决否定的。他说:“‘新政权’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专制的。它与‘旧政权’之间,只是存在着差别,而没有实质的不同。”因为“封建社会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领袖在起义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短期性政权,显然都没有、也不可能变广大农民为统治阶级,即没有、也不可能使广大农民在经济、政治上获得解放。因此,把这些短期性政权称之为‘农民政权’,也是不恰当的。”
为了论证封建社会的农民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孙祚民还触及了农民的阶级属性和他们所进行的起义和战争的性质问题。他说,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农民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下”,自然不会满意于封建统治与封建剥削,但他们“也不会看出这种生产关系有什么不正常之处。因而,农民起义曾经顽强地向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进行了战斗,可是他们没有同封建制度进行战斗。”“所有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和战争的矛头,自始至终总是指向某些为他们所深恶痛绝的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他们以为,暴君酷吏、恶霸地主,是农民的敌人;而剥削较轻和一定程度同情农民的‘明君’‘好官’,对于他们是并无损害的。”因此,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封建专制的最高与集中代表者——皇帝的身上。④
可以说,孙祚民的文章把历史主义学派后来所坚持所捍卫的基本观点、基本主张都提出来了。因此,我们把它的发表看作历史主义学派开始出现的标志。
如果说孙祚民的文章是历史主义学派开始出现的标志,那么,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在1961年8月的发表,则是历史主义学派正式形成和基本成熟的表现。
蔡美彪的这篇文章是全面阐述历史主义学派基本观点的力作。论文发表前后,正值关于农民战争史讨论的高潮期间。孙祚民的前述主张也正受到人们火力密集的批评,历史主义学派在遭受了第一次政治批判的厄运之后这时尚未站稳足跟。蔡美彪这篇文章的问世,是对流行阶级观点派的第一次有力反击,壮大了这一学派的声势,为这一学派赢得了更多的成员。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六节的篇幅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囊括了当时讨论中的几乎所有问题。“一、两种性质的革命。”作者指出:农民战争可以说得上是革命,“但它是不同社会革命的另一种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它不是革封建的命,而是在封建范围内革命。这是作者为农民的所谓“革命”降格。“二、农民战争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作者在这一节里继续为农民的所谓革命降格。作者说:“起义农民反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与压迫,却不曾自觉到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反抗,作为一整个的地主阶级来反抗。”或者说,“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指责归之于个别官吏、个别皇帝以至个别的王朝,却不曾指向那个制度那个阶级。”许多人都曾以“均贫富、等贵贱”来论证中国农民的觉悟和斗争水平如何高、甚至据此认为起义农民能自觉地反对封建制度。蔡美彪在第三节“关于‘均贫富、等贵贱’口号”中指出:绝不能把这些口号解释成当时的农民就已经“打土豪分田产”、“农民起义打倒地主”,“因为史料并不曾表明农民分了田产。”在“关于‘皇权主义’‘农民专政’”的第四节中,作者说:“起义农民领袖建立的那些所谓短期的政权,是不能看作‘农民阶级政权’、‘农民专政’的。”在“起义者所控制着的仅仅是‘一定地区’小范围内,”从来都没有实现过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专政。地主阶级依然是剥削阶级,农民阶级依然是被剥削阶级。这也就是说,这里的社会经济关系依然是封建的经济关系。”既然“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一定的地区里,经济基础……是封建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的。这样的政权又怎么能说不是封建政权,而是‘农民阶级政权’呢。”何况农民本来就是个皇权主义者阶级。在第五节“为什么中国农民战争总是反对王朝和官府”和第六节“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的一个特点”两节中,作者说明了中国农民战争和俄国农民战争不同的特点,但在信奉皇权主义方面却又是相同的,一致的。⑤
围绕着蔡美彪的文章,当时的史学界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历史主义学派就是在这场论战中走到一起来的。蔡文在许多方面发挥和展开了孙祚民所提出的论点,在这场论战中,孙祚民又就当时论战的各种热点——皇权主义、农民政权、农民战争的自发与自觉、如何运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一方面为自己辩诬,一方面又旗帜鲜明地向“阶级观点派”挑战,特别是他指名道姓地迎击了关锋与林聿时,使得他们的霸气有所收敛。这时属于历史主义学派的还有吴晗、⑥沙健孙、⑦周良霄、⑧吉敦喻、⑨吴天颖⑩诸位。他们或者挺身而出支持孙祚民、蔡美彪的论点而反击对立的观点,或者又进一步地提出了一些别有新意的见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翦伯赞在这时成为历史主义学派的旗帜。
翦伯赞《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蔡美彪的文章是差不多同时问世的。在这篇文章的第一节“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和在其他场合的讲演中,翦伯赞以最集中、最精炼、最准确的语言,概括了历史主义学派的基本主张:起义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反对封建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反对封建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11)在谈到农民政权问题时,他说农民能够并且曾经建立过政权,但他们不可能建立一种非封建性的政权,因为:“在同样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建立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权。农民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不能是其他的什么性质的政权。有人说农民的政权与地主的政权有区别,他是小农的政权,但小农的政权仍然是封建的政权。”(12)另外,关于农民是不是皇权主义者,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实质等,翦伯赞也都发表了有代表性的意见。
我们说翦伯赞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不仅仅是因为他提出了上述纲领性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他给这一史学流派提供理论根据和思想武器——历史主义。我们之所以把当时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被视为异端的人纳入历史主义学派,是因为他们都高举历史主义旗帜,都主张把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严格放入封建社会中去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的观点体系。
以翦伯赞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对农民战争史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看法,对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本质特性的认识,现在看来,不但经得起史实的检验,也经受住了现实政治实践的考验。但是,在农民意识愈来愈占支配地位的岁月里,历史主义学派的基本主张也愈来愈为现实所不容。最后,这一学派受到致命打击,其成员都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翦伯赞则为这些论点而付出了最为沉重的代价。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这一学派的基本主张也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13)其认识也被大大向前推进了,关于农民战争和农民的新认识这时集中反映在董楚平的观点中。
董楚平在1980年《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中指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任务就是推翻腐朽的旧王朝,建立开明的新王朝。打垮旧王朝与建立新王朝是一个任务的两个方面。后者不是对前者的“反动”,而是它的发展,是另一种质态上的发展。
翦伯赞、孙祚民、蔡美彪的论点由于受到当时极左的政治气氛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彻底的弱点,如他们也一般地认为农民“反封建”等等,这常常使他们的论点陷于矛盾状态。董楚平在这个问题上则克服了他们的不彻底性,提出了有名的“修理工”思想。他说,不论从总体上看,还是从全过程来看,农民战争都未曾反对过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相反,它是封建制度的“修理工”。因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根本不存在下降阶段,千百次农民起义都是由于封建制度的正常机能未能发挥而爆发。就是说,封建机器还未使用到极限,只是由于发生某些故障而无法运转,或由于时代水平的提高使它的某些部件需要换新。农民战争的任务不是把这部机器拿去报废,而是加以修理或改装。不管起义农民当时是如何想法,客观规律性的作用使农民战争只能起封建制度修理工的作用。在封建制度还未报废的时候,做它的修理工并不是屈辱的角色。只要修理得好,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14)
就象50年代孙祚民的论点、60年代翦伯赞、蔡美彪的论点曾经激起过人们的义愤一样,董楚平的“修理工”的论点,在80年代也同样使一些人感到怒不可遏。由此而引发了一场以平均主义功过为焦点的大论战。
有一面公开打出的历史主义旗帜,有一批学者明确表示在这面旗帜下从事研究,有一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品体现了历史主义精神,所以,我们说,以翦伯赞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构成了一个阵容整齐的学派——历史主义学派。
二
农民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且互相敌对。”(15)所以他们构成为一个阶级是不成问题的。但关键和要害在于,在这种“既定经济条件”下他们能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阶级。历史主义学派的最大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们还在60年代前期就提出了关于这个阶级的本质属性的见解。
农民阶级的社会属性问题,曾经极大地困扰过中国史学界。历史主义学派可以说早就摆脱了这种困扰。他们首先在农民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阶级这一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正是这个一致的前提导出了一系列趋同性论点。
他们认为:
(1)从农民阶级日常意识来说,他们和封建剥削阶级的成员一样,也具有强烈的“向上爬”的思想。孙祚民说:“农民的生根于其小私有经济的私有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本身,又在不断分化着。这样,农民头脑中必然滋生着一种强烈的向上爬的思想。平常,农民们在贫苦的煎熬中希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变成富人、地主、官吏,爬进剥削阶级的圈子里去;当他们参加并领导了农民起义,而且在对封建专制政权战争取得胜利、有了向上爬得更高的机会和可能时,逐渐变更其阶级立场,进一步要爬上皇帝宝座、做起封建皇帝来,也便是很自然的事了。”(16)蔡美彪说:“在平时,农民群众的现实愿望,就是地主阶级减轻些剥削和压迫,让他们还可以活下去,活得稍好些。而他们所追求和向往的则是发财致富,使自己也成为地主,或者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取得功名利禄,‘耀祖光宗’。”(17)
(2)农民不但在平时没有什么“革命”思想和“革命”积极性,就是在他们起来造反时,也不具备为人们所一再渲染的那种“反封建”的觉悟性、革命性。蔡美彪说:“在农民战争胜利发展的年代里,起义农民领袖所追求和向往的,就是推翻腐朽的旧王朝,推翻地主贵族的黑暗统治势力,而由自己去充当‘好皇帝’,建立‘好王朝’,实行‘好政治’。”“而起义群众也完全拥护领袖们的这些称号、这些目标。因为他们所要争取的本来就是一些较好的官吏、较好的皇帝、较好的王朝。一旦改了朝换了代,起义者即以为达到了目的,不再前进一步,也不能再前进一步。”总之,“起义农民争求建立新王朝,起义领袖则争求成为新皇帝,‘打天下,坐江山。’”这就是历史上“农民革命”高潮中的农民的思想状态。(18)
(3)农民起来造反,并不意味着“革命”,因为其指导思想仍然是封建的东西。蔡美彪说:“起义农民的领袖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的指南,不能不以封建王朝的体制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蓝本,因为当时还只有这样一个蓝本。”“封建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经验,”常常“构成了领导起义行动的理论基础。”“封建的思想理论影响着并且往往是在事实上指导着、支配着起义农民的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总之,“秦朝以来的历次农民起义……只是以封建的纲纪、封建的理论来反抗封建统治。”(19)
从上面几点,人们能引伸出什么结论来呢?(1)“农民本身是个封建阶级。”(20)马克思认为,农民是“旧社会的堡垒。”(21)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农民进行了极其精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正是以这些作指导,历史主义学派重新认识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在他们看来,千百次农民起义,并不具有人们所说的那种革命意义,而不过是“用封建的纲纪、封建的理论来反抗封建的统治,”目的和结果只是“建立新王朝”,“成为新皇帝”,“打天下,坐江山。”而这些,不过都是些封建的东西,何革命之有?!这样,那些用来证明农民是“革命阶级”的起义和战争,到头来都不过证明了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农民本身是个封建阶级,”翦伯赞的这一论断是能为全部史实本身所验证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性认识。
(2)农民的起义和战争不具有也不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历史主义学派在这一点上曾受到激烈而尖锐的批评。但这实在有点冤枉。因为历史主义学派在主观上仍然一般地承认农民“反封建”。他们说,农民只是自发地反,从未自觉地反。如翦伯赞的农民“三反三不反”就是。现在看来,说农民“自发地反封建”也是不能成立的。人类在认识规定历史发展的“规律”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自发的,不管哪个阶级都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此,在根本没有任何自觉性可言的情况下谈自发不自发,是毫无意义的。但是,由于中国还有一种自觉的农民战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了和这种革命相区别,说旧式农民战争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又是可以理解的。但可以理解的,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事实上,农民不是自发地反封建,而是自发地倾向封建。在没有一个封建主的一群小农中间仍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封建的社会关系来,会再生产出封建的社会制度来。
需要说明的是,说农民起义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并不意味着农民起义不起作用,只是说它在封建范围内起作用。一种历史运动所起作用的大小和这种历史运动本身的性质是两个问题。以往一些人之所以不自觉地把旧式农民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化,从认识根源上看,关键在于没有把这两者区别开。在他们看来,不把农民起义说成是反封建的,就好象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没有意义。这也难怪,因为在他们看来,“封建制度的总的历史,不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是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22)于是,为了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起义、农民的战争和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就非把农民起义拔到反封建的高度不可。这明显是误解。实际上,如同我们早就指出的,农民起义和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的“变法”、“革新”、“更始”具有同样的性质。他们都是封建机器的“修理工”,他们只能充当这样的“修理工”。在人类还需要封建主的时代,反对封建才是阻碍历史的进步,而充当封建机器的“修理工”,改造和换新封建机器的某些部件,促进封建制度自身的发展,恰恰是对历史进步的推动。
“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这个论点的提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它告诉人们,由这个阶级的成员领导和参加的革命本身不能不包含着许多消极的东西,特别是当这个阶级的一些要求和愿望——平均主义——反映到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去的时候,更会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后果。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而如果我们的革命运动是在落后的或者是错误的理论旗帜下发生的话,它将只在某几方面,但远不是在一切方面有革命意义。同时革命运动将在自己里面含有一些连自己的参加者也不知道的反动的胚胎,这些反动的胚胎将在或迟或早将要临近的将来使它失去这一部分的意义。”从而使革命走向反面。(23)农民是个取而代之主义者,(24)它本身仍然是个封建的阶级,既然如此,在农民意识即平均主义指导下的“反封建革命”,也只能获得个封建结局。
三
农民战争史研究和中国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农民革命同时起步,但它的“繁荣”却是在这场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全体中国人民的胜利。成功了的人民当然要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改造世界,既要改造政治,也要改造经济与文化。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主要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改造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它的命运当然要受这种改造本身的形势影响。建国之后,我们的社会并非风平浪静。从基本方面看,建国后政治论争的轴心为:是按照小农的面貌来改造中国呢还是按照现代工业文明的要求来改造中国?而主要矛盾是,是小农、小生产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改造呢还是整个社会接受小农文明的改造?倾向于后者的,说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倾向于前者的则说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小私有者小生产者,“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种政治上的分歧与斗争反映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是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冲突,具体到史学上,则是“阶级观点”派与历史主义学派的对立。
5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结构是复合的,政治生活基本上是求实和宽松的,对思想文化尤其是对史学的管理远不如后来那么严密。孙祚民对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新认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酝酿出来的。
孙祚民关于农民战争史的系统看法结集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中。在该书中,作者不但指出农民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是个皇权主义者,而且认为历史上的农民军并不象今天的人民解放军那样,绝对“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确确实实有“纪律败坏”的情形。作者还明确指出,对历史上的农民军“不能抹煞事实,按照主观愿望,任意进行夸张和藻饰。”(25)
今天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孙祚民的论点如何尖锐和坦率,而是这些论点公诸于世之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为什么被容忍,为什么未立即受到批判,象后来蔡美彪和董楚平的文章那样。由于受整个政治经济结构的制约,这时的中国对于究竟是按照小农文明来改造还是按照现代工业文明的要求来改造这个问题还未作出最后的抉择。这就是历史主义学派能被当时所容忍的主要原因。1956年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中国社会究竟如何来改造的问题,在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时得到迅疾而果断的解决。农民意识与此同时也开始抬头,并在1958年突然恶性发作,“共产风”——平均主义风——以十二级的风力一时间把整个中国刮得天昏地暗。当人们把平均主义当作理想和目标来追求的时候,那么对平均主义的主要载体——农民也就推崇备至了。而这也就意味着,农业社会主义终于支配了我们的现实。对孙祚民关于农民战争一系列论点的指责终于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开场了。
1958年3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章彬的《对〈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的几点意见》一文,这是全面批评孙祚民的开始。当孙祚民进行反批评后,章彬马上又以“《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的重大错误之一、之二、之三”的副标题连续著文还击。平心而论,章彬的文章这时毕竟还带有稀薄的学术色彩,而后来发表的批判历史主义学派的文章则基本上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进行的。比较典型的有《文史哲》1958年第11期之《批判赵俪生在农民战争问题上的谬论之一——对农民和农民起义的歪曲与诬蔑》,《史学月刊》1960年9月号之《中国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不容抹杀——批判孙祚民在农民战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1期之《批判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有关农民战争性质的严重错误》等等。这些文章在指责历史主义学派的同时,对历史上的农民则“一意藻饰,”“尽一切可能去加以‘美化’,”从而呼应了现实生活中的民粹主义。如果说,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是在支持蔡美彪的时候形成的,那末,阶级观点学派则是在批评和“围剿”孙祚民的时候集结起来的。政治上的极“左”观念从此在史学界找到了自己的承担者。
但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现实给农业社会主义以无情讽刺。在这之后,“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在经济上贯彻,政治上也相对地宽松起来,一些人试图乘势在思想文化领域清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孙祚民关于农民战争的一系列文章、蔡美彪自成体系的一套论点、翦伯赞的一些演讲和论述,都是在这时发表的。他们在这时出来反驳强加给他们的所谓“歪曲”、“污蔑”、“贬低”以至“否定”农民战争的指责,不仅仅是要求在学术上“拔乱反正”,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恶果中领悟到了什么。正如他们中的一位所说:他们所以那样估价农民及其起义,是为了在当前的“政治实践中得出正确的结论。”(26)
在估价农民的觉悟程度时,沙健孙说:如果历史上的“农民能够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把封建当着一种制度来反对……那么,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就不会是绝对必要的了……这种观点才是真正错误的和有害的。”(27)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显然是别有深意的。这种深意就是孙祚民在1960年所说的:“歌颂了农民的自发斗争,在客观上给‘农民可以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谬论制造了理论根据。”(28)我们在和农民结成联盟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必须时刻划清和农民意识的界限,“不要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记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因此,农民必须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改造。越是如实地研究历史上的农民,指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弱点与局限,就越是说明了农民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必要性。这就是历史主义学派要得出的“结论”。一位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评价孙祚民的农民战争史观点时说:“这个理论的最终目的,是通过阐明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的局限性,强调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体现了对现行体制积极拥护的鲜明政治色彩。”(29)相反,美化和拔高历史上的农民,不但不合历史实际,还会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农民本来就很先进。这只会鼓励农民的自发性,从而导致农民意识的泛滥。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应该承认,60年代前期的历史主义学派,是一个有着卓越理论贡献的集体,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尽管他们一再被排斥、打击、压制和埋没。
如果说60年代前期的历史主义学派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失败中看到了农民意识的危害的话,那么,70年代末期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从“文化大革命”中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彻底破产中,更进一步清楚地看到了平均主义和农民意识的严重危害,从而形成了他们对农民战争的突破性认识。
孙叔平在1980年谈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失败时说:“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失败的教训讲得少了一点,那是不利于教育人民的。”他认为,“对农民的历史作用的科学估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用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去领导农民呢,还是让农民的自发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自由泛滥呢?仍然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30)这些就是他否定“农民革命”、“农民政权”、“农民革命领袖”这些提法的现实动机。
在论及历史上平均主义的功过时,董楚平说:“革命导师经常批判平均主义的反动性,为什么它还会在我国史学界大走红运,被捧为评价农民战争的最高标准?”他认为,“主要的根本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小生产习惯势力在作怪。”他说:“二三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常受到平均主义的干扰破坏。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文化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潮,各个领域平均主义泛滥成灾,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社会上的平均主义思潮,必然要反映到史学领域里来。我们对历史上的平均主义的片面激赏,就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四害横行期间达到顶点。”(31)
60年代前期的历史主义学派在批判农民意识时还主要侧重于学理性探讨,看得出来,70年代末期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则是抱着明确的、自觉的现实目的去进行的,因而这一时期的一些文章比前一时期有更强烈、更鲜明的现实感。
新时期的历史学是在反封建的社会思潮高亢行进中展开的。由于建国后的封建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关系,反封建的社会思潮很快转向对农业社会主义——农民的自发思想——的全面清算,对农民和农民战争的重新认识又自然而然地被提上了日程。孙叔平、董楚平、王小强诸位的一批重新估价农民及其起义的文章,就是在这时面世的。很明显,这些文章感应了时代脉搏,顺应了历史潮流,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认识了农民意识、农业社会主义的危害,十年来的历史主义学派以其新颖的思维,构成了新时期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历史主义学派是一个不能低估、更不能漠视和抹煞的史学集体。几十年来,这个集体无论对于农民战争史研究学科的建设,还是对于极“左”历史观念的清算,贡献都是巨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如同“阶级观点”派一样,历史主义学派的产生和存在也与农业文明对我们整个社会的笼罩密不可分。如今,随着农业社会的即将终结,整个农民战争史研究学科,从而历史主义学派存在的必要性也即将消失。这就是近些年来环境越来越好而历史主义学派越发沉没的根本原因。“阶级观点”学派与历史主义学派的消失是同时不可避免的。除非中国社会还会发生长时间的方向性变动,否则,这种结局大概是不可更改的了。
注释:
①《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4页。
②《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78页。
③稽文甫的看法见《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漆侠的看法见《中国农民起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第36页。
④(16)《史学月刊》1955年8期。
⑤(17)(18)(19)《历史研究》1961年4期。
⑥参阅《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教育》1961年9期;《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和特点问题》(座谈纪要),《新建设》1960年12期。
⑦(26)(27)《〈是历史唯物论,还是经济宿命论〉读后》,1964年7月15日《光明日报》。
⑧《对农民战争反封建性质的理解》,《新建设》1964年4期。
⑨《“两种革命论”是“经济宿命论”吗》,《哲学研究》1964年5期。
⑩《有关农民战争问题讨论的两点质疑》,《新建设》1966年1-2期。
(11)1961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
(12)《怎样理解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1962年5月18日《文汇报》。
(13)《东风浩荡 史坛生辉——中国农民战争学术讨论会旁听记》,1978年12月6日《文汇报》;《融融聚一堂 无畏相交锋》,1978年12月14日《解放日报》。
(14)(31)见《历史研究》1980年1期,又见《农民战争特殊规律浅探》,《求是月刊》1981年4期。
(15)《马恩选集》第1卷第693页。
(20)翦伯赞《存在于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4期。此文是1963年3月在广西师院的讲话纪录稿。
(21)《资本论》第1卷第551页。
(22)、(24)见《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85页、第50页。
(2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98-99页。
(25)《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28)《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打击封建制度的问题》,1960年8月14日《光明日报》。
(29)(日)今凑良信《张献忠在四川研究动向》,《近代中国》第13卷,1982年6月30日出版。译文载《山东史学集刊》1984年1期。
(30)《谈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