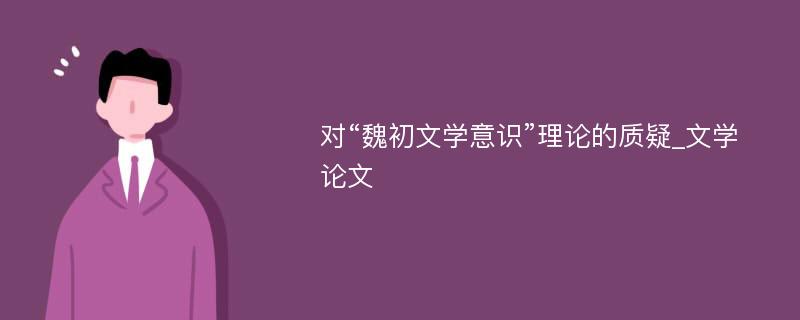
“魏初文学自觉”说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27年7月23日、7月26日,鲁迅先生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作了一个情绪激昂、手法机警的讲演。讲演后整理成文发表,这就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影响建国后的学界极大。鲁迅先生有关魏初文学及文学批评的有关论断,被不少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作为评价此期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特点的规范结论。事实上,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鲁迅先生有关魏晋文章及文学批评的一些结论是大有问题的。本文即以其有关“魏初文学自觉”说的论断作些剖析,以求方家教正。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先生对“魏初文学自觉”有如下论评: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班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以上摘引的这两段话,是建国后不少人论述“魏晋文学自觉说”的蓝本。前段关于三曹的介绍合乎事实。后段关于曹丕文学观念的分析以偏概全,违反了逻辑与文学史事实。大致说来,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曹丕说过“诗赋欲丽”,但并未说过“诗赋不必寓有教训”, “反对当时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
2、曹丕的“诗赋欲丽”, 是就他认为重要的八体文章中的两体而论的,仅就这两体概括其时的文学时尚,不够全面。
3、 用近代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见解解读汉末魏初的文章风格,甚或用“文学自觉”作为衡量文学进步的界尺,不足以说明文学发展的真正过程。
4.由曹丕以气论文,推出他的诗赋的风格是壮大,不合于曹丕以气论文的本旨及其诗赋的特点。
下面,试就上述问题作些辨析。
先说第一个方面。《典论·论文》论文体时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所谓雅、丽,主要是指语言风格。书论指议论性的子书及单篇文章。此类著作内容既是说理,表达亦须触理明晰,而不可徒事华辞。铭,指碑铬,曹丕认为它和诔一样,都应符合死者实际,不应溢美,风格亦应朴实。很明显,这段话是就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诸种文体的语言风格谈论的。在曹丕评论的几种文体中,比较接近后世文学作品概念的是诗、赋,鲁迅先生将“诗赋欲丽”这句话单挑出来作为曹丕时代文学风格的说明,正是基于诗赋这两种文体与近代文学观念的相通性。但由此进行的对曹丕一代文学风尚的论证并不合逻辑。诗、赋要写得华丽、有文彩,曹丕之前已有先声。关于赋丽,扬雄就曾说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对诗人之赋、辞人之赋作了同中有异的辨析。认为赋要用华丽的语言,但在内容上有的人写得比较规正(诗人之赋),而有的人则写得比较放荡。扬雄反对赋内容上的放荡,但不反对赋语言上的华丽。可以说从语言风格上认为赋丽是曹丕之前文章写作界已认同的观点。至于说“诗”丽,则是东汉后期以来文人制作五言诗风气日盛、诗歌语言日趋华丽这一情况的反映。《诗》三百的语言风格较为质朴,汉代的模拟之作,如韦孟《讽谏诗》之类也力求典雅、凝重。而五言诗从民间进入文人创作领域后,则逐步趋于讲究词藻,追求彩丽。建安时代曹植的诗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趋势。可见曹丕的“诗赋欲丽”是有其理论与创作依据的。曹丕讲“诗赋欲丽”,是就语言风格角度谈论的,和从内容角度讲的诗赋是否应寓有教训是并不矛盾的两个问题。从理论上讲,华丽的诗赋也不妨寓有、当然也可以不寓有训诫的思想。“诗赋欲丽”这一点可以肯定,但诗赋是否可以寓有教训,曹丕未明言,也不便究推究。从《典论·论文》中对文章的价值和作用的看法看,他似并不排除诗赋发挥褒赞、讽谏的作用。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在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的文章并不仅指诏、策、章、表、奏、议、史书等类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应用最为频繁的文字,当然也指诗赋等自汉代以来即成为文人喜欢的文字。赋可以褒赞功德、用于讽谏。郊祀、封禅一类被封建统治者高度重视的盛大典礼,也非有诗文加以配合不可,这都是当时文人熟见习察的事实。曹丕在《答卞兰教》中还说:“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符合大赋列举许多同类事物的写作实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符合诗中颂体多歌功颂德之类文字的实际。这些也许可以说明曹丕并非反对诗赋寓有教训。诚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盛赞的王粲、徐干的赋,都是抒情咏物之作。他自己的赋,在流传至今的作品中,也以抒情咏物之作为主,很少政治意义。他当时命诸文人作赋,也多是抒情咏物的小赋。建安至魏时的诗作,多是表现文人日常生活和情感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的作品,但这种现象并非始自曹魏,两汉之时抒情咏物的诗赋已不罕见。建安文人在诗赋创作中的发展,是以西汉以来的创作作基础的,并不足以当作曹魏时代“文学自觉”的证据。鲁迅先生由“诗赋欲丽”,便推出“诗赋不必寓有教训”,又推出曹丕反对“诗赋寓有教训”,其间有两个问题:其一,如前所述“诗赋俗丽”,并非说“诗赋不必寓有教训”,这是从语言与内容两个不同的角度下的判断。曹丕说:“诗赋欲丽”时并未说诗赋是否要寓有教训。其二,即便“诗赋不必寓有教训”勉强成立,也不能推出曹丕“反对诗赋寓有教训”的结论。总之,由“诗赋欲丽”推出“反对诗赋寓有教训”的论证,将不完全对立的两者当作完全对立的双方看待,是不可接受的。
次说以“诗赋欲丽”论述其时文学特点不够全面。原因在于魏初文章观念与近世文学观念有历史差异。汉末魏初,诗、赋创作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五言诗、抒情小赋在文人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以情动人、追求语言风格之美的诗、赋作品不只打动了当时读者的心,也感染着后代的读者,建安风骨甚至成为唐代复古的榜样。辑录先秦至梁初“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作的《文选》便收入此期的不少诗、赋作品。此期的诗、赋之作在《文心雕龙》、《诗品》中也给以极高的评价。诗、赋之作与近代所谓的文学可以对应。从这个角度讲,评价汉末魏初的文章不能不以诗、赋作参照。但同时应看到,仅从诗、赋来看其时的文学创作还是不够的,当时人所谓“文”“文章”的范围很广泛,不只包含诗、赋,还包含章、表、奏议、书论、铭诔、祝盟、檄移等应用性文体。《文选》(今60年卷尤袤刊本)收录此期这类文章颇多,如陈琳的《答东阿王笺》、《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为袁绍檄豫州》、《为曹公檄关将校部曲文》,杨修的《答临淄侯笺》,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与吴质书》、《与钟大理书》,曹植的《求自试表》、《求通亲表》、《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王仲宣诔》,吴质的《答魏太子笺》、《在元城与魏太子笺》、《答东阿王书》等。《典论·论文》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论及八种文体,诗、赋仅是其中的两种。这说明在对其时文章的分类上,曹丕是尊重并采用广泛的文体分类的。他自己也曾说:“琳、瑀的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论文》),对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甚为推重。我们知道,奏议、书论、铭诔之作多杂教训的内容,是不合于文学自觉论者所言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标准的,可它们也是当时认同并重视的文体,谈那个时代的文学,不及那个时代的上述应用文体,至少是不全面。就这个角度而言,由“诗、赋欲丽”勉强得出的汉末魏初“文学自觉”的结论也便不能全面概括其时的“文”。
复次用近代的“文学自觉”论解读汉末魏初的文章理论上亦有失误。“为艺术而艺术”是19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1811—1872)提出的一种文艺观点,它认为艺术是超功利的存在,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与现实社会无关。这种理论就其强调艺术自身的体性而言,有它的道理。近代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涌入中国,“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也深得不少新派人物的赏识。有人将这种理论作为建构“象牙塔”艺术的依据;也有人将这种理论作为批判中国古代重讽谏、宣喻的儒家诗教说的武器;还有人将其作为评价文学创作的标尺。凡此种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均有其必然性、合理性。但从理论本身说,“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所确定的“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的元命题本身是不成立的。艺术与社会功利性的关联是任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人们所可否定的只是艺术与社会的某种功利性关联,但在否定的同时,往往又建立起适合自己价值标准的功利性关联。“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不强调其适用的范围,是无以成为科学的理论的。具体到汉末魏初的创作、理论而言,尽管其时因社会动乱,汉代以来儒学的正统地位有所动摇,儒家诗教说有所松动,诗、赋的讽谏功能不如以往受到强调,而其渲泻情感、富于语言美的特征成为理论关注的热点,但儒家诗教说并未消声。在文人心目中,诗、赋以华丽的语言渲泻情感和诗、赋可以发挥讽谏、歌功颂德的作用并不矛盾。当时的不少诗、赋与帝王的游宴生活相关,不乏颂美的内容。当时的诗人较少提到诗教方面的论断,有它的历史先例与具体原因,下文将述及此点,不足以成为其时儒家诗教式微的证据。从汉末魏初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际看,是并不“为艺术而艺术”的。从文学史上看,文章写得好坏,评论是否得当,与是否“为艺术而艺术”并无必然的联系。汉末魏初并不“为艺术而艺术”、其后的两晋南朝,实亦不“为艺术而艺术”。相反,南朝时儒学对文学批评却具深远的影响,《文心雕龙》便以原道、征圣、宗经为论文的根本。再向后的唐代复古运动、新乐府运动,都强调文章的功利目的,但其时并不乏传颂千古的名作。这说明,试图从“文学自觉”的角度论证文章的成败是大可不必的。
最后,由曹丕以气论文推出他的诗赋的风格是壮大,不合于曹丕以气论文的主旨及曹丕诗赋的体貌特点。古代文论中最早提出文气说的是曹丕,前此孟子有知言养气的学说,但重点不在论文。曹丕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杂乎嘲戏。”“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与吴质书》)在曹丕看来,作品的气貌和作家的气质、才气是统一的,作家有怎样的气质、才气,在作品中就会有怎样的气貌。辟如徐干是齐地人,汉代齐地士人因受土风影响,其性格比较舒缓(见《汉书·地理志》),徐干的文章也带有这种舒缓之风,这就叫齐气。又如孔融,其人有很高的才气,《后汉书·孔融传》说他“贞其高气,志在靖难。”他的文章也是写得豪迈有气势,如其为人。很显然,他以气论文,讲的是作家的个性与文章体貌的关系,并无强调阳刚之气的意思。以阳刚之气论文,是古文运动兴起后,古文家的见解。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都发挥了孟子“知言养气”的学说,强调“至大至刚”的境界。我们不能以古文家的以气论文来理解曹丕的以气论文。那样做是不符合实际的。不错,曹丕称道孔融“体气高妙”,刘桢有逸气;他对徐于的作品带着舒缓之气有些不满,对王粲的文风较为柔弱表示惋惜,说明他比较称道豪迈俊逸的风格,但这不是他以气论文的主旨。从他的创作看,曹丕的诗歌,比较出色的是一些描写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之作。例如:《燕歌行》、《杂诗》、《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二首》及《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等,都能比较生动、真实地描摹出游子、思妇们缠绵悱恻的感情,情致凄恻,婉转动人。其次是几首描写出师盛况的诗,如《黎阳作三首》第三首,《至广陵于马上作》显示了他继承曹操要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另外就是《文心雕龙·明诗》所说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类的作品,不过是作为他们贵族享乐生活的写照。由于各种生活条件的限制,他的诗作缺少他父亲的壮彩,也不具建安时期多数诗人的“慷慨刚健”之风。他的散文《与吴质书》二篇及《寡妇赋》、《出妇赋》,抒写悱恻动人的情感,也并不壮大。
综上所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对“魏初文学自觉说”的论评是不足为据的。此点联系该文写作的时代背景及鲁迅立说的意旨,不难看到亦事出有因。这篇讲演的不少论断,多是借题发挥、借古讽今,并不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比如,他对曹植“辞赋小道”说的解释,认为系曹植政治上不得意时说的违心话,便不合事实。曹植写《与杨德祖书》系建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左右,〔1 〕此时曹丕、曹植矛盾尚未激化,对政治还充满幻想,并非不得意。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汉作了魏国皇帝,大肆排挤曹植力量,曹植在政治上才慢慢不得意起来。限于当时的治学条件,讲演里也有史实误记处:如将杀嵇康的司马昭误为司马懿。从鲁迅讲演的本意说,主要是借古讽今,于今有关的论题往往发挥较多,于今无关的古代情事相对而言不够重视。他谈司马照捏造罪名杀害异己,便有讥刺蒋介石意。他说:“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由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自料或与兄之意见有睽异之处。幸在知己,尚希恕言。”(《致陈浚1928年12月30日》)了解到这一点或许对认识此文的局限不无帮助。
汉末魏初的文学批评从“文学自觉说”首言者的论证看,已不能成立,但其说影响颇大。不少论者往往以此说为蓝本,极力论证魏初文学批评在强调诗、赋不必寓有教训方面,比两汉有了质的变化。这里关涉到如何看待“诗赋欲丽”诸说的历史地位问题,在此略为申辩。
在文学批评史上,从大端而论,汉代儒家文艺思想居于统治地位,受此影响,两汉的传统文论多是依经主义,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奠定了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学观。但另一方面,依经主义的内涵具有较大伸缩性,依经立义因观察主体的不同会有突破性创见。比如,刘安、司马迁和王逸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高度美学评价,对于楚文化的理想精神和浪漫气息的肯定和赞扬,他们强调“发愤著书”(司马迁语),强调文学的抒情特征,表现出与经学家的理性精神不同的审美眼光,已开魏晋论文重情之先声。又比如汉宣帝,据《汉书·王褒传》载,当时儒家对赋横加指责,以“淫靡”相罪。他辩驳说:“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娱乐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表面上,他依经立义,说辞赋与《诗经》一样,具有仁义讽谕,可以增加识见。其实,这不过是搪塞众儒的辩辞。“辩丽可喜”“娱乐耳目”才是他对辞、赋真正的认识。对于辞赋的评价,《西京杂记》卷三里说:“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其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子云学相如赋弗逮,故雅服焉。”汉代大赋当时已被视为典丽。典,就其讽谕而言。丽,就其形式而言。扬雄论赋云:“将以讽之,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正,然览者以过也。”(《汉书·扬雄传》)又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宜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言·吾子》)他一方面看到赋艺术上的靡丽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赋应典雅、规正。他甚至以赋的劝讽太少,而说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班固站在汉儒依经立义的立场上,对屈原的人格作了“露才扬己”“贬洁狂狷景行之士”的评价,但对其辞“弘博丽雅”也作了肯定,认为是“辞赋宗”(《离骚序》)。凡此种种说明,在汉代依经立义的语境中,尽管论者多强调赋应讽谕典正,但对赋语言上辩丽铺张的特点也是早有认识的,汉代赋的创作甚或都留有靡丽过甚的不足。由此可见,曹丕“诗赋欲丽”的说法有其先声,汉代经学影响下的文论对赋艺术形式的探讨相当重视,“诗赋欲丽”的说法并非是对两汉文论的冲撞,相反是对两汉文论有关诗赋认识的继承。
那么,曹丕为什么不强调诗、赋的典雅呢?这恐怕不能从曹丕反对诗、赋寓有教训上来理解,而应从曹丕说这句话的侧重点来理解,曹丕说“诗赋鹆丽”是与奏议、书论、铭诔相比较说的,强调的是各体文章的不同特点。很明显,与奏议相比,诗赋的典雅不是突出特点,故不言及。结合其他几体看这个问题或许更有助于理解:书论也不妨雅,不妨用骈丽的辞藻,但它的特点是理,故突出理;铭诔当然也应典重,但更重实,故只言实。从这个角度言,“诗赋欲丽”的说法并不一定具有很多论者津津乐道的反对儒家诗教说的意义。
二
对鲁迅“魏初文学自觉说”,北大张少康教授也不赞同。张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1996.2)发表《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一文,表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把文学的自觉等同于为艺术而艺术,作为魏晋时的特点,也许还可以备一说,但是要说文学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并且有了自觉的创作,是从魏晋开始的话,则是很值商榷的。文学的自觉与否和要求“寓训勉于诗赋”,并无必然的关系。文学的自觉和独立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和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各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直接相联系的。……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开始初露端倪,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逐步发展过程,到西汉中期就已经很明确了,这个过程的完成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笔者在不同意鲁迅先生见解这点上与张先生相同。笔者也赞同张先生所说的文学自觉与否和要求“寓训勉于诗赋”并无必然的关系,但对张先生确立的文学自觉和独立的标志及该说在概括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发展演进轨迹方面的理论价值尚有怀疑。因张先生论题与本文相关,故在此择要论述一下。
首先,张先生对鲁迅提出“文学独立和自觉始自魏晋”的概括不确。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只是说“用近代的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里的界定是明确的:所涉及的时代是曹丕的时代,充其量是魏,并不含晋;所下的结论是曹丕的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状态判断,并非起源判断。犹如说,这朵花是红的,并非说红花是从这朵开始的一样,显见其含义。张先生认为鲁迅提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始自魏晋”,是不合鲁迅原意的。
其次,张先生为文学独立和自觉确立了一些新的标准,这些标准失之宽泛。诚如张先生所言,西汉学术和文章分离后,一直到明清,文章与学术大致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别,文学观念不曾有多少新变,这样从文学观念看,中国古代文学自西汉中期以来,都是处于文学独立和自觉的状态之中。其确立的第一个标准,文章与学术分离,在概括文学发展轨迹方面并无区别作用。其确立的第二个标准,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也是西汉以后各代均有的现象。第三个标准,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和成熟,西汉以后代代相沿,且有递损旁衍。第四个标准中谈及的汉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新特点:在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两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从文学的外部规律来说,无论在文学和时代、文学和现实、文学的社会教育功能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从文学的内部规律来说,汉代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并作了比较充分的理论阐述。例如,关于文学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物感说”;关于创作中的艺术构思问题,司马相如提出了“赋心”说;关于文学创作的表现方法,诗歌方面总结为“赋比兴”说,散文方面总结为“实录”方法;关于文学本质的研究,则进一步突出了“情”的地位和作用;关于文学的批评鉴赏,提出了“诗无达诂”说。此外在文学的真实性、独创性、风格美以及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的体裁和语言等方面,也都有不少重要论述。凡此种种、在后代的评论中均不乏更强的回响。综合上述,依张先生确立的文学独立和自觉的标准,西汉中期以来,各代的文学便都独立和自觉了。这样,文学的独立和自觉这一理论规范只具有区分先秦与汉的作用,对描述其后的创作与批评就成为一把万能尺了。
最后,张先生对“文”的内涵演变的分析也失之简括。他认为,“汉代文学观念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学术和文章的分野日益明显”,这大致是不错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里,仍将诗、赋、经、子、史及一些应用文当作文章看,此点结合《宗经》、《祝盟》、《铭箴》、《诔碑》、《哀吊》,《史传》、《论说》、《诸子》、《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不难见到。这种做法梁代以后亦有效法者,直到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仍广收应用文体。可见,汉代以后学术与文章的分野也有不明显的时候。另外,张先生将刘向、刘歆父子在《别录》、《七略》里将诗赋与经传、诸子等并列。当成是明确肯定文学与政治、哲学、历史有不同的独立地位,其说亦值辨析。笔者认为,刘向、刘歆父子将诗赋并列于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主要是基于分类便利的考虑,并非认为诗赋外的六艺、诸子不是文章,不是文学,将其作为肯定文学独立地位的证据,即意味着诗赋是文学而经传、诸子不是文学,这样的论断,并不合乎刘向、刘歆的原义。
总之,从文学自觉的角度论证汉末魏初的文学发展是不恰当的,由此争论文学自觉始自何时亦大可不必。笔者认为,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更多地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这合乎中国文学的实际。中国古代创作与批评比较重视尊体辨体,这是个优良的传统。的确,在中国古代的创作中,文学的体性差异、作家的个性差异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特点,不考虑文体差异、浮泛地论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特点,结论往往不能中肯。关于这一点,容专文另行探讨。
〔注〕
〔1〕〔日〕冈村繁:《论曹丕的〈典论·论文〉》。 译文收入《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标签:文学论文;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论文; 典论·论文; 读书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曹丕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文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