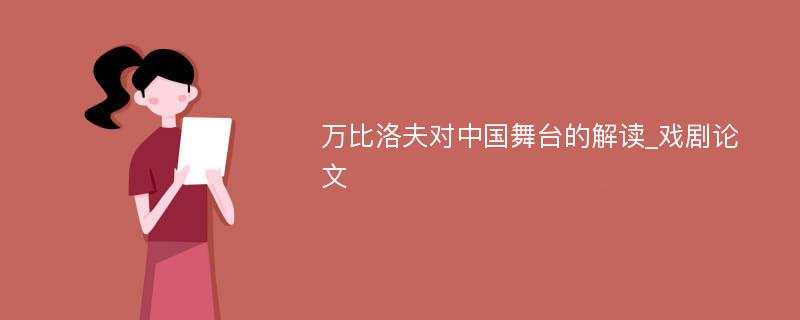
万比洛夫在中国的舞台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夫论文,中国论文,舞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万比洛夫与舞台阐释的发生 作为当代俄罗斯“一位闻名遐迩的戏剧家、散文家、评论家”,[1]52亚·瓦·万比洛夫“虽然只活了35岁,但他却如智者般了解和谙熟生活”,[1]52先后创作出《窗子朝着田野的房子》(1964)、《六月的离别》(1966)、《长子》(1968)、《打野鸭》(1970)、《外省轶事》(1970-1971)、《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1972)等名剧,其中《打野鸭》和《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可谓经典之作。在当代俄罗斯学术界,万比洛夫的艺术世界和“万比洛夫之谜”,得到深入研究并引起持续论争,一系列代表性研究著述先后问世,①不同剧作不断在各大剧院上演;在当代欧美国际斯拉夫学界,万比洛夫作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焦点备受关注,不仅剧作和散文随笔得到全部译介,而且戏剧文本得到审美分析,舞台剧演得到多样呈现。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万比洛夫得到广泛译介和深入研究,呈现出以译介为主、注重剧作的文本维度,以舞台为主、注重演剧的舞台维度,以研究为主、注重理性的学理维度。 作为文化传播与集体想象的媒介,文学不仅以艺术镜像方式反映社会现实,参与并驱动某时某刻的现实变貌,而且铭刻某一历史环境中的美学趣味,进而遥指掩映其下的政治潜意识。在跨文化交流语境中,作为多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跨语际实践可以呈现译介、接受、诠释等多种文学实践如何表述自我历史,确立民族文化,建构现代性话语。[2](1-8)据不完全统计,1949-1957年间,中国共演出外国戏剧113部,其中苏俄戏剧91部,占总数的80%强;[3](838-844)1957-1980年间,中国上演的俄罗斯戏剧直线下降,随着社会改革、国门开放和文化自由,欧美戏剧上演数量则急剧上升。在寂寥的俄罗斯戏剧剧演中,万比洛夫戏剧却在当代中国舞台上大放异彩,不断改编排演。由此,以导演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界和以观众为代表的普通受众群,对万比洛夫的认知呈现出认同与质疑、彰显与遮蔽、想象与误读等诸种形态,其意义不可忽视,即作为文化交流的中介而被公众接纳和认同,作为域外思想的他者而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万比洛夫在当代中国舞台的诠释态势如何?特点怎样?形象如何呢? 整体说来,在理解与误解、认同与赞赏、诠释与过度诠释中,万比洛夫被搬上当代中国舞台,流布不息,直至今日。这与万比洛夫在俄罗斯的舞台诠释,既彼此呼应,又明显不同,其中的赞赏与误解,移植与改编,诠释与过度诠释,显示出其诠释内涵的不断探索与逐步深入。万比洛夫在中国舞台的多样诠释和不同剧演,恰逢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际,与官方政治美学向大众消费美学转轨遥相呼应,在某种程度上悄然折射出当代中国个人意识勃兴、文学政治意识消弭、美学理念嬗变的宏观思想态势。 从青年成长到人性挖掘:《长子》在中国舞台 在昙花一现的短暂生涯中,万比洛夫与主流意识和官方思想一贯持审慎态度,保持相当的艺术距离,具有强烈的美学自省和艺术自觉。“万比洛夫在自己的话剧中构建了一个边缘(предместье)的世界,这不仅是地域概念,同时也是一个道德概念,主人公处于精神边缘上,站在道德选择的门坎上:只须迈一步,不是冲出琐细的日常生活,就是继续浑浑噩噩的生活。”[4]626万比洛夫剧作的舞台演出和演剧实践,对“文革”之后的中国戏剧走出“红色经典”的局囿和“革命样板戏”的迷雾,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 经过1977-1979年间的文艺论争和思想解放,②在苏联“解冻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中国话剧逐渐复苏,提出“写真实”、“干预生活”、“呼唤人性”等主张,涌现出一系列反思历史、批判申冤、反映社会的“问题剧”,③由此“预示着新时期中国戏剧的发展将进入一个艺术自觉、戏剧自觉的新阶段”。[5](242)1980年代,由“戏剧观”带来的“戏剧危机”,成为笼罩在中国戏剧界的阴影,也成为西方现当代戏剧大量译介传播、舞台剧演的契机,更是中外戏剧不断碰撞、交流和融会的动力。[5](243-262)根据现在掌握的有限资料,最早自发排演万比洛夫剧作的是上海戏剧学院“文革”后恢复高考招收的第一届表演班同学,其后蜚声全国的著名演员李媛媛、杨凤梁、谷亦安等亦参与剧作演出。[6](100) 1984年5月,融合幽默与抒情、偶然与误解为一体的《长子》,由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八一级改编排演,其中表演系主任于德先担任导演,周本义、倪荣泉、吕振环等担任舞美指导,学生王洛勇、宋佳等担任主要演员。在中俄关系尚未正常化和理性化的国际文化交流态势下,对中国艺术界而言,这出“内部演出”“乃是万比洛夫剧作在中国的第一次正规演出”,[6](100)其演出说明书白纸黑字,素朴简明,直截了当,没有任何花哨的装帧和人为的修饰,[6](100)这在当代中国话剧史上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作为早期剧作之一,《长子》几乎具有万比洛夫戏剧的所有特质:文本结构上具有环形布局(кольцевая композиция),[7](64)艺术风格上呈现出幽默戏谑,剧作体裁上表现为悲喜交加,人物心理上体现出道德变化,剧作主题上探讨着人性伦理。[7](58-76)如何在舞台的方寸之间,人物的关系之上,短短的时间之内,恰如其分地展示以上艺术特质,对于刚从“极左思潮”和样板戏迷雾中走出不久的中国艺术界,无疑是一个并不容易操作的导演困惑和时代问题。由于戏剧演出的一次性和即时性,相关演出资料一时难以搜集,中国导演如何改编、导演和诠释《长子》,留下一个模糊的历史背景和基于事实的想象。其实彼时彼刻,如何“对戏剧观念作新的探索和解释,充分发挥舞台假定性原则,多层的戏剧结构方法,不固定的舞台时空观念,追求表达思想哲理的深度,迅速反应人们思考的社会问题,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世界作深透剖析,追求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8](44)对急于摆脱困境的中国戏剧家和导演们充满了诱惑力和冲动性,也使戏剧家形成一个强烈的时代共识:“中国话剧必须变革,中国话剧必须借鉴西方现当代戏剧以寻求新的创造。”[5](244) 20-21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的自由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宽松,万比洛夫戏剧和《长子》的舞台诠释重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舞台上的《长子》侧重的是青年成长和思想启蒙,那么,世纪之交该剧改编关注的则是人性挖掘和伦理探讨。2000年5月,上海戏剧学院再次将《长子》搬上话剧舞台,作为97届表演系本科毕业演出。该演出由王学明担任导演,姜明会任舞美指导,主要演员包括王博、杨建平和当红影视小生佟大为。[6](100)此次演出情节叙事始于戏谑玩闹,中经误会和挣扎,终于严肃理性;通过人物从非理性意识向理性意识的转变,从伦理混乱向伦理秩序的回归,主要关注人性的复杂和精神的成长。《长子》舞台剧的当代改编和演出效果,得到师生观众的认可和赞赏。 简言之,万比洛夫的戏剧重视社会现实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探讨共同关注的道德伦理问题,散发着忧伤的抒情特色和淡淡的浪漫风格,充盈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观照。这种关注现实、重视精神、探索人性、手法创新的戏剧诉求,呼应并吻合1980年代以降追求“真实”、“人性”、“实验”的文艺脉搏和时代话语。“一度弥漫全国的迷信反过来启发了他们怀疑否定的精神;长期的自我压抑使他们追求强烈的自我喷发;‘文革’时期对人性的迫害使他们急切地重申人的权利和人道观念;先前粉饰现实的‘假大空’文学使他们转向寻求内心的真实;他们不满于一般的反映论和说教灌输的手法,积极向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学习;他们不赞同以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批评,力求从西方现代文论和各种新兴学科汲取营养,进行新的探索。”[9](100) 从道德批判到金钱人性:《外省轶事》在中国舞台 作为幽默讽刺剧的代表,万比洛夫的《外省轶事》延续果戈理的笑中含泪的艺术风格和契诃夫的淡然幽默的戏剧传统。该剧的丰富内涵和多元空间,诸如对社会丑恶的挞伐、道德滑坡的忧思、金钱罪恶的警醒、人性复杂的探索、善良人心的抚慰、等级压迫的遗毒,在中国舞台上得到程度不同的诠释和深度有别的解读。 1986年代前后,在艺术文化的计划体制之外,西安话剧院导演和演员积极探索戏剧排演和改革路径。在计划之外,导演曹景阳、特邀导演蒋立力、舞美设计尤宝诚以及部分演员采取自愿结合,自选剧目方式,利用空余时间排演了悲喜剧《外省轶事》。该剧包括《密特朗巴什事件》与《和天使在一起的二十分钟》两部短剧。前者故事以外省宾馆经理卡洛申与莫斯科排字工波塔波夫之间的见面、冲突、误解、猜忌为主线,嘲弄外省小人物庸俗的市侩本质和贫乏的精神世界;后者描写助人为乐的善良农艺师的尴尬遭遇,其背后包含着荒诞滑稽的意味和道德伦理的滑坡:天使本应代表善良博爱,现实中却备受猜忌,人与人本应彼此信任互助,现实中却自私猜疑。在中国舞台剧演中,为了方便深入基层塑造真实形象,西安话剧院从创作准备阶段演员们就力求使队伍精干,舞台布景简练而真实。在文本分析基础上,从彼时彼刻的中国现实出发,导演将剧作主题定位为批判社会丑恶和道德沦落。由于剧本情节安排巧妙,演员表演真实细腻,演出节奏明快而又流畅,因而剧场效果热烈。对此计划体制外的创作实验举动,西安话剧院予以肯定支持,将其看作是文艺改革中的有益尝试。[10](32) 1987年,北京人艺将85级学院班作品的《今晚照常演戏》(即《外省轶事》)搬上舞台。导演为张辛欣,演员包括著名的韩善续、丁志诚、冯远征等。在此之前,北京外语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都曾已上演过此剧。[6](100)1999年,作为“戏剧创作人和舞台监督”为专业的实验班,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97成人大专班,在毕业之际推出了两台独幕剧,即万比洛夫的《和天使在一起的二十分钟》和玻西瓦·淮尔德的《坦白》。[11]61两部剧作始于笑话,中经混乱、误会和不解,终于幽默,其主人公皆为熟知的生活类型。此次舞台演出是中央戏剧学院97导演系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独立制作、导演和表演的成果,融戏剧改编、导演技巧、艺术管理、舞台表演、宣传策划等不同艺术维度为一体。“金钱摧残人性”的主题,将两部毫无联系的戏剧巧妙结合在一起,使两部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间、不同作家的剧作,在异国话剧舞台上自然融为一体,体现出重视艺术(形象)思维、戏剧管理(逻辑)思维和艺术完整思维的实验培养理念。[11](61)与先前倾向于自然主义式的舞台风格不同,2009年9月,上海戏剧学院端钧剧场上演了风格现代、技术立体的《和天使在一起的二十分钟》。该剧作为上海戏剧学院08级MFA毕业演出,其新技术媒体的运用、自然流畅的表演、契合当下的改编,均获得好评。 总之,大致说来,《外省轶事》在中国舞台的诠释,在诠释主题上经历了从批判社会道德到探讨金钱人性的变奏,在表演技术上经历了从自然主义式到新媒体技术参与的变换,在风格上经历了从戏谑嘲讽到笑中含泪的嬗变。由此,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内部演出与公开演出,讽刺剧与抒情剧,艺术院校与外语院校,首都剧院与地方剧团之间,不约而同的剧作改编与舞台演出,使万比洛夫在中国话剧舞台上摇曳多姿,异彩纷呈。 从俄国视角到中国立场:《打野鸭》在中国舞台 随着1990年代以降中俄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文化氛围的日益开放,万比洛夫剧作在中国的舞台演剧,呈现出稳中有进、多次改编、本土试验的趋势,体现出外来与传统结合、历史与当下对话、西方与东方融会的特色,由此凸显的是导演的戏剧美学理念和舞台改编方式。在20-21世纪之交,《打野鸭》在中国舞台的实践中颇具代表性和象征意味。 如同《三姐妹》中“到莫斯科去”的朦胧而美好的期盼,“去打野鸭”既是贯穿《打野鸭》全剧始终的象征性主题,也是理解齐洛夫形象、“齐洛夫气质”乃至万比洛夫戏剧的关键所在。《打野鸭》的基本情节是中年男性维克多·齐洛夫的六段回忆,开头和结尾遥相呼应,呈现出明显的环形结构,氤氲着浓厚的忧伤气息和压抑氛围,具有比较浓重的荒诞特色和现代(乃至后现代)气息。作为典型的“多余人”形象,齐洛夫在身体上健硕青春,正值年富力强之际;在精神上萎靡不振,恰逢心灰意冷之时;二者的张力与反差,奇异而吊诡地结合在一起,无疑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暗示和隐喻性的陈述。一方面,他撒谎成性,生活放荡,假作忠诚,装出一副真挚状和可怜相;另一方面,又洞察世事人情冷暖,冷眼旁观人生百态,想过严肃而有价值人生,却一时心灰意冷,无从做起。这种介乎好坏,难辨善恶,不分美丑的复杂形象,不仅仅是齐洛夫形象的综合表征,也是1980年代苏联停滞时期一代人的群体肖像:“这是些不很善良的人,但又不是很坏;他们知道一切原则,但却又不总是遵守原则;不是绝对的傻瓜,但却根本也不真是聪明人;他们也识文断字,但绝不是博览群书;他们也关心父母、供养孩子、不抛弃妻子,但却不是爱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他们也在完成工作,但并不爱自己的工作;他们什么都不相信,但又迷信,幻想的东西别减少,自己的东西也能更多。”[4](628) 1990年12月中旬,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班学生在北京公演《打野鸭》,乌克兰基辅戏剧学院米·尤·列兹尼柯维奇教授应邀来京执导,舞台美术设计则是舞美设计家伊·彼·卡彼塔诺夫。[12](62)中方演员和导演在外方导演指导下,中外合作在华演出话剧,是1980-1990年代的普遍潮流和合作方式,也是中国导演迅速提高导演水平和戏剧理念的便捷方式之一。作为跨文化舞台实践的二度呈现,列兹尼柯维奇导演对《打野鸭》进行了相对较大的改编。在台词节奏上,舞台剧删节冗长台词,调整情节节奏。在剧目设计上,导演打破原剧三幕的排列,使之变成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集中写齐洛夫的青春回忆,表现他与加林娜、薇拉和伊林娜的爱情关系;后半部分写三个女性相继离开之后,齐洛夫心情低落,苦闷至极,唯一精神慰藉是朝夕相处的几个友人,然而友人却心怀叵测,觊觎家产。由此,探索与展现造成齐洛夫悲剧性命运的主观因素和客观环境的根源,成为舞台艺术处理的中心环节,也成为列兹尼柯维奇改编剧的重要特点。在主题阐述上,导演为人物增添必要台词和情节。在内容思路上,舞台剧部分改变剧作风格,在剧终时加进《三姊妹》结尾憧憬未来幸福生活的台词,由加林娜、薇拉、伊林娜说出,使演出洋溢着鲜明的积极向上精神:由此表达出导演二度创作的社会思想性和艺术倾向性。[12](63)列兹尼柯维奇导演舞台改编之举,透露出独特的艺术诉求和舞台剧演理念。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着力表现各种不同人物之间的思想感情冲突。齐洛夫与妻子加林娜回忆青春和最终分手等重点场面的加意处理,“充分揭示人物行动的心理逻辑和内在情感,使人物在关键时刻袒露真情,倾诉内心隐秘,从而加深人物形象的厚度和深度,开启观众与舞台交流的新的审美层次”。[12](63)其二,刻意追求诗意与哲理的表达,使舞台形象具有美感和象征意味。通过黑匣子般的舞台设计,简练概括的舞台造型,诗意化的雨声音乐,阴暗压抑的总体氛围,“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总体舞台形象的独特性,阴雨不停的天气,令人压抑的环境,与人物的心态相互渗透与映衬,给观众的审美视觉造成一个象征性的意境,从而诱导观众对生活和人生进行思考,获得一种新鲜的审美经验”。[12](64)其三,舞台表现手法灵活多变,大胆运用舞台假定性原则,融化汲取电影多组画面同时组合的方法,在同一舞台时空表现不同地点的人物行动,扩展舞台表现生活的容量。舞台五个表演区的分离勾连和灯光影色的转换回闪,“既为场景转换提供方便,也为多组画面组合创造了条件”,“为舞台人物行动创造出各种氛围与环境”。[12](64) 从演出效果和戏剧评论来看,该剧的二度创作、改编排演、毕业表演相当成功,不仅备受专业人士和戏剧观众的赞赏和好评,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当今中国话剧电影界的中坚和精英。在列兹尼柯维奇的严格要求下,身材高大的胡军饰演齐洛夫,将其萎靡散漫和洞察清醒等矛盾性特点完美表现出来,达到其话剧舞台演艺生涯的一个新高度。这段经历对其演艺生涯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毕业大戏《打野鸭》让胡军一跃出水面,两个半小时没下舞台,胡军把大家都震了。从此,《打野鸭》成了胡军对于舞台最完好的里程碑。”[13](29)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王斑认为,“胡军主演的表87班毕业大戏《打野鸭》给了全班深刻的印象,它使胡军的表演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国家话剧院演员韩青则认为,“毕业大戏《打野鸭》奠定了胡军扎实的表演路径。当时那位前苏联的导演要求很严,教学上很有办法,对于绝对是男一号的胡军尤其严格,抠他的戏最准确。他不但把胡军富有情感爆发力的强项发挥到极致,也把胡军细腻柔情的方面挖掘出来,让胡军的表演完整成熟了。”[13](31,32) 在1995年4月上海戏剧学院学生话剧展演系列演出中,《打野鸭》呈现出与中央戏剧学院不同的舞台二度诠释。该剧由李学通任导演,徐海珊任舞美指导,伊天夫任灯光指导,潘建华任服装设计,96届表演专业的于和伟饰演主角齐洛夫,温耀龙、沈瑜等亦在主演之列。与中央戏剧学院略带官方意味和俄国戏剧传统的舞台诠释不同,该剧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演出,则更多体现出海派文化气息和现代主义意味。其最大特色和理念不同在于,经由舞台背景反映心理状态展示生活本质,抽象的舞台设置与复杂的人物心理彼此呼应,相互彰显:舞台背景设置为形状不一的大块抽象白色几何体,透过它们舞台后上方现出幽幽蓝光,营造出比较浓厚的象征意味和荒诞氛围,而灯光设计则随着情节发展而不断变化。[6](100)在《打野鸭》中,万比洛夫巧妙运用戏剧独特的表现手法刻画人物性格,用灯光渲染气氛,利用某些道具(诸如打猎器具、野鸭、丝绒猫)刻画主人公的心理,用音乐烘托人物心理变化和故事情节转换。音乐贯穿戏剧始终,时而活泼,时而哀怨。对主人公的心理刻画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戏剧的最后一幕,主人公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主人公内心的道德冲突成为剧本的一大特点。作者把主人公回忆过去的事件和主人公后来的认识感受交织在一起,显得真实可信、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应该说,通过舞台背景和布景的巧妙设计和充分利用,上海戏剧学院的此次演剧诠释比较好地呈现出齐洛夫复杂丰满的人物内心:或快乐欢欣,或浑浑噩噩,或忧郁苦闷,或沉沦颓废,或冷眼旁观,或清醒冷静。[6](100) 总之,《打野鸦》在中国舞台上经历数度改编(1990、1995、2006、2012年数次被搬上舞台),经历了从俄国域外视角到中国民族立场的改变,实现了从以现实主义呈现为主到以现代主义表现为主的转换,很大程度上契合中国中年一代迷惘愤世的精神面貌和冷眼旁观的时代气质,体现出典型的跨文化、跨语言、跨时空的艺术诠释和双向交流。 从环境冲突到内心矛盾:《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在中国舞台 万比洛夫以人道情怀诗意化描写普通个体的现代性体验,颠覆既有的僵硬冰冷的政治乌托邦,呼唤鲜活自由的个人主义。《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在中国舞台的诠释,舍弃外在的环境冲突和社会规制,转而注重内在的内心矛盾和精神冲突,关注个体的现代体验和内在挣扎。这在很大程度上吻合当代中国文化界的时代要求和时代话语,部分成为中国当代知识界反抗后工业文化复制和后现代艺术解构的文化资源。 2004年,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2000级本科班选择万比洛夫的剧作《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以此作为毕业大戏,其中女主角瓦莲京娜由金晔、刘露、汤唯三人分饰,男主角沙曼诺夫则由耿暨张、田晓威、郭超一三人分饰。④该毕业演出由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副主任姜涛博士担任导演,鲍黔明教授担任艺术指导。[14]118在改编创作与舞台实践中,导演和演员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呈现万比洛夫的“生活性”与二度创作的写实象征,即“如何准确把握作家思想与作品风格,在剧本分析基础上形成导演构思、凝练出演出的‘形象种子’,使二度创作各部门在其启发下创造完整的演出艺术与舞台人物形象,并追求独特的演出风格”。[14](118)总体数来,该剧的二度创作主要体现在主题把握、舞美设计和表演分析三个方面。 在主题把握方面,导演通过剧作文本阅读和剧组集体讨论,认为万比洛夫戏剧的主题是内在的心理矛盾,而非外在的环境冲突。“构成万比洛夫戏剧冲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传统戏剧中‘人与环境的冲突’,而是生活对于人的内心状态的改变,是人物总在不断地选择、反思自己的生活。这种选择与反思常常是十分痛苦的。”[14](120)这在很大程度上吻合万比洛夫戏剧的艺术精髓和美学理念,即不追求表面的外部冲突和情节的跌宕起伏,而致力于在日常性和静态化的生活流程中描写复杂而强烈的心理冲突。因此,从万比洛夫的剧本中可以读出契诃夫的台词,触摸到俄罗斯的脉搏,听到俄罗斯的回声。[15](190)换言之,万比洛夫戏剧有明显的契诃夫戏剧的“日常性”、“静态化”和“抒情性”特点,其中最接近的正是《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16](249-261)由此,如何准确在舞台上对剧作的静态化、抒情性和日常性进行形象诠释,是舞台排演的主要难点;对此导演以生活化象征和写实化幻觉而处理之。如何凝练演出中哲理化的内心形象(即“形象种子”),是导演构思的重要内容;对此导演以青春凋零与生命苏醒而概括之:“我们将演出的形象种子简述为:早春的森林,一朵最绚丽的花朵被蹂躏,然而森林就在她不屈的生命与热烈的青春气息中苏醒过来!”[14](124) 在舞美设计方面,导演和舞美孙大庆凝练出“向日葵”、“修栅栏”和“花园”等核心意象,以“细节与局部写实,整体上‘写意’的指导思想”,确立舞台设置转台的总体方案,意在凸显舞台前部花园以及向日葵的象征意义。[14](124)这种整体象征氛围的营造和微观真实场景的设计,让人在具体场景中身临其境,在整体幻觉时抽身而出,“更加深入地揭示居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剧作的思想内涵”,[14](124)从而引导观众进行更高境界的审美共鸣和更深层面的思想反思,收到比较圆满的舞台影响和接受效果。“瓦莲京娜与沙曼诺夫爱情的‘向日葵’虽然枯萎了,但是……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于是在全剧的结尾,……整个乐池长满了鲜花,半透明的塑料底幕后面隐约现出一座美丽的大森林,当塑料底幕升起时,画幕上那一片美丽的俄罗斯森林完全进人观众的视线,整个舞台在转台的转动中渐渐成为一座美丽的花园。”[14](124) 在表演分析方面,姜涛提出“人物阵营划分”的表演分析方法,认为在万比洛夫风平浪静的戏剧表面之下,蕴含着人物思想互相交锋的戏剧核心,“进行人物阵营的划分有利于在贯穿行动中揭示剧作的思想”。[14](122)对演员而言,多人分饰一角以其假定性和陌生化特征呈现出人物的多种面向和多复杂心理,而演出最高任务则是青春和爱情的消逝与心灵和理想的警醒:“无比美好的青春在沉睡中消逝、甚至在自私与仇恨中被扼杀,演出要揭示这一残酷的事实并向人们大声呼喊:从看似忙忙碌碌的精神沉睡中猛醒吧,让我们在心灵中建筑起美好的家园!”[14](122-123)因此,从演出效果来看,《去年夏天丘里木斯克》的舞台诠释和二度创作,对导演执导和演员表演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我们对结果并不满足,然而不论是作为分场导演还是担任演员,我们很团结,我们互相帮助互相信任,我们很努力”,“剧中人物的命运思考我们自己的‘可不怎么样啊’的生活”;“要让未来的导演们打好心理现实主义演剧方法的基础,万比洛夫是很好的教材”。⑤ 本着忠实而虔诚的创作态度,导演和剧组对万比洛夫进行了个性化改编和集体化排演,其融合传统与先锋的二度创作,比较确切地触摸到万比洛夫戏剧的象征性与写实性、静态性与诗意性、喜剧性与悲剧性、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由此创作出丰满的演出总体意象和人物形象,实践着跨语际、跨时空、跨文化的他者凝视和域外反思。对此,作为话剧导演姜涛坦言:“对待经典剧目,导演无权将剧作当作‘素材’进行随意裁剪,改变剧作情节结构、甚至以改变人物命运为代价来‘拼贴’导演的‘演出思想’。……呈现经典需要准确的剧本分析、独特的导演构思与综合运用舞台手段的能力,其中‘构思’是整个二度创作的关键,是未来演出成功的保证。”[14](125)总之,在经济发展日趋全球化和生活方式逐渐同质化的时代,万比洛夫剧作超越时空局限和文化阻隔,呼唤着美好人性和人道理想,不仅在中国舞台引起颇多关注和研究,更引起亚洲高层戏剧论坛的理性思考和亚洲戏剧院校的舞台实践。⑥通过道德伦理分析和社会现实问题,展示心灵深处本真的精神特质,万比洛夫剖析着当代社会核心的精神病症,进而表达超越民族和地域的普遍价值和精神呼唤。在普世价值与伦理观念、地域特色与民族特性之间的艺术张力,乃是万比洛夫永恒不衰的原动力与核心所在。 结语与展望:万比洛夫在中国舞台剧演反思 在20世纪俄罗斯剧作家中,由于剧作意象的象征化、意境的诗意化、语言的抒情化、情节的静态化、形象的复杂化,万比洛夫与契诃夫戏剧传统密切相关,可谓是当代中国舞台上剧作改编次数最多、上演最频繁、演出最受欢迎的俄罗斯剧作家之一,堪与契诃夫、高尔基、布尔加科夫等剧作家相媲美。总体说来,万比洛夫在中国的剧场改编与舞台表演,主要集中在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等艺术院校的非商业性演出,兼及其他社会剧团的商业演出、公益演出和民间团体的自发演出⑦其演剧探索、教学效果和演出反映,并不亚于同时期其他欧美剧作家。由此,万比洛夫在跨文化语境的改编剧演中,呈现出一个充满文学艺术魅力和舞台诠释空间的演剧面向。 1980-2010近三十年间,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万比洛夫得到多样化、本土化和实验性的改编与剧演,在剧目选择、导演理念、表演队伍、演出团体、受众群体、演出效果等方面,别有特色,颇有意味,值得反思。其一,在剧目选择上,万比洛夫在中国舞台的剧演以讽刺性喜剧和喜剧性悲剧为主,集中在《长子》、《外省轶事》、《打野鸭》、《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四部剧作。其二,在导演理念上,万比洛夫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移植他者经本土试验到自我创新的过程,体现出域外与本土、借鉴与融合的张力冲突。其三,在表演队伍上,在中国舞台表演万比洛夫的多为专业戏剧院校的学生,少有专业剧团的专业演员,尚未大规模推广到专业剧院舞台,其演出影响多集中在话剧界和艺术界。其四,在演出剧团上,万比洛夫的中国舞台剧演,以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等专业艺术院校为主,以地方剧团为辅,多为非商业、毕业性、观摩性、教学性剧演,少有商业性、公开性剧演。其五,在受众群体上,观看万比洛夫的舞台剧演的多为艺术院校学生、话剧界专业人士和部分戏剧爱好者,少有普遍性的大众群体和艺术行为,未能如电影一般深入大众。其六,在演出效果上,此类舞台剧演效果普遍有声有色,达到应有的艺术水准,媒体评价普遍不错,但多局限在戏剧界业内和精英群体之中。以上种种值得称赞的成就,既说明万比洛夫戏剧的永恒艺术魅力,也推动着万比洛夫戏剧的本土化进程和传播接受范围;凡此种种令人深思的问题,既与中国话剧土壤和文化氛围欠佳有着密切关联,与演出的教学性和非商业性质有一定联系,也与大众消费主义盛行一时、戏剧改编方式单一、话剧宣传渠道单一、推广不力等因素不无关系。 在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看来,文本的诠释潜在地具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对任何事物的诠释和建构都有一个相对性和有限性,不能像流水一样肆无忌惮任意流淌,超出文本界定的大致范围。[17](71-95)中国舞台的万比洛夫诠释,并非完全忠于原作,合乎原意,而是既有合理诠释,又有个性改写,既有无意误读,又有故意误读。在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个体与家国、时代与政治、自我与他者之间,各类文学叙述粉墨登场各显神通,如何处理不同题材与主题、如何协调各种话语关系、如何平衡不同力量形态,就显得妙趣横生耐人寻味。在涉及到国家民族与意识形态、大众群体与社会现实、个人体验与商业消费等彼此纠缠的问题时,不同改编理念和表演方式尤其令人深思。在30年间,万比洛夫在中国经历了实验性与多元化、写实化与写意化、先锋式与传统式的多样舞台诠释,其间虽有相对保守和过度诠释,但整体而言,中国的舞台诠释丰富了后人对万比洛夫的理解。万比洛夫在当代中国的舞台诠释,证明了其人其作对人类精神生活和人生价值意义等问题的当代意义。回顾万比洛夫在中国的舞台实践,可以发现,相当数量的舞台诠释未能充分挖掘万比洛夫剧作(尤其是《打野鸭》和《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暗含的复调性,诸如幽默特质、讽刺特点、喜剧品性、悲剧特色、哲理沉思等,而是有意无意突出或彰显某一核心主题,诸如青年成长、道德探索、社会批判、人性揭露等。事实上,万比洛夫戏剧的“悲剧特点”或“喜剧谜团”,“主题之谜”或“戏剧遗产”问题,与其戏剧体裁的不确定性与戏剧主题的多样性紧密关联,如影随形。离开体裁形式来谈论主题思想,或脱离主题内涵分析体裁结构,或将戏剧文本与舞台演出彼此割裂,或将万比洛夫戏剧与契诃夫戏剧传统前后分离,对于充分理解万比洛夫的艺术世界,无疑难以登堂入室,得其三昧。在未来的中国舞台诠释中,万比洛夫问题将不断有新的探索和发现,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将伴随着不同程度的误读和过度诠释。无论是正读或适度阐释,还是误读或过度阐释,都是万比洛夫进入异质文化世界的一种可能路径,是其投射到不同民族时代的一束熠熠光影,是其不同语际诠释的一种呈现面向,显示出戏剧经典的人文恒久性和对话复调性。正因如此,万比洛夫的舞台诠释将始终伴随着人们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思索,对人类精神生活本质的探究,对其艺术世界特质的不断思考,对戏剧舞台艺术规律的不断深入。 概而言之,万比洛夫在当代中国的舞台诠释,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态势、中俄文化交流关系、文学总体态势以及时代主流话语等不同因素密切相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遮蔽到发现到认同的理性发展历程,这与当代俄罗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和传播可谓遥相呼应。与此同时,万比洛夫在中国舞台的奇异之旅,伴随苏联文学的终止、文学国家化的松绑、文学整体化的边缘、商业文化的兴盛,经历了一个解构政治崇高和逐次降阶反思、反抗主流意识规训到建构个体诗意心灵的过程,也显示出20-21世纪之交政治乌托邦向文化反思、从国家意识向消费主义的艰难转型,更呈现出面对市场新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戏剧话语向大众美学渐次妥协的幽微路径。由此,万比洛夫在中国的舞台诠释和接受态势,成为管窥当代俄罗斯戏剧在华演出和当代中俄文学关系的一个生机勃勃的诠释符码。 注释: ①См.:Гушанская Е.Александр Вампилов.М.,1990; Гушанская Е.Александр Вампилов: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Л.1990; 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а Вампилова.Иркутск,2000; Смирнов С.Р.Недопетая песня:Девять сюжетов из творческой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Александра Вампилова.Иркутск,2005; Смирнов С.Р.Творческая лабрато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Вампилова.(От《Ярмарки》до《Утиной охоты》)Иркутск,2006; Сушков Б.Александр Вампилов.М,1989; Зборовец И.В.Вампилов сатирик.Львов,1982; Стрельцова Е.Плен утиной охоты:Вампилов.Творчество и судьба.Иркутск,1998; Тендитник Н.С.Перед лицом правды(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Вампилова).Иркутск,1997; Тендитник Н.С.Александр Вампилов.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ортрет.Новосибирск,1979; Сушков Б.Ф.Александр Вампилов: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б идейных корнях,проблематике,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методе и судьбе творчества драматурга.М..1989; Зоркин В.Не уйти от памяти.Иркутск,1997; Смелков Ю.Новое в жизни новое в драме.М.,1978; Имихелова С.С.,Юрченко О.О.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А.Вампилова.Улан-Удэ,1999. ②在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戏剧家提出“写真实”的主张,认为“当前的关键是戏剧创作如何真实地、深刻地反映群众的生活实践”,尤其要“勇于面向生活,干预反映生活中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干预提出和解答千百万群众在实践中最迫切关心的问题”(参见本刊记者:《戏剧也要受实践的检验——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讨论“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人民戏剧》1978年第11期)。1979年,《剧本》杂志组织召开“青年题材剧本创作座谈会”,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真实。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我们的作者应当敢于写生活,敢于说真话”(参见剑雪:《努力描写我们时代的青年——本刊召开青年题材剧本创作座谈会》,《剧本》1979年6月号)。1980年,中国戏剧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协会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讨论“写真实”问题,一致认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文艺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反映生活”(参见剧本创作座谈会办公室整理:《剧本创作座谈会情况简述》,《文艺报》1980年第4期)。同时,《人民戏剧》、《戏剧艺术》、《文艺报》、《剧本》、《戏剧学习》等刊物也连续刊发了一系列相关论文、评论和文章。 ③彼时彼刻涌现出的问题剧主要如下:《报春花》、《未来在召唤》、《权与法》、《救救她》、《假如我是真的》等暴露社会黑暗的剧作,《丹心谱》、《于无声处》等反应“文革”灾难的剧作,《曙光》、《陈毅出山》等为人申冤、批判历史的剧作。参阅胡星亮:当代中外比较戏剧史论(1949-200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242页。 ④参见《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2000级本科班实习演出剧目、导演系博士生毕业研究剧目》,网址〈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Drama/18352?p=1〉. ⑤参见《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2000级本科班实习演出剧目、导演系博士生毕业研究剧目》,网址〈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Drama/18352?p=1〉. ⑥2009年5月18-21日,由中国教育部体育卫生艺术司和亚洲戏剧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届亚洲戏剧教育研究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来自12个国家26所院校的72位专家学者围绕“戏剧现状、戏剧教育与戏剧未来”主题进行研讨。期间,中国中央戏剧学院、印度国立戏剧学院、蒙古文化艺术大学、韩国中央大学演出了四台戏剧,其中即有万比洛夫的《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参阅刘晓村:第四届亚洲戏剧教育研究国际论坛简讯[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⑦比如1980-1990年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前线话剧团曾上演过万比洛夫的作品;2006年,复旦剧社曾剧演过《六月的离别》;2012年,天津曹禺剧院于上演过《与天使在一起的二十分钟》等。参阅顾宙寅:新时期万比洛夫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J]//剧作家,2014年第1期,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