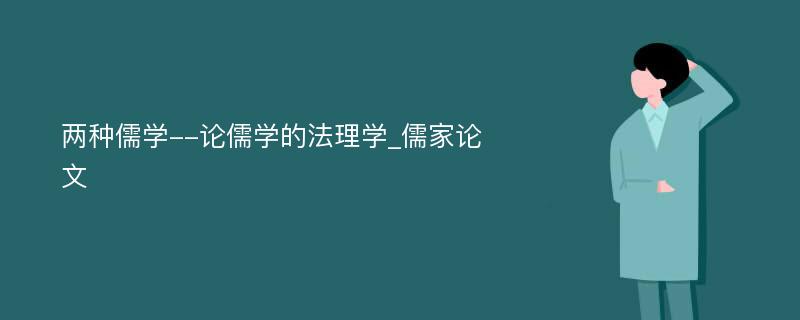
两个儒家——谈儒家的法家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法家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按照现代解释学的观点,任何古代文献的意义都是一定解释的产物,都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种所谓“视界交融”活动的结果。就此而言,在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研究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着绝对意义的“原典”,真正的“回归原典”只不过是思想家的一种天真的一厢情愿。任何所谓的“原典”,作为一定时代的一定解释者的解释的产物,都具有具体性、历史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对于中国古代儒家学说来说亦同样。对于儒家学说的把握,由于解释者所处的不同时代和不同立场而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见仁见智的不同观点。早在孔子的时代就有所谓“君子儒”与“小人儒”之派生,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孟子儒与荀子儒之双峰,宋明时期又产生了理学儒与心学儒之对垒,降至清代又为我们推出了汉学儒与宋学儒之争雄。而孔子的形象亦由于对其解释的大相径庭而呈现出种种不同面孔,在中国历史上有孟子的“民贵君轻”的孔子,有董仲舒的“君尊臣卑”的孔子;有朱子的“性即理”的孔子,有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孔子;有古文经学派的“述而不作”的孔子,有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的孔子。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就是面目各异的孔子脸谱的不断推出的历史。我们对儒学的了解愈深入,儒学自身所表现出的这种歧出也就愈深刻,愈丰富。
因此,在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中,把儒学简单地视为一种单一固定的学说模式不惟违背了解释学的原则,亦不忠实于儒学的历史本来面目。依现代语义学的观点来看,它实际上是犯了用共名取代殊名、用抽象取代具体这种语言学错误。所以,为了还儒学的本来面目,我们就必须在儒学的研究中力求做到用具体的分析取代抽象的分析,用生动的、多元的“儒学史”的研究取代僵硬的、一元的“儒学原理”的研究。借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话来说,儒学之真正经典,并非存在于一部最古老的历史文献里,而只能在时移世易的历史流变中去探求和发现。
二
一旦我们使自己置身于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就会发现在我们面前呈现出立意不同、风格迥异的两个儒家:早期的儒家与晚出的儒家,在先秦的诸子争鸣中代表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的呼声的儒家,与自由争鸣之风已告正寝、中国已进入思想专制时代的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
早期儒家是以孔子、孟子为其人物代表,以人道主义的“道统”为其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受胎于周礼的儒家所谓“仁学”理论正是这种“道统”思想发展的最高形式,而旨在一种双向的、平等交往的社会关系的确立可看作该“仁学”理论的真实内核。我们看到,也正是从这一仁学理论之中,由内及外地层层推出了儒家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科学原则。例如,强调“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的所谓“以情絜情”的心理学原则,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所谓“爱人”、“敬人”的伦理学原则,主张“中心悦而诚服”的“以德服人”而反对滥用武力、刑杀的“以力服人”的所谓“为政以德”的政治学原则。这最终使早期儒家逻辑地导向了一种极为早熟的民本主义的社会学说,孟子所公开宣布的“民贵君轻”的政治纲领堪称其代表,而明末清初黄宗羲对君本论的彻底清算以及王船山虚君共和思想的明确提出则是其逻辑发展的最后成果。这种早熟的民本主义学说既是对周人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思想的传接与承续,又是受当时风头正劲的以“霸”易“王”的时代风气所激而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强权政治思想的最早抗议。
与之不同,晚出的儒家则是以董仲舒和业已被官方化的程、朱为其人物代表,以专制主义的“君统”为其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与早期的儒家学说相比,在晚出的儒家学说里,其双向的、平等交往的“仁学”思想已大为退色,相反,鼓吹单向的、强制服从的“纪纲”思想却明显增强。众所周知的汉儒的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的推出正是这一儒家思想转向的有力反映。实际上,在这种“三纲说”中,“君纲”是其纲中之纲,而董仲舒对于这种至高无上的“君纲”的鼓吹,不惟开儒学议论之先,而且其观点中所表现出的奴颜与媚骨,也使所有的后儒难以望其项背。其在《春秋繁露》中不无肉麻地写道:
春秋之义,臣有恶,君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唯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
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
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恃变化之势,……天地、人主,一也。功出于臣,名归于君。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要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
在这里,早期儒家的“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君臣相须”演变为“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的“君尊臣卑”,早期儒家的“得乎五民而为天子”的“民贵君轻”演变为“君之所好,民必从之”的“君令民从”。尽管董仲舒在其学说里也提出“仁,天心”[①a],“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②a],提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残害民者,天夺之”[③a]等等观点,企图以儒家的仁学理论结构制约君的一意孤行,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其学说移情别恋的性质,毋宁说董仲舒已成为中国古代新权威主义的代言人,其新儒学的理论重心早已偏离早期儒学的轨道,心系于“君”而非“民”了。
我们看到,这种儒学本质的异化不仅体现在一代“新儒宗”董仲舒的理论里,而且也体现在后世很多被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中。其中,作为明清两代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就是显证。沿着董仲舒所开辟、所规定的这一儒学的辩护主义的思想方向,程朱理学对“君本”的护卫同样矢志不渝和不遗余力。如程子称“君道即天道也”[④a],“君德即天德也”[⑤a],“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专其?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⑥a];朱子称“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⑦a],“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其各得其宜,则甚和也。”[⑧a]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程朱对于汉儒的“君本”思想既有师承又有所发明。这种发明表现在,其不仅通过一种“泛理主义”进一步强化了董仲舒“君尊臣卑”、“君令民从”的宇宙论根据,而且把这种“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的“天理”更加天人无间地改造为人的伦理,从一种外在的强制性命令内化为一种道德的自律。这种对董仲舒学说的“准康德式”的改造,毋宁说标志着中国古代君本主义传统最终的理论完成。而明清两代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加强,实际上也正是得益于这一业已完善的深厚的理论背景的。
三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晚出的以专制主义君统为其主要内容的儒家,是一种人们所称的“援法于儒”的“法家化的儒家”。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从法家学说的专制主义实质谈起。
溯其本源,法家的专制主义政治思想滥觞于其所谓“性恶论”这一人性理论的提出。这种“性恶论”是由荀子率先创立,而最终集大成于韩非的人性论学说里。如果说荀子在其学说里尽管坚持“性恶”但又提出“化性起伪”,尚给人的善的可能留有一定余地的话,那么韩非则沿着“性恶论”的方向愈走愈远,最终把这种中国古代的反映人性黑暗面的人性说推向了极致。
在韩非看来,“皆挟自为心”、“以利之为心”是人性的唯一选择,是支配一切社会关系的绝对准则。翻开韩非的著作,所谓“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①b];所谓“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②b];所谓“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③b],这些充斥于全书中的对人类隐私的种种深刻的揭露,无一不是旨在张扬性恶论这种人性论。一部《韩非子》,毋宁说已成为人类黑暗的动物本性的记实之作。
其实,韩非子如此苦心孤诣地执著于人性的探幽阐微,并非出于学术之雅兴,而正如其《问辩》篇中“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一语所表明的那样,是完全急功近利地服务于现实社会政治之需要的。因此,正如孟子提出以恻隐之心为内容的“性善论”是为其平等交往的民本主义的“王道说”张目一样,韩非子对基于自私之欲的“性恶论”的孤明先发不过是向人们论证弱肉强食的政治法则之必要,从而最终为其心往神仪的君本主义的“霸道说”辟路开道。在谈到这种人性与治道之间的微妙关系时,韩非子曾用心良苦地为读者讲述了一个“秦襄王病,百姓为之祷”的故事,并借用秦襄王的话写道:
王曰:子何故不知于此?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吾释势与民相收,若是,吾适不爱而民因不为我用也,故遂绝爱道也[④b]
在韩非子看来,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切所谓的爱实际上都是受利驱使的。百姓之所以服侍于君主,并非爱他之心使然,而不过是利己之心所致。因此,势与利完全是异名同谓的,人之“趋利避害”必然也就“趋炎附势”。于是,正如西方马基雅弗利从人之自私自利、贪生畏死的本质中得出君主要象狮子一样的“以兽治兽”的政治学法则,霍布斯从“象狼一样”的自然状态的人性中得出专制政体之必然性一样,韩非子亦从“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⑤b]这一性恶说中为我们堂而皇之地推出了法家铁腕的势治政治理论。
也正是从这种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的势治理论出发,一方面,韩非对上断然主张用法家的强权政治取代儒家的“贤人当政”,其提出“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⑥b]另一方面,他对下师承商鞅的“民不贵学问”的思想,而对周礼的“天视民视”、“天听民听”观点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其提出“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①c]
同时,也正是从这种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的势治理论出发,韩非子成为中国古代君主权势的最为卖力的鼓吹者与辩护士。他提出“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②c],把权势视为“胜众之资”,苦口婆心地要求统治者象对待自己生命一样看护好自己的权势,即所谓“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③c],即所谓“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④c]。而这种“有权就有了一切”的权势决定论观点的提出,必然使韩非子醉心于一种高度集权的社会政治理论。故在韩非子著作里,反对“权借”而主张专政,反对政治容忍而主张“明君贵独断之容”就成为其势治理论的中心内容。其提出“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⑤c],“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⑥c]。提出“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⑦c]等等。而考之中国历史,历代专制君主们对于这一独裁说无不虔敬地奉为至理要道,而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兔死狗烹、阉宦当政、避讳、文字狱等等政治奇观和社会异行,不正都是其对韩学的烂熟于心的发明和深造吗?
因此,通观韩非子的著作,其学说从一种极端的性恶说最终落脚于一种赤裸裸的君主专制的社会理论。尽管韩非子的这种学说被人冠以所谓“法家”的美称,尽管其不仅强调“处势”亦力倡”抱法”,但是这种所谓的“法”充其量不过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一种新型武器,一种与“术”的“阴谋”互为发明的“阳谋”,其法治学说中所谓的“法不阿贵”[⑧c]、“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⑨c]等等捍卫法的尊严的呼声,最终被埋葬于“非法之法”的君主的纵横捭阖的个人意志之中。这种所谓的“法治”不惟与建立在人格尊重基础上的现代文明社会的法治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恰恰体现了一种对其的顽固的反动。它与其被人们称之为“法治”,不如说是一种以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为其真实内容的地地道道“兽治”的代称。
韩非子的这种极端专制的君统思想的出现,是与当时中国历史的社会现实紧密呼应的。它是春秋战国之际脉脉温情的“王道”式微而“霸道”恶性膨胀的理论写照,代表了正在崛起的社会新贵和日益暴发的政治赌徒对权力的贪婪的渴求。难怪一代枭雄秦始皇读《五蠹》时有“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一英雄相见恨晚之感叹。实际上,韩非不仅被秦奉为座上宾,而且秦始皇的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和政治举措都可视为是由其一手设计和制定的。秦始皇的“武力兼并”的对外政策不过是对韩非的“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的“力可以王”[⑩c]的思想的兑现,秦始皇的“偶语弃市”、“焚书坑儒”的社会举措不过是对韩非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11)c]的思想的推行,而秦始皇以“朕”自居,登极“帝”位亦可以在韩非的“明君贵独断之容”思想里找到其初衷。所以,尽管韩非已成为秦的专制政治迫害下的屈鬼,但其幽灵却借尸还魂地始终附身于秦始皇身上,附身于以后的历代专制主义君主身上而成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君统传统的坚强的精神依凭。
故而,正本而清源,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君统思想实溯自为韩非所集其大成的法家。而把这种思想归咎于先秦的儒家,完全是对该儒家学说的一种误读。实际上,儒家学说中的专制主义思想并非儒家之固有和独创,而是后儒们“援法于儒”、“糅法于儒”的结果,是一种“后韩非思想”在汉代儒学中的复活。深稽后期儒家学说中的诸种专制主义的观点,人们就会发现,无论其内容还是其表述都是法家版的。例如,被视为是汉儒独创的“三纲说”,正如很多人已指出的那样,其最初源自韩非的“三顺说”。《韩非子·忠孝》篇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与其同期《吕氏春秋·恃君览》篇里亦有类似的表述,其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而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的思想,更是与《韩非子·主道》篇中所谓“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等等论点几乎如出一辙。
四
如果我们一旦把“援法于儒”、把儒家的法家化作为一种思想事实予以承认,我们实际上就不能不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这种儒家法家化的现象,造成儒家法家化的原因又是什么?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就不能不回到导致儒家法家化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问题上来。依据解释学的观点,一定的思想文化现象都是解释者根据自身的需要解释的结果。然而,人们又必须看到,这种解释者的自身的需要实质上又是非解释地受其所处时代的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严格制约的。儒家法家化的现象最早出现于中国的汉代。虽然汉代社会的兴起是对暴秦的取而代之,但这种取代却完全是通过一种“以暴易暴”的方式完成的。而暴力既是新社会的摇篮,又是新社会的坟墓,一个完全求助于暴力产生的社会,其也必然使自身屈从于武夫哲学的支配。因此,正如史家所公认的那样,“汉承秦制”,汉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依然是对秦制的忠实的因袭,其政体不过是对秦的以强大武力为后盾的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的继续。所不同的是,赢姓皇帝换成了刘姓皇帝。《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汉书·杜周传》云:“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故在汉代,皇帝的意志即为法律,汉人对专制君统之奉若神明与秦实际上别无二致。对于这一点,汉代统治者们自己亦是不打自供的。这种自供除可见之于汉高祖“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这一志得意满的赤裸裸的“家天下”的表白,还体现在儒学已被“定于一尊”多年后汉代皇帝的耳提面命的家训里。《汉书·元帝本纪》曾记载了元帝为太子时与其父宣帝的一段对白,从中可看出当时汉政权的实质: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盍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因此,正是这种在现实政治中对“周政”的背离和对秦的“霸道”的继续坚持,决定了汉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般面貌与性质,决定了汉代的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与以“礼治”、“德教”社会为其存在依托的早期儒家之间的截然异趣,也即决定了其对法家学说的历史继承以及其儒家学说的法家化的必然趋势。故思想意识上的专制主义实际上是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专制主义为其原型的,其既非可以用所谓“民族心理”的劣根性这种纯粹的唯心论观点所能解释,又非可以用所谓的“移孝于忠”的移情作用这种纯粹的唯情论观点所能说明的[①d]。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汉代的儒家的法家化过程实际上是通过两方面的工作来展开和进行的。一方面,它体现为在理论路线上改造早期儒家学说的内容,使其成为维护君统政治的护符与工具。这即所谓的“以经术润饰吏事”、“以圣经为缘饰淫刑之具”的社会行为在汉代的风靡。于是,经汉人的学术阉割,本是“相接以敬让”的儒家的礼在叔孙通手中一变为使沐猴而冠的刘邦“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的君臣气象迥异的朝仪,本是爱人、敬人的儒家的仁在董仲舒手里一变为以上凌下、以尊责卑的一人独裁的“纲”与“纪”。另一方面,这种汉代的儒家的法家化过程还体现为在组织路线上把儒家知识分子纳入现政权体系,使其由“守死善道”的社会中的独立的议政力量被改造为为一己之私的君统统治袒卫的护士。被人称为以“与时变化”和“曲学阿世”为能事的汉儒公孙弘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汉书·儒林传》言其不仅被“封侯拜相”,而且因此被“天下学士靡然乡风”而成为一代“汉家儒宗”。这种对儒家知识分子的“赎买”和儒家知识分子自身卖身求荣地对现政权的人身依附,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的士官一体、政教合一的社会政策颁布以及隋唐科举制度正式确立后更是被进一步地强化和巩固。
这样,这种汉代统治者对儒家的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双管齐下的改造,最终促使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儒家与现政权“一体化”,也即儒家的法家化过程的完成。这一兵不血刃的演变过程在汉代的完成,有力地向人们说明了社会存在之于社会意识所具有的极其巨大的决定作用。因此,虽然这种与现政权“一体化”的法家化的儒家依然还保留着儒家的名分,还给予传统儒学的“道统”以一定的思想地位,但实际上这种对传统儒学的容忍毋宁说已成为一种现代西方哲学家马尔库塞所谓的“镇压的容忍”。这种“镇压的容忍”使儒家所追求的“道统”的超越性永远不出君主专制的窠臼,恰如现代西方代议制的民主自由始终难以逾越资本专政之范围。
五
事实上,社会的思想文化的演义变化不仅受制于作为其现实生活基础的一定的社会存在,而且亦受制于其自身所具备的一定的理论条件。因此,汉代社会儒家法家化现象的出现,除由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决定外,还与当时思想文化的理论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汉儒们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儒法两家先期的理论成果的反思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将二者加以互补和结合的产物。
众所周知,就其实质而言,先秦时期的儒家道统文化是一种源自中国古老的礼治传统的高度道德化的文化。其旨在“反求诸己”、“深造自得”的内倾型的文化路线固然使儒家避免了“见用忘体”的“非人称化”的弊端,但这种注重“心传”、“情絜”的社会文化相对来说却缺乏现实的参照和客观载体的坚强支持,缺乏政治组织和社会制度建设的有力保障而易于人为地流失和歪曲[①e]。在中国古代礼治政治体系崩溃、社会由治世转入乱时世这一缺陷尤为明显和突出。然而儒家文化这一不足,却恰恰是法家文化的长处和优势。法家所提出的建立强有力的君主权势以及社会控制机制的主张,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对儒家文化的补漏纠偏。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争峰中儒家一方之所以始终处于下风,以致于以秦为代表的坚持法家路线的国家最终在政治角逐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其中固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因素可资说明,但就思想文化本身而言,儒家学说自身亦不能全辞其咎。这一儒家文化自身的局限和不足,不仅为先秦法家所无情揭露,也成为汉儒们的理论共识。故援法于儒,用法家思想补充儒家思想已成为汉代新儒家运动的不可避免的理论趋势。
但实际上,汉代的新儒家运动既是援法于儒而对法家学说内容的大量吸收,同时又是援儒于法而不乏对儒家思想因素的利用。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一种重体轻用的文化的话,那么法家文化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有用无体的文化。这种文化对君主权势的无上膜拜和对社会的强制性控制手段的过分迷信,导致了其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心理基础的极度漠视,使其最终流于一种“专决于名而失人情”的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理论。这种理论的反动性质在秦政权的迅速败亡之中得到有力的验证。同时,“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也正是从这种法家“君统”文化的物极必反之中,儒家的以“仁学”为其核心的道统文化开始显示出其理论的优越性。于是,对法家思想予以理论弹正和重新认识,吸收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在坚持法家的“力可以王”的同时兼顾儒家的“保民而王”的主张,宗守法家的严刑峻法又不失对儒家的“复古更化”的鼓倡,就不能不成为汉代新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故汉代“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推出既是一种“文化缘饰”,但又远非用单纯的“缘饰”作用所能概括和说明的,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逻辑理论背景的。
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儒法文化的合题,一个法家的政治的“君统”和儒家的道德的“道统”的杂交的混合体。它是一个以法家的“君统”为其根本、以儒家的“道统”为其辅助的体用颠倒的混合体。而人间至高无上的皇帝则成为这一文化合体的完美的化身,其既“作之君”地是社会最高权威的体现,又“作之师”地成为人们心目中至为神圣的圣人。故自汉开始中国历代皇帝无不一身而二任:一方面用法家的理论继续维护君统统治,一方面又用儒家的理论缓冲尖锐对立的人际关系;一方面坚持秦制专任酷吏,一方面又师承周孔侈谈道德仁义。这即汉宣帝所谓的“霸道”与“王道”的互糅相杂,也即中国历史上最具“中国特色”的所谓“经史断事”、“春秋断狱”的创举的推出。它是为汉代统治者所首倡,为汉代曲学阿世的知识分子所苦心发明的一种恩威并施的新社会政策。在这里,无论是法家的“大棒”还是儒家的“胡萝卜”都万变不离其宗地服务于绝对的君主统治。而二者中尤其后者更为聪明的君主们所垂青,因为它能使势的威慑内化为心的臣服,使君主们不假外力地坐收渔翁之利。后者的这种特有的社会功能,借用清人戴震的形象化比喻即所谓的“以理杀人”。戴震写道: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①f]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贵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②f]
这些如泣如诉的话语,不仅是对“后儒”助纣为虐行径的愤怒的抗议,而且不也正是对中国古代儒法合流的黑暗的文化本质的一针见血的揭露吗?
六
这种法家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也即人们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外儒内法”、“阳儒阴法”的文化现象。就其法家实质而言,它与其说是儒家的法家化,倒不如说是法家的儒家化更为贴切。实际上,关于后世儒家业已被偷梁换柱的这一事实,在中国历史上早已被众多思想家所揭破。宋人朱熹曾极不客气地指出,“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并宣称“千五百年之间,……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③f]明人黄宗羲在“藏天下于天下者”的“三代之法”与“藏天下于筐箧者”的“后世之法”之间作出区别后,对于中国历史亦有“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④f]这一深刻之总结。而对于儒家的名存而实亡的现象,清人谭嗣同的批判更是出语不逊,言词激昂,其称“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相交相资,而罔不托于孔。执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⑤f]这一评论,不仅是对后世儒家的法家实质的体无完肤的揭露,而且实际上亦可看作中国历史上最早清算法家化儒家的先鸣之声。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确乎存在着两个儒家,即一个早期的民本主义的“道统”的儒家,和一个晚出的官本主义的“君统”的儒家。当然,我们在看到二者对立的同时亦要承认二者之部分的同一,在重视儒学历史之中断的同时亦不能忽视其前后一定程度的续承。虽然后世统治者祭出儒家的旗帜从根本上说是出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之目的,但手段一旦成为目的之手段,其就不仅受制于目的而又可以积极作用于目的:儒家的文化一旦被“定于一尊”地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就不仅服从统治者的意志而同时又成为对统治者自身的一种必要的规定。尽管这种规定主要是在道德层面而非政治层面上进行的,尽管这种规定对于专制君主统治的地位根本不可能有所撼动,然而它却可以通过一种“文化驯服”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君主的行为,消解和弱化强权政治的恶性发展而使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在一定时期具有和保持着一种温和的色彩和特性。而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少的所谓“开明君主”的出现正可为之佐证。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的晚出的儒家意识形态既是“外儒内法”的,又是儒法互为里表的;既是法为体儒为用的,又是儒法互为体用的。这种儒与法的相互淹贯错综,使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真实面目更加扑朔迷离,也使后人们对真儒学与伪儒学加以区分的工作更加困难重重。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而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两个儒家这一事实,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而否认对二者加以理论区分的必要性。恰恰相反,对中国历史上两个儒家这一事实的承认,对二者加以理论的区分,不仅是对历史上中国文化客观原貌的一种真正的澄清,而且亦对今天的文化批判、继承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人们进一步深化了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两重性问题的认识。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以“道统”为其主要内容的早期儒家,而正是这种道统主义的儒家代表了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积极的一翼。其对平等互敬的道德原则的倡导,其对“民贵君轻”的政治准则之呼吁,使其不仅成为中国历代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旗帜,而且也应成为我们今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与课题。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作为其对立面亦存在着一个以“君统”为其主要内容的晚出的儒家,而正是这种君统主义的儒家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中最黑暗的东西。其对人间尊卑秩序的“纲常”、“名教”的鼓吹,其对不可触犯、顺昌逆亡的君主“逆鳞”之护翼,使其不仅成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有力的思想工具,而且作为一种沉重的历史积习,也使其成为现代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巨大羁绊。
因此,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现象,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在这种具体分析中,区分出儒学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从而最终实现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历史与今天的接轨。我们相信,正如西方近代人通过对基督教文明的重新解释而去伪存真,发现其内涵的现代意义一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将通过对古老的儒学的重新解释而革故鼎新,再现中国文化的日新精神。
注释:
①a 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②a 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③a 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④a 《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
⑤a 同上。
⑥a 《周易程氏传》卷第一。
⑦a 《朱子语类》卷二四。
⑧a 同上书,卷六八。
①b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②b 《韩非子·备内》。
③b 《韩非子·孤愤》。
④b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⑤b 《韩非子·难二》。
⑥b 《韩非子·功名》。
①c 《韩非子·显学》。
②c 《韩非子·难三》。
③c 《韩非子·喻老》。
④c 《韩非子·心度》。
⑤c 《韩非子·爱臣》。
⑥c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⑦c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⑧c 《韩非子·有度》。
⑨c 同上。
⑩c 《韩非子·显学》。
(11)c 《韩非子·五蠹》。
①d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中,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中国古代专制思想是中国古代宗法思想的进一步的逻辑发展,是一种“移孝于忠”的产物,君主崇拜不过是所谓父亲崇拜的一种变式。实际上,尽管“移孝于忠”是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服务的一重要文化方式,但“孝”与“忠”不仅分属不同文化范畴,而且在价值取向上甚至往往表现为尖锐的对立,故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本质上的必然联系。所以我们看到,注重宗法、亲亲的周代社会并没有因此而走向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同样,鼓吹孝悌为仁本的孔孟学说不仅也没有因此导向一种君本的专制理论,而且还恰恰相反地从孝悌原则走向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原则,从而最终走向一种民本主义的理论。
①e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内倾型文化路线的局限性不仅表现在其“重德”而“轻刑”上,而且还进一步表现在由此出发其把“内圣”与“外王”不加过渡地简单地混为一谈,把“德治”理想最终寄希望于英明仁慈的君主身上。如孔子对尧、周公等古圣王的热情称颂,孟子“一正君而国定”等等社会思想都表明了这一点。尽管儒家理想中的君主是“先王”而非“后王”,是“开明”的而非“专制”的,但这种理想化的“人治”思想实际上已经为法家的“君统说”作了铺垫。它使法家可以从容地接过儒家的旗号,在“王”的形式上塞进“霸”的内容,最终实现其用“君统”取代“道统”这一文化演变。
①f 《戴震集·与某书》。
②f 《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上》。
③f 《朱文公文集》卷三六,“答陈同甫”。
④f 《明夷待访录·原法》。
⑤f 谭嗣同:《仁学·界说》。
标签:儒家论文; 法家论文; 董仲舒论文; 国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韩非论文; 孔子论文; 君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