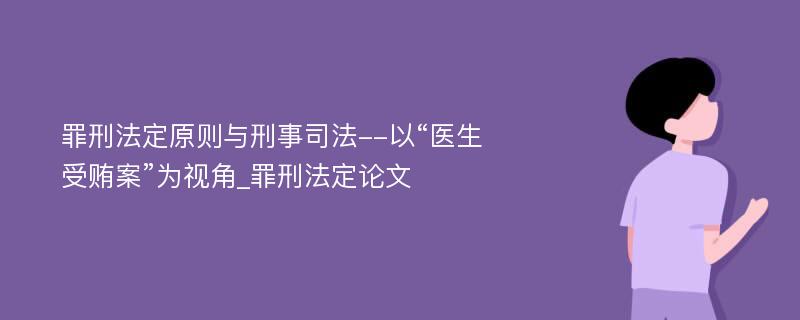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以“医生受贿案”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受贿案论文,刑法论文,视角论文,司法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27-2663(2005)04-0050-04
一、引子
医生收受回扣,可谓屡见不鲜:湖南邵东县100多名医生收受回扣事件,浙江瑞安市人民医院40多名医生收受百万元回扣事件,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2005年福建省福鼎市某国有医院医师华某、孙某、何某因收受药商回扣,被该市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再一次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法院审理查明:华某、孙某、何某身为国有医院医师,利用职务便利,大量开出药商事先承诺给予回扣的药品给患者使用,从中收受药商给予的药品回扣款,回扣金额分别达2.6万元、2.5万元、1.2万元。福鼎市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系国家公益性事业单位医生,从事医疗、预防、保健等国家公益活动,属国有事业单位从事公务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被告人客观上实施了利用给患者配药、施药的处方权而收受药商给予的回扣,符合受贿罪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权钱交易的特征①。
医生收受药商回扣的事件,在我国可谓公开的秘密。在某些医院,医生的这种行为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回扣已经成了一些医生的主要收入。人们在感叹世风日下、医德滑坡的同时,对医生的行为束手无策,找不到遏制的对策。这个案件的审理,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引入刑罚手段对国有医院的医生收受回扣的行为进行惩罚。从该案的第一审结果来看,有许多的叫好之声,甚至一些法学界人士也发表评论,认为该案的审理对今后同类案件的审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案已随第一审法院法棰的落下而告一段落,然而,我们对一审法院的裁判似乎没有理由欢欣鼓舞,鼓掌喝彩。诚然,医生利用给患者配药、施药的处方权而收受药商给予的回扣,在患者已经饱受病痛折磨的痛苦上,还对其进行经济上的欺诈与剥夺,不啻趁火打劫,其行可憎,其人可鄙,有辱白衣天使的美好声誉。但当我们运用刑罚的手段进行规制惩罚的同时,我们就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理性地思考:以受贿罪对三名医生进行惩罚,有无刑法上的依据?或许笔者的思考不免于“至今已觉不新鲜”的老生常谈,但作为一个生活在大力倡导并努力建设法治文明的昌明时代的人,思考并表达自己的思考,也是生逢法治时代的责任。
二、刑法的尴尬
医生收受回扣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根据犯罪构成的理论,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可以从四个方面,即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以及犯罪客观方面进行考量。这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该种犯罪,舍一不可。
受贿罪的构成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一,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其二,受贿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索取他人财物与其职务上的便利有关而故意为之,或者明知他人给予自己财物是因为自己利用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予以收受;其三,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其四,犯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
本案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医生是否是受贿罪的适格的主体。令人遗憾的是,在现有的刑法框架里,笔者找不到医生是受贿罪主体的论据和有力论证,相反,从现有的法律规定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有医院的医生不是适格的受贿罪的主体。在这里,我们不必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进行繁琐的论证,仅从犯罪主体一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医生从事的不是公务活动,而是业务活动。
我国刑法将受贿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不难看出,《刑法》第93条着重强调了一点,不管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都必须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也是构成受贿罪的主体的实质要件。即便不是国有单位的人员,如果是受了委派,或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也“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虽然学界对公务的理解存在分歧,一般认为,公务是指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事务的活动。刑法意义上的公务,指国家性质的公务,具有职能性、管理性、强制性和隶属性四个特征。这种公务活动是行使国家权力或者公共权力,对国家和公共事务进行领导、组织、监督、主管等管理性的活动,对被管理者来说,有服从管理的法律义务。同时,这种公务行为是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管理活动,非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从事公务活动,必须受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的委派。
显然,医生为病人开处方的行为不具有刑法学上的公务行为的性质。医生依靠其医疗技术,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医生和病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医患双方是一种典型的民事关系。如果发生医疗事故,产生医患纠纷,患者提起的也只能是民事赔偿,而不是国家赔偿。医生对病人不具有任何强制权力。虽然医生的医嘱对于病人来说,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是基于病人对医生的信任,自愿接受医生的医疗服务而产生的。这种影响力,是不以强制手段为其后盾的,病人如果对医生失去了信任,医生无权强制病人接受其治疗。对于医生开具的处方,病人认为不合理,不愿意接受,医生也无权强制其接受,病人完全有权利另择良医,病人违反了医生的要求,并不要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其次,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并不必然是国家工作人员。法院的理由很简单,这三名医生是国有医院的医生,属于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医生从事的医疗、预防、保健活动是国家公益活动,因此,就认定其为国有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笔者认为,这样的推理是不合逻辑的,是对《刑法》第93条的超越,因为它混淆了公务活动和公益活动,国家工作人员和国有单位工作人员这两组不同的概念。上文已述,公务活动是有其确定的内涵和严格的范畴的,国家公益活动和公务活动是否重合,二者的内涵和外延是否完全一致,法院并未做进一步的解释。事实上,公益活动和公务活动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二者强行混同,其实是在偷换概念,对“从事公务”作了泛化的理解。我国1952年《惩治贪污条例》将受贿罪作为贪污罪的一种形式,并将此类犯罪的主体规定为“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刑法》第93条在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时,特别指出其从事公务的性质,而不是笼统地规定为工作人员,是有其深意的,其目的是为了廓清我国刑法以前对受贿罪规定的不足。
此外,法院在这个案件中使用了公益活动的概念,笔者认为大谬不然。何为公益,这本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身份意义上的划分,其含义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指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其目的是对不同的单位进行一种身份上的区分,以确定其相应的待遇。这种划分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有多大意义?现在许多国有医院纷纷进行改制,强调其不营利性质,未免有点底气不足。法院在这里强调医生工作的公益性,其实反映了法院在处理医生收受回扣这个案件上的无奈。
再次,把医生当做国家工作人员,必将造成理论和实践的混乱,使法律的规定名存实亡。一方面,如果医生收受药商的回扣构成受贿罪,意味着实践中把国有医院的医生纳入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那么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礼品,也应当构成受贿罪。不可能在收受药商的回扣时国有医院的医生是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而在收受病人的礼金时,其身份又变成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国有医院的医生成了国家工作人员,那么,性质与之相似的公办学校的教师,也应当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当公办学校的教师接受学生或家长的礼品时,只要达到一定的数额,也应当构成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这势必在司法实践中推翻《刑法》第93条关于受贿罪中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把“国家工作人员”实际上变成了“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规定完全成了赘文,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医生的行为不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当然不能以受贿罪定罪科刑,那么能否以其他罪名进行惩罚?要考量医生收受回扣行为是否具备了刑法上的当罚性,最直接的方法是在我国现有刑法中寻找与医生收受回扣行为相类似的而刑法将其纳入调整范畴的行为,并将其与医生收受回扣的行为进行比较。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中,与医生收受回扣行为较具有可比性的,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刑法》第163条中规定:“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便利,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首先要弄明白一个问题,即医生是否有职务上的便利。医生固然不直接决定医院的进药,但由于医生有处方权,如果某类药品,医生不开给病人,则该类药品是无法销售出去的,当然影响了医院对该类药品的采购,可以说,医生通过决定药品销售的方式间接决定了医院药品的采购。因此,认为医生具有职务上的便利,是没有疑义的。必须明确的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中非从事公务的人员。我国的国有医院属于事业单位,与公司、企业的性质是不同的,因此,国有医院的医生虽然不是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但不同于国有公司、企业中非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在定罪科刑上也不能参照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来处理。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同样没有从事公务,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便利,达到较大的数额的行为,如果是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构成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如果是国有事业单位中非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刑法却对其束手无策。仅仅因其所属单位不同,在刑法上却产生截然不同的法律效果,这不能不说是刑法的尴尬。
刑法的疲软无力的原因是因为医生有了一把特殊的保护伞,即国有事业单位非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以受贿罪处罚,则失之不公,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则失之不明。造成刑法尴尬的原因是我国刑法在惩治贿赂犯罪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我国刑法在贿赂犯罪的规定中,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中,漏掉了国有机关、事业单位中非从事公务活动的一类群体。公司、企业人员收受贿赂罪并不以从事公务为要件,而国有机关、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因其单位的性质,决定其不可能成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而其工作本身不具有从事公务的特点,也决定了其不能成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刑法将其关在自己的大门之外。贿赂犯罪立法上的疏漏为医生收受回扣的行为撑起了保护伞。
三、罪刑法定与刑事司法
“医生受贿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试金石。这个案件给司法人员出了一道难题,这道难题的难点不在对三名医生的行为如何定性,难点在于司法官员在民愤和法律之间,在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怎样寻找一个平衡点,在法的价值和社会需求之间如何维持平衡,一言以蔽之,即如何在具体的刑事司法中贯彻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1.不以情理害司法
情、理、法三者关系密切,却又各自独立,各有其严格的范畴。情反映的是民众的愿望、态度。“情”是立法的基础。法律的制定,要得于民心,顺乎民情,这样的法,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才能得到很好的遵守与施行。“理”的理解则比较多样,中国古代的“天理”,更多地体现了一种被统治阶级世俗化的政治伦理。今天所说的理,更主要的是指的一种合理性,是用来检验、指导立法科学的标准。这种“理”,有其内在的价值标准,必须体现对人的权利的尊重。需要明确的是,“情”和“理”对法的影响范围是有严格限制的,主要是在立法层面。在司法层面,要牢牢地贯彻司法独立的原则,这既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因此,司法官应尽可能独立地不受干扰地司法,以确保法律的执行尽可能少地受到人情的干涉。
2.正确看待法律的滞后性
法律滞后是正常的。“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1]法律的预见性总是有限的,因此,出现了法律没有预见的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事件,也就不足为怪。当一种事情已经在社会中出现,而现行法律对其并无规定,对这种事情司法上如何处理,应持什么态度,不仅仅是个案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罪名选择的问题,反映的是罪刑法定原则是否真正在刑事司法中得以确立。
承认法律的滞后性,对于真正在实践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具有极大的意义。罪刑法定的“法”,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制定法,这种法,不可能尽善尽美,必然有其局限性。即使存在种种不足,也应尊重其法律的权威,只能通过法定的程序才能进行修改。因为法治社会的刑法“追求刑法的形式合理性,将罪刑法定主义确认为刑法至高无上的原则,是刑法的内在生命”[2]。医生收受回扣行为,如果单纯从医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其危害性比之公司、企业人员收受贿赂,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刑法手段来进行惩罚,有其社会意义,也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但这样绕过刑法,直接追求实质合理性,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将剥夺法律的尊严,使法律变成舆论的婢女。被剥夺了尊严的法律,既不能很好地保护人民,也不能很好地打击犯罪。当法律完全沦落为一种工具时,那是法律的不幸,也是国家和人民的不幸。甚至会出现为了达到保护社会的目的而牺牲人权的现象,正如功利主义刑罚论者所鼓吹的,“惩罚无辜者有时在实际上可以是正当的,例如,有时通过陷害一个无辜者可以避免一场大灾难”[3]。
因此,在现有刑法未进行修改或相关的司法解释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对医生以受贿罪定罪量刑,是不足取的。以牺牲一部基本法的威信为代价,得不偿失,极不经济。刑法立法上的疏漏,应该通过正当的程序来完善,切不可强制医生为刑法的疏漏买单。
3.摒弃刑罚万能的陈见,树立人权神圣的现代理念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罚万能的陈见是不相容的。刑罚万能,对刑罚的推崇迷信,可谓由来以久,在世界各国都广泛存在。刑罚因其特别的严厉性、强制性,以及对违法者剥夺其权利带来的痛苦性,因此在运用刑法调整社会关系时,往往立竿见影,于是,刑罚的作用极易被人夸大,甚至惟刑是依。
然而我们更应看到,对刑罚的过度迷恋,必然会造成侵犯人权的后果。刑罚本身是一种恶,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带来秩序,但“由于刑法以特别严厉的方式损及受法律管辖的主体利益”[4],它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种代价是对人的权利的否定。虽然一般情况下,被刑法剥夺权利的人往往是犯罪的人,具有刑罚的该当性,但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来看,任何个体的损失也是整个社会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为刑罚表面的效果所迷惑,从而对刑罚过分依赖,势必扩大刑罚的打击对象。在具体案件中,务求深文周纳,动辄绳之以刑,甚至超越法律践踏法律,其结果必然是严重侵犯人权。我国“严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刑罚的崇拜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忽略。
罪刑法定原则与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血脉相连、互为表里的。尊重、保障人权是法治的基本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罪刑法定原则是尊重、保障人权的法治基本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化。罪刑法定原则的诞生,正是为了防止罪刑擅断,保障人权。对人权的尊重、保障,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社会文明程度愈低,人的权利愈不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反正,社会文明程度愈高,人的权利愈是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因此,树立人权神圣的理念,推进刑事法治化,真正确立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已成我国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刑事法律制度的改革,更是具有方向和价值目标的意义,是在刑法中真正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否则的话,罪刑法定原则永远不可能在中国刑法中得到真正的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永远不可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法治’永远是一个意义不大的漂亮标签”[5]。
收稿日期:2005-06-08
注释:
①参见《检察日报》第3918期电子版。网址:http://www.jcrb.com/nl/jcrb695/ca338353.htm。最后登录时间2005年3月20日。
标签:罪刑法定论文; 法律论文; 犯罪主体论文; 法律主体论文; 古代刑罚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时政论文; 受贿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