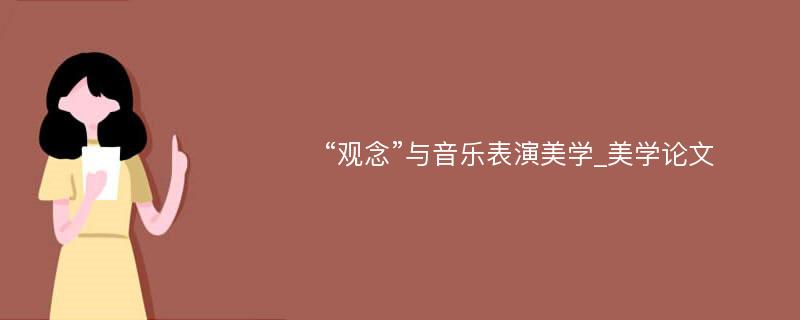
“意念”与音乐表演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念论文,美学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类别 音乐表演美学
“意念”(英语noetic,源自胡塞尔的术语noetisch,noese,具有意向作用、意向行为、意向过程的含义)是前卫派(Avant-Guard,即先锋派)音乐创作的核心概念,指的是音乐创作中的艺术独创性。意念与“意向作用”为同义语,它产生于现代,但在其强调艺术独创性这一点上却适用于任何时期的艺术活动,其中也包括音乐表演艺术。
现象学的“意念”
按胡塞尔,意识是由意向(Intention)与意向对象(noema)构成的。意向称为“内在主体”,意向对象称为“内在客体”亦即人对“外在客体”的印象。意向对象的意义是由人的意念即意向作用所“设定”的。
“有意义或‘在意义中有’某种东西,是一切意识的基本特性,因此意识不只是一般体验,而不如说是有意义的‘体验’,‘意向作用的’体验。”(胡塞尔《纯粹现象普通论》227页)这里说的“意义”正是由意念给与意向对象的意义。说这意义是由意念所“给与”的、所构成的、所设定的、所创造的,并无本质的区别。
“现象学的存在流具有一个质料层和一个意向作用层”(同上217页)。质料层对应于初级体验,意向作用层对应于高级体验。
在质料层,客体物的显现因素还是一种未定性的质素(hyle),在与主体构成对象性关系时,发生着客体物的“显现因素内容”向主体的视觉、触觉、听觉等等具有定性的“感觉内容”的转化运动。这一转化运动形成初级层次的体验即“感性的体验”。主体从客体物的显现因素获得“颜色感觉材料,触觉材料和声音材料这类‘感觉的内容’,我们将不再把它们与物的显现因素混同,如颜色性,粗糙性等等,它们借助于那些‘内容’‘显现于’体验中。”(同上214页)
高级层次的体验是“意向性的体验”即“意向作用的体验”。包括“感性的快乐感,痛苦感,痒感等等,当然还有‘冲动’范围内的感性因素。我们把这些具体的体验材料看作在包含更广的具体体验中的组成成分,后一种体验整个来说是意向性的;于是我们看到在那些感性因素之上有一个似乎是‘活跃化的’、给与意义的(或本质上涉及一种意义给与行为的)层次,具体的意向体验通过此层次从本身不具有任何意向性的感性材料中产生,”(同上214页)这包含着判断的意向作用的体验标志着意义的生成。
“我们必须仔细注意在具体的意向作用体验,具有其质素因素的体验和仅只作为意向作用综合物的纯意向作用之间的区别。”(同上251页)所谓“纯意向作用”,发生在以精神客体为对象时的体验之中。当我们面对艺术作品时,就处在“纯意向”的条件下。意义的产生虽也通过客体物所显现的感性因素,但是,客体物所显现的感性因素只是符号(不管是纸张上的墨迹材料还是音响感觉材料,都仅仅是符号或信号),是物质载体,符号或信号不等于它们所负载的信息,读小说和听音乐时的译码过程也就是“设定”意义的过程。与其说这意义是给与感性材料的,毋宁说是给与信息内容的。作为意向对象的信息内容就是意向性而非物质性的,这对象才是“纯意向性对象”。
我们还要把意向对象(noema)与对应意向对象(Gegennoema或译意向对应物)区别开来。意向对象存在于意识之中,对应意向对象则存在于意识之外。在面对物质对象时,它指的是主体意向所指向的现实生活中的客体物。在面对艺术作品时,它指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实有之客体物,而是指现实生活中实有的想象、体验等等与艺术作品中的思想感情感受之类相对应的东西。
胡塞尔学说的优点在于对意识的能动作用的阐发方面,胡塞尔学说的失误也正在于对意识的能动作用的夸大。胡塞尔把“意识”称为“内在的存在”。“内在的存在”无疑在如下的意义上是绝对的存在,即它在本质上不需要任何‘物’的存在。另一方面,超验‘物’(res)的世界是完全依存于意识的。”(同上134页)他断定意识主体是第一性的,物质客体是第二性的。茵加尔顿在《文学艺术的认识》中则写道:“认识过程不仅依靠认识主体的主观活动,而且依靠认识客体的性质。因为归根结底要由认识客体来确定什么是最适当的认识方式。”客体决定主体,这一修正是极其重要的。
胡塞尔说了意向对象的价值意义是由主体的意念所决定的,却没有说主体的价值追求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托夫勒在《科学和变化》中说:“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是嵌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难道艺术不也同样是嵌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吗?不正是主体与社会的现实关系制约着主体的价值追求吗?
前卫文化的“意念”正是这种主体为纯意向对象设定意义的“意念”。其中许多人追求“新、怪、曲、难”、“反传统”、“反功利性”、“重过程而不重结果”、“追求哲学性思维”等等。但是,也有人追求某种平易性、传统性、社会功利性和贴近现实生活。前卫文化到底追求什么呢?茅原在《未完成音乐美学》一书中曾说:“新、怪、曲、难,还只是现象。灾象的背后,有一个思想本质的基本点,那就是要求艺术自由,不受成规限制,要求打破一切束缚即突破‘框框’。正是这一基本追求决定着前卫文化的探索具有不断变化的开放性质。”这样就回答了为什么有些现代音乐家也会向传统性和社会功利性回归,在重视创作过程的同时也重视创作结果的问题。同时也阐明了他们的价值追求的社会性——追求艺术自由也是追求一种人权,它也是嵌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性系统。
“意念设定”与“同化适应”
根据皮亚杰的“同化”“适应”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就是主体的信息积累过程。主体的信息储存库很像一个分类储存书籍的“书架”,自身形成了一定的结构即“心理图式”。主体接收到信息时总是以自己的信息储存对新信息进行译码,并分类纳入原有的心理图式,这种对信息的主观理解就是主体对信息的“同化”。新信息又使原有的心理图式发生变化即调整,这也就是主体对新信息的“适应”。据此,皮亚杰把心理学的S(刺激)—R(反应)公式修改为:S(刺激)—A(同化)—R(反应)。三分法的公式比两分法的传统公式更符合实际。这正是有一千个演员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对象是一个,本身并无差异,差异就发生在“同化”的主体性上。
胡塞尔关于意念设定意向对象的学说,与皮亚杰的同化、适应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时又有重要的区别。
二者的相似性表现在:认识的发生有赖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客体物所提供的质素相当于S(刺激)项,意念的设定相当于A(同化)项,意向对象的结果相当于R(反应)项。意念对质素的组织作用即体现了同化与适应两个侧面。
二者的区别表现在:在胡塞尔那里,任何人都无条件地具有意念设定意向对象的能力,意念设定是无前提的。在皮亚杰那里,主体确定对象的意义的前提就是必要的信息储存,出生物性本能外,信息储存都是从学习中得来的,缺乏这一前提就根本谈不到什么设定能力。正如胡塞尔不学习哲学就不可能设定他的现象学一样。这证明皮亚杰的观点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意念在音乐表演艺术中的应用
音乐表演者是先于他的听众听见作品的人。他首先是一个听众或读者。如所周知,即使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作品的倾听与表演,也不可能每次都完全等同,每一次表演或倾听都是一次“重建”。
茵加尔顿在《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一书中,把“作品本身”与“审美客体”区分开来,分别占据“重建”过程的起点与终点。作品不等于“文本”,作品为主体提供“文本”,文本却只是该作品的基本特征的综合体,在“文本”中存在着许多“潜在的”“不定点”或“空白”,有待于主体去填补即具体化,这一创造性的参与活动也就是意念设定意向对象的活动。审美经验开始于听众的情绪体验受到音乐中某种属性感染的时刻。所谓“审美客体”正是经过意念具体化的产物。“作品”作为客体对象存在于主体的意识之外,它只有一个。“审美客体”则存在于主客体相互作用之中。对同一作品,有人说美,有人说不美,他们往往以为自己是在评价“作品本身”,实际上,他们所谈论的不过是自己对于“审美客体”的主观反应。
每一门学科都有历史积累下来的必要的资料,不学习历史资料就难于创造。但是历史资料是前人的意念“设定”的产物,无论如何,它不能代替自己的意念设定即创造。
古人有活法死法之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语活法矣。”([宋]吕本中《夏均文集序》)不知是者就只能是“死法”了。
学“法”,无非是学前人的经验与理论。对于前人来说,它们本来是活的适用于具体对象的有效之法。如果我把它们当做万应灵药,那么,在前人那里原来是活法的东西到了我们的手里就变成了死法。与其说这是活法与死法的区别,毋宁说是活用与死用的区别。死用往往发生于对前人的模仿行为中。模仿,就取消了我的创造,这样的表演是没有艺术生命的。我既不具备前人的信息储存,模仿只能等而下之。如海菲斯这样的演奏家,他有他的天才、修养和技巧。他能做得到的事,我不可能做到。邯郸学步,不但人家走路的本事没有学会,连自己走路的本事也将丢失殆尽。
所以,演奏家第一件事是读谱即首先自己在内心听觉中建构音乐。这才是以意念来“设定”意向对象,才真正是二度创作。
人们对音乐的要求决不限于仅仅是把作品创造出来——写出来和演奏出来,人们更要求这音乐中爆发出灵感的火花,这才是艺术中闪光的、最令人们喜爱的东西。在意念的创造中探索灵感发生的规律性,应该是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音乐创作和表演中的灵感必定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只有在潜意识发挥作用时,一切才都是自然的,就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表情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自然流露一样。人们越是有意识地要自己“做出”什么感情,这感情就表达得越不自然,这是事实。从表面上看好像理性控制与自然而然是矛盾的。
从“是即是是,否即是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来,好像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鸿沟是不存在的,意识与潜意识存在着相对的双向交流的规律性。其相对性表现在有些东西也永远不会再回到意识领域中来,但是,被忘却了的记忆会沉入潜意识,即储存于记忆储存库之中,遇到一定的相似性的信息刺激即所谓“相似块”,那些与之相关的潜意识中的信息储存就会重新以变了形的或者重新组合的姿态回到意识领域中来,这尽管是相对的,却是有规律可循的。
潜意识领域就是一个记忆储存库。人们能够往库里存入东西,也能够从库存中提取东西。这一存入和提取信息的活动,也就是识双向交流的过程。人们既可以有意识地积累记忆的库存量,也能有意识地即理性地设定“相似块”,以刺激、引导潜意识的库存重新活跃起来。艺术家的丰富的生活与艺术的积累就是对记忆储存库的“存入”,艺术家对艺术想象的设定,所设定的就是“相似块”。忘掉一切生活与艺术的积累,“忘记”即是储存行为,在忘记的背后,记忆就被存入库存,只记住“相似块”,就足以促成潜意识的重新活跃。这个“相似块”不是别的,就是艺术想象的浓缩物——很像教师为每堂课所准备的“教案”。意念设定的艺术想象自然能够控制操作,实际上,每个演奏家所奏出的音乐也只能是他的艺术想象的必然结果。
音乐表演是否具有艺术生命,关键在于艺术想象的质量。关于艺术想象怎样到位的讨论,就只能试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的另一专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