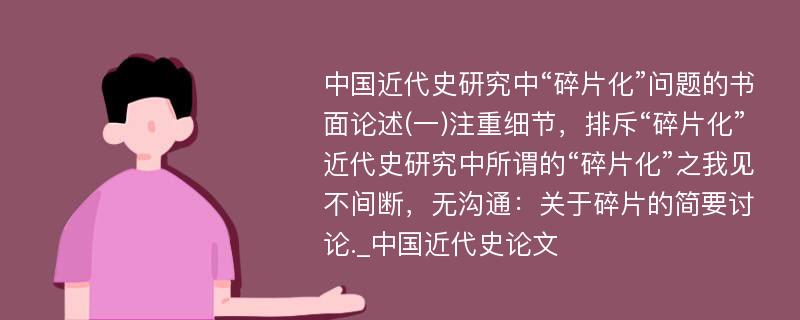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1.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2.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3.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4.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5.“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惑——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6.不必担忧“碎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碎片论文,史研究论文,笔谈论文,史学论文,我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研究原本就存在宏观、微观(或许还可加上两者之间的中观)的区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宏观研究也可以叫做系统研究或整体研究,着重对史事的全面陈述与把握,微观研究或可称为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着重史事的细节钩沉与精审考订。但宏观与微观都是相对而言,对于中国史来说,区域研究为微观;而对于某一省区来说,县以下的乡镇村落又属微观。再则宏观中有微观,微观中亦有宏观,相互交织,实际上很难截然区分。
学海无涯,史海更加无涯。作为个人的史学家,穷毕生之力,再勤奋也很难把握人类历史的整体,即使是从总体上把握一个国家历史(特别是像中国、印度、埃及这样的古老大国)也有很大难度。所以随着时代的进展与社会文明的繁复,便出现了断代史与区域史的分工合作。就学者个人而言,堪言宏观把握的大家越来越少,而精密于某一地区、某一断代、某一领域的专家则日渐增多。
史学离不开实证,实证必须以史料为基础。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展,仅以文字记载的史料数量激增而言,所谓“车载斗量”已不足以形容其万一。特别是近现代史,公私档案、报刊书籍乃至各类未刊文献之繁多,简直难以想象。这些客观条件,极其有利于个案研究,有利于从细节上再现历史情境,然而却大大增加了宏观把握的困难。同时,由于学术理念的进步,人们愈来愈重视社会史与群众史的研究,特别是下层群众的研究,而许多此类研究又属于起始阶段,这样也不免增加了研究视角“细化”的权重。
历史研究如果涵盖自然史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学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样,只有分工合作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史学研究的整体进步,因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于细节研究的重视,或所谓“细化”的提倡,自有其合理性,丝毫不必为此而感到忧虑。重要的是,学术研究的领军人物必须要有综览全局的战略思想,根据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力、物力资源的客观配置,合理地调整布局并顺其自然地给以正确诱导。
从学术评价角度来看,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无高下之分、优劣之别,关键是研究者自身的治学态度、功力与境界有所差异。过往的史学大家有些侧重于融通,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既有纵向的断代连贯,又有横向的归类阐析,对二十四史的基本史又滚瓜烂熟,然后成就其圆融顺畅。陈寅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举世无双,然而其研究每多属于专题,或一个人,或某现象,因小见大,考订精翔,论析自见高明,堪称寓宏观于微观的典范。何炳棣1979年冬与我初识即彻夜长谈清华学风,虽强调实证精审,但更重视“大归纳”的境界①,盖考证虽然入其深,“归纳”始可出其大。前辈学者以毕生经验传授后学,又有其成功业绩作为佐证,使我们这代学人受益匪浅而又自惭形秽。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运动,是前后连续的过程,然而无论是整体或过程,都是成千上万细节组成。或许可以说无细节即无历史;然而组成历史的细节毕竟有主次与层次之分,随意摭拾罗列的细节仍然难以重现真实的历史情景。宏观研究容许在他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概括,细节研究则必须以自己的实证工作为基础,而且要能进能出,因小见大,这才能形成真知灼见。
“碎片”一词,易生误解。或许可以说,我们所已知者无非是历史的一鳞半爪,往往都是组成历史的碎片,然而却不能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于日趋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的反弹,其成绩在于深刻的批判,然而其偏激者又流于消极的破坏,即走向极端的所谓“解构”。而袭其皮毛者又大多没有什么高见卓识,无非是当做“时髦”即兴仿效,把原本已清晰完整的历史撕裂成为碎片,然后又给以随心所欲的所谓“解构”,借以哗众取宠,自鸣得意。这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学术工作也流于商业化与娱乐化的可悲结果。
重视细节研究,同时拒绝“碎片化”。这就是我的一贯主张。
2010年冬,我曾参加中山市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论坛,会上确有学者提出辛亥革命研究日益“碎片化”之类问题,但似乎并未展开讨论。会后个别媒体对此有所报道,但是报道话语又过于简单,未能把严肃的“细节研究”与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区别开来。这就很容易引起读者误解,好像这次会议是在反对“细节研究”,所以我借《近代史研究》的笔谈,比较明确地说明自己的看法,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
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繁荣发展,但不足也日渐显露。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更备受关注。在这里,笔者愿申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大家。
一、区分两种“碎片化”
以往学界前辈常会这样提醒后进:“研究问题要注意抓大的重要的题目,不能搞得太细太碎了。”那时没有“碎片化”这个概念。所谓“碎片化”的概念,是近些年由西方引入的。
1987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在其成名作《碎片化的历史学》中,对年鉴学派及其“新史学”作了尖锐的抨击,指责其第三代领导人背弃了先辈注重总体史的传统,而使自己的历史研究归趋“碎片化”,并预言“新史学”的危机与终归瓦解。多斯富有学术勇气,目光深邃,这不仅是指他不幸而言中,年鉴学派从此走上了不归路;而且是指他实际上也切中了整个西方历史学界的时弊。二战之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尤其是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产生了有力的冲击。一方面,它深化了人们对于史家与史料、历史认知的对象与方法、历史知识的内容与性质以及历史叙述的形式与历史文本的解读等的理解,从而推进了历史学的新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它极端地主张颠覆传统,否定任何历史的统一性与认识历史真实的可能性,又造成了历史学碎片化、虚化,乃至于面临消解危险的种种消极影响。所以,多斯的锋芒所向,其意义不限于年鉴学派与法国,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借助多斯的视角,反思当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自然也是十分有益的。
不过,首先还必须弄清楚“碎片化”的概念。
在笔者看来,在语义上,“碎片”是指整体瓦解的结果。但在实际生活中,“碎片化”的语义可有两层理解:一层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二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或过程。二者的区别,在价值取向上不同:前者的目的只在于碎片化本身;后者的目的却在于追求新的综合化。前者是消极的,而后者是积极的。
多斯在其书中,虽然并未对自己使用的“碎片化”一词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他的概念还是明确的,即是指上述在语义上消极的层面的取向:在价值观上,以“碎片”为究竟,执意颠覆和反对任何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目标。所以,多斯指出:年鉴学派深受米歇尔·福柯理论的影响,后者“先是摧毁了人类作为文化主角的主体地位,然后抨击历史主义,并反对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和参考对象”。福柯主张“历史学必须放弃宏观综合,改为关注零碎的知识”,不应再描述历史的演变、进步与连续性,只需“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他反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完全“断绝了追求整体现实和再现全面性的可能”。总之,由于年鉴学派追随福柯的理论,“历史被解构为局部性实践,并放弃了任何总体目标”。②换言之,在多斯看来,任何放弃了总体性目标的历史研究,就必然导致“碎片化”。
然而,就积极的语义而言,却不可同日而语。
从历史上看,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正是经历着不断的“碎片化”与不断的“总体化”(或叫“综合化”),二者相辅相成,构成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人们认识历史,总是先从局部与具体的事实(“碎片”或“碎片化”)入手,渐求达于综合的理解与把握。古人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又谓“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是也。历史的认识无止境,人们自然要不断超越既有,从而不断进行新的“碎片化”与综合,或叫“解构”与“重构”。20世纪初年,近代中国“新史学”兴起之际,梁启超诸人批评中国传统史学不足“当意”,无非是一部“历代帝王的家谱”,一部“相斫书”,在主张引进西方进化论史观,探求中国民族进步的真相的同时,复主张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马叙伦说:“若是推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而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③新史学的兴起,生动地说明了其时的中国史界努力追求在新的基础上,实现“碎片化”与综合化相统一的积极取向。
上述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统一。缺乏总体宏观的视野,微观研究难免细碎,无关大体;反之,不以微观研究作基础的所谓总体宏观把握,也难以深入,失之空泛。所以,具有宏观视野与总体观念的微观研究是积极的,不能因其选题具体甚至细碎,而低估其意义。缘于史家的个性与秉赋,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综合与宏观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垣说,考据虽非史学的究竟,但它是“一人劳而众人逸”的工作,功德无量,不容轻忽。胡适也以为,发现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行星,可以一样伟大。
也可以说,上述乃是人们认识与研究历史的常态。
由上可知,在历史研究中,需区分两种不同的“碎片化”:一是放弃总体性(总体史),导致了“碎片化”;二是坚持总体性(总体史),但在新旧更替之际,史家超越既有,研究趋向多元化,一时也会呈现某种“碎片化”现象,那是学界酝酿新突破、新综合的必要过程。
二、尊重历史学发展自身规律与多斯的启示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以1978年为界,大致可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是所谓反帝反封建“一条红线”,包括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在内的“八大事件”以及“三次革命高潮”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争论的焦点,也多集中在所谓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发展脉络等重大的理论性问题。后期,上述话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以至于有学者感叹:辛亥革命史等重大事件的研究,已是门可罗雀,多成了“节日学术”,除了逢五逢十的纪念性会议外,平时学者沟通都难。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政治史与理论问题的兴趣减弱,一些学者的研究题目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小。文化史、社会史的兴起,虽然展拓了近代史研究新的领域,但这种趋向却似乎变得更加明显。
前后期反差是如此之鲜明,以至于人们对近代史研究现状产生忧虑,以为不尽如人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随着2008年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中译本出版,“碎片化”一词也开始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流行,人们进而将此种忧虑上升为当下的近代史研究是否也存在多斯所说的“碎片化”的担心,这是不难理解的。
当下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看待它。我以为,这里所谓的“碎片化”与多斯所说的“碎片化”,是不同的概念。它是属于在语义上价值取向积极的一类。理由有二:
雷蒙·威廉斯说,在文化发展史上,一种新概念的出现,既是人们对共同生活的外部环境变迁作出反应的记录,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此种变动努力进行的总体评估并逐渐形成的重新控制的过程。④如前所述,多斯是在西方的语境下概括出“碎片化”的概念,他对年鉴学派的抨击,同时也切中了西方历史学研究的共同时弊,而这正是二战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冲击产生的负面结果。欧战前后,西方以尼采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兴起,批判理性主义与“科学万能”论,反映了时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省,同时也开启了今天后现代主义的先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其积极的影响固不容低估,但其存在走向极端的片面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讳言。这即是说,多斯所以提出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不是孤立的,说到底,它既反映了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此的总体评估与积极的回应。反观中国,当下表面相类的“碎片化”问题,却不容作等量齐观。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曾说,他对于尼采诸人的反省现代性深表敬意,但因中国现实是科学与物质文明还太过于落后,故作为一种理论指导,这是中国不应当接受的。他注意到了语境的差异与理性选择的重要性。当下的中国固然已是今非昔比,后现代主义的欧风美雨也显然顺势而至;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其百年来努力追求的理性与科学的精神也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培育,故后现代主义某些极端片面的思想主张对于国人的影响虽然不能轻忽,却也不应作过高的估计。例如,在这个具有重史传统并以追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最高治史境界的国度,有多少真正的学者能忘情于历史学的总体性?在这个曾遭受过百年民族屈辱的国度,有多少人能忘情于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思考,而相信应当颠覆任何“宏大的叙事”,能相信诸如“帝国主义侵略”、“南京大屠杀”等等,都无非是话语建构的故事,而非历史的真实?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当下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所谓“碎片化”,从整体上说,是不可能与反对、颠覆历史研究总体性的目标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当下近代史研究的所谓“碎片化”,与多斯面对的年鉴学派史学的“碎片化”,不是同一个问题。此其一。
值得注意的是,《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的最后一节是《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其中写道:“当代的史学观点倾向于抹杀历史进程中的加速期,以及制度更迭所造成的转折点和交替时期。因此,沦为僵化结构的历史势必要排除所有被视为重要断裂的现象。”这些历史学家刻意抹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革命的发生。在他们笔下,“事件变得无足轻重,它不再是历史进程的动力和加速器,而仅仅成了一种符号、神话和幻觉”。⑤多斯用了很大的篇幅猛烈抨击以弗朗索瓦·孚雷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对法国大革命的粗暴否定。在他看来,这正是年鉴学派史学走向“碎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耐人寻味的是,去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规模盛大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却是:应当进一步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老一辈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更进而提出,必须从前后三百年的历史长时段中去考察,才能真正理解这场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章先生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这与多斯指斥孚雷诸人以长时段为借口,抹杀法国大革命代表历史重要转折的伟大意义,正形成了鲜明对照。近200篇的会议论文,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不少选题也很具体,但彼此内在的联系与综合的指向,即追求总体性的目标——综合把握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依然十分醒目。在历史研究中,选题的大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以大可以见大,以小也可以见大。故多斯以是否心存总体性即总体史的目标这一学术的“终极关怀”为究竟,作为判断历史研究是否“碎片化”的标准,是十分深刻和极为重要的见解。“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说明,绝大多数近代史研究者在事实上也始终并未忘情于历史家的学术关怀和陷入多斯所说的“碎片化”误区。此其二。
要言之,从整体看,坚持总体性的当下近代史研究仍属常态。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尽如人意,不存在消极面。实际上,即便是属于在语义上价值取向积极的一类,“碎片化”本身也并非目的。所以,问题更为积极的提法,似乎应当是:何以后期的近代史研究虽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事实上,却依然处在“碎片化”的阶段(或仍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并没有达到实现真正的结构性突破——铸成综合性的新体?人们对前期积淀下来的近代史学科框架多有批评,但迄今却无以取而代之。这只需看一看此期出版的为数众多的各类近代史教材,其体例框架较前大同小异,便不难理解这一点。至于所谓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更新云云,似乎也于事无补,同样也是反映了这一点。许多论者将导致当下不尽如人意的“碎片化”的原因,归结为诸如学者选题与视野过于狭窄,缺乏理论兴趣,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人才培养上的种种不当等等;这些自然都有道理,但我以为,不是就个人而是就整体而言,人们似乎还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学术发展自身规律使然。
平心而论,前期的近代史研究尽管有诸多不足,但它实际已成就为一座高峰,后人欲行超越,并非易事。梁启超曾将学术思潮的演进,概括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个时期,以为中外古今大致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其见解自有合理性。若将前后期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也视为一种学术思潮演进,则其全盛期显然已过,但就新旧思潮更替而言,却不能说业已完成。客观说来,当下仍处于第三与第四期,即蜕分与衰落期之交。依任公说法,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后起者“只取得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方法,应用之别方面”;衰落期“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豪杰之士”遂起破坏,超迈既有,从而开拓为“第二思潮之启蒙期”。⑥这里所描绘的蜕分期与衰落期交汇的特征,正不妨看做是新时期以来近代史研究堂府扩大,成果迭出,却复不免于“碎片化”之讥的一种写照。换句话说,当下近代史研究之所以还未能走出“碎片化”阶段,达于新的总体性目标,从而展现全新的时期,端在于任公所谓超迈旧有的“豪杰之士”(堪称划时期的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尚未真正出现。
尊重学术思潮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助于我们对当下近代史研究的所谓“碎片化”问题,持更为清醒与客观的态度。
其一,多斯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必须坚持历史的总体性,否则,历史研究必然导致“碎片化”的灾难。令人欣慰的是,当下我国近代史研究依然坚持追求总体史的传统,因之,不存在多斯所批评的现象。换言之,若一定要使用“碎片化”一词,就必须明确:此“碎片化”非彼“碎片化”。当下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谓“碎片化”,既属于语义上价值取向积极的一类,就不应一概而论,作简单否定。实际上,它是新旧思潮更替在特定阶段上的应有之义,本质是积极的。个中自然也会有部分学者缘个性及社会诸多因素的制约,做不到“贤者见其大”,那也只是任何时期都会存在的方法论层面上的一种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碎片化”,并非“危机化”,相反,它恰是近代史研究酝酿大突破的征兆。
当然,也应当看到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历史学家作为个人,研究什么以及怎样研究,是他的自由;但历史学界作为整体,若多数人都对总体性、综合性与理论问题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失去兴趣,只满足于具体细碎问题的研究,也会使历史研究偏离正确的方向,这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多斯指出,年鉴学派中仍有“坚持历史总体性的历史学家”,但问题在于他们已非主流,故其趋向仍是暗淡的:“随着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和大量增加,历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⑦尽管当下并不存在这种趋向,但积极倡导与鼓励学者对近代史重大问题的研究,避免失之细碎化,这在学术发展上,于公于私,无论何时,都是必要的。
其二,当下近代史研究之所以仍不免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说到底,是因为它对于近代历史的阐释,在根本的理论架构上,仍未实现真正的突破。由于缺乏新的权威性理论架构的统整,具体的研究便无由得到整合,进而提升为对近代历史总体性新的认知。当下的现状不仅说明,我们对正努力超越的前期近代史研究成就所已达到的高度,不容低估,而且还说明,新旧学术思潮的“递相流转”,在本质上是表现为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故前后期的近代史研究是统一的,不容割裂,更不应将之对立起来。重要的问题,是关注政治史与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强调继承与创新统一的基础上,形成阐释近代历史发展新的认知架构。
其三,在多斯的眼里,所谓的“碎片化”问题,它所涉及的首先是历史观。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在书中,不仅认为年鉴学派所以走向“碎片化”,与其放弃了自己先前认同的唯物主义,也不无关系;而且,在全书的结论部分,还特别强调指出:“年鉴学派中的第二派势力提出了另一条道路。该派势力倾向马克思主义”;真正创立新史学的使命,已落在了这些“主张总体历史的史学家肩上”。⑧多斯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思考当下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是一种有益的启示。要充分估计并自觉继承前期近代史研究的成就,要看到,它所以达到了至今尚未被真正超越的高度,说到底,是体现了唯物史观的魅力与史家的时代激情。理解这一点,对于人们自觉避免实际上可能导致研究碎片化的误区,也是大有裨益的。
其四,讨论学术,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既然对于所谓“碎片化”的概念,可以有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当下的近代史研究也不存在多斯所讲的“碎片化”问题,本人以为,应慎重使用“碎片化”的提法。这不仅与我们倡导关注重大的选题与理论问题的研究本身并不矛盾,更重要还在于,它有助于人们集中目光,关注属于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自身的真正问题。
注释:
①何炳棣所说的“大归纳”,根据我的理解,应是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前后连贯且左右横通的宏观通识,并非专指某项专题研究。他反对预设结论或理论先行,特别是鄙薄那些不肯下死功夫的简单演绎推理。他从世界史转向研究中国史,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也颇具功底,因此其学术博大气象在北美独树一帜,敢于向哈佛抗衡。
②[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170、235页。
③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号。
④[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吴松江、张文定译:《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
⑤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第220—221页。
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页。
⑦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第220—221页。
⑧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第240—241页。
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近年所谓史学碎片化的感叹,多受外国影响①,却也有本土的渊源。贺昌群在1934年就感慨:清末民初《国粹学报》和《中国学报》上的文章,“大多仍能巍然保持着它的价值”,不过只是一种碎片化的价值,“在一门学问或一个问题中,只见零篇断目,如三五小星在夜天闪烁”;表现出中国“整个学术的内容,步调太不整齐,缺少连锁性,很难寻出一贯的文化线索来”。这些“论文中新旧方法与观点的不同,显出绝大的矛盾”。他承认矛盾是不可免的,却仍想要“求得一个矛盾的统一”。②
贺先生的说法有相当的代表性。寻求一种系统而贯通的解释,本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很多人努力的目标,就是想要贯通那些似乎不通的内容。因为没能做到学术步调的整齐,而反观到满眼零篇断目,这并非一两人的看法,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不过,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呈现出“碎片化”的面貌,因为并非每一史家的每一题目都必须阐发各种宏大论述;越来越多的近代史研究涉入更具体的层面,或许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现象。
我的基本看法,第一,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则史学即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第二,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需要探讨的,毋宁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这已牵涉到史学的基本面相,个人学力有限,不得不多引前贤之言,以壮声势。
一、言有枝叶:历史的断裂和片段特性
首先,历史上每一人和事,都有其独特性。兰克曾说:“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③这一见解可以推广,不仅时代,大至文化、族群、国家,小至个人和细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梁启超后来甚至提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故史家的工作,是“专务求‘不共相’”。④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偏至,但不要忘记,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是历史的主体,他/它们的主体性,确不容忽视;而所有的主体性都是独立的,这就奠定了往昔的独特性。⑤
这一点更因史料存留的实质而强化。我们所面对的史料,不论古代近代,不论是稀少还是众多,相对于原初状态而言,其实都只是往昔所遗存的断裂片段。就是像中国史学那样一直重视当下的记录功能,所能记下的也不过是一种人为选择的遗存;与未被选留的部分比较,仍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言,历史的断裂和片段特性是毋庸讳言的。可以说,史学从来就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
从史料存留的残缺角度言,每一时代的差别,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程度不同。即使不论史料存留的片断特性,时代的断裂经常发生,也是不可否认的。尤其像近代中国这样天崩地裂式的大中断,是必须认真对待和处置的。通常一时代一社会之典范未变,则可能维持所谓“道一同风”的状态;而“道”一旦失范,典范不能维持,就容易杂说并出,即《礼记·表记》所说的“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刘咸炘所谓“道晦而学末,学末而各道其道”⑥,是很有分寸的概括。
然而,“各道其道”,也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传统中断之后,确可能出现非复既往的散乱无序状态。常乃惪曾说:“一种文化,当其主要之一部分改变之后,纵然其他部分仍然保留,就全体的见地言,已经不与旧时相同了。”⑦本体既失,各部分便不复能展现整体。若处于类似近代经典淡出后的语境之中,则旧事物的残存即或复出,也可能更多是一种无序的再现,带有似是而非的特点。不仅从全体着眼已不同,就部分本身言也未必同。如麦金太尔(Alasdair C.MacIntyre)所言:许多关键性词汇仍被继续使用,却仅是先前概念体系的断裂残片,未必完全表现着这些术语曾有的涵义。⑧
故进一步的问题是,断裂的片段可以反映出整体吗?假如历史是一棵树,其理想状态便是“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但这只在热带或温带的一些地区才可能始终如此,在其他很多地方,秋风扫落树上的叶片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冬天的一棵树可能叶子很少,甚至光秃秃的。我们现在见到的许多史料,既可能是往昔那兀立的秃干,也可能是折断的枯枝,更可能就是一片片散乱的落叶。惟不论干、枝、叶,都有其“独立的生命”或单独的意义。⑨很多时候,叶片的独立意义固然不能取代它们与树干连接在一起时的意义,后者却仍可反映在飘零的落叶之中。干、枝亦然。
我们现在知道,任何脱离整体的生物片断,都保留着原有的基因;若得到很久以前的生物碎片,便可通过DNA的检测反观生物的整体。文化其实也相近。文化基因的传承能力,包括中断后的传承,是非常强的。例如,四川至少从汉代起,其文化特色以今日所谓“文学”见长,而正统的经学则相对弱(至少对经典的理解和表述,都与中原互异)。因明末的战乱,四川人口剧减至清初的不足10万户,在“湖广填四川”后更成为一个移民为主的社会。但直到清末民初,四川仍以“文学”见长;而在经学方面,也还颇显特异之处(后来公认的大师廖平,便曾被视为儒学异端)。⑩
退而言之,即使是滴水可见太阳或月映万川那种间接的映照关系,在太阳和月亮从我们视野中的天空消失之后,映射过太阳的水滴和映照过月亮的万川仍存留着日月的痕迹。章太炎所谓“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11),其实未逝,不过需要特定的观测手段和方法才可见。今人可用高倍摄影留其痕迹,而惠施所谓“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庄子·天下》),也是一由影观形的侧面进入之法(详另文)。
而且,传统的中断永远不是绝对的。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12)蒙思明也提出,“某事件的史料消亡”,未必意味着历史上“并无其事”,更不能以为其“对于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思想就无影响”。(16)所谓传统,或许就像孔子所说的,“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同时又“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礼记·中庸》)。古人常说:盐化于水,盐已无形,而仍在水中;且每一滴水中,皆有盐在。历史亦然。它早已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招之未必来,挥之难以去;就像曾化于水的盐,不必有形,不必可见,却始终存在,且无所不在。
进而言之,散碎其实有着多方面的涵义。中国固有的表述风格,提示出片段不一定就是断裂,反可能是表述者有意为之,不过点到为止,甚至故作不言之言。中国古人著述的特点,不仅长期体现着傅斯年所谓“电报语法”的特征,语尚简洁;而且有着一种学理的自觉,即承认言不尽意,却又很注重言外之意,甚至追求一种冯友兰所说的“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的表述方式。
冯先生注意到,“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按道家的说法,“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古人“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皆不够明晰。然虽“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且正因昔人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14)
或因此表述风格的影响,或因为时代的距离,也可能就因研究者有成心在,都可能造成今昔的不理解。故熊十力提醒我们:从表面看,“古人著书,虽无体系,而其思想囊括大宇、穷深极幽,决非零碎感想”。善学者当“由其散著之文,以会其无尽之意”。(15)其实,说古人著书无体系,多少也带有后人的“体系”观。在朱子看来,“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齐整。今人只是心粗,不子细穷究。若子细穷究来,皆字字有着落”(《朱子语类·读书法上》)。读者一旦明白了字字的着落,“枝枝相对、叶叶相当”的整齐排列就自然显现。
后人眼中的“体系”或非昔人的追求,然第一可知其决非零碎感想,第二他们还可能是有意追求一种“枝叶”式的表述。再看《汉书·艺文志》描述汉代经学的现象:“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这不就是孟子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孟子·告子》)的典型现象吗?若揆诸前引《礼记·表记》关于“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的说法,在一般以为经学确立也特别繁盛的时代,其说经方式却表现出了“天下无道”的征兆,岂不可思!
若从“各道其道”的眼光看,“言有枝叶”本身固是一种典范衰落的现象,唯在典范既逝、“道术将为天下裂”之时,各种思想处于竞争中,“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却也未必不是一种有意的表述方式。传统中断之后,“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以上皆《庄子·天下》);且很可能如熊十力所说,“下流之水,既离其源,便自成一种流,而与源异”。(16)故因传统中断而散乱无序,仅是“各道其道”的一种现象;因中断而独立,则是“各道其道”的另一种现象。
就学术言,一旦下流的独立成为一种定见,便有所谓门户的确立,并会形成某种思维定见(即庄子所谓成心,或西人所说的mental set),影响学人的眼光,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效果。廖平以为,《春秋》“三传本同,自学人不能兼通,乃闭关自固。门户既异,矛盾肇兴。”(17)按三传之同,或更多指其根源;其具体诠释,当然有同也有异。但不论同异,都不仅有中断,更可能见创新。尤其“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庄子·天下》),“枝叶”式的表述,或许即是开启一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机缘。(18)
钱锺书就曾注意到,往昔“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对后人而言,往往只有一些片段思想还有价值。不过他也补充说,“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这一区分至关紧要——碎片既可能是凋零的结果,也可能是创新的起点。不能因为“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就忽视它们。“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这些“自发的孤单见解”,可能就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19)
简言之,第一,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第二,有些看似散碎的片断,却可能是有意为之,要善于从散碎的表象看到其背后隐伏的体系或关联;第三,中断亦如四时,“终则有始”(《易·恒·彖辞》),方死方生,它本身可能是独立的前兆,故片断也可能是创新的机缘,甚或本是新说的起点。
杨国强教授有句名言:清季士人的思绪,“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辞,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办法串起来”。(20)我的感觉,他就像傅斯年反对“疏通”,主要是针对别人而不是说自己。(21)如果承认史学本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则其基本精神,或许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或者说,我们怎样使书写出来的历史并非一堆碎散的文辞,又尽可能避免让历史成为后人的系统性“代言”,而失却了本来的面目?
文化DNA的检测,当然没有生物学那么直截了当,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毕竟历史文献中任何“单词片语”,都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22)史学不能无中生有,却可以由末见本(这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要项,详另文)。要收拾一地散碎的文辞,既非不可能,也不那么简单。
二、以碎立通:收拾一地散碎的文辞
假如那一地碎散的文辞原是一串或多串的钱,它们是可以重新串起来的,因为钱币是按模具人工制作的,其共性远大于其个性;但若这根本就是一地秋风扫下的落叶,离开了与树干相连的树枝,甚或被吹离了原来的树林,它们还能复原其本义么?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能找到其原来的树,通过树枝确立落叶和树的关联。但更多时候,我们恐怕不得不面临一个无法觅得其原树的状态,或无法重建其与原树的关联。
于是产生了问题:一方面,在失去了原有的穿钱绳索之后,以现代的绳索重新串起来的钱币,是否还具有接近原状的意义?或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体现其原初的意义?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确立落叶与树的关联,即使我们搜集起一堆落叶,我们怎样理解特定的一片树叶或一堆树叶?怎样把它或它们置入我们希望再现的历史场景之中?进而言之,即使这一地碎散的文辞原就是一些散乱而零碎的无系统见解,他们是否有某些时空的共性,经过整合可以表现出某种未必系统却具有关联性的意义?这样的历史意义究竟类似于树叶构成的拼图,还是新绳索串起来的旧钱币?这些恐怕都是见仁见智、仍存争议的问题。
非常可能的是,后人用树叶构成的拼图,更多不过反映出拼接者对树叶的认知。即使用新线绳串起了旧钱币,也很可能带有新线索的时代意识、反映出串钱者的后起立意。遑论那些原本确实散碎的零星史料。但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继续发展的进程,后人对往昔的重构,不论是否是复原或再现,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是复原和再现,它们已然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许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然而河的下游仍然流淌着上游的源头活水;且不论后之整合是复原还是再造,多少都有往昔的因子在,因而也是往昔的一种再生。
引申而言,上述所谓断裂的碎片,也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细节。史贵能见其大,而不避其细。治史以具有通识为上,而任何通识,都靠细节支撑,并须以细节约束。
《管子》言,“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管子·宙合》)。故廖平以为,治学当“先急其大者,而小者自不能外。若专说细碎,必失宏纲,而小者亦不能通。”(23)另一方面,又要平等看待大与小。如张申府所说,以求真求实为目的者,“大至于仅约略可想象不可测度的全宇宙,小至于几万倍的显微镜下看清楚的微尘”,都要“一律看待”。(24)
一方面,大体不存(或被修改)便可能破碎。如《汉书·艺文志》所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而后世经传乖离之后,学者“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的结果,却是“破坏形体”。另一方面,细节去则同异失而关系断。吕思勉指出,“史事关系之有无,实为天下之至赜”。一些看似无可隶属的零星之事,若因修史者“见为无关系而删之,在后人或将求之而不得”。修通史者常“除去复重,然同异即在复重之中”。(25)重复除则同异失,史料之间本可显现的关系,也就切断了。
在实际研究中,有时一个细节即可导致根本的转变:“小事似无关系,然大事实合小事而成。一节模糊,则全体皆误。”(26)盖“考证上的事情,往往多一条证据,少一条证据(如发现不足信的材料,抽去一条),事相即为之大变”。(27)故“考据之家,一字为宝”(28);“一瓦一甓,大匠不弃”。(29)
更重要的是,朱子已注意到,“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后人必仔细穷究,方“字字有着落”,而可见其整齐地排列。若心粗而不仔细穷究,即使在尊经时代,圣人言语也可能被人作“碎片化”的理解。故蒙文通要求学生“养成读书要细致的习惯”。平时读书中遇到细小问题,“莫嫌其细小”,都必须搞清楚,因为它们“常常也会给我们提出一些重要问题”。(30)
微末细节的建设性意义,正在于从中可能看到与整体相关的重要问题。具体之一法,或即如蒋梦麟所说,“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31)傅斯年在讨论专史和全史的关系时强调,专史乃“全史上之一面”,做专史要记住“无以一面之故,忘却历史大轮廓上所示之意义”。(32)在此基础上,“考定一书的时代,一书的作者,一个事件之实在,一种议论的根据”,虽是具体问题,“也正是通史中的事业”。(33)
细节与整体,本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朱子曾论《大学》说,“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34)析之极其精,正为合之尽其大;若不能析之极其精,也就很难合之以尽其大了。故柳诒徵主张,“非大其心以包举万流,又细其心以厘析特质,不能为史,即亦不能读史”。(35)
陈寅恪就向来注重从细节看整体,又将细节置于整体之中。这一取向在其研究中体现得极为充分。在他眼里,任何“具体之一人一事”,都始终反映着所处时代和社会文化那“抽象理想之通性”。(36)王国维治学,也是“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37)两人的治学取向,最能体现刘咸炘所谓史学当“似个别而实一贯”的通达见解。(38)
疏通知远是中国传统学术一个长期追寻的目标,而真能疏通知远者,又从不忽视具体的一人一事一物。《中庸》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最能概括这一精神。清代训诂学盛,学者知字字有用,一不可忽。考证学兴,草木虫鱼,皆可见道;也只有将其弄得清楚明白,方可见道。治学之趋向,于是大异。史学亦在此风气影响之下,细节之可贵进一步凸显,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不重要的细节。但这一取向在当年就曾引起反弹,视为支离破碎,无关大体。人民国后,考据琐碎之批评,更不绝于耳。
早年也曾批评清儒的顾颉刚,后来认识到,“人的知识和心得,总是零碎的。必须把许多人的知识和心得合起来,方可认识它的全体”。学理如此,学术史上的实际历程亦然:“必有零碎材料于先,进一步加以系统之编排,然后再进一步方可作系统之整理。”如若只“要系统之知识,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犹欲吃饭而不欲煮米”。有些因时代风气而气魄恢宏的东西,一旦风气转变,转瞬即“烟消云散”。故“与其为虚假之伟大,不如作真实之琐碎”。(39)在此基础上,他深感“清人之学范围固小,其成就固零碎,然皆征实而不蹈虚”。且因清代考据“已遍及各个角落”,若“能集合同工,为之作系统之整理,组织其研究结果”,便易“获得全面性之结论”。(40)
实际上,碎与通虽有紧张冲突的一面,却也呈现出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钱穆指出,很多人以为“考据琐碎”,其实是自己“徘徊门户之外,茫不识其会通,而讥其碎”。盖碎是通的基础,“非碎无以立通”。(41)钱基博稍后申论说,“读书欲得要领,贵乎能观其会通。然欲观其会通,必先分部互勘”,否则就可能“以笼统为会通”。(42)这是对“非碎无以立通”的最好诠释,会通自分别、比较得来,能分而后能通;细节中可以见整体,也只有从细节入手,才能认识整体。不以细节为基础,就只是笼统,不是会通。
由于现存史料在本质上就是断裂而零散的,在每一“个别”之中,或不一定都能找到“共通性”;且每一细节与大局的关联程度,也可斟酌。但在一定的范围里,各细节之间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有时甚至到了相生相克的程度。重要的是,相互的关联性多少也反映着共通性。很多时候,我们不仅需要从断裂的碎片中看到整体,也只能从残存的断片中了解整体。
陈寅恪早就提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史家只能“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43)另一方面,如他在“晋至唐史”课堂上告诉学生的,若“一幅古画已残破,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44)这样的“绘画眼光”,正体现着碎与通的辩证关联。
这里最需要的,就是历史想象力。如顾颉刚后来所说,“古史本属破甑,不作假想就联系不起”。(45)张尔田也认为:“历史事实,当初如一整碗,今已打碎。欲为之补全,其有缝可合者,固无问题;但终不免有破碎无从凑泊之处,即不能不用吾人经验判断所推得者,弥补完成。”(46)两人想法相近,都想要从断片复原整体(有意思的是,通常视为守旧的张尔田主张更理性的推理,而一般以为更“科学”的顾颉刚则敢明言“假想”)。
然而想象也当有限度,正因材料不全,叙述就不能不留有余地,切忌过于“系统”和“整齐”。更早提出此说的傅斯年也更有分寸,以为“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47)作为一种始终从残余断片窥测全部结构的艺术,任何历史叙述,多少都有些史家“主观的分数”在里面。也只有一面不放弃对客观的追求,同时以“多元主义”来弥补“主观主义”。(48)盖历史现象本“是极复元(heterogeneous)的物事”,如“不从小地方细细推求比论,而以一个样子定好”,则难免疏误。(49)
毕竟史学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的学问,众多选项的平等(即不具排他性)存在,是治史者进行比较和做出选择的基础,也是读史者形成判断、决定取舍的基础。研究和叙述取向越“多元”,呈现出的史事越丰富,便越可能接近研究对象的“全部结构”。我们既要肯定历史的丰富性,并力图将其峰回路转的原貌呈现出来;又要充分承认史料的有限性,愿意接受不那么系统整齐的历史作品。历史本是已逝的往昔,在这方面,文物界所谓“修旧如旧”的讲究,是可以借鉴的(唯所谓“旧”,也有当世原状和存留状态的区分)。若历史的丰富一面得到凸显,则其虽不那么“整齐”,可能还更接近史事发生发展的原状。
三、余论
就前引贺昌群所谓“三五小星在夜天闪烁”之比喻言,星光不过是星空最显而易见者,后面还有那漫无边际的“夜天”在;没有寥廓的夜幕,也就无所谓闪烁的小星。整体从未隐去,只是所见层次有深浅之别。史学的具体问题,就如一颗颗寥落孤星,星点之光既是星与星反射彼此之光(日月亦星体),也是其自我状态的无声言说。如果我们既看到孤星的闪烁,又看到诸星之关联,复不忘其背后无尽的夜幕,则史学之具体研究,虽在细节而不废整体,且与其他细节交相辉映,乃一片广阔的天地,又何须忧虑什么碎片化?(50)
且从上面的讨论看,如果史学本是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似亦不必太担心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相反,比较可怕的是,即使在一些已显“琐碎”的题目中,还是常见从头到尾的空论。若习惯了蹈空之论,久假忘归,或沦入真正的历史虚无取向,即朱子所警告的“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寄怀》)。至少对史学的初入道者而言,题目不论大小,论述都宜由虚入实。把问题讲清楚了,再言能见其大不迟。
在我们的学术流程中,确有一个真正导致了文科研究“碎片化”的因素,那就是很多刊物的字数限制:不少刊物都将文长限制在万字以下,甚至更少(这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欧美学术刊物文长动辄数万字,很少看到这样“少而精”的现象)。通常一个稍有意义的题目,多少总要回溯既往的研究,以将本文论题置入学术脉络之中;然后要提出自己的新见,并以史料为基础论证之;有时还需要适当的总结,或对可以继续开展的研究提出建议。试想,除极少数可遇不可求的题目外,有多少不破碎的论题能在万字以内完成这些任务?或者说,在万字以内能达成上述要求的,能够是多“大”的题目?若在这样的字数范围里讨论宏大的主题,除了定性表态,我们还能做什么?
同时也要注意,前些年西方流行的“微观史”,就是通过对无名之辈的生命和观念进行细致分析来展现普通人的思想世界,其核心是以可分享的个体生活“经历”来颠覆被既存论说抽象出来的整体历史“经验”。其所针对的,正是更早那些众皆认可的宏大叙事。这些作者和作品,既是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所抨击的“碎片化”典范(尽管那些作者未必承认),也是我们不少学人赞叹、传播和临摹的榜样。
我无意在这里讨论究竟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我的基本看法,一、凡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往昔的取向,都是可以尝试的;二、史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取向、而不是一种众皆认可的取向,才是最正常也最理想的状态),我只希望那些担忧近代史研究已呈“碎片化”的学者,不妨想想自己究竟期望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氛围?任何一项具体的课题,研究者都不能不对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主线、或基本倾向等有自己的认识,否则便难以推进;但我们似不必要求所有学人,特别是初入道的年轻学人,都来辩论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和特性。
学术的整体发展正类积薪,后来者居上。李济向来主张学者思考和解决基本问题,但他也指出:“考古学上所能解决的,也并没有‘全面的’。纵然有一个像是全面的解决,也是靠着一点一滴小解决积起来的。”(51)顾颉刚也强调:“千万个小问题的解决,足以促进几个中问题的解决;千万个中问题的解决,足以促进几个大问题的解决。只要我们努力从事于小问题的研究而得其结论,则将来不怕没有一个总结论出来。”(52)
“总结论”一说或隐含历史终结之嫌,但学术认识的确是层层推进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过去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我们史学界真正关注具体研究的时段实在不多。如徐秀丽教授所言,近年相对兴盛的“‘窄而深’的研究”,自有其特定的针对性;这是“近代史学科发展道路上的必经阶段,也是重新进行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53)我的感觉,这个“必经阶段”才刚刚开始,与“必要前提”尚有不短的距离。
注释:
①不过,欧洲史家对“碎片”的感觉是很不一致的,对于多斯来说,碎片化是一个负面的现象(参见[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于安克施密特来说,这即使不是一个正面的追求,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参见[荷]安克施密特著,韩震译《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23页)。
②贺昌群:《一个对比》(1934年),《贺昌群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46页。
③[德]兰克著,斯特凡·约尔丹、耶尔恩·吕森编,杨培英译:《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④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约1922年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并参见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年),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文集》(4),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页。
⑤参见罗志田《相异相关的往昔:史学的个性与通性》,《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⑥刘咸炘:《中书·流风》,《推十书》第1册,成都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⑦常乃惪:《与王去病先生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续)》,《民国日报》,1928年4月13日,“觉悟副刊”,第2版。
⑧Alasdair C.MacIntyre,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Notre Dame,In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4),pp.1—3.此书有中译本《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参见第3—4页。
⑨若深入追寻,树也是个“片段”——它本从种子一路成长而来,而种子又是树所结之果实。树既非起源,又非结果,而有其价值。树如此,枝、叶亦然。
⑩参见罗志田《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6期。
(11)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12)《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页。
(13)蒙思明:《历史研究的对象》,《华文月刊》第1卷第6期,1942年11月,第15页。
(1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三松堂全集》第6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15)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仲光记语》,《熊十力全集》第5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16)熊十力:《读经示要》(1944年),《熊十力全集》第3卷,第673页。
(17)廖平:《公羊验推补证凡例》,《国粹学报》第2年第7期,1906年8月,“学篇”,第6b页。
(18)“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出自何休《公羊传注自序》。关于其积极的创获一面,参见蒙文通《孔子和今文经学》,《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57—221页。
(19)钱锺书:《读〈拉奥孔〉》,《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34页。
(20)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44页。
(21)杨教授自己的研究皆识见宏通,处处都在串起那一地碎散的文辞。关于傅斯年,参见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秋季号。
(2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2—13页。
(23)廖平、吴之英:《经学初程》,成都存古书局1914年版,第9b页。
(24)赤(张申府):《自由与秩序》,《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13日,第1版。
(25)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7页。
(26)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著史学与史籍》,第63页。
(27)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著史学与史籍》,第25页。
(28)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著史学与史籍》,第46页。
(29)钱穆:《序言》(1933年),罗根泽主编:《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30)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页。
(31)蒋梦麟:《西潮》,台北,中华日报社1960年版,第25页。
(32)傅斯年:《中国民族革命史》,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
(33)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叙语》,《傅斯年全集》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2页。
(34)朱熹:《四书或问·大学》,黄坤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35)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36)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1927年),《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37)梁启超:《〈国学论丛·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5—1076页。
(38)刘咸炘:《先河录·序》(1929年),《推十书》第1册,第744页。
(39)顾颉刚:《零碎资料与系统知识》,《顾颉刚全集·读书笔记》第4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1页。
(40)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序》(1949年7月),《顾颉刚全集·读书笔记》第16卷,第7页。
(41)钱穆:《序言》,《古史辨》第4册,第4页。
(42)钱基博:《〈史记〉之分析与综合》(1935年),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
(4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44)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3页。
(45)顾颉刚:《科学思维与宗教神话之联系;向新的知识领域探索之不易》,《顾颉刚全集·读书笔记》第10卷,第184页。
(46)张尔田:《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六·论作史之方法与艺术》,《学衡》第71期,1929年9月,“文苑”,第10—11页。
(47)傅斯年:《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1924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0期,第223页。
(48)傅斯年:《台大〈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1950年),《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62—363页。
(49)傅斯年:《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0期,第223页。
(50)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果同学提示。
(51)李济:《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1944年),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页。
(52)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1930年),《顾颉刚全集·古史论文集》第1卷,第93页。
(53)徐秀丽:《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2007)》,《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62页。
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
行龙(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社会史更被人认为是“碎片化”表现突出的领域。针对如何克服碎片化的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①这就是说,克服碎片化的途径就是回归总体史。借《近代史研究》组织讨论“碎片化”问题之机,笔者愿就此观点再做进一步的申论。
应该如何去看待目前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或者说,它有哪些具体表现,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属于“碎片化”现象,这是一个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简单而言,所谓“碎片化”是指原本完整的东西破碎成零散的块状,成了诸多碎片,不再是一个整体了。可以说,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这一话语就已被广泛应用在信息、传媒、社会、技术、文化等领域,用来形容事物主体的琐碎、细碎、零碎状态,即没有整体关怀,只强调个体、片断的存在。因此,人们在谈及“碎片化”时,即是指一种零散、不完整、断裂的取向。如果再往深一点讲,这一取向的出现主要还是当时一些社会思潮影响的产物。其中,西方国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入,就给当时的中国文化艺术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尤其是后现代思潮提倡的非理性、去中心化、去主体性,不相信有宏大、一致的规律性存在,关注个体的自由选择,甚至追求杂乱无章的生活体验等,这些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中国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例如,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自由主义的兴盛,等等,于是乎人们对自身的存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反而对个体之上的整体性存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现象。另一个影响则来自于中国内部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建立全新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渐放弃了1949年后实行了30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作为一个强大的主体性主宰一切的治理模式,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出现了多样化形态,人们觉得自己就生活在一个到处充满“碎片化”的环境当中。人文社会学界试图站在自身的立场为当下的社会发展态势寻求学理上的依据和地域上的经验,以作出各种各样的回应或调适,其实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顺理成章”。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也是在上述大的时代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学术表象。从具体的学术影响上来看,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现象事实上与“中国中心观”、社会史的区域转向、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兴起等有直接关联。具体而言,柯文试图通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进而在批判“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费正清)、“传统与现代”模式(列文森)、“帝国主义”模式(佩克)等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建构出所谓“中国中心观”,至于如何以中国的内部立场而非以西方的外部视角去“发现”中国的历史,柯文认为可行的办法有:从“横向”上,将中国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从“纵向”上,把中国社会再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此外鼓励将社会科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当中。②这一主张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由整体性的探讨转向区域性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史研究也由原先注重整体学科体系建立的讨论开始转向具体操作实践的区域史研究,当时出版的一批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即是有力的证明。③可以说,正是在区域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之时,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史越来越趋向于专门化、精细化、微观化、具体化,于是在那些从事宏大历史建构和侧重一般历史问题研究的学者看来,社会史、区域史研究日渐“碎片化”了。至于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影响,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发展,更为引人注目。其中以孙江、杨念群、黄兴涛等人的研究实践为代表,从他们先后主编的《新社会史》、《新史学》丛书中,不难看出其综合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架构来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抱负和追求。例如,已出版的《新社会史》三卷分别以“事件·记忆·叙述”、“身体·心性·权力”、“时间·空间·书写”为主题,《新史学》则以“感觉·图像·叙事”、“概念·文本·方法”、“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再生产的近代知识”为各卷主题,很显然,这些醒目的关键词不仅凸显了著者试图从细微具体的层面去展现历史真实,而且更加注重了对历史展演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深入解读。在这样的新史学实践推动下,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细微化、零碎化,诸如人口、婚姻、家庭、宗族、城市、农村、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习俗、教育赡养、自然灾害、会党土匪、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心理以及身体、疾病、记忆、图像等内容都可以被用来作为建构复杂历史画面的着眼点。应该说,此类研究揭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细节,着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也难免会被视为一种“碎片化”的表现。
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历史解释概念体系和研究路径为中国史学的繁荣发展开拓了新局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和理解,但与此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一些所谓的“碎片化”问题。④在笔者看来,“碎片化”倾向固然需要警惕,但是也没必要过于敏感,以免无形中将其“扩大化”。因为即使是“小”的研究也依然可以做出“大”的文章来。区域史研究者倘若能够始终追求“以小见大”、“小中有大”,微观与宏观、具体与一般、区域与整体的有机对接,不只是就区域谈区域,就片断谈片断,即使是再微观乃至不起眼的小事情还是会彰显出“大历史”的实践轨迹的。众所周知,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蚶虫》、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等西方史学家的经典著作,以及新近国内出版的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等论著,就很好地凸显了作者力求通过微观的细致研究去深化对宏观历史的系统理解和把握的信心。从表面上看,这些著作选题具体而细微,要么是一个村庄,要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要么是一个汉字,要么是一个特定的地域和一个社会阶层,如果笼统地将其视为“碎片化”,则过于简单化了。
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往往被认为是“碎片化”表现突出的领域。其实,现在我们谈论所谓的“碎片化”问题,主要还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区域史(包括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研究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面相不断进行局部解释的缘故。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区域社会史的历史书写也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为“碎片化”。不可否认,目前学界确实存在一些区域社会史研究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就区域言区域,未能将区域内部各组成部分以及区域与整体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讨论,虽然占有区域性的具体史料,但却陷在史料当中不能自拔,更多的只是将视野限定在所掌握的史料层面上,就史料言史料,不能很好地将“小地方与大历史”的复杂关系全面客观地诉诸笔端,对史料自身的产生背景及具体意图也视而不见,结果实践越多,“碎片化”日深。就“区域研究”中的“某种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态度”而言,陈春声教授也曾指出:“深化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区域研究的关键之一,在于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毋庸讳言,时下所见大量的区域研究作品中,具有严格学术史意义的思想创造的还是凤毛麟角,许多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仍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几十年来常见的《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地方性版本,有一些心怀大志、勤奋刻苦的学者,穷一二十年工夫,最后发现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一场既有思考和写作框架下的文字填空游戏。传统社会区域研究中,学术创造和思想发明明显薄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术从业者追寻历史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的严重缺失。”⑤显然,做区域社会史研究,要想不被人误解或讥讽为“碎片化”,确有必要对区域与整体及两者的相互关系有着相当的认识和把握,直至内化为研究者心中可以运用自如的一种学术自觉。区域是部分的、具体的,而社会是整体的、系统的,区域社会史是在研究具体的区域,但关注点却应该是整体的社会。区域可大可小,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性概念,而整体则是众多的区域通过一系列的内在机制所生成的但又超越了区域原有特征和属性的系统性存在,因此,区域形式上看似独立于整体,但是其存在的前提和意义正是通过和整体的紧密关联而显现的,如果脱离了整体性的存在,区域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真正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实际上是“形散而神不散”,即便是对原本完整的历史进行不同面相的展现,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回归到整体史层面上来。
除上文中提到的区域史研究作品外,以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科大卫等人为代表的“华南学派”同样引人关注,他们三十多年的区域史研究不仅没有落入“碎片化”的窠臼中,相反,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有助于剖析整个中国历史的实践经验与解释体系。近年来,由陈春生主编的“历史·田野”系列丛书就凸显了把区域史与整个中国史融为一体的治史理念。另外,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海外中国研究论著,无论是在选题还是理论与方法上,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不容轻视的影响。它们也都是从具体的区域或事件入手,但是对区域内容的讨论则放在了整体的大历史的进程中,通过区域研究去透视具有更加普遍性、一般性的问题。例如,杜赞奇在其书中研究的是晚晴至民国的华北农村社会,涉及地方政权、乡村政治、宗族、水利、祭祀、婚姻、税收摊派、市场、乡村组织和领袖等内容,但是作者通过这些看似支离破碎的农村问题,构建了清末以降华北农村社会变革背后的结构性特质,如“国家政权内卷化”、“权力的文化网络”、“保护型经纪与赢利型经纪”等深层问题,进而为整个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历史演变作出了一个“普适性的”解释。笔者多年来倡导“走向田野与社会”,在从事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中,也试图通过区域研究反映整体的历史,以此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理论。明清时期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是探讨该区域社会的重要方面,彼此间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的发生。我曾指出:“明清以来山西生态环境恶化的最突出表现是水土流失,水土流失不仅引起土地的大面积沙化,而且使汾河流域的含沙量急剧增加。河道、渠道的变更,由森林减少而引起的气候环境的变化,又加剧了旱灾及争夺水资源的各类‘水案’的频发,这种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一直是困扰山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⑥基于此,我们开展了水利社会史的一系列研究,包括水资源的紧缺、争夺导致的“分水”事件,水利灌溉、祭祀与信仰,水利与造纸等手工业的运作,水环境与自然灾害的发生等,试图“以水为中心”去展现乡村民众、宗教信仰、民间组织、精英士绅、国家政权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山西区域社会。明清以来的山西区域社会是否“以水为中心”这样的问题仍可讨论,但我们是试图通过“以水为中心”反映整体的区域社会变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保持“总体史”的眼光。区域史研究并不一定就是“碎片化”,其价值所在就体现于它与整体史的密切关系之中。
既然区域社会史并不等同于所谓的“碎片化”,那么,我们在警惕“碎片化”的同时又该如何去克服它呢?笔者以为,最主要的还是要回归“总体史”,而要实现“总体史”追求研究者至少需要把握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二是重视“长时段”,三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多学科交叉。
可以说,具有问题意识,对一切史学研究都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就这一点而言,国内社会史学界更多的是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问题史学”的影响。费弗尔明确地说“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乃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⑦如果研究中不能贯穿鲜明的问题意识,则很可能就像钱乘旦先生所言的“只满足于史料堆积,而缺乏对历史的思考,缺乏深层的思维,轻视理论和整体研究的倾向”一样⑧,难免走向“碎片化”。至于“长时段”,这也是人们在谈及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的作品时使用最多的重要概念,并成为衡量“总体史”的关键尺度。布罗代尔强调:“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就必须准备改变自己的风格、态度,必须彻底改选自己的思维,而采用崭新的思考社会事物的概念。这意味着逐渐习惯一种比较缓慢的、有时近乎停滞的时间……总之,相对于这种缓慢的、层积的历史而言,整体的历史可以重新思考,正如要从底层结构开始一样。无数的层面和无数次历史时间的剧变都能根据这些深层结构、这种半停滞的基础得到解释。所有的事物都围绕这个基础转。”⑨按我的理解,布氏强调“长时段”的重要性,是由于这一解释概念有助于研究者透过历史现象揭示那些看似不变的“结构”性东西,正是这些“深层结构”的存在支配着借助于“短时段”所表现出来的纷繁复杂、变幻无常的“事件”、“局势”。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勒高夫也曾指出:“历史的发展时快时慢,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却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起作用并被把握。”⑩也就是说,捕捉到了历史中的“结构”才可能从整体的视角去展现历史。“长时段”的方法运用是与历史中的整个“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对于区域史研究中真正实现“总体史”关怀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相比之下,多学科交叉渗透则可以看做是追求“总体史”的必然产物,也是强调“问题意识”和“长时段”两方面的一个内在要求。研究者提出明确的问题,然后全方位地找寻各种各样的资料、工具、手段来求证已有的问题假设,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必然会打破学科专业间的种种限制,只要是对自己有用的都可以为史学家所重视和利用,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如此,多学科视角的运用对于研究者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变化轨迹和内外关联,注重整体性,避免“碎片化”,就显得非常必要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借鉴多学科理论方法的过程中,生搬硬套、盲目利用或滥用西方的时髦概念来套用中国历史事实的做法仍旧屡见不鲜,将原本丰富多样的历史画面搞得“支离破碎”,甚至是“非驴非马”,晦涩难懂,实为“碎片化”的另类表现。有鉴于此,多学科交叉又一定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只有通过对史料的全面爬梳与深入解读,才能够将经验事实与概念体系真正地衔接起来,才可能建构出整体的、总体的历史。
总之,笔者以为,对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热议的“碎片化”倾向,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但也不要扩大化。区域社会史研究并不必然会带来“碎片化”,只要研究者能够将“总体史的眼光”始终作为一种学术自觉,敏锐地提炼“问题意识”,重视“长时段”研究,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即使再细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是“碎片化”的。否则,表面上看似再宏大的选题,也只能是一种没有太多学术价值的文字。
陋知浅见,有以请教。
注释:
①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4页。
②[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0—212页。
③代表性著作有: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乔志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
④主要观点可参见: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桑兵《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滞碍》,《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等。
⑤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读书》2006年第9期,第24页。
⑥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3页。
⑦[法]费弗尔:《为史学而战斗》,第22页。转引自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页。
⑧参见韩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体系:争辩与思考——“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研讨会”学术观点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⑩[法]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惑——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近30年来的中国史学研究,一直寻求打破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单一诠释路径,在方法论探索上呈现多元竞进的局面。此一局面的形成既是改革开放的时势推动使然,也有史学方法受各种思潮影响而发生内在理路变迁的复杂原因。从大的方向上观察,中国史学有一个从着重以时间界标划分历史演进结构的分析模式转向注重考察历史进程的空间分布态势的转化过程。具体就方法论而言,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界对人类学诠释模式的汲取引发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区域转向”,并连带导致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两者都日益关注对基层社会组织和民众日常生活状况的书写。但以上探索路径的变化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那就是过去史界所热衷讨论的诸如历史发展趋势之演变、走向、规律等等“大问题”渐遭冷遇,由主流退居边缘。由于日益从眼光向下的视角观察民众日常生活的经验逻辑,对之进行诠释辨析的手段也渐趋细致多元,遂导致对历史发展总体趋向的判断日益模糊不明。同时,这些新的探索路径亦不断遭致缺乏整体视野和研究方法日益“碎片化”的批评。与之相呼应,史界中回归“整体史”传统的呼声亦时有所闻。争论双方似乎各有所据,均力图突破自身局限,寻求一条更适合中国历史研究的独特道路。本文即以这些论争为基点,概要展示各类方法对中国史学影响之得失,以商讨解决之策。
一、中国史学研究的“区域转向”
我们发现,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所有被视为“整体史”意义上的传统史学所提出的研究命题都或多或少以“时间”为参考坐标,作为观察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要依据。如“封建社会的起始年代和长期延续问题”即因为出现争议而划分成“战国”、“西汉”、“魏晋”三个主要派别。有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也常常聚焦于其出现时间,尽管多数论者认为“明末”这个时间段已可发现与资本主义萌芽类似的若干变化因素,却也出现过个别比较荒诞的例子,即完全不顾早期商品化与工业化时代商品经济的差异,强行把“资本主义萌芽”肇始的时间前推至汉代。“农民战争史”研究作为另一朵“金花”也是从打破王朝循环逻辑的角度论述其作用的,大致可以看做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叙述模式。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最具约束力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同样包含着强烈的时间递进意识,最终都是要证明中国历史演变与“世界史”叙述中的普遍时间进程相互吻合。
与古代史相比,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时间意识。如曾经被热议过的“中国近代史”应从何时开始的争论,突显的焦点问题仍然是应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还是以19世纪起始年(1800年)为基点作为划定“近代”源起的依据。著名的“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革命史叙事更是以特别标定出的若干重大事件所发生的时间顺序划分历史周期,其中几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如1900年(义和团)、1911年(辛亥)、1919年(五四),均起着重要的标识性作用。这样按时间顺序标示历史事件重要性的做法其实是“五种社会形态”时间划分策略的一种变通和延续,目的是打破以王朝更迭为核心的循环叙事,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性的“通史”序列中加以定位。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时间”对中国历史的演化进程起着强制的定性规范作用,故“封建”作为一种历史阶段尽管早已在中国消失,但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思维逻辑仍然习以为常地被加以使用,即是因为只有把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某个阶段强行纳入“封建”的诠释框架,才能突显出近代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接轨状态。因此,在用“世界时间”所规定的历史逻辑规范中国历史特质等方面,“革命史”叙事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说”犹如一枚银币的正反面,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只不过一方强调外力冲击的负面作用,从而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兴起提供合法性解释;另一方则强调西方冲击结束了中国历史的停滞状态,更加彰显其正面的影响力。
即使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当中国史学界迫于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一度全盘接受现代化理论的支配时,仍然可以看出其与革命史逻辑的深层相似性。在80年代,革命史叙事迅速退潮进而向现代化叙事转化所持的理由,恰恰说明在一些认知前提上两者存在着一致性。比如传统唯物史观坚持经济发展作为原初动力可以连带决定社会文化变迁的趋向,也同样为历史研究中的现代化模式所接受。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模式均认为,只要中国率先在经济领域实现现代化,就一定能自动引领社会文化向正面的方向转化。更具体而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那些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封建毒素”就会越快地遭到彻底清除。这种机械的“连动模式”不久就遭遇到了巨大挑战。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呈现出了高速发展的势头,按上述“连动原理”的决定论逻辑,与之相对抗的地方社会习俗和传统文化必然会被荡涤殆尽,仿佛轻易就会置换为与现代化模式相配合的新型文化。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东南经济富庶区域出现了大规模的“逆现代化行为”,这些“逆现代化行为”包括重新倡导敬宗收族,重修族谱庙宇等回归传统的现象,一时间祭祖崇先层出不穷,拜庙敬神遍地皆有,这些原先属于“封建迷信”的行为呈大幅回潮之势,完全违反了“连动原理”所设定的思维逻辑,至此接替革命史模式出场的现代化模式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实质乃是在于,东南宗族重振与拜神运动的复兴通过区域空间的异动消解了以“世界时间”为主轴诠释近代中国变革的刻板思维的有效性,因为无论是革命史叙事还是现代化叙事,其观点虽然表面对立,实际上仍没有逃逸出“世界时间”所规定的直线演进轨道,这也逼使中国史学工作者在面对复杂的中国历史状况时,必须重新思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解释工具才更有说服力。
当然,中国史学的“区域转向”也受到一些外缘因素的影响,如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其核心涵义即是把中国历史作纵向和横向的切割划分,然后予以重新审视。“纵向”切割是指从过度关注上层精英阶层转向重视下层民众的生活,“横向”划分是指把过于广阔的中国缩微到区域一级的单位进行检视,这就是后来历史学者常挂在嘴边的“眼光向下”研究取向。“中国中心观”是美国中国学内部研究范式转变的一种表述,与中国史学的内部转型不能等而论之。中国史学研究出现“区域转向”主要仍是因为现代化理论无法回答日趋复杂的当代中国现实问题时所进行的一种方法论自觉调整,“中国中心观”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只不过恰恰契合了中国史学从单纯遵循直线进化的时间观到倾力考察空间样态的多样性的内在自我转型要求。
二、“区域转向”的方法论依据及其后果
中国史学出现“区域转向”无论是受迫于现实问题的逼促,还是源于“中国中心观”的启示,都不约而同地共享着一个人类学式的思考前提,即均把基层“社会”作为观察对象,从而与以往把“王朝”或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作为核心考察对象的解释模式对立起来。近年来流行一时的“国家”—“社会”依存互动的分析框架即是此方法论取向的反映。但是,中国是否存在着类似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峙结构令人生疑,故过于强调二者区别的西式分析方法显然无法被直接套用。中国“社会”更像是以村庄为单位的有机细胞群,其与“国家”的连带关系也从未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故首先以村庄为细胞单位做切片式检视,可能是了解中国“社会”独特形态的一条有效途径。这一时期,以村庄观察为切入点的“民族志”研究蔚然勃兴,逐渐构成了历史人类学解释的基石,当在情理当中。
中国史学方法论的借壳转型,甚至可以较为粗略地概括成从以社会学理念为主导模式向人类学方法转变的过程。因为素为中国史学所借鉴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上沿袭的是西方社会学传统,马克思在西方即被称为与韦伯、涂尔干并列的社会学三大家。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学继承的是一种“社会学”传统,其明显特征是专注于描述历史的长程演进所构成的因果关系。而人类学方法则更注重基层社会历史在现实状态下是如何被复原与重构的。不过人类学方法在中国的村庄研究中至少面临着两重困境:第一重困境是研究者的“身份认同”问题。人类学家吉尔兹曾经担心,当一名研究者参与田野观察时,有可能因为过度认同于研究对象的文化处境而最终丧失自己的反思和判断能力,当然他也同时担心对观察对象的历史文化脉络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解会导致得出武断的结论,从而造成另一种偏颇,因此研究者需要具备高度的感觉平衡能力。
中国历史人类学学者也同样面临着上述“身份认同”的挑战。因为当代大规模的宗族与庙宇复兴运动大多发生于东南一隅,其他区域只是零星有所发现,构不成与之相匹敌的规模,这就使得中国历史人类学局限于某个地区进行“区域”观察的个别性特征表现得相当明显,难以泛化为普遍的解释力,进而可能形成“在地化”的困境。①即研究者基本上是从某个特定地区成长起来,其优势是熟悉当地的语言和社会习俗,有利于在田野调查时与民众直接进行沟通,以便近距离观察其生活样态。劣势在于研究者可能受限于“在地化”的身份,从而不自觉地把某个特定“区域”的现象升格概括成更为普遍性的结论。
“区域转向”有可能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合理有效地界定研究单位?我们是应该如人类学所要求的那样把文化视为一个“孤岛”,只在本地意识框架的传承脉络内部理解民众生活,还是应该把文化定位为一个处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支配之中的全球地理性现象?特别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呈跨国体系到处渗透的局势下,文化的“地方性”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保持其纯洁度?均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人类学家有时只强调对既定“存在”着的历史现象进行观察而不顾及历史“因果”关系的梳理,他们认为,过去的大叙事就是因为过度迷信历史大都是由某种因果链所支配,才造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统领下历史观的日趋僵化。然而,如果不加思考地拼命奔向另外一个极端,其后果也同样不妙。以柯文为例,他早期的著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仍采取的是“冲击—回应模式”,把中国划分为沿海和内地两个区域,认定沿海的近代化进程连带促使内地发生转变。外缘的压力显然被当做改变近代中国的决定性动力。而在前些年出版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由于受到人类学方法的深刻影响,柯文明显转向了“后现代”立场,把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完全视为中国内部孤立发生的历史现象,而基本弃绝了其民族主义的源起背景。结果在他的眼里,义和拳民不外乎是一群操弄巫术的群氓,似乎与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没有什么关联,如此极端的说法同样缺乏说服力。
有鉴于此,有些人类学家发出了和解的呼声,希望将研究对象牢牢置于历史事件之流,以及长时段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运作之中,力求在这两种不同诉求之间达成和解,这将使人类学与历史学聚焦于一个共同的对象,一种由多元的,既流动又受限的成分组成的、历史性而异质混杂的世界体系,在其中,“岛屿”与“世界”相互制约但不能被对方简约。②
除了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较易使村庄一级的基层组织被固化为封闭的细胞单位之外,另一个人类学派别对象征符号的解读同样影响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趋势。因有感于功能学派对文化现象时常做出过于功利的解释,“象征人类学”强调“文化”相对独立的意义,其具体的方法是注重对田野考察对象进行深描,只阐释研究对象在特定历史语境内的当下意义,而回避深究其背后有可能发生变迁的历史动力机制和政治社会涵义。经过如此“深描”出来的历史图景往往精致好看,甚至细腻入微到相当诱人的地步。但这类研究犹如绘画中的静物写生一般,基本无法看清静物设置的背景和空间参照物。
对“文化”进行极度深描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历史对象到底要阐释到何种程度才是合理的?或者说,我们无法为“深描”的确切性厘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也就无法在“深描”与其他解释模式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关联。当年年鉴学派第三代群体曾标榜“心态史”的研究取向,也曾遭到类似的质疑,那就是以何尺度衡量“心态”的范围与内涵。
为了和“功能论”相对抗,象征人类学特别强调对“仪式”本身做深描式的解读。但大量细节的披露却把颇具活性的“仪式”内容给严重固化了,其后果可能会导致对历史变迁复杂动态过程的漠视。因为,对“仪式”的深描过度强调参与者力量的自身凝聚作用,或者说是对共同体团结机制的重视,却相对忽视“仪式”背后有可能发生的转型、冲突和权力渗透与更替等问题。“文化”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维持秩序、意义和社会团结的精妙机制,这容易造成一个后果,那就是对“仪式”的所有解释摹本都是可以互换的,比如我们知道“中山陵”、“岳飞庙”和“黄鹤楼”都是作为某种政治或文化符号被加以解读,但我们如何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异何在呢?表面上看,这些建筑都是纪念某个特殊历史人物或登高望景的产物,我们却无法发现这些建筑符号背后更深远的历史动力机制是如何产生的。人们似乎并不关心国民党利用中山陵和乾隆帝祭奠岳飞庙背后政治权力运作的差异是什么,而只是热衷于把它们笼统定义成权力运作的范本。如是解读下去,各种建筑、仪式符号之间的意义就完全可以互换,就像一个无所不包的笼子一样装载一切类似的东西,而没有必要顾及其历史发生语境的具体差异。
同样道理,在区域史研究中,对宗族与祭拜仪式的大量重复性工作也是从深描入手,却无法洞悉其背后与整体历史的关联意义。目前有些研究者痴迷于大量收集各类碑刻等地方史料,却无法真正理解这些碑刻中所记载的各类仪式史实如何与广阔的历史背景建立起有机联系。在我看来,对仪式和象征等民间要素的文化研究必须与传统民族志方法,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甚至与他们所反对的“功能论”解释形成对话才有出路。
关于“功能论”的作用,我们可以回溯到费孝通先生有关近现代中国农村演化的观点进行一些辨析。费先生曾经区分“欲望”与“需要”的异同,在他看来,乡土中国的民众基本上由一种朴素的“欲望”所支配和行事,一旦进入现代社会,“欲望”就无法指导人们的行动,而必须根据理性设计的“需要”计划和安排生活。所以他的结论是人类发现“社会”也可以计划,是个里程碑式的重大转折。费孝通把这套“功能论”观念运用于观察中国乡土社会,发觉进入近代时期的中国人开始把生存条件变成了自觉,并用“需要”的标准去区别于传统的“欲望”。③
其实,近现代中国的农民的确遵循着某种“需要”的规则,但这种需要未尝不是传统“欲望”的一种变相表现,无法完全用文化象征主义的方法予以单独分析。此处不妨以我在陕南调查的有限经验加以简略的说明。我调查的村庄曾经有一座庙宇,“文革”期间被拆除,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担心政治运动卷土重来,村民不敢重修庙宇,只象征性地搭了一个简易的石头棚子,把它恢复成一座简陋的小庙,里面一座佛爷像也被寻回重新安置在小庙里,这个重建的庙宇似乎很适合作为人类学象征学派的解读对象。据传这座小庙中那佛爷像的头颅曾在“文革”期间被人砍下后丢失,“文革”后由人找回后勉强重新置放在残缺的身子之上。有趣的是,这颗不固定的佛头却几次被乡民偷偷移动。第一次挪动的原因是佛头正对着的东北方向的一家不但连生几个孙子和外孙,还随后成了大学生,仿佛是神灵佑护的结果。于是有一天,佛头就神秘地移动了,面孔正对着西北方向的另外一家,据说后来这家也发达了,于是神头又再次遭到挪动。由此事例可见,人们信仰某个神祇的心理仍然与具体的利益诉求有关,很难用西方的信仰标准和动机予以说明。这也恰恰印证了费先生对文化的功能性解释。这个例子还证明,乡土民众自近现代以来的各种“需要”与传统的“欲望”之间未必能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也许一直存在着某种传承性。
同样道理,象征人类学方法对目前正在兴起的新文化史研究也有广泛的影响。在有关18世纪英国习俗社会的研究中,汤普森曾经表示,关键问题往往不是变化的过程和逻辑,而是要对过去时代意识形态状态和社会、家庭关系的重构过程进行缜密分析。即中心问题是存在(being),而不是生成(becoming)。④既然是对“存在”的描述,那么各种以往为我们所忽视的历史细节自然会浮现出来,统统成为审视的对象。近些年来,各种属于“物质文化”形态的历史越来越受到重视大约与此有关。诸如从脚踏车、巴士到煤油灯与家庭照等近代现象的出现均在探索之列。由于强调对“存在”的细节描写,这些文化形态的生产过程往往被有意忽略,或仅以现代性转化的断言概而论之一笔带过。一篇文章读起来往往会使人沉醉于不厌其烦地细腻描写的愉悦感之中。对“物质文化”形态的呈现也往往集中于富庶地区或著名城市,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这类研究仍可算是社会史“区域转向”的一个另类表现。比如对所谓近代城市的“现代性”研究往往大多设定于“江南”等文化变迁明显的地区,或者如上海、北京、汉口、成都这样的大城市,至多偶尔涉及那些颇具文化韵味的小镇风情,观照的时间段可以从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早期,观察人群也多聚焦于士人群体或底层女性。故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新文化史”研究确实承接了社会史研究“区域转向”的基本走势,但两者又有不同。
其区别在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更强调基层传统在现代世界中的延续性及其再造的可能,而一部分新文化史研究者除了少数人出于怀旧心理对一些士大夫生活故态深表留恋,从而被视为具有“后现代”倾向外,大多数人则更强调传统所发生的变化在塑造国人近代生活品质方面的重要性。因此,“新文化史”方法在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中日益得到了广泛运用。然而,“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在中国的移植至少面临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打着“文化史”旗号对各种所谓“文化”表象的描写与叙述,特别是对文化消费趋势的阐释与迷恋,如对明清至近代以来各种消费现象不加甄别的深描式记述,极易模糊和遮蔽一些具有自主性的问题意识。故有人讥刺这种研究取向的转变是从“经世济民”到“声色犬马”。我们除了和西方学界共享一些文化细节的有趣观感外,很难断定,这类文化研究的主旨仅仅是为了论证中国在明清之际就已出现了“早期近代”的征兆呢,还是仅仅为了昭示出明清到民国初期消费主义的奢华竞逐已泛滥到与西方近似的地步?如果是前者,那么文化史研究的目的难道只是为了论证西式近代化在中国提前实现了若干年吗?那岂不是又变相跌入了现代化论的圈套。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类文化史研究似乎不过是为当代消费主义盛行提供某种历史合理性依据罢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强调研究者以经验主义的方式介入历史过程进行叙述,的确为恢复中国史学的优美叙事传统打开了一扇窗户,不过如果研究者过度沉迷于研究对象所经历的那种生活方式,或沉溺于士大夫和晚清遗老的生活品味之中而不能自拔,对此仅仅简单地持一种诗意的怀旧感伤态度,那么也有可能使中国近代史研究丧失自身的反思和批判的立场。我个人认为,史界出现的所谓“碎片化”倾向,也与文化研究者过度沉迷于复古体验和对此体验的过度消费有关。
如果进一步深究原因,即可发现,新文化史研究正是因为过度沉迷于生活细节描述本身,遂无法与其他相关政治社会历史状况的解释模式之间形成有效的关联。西方的社会史或新文化史研究虽然主要关注仪式与象征行为的意义,却仍力图与整体性的各类政治行为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如汤普森尽管否认阶级意识的首要作用,强调工人的经验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却并未完全忽略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政治与制度建构的背景。林·亨特探讨法国大革命的仪式与象征文化,并非抱持一种优雅逍遥的品鉴心态,而是为法国大革命政治行为的动因做补充说明,探究的仍是政治的文化表现形式,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戴维斯的文化史观涉及女性支配和暴力仪式中为人所忽略的细节,试图回答的则是各种文化现象是否可以成为社会控制的安全阀等广义的政治主题。由此看来,如果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无法在文化现象与政治社会问题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言说关系,就难免会加剧史学研究的“碎片化”趋势。
与之相关的是,大量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涌入中国史界之后,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转向造成了深远影响。“后殖民理论”强调从跨区域跨文化的角度探究原属于封闭系统中的历史现象,它促使我们意识到,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西方的文化生产机制密不可分,往往是西方想象制造出来的产物。可如上观点一旦被推至极端,就极易堕入“文化相对主义”的逻辑,甚至简化为一种单纯的“阴谋论”,仿佛所有近代中国文化现象的形成大多是西人有意设计的结果。比如有关近代中国“国民性”的讨论,中国学者由于太受萨义德东方主义思维的制约,颇有些反应过度地认为,西方把中国作为“他者”加以塑造的目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为了满足西方中心主义的虚荣心。因此所有对中国文化价值和道德人格的批评都是别有用心的歪曲,肯定会服务于某种险恶的殖民目的。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者又仿佛可以凭借对“国民性”话语的批评,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归提供一个有力的历史佐证。如此过度反应的结果就是,中国文化仿佛就像一块纯洁无瑕的美玉,只是在受到西方污染的情况下才变换了颜色。“东方主义”恰可作为清算“五四”批判传统文化的挡箭牌加以反复使用。如此奇怪的思维导致西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反而成了国人进行文化自恋的资本。而事实则是,当世界发展到近代阶段,不同类型文化之间一定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中演进的,不存在一种“文化”仅凭单方面的极端想象就被轻易加以塑造的可能性。
三、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整体史”?
中国史学研究出现“区域转向”后,各种微观研究大受青睐,但由于研究单位和对象发生变化,中国史研究从整体上似乎缺乏一以贯之的宏大气势,故又常被讥之为有趋于“碎片化”的危险。言外之意,如果不找到一种“整体史”的研究路径,任何局部研究都很难真正获得合法性。或者说在人们的心底里,“区域研究”只能作为“整体史”的附属品才有存在的价值,或者只能为“整体史”的解释做基础准备。“区域”与“整体”被作为截然对立的两个范畴加以看待。然而在我看来,如何严格地界定“整体史”并非易事。因为以往的叙述显然太过于依赖世界史的普遍演化框架,所谓“整体史”基本上就是世界普遍历史发展逻辑的一个中国式翻版。
在我们的印象里,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罗代尔对世界历史长时段的分析应该可以归入“整体史”的序列,特别是其对环境因素如何制约历史长程发展的观点,可以直接与国内传统的政治经济史叙述遥相呼应。近期兴起的“全球史”解释也延续了这一思路。比如最近译成中文出版的美国全球史教材《世界:一部历史》即并非以各国的王朝更替兴衰为据搭建整体的诠释架构,而是以马赛克拼贴式的发散叙述展开多重线索,突出世界各地之间生态变迁与经济政治文化的网络互动关系。只是这套解释如果直接嫁接到中国史的叙事中也可能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主要是在处理“人”的活动与自然关系时需要大量资料的积累,否则难以构建起连续性的图景。
还有一种重构“整体史”的倾向,即通过“边缘研究”取代“内涵研究”的方式重新勾勒中国文明史的地图。所谓“内涵研究”是指以“中原”或“江南”等汉族文化发达地区为中心,并以其向周边扩散的过程作为界定中国文明内涵或解读中国历史演变的核心依据,形成了“中心—边缘”的对称解释关系。“边缘研究”则希图通过对散布于“中原”或“江南”地区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为观察切入点,从边缘如何塑造“中心”边界的视角重新梳理核心与边缘的关系,探讨“中国”形成的复杂态势,以及华夏文明的构造特征。近几年美国兴起的“新清史”研究也大致可归入此类模式。上述研究均从“边缘”地带出发,力图打破传统叙述所设定的“中心”表述逻辑,比较关注清朝对新疆、蒙古、西藏等地区的开发与控制,并把诸种控制手段与广阔的“内亚”大陆帝国的统治模式连接起来加以认识,故仍可视为广义的“区域史”研究,不宜以“整体史”视之。
如果我们再转换一个角度,仅从“空间”上来定义“整体史”研究,同样面临到底如何理解“什么是整体”这个问题。从实际控驭规模而言,清朝确实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统治格局,在空间上基本可以视为“整体史”的研究对象,但若从长时段历史演变中观察,这种统治格局只存活于清朝一个朝代,在此之前,大部分朝代均没有真正实现“大一统”理想。从时间上估算,中国分裂的时间还要略长于“统一”的时间,在疆域界限不断伸缩变化的境况下,如何界定中国历史的“整体”内涵和边界尚存疑问。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对“分裂”与“统一”聚分态势的描述和诠释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整体史”的研究方法,但就目前的探索水准而言,中国史界对历史发展线索与空间疆域治理过程尚处于初步勾勒的阶段,远远达不到构架整体认知图景的程度。也许在“什么是整体”这个问题无法厘清之前,把“区域史”与“整体史”对立起来,且抬高“整体史”地位,并以“整体史”研究作为史学最高境界和终极目的的想法在具体的历史叙述中根本无法实现。如此看来,“区域社会史”研究从剖析各个微观地域特质的角度出发理解中国历史作为一种变通选择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的,不应该被讥为“碎片化”倾向的源头,或简单评定其研究价值就一定低于“整体史”一等。尽管如此,“区域史研究”虽然至今已呈蔚然大观之势,或几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代名词,从事此类探索的学者却似乎仍难以摆脱内心的焦虑感。他们总是想证明“区域史”研究就是“整体史”研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们总是试图证明某一区域发生的现象恰恰是整个帝国的政治运作在地方上的投射,实际上以缩微的方式表现出整体历史的存在状态。我称之为“缩影说”。“缩影说”给人的最大困惑在于,无法印证某一地区性政治运行的状态就一定与整个王朝的治理规划相一致,抑或只不过是其某种局部的有限表征和实践。
面对以上困境,我们不妨再变换一个思路,尝试摒弃“区域”与“整体”二元对立的刻板模式,转从“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治理能力”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中国历史演变的轨迹和特征。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一个王朝或政权在建立之初必然要调动各种资源以寻求在政治威权统治上的合法地位。“合法性”要素包括疆域空间的拓展及其维系,各类仪式的设计和实施,多样族群身份的界定以及因俗而治分寸的把握,基层社会治理权限的厘定等方面。清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实得益于合法性政策的有效制定和运用,其实践理念显然与前朝大有区别。“合法性”问题一直会延续到近代历史的转型时期,比如晚清覆亡以及民国初年宪政政治的发生,到底是暴力革命的后果,还是逊位禅让的作用,目前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已经形成了某些争议。有学者认为,清帝逊位是一场类似英国近代变革式的“光荣革命”,由此形成了“宪政建国论”、“协议建国论”等诸种说法,以区别于“革命建国论”,这些说法都可视为讨论清朝统治“合法性”如何崩解,以及传统王政如何向民国政权让渡的新趋向。
所谓“政治治理能力”是指王朝所依赖的管理技术群体如何与皇权统治相协调,以及自身如何在最节约制度成本的情况下从容治理日趋广大的领土,以便建立起一个高效的官僚运行系统,特别是中层官僚与基层士绅之间的治理职责如何划分和相互衔接等问题仍有不少讨论的余地。这类问题的探索同样可以延展到近代时期。比如对诸如近代国家权力一直向基层不断渗透,导致地方文化资源遭到摧折流失等现象的考察均可成为政治治理技术视域下的重要课题。又如我一直认为,科举制并非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更是一种身份分配和教化系统,它能把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人群合理配置于不同层面,转化为有力的教化和治理力量,以配合官僚行政与地方体制的运作。科举制度瓦解后上下层教化机制的流通随即产生淤塞不畅的难题,最终导致拥有文化控制力的基层治理体系彻底崩解。以上所列课题在“区域社会史”和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研究中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探讨。例如区域史研究对宗教崇拜仪式在上下层之间存在互渗关系的辨析就可看做是观察“政治合法性”发挥效果的另一种方式。又如宗族控制的有效性与否也可以说是衡量政治治理能力的表现之一。未来的中国历史研究如果能从动态的角度理解上述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倒不失为进一步拓宽“整体史”研究视野的一个新路径。
注释:
①参见杨念群《“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美]阿勒塔·比尔萨克:《地方性知识、地方性历史:吉尔兹及其他》,[美]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③参见《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387页。
④[美]苏珊娜·德山:《E.P.汤普森和娜塔莉·戴维斯著作中的群众、共同体和仪式》,林·亨特编:《新文化史》,第53页。
不必担忧“碎片化”
王笛(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不少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其实,这种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在西方,过去史学家在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响下,主张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他们热衷于大历史的研究。但西方历史学界随后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特别是1970年代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对整体史提出了挑战,主张历史和文学的结合,强调历史写作的叙事性和故事性,然后又是微观史、新文化史的兴起。①史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特别是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题目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但这些研究最容易被诟病为“碎片化”。②
但在中国历史学界,我怀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为了一个问题;即使有了问题的苗头,但也不是现阶段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整体化研究是近代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家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够为执政者提供历史借鉴,犹如司马迁所说的,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界,更是把这种抱负发展到了极致,史家们或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或实现指点江山的抱负,结果复杂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被简单地总结成为了几朵金花、几次战争、几次革命高潮等等,众多的学者拥挤在若干重大课题的狭窄道路上。
最近二十余年来,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影响,宏观视野的通史性题目大大减少,专题研究日渐盛行,具体的小题目越来越受到青睐。但这种倾向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他们开始对“碎片化”进行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因为老一辈历史学家基本上是不研究“碎片”的。过去中国传统的精英研究取向,造成学者只关心历史重大事件、政治经济、风云人物等方面的研究,对芸芸众生和日常生活缺乏兴趣,或者认为没有研究的价值。其实,我认为,历史研究的价值不是由研究课题本身的重要性来决定的,而在于研究的历史眼光和历史解释,一些貌似平淡无奇的对象,史家却能从中发现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深刻内涵。史家对什么叫研究的价值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这经常是由他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所决定的。例如,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拉撒有没有价值?主张眼光向下、微观历史的研究者,当然会给一个肯定的回答。
现在我们讨论“碎片化”,是因为我们已经觉得这在中国成为了一个问题,认为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可否认,任何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个意义的理解却是很不相同的。不少批评“碎片化”的学者,认为意义一定是能说明一个大问题,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理解。难道我们不认为如果一个研究,促进了我们对历史任何一个微小方面的理解,不也是一种贡献吗?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弊病来看,我觉得应该容忍或者说宽容“碎片化”,因为“碎片化”的研究,毕竟解决了一个小问题。
其实,我们所说的“碎片化”,是针对整体化而言的,如果我们不使用“碎片化”这个词,用“局部化”来代替,或许我们会觉得“碎片化”并非总是消极的了。任何一种“化”,都存在消极的因素,关键是消极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说“碎片化”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结果,难道整体化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吗?难道我们可以认为整体化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值得提倡的积极倾向?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现存的中国史学研究的成果,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得多,而“碎片”或细节了解得少。而缺乏细节或“碎片”的整体史,经常是一种有偏差甚至谬误的整体史。因此,我更倾向于对整体研究持挑剔的眼光,因为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研究是整体旗帜下的空洞化、重复研究,人云亦云,了无新意。
学者认为史学“碎片化”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问题小,而在于“以小见小”。③一些研究者不能把其课题放到更大的宏观问题上去讨论,并不能说就不具备研究的意义。我们喜欢用“开拓性”这个词来说明研究价值,其实一般来讲,研究“碎片”比研究整体更容易创新。所以,与其要求没有多少经验、没有能力去把握整体、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甚至没有出茅庐的研究生)去思考大问题,还不如鼓励他们去研究“碎片”。他们的论文哪怕有一丁点儿新意,有一丁点儿独到的发现,也比那些大而不当、雄心勃勃、但没有任何独创的所谓研究更有意义。“以小见大”固然不错,“以小见小”也并非不好,即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而不是勉为其难地回答所谓历史的重大问题,或说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空话。也就是说,在任何研究中,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所下的结论,一定要在课题和所使用的资料所能支撑的范围之内。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被归入所谓“碎片化”的研究,也并非都是简单的描述,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努力探索历史的意义,虽然那些研究可能存在种种毛病,但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碎片化”,而是学术研究和写作的能力的制约。我们应该理解,课题本身经常决定了研究者最后所能回答的问题,若一些史家致力于一些政治性课题(如战争、政府、政党、思想等)的研究,我们当然期待他们的成果能够为我们了解中国政治变迁等大问题作出回答。而另一些研究课题,如物质文化的研究,我们的读者却不必有这样的期待。当然,如果有这类的小课题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或现实的重大问题,固然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但这不是我们总是应该期望的结果。
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没有局部,哪有整体?没有零件,哪有机器?当然,我充分理解一些学者批评“碎片化”的初衷,他们担心我们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迷失在细节之中,特别使他们诟病的是,这些年轻学者不能把小问题提高到解释大问题或从更宏大的理论高度来进行分析。而我认为,批评“碎片化”的学者,对史学研究要求太高,雄心太大,不满足对“碎片”(局部)的认识,似乎任何研究课题,都要提供对国计民生等大问题的深刻认识,才算具有了研究的意义。
所谓“碎片”和“整体”,就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整体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没有整体,但却不能没有碎片。一个技术不怎么好的技工,如果无法把零件组装成机器,零件毕竟还在,以后还会有高手利用这些零件组装机器。但如果没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机器。同理,历史研究没有碎片是不行的,这犹如机器没有零件。这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碎片”组合起来,让历史研究逐步趋向整体认识。所以,任何提供这些历史碎片的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整体的历史作出了贡献。以考古学研究的碎片为例,如果在地下发现了一个古代瓷瓶的碎片,一个学者对这个碎片进行考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碎片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史上存在的一件小事,一个微小的对象,不也是犹如考古学中对碎片的研究一样吗?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以城市史的研究为例,我们在日本的大学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一排排书架上,叠放着一层层关于东京城市史的作品,大到宏观城市发展,小到社区街道、上水下水、吃喝拉撒等等,我们就会深切感触到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是细了,而是太粗犷了。正如研究整体史的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指出的:我们对宫廷和宫廷生活的了解是事无巨细,但却不知道鲜鱼怎样装在水箱里被运到市场,在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野味的贩卖,我们从中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④这种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已有知识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布罗代尔所批评的对欧美历史的研究,而且中国历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较之现有之欧美历史,这方面的缺陷则更为明显。因此,“碎片化”在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的语境中,我认为并不是一个明显的问题,甚至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研究小问题、研究“碎片”的历史,不过仅仅才开始,等十几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再来纠正也不迟。
说到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史景迁的研究就相当“碎片化”,如他的《王氏之死》、《胡若望的困惑》、《书的叛逆》等,把各种零散的资料、各种碎片组合在一起,没有理论分析,没有学术回顾,没有主要论点,不过建构了一个历史叙事。⑤另外,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人类学的研究就相当碎片化,他们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一切方面,非常繁琐,但人类学并没有碎片化的担忧。人类学在中国是新学科,它没有中国历史学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雄心壮志,他们热衷于小问题,并不认为宏大问题就优于微观研究。
碎片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方法论、史学观等的不同,我们的历史认识和眼光都有相当的局限,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我们还不能认识到这些碎片的意义,但是,当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随着方法和史学观点变化,我们可能发现过去看起来似乎没有意义的碎片,其中却蕴含非常有意义的玄机。犹如我们拼图一样,在碎片缺失时,不可能拼成完整的图形,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碎片组合在一起,完整的图形就逐渐展现出来。历史的碎片也是如此,我们了解的碎片越多,便越接近对历史的整体认识。
总而言之,在这篇笔谈中,我想指出四点:一是“碎片化”并不是消极的;二是整体化和“碎片化”共存;三是碎片和整体的研究是同等重要的;四是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中间作出选择的话,宁愿选择“碎片”。不过这里我应该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我们有理由忽视整体研究,而且对那些研究大问题、加深我们对中国和历史重大问题认识的学者抱着极大的敬意。其实我理解,大多数担心“碎片化”的学者,并非反对研究小问题,而是强调研究不能停留在小问题上,而应该把这些小问题同我们想探索的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把小问题的研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希望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我们对小问题或碎片的研究过于苛求,就会使研究者望而却步,甚至造成过去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挤在不多的重大题目的狭窄道路上。毕竟,研究“碎片”撞车的机会少。而且,对碎片的理解越丰富,对整体的研究就越有利。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建构完全客观的整体历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探索是永无止境的,过去的历史就永远过去了,史家力图利用各种途径去重新建构逝去的历史。但无论他多么努力,多么公正,方法多么正确,资料多么丰富,他建构的历史,也是带有主观性的。兰克所憧憬的所谓客观的历史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任何历史写作都不可能脱离主观或自我意识,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真实和完整再现的。根据历史资料建构的历史,都是主观性的历史,也即是说,我们所写的历史都是通过我们所理解的历史,无非是我们眼中或头脑中所反映的历史,因为历史观、方法论、阶级立场、政治观点、个人背景、种族、文化、语言、思维习惯等等,无数的因素都制约了我们写出完全客观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写的历史,无论我们有多么深邃的眼光,多么远大的抱负,多么宏伟的叙事,也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碎片,至多有的碎片要稍微大一些而已。
注释:
①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Hayden White,The Fiction of Narrative:Essays on History,Literature,and Theory,1957—2007.Robert Doran(ed).(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0).关于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参见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6—140页。
②例如关于厕所和大粪的专著就洋洋大观,以下是若干例子:Julie L.Horan,The Porcelain God: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oilet(Carol Pub.Group,1996);Wallace Reyburn,Flushed with Pride:The Story of Thomas Crapper(Fourth Estate,1998);Penny Colman, Toilets,Bathtubs,Sinks,and Sewers:A History of the Bathroom(Atheneum Books for Young People,1994);Nelson Yomtov and Barbara Penner,The Grimy,Gross Unusual History of the Toilet(Capstone Press,2011);Dominique Laporte,History of Shit,trans.Rodolphe el-Khoury and Nadia Benabid(The MIT Press,2002);Daye Praeger,Poop Culture:How America Is Shaped by Its Grossest National Product(Feral House,2007)。
③胡永恒:《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综述》,未刊稿。
④Fernand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1400—1800,Vol.I,trans.Miriam Kochan(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5),p.430.
⑤Jonathan Spence,Death of Woman Wang(New York:Viking Press,1978);The Question of Hu(Vintage Books,1989);Treason by the Book(New York:Viking Press,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