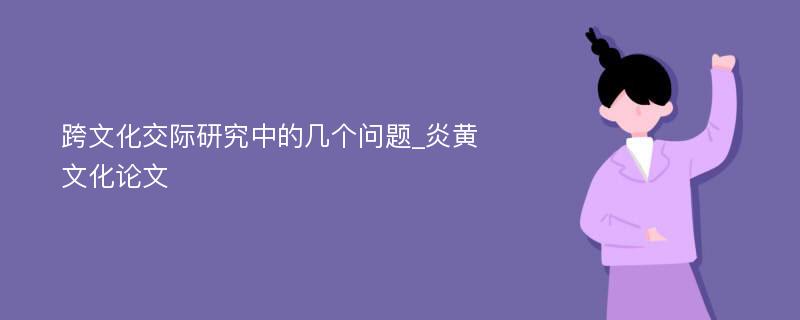
跨文化交流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1996年8月14—1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与世界:面向21世纪的传播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大会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国际政治系)国际文化传播研究所(现为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系)和美国肯特州立大学传播学院主办,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美国中国传播学学会协办,全国10个省市的50名从事传播和文化交流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新闻学院等28个单位都有人员参加,我国香港和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的与会者有52人。
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80余篇。这次学术讨论会涉及了传播学的诸多领域,本文是对其中跨文化交流学研究论文的综述。
跨文化交流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与会者从哲学、政治传播中的文化影响、中美人际交流上的情感上的差异、中美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异同、中美人际交流中的语言问题、中美商务谈判上的差异等多种新角度对跨文化交流学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跨文化交流能力研究中的哲学问题 日本学者宫原哲(Seinan Gaknin大学传播研究所)在题为《传播能力上跨文化研究的哲学问题》的论文中提出,在跨文化交流研究中,把西方文化中创造出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运用到亚洲文化中去,可能会对亚洲人运用的交流策略作出错误的描述和解释。该文以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跨文化交流研究的一个通用尺度)不能正确地描述日本人传统的传播特点为例指出,目前进行的大多数研究使用的观点,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者(大多数是美国研究者)所阐述的观点。由于缺乏对日本特定文化的人际交流能力概念的理论框架,就限制了对日本人交流的描述和解释的准确性。作者提出了进行人际交流能力的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考虑面临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哲学问题的重要性。
该文首先指出,霍夫斯特德提出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尺度(对集体主义者的界定是个人的目的服从于集体的目的。他们对和谐、相互依靠的关心他人有明确的意识,在一个集体主义文化中,集体的决定比个人的决定更受到赞成,个人的决定不受到赞成,一个人的特征是基于与内部集体的关系,有强烈的“我们”意识)难以正确地描述日本人的传播能力。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发现,日本人的传播行为中,给予集体的关心只限于自己认为要十分忠诚的群体之内。因而,与霍夫斯特德研究的那些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的社会行为绝然不同。同样,从“正直”和“真诚”这两个美国人来说是重要的交流能力的规范来看,该规范与日本人的价值观,例如保护脸面,不一致。因而,在行为方面似乎是有其他倾向日本人的交流可能被认为是“欺骗”,“不真诚”、“不道德”的。一般来讲,很多亚洲人,特别是日本人,当需要时,是很看重克制个人的感情的。这说明,把美国的人际交流能力的标准应用到日本人,就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会导致文化上浓重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特色。这里,在确定日本人人际交流能力构成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issues):日本的个人可能进行选择在特定的场合运用相应的交流策略,这种选择基于该人对情境特质的感知,而不是该人独立自主的目的。从认识论上讲,为了建立一个日本人际交流能力上一个有道理的理论,他必须在广泛的不同社会情境中考察人们对“称职的交流”的感知。
关于传播能力研究中的本体论的问题(ontological issues),宫文指出,日本人对自我的观念与西方的交谈者不同。日本人中的“自我”概念从个人中引出的不如从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引出的那么多,取决于他人是谁,自己与该人的关系属于哪一种,每个人需要去调整交流目的和行为举止,这就产生了交流目的,及达到这些目的的方法多种多样。因而,对他人表现出敏感,以及调整自己的交流策略是成熟的象征,同时,这样做又有助于日本获得他人的认可。日本人一直被认为在交流中缺乏个性,具有集体主义的和高语境倾向。但是这些特点是通过与那些文化倾向有诸多不同的人们进行跨文化比较得到的。例如,Hamaguchi提出,日本人一直被认为是集体主义的,只是因为他们不是个人主义。同时,日本人民在与他人关系中如何发展和维系自我特色的问题可能一直被歪曲,或被忽略了。认为既然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对,集体主义把人民的总的集体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因而这样的西方式的两分法未能考虑到日本人的社会行为。在日本,人们存在的基本形成既不是个人的也不是群体的而是情境的。这里提出了在西方人和亚洲人的人际交流领域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本体论问题:
一个人看待自己与他人的距离在日本社会要小于其他社会,特别是更具个人主义倾向文化的社会,例如美国这样的社会。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分析的单元,不应是太集中于个体和独立个人作为其关于环绕着的与他人关系的感知。
在交流能力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methodological issues),该文指出,许多至今进行的研究都是典型的“etil”(语音学的)研究,利用的各个概念都是由西方人界定和发展的。例如,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两分法,就是一个由西方研究者阐明的“emic”(音位学的)概念。在大部分跨文化研究中所讨论的有关人们交流行为中的区别是“科学的”和“客观的”说法,可能只是西方emics强加性观点的一个结果。在亚洲文化和欧美文化进行人际交流能力的系统跨文化比较时,更需要对亚洲人传播行为进行更多的emic分析。emic方法的目的是从内部发现一个系统是如何构成的,emic方法将有助于从亚洲及交流者的观点进行界定分类和界定行为规范。参加观测是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etic方法将有助于通过外部观察人们的行为进行文化比较。
虽然许多关于人际传播的当代学者很大程度一依赖于使用统计来证明、支持和加强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可能限于一种狭隘的观察模式和解释模式。如果他们进行研究时,以自己文化标准作为证明结论是有效的可行的这样一种僵硬的概念框架开始的话,那么他们可能错误理解、错误解释或忽略不同文化人们进行交流时的重要特性。任何脱离其僵硬概念框架的交流行为,可能会简单地标以特殊的奇怪的低效率的行为。更注重定性的研究,以一种开放和灵活的概念框架去简单地观察交流行为,则可能会导致对亚洲人社会活动的更为准确的描述。在充分的emics被界定后,把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一起用于研究,将会是很有意义的。该文提议:从一些亚洲国家来的研究者可以进行合作,以便界定emics,或是与亚洲文化相关的相应的交流概念。在交流能力上的相似易于被彼此理解,当然也很容易在传统的跨文化交流研究中被忽视。绝大多数跨文化比较研究是在以下对比中进行的:美国与日本,中国与法国,韩国与英国等等,而亚洲各国之间的比较,像日本与中国,韩国与日本之间的比较研究至今很少看到。为了界定亚洲人际系统的特点和对交流能力的理论化,研究者需要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搜集充分的emics。亚洲类似文化的跨文化比较可以产生出有用的结果。
宫原哲的意见对于那些致力于开拓亚洲各国带有本国特色的跨文化交流学的研究,避免跨文化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以准确地描绘各国的交流能力,很有参考价值。
中美跨文化交流中的情感方面的文化差异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陈向明副教授在《中国留学生在美大学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一文中,用系统的定性研究方法,对9位在美国波士顿地区的著名院校的中国留学人员(年龄23—46岁,其中8男1女,5位学自然科学,4位学人文科学,均取得学士以上学位)进行了1年的跟踪调查研究。对学术界关于中美人际交往中的价值(中国人有群体倾向、注重人情与和谐,美国人有个人主义倾向,注重个人的独立和竞争)差异上的笼统论述,进行了深入研究。她通过被调查者常用的用中国人的概念,如“人情”(human feelings)、“情感交流”(emotional exchange)、热情(externally warm)、温暖(internally warm)、自由(freedom)、自在(freeness),来区分中美在跨文化人际交流上反映出来的文化差异。其研究结果如下:
人情 在人情方面(被调查的中国留学生所说的人情的成分包括:关心、照顾、帮助、体谅、容忍、留面子、表达含蓄)中国人的人情要比美国人浓得多。美国人人情味淡,体现在美国人对这些留学生的事不管不问。由于美国人更看重个人的独立和隐私(privacy),美国人在问及中国学生的生活方面缺乏主动性,以至于使中国留学生感到美国的人情要比中国淡得多。
情感交流 情感交流的英文译文是emotional exchange。该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情感交流和美国人的emotional exchange不同。美国人的emotional exchange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宣泄自己的生理感觉和心理感情。而中国人的情感交流是更为彼此的交流,并带有以他人为主的倾向,表现对他人的关心。在中国看来,如果说一个人没有情感,不是由于该人缺乏哭或笑的能力,而是对他人没有同情心和不能设身处地替别人考虑问题,是个冷酷无情的人。美国人的emotional exchange中,美国人主要考虑的是发泄自己的感情,而不必向他人敞开自己的心扉。在中国人的情感交流中,交流者的心和所有的感官不得不向他人敞开,以便感觉他人心理正在进行的心理活动。正是这种文化差异使得许多被调查的中国留学生抱怨道:“在美国没有情感交流”。而许多美国人则认为“你们中国人不表述情感”。中国留学生认为,美国人交流“情感”的方式不同于中国人。中国人的情感交流是委婉的和微妙的,而美国人的是明确的并用言语表达出来。典型的美国人的“emotional exchange”是向别人大声说出自己的感情。而中国人的情感交流不是那么直接、明确,并不一定用言语表达出来,当一个人与他人呆在一起或共做一件事时,一个人可以通过非言语的信号和婉转的表示进行静静的或深深的情感交流。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比美国人更精致更微妙。
热情与温暖 这对词浓缩了中美文化在表达情感方式上的差异。尽管中文的两个词在意义上有区别,热情强调的是外在表现,在遇到他人时可以看到的热心;而温暖更强调的是在和他人接触中的内在感受,是内心看不见的一种感受。在英文中热情和温暖都是warm,正像“motional exchange”和“情感交流”这对词一样,热情是自我的表现、是外在的;而温暖则是以他人为中心的、是内在心理的。热情不等于温暖。由于美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较为明确,中国学生如果未感受到言语下面的情感互动,就会只感到美国人外表上的热情,而未感到内心的温暖。由于中国留学生坚持获得温暖是通过人的互相交流获得的,所以他们在美国没有发现他们所期待的那类中国式的情感交流。
自由与自在 这些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后,都有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并未确保他们日常生活的自在。作为美国主流圈子之外的局外人,这种自由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意义。由于中国学生不熟悉一种新文化中的各种规范,他们发现自己干起事来很笨拙,对发生的一切很失望,对自己和周围的人不满意,他们也不知道错在何方。他们不得不忍受着一种无根的、在空中摇摆的不舒服的状态。
总之,通过对中国留学生使用的一些中国概念的探讨中,可以看到,由中国文化所构造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规范影响了他们与不同文化的人民交流的经历的解释。在两种文化相遇后,中国留学生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价值观、信仰和行为规范的原来涵意,并重新检验了在自己家乡文化和母语中一些通用的表达方式的文化涵意。
从陈教授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她的研究结果使我们对中美跨文化人际交流中在情感上的差异及障碍的了解深入了一步。
中美跨文化交流中交流能力的异同 美国都恩大学钟玫博士在《中美交往中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一文中首先回顾了文献中关于“人际交流能力”和“跨文化人际交流能力”的论述,然后利用马丁(J.N.Martin)和哈莫(M.R.Hammer)的关于跨文化交流行为的四个主要方面(非言语行为、语言行为、会话控制行为、交流功能)设计了调查问卷,对美国中西部地区一所大学的150学生以及侨居美国的74名中国学者和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一系列的统计数据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的被调查者对于问卷内容中各项的看法没有明显差异。总的来说,两组均认为在衡量一个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时,交流功能方面的因素最重要,其次是会话控制行为和非语言行为。调查中惟一显示差异的一项为语言行为。美国参加者比中国参加者认为语言行为重要一些。作者指出,由于收集到的中方调查问卷较少,而且中国学者在美国生活了近5年,受到了美国文化的涵化,可能影响了结论的代表性。
跨文化交流中的语用问题 语用问题是本次讨论会中一个谈论较多的话题。北京大学英语系封宗信博士在《跨文化交流语用原则与跨文化交流失误》文中,对跨文化交流中的语用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他首先评述了语用学的权威学者的有关论述:语用学专家格瑞斯(Grice)的“合作原则”认为,人们在交谈时是互相合作的,交谈双方怀着一个共同愿望:相互理解、共同配合。但是实际上人们并不总是遵循这些准则,而是一方面遵循另一方面故意违反他们。利奇(Leech)认为格瑞斯对人们违反合作原则的根源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又提出了“礼貌原则”,认为人们违反这些准则是出于“礼貌”的需要。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冲突与准则的先后取舍是研究人际交流的关键,跨文化场合的人际交流更为复杂。
合作原则首先是一种配合性规约,它具有规定性。它的次准则是衡量讲话人违反会话常规的具体标准,对产生“会话含义”有描述性和解释性。礼貌原则同样具有规约性和解释性。由于跨文化交流双方不共享交际规约,所以一方未必总是能按另一方的期待去理解他的话语含义和元信息(metamessage)。尽管合作与礼貌各准则之间的冲突和先后取舍有文化差异,但“人际修辞”有跨文化的共性,差异只是表现形式上的不同。恰恰是表现形式的文化差异使语用原则各准则之间出现的“冲突”在跨文化场合造成交流失误。
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始于80年代。在中国,跨文化语用研究大都停留在探讨文化差异上。大多数研究主要列举中外交流“失误”体例,仅从语用学角度或从文化因素出发进行解释,几乎一致把失误的根源归结为中国学生的语言行为不当,并建议外语教学中应加强外国文化内容等,很少对影响跨文化交流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该文讨论了语用原则的规定性和描述性、不稳定性和相对普遍性,语言交际的社会意义之共同性和表达形式的相对多样性。通过对学英语的中国学生与学汉语的英美留学生这一群体之间的交流进行探索,该文对跨文化交流中的语言间迁移、社会语用匹配以及观念定型和文化冲突等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英汉跨文化交流中的所谓“失误”,从语言本身的特点(如词汇缺项和巧合)看,有其客观性;从社交语用角度看,言语行为的“误配”有其相对可接受性;从社会文化差异和文化定型以及冲突来看,“失误”有不可避免性。该文从而提出,跨文化交流失误属谁之“过”,以及语用原则应入孰之“乡”随孰之“俗”等问题是语用原则在解释交流失误,增强国际间沟通和合作的关键。
河南省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郭爱先副教授在《中国人总是否定称赞吗?》一文中,对跨文化交际研究中一种流行观念“中国人受到称赞后,出于谦虚往往对称赞予以否定”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该研究中,语料的收集采用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调查的对象是某师专二年级中文系和英语系的学生,问卷分两组用汉语进行,为开放性问题,要求被试给出实际生活中最可能的回答,得到答语2024条;观察的主要对象是在北大进修的国内访问学者,笔者用98个多月的时间共收集称赞——回应96例。
结果分析表明,中国人回应称赞的主要方式有:明确接受、含蓄接受、直接拒绝和间接拒绝。他们对称赞的态度是:1.被试者中有90%听后很高兴,接受的例子占答语总数的80%以上。2.问卷中50%以上的例子为含蓄接受。3.“胖”与“瘦”在人们的价值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4.人们对地位高、年纪长、关系较远的人的称赞往往以谦虚的态度回应。5.以玩笑接受地位相当、年龄相仿、关系较熟人的赞扬。6.女性一般乐于接受熟悉男性的赞美,而不喜欢陌生男子的恭维。7.多数人通常接受对自己服饰、拥有物等的赞扬,而回应长相、能力、成就的赞扬时态度很谨慎。8.女性一般含蓄接受对孩子与丈夫的赞扬,男性则很喜欢别人夸自己的妻子或女友。总之,现代年轻人对赞扬不像美国人那样爽快地接受,也不像传统中国人那样立即拒绝,通常以各种方式含蓄接受赞扬。该文认为,1.“中国人一般拒绝称赞”的概括已不能涵盖所有中国人的现实做法,这种概括忽视了“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和人们言语的变化,会形成跨文化交际的新障碍。2.文化是开放的、变化的,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年轻一代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在变化中得到发展。3.人们对赞语态度的变化证明了语言与社会共变这一古老的社会语言学命题。
沈阳师范学院的崔丽杰老师在《中国学生跨文化交际语误分析》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学生有了更多直接参与跨文化交往中,除了由于语言不通而使许多人“望洋兴叹”以外,更有由于交际语误给交际双方带来的不快与遗憾。通过对中国学生跨文化交际语误实例的分析不难看出: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之一。缺乏文化意识及语用知识是造成语误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提高中国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把文化知识、语用知识教学紧密结合贯穿于语言教学中。
从跨文化交流中语用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理论和实用研究上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跨文化交流中的翻译问题 北京大学英语系高一虹副教授在《文化视角的可译性一例个案的“散点透视”》一文中,对英汉互译中的文化冲突问题进行了论述。该文作者曾与学生、朋友合作英译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文化认同派”代表申小龙的文章,并就此过程中的问题请教一位母语是英语的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学家。这位学者对译文作了尖锐激烈的点评,而原作者申小龙对其点评的反应也很强烈。在这一跨文化交流的冲突中,责任者究竟是谁——作者、译者,抑或读者?语言和文化是否可译?在北大英语系语言学沙龙上,作者邀请了申小龙和一些译者、读者就此交换看法,并且在“语言与文化”课上组织学生进行了讨论。该文将申的原文、译文、点评及众人众言摘录汇集一起,使读者通过个案分析,具体深刻地体会和认识翻译以及跨文化交际中的问题。
文化因素在政治传播中的影响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传播学院海西教授(Ray Heisey)在《政治传播中文化因素的影响》一文中,回顾了学术界对文化在政治传播中作用的研究历史和现状之后,赞同斯万森(D.L.Sanson)和尼姆(D.Nimmo)在1990年编辑出版的《政治传播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A Resource Book)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政治传播研究领域除了“投票者说服”和“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两个模式外,应对当前政治传播研究中日益增多新的角度给予进一步的论证。海西在该文中,对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研究中一个正在显现的新角度,海西称之为“文化影响”的角度,进行了探索。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滤镜,能起到使人民建构政治偏好的作用是从文化视角研究政治传播基点。该文在综述政治传播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欧洲领导人、美国总统、中东各国领导人、南非的领导人以及最近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后指出,这些研究是从所有社会都有结构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接纳和抵抗文化变化“强制性和激励性”观点进行分析的;在政治家的演说中,往往利用体现其所在国文化价值观,作为实现其赢得受众的支持,以达到其政治目的修辞手段。海西还认为,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把文化价值观作为一个中心问题来考察修辞学和传播。
该文认为,国际上各国政治领导人在政治传播的模式中,麦克菲尔(McPhail)的“对话式的演说模式”应取代“对抗式的演说模式”。对话式的演说是一种“一体化政治演说”的前提条件。不论文化背景如何,政治领导人物对文化价值的支持最终会导致社会的分裂或整合的趋势。
中美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差异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异虹在《中美商务谈判文化差异比较》一文中指出,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由于双方历史、文化背景和商业习惯的不同,在达成协议时会遇到一些障碍。这些障碍或大或小因人而异。小的,至多造成一点谈判中理解障碍,不至于影响最终的谈判结果;大的,甚至使谈判破裂或陷入僵局,这在大公司间、大型的商务谈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跨文化交流中中美两国有着较大的文化差异,所以有关中美双方的商务谈判也毫无例外地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理解,到部分融合的过程。目前国内外有关谈判的论述,都提出中美商务谈判间存在差异,宏观地指出了这些差异存在的方面;但大都没有指出哪些因素引起差异。该文从引起差异的根源入手,对中美商务谈判中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社会规范和语言等四个方面假设差异存在,并进而认为10个不同的因素引起差异。最后在国内外中美商务谈判理论以及跨文化交流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电话采访,问卷调查,分析验证了这些假设。应该说,该文在跨文化交流学的实用研究方面已经迈出了一步。
跨文化交流学的跨学科研究问题 最早把跨文化交流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介绍给国内(大陆)读者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现在跨文化交流学研究者多数为从事外语教学的学者,为了促进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全面发展,他呼吁更多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加入队伍。
跨文化交流学这个70年代兴起的传播学中的新领域,在80年代后期传入我国以来,在大学的外语系的研究者、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研究者以及从新闻学研究中发展出来的传播学研究者之间,互相缺乏沟通,影响了这一学科在我国的发展。这次研讨会提供了这一领域研究者相互沟通的渠道,也增进了与国外学者的接触和了解。从中国学者提交大会的论文中,也可以看到,中国跨文化交流学的研究的选题仍主要集中在中美跨文化交流的研究方面,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跨文化交流研究仍不多见。跨文化交流学是一个有很大开拓领域的新学科。这次在跨文化交流学领域的学术交流无疑开拓了与会者的视野,促进跨文化交流学在我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