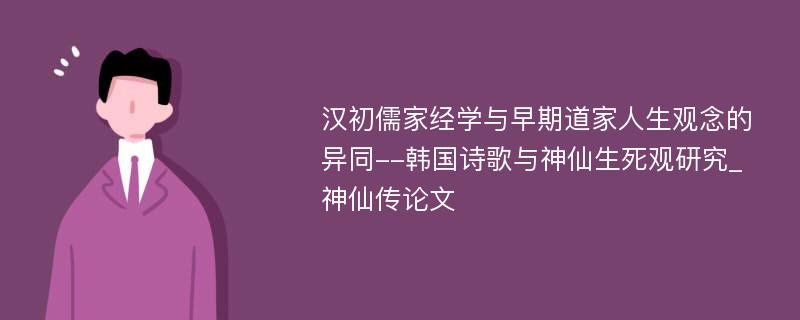
汉初经学与早期道教生命理念的异同——《韩诗外传》、《神仙传》生死考验故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经学论文,异同论文,外传论文,神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1—0168—05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生死考验是个体生命趋近道德完善的过程中面对的重要环节之一,在生死考验面前个人道德境界的高下不言自明。能够克服本能的恐惧,为义而死,已经被视为儒家君子的精神特质之一。西汉初期的儒家经学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诗经》的传授体系把生死考验作为讲经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在西汉初期今文经学唯一留存的《诗经》讲经文本《韩诗外传》(以下简称《外传》)中可以得到确证。
汉初是儒家经学的前经典化时期,儒家的代表性典籍已经在经学传授中体现出向经典化过渡的特征。儒家经师将《诗经》经典化的手法之一,就是用包含着儒家学说理念的故事对诗句的意义进行引申、推类和讲解,以此将儒家理念纳入到经学体系,并以“故事+诗句”的形态传达。传统儒家生死考验思想在《外传》中也文学化为生死考验为题材的故事,它以记述先贤往事为主要形态,通过塑造多个舍生取义的人物形象,强调儒家对道义的推崇和对生死的超越。最后用《诗经》中与故事内涵相关或相似的诗句作结,将故事与经联系起来。这类生死考验故事接续了儒家舍生取义观念而又有所发展,同时因其以叙事形态出现,具有更浓的文学色彩。
《外传》中的生死考验故事共计15篇。这15则故事有着共同的主题,在道义与生死相冲突的情境下,以能否通过生死考验作为衡量道德境界的标准,具有典型的儒家色彩。因其考验方式与宗教考验类似而考验性质又与之不完全相同,故称之为汉代经学亚宗教生死考验类故事。
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道家的生死考验观念作为道教思想渊源的一部分,也成为宗教教义的构成因素。魏晋时期,纯宗教性质的道教教义中已经明确地包含了这一倾向,认为对信徒的考验是非常重要的修行途径之一。《抱朴子·内篇·极言》第十三中有这样的论述:
或问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学以得之。将特禀异气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欤?彼莫不负笈随师,积其功勤,蒙霜冒险,栉风沐雨,而躬亲洒扫,契阔劳艺。始见之以信行,终被试以危困。性笃行贞,心无怨贰,乃得升堂以入于室。”[1](P94)
在道教看来,仙人得道并不是由于天赋异禀,而是因其学习过程中的诚心。学习道术者不但要甘于勤苦,最终还要经得起危困的考验,才能够升堂入室,成为真正的道教弟子。学道者如何“被试”?危困到何种境地?《抱朴子》的作者葛洪在另一部著作《神仙传》中,以具体的考验故事传达了道教的宗教生死考验观念。《神仙传》各类神仙传记中所记述的考验系列修行途径中,生死考验故事是重要的一种。它以道教弟子在生死考验面前的不同表现和相应的不同结果,强调修行中信仰的重要,对道家的生死观有所发展,其情节曲折,文字生动,有较高的文学性。
《外传》和《神仙传》成书时间较为接近,又存在相同的生死考验故事,这并不是纯粹偶然的巧合,而是因其各自思想渊源中的传统观念,都以生死考验作为通往理想道境的途径。分析、比较两书生死考验故事,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儒家经学叙事与宗教文学之间的关联,对于这一长期游离于学术视线之外的问题加以重视。
一
道教教义中对弟子的考验是修行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神仙传》当中,记载了十余则考验主题故事,其中生死考验故事三则,分别是卷一《魏伯阳传》、卷四《张道陵传》、卷五《壶公传》。
最为典型也最为人们所熟知的道教生死考验主题故事是《张道陵传》。赵升追随张道陵入教学道,道师设下七重考验试探赵升。前六重考验分别是:辱骂、美色、金钱、恐惧、心胸、仁厚。这七重考验一重比一重艰险,第七重生死考验已经在难度上达到极致,与前六重考验相比较,用墨最多,描写细腻:
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下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之者二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敢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升一人乃曰:“神之所护,何险之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掷投树上,足不蹉跌,取桃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缘,不能得返。于是乃以桃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升。陵乃以手引升,众视之,见陵臂加长三二丈引升,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之。升食桃毕,陵乃临谷上戏笑而言曰:“赵升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试投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唯升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唯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堕陵前。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见升长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治旧舍,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升长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而没于云霄也。[2](P31)
求道者赵升、王长因对神师的至诚至信,冒死去摘取仙桃,在师父坠崖后,舍生入死地追随。在对师父无以复加的绝对信仰支配下,最终通过考验,得道成仙。
《神仙传》当中的赵升故事篇幅较长,在叙事中有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如上文所引“七试赵升故事”,在生死考验关头,有一处描写众弟子的恐惧之态:“于时伏而窥之者二百余人,股战汗流,无敢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以对众人情态的生动刻画来渲染形势之危,衬托赵升诚心与忠信之难得,尽显叙事之技巧。
相形之下,《外传》中的生死考验故事的情节及描写则相对简略得多,虽然有一些生动的细节,但都是片断式的,不能够左右整个故事的叙事风格。以第二卷第十三章崔杼弑庄公为例,与赵升故事极为相似,主人公晏子同样处于极危难的境地,同样有一群身份、处境相同的人,故事也是用其他人的行为来衬托主人公的卓尔不群,但《外传》中却只用了一句简单的描述——“盟者皆视之”,以他人关注的一个大略举动来表现晏子的勇气,这与《神仙传》中对于众弟子的形象刻画相去甚远。
《外传》除了细节上与《神仙传》有着精细与粗略之分外,在叙事上也有着很大的区别。仍以赵升故事和晏子故事为例,从行文中可以清晰看到,赵升故事以生动、细致的描写为主,人物的对话只是穿插其中的点缀,而晏子故事中则主要以人物对话为主,描写性的语言作为人物对话之间的衔接出现,以简单地交代人物所处情境为目的。这种差异使两类生死考验故事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相比之下,赵升故事在叙事技巧上更为成熟,生动性、文学性都要比晏子故事高出一筹,是更为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这两则故事在叙事上的差异具有典型性,在《神仙传》与《外传》其他生死考验故事的对比中也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差别。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文学发展所带来的叙事语言的丰富。魏晋比之于汉代,文学在语言及技巧上的发展是明显的,这自然带来创作主体在语言及叙事风格上更为丰富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与两类故事不同的创作方式及目的有关。《外传》是经师口头传授《诗经》的文本记录,因而有着很强的经学特征。经师注重故事的真实感,因而注重以人物语言来传达理念,再现情境,增强故事的可信性。这与当时人们以信史为据的观念有关。虽然《外传》对一些史实多有改写,“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4](P461),但其大体上仍有史实为基础,《外传》在经义解说中仍考虑到信实。故事中具体的细节描写往往使故事在生动之余流于虚妄,使人产生经师如何能了解事件如此详细的疑虑,进而危及经义的顺利接受。此外,经师作为《诗经》的传授者,其目的是树立儒家君子的道德权威,以此引导学习者的道德提升,因而注重的是通过人物对话展现人物内心道德境界,细致的情节描写被视为可有可无之物,其细致入微、生动曲折之处会分散听者的注意力,使之过于关注情节,从而影响到最主要的经义传达。
而《神仙传》从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到最后的文本形态,都是典型的文人书面创作。葛洪《神仙传序》明确指出自己创作此书的目的是“以传知真识远之士”[2](P1)。即以书本形态传播于后世好道之人。书面创作比口头创作有更多的时间斟酌、加工,因而在叙事上可以更为精细、传神。此外,讲经作为口头传播,稍纵即逝,不可再现,因而留给听讲者的理解、接受时间也很短,经师在讲经时,必然要对内容及篇幅的繁复有所回避,力求简单明了地传达出最主要的经义。而文字则可以超越时空限制,反复多次阅读,因而书面创作较口头创作在篇幅和创作上拥有更大的自由。葛洪自述因刘向的《列仙传》“殊甚简略,美事不举”,希望此书“有愈于刘向多所遗弃也”[2](P1),这印证了《神仙传》有意铺陈笔墨、曲笔妙录的事实。
后世对《神仙传》情节的虚幻有明确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了评析:“淮南王刘安谋反自杀,李少君病死,具载《史记》、《汉书》,亦实无登仙之事,洪一概登载,未免附会。至谓许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黄丹,今在中岳中山,若二人晋时尚存,洪目睹而记之者,尤为虚诞。”[4] 宋代葛立方的《韵语阳秋》指出:“如淮南王安,汉史以为自杀,而《神仙传》以为白日升天,有鸡鸣天上,犬吠云中之语,其妄乃尔。”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需要辨析的是,《神仙传》中对明显的虚幻情节不加回避是由其生死考验故事的宗教性质决定的。与《外传》产生的时代文化心理不同,魏晋时道教处于兴盛时期,人们对于道教的神异普遍能够接受、认同,认为长生久视的成仙之道必有其神妙及不可理喻之处,这既符合信徒们的心理预期,也是道教所极力宣扬的。因而这些虚幻而细致的情节出现在道教典籍中,不但不会影响教徒对教义的信仰,反而加强了道教的神秘和权威。对于传记真实性的怀疑,也在作者葛洪的意料之中,认为“其系俗之徒,思不经征者,亦不强以示之”[2](P1),把那些怀疑传记真实性的人视为不可教诲的凡俗之人,将对于传记权威性的挑战消解于无形。葛洪对《神仙传》的风格自定为“深妙奇异”[2](P1),也可从另一侧面体现出他在创作中基于宗教性质而有意为之的美学追求。
口头与书面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讲经和传教两种不同的预期目的,经学与道教两种不同的思想基础,使儒家经学和道教传记当中的生死考验虽属于同一题材,但却呈现出不同的叙事风貌。
二
《神仙传》中的另两则生死考验故事的大致情节如下:
卷五《壶公传》记载,汝南费长房求学道于壶公,“公乃留房于群虎中。虎磨牙张口欲噬房,房不惧。明日又内于石室中,头上有一方石,广数丈,以茅綯悬之。又诸蛇来啮绳,绳即欲断,而长房自若”[2](P39)。这则故事中,费长房在生死关头,置生死于度外,神色自若,通过了壶公的最初考验。故事中费长房最终虽然因无法通过所有考验而得道,仍旧因其在考验中表现出色而得“为地上主”,得寿数百岁,并得一符,可以主鬼神、治病消灾。可见,对道术的渴望和追求要超过对生命的珍视、对死亡本能的恐惧,才能够得到道师的基本认可。
卷一《魏伯阳传》中,记载了魏伯阳对弟子们的生死考验。魏伯阳与弟子三人入山炼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怀未尽,乃试之”。先以狗做试验,狗吃后马上死掉了。魏伯阳将是否服食丹药的难题交给弟子,弟子反问魏伯阳是否服丹药。魏伯阳以不得道而耻于归家为由,吃丹药而死。弟子三人中只有一虞姓弟子坚信魏伯阳,“吾师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无意也?”随后也服药而死。其后二弟子出山为魏伯阳及虞姓弟子求棺木时,魏伯阳“将所服丹纳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魏伯阳、虞姓弟子、白犬皆得道成仙。二弟子得知后“乃始懊恨”[2](P8)。得道的条件是必须对教主完全信服,并且这种信任要能够克服心理上对于亲眼所见的死亡的恐惧。
无论怎样看待这两则宗教生死考验故事,其中对于弟子的要求都是难逃苛刻二字,尤以第一卷魏伯阳故事为甚。虞姓弟子在亲眼看到师父的失败后仍旧认为师父别有深意,在死亡的事实面前仍旧相信师父的异能,这在思维正常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正是这种貌似无理的考验透露出宗教考验的本质:对于教义的无条件信仰,对于教主的全身心信任,个人独立的经验、推理、逻辑、思辨在求道过程中都是无用且有害的,能够得道的人依靠的是近乎盲目的执著和信任,被考验者独立思考的价值和作用被抹杀。而儒家的亚宗教生死考验故事却强调个人理性的思考和选择,有着明确的主体独立性和价值判断。如第六卷第十二则田常弑简公故事:
田常弑简公,乃盟于国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亲,非忠也。舍亲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则不能。然不盟是杀吾亲也。从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呜呼!生乎乱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义。悲夫!”乃进盟以免父母,退伏剑以死其君。闻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诗曰:“人亦有言,进退维谷。”石先生之谓也。[3](P216)
石他面对生死考验,对情势有着清晰的洞见,认识到自己在乱世中的命运,并在清醒的分析、假设中形成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即:以死全义。这一生死考验过程中,主体独立的价值判断、选择都建立在理性之上,其舍生就死的行为也来自自我的思考和选择。《外传》中其余生死考验故事,也无一不体现出主人公清醒的心智和强大的理性。相比于宗教考验中对个人理性的排斥,对教义、道师的迷狂式崇拜,经学的亚宗教生死考验故事体现出对个体理性思考和独立判断的倡导。
《神仙传》中的三则生死考验故事,讲述的都是弟子全身心地忠道信师,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随道师,方可得道成仙,修成正果。但是要注意到,道教弟子付出生命代价都只不过是暂时的舍弃,并不是真正的死亡。这种面对生死的超越最后都会为舍生者带来实质的利益,最终化悲为喜,死者不但复生,并且因一时间对于生死的超越而求得了永生。从本质上来说,舍弃生命成为道教诱导学道者求得长生久世的一个途径,即所谓向死求生,因勇于追随教主、舍弃生命而得道成仙,永远不死。
《外传》中的生死考验故事则不同。《外传》中故事的主人公明知生命的可贵且不可再得,一旦失去则与世永隔,但是因为以道德为最高追求,生死考验故事当中的儒家君子仍毅然选择以生命来完成对于理想和精神的守护。阅读两类同题材故事时,《神仙传》较《外传》具有更为生动的情节和细致的描写,但是并不能激发起读者对故事的悬念,也无法有一种崇高感,因为人们知道,主人公的死亡只是暂时的,作为补偿和奖赏,他最终会得到所追求的长生不老。既以死亡为考验手段,又以永生为最终目的,这两者的悖反乃是宗教生死考验的吊诡之处,它决定了宗教生死考验只能以永生作为舍生后的结局。如果跳脱出这个固定的圆满结局,道教生死考验故事将解构自身的神异和以长生为最终目的的道义,反而成为对道教教义的质疑和颠覆。宗教生死考验对通过生死考验者只能安排相同的固定结局,这种可预知的结局消解了故事中道教信徒舍弃生命这一行为本身的崇高意义和震撼力。《外传》中的故事虽然简略,但那种舍生就义之际明知生命之不可挽回而毅然决然的选择,为追求道德的圆满而不惜舍弃生命的高行义举,给人以一种精神上的强烈震撼。宗教以神异而虚幻的承诺给予人们解脱生死难题的企盼,儒家学说以崇高的道德境界激发人们超越生死困扰的意志,前者的世俗本质相比于后者的内在超越性,正可揭示同一题材生死考验故事在审美内涵上有着如此巨大差异的内在原因。如果说道教文学中的生死考验故事是情节生动、起伏跌宕的悲喜剧,并且最终仍是以喜剧作为其基本底色,那么《外传》中的儒家生死考验故事则无疑是蕴涵着崇高、壮烈之美的悲剧,并且其叙事自始至终都以一种庄严的品格进行。
三
以上所述两类生死考验故事在审美精神及叙事形态上的差异并不能割裂两者的内在联系。《神仙传》当中的某些生死考验故事也有着浓重的儒家色彩,明显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首先,在这些道教生死考验故事中出现了有着儒学背景的道士、神仙。如《张道陵传》故事开头介绍张道陵“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作为天师的张道陵在信仰道教之前,是以儒生身份出现的。综观《神仙传》,以儒生或明经者身份出现的神仙、道士达二十余人之多,如栾巴、王烈、孔安国、孔元方、葛玄等等。这些有着儒学背景的人物作为道教神仙出现在传记当中,体现出在当时儒学影响深远的背景下,道教为使教义获得最大程度的开放性和影响力,对儒家学说采取的是自觉接受和吸纳的态度。
其次,生死考验故事当中,也传达出明显隶属于儒家的理念。如《张道陵传》中七试赵升的故事,张道陵对赵升的七重考验与其说是针对信徒道心的考验,不如说是对赵升的道德考验。七重考验中除了恐惧考验中的以虎相恐吓之外,举凡辱骂、美色、金钱、仁厚、生死考验,赵升通过的考验都与儒家对于君子的道德考验无异。与美女同床而居数日,“亦复调戏,升终不失正”,与儒家君子柳下惠相似;路遇遗金三十饼,过而不取,与儒家君子华歆无异。生死考验当中,张道陵自投于悬崖之下,杳无踪迹,赵升与王长在决定投崖追随师父之前有一段内心的剖白:“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相比于《外传》生死考验故事中人物在选择死亡之前的自陈,虽然过于简单且不见对忠孝等观念的提及,但是在义理上是相通的。赵升与王长并不是因绝对信任神师必无生命之虞而跳崖追随,而是以师比父,将对父的孝与对师的忠相联系,师父已死,内心无法自安,因而以死相随。这当中蕴涵的儒家忠、孝学说成分远远超过了道教教义,与《外传》生死考验故事中荆蒯芮、弘演、仕之善等儒家君子追随君主、为忠而死的行为同出一辙。《神仙传·魏伯阳传》当中,虞姓弟子因信任师父的神异,认为死必有深意在,因而也服丹药而死,这才是纯粹的道教教义。可见在宗教生死考验故事中,有时也存在着儒家思想的因子。
道教生死考验故事中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原因还在于它在内容及题材上将儒家学说作为重要的来源之一。葛洪自述《神仙传》的题材来源:“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2](P1) 生死考验故事中的代表作《张道陵传》由内容和细节上看,更无疑有其儒学渊源。它的宗旨虽然最终是为宣扬道教服务的,但在故事中却夹杂着儒家经学的理念,带有儒家经学色彩,是儒家生死考验故事在道教文学中的一道投影。
收稿日期:2006—0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