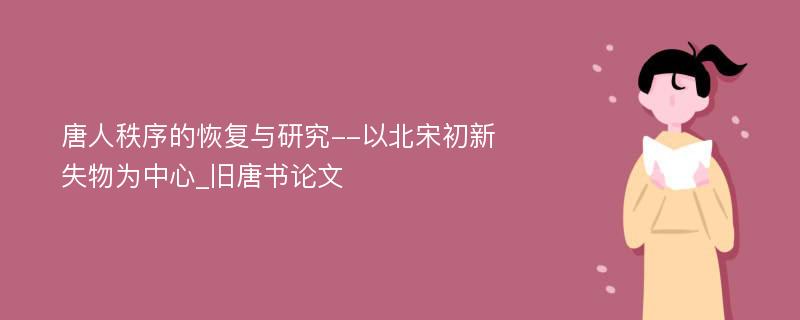
唐职员令复原与研究——以北宋前期文献中新见佚文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职员论文,中新论文,文献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唐职员令复原再审视
唐代以律、令、格、式构成完整的法律体系,而“设范立制”的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规定,①在四者之中具有纲领作用,是唐代制度最直接、最原始的记录,也对后世及日本的律令法典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唐代各个时期所编撰的令文虽然在宋元时代渐次散佚,②但现代意义上的唐令研究起步甚早,成果也最为令人瞩目。日本学者从20世纪初开始便致力于唐令的研究与复原,30年代出版的《唐令拾遗》、③90年代出版的《唐令拾遗补》,④集中体现了日本学者对唐令的研究成果。其后中村裕一《唐令逸文の研究》在二书的基础上续有增补。⑤至此,日本学者复原唐令33篇,大致恢复了唐令的整体结构和半数以上的唐令条文。
1998年,戴建国在宁波天一阁发现明钞《天圣令》残本,为唐令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材料。修订于北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的《天圣令》以唐令为蓝本,⑥同时在每篇篇末附录当时已不行用的唐令原文,为唐令的整体复原提供了迄今最为完整而可靠的材料。⑦该钞本原为四册,现存最后一册,存《田令》至《杂令》12篇。新近出版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即据此复原了12篇开元二十五年令。
在整个唐令系统中,规定唐代内外官员员数和执掌的《职员令》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六典》所载27篇令文之中,《职员令》占了第二至第七的六卷篇幅,⑧分别为《三师三公台省职员》、《寺监职员》、《卫府职员》、《东宫王府职员》、《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内外命妇职员》。因为唐格与唐式亦“以尚书省诸曹为之目”(式益以秘书省,太常、司农、光禄、太仆、太府诸寺,少府监,监门、宿卫各篇),⑨故可以认为《职员令》系唐代除律以外的整个法律体系的纲领。
由于《天圣令》残钞本中的《职员令》部分已佚失,故而《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所复原的唐令并未包括这部分内容,而随后一系列对唐令的讨论也并未涉及于此。⑩因此唐职员令的复原成果仍主要集中于日本学者的研究之中,而其依据的最重要也是最完整的材料是敦煌所出钤有“凉州都督府”官印的《永徽令》卷6《东宫诸府职员》残卷。该残卷断裂为数片,分别藏于法国与英国,编号为P.4634、4634C1、4634C2,S.1880、3375、11446。(11)这一文本自发现以来,一直是中日学者讨论的热点。由于当时并未见到所有残卷,《唐令拾遗》仅据S.1880复原了原卷215行文字中的28行,(12)也没有确定该残卷的确切年份。《唐令拾遗补》吸收了其后大量研究成果,完整地呈现了原卷面貌,使《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的大部分内容得以重现。此外,《唐令拾遗》又据中日传世文献中所保存的唐职员令佚文复原得《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7条、《寺监职员令》3条、《卫府职员令》2条、《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令》2条、《内外命妇职员令》2条,《唐令拾遗补》则吸收了中村裕一等对《职员令》的研究成果,据万历本《记纂渊海》等文献增补了开元二十五年(737)《职员令》7条。中村裕一在《唐令逸文の研究》中再一次对传世文献中所保存的职员令佚文与《通典·职官典》、《唐六典》等唐代职官书作了细密的比对,又增补了一条佚文,同时认为《通典·职官典》的官员执掌部分是职员令佚文的宝库。(13)
综观日本学者复原《职员令》的方法,往往将一般认为来源于开元七年及二十五年令的《唐六典》与《通典·职官典》作为直接的引据资料,通过唐令佚文与《通典》及《唐六典》的比对,来整体恢复令文的内容与年代。(14)由于《通典·职官典》与职员令佚文的高度一致,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可以据《通典》复原大部分的开元二十五年职员令。(15)
但是仔细分析这一方法,似乎值得商榷。首先,《唐六典》所载的官员执掌并非即是开元七年令原文。李锦绣通过《唐六典》与开元二十五年《仓库令》的比读,发现《唐六典》中“金部郎中员外郎”、“仓部员外郎”执掌虽然来源于《职员令》,但并非照录原文。(16)至于《通典》,虽然一般认为《职官典》的官员执掌部分可能完整抄录了开元二十五年《职员令》原文,(17)但实际仍掺杂有开元以后制度,如卷23注文载司封郎中掌道士、女冠,(18)即已是天宝至元和间的制度。(19)虽然尚无法坐实《通典·职官典》究竟掺入了多少后代制度,但以此为基准复原开元二十五年令尤须谨慎。
其次,高宗龙朔二年(662)、仪凤二年(677)两次定格令的起因皆是由于官名的变化,其方式“唯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20)因此各年度令文虽及时地体现了此前的制度变化,但总体仍保持了文字的相对稳定,这一点在《天圣令》对唐令的修订中也同样得到体现,(21)因此唐代不同年份令文之间文字的差异并不很大,故并不能根据佚文与《唐六典》或《通典》在文字上的相似即判断为某年度令。实际上即使是日本学者认为很可能即是唐职员令原文的《通典·职官典》,与其他文献中所存佚文仍有不一致的地方,而某些细微但却关键的差别恰恰体现了不同时期唐代制度的变化。仅仅注意到二者的相似之处,不免会造成令文年代的误判。例如《太平御览》卷216所引有关司封郎中执掌的《职员令》佚文,较《通典》所载执掌多“国官、邑官告身并选流外、[视](亲)品”一句,(22)实际上反映的是太极以前制度,(23)而《唐令拾遗》虽然引据《太平御览》此条,却根据《通典》复原为开元二十五年令就值得推敲。(第32页)又如《唐令拾遗》作为复原开元七年及二十五年令中“左右司郎中”条引据资料的《太平御览》卷213所引《职员令》。(第28页)此条载左右司郎中执掌有“知台内宿直”一句(第1019页上),《通典》卷22作“省内”。实际上龙朔元年二年及武后光宅元年(684),尚书省改称“中台”及“文昌台”以后,“省内”即被称为“台内”。而龙朔二年以后,“左右司郎中”改称“左右承务”,直至咸亨元年(670)复旧。故此条文字兼有“左右司郎中”及“台内”,实际上反映的是武后时期制度,应复原为《垂拱令》,而不应与《通典》一同作为开元七年及二十五年令文的引据资料。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中村裕一对《记纂渊海》6条唐职员令的复原之中。(24)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除了此前对于唐职员令的研究较多关注被认为系统保存于传世文献中的唐开元七年与二十五年令文之外,还与职员令佚文本身留存过少有关。考《唐令拾遗》据以复原职员令的材料,除了敦煌本《东宫诸府职员》以外,真正标明为“唐令”的仅仅6条,加上中村裕一从万历本《记纂渊海》、《古今事文类聚》、《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职官分纪》、《总事始》中增补的9条,相对完整的职员令遗文不过15条。而这些遗文中虽然也透露出唐代各个时期制度变迁的些微讯息(如上引《太平御览》条),但有限的数量或许也是限制它们被进一步认识的重要原因。
二、《类要》中的唐职员令
由于传世文献所提供的职员令佚文过于稀少而不成系统,使得此前对于职员令的认识或有所偏差,因此,新材料的发现无疑对唐令的复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近年来从事北宋名臣晏殊所编类书《类要》的研究,发现其中保存了大量唐职员令佚文,绝大部分前人不曾注意。这批材料的发现无疑为唐令的复原提供了更为直接的依据。
《类要》原书74篇,(25)76卷,(26)是晏殊平素读书心得之总汇,(27)直至晏公去世,其书仍未最后定稿。南宋初年,其四世孙晏袤将《类要》增补为100卷,国内现存的三个残钞本,皆属于这一系统。三本分别藏于陕西西安文物管理委员会、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下分别简称“陕本”、“北大本”、“社科院本”)。陕本和社科院本存37卷。北大本存16卷,内容包含在37卷本之中。曾巩《类要序》称其书“于六艺、太史、百家之言,骚人墨客之文章,至于地志、族谱、佛老、方伎之众说,旁及九州之外,蛮夷荒忽诡变奇迹之序录,皆披寻纯绎,而于三才万物、变化情伪、是非兴坏之理,显隐细巨之委曲,莫不究尽。”(28)揆之今存37卷残本,其引录文献达700种以上,已佚文献占80%左右,内容涉及宋初以前四部图书,可证曾巩所言不虚。而其引书大约有三分之一注明卷数,尤以唐代文献为多,应是自原书录出,故其价值远非后世辗转抄袭的类书可比。
《类要》中标明出于《职员令》的多达27条,皆为中书、门下、尚书及御史台、殿中省官员职掌,一般采用“掌……之事”的格式,与《通典·职官典》相关条目文字极为近似,可以确认为唐令。另有19条未标出处,但格式与上述27条基本一致,文字也可与《通典》相对应,因此可以肯定也是唐职员令佚文。由此《类要》中所保存的唐职员令佚文达到46条,远远超过此前所知的佚文总数。
其次,比照《唐六典》所载开元七年令之篇目,《类要》所引职员令文字分别属于《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与《寺监职员》,其中六部尚书及二十四司郎中执掌基本完整,为整体复原这一部分唐令提供了直接材料。
另外,比对《通典·职官典》,可以发现,这部分佚文,除“中书令”与“侍中”2条外,其他基本未经删略,仍旧保留了唐令中独有的一些语汇。以万历本《记纂渊海》所引5条职员令为例。这5条佚文同样见于《类要》,其中“工部郎中”与“刑部尚书”2条与《类要》引文基本一致,但“兵部郎中”、“司门郎中”、“殿中侍御史”3条则省略了“亲事”、“帐内”、“过所”、“非违”等极为重要的文字。考虑到万历本《记纂渊海》引录了《类要》不少内容,这5条《职员令》很可能即转引自《类要》。(29)由此可以认为,《类要》中的职员令佚文,更接近于唐令的原始面貌,或即是唐职员令的原文。
最为重要的,这部分佚文中所载录的官称与执掌,往往反映了唐代不同时期的制度。如卷15“吏部尚书”引文记其执掌“判天官、司勋、考功等四司事”。(30)武后光宅元年九月改吏部为“天官”,至神龙二年(706)二月复旧。(31)可知此条为武后时所修订的《垂拱令》的遗文。类似例子并非个别。这些佚文的存在提示我们,天宝以前,令文屡经修订,开元七年与二十五年之外的令文虽然未被整体保存,但直至北宋前期仍旧没有完全湮没。因此在唐令的复原中,仅仅依靠同类文献的比对来确认其时代,很可能忽略佚文本身所反映的制度的真正时代性。
三、唐职员令复原——以北宋前期文献中新见佚文为中心
《类要》所保存的这部分不同时期的唐职员令佚文,或许提示了我们另外一种职员令复原思路,即在与《通典》等唐代文献比对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佚文本身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有唐一代多次撰辑删定令文,《唐会要》卷39《定格令》详细记录了武德至开元年间的历次改订,计有武德元年(618)、贞观十一年(637)、永徽二年(651)、龙朔二年、仪凤二年、垂拱元年(686)、神龙元年、景龙元年。(707)、景云元年(710)、开元三年10次,加上开元七年和二十五年2次,则有12次之多。(32)虽然龙朔、仪凤、垂拱、神龙、景云及开元三年的几次修订似乎仅及于格、式,但《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注文明确指出这些年度都曾修订过令文(第185页),而《旧唐书·职官志》也明确引录了《乾封令》(即《麟德令》)、《垂拱令》、《神龙令》,(33)因此可以认为,除景龙年间的修订并未完成以外,其他各年度皆曾修订过令文。正如上文所说,各年度令文在整体上仍保持了文字的稳定性,因此对于唐职员令佚文时代的考虑并不应当局限于某一两部唐令,而应根据其本身所包含的制度来确定其时代。
有鉴于此,本文对于唐职员令的复原,在比对以《通典·职官典》为代表的相关文献以确定佚文性质的同时,更注重对佚文时代的考释。
其次,《类要》所保存的46条职员令佚文,此前从未引起注意及利用,无疑是本文最重要的复原材料。另外《太平御览》、《职官分纪》中所引录的唐职员令,虽然在《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唐令逸文の研究》都有过详细的考察,但部分结论似乎仍有斟酌的必要,因此对于这部分内容亦重加考订。又《唐令拾遗补》及《唐令逸文の研究》据《职官分纪》等复原的“太常卿”一条,并非唐职员令,今作为附论,另行考察。
复原所据文献之版本,现胪列如下:《类要》据《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66册影印陕本,《太平御览》据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北宋本,《职官分纪》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23册,《古今事文类聚》据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元刻本,《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0册,《翰苑新书》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影印宋刻本,万历本《记纂渊海》据《唐令逸文の研究》转引。以下所注出处中页码皆指这一系列文本,不再逐一说明。
所复原的令文直接标注出处,不再另列引据资料。引文误字随文订正,以[]表示改正后的文字,以小一号()表示原文。所复原的令文,可考其时代者,则以【】标年号于条目之前,文字与《通典》一致者,姑据之复原为开元二十五年令,但不排除为其他年度令文的可能性。其他不可确考者则以【唐代】泛称。所存佚文一般未录官名,可考得明确其时代者,补入当时官称,否则则据《通典·职官典》补入相应官称,以()标示。
1.【唐代】太师、太傅、太保谓之三师,师范一人,仪型四海。(《类要》卷14“三师”引《职员令》,第602页上)
考释:《通典》卷20《职官二》:“大唐复置,以师范一人,仪刑四海。”(第509页)(34)《令集解》前篇卷2《职员令》“(太政大臣)师范一人,仪形四海”注引“穴云”:“《永徽令》‘仪形’者,《开元令》‘仪刑’也。”(35)则本条应是《永徽令》、《开元令》以外令文。
2.【乾封】【垂拱】(左肃机/左丞)管辖诸司,纠正台内。(《类要》卷14“左右仆射”、“总叙左右丞”引《职员令》,第611页下、612页下)
考释:《通典》卷22《职官四》:“左丞掌管辖诸司,纠正省内,勾吏部、户部、礼部等十二司,通判都省事。”又同卷:“龙朔二年,改尚书省为中台,咸亨初复旧。光宅元年,改为文昌台。垂拱元年,又改为都台。长安三年(703),又改为中台。神龙初复为尚书省”。又同卷:“左右丞……龙朔二年,改为左右肃机,咸亨元年复旧。”(第601、590、600页)本条称“台内”而非“省内”,反映的是龙朔至咸亨、垂拱至神龙的制度,应为《乾封令》或《垂拱令》。
3.【垂拱】左右司郎中掌副左右丞所管诸司事,署抄目,举稽失,知台内宿直。若本司郎中不在,并行之。(《太平御览》卷213引《唐职员令》,第1019页上)
考释:此条《唐令拾遗》复原为开元七年及二十五年令(第28页),误。《通典》卷22《职官四》:“(左右司郎中)掌副左右丞所管诸司事,省署钞目,勘稽失,知省内宿直,判都省事。若右司不在,则左并行之;左司不在,右亦如之。”本条称“台内宿直”,反映的是龙朔至咸亨、垂拱至神龙的制度。又同卷:“左右司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左、右丞务,咸亨元年复旧。”(第601页)故本条为《垂拱令》。
4.【太极】【开元】(员外郎)掌司内簿书孔目,分判曹事,二十四司皆同此。(《类要》卷15“员外”、“吏部”引《职员令》),第619页上、下)
考释:此条《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10作“二十四司皆其选也”(第1857页上)。《翰苑新书》前集卷14作“司内部书,二十四司皆其选也”。(第146页)《唐令逸文の研究》据二书复原为唐代令文。(第25页)《唐六典》卷1“三师三公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掌付十有二司之事,以举正稽违,省署符目。”(第10页)《新唐书》卷46《百官一》:“(尚书省)员外郎……掌付诸司之务,举稽违,署符目,知宿直,为丞之贰。”(36)《唐会要》卷58“左右司员外郎”:“永昌元年(689)十月五日置,各一人……神龙元年三月初八日废,二年十二月复置。”(第1177页)永昌元年以后,中宗与睿宗皆刊定过格令。神龙格令删定之时,员外郎已废,尚未复置,而景龙元年对神龙格式的改订并未见完成。故本条应为太极或以后诸令。
5.【垂拱】(天官尚书)掌文[官](员)选举,判天官、[司封]、司勋、考功等四司事。(《类要》卷15“吏部尚书”引《职员令》,第622页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27,第26页下)
考释:《唐令逸文の研究》据《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复原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第17页),误。《通典》卷23《职官五》:“(吏部尚书)掌文官选举,总判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曹事。”(第631页)《旧唐书》卷42《职官一》:“光宅元年九月,改……吏部为天官……神龙元年二月,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第1788页)故本条为《垂拱令》。
6.【贞观】(吏部郎中)掌选补流外官及文武官名簿、朝集、禄赐、假故,并文武官告身之事。(《类要》卷15“吏部郎中”引《职员令》,第623页下)
考释:《通典》卷23《职官五》注:“(吏部郎中)掌选补流外官,谓之小铨。并掌文官名簿、朝集、禄赐、假使,并文官告身,分判曹事。”(第633页)《令集解》前篇卷3《职员令·式部省》:“卿一人,掌内外文官名帐。”(第76页)《养老令》之蓝本为《永徽令》,则自《永徽令》以来,吏部郎中皆不掌武官名簿及告身。前引《令集解》注引“朱云”:“‘未知武官杂任名帐,何官可掌乎?式部欤?兵部欤?’何答:‘元式部可任耳,但今行事,门部者兵部补任耳。此违令文耳。但兵部官人等名帐式部可掌’”。(第77页)则日本曾有过式部掌武官名帐的制度,而其来源很可能即是唐代制度。又敦煌文书P.4745:“(前缺)长史、司马、司录、上总管从四品,中总管正五品,下总管从五品。随勋官、散官及镇将、副五品以上,并五等爵,在武德九年二月二日以前身亡者,子孙并不得用荫当;虽身在,其年十二月卅日以前不经参集,并不送告身经省勘校奏定者,亦准此。随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在贞观五□□□□□前省司勘定符下者(后缺)”。(37)刘俊文据《唐律疏议》卷25“伪写前代官文书印”条疏断为《贞观吏部式》断片。(38)则贞观时期,文武官员告身皆经吏部勘定,吏部亦当掌武官名籍。故本条应为《贞观令》。
7.【垂拱】司封郎中,掌封爵皇诸宗亲, 内外命妇及国[官] (宫)、邑官告身并选流外、视品等事。(《类要》卷15“司封”引《职员令》,第624页下;《太平御览》卷216引《职员令》,第1031页下)
考释:此条《唐令拾遗》据《太平御览》复原为开元七年及二十五年令(第32页),误。《通典》卷23《职官五》注:“(司封郎中)掌封爵、皇之枝族及诸亲、内外命妇告身及道士、女冠等。”(第634页)《唐会要》卷58“司封郎中”:“武德元年因隋旧号为主爵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司封大夫,咸亨元年改为主爵郎中,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为司封郎中,神龙元年九月五日改为主爵郎中,开元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复故。”(第1181页)《御览》引作“司封郎中”,应为《垂拱令》或《开元二十五年令》。又国官、邑官即亲王、公主之属官,《旧唐书·职官志》从七品上阶之“亲王国令”注:“旧[视](规)流内正九品,太极年改。”(39)又“公主家令”条注:“旧[视](规)流内正八品,太极年改。”则太极以前,国官、邑官为视品官,由司封判补并给告身,而在太极年间改为流内官后,亦由吏部给告身,(40)故本条所载为太极以前制度,故复原为《垂拱令》。
8.【天宝】司封郎中一人。掌封爵皇帝诸亲、内外命妇告身等,寺观及道士、女冠等事。(《职官分纪》卷9“司封郎中”引《职员令》,第251页上)(41)
考释:此条《唐令逸文の研究》据《职官分纪》复原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第8-9页),误。《唐会要》卷49“僧尼所隶”:“天宝二载三月十三日制:‘僧尼隶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检校,不须隶宗正寺。’元和二年二月,诏僧尼道士同隶左街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复关奏。”(第1006页)则本条为天宝至元和制度。
9.(开元七年及以前)(司勋郎中)掌校定勋绩,论功行赏、勋官及视品、府佐等告身之事。(《类要》卷15“司勋”引《职员令》,第624页下)
考释:《通典》卷23《职官五》注:“(司勋郎中)掌校定勋绩、论官赏、勋官告身等事。”(第634页)《旧唐书》卷8《玄宗纪》:“(开元)十年春正月……甲子,省王公已下视品官、参佐及京三品已上官[仗](伏)身职员。”(第183页)本条尚有“视品、府佐”等官称,当为开元十年以前制度,应为开元七年及以前令文。
10.【武德】 (考功郎中)掌考察内外百司,策试、贡举及功臣家传、碑、颂、诔、谥之事。(《类要》卷15“考功”引《职员令》,第624页下)
考释:此条《通典》卷23《职官五》注引《武德令》作“考功郎中监试贡举人”。(第635页)《职官分纪》卷9“员外郎·掌贡举”条注引《武德令》同。(第254页)《唐令拾遗》据《通典》复原为武德令,未及其余职掌。(第31页)《通典》卷23《职官五》注:“(考功郎中)掌考察内外百官及功臣家传、碑、颂、诔、谥等事。”(第634页)
11.【垂拱】(地官尚书)掌总判地官、度支、金部、仓部事。(《类要》卷15“户部尚书”,第625页下)
考释:《通典》卷23《职官五》:“(户部尚书)总判户部、度支、金部、仓部事。”(第636页)《旧唐书》卷42《职官一》:“光宅元年九月,改……户部为地官……神龙元年二月,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第1788页)故本条为《垂拱令》。
12.【开元二十五年】(户部郎中)掌户口、籍帐、赋役、[孝](礼)义、优复、蠲免、婚姻、继嗣,百官众庶[园] (阖)宅(户)、口分、永业等事。(《类要》卷15“户部郎中”,第626页上)
考释:此条同《通典》卷23《职官五》注所载户部郎中执掌。(第637页)敦煌文书S.1344《开元户部格》所载格文涉及户口管理、赋役管理、蠲免优复、土地管理、土贡管理、朝集使等,(42)与本条及《通典》所载基本相合,疑为开元令。
13.【开元二十五年】(度支郎中)掌度支国用。(《类要》卷15“度支”引《职员令》,第626页上)
考释:此条同《通典》卷23《职官五》注所载度支郎中执掌。(第637页)
14.【唐代】(金部郎中)掌库藏金宝、货物、权衡、度量、市易之事。(《类要》卷15
“金部”引《职员令》,第626页上)
考释:《通典》卷23《职官五》注:“(金部郎中)掌库藏金宝货物,权衡度量等事。”(第638页)《新唐书》卷46《百官一》:“金部郎中……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两京市、互市、和市、宫市交易之事,百官、军镇、蕃客之赐,及给宫人、王妃、官奴婢衣服。”(第1193页)
15.【开元二十五年】(仓部郎中)掌诸仓廪之事。(《类要》卷15“仓部”引《职员令》,第626页上)
考释:此条同《通典》卷23《职官五》注所载仓部郎中执掌。(第638页)
16.【垂拱】(春官尚书)总判春官、祠[部]、膳[部]、主客事。(《类要》卷15“礼部尚书”,第626页下)
考释:《通典》卷23《职官五》:“(礼部尚书)总判祠部、礼部、膳部、主客事。”(第639页)《旧唐书》卷42《职官一》:“光宅元年九月,改……礼部为春官……神龙元年二月,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第1788页)故本条为《垂拱令》。
17.【唐代】 (礼部郎中)掌礼乐、学校、仪式、制度、衣冠、符印、表疏、图书、策命、祥瑞、铺设、丧葬、赠赙、王及[宫](官)人之事。(《类要》卷15“礼部郎中”,第627页上)
考释:《通典》卷23《职官五》注:“(礼部郎中)掌礼乐、学校、仪式、制度、衣冠、符印、表疏、册命、祥瑞、铺设、丧葬、赠赙及宫人等。”(第639-640页)
18.【神龙】【太极)【开元三年】【开元七年】(祠部郎中)掌祠祀、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道士、女冠、僧尼簿书之事。(《类要》卷15“祠部”,第627页上)
考释:《通典》卷23《职官五》注:“(祠部郎中)掌祠祀、天文、漏刻、国忌、庙讳、 卜祝、医药等及僧尼簿籍。”(第640页)《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道、佛之事。”(第120页)《唐会要》卷59“祠部郎中”:“延载元年五月十一日,敕:‘天下僧尼道士隶祠部,不须属司宾。’……(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七日,道士、女道士割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第1207页)则本条为垂拱以后,开元二十五年前令文。
19.【开元二十五年】(膳部郎中)掌饮膳、藏冰及食料之事。(《类要》卷15“膳部”
引《职员令》,第627页下)
考释:此条同《通典》卷23《职官五》注所载膳部郎中执掌。(第640页)
20.【开元二十五年】 (主客郎中)掌二王后及诸[藩] (蕃)朝[聘] (宾)之事。
(《类要》卷15“主客”,第627页下)
考释:此条同《通典》卷23《职官五》注所载主客郎中执掌。(第640页)
21.【垂拱】 (夏官尚书)掌武官选举,总判夏官、职[方]、驾[部]、库[部]事。
(《类要》卷15“兵部尚书”,第628页下)
考释:《通典》卷23《职官五》:“(兵部尚书)掌武官选举,总判兵部、职方、驾部、库部事”。(第641页)《旧唐书》卷42《职官一》:“光宅元年九月,改……兵部为夏官……神龙元年二月,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第1788页)故本条为《垂拱令》。
22.【开元二十五年】 (兵部郎中)掌武职、[武]勋官、三卫[及] (又)兵士簿书、朝集、禄赐、假使、差发、配[亲]事[帐]内考校及给武职告身。(《类要》卷15“兵部郎中”,第629页上)
考释:此条《记纂渊海》卷28“兵部郎中”引《职员令》作“掌武职、勋官、三衙及兵士簿书、朝集、禄赐、假告、差发、武职告身之事”(第10页),中村裕一《唐令逸文の研究》据以复原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第10-13页),《唐令拾遗补》收入(第335页),宜以此条为引据资料。“兵士”下《通典》卷23《职官五》注所载兵部郎中执掌多“以上”二字,“校”作“覈”,余同。同卷注:“(郎中)掌与侍郎同”。(第642页)
23.【开元二十五年】(职方郎中)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防人路程远近、归化酋渠之事。(《类要》卷15“职方”引《职员令》,第629页上)
考释:“酋渠”,《通典》卷23《职官五》注所载职方郎中执掌作“首渠”(第642页),余同。
24.【开元二十五年】 (驾部郎中)掌舆马、[车] (典)乘、邮驿、厩牧、官私马驴、阑遗杂畜之事。(《类要》卷15“驾部”,第629页下)
考释:“舆马”,《通典》卷23《职官五》注所载驾部郎中执掌作“舆辇”,“官私马驴”作“司牛马驴骡”(第642页),余同。
25.【开元二十五年】(库部郎中)掌军器、仪仗、卤簿、法式及乘舆之事。(《类要》卷15“库部”,第629页下)
考释:此条同《通典》卷23《职官五》注所载库部郎中执掌。(第643页)
26.【开元二十五年】 (刑部尚书)掌总判刑[部]、[都] (部) [官]、比[部]、司[门]事。(《类要》卷15“刑部尚书”,第630页上)
考释:《记纂渊海》卷28“刑部尚书”引《职员令》同。(第13页)《唐令逸文の研究》据以复原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第13页),《唐令拾遗补》收入(第335页),宜以此条为引据资料。此条同《通典》卷23《职官五》所载刑部尚书执掌。(第644页)
27.【垂拱】(秋官郎中)掌律令、定刑名、按覆司刑及诸州应奏之事。(《类要》卷15“刑部郎中”,第630页下)
考释:《通典》卷23《职官五》注:“(刑部侍郎)掌律令、定刑名、案覆大理及诸州应奏之事。”同卷注:“(郎中)与侍郎同。”(第644-645页)《旧唐书》卷42《职官一》:“光宅元年九月……改大理为司刑……神龙元年二月,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第1788页)故本条为《垂拱令》。
28.【开元二十五年】 (都官郎中)掌簿敛、配入官户奴婢簿籍、良贱及部曲、客女、俘[囚](国)之事。(《类要》卷15《都官》,第630页下)
考释:“配入”,《通典》卷23《职官五》注所载都官郎中执掌作“配役”,“官户奴婢”作“官奴婢”(第645页),余同。
29.【开元二十五年】(比部郎中)掌内外诸司公廨及公私债负、徒役、工程、赎物帐及勾用度[物]之事。(《类要》卷15“比部”,第630页下)
考释:“赎物账”,《通典》卷23《职官五》注所载比部郎中执掌作“赃物账”(第645页),余同。
30.【开元二十五年】 (司门郎中)掌门籍,关栈、桥梁及道路、过所、阑遗物之事。
(《类要》卷15“司门”,第630页下)
考释:此条《记纂渊海》卷28“司门郎中”引《职员令》作“掌门籍、关栈及道路、[过]所、阑遗物之事”(第17页),《唐令逸文の研究》据以复原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第17页),《唐令拾遗补》收入(第336页),宜以此条为引据资料。“关栈桥梁”,《通典》卷23《职官五》注所载司门郎中执掌作“关桥”(第646页),余同。
31.【垂拱】冬官总判[冬官](工)、屯[田]、虞[部]、水[部]事。(《类要》卷15“工部尚书”,第631页上)
考释:《通典》卷23《职官五》:“(工部尚书)总判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事”。(第646页)《旧唐书》卷42《职官一》:“光宅元年九月,改……工部为冬官……神龙元年二月,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第1788页)本条为《垂拱令》,在抄入《类要》时有所改写。
32.【开元二十五年】 (工部郎中)掌兴造、工匠、诸公廨屋宇、五行、纸笔之事。(《类要》卷15“工部郎中”引《职员令》,第631页下;《记纂渊海》卷28“工部郎中”引《职员令》,第18页;《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16“工部郎中”引《职员令》,第1919页)
考释:《唐令逸文の研究》据《记纂渊海》、《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复原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第19页),《唐令拾遗补》收入(第336页),宜以此条为引据资料。“纸笔”,《通典》卷23《职官五》注所载工部侍郎执掌作“并纸笔墨”,余同。同卷注:“(郎中)所掌与侍郎同。”(第646-647页)
33.【唐代】(屯田郎中)掌屯田、诸司公廨、官人职分、赐田及官园、官宅之事。
(《类要》卷15“屯田”,第631页下)
考释:《通典》卷23《职官五》注:“(屯田郎中)掌屯田、官田、诸司公廨、官人职分、赐田及官园宅等事。”(第647页)
34.【开元二十五年】(虞部郎中)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类要》卷15“虞部”,第631页下)
考释:此条同《通典》卷23《职官王》注所载虞部郎中执掌。(第647页)
35.【开元二十五年】 (水部郎中)掌川泽、津济、船舻、浮桥、渠堰、陂池、渔捕、运漕、水碾硙之事。(《类要》卷15“水部”,第631页下—632页上)
考释:《通典》卷23《职官五》注:“(水部郎中)掌川渎、津济、船舻、浮桥、渠堰、渔捕、运漕、水碾硙等事。”(第648页)敦煌文书P.2507《开元二十五年水部式》残卷所涉内容大体与此条合,(43)当为开元二十五年令。
36.【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年】 (侍中)掌侍从,负宝,献替,赞相礼仪,审署奏抄,驳正违失,监封题,给驿券,监起居注,总判省事。(《通典》卷21《职官三》“侍中”引《令文》,第549页;《类要》卷16“侍中”引《职员令》,第633页上)
考释:此条《唐令拾遗》据《通典》复原为开元七年及开元二十五年令(第34页),未加论证。按本条称玺作“宝”。《通典》卷21《职官三》: “符宝郎……隋初有符玺局,置监二人……炀帝改监为郎,大唐因之。长寿三年(694),改为符宝郎。神龙初,复为符玺郎,开元初,复为符宝郎。”(第559页)《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开元六年十一月)乙巳,传国八玺依旧改称‘宝’,符玺郎为符宝郎。”(第179页)长寿三年至神龙初无修订格令之事,故当为开元七年或此后之令。
37.【开元二十五年】(门下侍郎)掌侍从,省署奏抄,驳正违失。(《类要》卷16“门下侍郎”引《职员令》,第634页下)
考释:《通典》卷21《职官三》:“(门下侍郎)掌侍从,署奏抄,驳正违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阙,则监封题,给驿券。”(第550-551页)《唐令拾遗》据以复原为开元七年及二十五年令(第34页),宜以此条为引据资料。
38.【开元二十五年】 (给事中) [掌] (常)侍从,[读](诸)署奏抄,驳正违失。
(《类要》卷16“给事中”引《职员令》,第634页下)
考释:《通典》卷21《职官三》:“(给事中)[掌](常)侍从,读署奏抄,驳正违失,分判省事。若侍中、侍郎并阙,则监封题,给驿券”。(第551页)《唐令拾遗》据以复原为开元七年及二十五年令(第34页),宜以此条为引据资料。
39.[贞观][永徽](散骑常侍)掌侍从赞相。(《类要》卷16“散骑常侍”引《职员令》,第635页下)
考释:《通典》卷21《职官三》:“(散骑常侍)贞观十七年,复置为职事官,始以刘洎为之。其后定制,置四员,属门下,掌侍从规谏。显庆二年,迁二员,隶中书,遂分为左右。左属门下,右属中书……龙朔二年,改左右散骑常侍为左右侍极,咸亨元年复旧。”(第554页)《类要》置散骑常侍于门下省,且未分左右,疑本条为《贞观令》或《永徽令》。
40.【开元二十五年】(谏议大夫)掌侍从规谏。(《类要》卷16“谏议大夫”引《职员令》,第637页上)
考释:此条同《通典》卷21《职官三》所载谏议大夫执掌。(第555页)
41.【唐代】(起居郎)掌侍从,录起居注。(《类要》卷16“总叙起居”引《职员令》,第637页下)
考释:《唐六典》卷8“门下省”:“起居郎掌录天子之动作法度,以修记事之史。”(第248页)
42.【开元二十五年】(中书令)掌侍从、献替、制敕、册命、敷奏文表、授册,监起居注,总判省事。(见《通典》卷21《职官三》引《令文》,第562页;《类要》卷16“中书令”引《职员令》,第640页上)
考释:《唐令拾遗》据《通典》复原为开元七年及二十五年令(第36页),此条可补为引据资料。
43.【开元二十五年】 (中书侍郎)掌侍从、制敕、册命、敷奏文表。(《类要》卷16“中书侍郎”引《职员令》,第640页下)
考释:《通典》卷21《职官三》:“(中书侍郎)掌侍从、献替、制敕、册命、敷奏文表。通判省事。”(第563页)《唐令拾遗》据以复原为开元七年及二十五年令(第36页),宜以此条为引据资料。
44.【垂拱】【神龙】(左肃政台/左御史台大夫)掌肃清风俗,纠弹在京非违。(《类要》卷16“御史大夫”引《职员令》,第647页下)
考释:《通典》卷24《职官六》:“大唐因隋,亦曰(御史)大夫……掌肃清风俗,纠弹内外,总判台事。”(第666页)《令集解》前篇卷5《职员令·弹正台》:“尹一人,掌肃清风俗,弹奏内外非违。”注曰:“内者左右两京,外者五畿七道也。”(第137-138页)《通典》所谓“纠弹内外”,与此一致,而与本条“纠弹在京非违”显然不同。《唐会要》卷60《御史台》:“武德初,因隋旧制为御史台,龙朔二年四月四日改为宪台,咸亨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复为御史台,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左肃政台,专管在京百司及监军旅;更置右肃政台,其职员一准左台,令按察京城外文武官僚……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左右御史台,景云三年二月二日废右台,先天二年九月一日又置右台,停诸道按察使,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又置诸道按察使,废右台。”(第1225页)则武后、中宗时期,左台纠弹京城,右台按察州县。又《旧唐书》卷7《睿宗纪》:“(太极元年二月)辛酉(二十二日),废右御史台官员。己巳(三十日),颁新格式于天下。”(第159页)则太极格令已无右台内容。则本条当为《垂拱令》或《神龙令》。
45.【开元以前】(殿中侍御史)掌[驾](届) 出于卤簿内纠察非违,余同侍御史,唯不判事。(《类要》卷16“殿中侍御史”引《职员令》,第650页上)
考释:此条《记纂渊海》卷30“殿中侍御史”(第19页)、《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25引《职员令》作“掌驾出于卤簿内纠察,与侍御史同,惟不判事”(第12页上)。《唐令逸文の研究》据以复原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第19-20页),《唐令拾遗补》收入(第336页),误。《通典》卷24《职官六》:“(殿中侍御史)初掌驾出于卤簿内纠察非违,余同侍御史,唯不判事……自开元初以来……兼知库藏出纳及宫门内事,知左右巡,分京畿诸州诸卫兵禁隶焉,弹举违失……”(第673页),则本条应为开元以前令。
46.【垂拱】【神龙】(左肃政台/左御史台监察御史)掌在京纠察、祠祀及诸出使之事。(《类要》卷16“监察御史”引《职员令》,第650页下)
考释:《通典》卷24《职官六》:“(监察御史)掌内外纠察并监祭祀及监诸军、出使等。”(第674页)本条作“掌在京纠察”,亦是武后、中宗时制度,当为《垂拱令》或《神龙令》。
47.【垂拱】(尚食局奉御)掌总知御膳,进食先尝,分别判局事。(《类要》卷19“尚食局”引《具员故事》引《令·职员令》,第698页下)
考释:《具员故事》,唐梁载言撰,梁载言事迹附见《旧唐书》卷190《刘宪传》,著有《具员故事》10卷、《十道志》16卷(第5017页),卒于开元前期。(44)《类要》卷19“詹事府”引《具员故事》:“宫尹府,即詹事府,宫尹府有此名也。”(第711页上) 《旧唐书》卷42《职官一》:“光宅元年九月,改……詹事府为宫尹府……神龙元年二月,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第1788页)则《具员故事》作于武后光宅改官名以后,所引为《垂拱令》。
48.【唐代】 (奚官局令)掌[守]宫人、伎乐、导(守)引、宝仗、疾病、罪罚、丧葬之事。(《类要》卷19“奚官局令”引《令·职员令》,第700页下)
考释:《通典》卷27《职官九》:“(奚官局令)掌守宫人、使药、疾病、罪罚、丧葬等事。”(第758页)
附论:太常卿,位任特隆,学冠儒林,艺通礼乐者可以居之。(《职官分纪》卷18,第418页下;《记纂渊海》卷23,第21页;《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26,第2036页上;《翰苑新书》前集卷21,第202页下)
按,此条《唐令逸文の研究》据上述文献复原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第21-22页),《唐令拾遗补》收入(第366页),误。此条实为北魏《职员令》佚文。首先,本条在《职官分纪》中列于《齐职仪》与《隋百官志》之间。以《分纪》体例,此条所叙并非唐制度。其次,此条“艺通礼乐者可以居之”,系对任职资格的描述。据敦煌本《东宫诸府职员》可知,一般而言,唐职员令仅载员数与执掌,并不包括任职资格。《唐令拾遗》复原《三师三公台省职员》虽有任职资格的描述,但由于三公三师皆属虚职,故无员数,亦无执掌,但空论其资格,未必本于《职员令》。而《唐令逸文の研究》认为本条所载的员数与执掌已佚失,并引《通典》卷27《职官九》所载“凡祭酒、司业,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认为《职员令》原有对任职资格的描述(第21-22页),实无确证。第三,北魏孝文帝曾撰《职员令》21卷,(45)《太平御览》、《职官分纪》所引《后魏职令》皆载明任职资格,体例与本条同,例如《职官分纪》卷18引《后魏职令》:“宗正卿第四品上,第三清,选用忠懿清和,识参教典者。先用皇宗,无则用庶姓。”(第434页下)其位置亦在《隋百官志》之前,而体例与此略同。《唐令逸文の研究》及《唐令拾遗补》应剔除此条。
四、北宋文献所引职员令佚文来源推测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太平御览》、《类要》及《职官分纪》中所保存的令文,涉及唐前期所修订的多部令文,(46)显然并非单纯地抄录自某一年度的唐令。那么探究这些佚文的可能来源,对于我们认识北宋前期唐令的流传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追究《类要》及其同时代文献所存佚文的可能来源之前,不妨先看一下北宋前期,尚有多少文献可能保存《职员令》佚文。
其一,完整的《唐令》。《新唐书·艺文志》载《唐令》共4部,分别为《武德令》、《贞观令》、《永徽令》和《开元令》,包括《唐会要·定格令》明确提及的几部令文。但在记录北宋前期秘阁实际藏书的《崇文总目》中却只提到《唐令》一部,30卷,未题撰入。曾巩虽作《唐令目录序》,但仍未指出其年度,(47)很可能即是《天圣令》以为蓝本的开元二十五年令。另外,《直斋书录解题》卷7《法令类》载《唐令》30卷,题宋璟撰,为开元七年令,(48)则此本在北宋时代亦应有流传。由于《新志》的补史志性质,所载并非为一时实际藏书,(49)故北宋前期所能见到的完整《唐令》,很可能仅有开元七年与开元二十五年令。
其二,律令格式汇编。除有限的《唐令》以外,北宋前期尚有为数不少的摘录汇编唐代律令格式的文献。《新志》、《崇文总目》刑法类所载包含唐令的法令汇编,有李林甫等编《格式律令事类》40卷、王行先《律令手鉴》2卷、裴光庭《唐开元律令科要》1卷。《宋志》刑法类又载萧昊《开元礼律格令要诀》1卷。这些律令汇编应当包括《职员令》内容。
其三,职官书。《类要》所引《具员故事》包含《职员令》文字,提示了各年度《职员令》很可能是这类职官书的材料来源之一。除《具员故事》以外,《新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补》职官类所载这一类文献尚有杜英师《职该》2卷、任戬《官品纂要》10卷、李吉甫《元和百司举要》1卷、韦述《唐职仪》30卷、杜佑《唐外典职官纪》10卷、无名氏《唐百官职纪》2卷、孔至道《百官要望》1卷。这些著作都记载了唐代各个时期官员的员数与执掌,(50)《职员令》无疑是其重要的材料来源之一。
其四,职员令汇编。《太平御览经史纲目》载《唐职员令》一种,《太平御览》所引3条皆出于此书。《唐职员令》不见于史志著录,但太平兴国九年(984),日本僧奝然入宋之时,所献之书即有其国《职员令》1卷。(51)考虑到唐代出现的大量律令汇编及职官书在当时已有不少传入日本,(52)可以认为奝然所献《职员令》很有可能即受了这一类文献的影响,而将令文之中的《职员令》部分单独汇编成书。《唐职员令》的产生亦当源于相同的背景。《御览》所引《唐职员令》皆为官员执掌,故而可以视为以原始令文为材料的职官书。
综上所述,北宋前期,唐代各年度《职员令》仍或零或整地保存于各类书籍、档案之中,因此《类要》、《太平御览》以及《职官分纪》中这部分内容的来源也并非单纯。以下即对其可能来源稍作推论。
《职官分纪》所载两条唐《职员令》皆载录员数,而以执掌为注文,与敦煌本《永徽职员令》体例相合,很可能出自完整的唐令。而“司封郎中”一条及于天宝制度,因此《职官分纪》所引《职员令》或即出自《天宝令》。
《太平御览》所引职员令佚文的来源已如上文所示,三条佚文中,“左右司郎中”与“司封郎中”两条可确定为垂拱令,可知《唐职员令》一书很可能包含了不同年度的职员令。
《类要》之中,“尚食局”一条出于梁载言《具员故事》,“奚官局令”一条,由于引录格式与“尚食局”条同,皆作“令·职员令”,而完全不同于其他各条,很可能同样转录自《具员故事》。除此而外的44条分属于武德、贞观、垂拱、神龙、开元等不同年度,故并非抄录自某年度《唐令》。考虑到《类要》所引《职员令》与《太平御览》一样,仅载执掌而不及员数,而且现存的37卷中除了这46条职员令以外,并未见引录唐代律、格、式及《职员令》以外的其他令文,故其来源很可能也出于《唐职员令》或者类似的职员令汇编。
《太平御览》、《类要》及《职官分纪》所引《职员令》佚文的可能来源提示我们,北宋初期,除不多的几部《唐令》以外,唐代各年度《职员令》以多种形式保存于律令汇编及职官书中,其中甚至有《唐职员令》这样专门以官员执掌为内容的唐令汇编,其内容不仅仅包括现行之令,还保存了相当一部分久已废除的旧令,因此北宋前期的文献中仍有可能对其进行引录。进一步来说,《新唐书·百官志》中不见于《六典》及《旧唐志》的文字,其来源很可能也是北宋初年尚存的律令汇编或职官书中所保存的各年度《职员令》。
通过本文对以《类要》为代表的北宋前期文献中所保存的《职员令》佚文的考察,可以发现,唐代令文并不一定随着其本身的废止而失去生命力,实际上它们仍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被引用而流传后世。而令文本身文字的稳定性,使各个时期制度的变迁往往体现在细微的文字差别之中,因此唐令的复原,不应当局限于有限的某些年度的令文,也不应当仅仅从与传世文献在文字上的相似来判断佚文的年代,而应当着眼于佚文本身所透露出的时代讯息,如此,或可稍稍接近于唐令的本真面貌。
注释:
①《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5页。
②参见黄正建:《天一阁藏〈天圣令〉的发现与整理研究》,《唐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③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栗劲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
④仁井田陞:《唐令拾遗補》,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
⑤中村裕一:《唐令逸文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
⑥学界一般认为《天圣令》所附唐令为开元二十五年令,但黄正建《〈天圣令〉附〈唐令〉是开元二十五年令吗》(《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一文,指出其在部分细节上反映了唐代后期的制度,可能是唐后期修改过的一部唐令。
⑦参见宋家钰:《明钞本北宋〈天圣令〉(附唐开元令)的重要学术价值》,收入《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13页。
⑧《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第183-184页。
⑨《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注,第185页。
⑩参见黄正建:《天一阁藏〈天圣令〉的发现与整理研究》,《唐研究》第12卷,第1-220页。
(11)参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0页。
(12)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第49-54页,原卷行数参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第180-197页。
(13)参见中村裕一:《唐令逸文の研究》,第27頁。
(14)仁井田陞在《唐令拾遗·序论》中把《唐六典》与《通典》列入选用的资料,并认为《唐六典》“可能是以开元七年(又云四年)令作为基准”(第853页),而《通典》“很多地方依据撰成时施行的开元二十五年令”(第858页)。虽然仁井田陞也注意到《唐六典》中可能包含其他年度的令文(第853页),但在职员令的复原中,仍将与《唐六典》或《通典》相合的条文处理为开元七年与开元二十五年令,如第27页“尚书都省”条,第32页“吏部”条等。
(15)(17)参见中村裕一:《唐令逸文の研究》,第27頁。
(16)参见李锦绣:《唐开元二十五年〈仓库令〉研究》,《唐研究》第12卷,第11-18页。
(18)《通典》卷23《职官五》,“司封郎中一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34页。
(19)《唐会要》卷49《僧尼所隶》:“延载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隶祠部,不须属司宾。’……至(开元)二十五年七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天宝二载三月十三日制:‘僧尼隶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检校,不须隶宗正寺。’元和二年二月,诏僧尼道士同隶左街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复关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06-1007页)故司封掌道士、女冠仅在天宝二载以后,元和二年以前。
(20)《唐会要》卷39《定格令》,第820页。
(21)参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第437-753页。
(22)《太平御览》卷216,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31页下。
(23)参见李锦绣:《唐代视品官制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68-81页。
(24)参见唐雯:《〈《记纂渊海》所引的《唐职员令》逸文〉补证——兼述晏殊〈类要〉所见〈唐职员令〉》,《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4期,第26-27页。
(25)(28)《曾巩集》卷13《类要序》,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0页。
(26)此从《直斋书录解题》卷14《类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26页)所载,《中兴书目》载77卷(见《玉海》卷5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33页),多出的一篇或为目录。又《郡斋读书志》卷14《类书类》(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63页)载65卷,应非全本。上述考证,参见陈尚君:《晏殊〈类要〉研究》,收入《陈尚君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1页。
(27)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2:“晏元宪平居书简及公家文牒未尝弃一纸,皆积以传书,虽封皮亦十百为沓,暇时手自持熨斗,贮火于旁,炙香匙亲熨之,以铁界尺镇案上,每读书得一事,则书以一封皮,后批门类,按书吏传录,盖今《类要》也。”(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9页右栏)
(29)参见唐雯:《〈《记纂渊海》所引的《唐职员令》逸文〉补证——兼述晏殊〈类要〉所见〈唐职员令〉》,第27页。
(30)《类要》卷15“吏部尚书”,《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6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23页。
(31)见《旧唐书》卷42《职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88页。
(32)《唐会要》卷39《定格令》,第819-824页;另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序说”,第809-821页。
(33)《旧唐书》卷42《职官一》,第1793、1794、1796、1797、1798、1799、1801页等。
(34)“刑”,北宋本《通典》作“形”,见《北宋本通典》第1册,东京:汲古书院,1981年,第508页。
(35)黑板胜美:《令集解》前篇卷2,《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本,第2部,第3册,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年,第41页。
(36)《新唐书》卷4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85页。
(37)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下;录文参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第307-308页。
(38)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第308页。
(39)《旧唐书》卷42,第1799页。其中“规”改为“视”,参见李锦绣:《唐代视品官制初探》,第69页。
(40)参见李锦绣:《唐代视品官制初探》,第69-70页。
(41)《天宝令》的编纂,史无明确记载,刘俊文考敦煌文书P.2504为《天宝令式表》,并认为天宝四载玄宗曾再次修订过律令式。参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第374页。
(42)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2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9-270页;录文参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第283页。
(43)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5册,第1-4页;录文参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第326-354页。
(44)张鷟:《朝野佥载》卷6:“怀州刺史梁载言昼坐厅事,忽有物如蝙蝠从南飞来,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绞痛,数日而卒。”(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4页)则张鷟(658-730)见其卒。见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第1卷“游仙窟”条,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45)《魏书》卷7下《孝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2页。
(46)《职官分纪》虽成书于北宋中期,但其书以宋初杨侃《职林》为蓝本,增补了宋代制度, (见《职官分纪》卷首秦观序,第3页)故所载唐制犹是杨侃旧本,与《太平御览》、《类要》仍属同一时期文献。
(47)《曾巩集》卷11,第189页。
(48)见《唐会要》卷39《定格令》,第820页。
(49)参见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自序”,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50)参见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第82-83页。
(51)《宋史》卷491《日本国传》作“职员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31页;《校勘记》引日成寻《参见天台五台山记》延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条引《杨文公谈苑》及黄遵宪《日本国志》作“令”,第14149页。
(52)《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职官家”载李吉甫《百司举要》1卷及《唐六典》,“刑法家”载《唐令私记》30卷、《金科类聚》5卷。见《古逸丛书》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43-7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