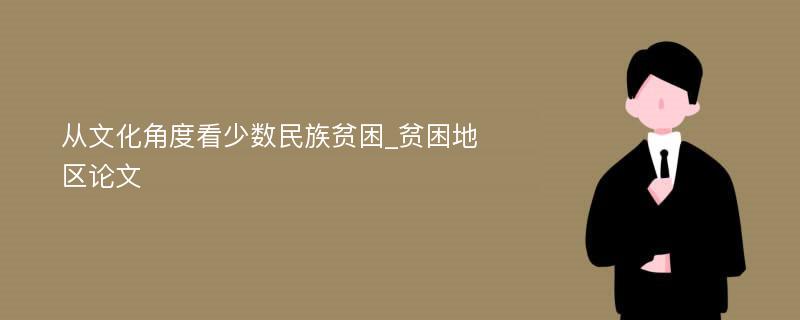
从文化角度探讨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贫困论文,角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2亿多文盲、半文盲与数千万贫困人口所在的贫困县, 在分布上是大体重合的。大多数描述贫困的文献,几乎不约而同地同时涉及到文化方面的问题,把文化“落后”视为贫困状态的特征和导致贫困的根源之一。
一.文化教育的落后,构成了经济贫困的“马太效应”
当贫困不仅被界定为经济收入的低水平与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还同时被界定为社会文化与教育科学卫生水准的严重滞后,从而使人们丧失了发展的权利与机会,亦即发展不足时,贫困的本质也就具有了双重的属性。几乎在所有的贫困地区,经济滞后,文化事业落伍,观念形态陈旧,心理定势保守等,都是一丛共生的社会现象。在陕西省贫困农村,尤其在秦巴山区,尽管由于教育行政系统的支撑,乡村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村一级都建立了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0%以上,但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育质量存在着许多问题。家长们常常认为:读书识几个字,能认得钱币面值不被人哄就行了。师资水平差与升学型的教育体制,并不能直接为乡村社会提供生计帮助;村民们说“不上学是放牛娃,上了学也是放牛娃,花钱耽误时间不合算。”在这里学生中途辍学率高达20—40%,其中女生辍学率更高。
文化教育事业落后的现状,构成了经济贫困“马太”效应的重要环节;与教育事业严重滞后相关的直接后果,便是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很低。贫困人口中文盲与半文盲的比重高得惊人。其中又有相当比例为中青年,这表明老文盲未扫完,新文盲又大量涌现出来。在陕西省商州市,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文盲与半文盲占总人口的21.7%。贫困地区农、林、水、牧等专业人才缺乏,商州市平均每村才摊上0.66人,平均每1.3个村才有1名农技人员,科普事业当然也十分落后。中国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交通阻隔,各种公共文化设施与大众传播媒介也相对落后,这种状况突出地反映了贫困地区的封闭性。调查资料显示,农村贫困户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低,其进取精神也就越差;贫困农户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与农户的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系。
二.贫困落后,导致多种疾病发生
在中国贫困农村,各种地方病与常见病流行,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痴、呆、傻、聋、哑、残人口。根据对全国100多个贫困县的调查, 约有85%以上的县存在着血吸虫病、克山病、大骨节病、甲状腺增生病、氟中毒等各种地方病的高发区。另有调查资料表明,在中国贫困山区的贫困人口中,约有半数左右的人患有肺结核、支气管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肺气肿、贫血、胆襄炎、营养不良症等常见病,在贫困地区约有70%左右的妇女患有各种妇女病。疾病大面积存在的原因,根植于不卫生的生活习惯与卫生科普工作的落后,它同时也是直接导致不幸与贫困的重要途径,疾病使相当一部分人口丧失劳动能力,更摧毁了许多人的生活信心。落后地区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现状与经济贫困的事实交互影响,使许多病人陷于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花不起钱治的状态。
近亲通婚、低能人互婚以及较小地缘范围内的长期交错通婚,也是导致贫困人口增加的根源。在宁夏泾源县,痴呆等缺少生存能力的弱能人口,甚至占全县人口的10%,几乎平均每户就要负担一个这样的人。这些人从根本上缺乏生产与生活的自理能力,一般应将他们列为社会救济的对象,而不是扶贫帮助的对象。但是,导致弱能人口不断产生的根源,至少部分地是基于文化上的愚昧,这是必须花大气力予以根除的。
三、视商品交易为畏途,囿于封闭环境
置身贫困地区封闭环境之中的人们,其社会经济关系仍然较多地囿于家庭、宗教、邻里、亲友、村落等血缘与狭小的地缘社区的范围。人们价值取向的传统属性与生存经验,都根植并依赖于传统的农耕社区;在民间的集市贸易活动中,有许多低收入者的行为,是根据社区血缘人伦的情感原则,而不是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原则。数千年重本抑末、轻商践役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贫困地区仍然直接支持着单一农业和单一粮食的生计,并阻遏着商品经济的生长;某些贫困地区毁林开荒,广种薄收的掠夺性短期经济行为,也有此种文化背景。贫困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视商品交换中讨价还价为羞耻之事,视商业收入为不义之财,单一的粮食种植业的商品率很低,许多人不屑或羞于到市场上出售自产的农副产品。
贫困地区的经济道德更多地仍是保守的传统伦理型,而非商品等价交换的现代型,从潜意识中,他们视商品交易为畏途,为不道德。
形成于历史之上而延续至今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断滋生着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得过且过的观念与行为,加上长期的心理受挫,又进一步强化了听天由命的生活态度。人们缺乏接受新事物的愿望与能力,缺乏创业冲动与进取精神。在陕西贫困地区,许多人的理想生活是“糊汤杂面不断,天天能吃饱饭,不求两转一响,惟求瓦房一间”;无非是肚子、妻子、房子与儿子。人们忙时种庄稼,农闲时外出打工的目的,一是为了打工者自己吃饱肚子,二是挣一点油盐零用钱。“有粮吃、有衣穿,温饱知足求平安”,小“富”即安的心理与行为,在贫困地区是普遍存在的。这是许多脱贫户又不断反复,甚至大面积返贫的原因之一。
数十年之久的输血照顾式和撒胡椒面式的救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等、要、靠的依赖思想。在贫困地区,有一些人常年享受救济粮款而心安理得,甚至还有因救济粮款稍有迟缓便破口大骂者。“反正共产党不让饿死人”,在部分贫困地区已经成为少数贫困者懒惰和混日子的依据。严重的是,借贷和救济已经构成了相当一部分贫困农户必需的生存条件。在贫困地区的许多地方,山多无矿,人多无活,人口压力迫使人们不断毁林开荒以扩大广种薄收的贫瘠土地的面积,进而不断强化了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人口剧增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在陕西省商州,农村人均耕地0.79 亩, 其中个别贫困乡人均耕地仅0.3亩。尽管在人口繁育增长与收入水平之间, 未必呈现为简单的负线性相关关系,但生育文化抑制脱贫进程,却是无疑的。早婚早育、超计划生育,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在许多贫困地区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贫困使人们的行为具有严重短期化的倾向。除了粗放、原始而沉重的农耕劳动需要通过生育增加劳动力之外,中国民间文化中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早栽树,早乘凉”的传统观念与习惯的根深蒂固,也是不容忽视的内因。
贫困地区农民的乡土观念极为浓厚和顽固,没有相当把握,绝不轻易离土经营非农生计,“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土窝”,这种守旧观念给通过移民解决贫困问题的尝试造成了困难。在某些场合下,还有因移民而导致贫困的情形,这除了政策性移民往往忽视社区重建工作的原因之外,还有移民不能适应新环境而导致文化心理综合性失调等方面的原因。
在生活方式上,节令岁时,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以及建屋乔迁等节庆礼仪,给单调的贫困生活带来了变动、期望和某种节奏感,但其间的无度浪费与非生产性超额支出,却直接阻滞着一些有限积累以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
经济贫困、文化滞后、观念保守陈旧,三者相互影响制约,互为因果条件,说明实际上是一个范围更大,内涵也更为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从文化的视角看来,扶助或减缓贫困的努力,不应只是帮助贫困者暂时增加一些收入,还应包括传统经济道德的转变,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和传统人格与行为的重塑。
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扶贫应是重点
我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已逐渐逼近1亿大关。数十年来, 少数民族地区获得了许多长足的进步,但至今仍有大面积贫困现象的存在。在国家重点扶持的数百个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贫困县约占42%(且不含西藏自治区所辖的贫困县),在中国,整个少数民族地区,总体上都属于不发达地区,除绝对贫困之外,更有大量相对贫困现象体现为不同民族之间尤其是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之间的差距。
除个别少数民族的某些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超过汉族与全国平均水平之外,更多的少数民族尚未完全摆脱贫困,据统计,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约占民族地区农村贫困总人口的70%左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解决温饱的人口大约要高出8至10个百分点。 对于某些民族如独龙族、怒族、僳僳族、佤族、景颇族、德昂族、布朗族以及部分彝族、回族和苗族等而言,贫困表现为区域、族体乃至时间的整体连续性。在云南省怒江州,贫困户与贫困人口分别约占总农户与总人口的85%和80%;金平县的拉祜族农户中有80%左右,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与落后状况,已经成为中国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少数民族经济上的相对贫困,又通过民族差距部分地反映到国家各民族的政治关系之中。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与焦点。
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状态的描述,应该说更不能回避文化的视角。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其人口中受教育程度等衡量发展的指标,通常都显示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格局。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虽然超过其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但因起点太低,目前,仍远不能尽如人意。
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约有近20%左右的适龄儿童不能入学;云南、贵州、青海,少数民族人口的文盲率甚至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数十个百分点,其中少数民族妇女的文盲率就更高了。在贵州省3 个自治州的农村,每年约有20万左右的新文盲产生;全省少数民族人口仅有6%左右的人从事工商业或半工半农的职业。 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人员与各种专门人才奇缺;文化设施与卫生设备也相对落伍;交通阻塞,信息不灵。这些与贫困相纠葛的现状,都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改观。
为某些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所认可的近亲婚姻和高生育现象,也给少数民族人口的生活质量和受教育程度带来不利影响。西南地区某些少数民族的部分人口中,甚至已经出现在身高、体重等方面递减的种群退化趋势。少数民族的人口出生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习俗助长、政策宽松、宗教鼓励等因素影响下,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高速增长使人均收入呈现出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状态,并给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严重压力。
少数民族地区约有数十种乃至更多的民族语言或文字,被实际使用着。语言文字的多样化,维系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共识与族内交际,但却实际存在着与多数民族及主流社会对话沟通的阻碍,客观上影响到现代文化信息的传入。村寨、家庭或狭小的区域社区等,作为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空间,也强化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内向封闭性。在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中,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习惯及其相关的一些消费特征,突出地表明与贫困相联系的“大锅饭”,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顽强。粗放的农耕或畜牧生计,必须以互助、馈赠等方式换取传统社区的帮助,才可能维持生存。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普遍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社区互助共济的传统,这对维持过去和现在某种程度仍然存在的低层次的生存需求曾是必要的,它也常被作为民族美德而受到赞许,但与之伴生的低效率却阻滞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亲族或社区内的共食被视为是高尚的,它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观,与此相应的是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缺乏合理安排家计的习惯。
五、非经济和反资本积累的消费方式必须改变
许多少数民族人口的消费方式,具有宗教性、伦理性和礼仪性,但都以非经济和反积累为特征。在某些藏族地区,曾发生过倾家修筑经堂,甚至贷款朝圣的事;在某些回族地区,清真寺的奢华与村民的贫困相并存;在某些傣族区,人们勤俭积累的财富,常一举用于赕佛等活动;在某些彝族地区,甚有为死者送葬而生者倾其家资的。此外,还有剽牛祭天、学师祭祖等各种宗教性消费的例证。消费的伦理性,主要体现为亲友或社区内的共产共食。在个别地方,甚至还有互相攀比争相款众,不惜破产以博传统美名的类似于夸富宴之类的习俗。少数民族的节庆礼仪十分丰富繁多,操办又十分隆重而奢侈,与之相伴的馈赠礼尚往来,好客的风俗甚至发展到确立集体互访制的地步,每一次节庆聚会,常常也是一次“大吃大喝”的大会餐。一些少数民族消费生活非经济和反积累的文化特性,还突出地表现为大面积存在的酒俗与银饰。在桂西北,调查者曾搜集到以国家救济粮换酒喝的个案;在其他一些地方,闲暇时间是以饮酒作乐的方式度过的,在贵州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人们要将自给不足的粮食的三分之一用于酿酒以备年节时消费,那些不自己酿酒的农户,每年也要花数百元于饮酒。在这样的消费方式下,很难积累起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财富。
六、因地制宜,制定最佳扶贫方略
每个民族在其长期的生存与发展中都适应其人文与生态环境,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就其相对于他们各自的环境而言,都有各自的特长,相互间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是,当某个民族自觉或意识到摆脱其贫困的迫切与必要性时,对其文化与贫困现状之间的关系加以反省,就是必要的了。在不发达地区,发展须始于脱贫,脱贫则不能忽视对其民族文化的某些创造性的转化。任何扶贫计划都应立足于某个文化的原点之上,这除了必须明确扶贫工作在文化方面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之外,还意味着可从民族文化的内核中找到发展的启动、依托或形式。在中国扶贫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不少这方面成功的例证。
一般地说,中国并不缺少一个致力于扶贫计划的统一的行政传递系统,正因为如此,基于对广大贫困地区区域文化多元性及区域生态类型多样性的深入研究,因地制宜,寻找针对不同区域及不同民族的不尽相同的最佳扶贫方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现了与不同的民族或区域文化特点或特长相契合的文化原点,扶贫努力就可能获得意外的进展。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正是找到了中国文化中家庭这个重要的文化原点,才使亿万农民摆脱贫困而走上富裕之路。在商州市,人们也立足“家户”,发展家庭“种加养”的商品经济。商州市的扶贫方略中,突出地要求每户有一个见效快的种植或养殖的短项目,每户有一个林、果类的有后劲的长项目,每户有一名劳动力掌握一门生产实用技能,每户有一名劳动力在农闲季节能够转入劳务输出或其他非农生计的行业等等。这种传递落实到户的内部启动式扶贫方略,旨在稳定和加强贫困农民的家庭经营结构,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益。在1990年全市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8.1 万贫困户中,约有一半以上是通过此种方式实现的,该市利用农村妇女传统的女工手艺,引进的刺绣项目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在贫困的商洛山区,以农民的庭院场地及房前屋后空地为依托,以农家闲散劳力利用农闲季节,大力发展经济作物、饲养及养殖业,逐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山区庭院经济,也是因为找到了文化传统上的原点而获得了收效。1989年的调查显示,庭院经济的收入占到被调查家庭总收入的70%左右。
根据中国贫困农村人们的文化心理与行为特点,通过示范方法移入新的生产项目与实用技术,在各地也被证明是有效的。实用科技人员下乡,努力扶植科技示范户,由此引起的模仿从众正效应将使许多人摆脱贫困。山区大面积推广薄膜玉米栽培技术的尝试,正是这样才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发挥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特长,从而逐渐走上了富裕之路。朝鲜族人民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已使他们各方面走在了发展的前列,西北某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素有重商入世的传统和善于经商的能力,他们的商业活动不仅在搞活流通渠道、活跃市场方面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也使他们自己从中得到了实惠。少数民族的文化特长,还有许多可以在发展经济的目标上做更深一步的开掘,诸如边疆跨界民族的边贸传统,侗族地区的植树习俗,西南地区的集市贸易传统与传统的马帮商业,各少数民族的土特名优产品及其传统工艺,少数民族适应恶劣环境的顽强生存能力等等,都可能成为人们脱贫致富的文化原点。在广西大石山区的环江县土纳屯,毛南人脱贫的成功范例,正是基于养猪的传统,引进科学喂养的技术,从而走上致富之路的。
要发展,要脱贫,就必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文化移入、文化冲击以及与之伴生的文化失调与重构。外来生产技术与生活方式的文化移入,如果能够以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形式为依托,进而找到相互结合的原点,就会极大地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引进科技改造山区原始农耕,重视教育文化事业,正是云南基诺族人民走上富裕之路的经验。
消灭“文化”的贫困和改造贫困的“文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农村现存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应该加强乡土教材的建设,增强农牧业科普、实用技术、计划生育以及健康卫生等方面的辅导与训练,逐渐在传统的社会与文化化过程中不断介入现代文明的影响。农村教育是农村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目前升学型的农村教育,并不能为贫困者解决在当地就业和提供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实际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它成了少数人脱离农村环境和争取城市生活的一种出路。如何培养适宜于社区环境并能带动大家一同发展的人才是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的一大课题。
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方略,除了上述政策之外,强化持家理财能力的培训,提高家庭经营与合理消费的各种技能,或许也是重要的突破口。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可以利用非正式权威组织与当地领袖人物在脱贫与发展上的示范意义,倡导以人均收入和家户消费的基础的生活方式。总之,着眼于文化意识的重构,基于文化原点而起步的扶贫与发展计划,可能更具有生命力。
我们讨论贫困与文化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文化脱贫是唯一重要的,而只是想在经济开发脱贫的各种努力中增加一些文化的视角和文化的目标,因为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真正要解决的,并不只是使贫困者增加一些收入或者暂时能够温饱生存,它最终的目标是人口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和贫困地区社区、经济与文化事业的全面进步。
标签:贫困地区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文化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汉族人口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