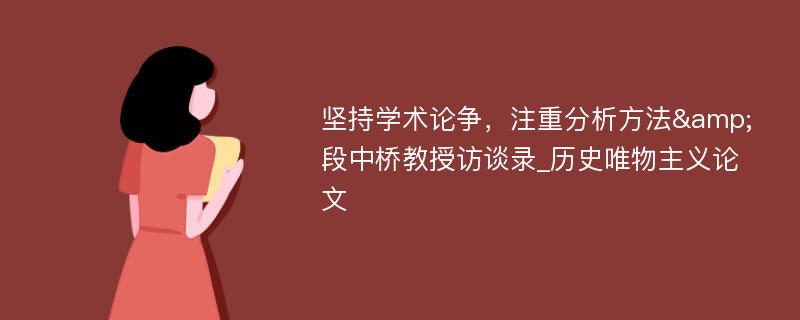
坚持学术争论,注重分析方法——段忠桥教授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注重论文,教授论文,学术论文,方法论文,段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段老师,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我希望借此机会能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您能先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吗?
●说来话长。我是“文革”期间的“老三届”。1969年1月,我作为北京知青,到山西省农村插队落户。1971年3月,我被推荐到地处长治的“晋东南地区太行五七大学”上学,并在那里第一次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知识。两年后毕业,被分配到晋东南地区文化工作站工作。1974年8月,我又被推荐到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上学。我真正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教育是到南开大学之后。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真正坐下来学习哲学知识的时间并不多。但不管怎样讲,南开大学哲学系还是给我们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课程,并安排温公颐、方克立、杨焕章、冒丛虎、车铭洲等老师给我们上课,这使我的哲学知识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深化和扩展。特别是当时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杨焕章老师和教西方哲学的车铭洲老师,他们在学习上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指导。
○您在历史唯物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哲学等领域都有建树,至今仍相当活跃,葆有学术和思想的活力。您的著述给读者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以学术争论的方式充分彰显思想上的个性。很多人都注意到,您的论文标题常常冠有“质疑”、“商榷”、“也谈”、“再考察”、“再思考”之类的语汇,请问,您为什么坚持这样的思考和研究方式呢?
●概括起来,这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学术争论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动力和途径。且不说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西方启蒙以来的“古今之争”,仅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为例,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新哲学论战、新启蒙运动等等,都极大地激发了学术和思想的活力。再如,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如果没有诺齐克、德沃金、科恩等人与罗尔斯就正义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它能得到那样大的发展吗?
其次,争论既体现了对学界既有成果的尊重,又能彰显创新性的成果。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推动学术的进步和发展,而学术的进步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对既有成果的超越上;只有通过争论,才能充分表明超越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我和一些学者进行争论,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的见解最值得重视、且具有广泛影响。那些丝毫不提他人已取得成果、仿佛全都是创新见解的论文,不但是对他人成果的不尊重,而且无从显示个人的创新所在,无助于读者了解学术的进展情况,无益于学术的进步。
再次,缺少争论的论文不能算做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在英国留学,特别是在牛津大学从事研究的经历,使我深刻领悟到进行学术争论的重要性。我的博士论文,即后来由英国埃维巴里—埃希盖特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其内容就是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与英美一些学者的争论。例如,针对汤姆·博托莫尔界定的“社会形态”概念,普拉梅内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后”的观点,科恩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功能解释”,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无主体过程论”,翁贝托·梅洛蒂的“多线图式”,特奥多·沙宁的“未来社会变革道路的多样性”的主张,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这本书能够获得西方学者的认可和好评,就是因为积极地参与国际的学术争论,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
○这是否意味着争论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或必要条件呢?可能您也清楚,有些学者对您的“质疑”和“商榷”颇有微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进行争论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或必要条件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不是说争论性的文章一定就有创新性。我们都看到过,一些与人商榷的文章其实连对方的基本观点都还没有弄懂。争论性的文章实际上很难写。在写这样的文章时,首先要准确把握对方的论点,进而分析它的论点和论证究竟存在什么问题,确定自己能够怎样反驳和“证伪”,最后,还得找到令人信服且容易接受的叙述方式,把自己的论点清楚明确地表达出来。至于人们对我坚持争论的一些微词,我这里愿意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的最后一段话作为回应,这段话大家应当都很熟悉:“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在我看来,国内近些年来学术发展的相对停滞,与学术争论匮乏直接相关,与有限的一些学术争论缺乏应有的学术含量有关。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人在大声疾呼积极开展学术争论,这从一个方面来看是对我坚持争论的认可和呼应。事实上,我发表的论文也不全是争论性的,既有侧重于分析、评介国外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文章,也有一些就国内学者尚未涉及的问题阐述个人见解的文章。
○我们还是继续学术争论这个话题,请您系统谈谈争论中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
●先说历史唯物主义。我在这一领域有不少论文是针对国内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主要是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赵家祥、李清昆、李士坤合著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的观点提出质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的论文,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没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而只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此文发表后不久,南京大学的奚兆永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赵家祥教授分别发表论文对我的那一见解提出了质疑①,我对他们的质疑又分别做了回应②。这场争论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针对近些年来国内流行的一些关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见解,主要是俞吾金教授和孙正聿教授的见解,我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与俞吾金教授的争论涉及五个问题:(一)是否应将恩格斯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能否作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主要文本依据;(三)实践唯物主义是否是马克思本人提出来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否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四)异化(劳动)概念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是实质性的、基础性的,还是连象征性的、边缘性的地位都谈不上;(五)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③ 针对孙正聿教授的观点,我提出了四个不同看法:第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不能仅仅依据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而且还应依据《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明确谈到的阐述已经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第二,从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和《提纲》本身,推导不出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第三,“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第四,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观”,而不是以“历史”的解释原则构成的“世界观”。④
再说国外马克思主义。我在这一领域主要同两位学者进行过争论。
先是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余文烈研究员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特征展开的争论。针对余文烈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在于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我写了两篇商榷的论文,一篇是《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问题——与余文烈同志商榷》(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4期),另一篇是《再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6期)。这两篇论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观点:第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分析”,不是特指20世纪以来流行的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而是泛指包括分析哲学的方法在内的从当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出来的一些研究方法。第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推崇分析的方法、反对辩证法;二是推崇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整体主义。
接下来是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崇温研究员在两个问题上的争论。第一个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针对徐崇温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我写了一篇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吗?——与徐崇温同志商榷》的论文(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6期),从区分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入手,论证了徐崇温的观点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本身。针对徐崇温界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我写了四篇与他商榷的论文⑤,从不同方面表明他的概念界定在逻辑上根本不能成立,在实践上也会妨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是政治哲学。我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时间不长,在这一领域写的争论性论文只有两篇。一篇是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的《马克思认为“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吗?——对中央编译局〈资本论〉第三卷一段译文的质疑与重译》。写这篇论文是因为,在当前国内学者有关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而且众说纷纭的问题是马克思本人如何看待正义。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提出,马克思认为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而他们的文本依据则直接来自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1章“生息资本”中的一段话:
在这里,同吉尔巴特一起(见注)说什么天然正义,这是毫无意义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⑥
马克思对正义的看法真是这样吗?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因为从我读过的马克思有关正义问题的论著来看,除了上面引用的那段译文以外,就再也见不到什么能够表明马克思持有这种看法的文本依据。这是为什么呢?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查阅了马克思那段论述的德文原文及其英译文,结果发现,马克思这段论述的德文原文实际上并不含有这种看法,这种看法是中央编译局译文存在的严重误译所导致的。为此,我在论文中通过对这段德文原文的语义和语境分析,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编译局的译文存在严重误译的问题,并对这段德文原文做了重译。另一篇是针对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在《社会公正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以及中山大学林进平博士在《马克思的“正义”解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中对马克思的正义概念的误解,重新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观。这篇论文就是发表在《哲学动态》2010年第11期的《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正义问题》。
○您所争论的问题都不是枝节性的,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问题,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关系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特征和走向,关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和正义观的正确理解。我注意到,您在争论中非常注重运用分析哲学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证有很强的说服力,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分析哲学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对于我们从事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非常重要。在这一问题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牛津大学的科恩教授那本开山之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我看来,国内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训练,在必须给予论证的地方却没有论证,写出的文章往往概念不清晰、逻辑不严谨,观点和见解自然也就经不起严格的推敲。
就我本人的情况而言,读大学和硕士研究生期间对形式逻辑很感兴趣,写文章时注重逻辑推理的严谨性,但真正感悟到分析哲学方法的重要,却是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以及后来在牛津大学做客座研究员期间。在与英国学者的交往中,特别是在与科恩教授的交往中,潜移默化地掌握了分析哲学的一些方法。我的博士论文,就在不少方面应用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对此,加拿大学者默里·E·G·史密斯在为我那本《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写的书评中指出:“段的说明方法在许多方面使我们想起杰拉德·艾伦·科恩、约翰·罗默和乔恩·埃尔斯特这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的确,他常常表现出首先关注的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关键的概念,如‘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等等,提供经过分析的严格的定义,并同时力图在他自己对马克思原文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确立马克思的各个命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⑦
○您能具体谈谈您是如何应用分析哲学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吗?
●好的,我来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⑧ 国内一些倡导实践唯物主义的学者由此推论:“尽管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术语,但可以肯定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蕴含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可。事实上,没有‘实践的唯物主义’,又何来践行这一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者’?”⑨
○这个推论我们都很熟悉,似乎它是依据于某种公认的逻辑。论证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时,除了这句名言,还有一句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
●从表面上看,这种推论不无道理,但只要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进行语义分析和语境分析,就会发现推论不能成立。
从语法上看,这一概念是由作为形容词的“实践的”和作为名词的“唯物主义者”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将“实践的”加上着重标示就表明了这一点。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结构,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概念的德文表示和英文表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唯物主义”被表示为“den praktischen Materialisten”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英译本中,这一概念被表示为“the practical materialist”(11)。可见,无论在中文、德文还是在英文中,“实践的”(德文的“praktischen”和英文的“practical”)都是作为形容词来修饰名词“唯物主义者”(德文的“Materialisten”和英文的“materialist”)的。如果“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的语法结构是这样,那就不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这一概念就蕴涵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可,因为“实践的”是修饰“唯物主义者”的,不是修饰“唯物主义”的。
再从语境上分析一下“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的含义。应当说,构成这一概念组成部分的作为名词的“唯物主义者”的含义是清楚的,即它指的是信奉唯物主义的人,那构成这一概念组成部分的作为形容词的“实践的”含义是什么?我认为,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一概念的那段话中没有对其中的“实践的”的含义作专门的说明,那对“实践的”的含义就只能在其出现的语境中去理解,即在其出现的那段话中去理解。然而,在那段话中我们只能看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样的表述,只能推断由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存在等同关系,因而后者的含义对于理解前者具有重要意义,但却看不出“共产主义者”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是什么。这样一来,要弄清“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含义就需要将语境扩大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里对“共产主义者”有多处论述。其中有两段直接相关的论述:
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是互相需要的,而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确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12)
费尔巴哈在那里阐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这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13)
如果在这两段话中出现的“共产主义者”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中的“共产主义者”是同一概念,那我们就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指的就是“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的,或“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的唯物主义者。由此我们可以进而推断,“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中的“实践的”的含义,指的就是投身“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的或“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简言之,投身推翻现存事物的革命的。这种理解可以而且恰好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出现于其中的那段话的其他内容相一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概念就等于认可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和启发性,有助于我们恰当地展开文本解读、思想阐发和历史书写。在20世纪8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客观地讲,它的文本依据还是有问题的,您的语义分析和语境分析从推理—论证上也证明了这一点。学术研究要面向现实,立足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使经典文本的诠释屈从于当下的现实和需要。最后一个问题,对于当下的思想与社会,您有什么样的研究计划?
●我目前正在研究科恩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思想。在当代西方重要的政治哲学理论中,除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就是科恩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三者可谓并驾齐驱,旗鼓相当。对它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已发表了三篇论文:一是《拯救平等:G·A·科恩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两个批判》(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二是《差异原则只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吗?——科恩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质疑》(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7期),三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于它更平等——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载《学术月刊》2011年5月号)。近期我还将陆续推出这方面的系列论文。
○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感觉“坚持学术争论,注重分析方法”可以说是您的学术研究特点所在,期待着您有更多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别客气。在争论中推动学术进步,在分析中深化理论探究,是我的追求所在,相信这也会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注释:
① 奚兆永:《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载《教学与研究》,2006(2);赵家祥:《对质疑“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质疑——与段忠桥教授商榷》,载《北京大学学报》,2006(2)。
② 段忠桥:《马克思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吗?——答奚兆永教授》,载《教学与研究》,2006(6);《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答赵家祥教授》,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5)。
③ 段忠桥:《对俞吾金教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三点质疑》,载《学术月刊》,2006(4);《“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辨析——答俞吾金教授》,载《河北学刊》,2007(6);《质疑俞吾金教授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两个说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6);《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载《江海学刊》,2009(3);《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答俞吾金教授》,载《学术月刊》,2010(2)。俞吾金:《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兼答段忠桥教授》,载《学术月刊》,2006(4);《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载《学术月刊》,2009(10)。
④ 段忠桥:《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孙正聿教授商榷》,载《哲学研究》,2008(1)。
⑤ 段忠桥:《真是“按照西方学术界的习惯用法”吗?——质疑徐崇温同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载《现代哲学》,2004(1);《对安德森“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说法的质疑》,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2);《试析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逻辑矛盾》,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3);《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与徐崇温同志商榷》,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6)。
⑥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⑦ 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4)。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⑨ 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第422-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⑩ Karl Marx Friederich Engels,Band 3,Berlin:Dietz Verlag,1959,p.42.
(11) Karl Marx Frede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ume 5,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6,p.38.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
段忠桥,1951年9月生于北京;197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被分配到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工作;1981年5月调入北京商学院;1984-198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1年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哲学系学习,199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担任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客座研究员。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兼任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主要学术专著有《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英文,英国埃维巴里—埃希盖特出版公司(Avebury Ashgate Publishing Ltd),1995]、《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要译著有《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教材有《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主编及主要作者,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在国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学术月刊》及美国的《自然、社会与思想》(Nature,Society,and Thought)、英国的《批判》(Critique:a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和《政治学》(Politics)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张文喜,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 资本论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