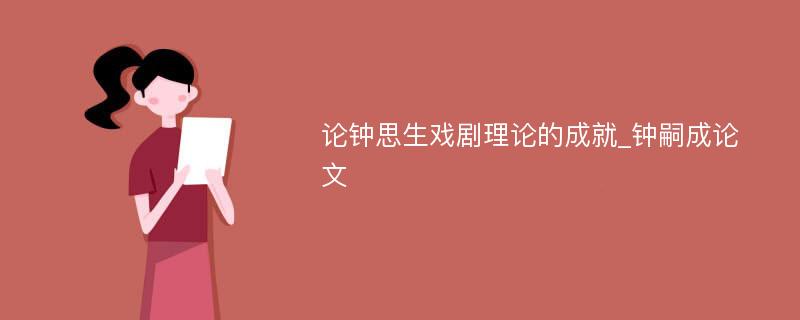
试谈钟嗣成的戏曲理论建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树论文,戏曲论文,理论论文,试谈钟嗣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后期戏曲史家钟嗣成所作《录鬼薄》一书,记载了中国戏曲繁盛期之一元代的戏曲、散曲作家生平事迹和作品目录,计有作家152人,作品四百多种,历来为金元戏曲研究者所重视。然而,其中的有关理论观点则往往被忽略。相对史料内容而言,《录鬼薄》中的理论虽然显得薄弱,但就整个戏曲理论的发展和研究而言,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录鬼薄》中涉及戏曲的理论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有关创作的,一是有关鉴赏批评的。
一
在有关创作的部分,钟嗣成论及了对戏曲创作的认识、态度和创作中作家的修养问题。这二者在他的理论中是息息相关的。但对于如何进行创作,他还论述得不够,不能从整体和独特性上把握戏曲的创作。
中国文学批评历来有雅俗之分,有文章与文学之辨,词论出现时,就面临着为“词”争地位的尴尬,这种尴尬在戏曲理论中也有表现,虽然方式不同,但也是就戏曲的地位问题产生的。钟嗣成作《录鬼薄》,首先就是要为戏曲作家留名。序言中他把戏曲作家同“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著在方册者”并举,认为虽然“门弟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以此激励后学,“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
在序言中钟嗣成对戏曲作家及其创作做了充分肯定,他不是一味空洞地抬高其地位,而且在具体的叙录中,从纯文学和娱乐的角度,进一步表明其态度。他评价官天挺说:“见其吟咏文章笔力,人莫能敌;乐章歌曲,特余事耳。”在录完已死才人名公不相知者时说:“右所录,若以读书万卷,作三场文,占夺巍科,首登甲第者,世不乏人。其或甘心岩壑,乐道守志者,亦多有之。但于学问之余,事务之暇,心机灵变,世法通疏,移宫换羽,搜奇索怪,而以文章为戏玩者,诚绝无而仅有者也。此哀诔之所以不得不作也,观者幸无诮焉。”诗与文历来都认为有关于移风化俗的,有关于经国大事的,虽然陆机《文赋》中也说,“诗缘情而绮靡”,然而孔子以来的诗教传统却是根深蒂固的。钟嗣成不否认这些,他认为戏曲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戏曲摆脱了作为政治的辅附之物,在学问和政事之外是独立的。戏曲是“余事”,是“学问之余”、“事务之暇”的“戏玩”,也不是等闲之辈所能做得。“戏玩”表面看似不够严肃,但作为一种实现自我的途径,作家的内心是极严肃的。与此相关,戏曲是自娱、娱人的。只是钟嗣成对“娱人”这一点认识和阐述都不够。诗、词亦可用于自娱,抒情或排解闲愁,都不象戏曲对于元代士人这样重要,这种“戏玩”、自娱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
元代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蒙古统治者取消仕进,但对士人思想的控制却很松,使许多士人不平则鸣,混迹勾栏,发挥才智,发泄苦闷。元代士人无路仕进,只有将一腔热情寄于乐章的创作和演出,戏曲更多地被作为立身、立志的工具,是知识分子在“消遣”自己。这种自娱、娱人的观点,关汉卿在散曲《不伏老》中已有表达,钟嗣成又有进一步的阐发。正如关汉卿云:“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生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搥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注:隋树森《全元散曲》(上),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2页。)
基于这种观点,对创作者的修养也有了不同的要求,更重视天赋和才性。钟嗣成的基本观点表明在以下言论中:
右前辈名公卿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乐府留心。盖文章政事,一代典型,乃平日之所学,而歌曲词章,由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自有乐章以来,得其名者止于此。盖风流蕴藉,自天性中来,若夫村朴鄙陋,固不必论也。
右所录……但于学问之余,事务之暇,心机灵变,世法通疏,移宫换羽,搜奇索怪,而以文章为戏玩者,诚绝无而仅有者也。
这两段话指出,文章政事可以学而得之,歌曲词章的创作却来自天性,所谓“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占夺巍科,首登甲弟”,“甘心岩壑,乐道守贫”易,为歌曲词章难,只有“心机灵变,世法通疏”的人才能为之。总之,强调的是作家的天赋、才性。所录的作家亦是如此,官天挺“豁然胸次扫尘埃,久矣声名播省台,先生志在乾坤外,敢嫌天地窄,更词章压倒元白”;沈和“天性风流”;范康“一下笔即新奇,盖天资卓异,人何及也”;曾瑞“洒然如神仙中人”;施惠和黄天泽“和气雍容自有春”;赵良弼“不风流难会此,更文才宿世天资”;周文质“学问该博,资性工巧,文笔新奇”;王庸“其制作清雅不俗,知音者服其才”。在钟嗣成看来,这些人的创作都是“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明代宋濂对此作了更形象的阐述:“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譬若水怀珠而川媚,石韫玉而山辉,其理固应尔也。”(注:(明)宋濂《王君子与文集序》,转引自安徽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室编《中国古代文论类编》(征求意见稿)下册,第599页。)
古代文论中,论及作家时,多涉及到才、学、识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要写出好作品,才、学、识三者缺一不可,但对三者的轻重关系的认识各有不同。戏曲不同于诗词是“心机灵变”者的自娱,钟嗣成重视作家的天赋和才气,同时也强调乐章的灵动与不俗。《录鬼薄》中对作者与作品的评价往往浑然一体,钟嗣成多次用到“风流蕴藉”,既是指作者,又是指作品。明代的诗、文、曲都讲性灵,钟嗣成的“才性”、“风流蕴藉”大概就是它的先声了。清代一些戏曲、小说理论也强调天赋、灵性,与钟嗣成的理论息息相关,一脉相承。李渔云:“予又谓填词种子,要在性中来,性中无此,做杀不佳……”(注:李渔《闲情偶寄·重机趣》,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哈斯宝批《红楼梦》云:“文章自有灵性,灵性亦随文而生……袭人收拾行装,王夫人伤心,李纨落泪,宝钗咽泣,写这些琐细事,都只是为了一个宝玉出家。说一句‘宝玉出家而去’不就行了?又何必写这许多?这就如同小厮所说,‘各有原因’。所以,读者不能小看灵性文章,文章灵性。”(注:(清)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三十九回批语,转引自《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下册,第87页。)
二
有关鉴赏的批评,钟嗣成对戏曲作品往往只有片言只字的评价,但却是戏曲评论可见的最初的文字,为后来的戏曲评论奠定了基础。
《录鬼薄》所录作家有擅长杂剧的,有擅长散曲的,所以他的批评也包括散曲在内。评价大致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剧曲中曲辞或韵白及散曲的评价,如新奇、工巧、骈俪、华丽自然等;一是对戏曲的选材和排场的评价,如搜奇索怪、占断排场等。
新奇、工巧是评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新奇,即新鲜、奇特。钟嗣成既是指遣词造句及意象的新奇,比如说到廖毅“时出一二旧作,皆不凡俗。如越调[一点灵光],借灯为喻;仙吕[赚煞]曰:‘因王魁浅情,将桂英薄倖,致令得波烟花不重俺俏书生”,越发新鲜,皆非蹈袭。评范康“一下笔即新奇”,我们试看他的《陈季卿悟道竹叶舟》第二折[驻马听]一段,“我故国神游,见物换星移几度秋。将浮生讲究,经了些夕阳西下水东流。叹兴亡眉锁庙愁,为功名人似黄花瘦。归去休,看银山铁壁层层秀。”(注:宁希元《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页。)这段曲辞或借古人意象,或自造意象,都使人耳目一新。新奇,又可从全篇着眼,指角度的新奇。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一个农民的眼光和口吻来写,让人不禁拍案叫绝。
《文心雕龙》称“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6页。)把奇与正相对,认为“新奇的,是抛弃古旧的,追求新颖的,未免走着危险和诡异的路子的”。(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6页。)钟、刘二人的理论都是在一定历史前提下提出的。刘勰是针对当时的文风流弊而言的,而钟嗣成的时代,前期的杂剧创作尤为兴盛,后期如不追求新奇,难免蹈袭前人,落入俗套,所以钟嗣成所倡导的新奇,是为了让人耳目一新,吸引观众,而非追求奇诡。袁宏道有一段话,更能说明钟嗣成时代的思想:“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前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注:袁宏道《答李元善》,《袁中郎随笔》,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工巧,工致巧妙。睢景臣“南吕[一枝花·题情]云:‘人间燕子楼,被冷鸳鸯锦,酒空鹦鹉盏,钗折凤凰金。’亦为工巧”四句中分别嵌着四种鸟名,真可谓巧妙了。沈和甫“潇湘八景、欢喜冤家等曲,极为工巧”,其中《潇湘八景》可以说是工巧的典范。比如里面的一支[北寄生草]:“春景看山色晴岚翠,夏天听潇湘夜雨疏。九秋现洞庭明月生南浦,见平沙落雁迷芳渚。三冬赏江天暮雪飘飞絮。一任教乱纷纷柳絮舞空中。争如俺侬家鹦鹉洲也住。”(注:隋树森《全元散曲》(上),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32页。)写四时景色,整齐中求变化,亦工亦巧。另外还有钱霖“醉边余兴,极为工巧”;高克礼“小曲、乐府,极为工巧”;王晔、吴朴“所制工巧”。
骈俪,指文章的对偶字法。钟嗣成认为陈以仁“具有骈俪之句”,金仁杰“所述虽不骈俪,而其大概,多有可取。”把二人做一比较,也可见骈俪为何。同样写怀才不遇,金仁杰《萧何月下追韩信》中韩信感叹:“寻思我枉把孙吴韬略学,天交我不发跡直等到老。一回价怨天公直恁困英豪,叹良金美玉何人晓,恨高山流水知音少!礼不通亡了管辖,道不行无了木铎。枉了那兵书战策习的妙,争奈俺命不济漫徒劳。”(注:宁希元《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陈以仁《存孝打虎》中存孝感叹:“比似我辛勤放羊北海,几时逞英雄射虎南山。眼前光景成虚幻,怕的是雁门月冷,紫塞风寒,黄沙漠漠,衰草斑斑,几般儿生熬的人皓首苍颜,消磨尽义胆忠胆。用功劳如韩信、周勃,施妙策如张良、谢安,呀,呀,呀!逞英雄似乐毅、田单。枉将人等闲,小看,便有那吐虹霓志气冲霄汉,命不济枉长叹。每日价伴着沙陀老契丹,受了些摧残。”(注: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9页。)这两段比较,存孝的感叹,骈词俪句,气势连贯,更能感染听众。
钟嗣成评价“方今才人相知者”,所推崇的多为“乐章华丽”者。曹明善“有乐府,华丽自然,不在小山之下。”屈子敬,“乐章华丽,不亚于小山”。张可久,字小山。《中国文学史》评价他:“专以炼句为工,对仗见巧,且多撷取诗词名句,失掉散曲的质朴本色。”(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1页。)这两种评价不管是否公允,都可见华丽是与质朴相对的一种风格,而且华丽同工巧是不可分的,因此华丽常有雕琢之嫌。但钟嗣成把它同自然并举,“华丽自然”大概是说雕琢又不露痕迹,是“终自行为规矩中而其迹未尝滞也。”(注:(宋)葛立方《韵诘阳秋》卷三,转引自《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上册,第701页。)《全元散曲》载张可久事:“涵虚子论曲,谓其词如瑶天笙鹤。又曰:其词清而且丽,华丽不艳,有不喫烟火食气,真可谓不羁之材。”从此记载可见,清且丽,华而不艳,即是华丽自然。
以上是钟嗣成就作家作品进行的评价,但这些评语绝非偶然而发,被用在一起也非巧合,恰恰反映了钟嗣成及当时作者对戏曲的审美追求,新奇、工巧、骈俪、华丽自然反映了他们更多地趋向于追求曲辞和意象上的华美。钟嗣成批评俳谐,认为郑光祖“贪于俳谐,未免斧凿”,说明他们屏弃质朴、俳谐,而这些正是元代前期戏曲的特点,在审美上更接近于壮美。这种前后期的差异主要是社会环境、地域条件和审美角度的不同造成的。元前期戏曲中心在北方的大都,且当时士人的苦闷与反抗精神都很强烈,使曲辞呈现质朴、刚烈的气息。元代后期士人由苦闷转为安于现状,戏曲中心南移至杭州,这时戏曲创作更注重形式,转入曲辞艺术的自觉探索,曲辞呈现南方特有的清新、华丽气息。就如关汉卿是一粒铜豌豆,张可久则是一派渔樵夫的闲谈。
钟嗣成所代表的审美理想影响着后世的创作和理论。明初朱有燉即以华丽为主,主张典雅、华丽的语言,遗弃自然,把华丽推向了极端。明中叶戏曲理论出现了骈俪派和本色派。本色派发扬元前期的理想,以李开先、何良俊、徐渭、李卓吾为代表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本色理论。骈俪派更重视后期的理想,梁辰鱼、王世贞是其中的代表。明末又有临川派和吴江派的论争,吴江派重音律,强调本色,临川派重才情,重意趣神色,强调“情”。这一论争又是本色与骈俪之争的延续。
钟嗣成的戏曲鉴赏批评理论,设有完全脱出论诗、论词的窠臼,还未能发现戏曲自身的特色。后来的戏曲理论亦是如此,或重音律、或重曲辞,直到李渔的戏曲理论出现,在这方面才有所突破。李渔开始重叙事,《闲情偶寄》的语言论及关于“结构”的论述都是就戏曲自身的独特性来论述的。
钟嗣成理论中也有着眼于戏曲整体的评价,这是他理论中的闪光点,难能可贵。在吸引观众上注意了一是排场,一是选材。郑德辉之所以“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才先生’”就是因为他“番腾今共古,占词场,老将伏输”,选材多样,不拘一格。比如有写怀才不遇的《王粲登楼》,有写爱情的《倩女离魂》,有写战斗的《三战吕布》;写古人上自齐景公,写今人下至谢阿蛮。鲍天佑“跬步之间,惟务搜奇索古,故其编撰,多使人感动咏叹”,“谈音律,论教坊,唯先生占断排肠。”“搜奇索古”就是指搜索古今有新意的题材,正是这样的题材,使人感动咏叹。“排场”指戏曲演出的场次安排、舞台调度。如主帅升帐,先由众将“起霸”,造成声势,然后主帅在吹打声中“四记头”出场,念大“引子”归座,“自报家门”。又如次要情节用一个“过场”,甚至“圆场”交代。(注:《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好的排场,收放自如,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鲍天佑大约在创作中更注重这一点。
声腔是戏曲的一大特点。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周德清《中原音韵》等对声乐或音律都有专门的论述。钟嗣成则注意到戏曲作家应知音谐律,如沈和甫即是文学家与音乐家的合一,“以南北调合腔,自和甫始。”
钟嗣成开创了戏曲批评的方法、方向,后代的理论批评在此基础上得以丰富发展。而他只重曲辞不重叙事,忽略了戏曲整体的批评,这些不足之外又是显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