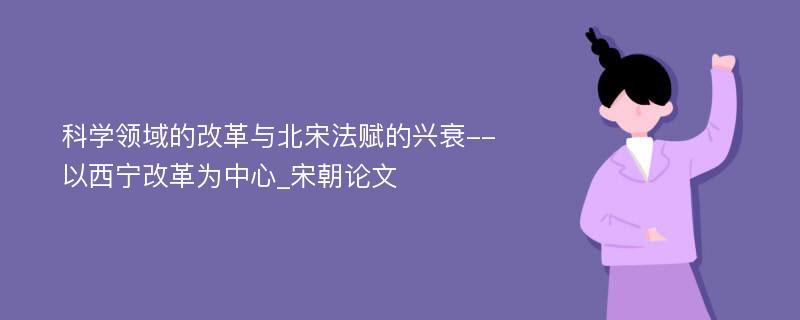
北宋科场改革与律赋沉浮——以熙宁变法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科场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4-0037-09 熙宁四年(1071),宋廷颁布贡举新制,科举只设进士一科,撤销明经等诸科;进士科罢诗赋、贴经、墨义,以经义、策论升降天下士。这一举措影响至为深远,它既是北宋以来,尤其是庆历新政以后科场改革呼声的一个归结点,也是之后围绕科考引发的一系列争论的出发点。在此之前,律赋在与策论的较量中地位就不断下滑。元祐六年(1091),宋廷立诗赋、经义两科,礼部试恢复诗赋取士,绍圣述圣期间,则又回到了熙宁新制上来。那么,宋人为什么要改革科考,律赋在科场地位的沉浮是在怎样的学术环境下发生的呢?如果我们把这一文化现象置于儒学发展的语境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由于儒学深入而持久地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宋人的人才观、文学观均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引发律赋在科场地位动摇的直接诱因。 宋廷于熙宁四年颁布的贡举新制是以罢诗赋而以经义取士为核心的,其学术背景乃是儒家道德至上的人才观,是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政治文化进行改造的一次努力。早在庆历年间,人们就从道德至上的人才观出发对科举表示不满,熙宁变法前后,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希望建立学校,阐扬六艺,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因此,他们对诗赋取士进行了深入反思并表示出相当的愤慨。这种焦虑有力地推动着科场改革。 熙宁四年的贡举新制直接发端于两年前朝臣关于科场改革的争论。当时对于罢诗赋,除苏轼等外,绝大多数朝臣持赞成态度。主事者王安石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指出:“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其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庶几可复古矣。所对明经科欲行废罢,并诸科元额内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①王安石雄心勃勃,希望在取士方面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笃道崇儒,以创立大业。他的设想是先道德而后艺能,通过学校培养士子的学行修养,诗赋拘忌于声病对偶,对于考校道德之高下没有多大益处。他的最终目标是推行学校制度,经义取士只是一种过渡。他的思路是由科场出发,道斯民于至德,洒仁风于四区,使科考取向与治国理念取得一致。 政治主张倾向于保守的吕公著看法和王安石相呼应,他说:“夫上之取士者,将以治事而长民,而所以取之者,乃不过试之以辞章、记诵之学,盖亦乖矣。……故臣窃以谓贡举之弊不可不革,而学校之制所宜渐复。虽进士经学,行之既久,为有司者安于课试之格,为士人者狃于进取之术,可以渐去而未可以遽废。”②取士的目的是临政事而治齐民,而取士的方法是诗赋这样的辞章之学和墨义、括贴这样的记诵之学,方法与目的相去甚远。在吕公著看来,政治之才应该具备一定的德行和经学修养,这样才能习民靖俗,端本抑末。他也和王安石一样,寄希望于学校举士,他主张罢律赋而以与儒典关系密切的经义、策论选士,以后建立学校,也应该以经术教养士子。旧党核心人物司马光则认为九品中正制亦能作到关乎道德举士,而以后的科举则渐渐乖离根本,用诗赋则又等而下之了,儒雅之风日益颓坏、士风日益狂躁险薄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诗赋取士的导向作用③。 可以看出,不管是变法者还是旧党人物,他们在废除诗赋取士、彰显道德方面相当一致,这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有着共同的根基,那便是从韩愈那里传承下来的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儒学思想。他们都主张尽快把贤能政治落到实处,除了以内圣外王之道规范皇权外,更重视砥砺名节,提升士人的道德层次,由此而风化天下,开创太平局面。因此,这个时期的儒学思想提倡道德风范的确立,人才的第一要素是学行修养,政治才能是建立在品德基础上的对儒家典籍的领悟能力,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为学要宗经,选才要考察其对经籍的领会程度。当然,较之司马光等,王安石更偏重于经世致用的才能,不过,他的变法主张虽是针对现实积弊的,但是他往往从对儒家所标榜的“三代”“古者”的想象图景中去寻找变法之道,这次科场变法也是这样。虽然新旧党人及其内部在推崇经籍方面各有差异,但是他们对国家选才的观念大多是立足于融通儒典之上的道德至上、宗经崇道。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若依然采用与经籍联系不太紧密的辞赋来衡才,就显得颇为不伦。熙宁年间的科场罢黜诗赋,正是这种人才观念催生的结果,也是儒学深入渗透社会生活的表征之一。 科场罢诗赋的呼声和儒学复兴几乎是同步的。宋初,人们对科考承袭唐制的合理性并没有表示怀疑。之后,在真宗天禧年间,儒学方兴未艾之际,人们意识到诗赋不近治道,因而希望提高以阐发儒家思想和政治主张为主的策论在科考中的重要性。随着通经致用成为士人的共识,律赋在衡才方面的价值就不断遭到质疑,策论的地位随之日益提升。到了庆历新政前后,变革科场的呼声异常高涨,庆历新政是宋人立足于儒学思想整饬政治的一次努力,其中一个内容就是“精贡举”,范仲淹等人认为科考主六经才是正道,诗赋取士远离圣道,久之将引发祸乱,因此应该先策论而后诗赋,这样可以引导士子不专注于辞藻,而用心于儒家大道。他们认为济世本领蕴含在六经之中,需要士子通过学习揣摩领悟儒家典籍来通晓,而诗赋和墨义却与此无补。这些看法正是由于儒学兴起的学术背景下人才观念的变化,他们认为不能致太平的关键因素是科考把人心导向浮薄之境,因此必须兴学校、崇道德、宗经籍,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延续几百年的考试制度。 先策论而后诗赋是庆历科场新政的重要收获,之前的天圣二年(1024),叶清臣即以策论擢进士高第。可以说当时的科场局面是积势使然。策论从汉代以来就是考试文体,不论是对策、射策还是申论治道,皆立足于治国之理。在宋代,策还被细化为时务策和子史策,旨在阐述儒家治道和国家大政方针,正可考察士子的“经济”抑或政事才能。诗、赋不过工浮词,论、策则可验实学。那么,考察经术才能的经义,其科场地位自然更优于策论,在熙宁变法期间确立经义取士而罢诗赋,正是沿着这种人才观念发展的结果。当然,宋儒看重的才能的根本是“德行”,经术与德行并不是一回事,不过,经术内则修身,通向德行;外则齐家平天下,通向政事,具有贯通道德与政事的功能,修己与成物在经术这里可以统一起来。因此,以经义取士反映了王安石们落实儒家人才观念的苦心孤诣。 其实,北宋时期科场罢黜律赋的思路并非宋人首倡,在唐代,那些固守“河朔”文化传统的人们就依宗经和道德至上以及重视“经济”立论,反对进士科。开元十七年(729)洋州刺史赵匡在《举选议》中提出考试“笺、表、议、论、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不试诗赋”④。唐肃宗时,杨绾的主张则与熙宁年间士大夫的主张更为接近,他在《条奏贡举疏》中说:“望请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策试者,以孝廉为名,荐之于州。……其所习经,取《左传》《公羊》《谷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⑤这一动议还得到古文家贾至等的呼应。唐人的这些论调是从北周以来延续下来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念和人才观念的回响,主张宗经、鄙薄文华风采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北宋时期反对诗赋取士、主张复古者,其立足点与此类似。问题在于,唐代的这股反对诗赋取士的逆流其发端是南北长期的隔离以及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北方一些士人对文华风采的反感,这和隋文帝时反对辞采是一脉相承的,是文化落后的后遗症,而北宋时期则不然,它反映的是儒学在其发展时期对文化发展的规范或者挤压。 王安石改革科考的最终目标是废除科考,以学校制度培养人才,这样可以关照到士人的品行,知人而用,经义取士只是在学校制度建立完善之前的权宜之计。熙宁年间的科场新制,是庆历新政的呼应。王安石的这一设想也得到了旧党人物包括司马光等的认可。 但是建立学校制度毕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作为一种过渡,宋人为什么废诗赋而用经义,却不恢复汉代的征辟荐举制度呢,或者依照唐之旧制,取消糊名、誊录制度,结合士子的“誉望”综合衡才呢?这些举措要比经义取士更能突出德行修养的考量,更符合儒家道德至上的准则。但是欲行征辟荐举或者兼采“誉望”,就必须突破糊名、誊录制度,对此早就有人呼吁过,只是宋初三朝逐步确立、完善起来的糊名、誊录制度作为杜绝官员徇私舞弊的措施,早已载入《三朝宝训》中,是圣朝美政,祖宗家法,难以轻易撼摇。范镇就指出:“世之所谓糊名者,待盗跖可也。以待盗跖之法而欲求颜、闵之人,其为颜、闵者不化为盗跖几希矣。而议者以为糊名不可废。糊名不可废,而欲责士之行谊,难矣哉!臣请择良师而教之于学,以观其素;弛糊名之禁而待之以礼,以养其诚:以谨士之初也。”⑥他认为当下的考试制度完全忽略对士子的道德品行的考量,通过试卷“较艺”,不是鼓励人心向善,而是待盗跖与颜回、闵损一视同仁,这是对有德者的极大不尊重,范镇认为弛糊名之禁而礼贤下士,择良师而教之,这其实就是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所主张的兴学校。 熙宁二年的科场讨论,糊名、誊录颇为人们关注,因为这是道德品行衡才的一大障碍。其实,道德高下是人的境界问题,是难以做出精准的考量的,在这个问题上某几个官员的意见很难有多大的可信度,人们的眼睛所见只能是表象,甚至是印象,以此来考量人才,只能是一种期望,或者成为被主事者“代表”的遁词或者托词。因此征辟荐举、乡评里议,这种办法在东汉后期就已经行不通了,并且直接催生了九品官人之法,也为以后士族门阀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变法者似乎忽视了征辟荐举制度的历史命运,一些人执意要依古制,行古礼。那么这种制度在当时真的行得通吗?刘攽等人担心掌握选举之柄的人道德低下,缺乏识才量才之能,那样会使得整个吏治乌烟瘴气。他认为汉代官人皆贤士,这是推行此制度的保障,而如今已经失去了这一基本条件⑦。司马光等则认为人们的迁徙较之前代更为自由,使得乡里评议失去了基础,而且众人之毁誉也难以尽其实,其结果必然是请托公行,贿赂上流,封弥、誊录制度,是杜绝这种情况的一道屏障⑧。 征辟制度对于当时的儒者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变相的乡里评议在不违背祖制的前提下还是在尝试着。宋廷曾于大观元年(1107)推行与之相类似的“八行取士”,这其实是通过乡举里选的手段推荐入太学学习的名额,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取士”。这“八行”是:“诸士有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其施行的办法是:“诸士有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行见于事状、著于乡里者,耆邻保伍以行实申县,县令佐审察,延入县学,考验不虚,保明申州如令。”⑨不过,“八行取士”最终因为迂阔难行弊端丛生而不了了之。 可见,将儒家的道德至上的人才观贯彻到国家政治生活中,选择罢诗赋而以经义策论取士,是较为便捷和务实的途径。理论上讲,这样可以诱导士人专研经籍以涵养心胸,不尚浮靡以正心诚意,由此返璞归真,淳厚风俗,揖让而四夷服,缓带而天下从,正是走向贤能政治的达途。熙宁年间的济世干才和道德君子可能没有意识到,科举其实是朝廷用高爵厚利引诱天下士子入我彀中的举措,它既是在笼络读书人,以确立其政权的合法性和重申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是为了在对其有利的知识和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统治体系,巩固士绅阶层。可以说,科举是官方和士人的一种交易或者博弈。不管是诗赋抑或经义、策论,最终是要在科场上被工具化的,即使是道德取士,道德也是要被工具化的。因此,道德至上,选贤授能,只是儒家先贤们留给后人的一个美丽的幻梦而已。熙宁变法中的经义取士,注定难以达到关乎治道的初衷。而且,这个制度的颓势来得出乎意料地快,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把由自己组织编定、反映自己经学思想的《三经新义》作为科场的权威读本,经义矮化为阐发王安石新学的工具,“王学”则可以凭借科场的利诱遍行天下,并对其他学术形成打压之势,这是深具忧患意识的士大夫不愿意看到的。本来宋初以来形成的较为宽松的学术思想氛围,已经在因变法而不断加强的集权专制的挤压下岌岌可危,科场改制由重道德而导致“一学术”,则更使得放任的皇权难以控制,以科场新制之名行罢黜百家之实,这恐怕是司马光等道德君子始料未及的。 律赋在科场地位的旁落也与当时的文学风尚密切相关。欧阳修等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基本上与儒学发展保持着同步态势,古文创作在这种背景下日渐繁荣。古文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宋儒在遥接韩愈学术的同时,也继承了他的古文创作传统。他们对韩愈的继承,是在发扬韩愈倡导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构。这就要求突破传统的章句之学的束缚,甚至摆脱儒家元典和经典化了的传注的束缚,开拓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以便依己意揣摩圣人奥旨,疑传惑经,经世致用,重构儒学体系,开太平之基。因此,古文自由表达的优势被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文学观念也因此悄然发生变化。诗文革新运动是对重构儒学体系的回应,也是对儒学影响下的士风转变的回应。于是,经世致用、激励士风、流畅自然、富于深思,就构成了文学创作的核心元素。文学观念的这些转变,自然会在科场上有所体现,而整齐密丽的律赋,则与这种文学风尚颇为龃龉,尤其是它日益繁琐苛刻的形式方面的要求,更加剧了其与主流文学创作的距离。熙宁变法是一场具有儒家实用主义色彩的变法运动,罢诗赋取士折射出已经成为主流文学观念的儒家文道观对科场衡文标准的强烈不满和积极干预。 推动儒学复兴的主力之一是一批具有隐士气质或者隐居经历的在野人士,如柳开、石介、穆修等。与其呼应的是范仲淹、欧阳修以及后来的王安石、苏轼等士大夫。这些在野人士有着与科考出身的士大夫对比鲜明的文化色彩。他们不同于那种高蹈尘外的岩穴处士,更不同于通过追求雅致情趣以强调自己身份地位的士大夫,他们是一群捍卫道统、抱道而居的偏执的保守主义者。正是他们,架起了连接韩愈以及中唐古文与当时学术文化的桥梁。他们与积极进取的士大夫们同气相求,促进了儒学的深入发展,也推动着文学由宋初的闲逸淡雅格调向张扬忧患意识的革新道路迈进。庆历年间,这批在野人士的一些人进入太学担任教职,有些人甚至很早就在民间课徒讲学。他们的学术主张通过这种较为直接的方式对科场施加着影响。宋初以来,科场不断向关乎治道的方向发展,与他们的孜孜以求不无关系。欧阳修等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则在主流文学层面呼应着科场的这种潜移默化。因而,当具有浓厚儒家保守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和追求自由表达的文风追求逐渐成为主流观念的时候,律赋辞藻华赡的审美品格就越来越不合时宜。而科场的墨义、括帖因其只考察记诵经传的死功夫,有悖于当时自由议论的风尚而遭嫌弃。律赋在这种学风文风的影响下虽然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命题范围由子史而趋向儒典,句式由以四六句为主变而为三言、七言、九言、十一言,句式不断加长,行文更为灵动,文辞更为质朴典重,等等,但还是跟不上时代学术的步伐。 不论当时还是以后,人们多喜欢用“险怪”来评价当时的科场文风,甚或以此来指陈推动这种文风的太学、书院的诸先生——那些在野人士的文风和人格。怪,指的是其思想或风范不合主流;险,则是一种审美感受,指的是其思维或行为执拗偏激,具有一定的感觉冲击力。这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在儒学影响下的士风和文风与宋初的尚雅的主流风尚之间的轩轾。这些“险怪”人士认为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风日滋,骈体文风,以及科场上尊崇律赋,对古文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是弘扬古道的威胁。他们对这种文风强烈不满,猛烈抨击。其实在弘道过程中他们所遇到的阻力微乎其微,他们以一种近乎夸张的亢奋来声讨圣道不行的末世,并且对科场文风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穆修就说:“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⑩认为科场试诗赋是古道流行的主要障碍,古文应该占领这片领域,以便弘扬圣道。这些在野人士对律赋的憎恶,除了弘道外,是否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很值得深思。因为这些人多是出身社会文化的边缘,科考又非其强项,他们不甘心作真正的处士,不甘于被边缘化,而是意欲有所作为,因此,他们对当时文风世风的抨击似乎含有个人不遇的压抑感,而非仅仅是出于接续圣人薪火的冲动。 经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科场文风终于发生了转变,庆历六年(1046)张方平所上奏疏《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指出:“自景祜元年,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后进传效,因是以习。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故下诏书,丁宁诫励,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贡院考试,诸进士太学新体,间复有之。其赋至八百字已上,而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论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者。”(11)这则文献清晰地展示了科场险怪文风与石介等人的关联,以及文风的转变引起的士大夫阶层的不快。科场文风追求新意、妄肆胸臆,这与儒学的疑经惑传风气相一致,而律赋等时文句式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则是模仿古文使然。需要指出的是,以欧阳修为中坚力量的诗文革新运动并不是完全承接这股强劲的儒学和古文的复兴思潮,而是既吸收士大夫主流文化,又融贯经世致用的淑世精神和流畅表达的古文风范,兼采众长,美善并重。因此,诗文革新运动与儒学复兴的展开并不一直都是和谐的。欧阳修对那些险怪的儒者掀起的科场新风——主要是时文的空谈心性和故作艰深的“太学体”文风,从来就不是太感兴趣。嘉祐二年(1057)的科场风潮就是这种冲突的结果。 文学观念向着文以载道和自由表达的方向发展,而科场律赋的发展方向却与之乖离。首先,和唐律相比,宋律的命题逐步限定在《九经》、子、史范围内,使得士子骋才的空间越来越小;其次,限韵越来越严格,唐代律赋,韵数多寡、平仄次序,没有定格,宋律不仅恪守八韵,而且遵守题目给定的用韵次序,平仄次第用韵;第三,宋代律赋的用韵限定于《礼部韵》。宋代科考严格恪守这些规矩,一旦“不考式”,即遭黜落。在这些规矩的拘束下,宋律形成了一整套极其繁琐的写作程式,这严重制约了士子心胸学力的展现,变成了在细枝末节上较艺的文字游戏。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学如戴着枷锁跳舞,限制越严,越能自由驰骋,越能展现作者的才华。其实这是把规矩的作用绝对化了。凡事有个限度,形式方面的规矩太多太繁琐,就会扼杀作品的生命力。李调元《赋话》云:“宋初人之律赋最夥者,田、王、文、范、欧阳五公。黄州一往清泚,而谏议较琢炼,文正游行自得,而潞公尤谨严,欧公佳处乃似笺表中语,难免于陈无己以古为俳之诮。故论宋朝律赋,当以表圣、宽夫为正则,元之希文次之,永叔而降,皆横骛别趋,而俪唐人规矩者矣。”(12)宋代律赋远离唐人法度,主要原因就是命题范围、形式规矩方面的限制使然。由于律赋的拘忌太多,一些有识之士曾希望通过提倡唐律的传统来补救。范仲淹的《赋林衡鉴》多选唐代律赋,希望律赋具有格乎雅颂、达乎韶夏的功能。欧阳修等看到宋律已经严重阻碍了士子才华的展示,因此希望恢复唐律的传统,以救时弊(13)。司马光看待律赋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元祐年间关于恢复诗赋取士的讨论中曾说:“至于以赋诗、论策试进士,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摘其落韵,失平侧,偏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虽顽如跖、硚,苟程试合格,不废高第;行如渊、骞,程试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举人专尚辞华,不根道德,涉猎钞节,怀挟剿袭,以取科名。”(14)认为律赋拘忌太多,一些道德低下巧于钻营的人或可因此侥幸得中,这不利于选拔人才。 在熙宁二年(1069)的科场讨论中,人们对律赋的不满除了它不能对士人的德行和“经济”进行衡量外,还在于它的拘忌过多,即使它已经和儒家典籍以及思想很亲近了,但是因其表达能力的限制而难以承担载道的重任。司马光虽然与那些偏执的儒学君子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作为一个务实的历史学家和谨慎的政治家,他也看重文学的实用功能,推崇流畅自然的古文风范。在文道关系之外,他引入了“辞”这个概念,把律赋,或者一切与治道裨益不大的、重视辞采的文字,统统纳入“辞”的范畴而排斥在“文”之外,他以为,承载六经之道的是文而不是辞。若将文与辞混同,则庄、列、杨、墨等异端之言,其华藻宏辩的程度甚至比经典文章有过之而无不及,足以泆目荡心,动摇正统意识形态学说的尊尚地位。因此,他也主张罢诗赋取士。其实,随着儒学的复兴发展,律赋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也在下降,许多人明确表示它只是科场工具,一旦取得科名,就甚少留意了。宋初文人的集子中收律赋较多,以后则越来越少。而且即使是作赋高手,也表现出对律赋的不屑和无奈。 文源于经,文以载道,这种观念逐渐成了知识界的主流认识,这就是熙宁年间律赋被逐出科场的思想环境。可以说,王安石的科场新制是实用主义文学观的胜利,但是这种文学观并没有牢笼一个时代,更没有取得独尊地位,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还是给文学留下了充分的展示空间。而且,其在变法期间表现出的专制主义倾向并没有得到彻底贯彻,这为苏轼等比较通脱的科考衡才观念的表达留下了一定的余地。 支撑罢诗赋取士的基础是实用主义文学观和通经致用的人才观。政治才干除读书明理外,主要依靠实际工作的磨炼。读书不仅仅是学习政治才能,更主要的是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眼界、胸襟。广博的知识是造就高远的见识、开阔的胸襟的基础。经义取士真的能担当起这样的选才重任吗? 熙宁年间的科考新制并没有按照新政的设计者预想的方向发展,由于利禄的巨大诱惑,人们很快就找到了对付这种考试的办法(15)。科场制度的设计者们忽略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科场代表着富贵利达,已经成为学优则仕的驱动力,甚至士人的心灵因此而改造,科场的任何变动,哪怕是极细微的,都会牵动整个社会的神经,它吸引的社会和知识的资源是相当庞大的,因此,当朝廷经义取士后,也引发了针对它的钻营活动,各种编类、义题、传集、海语,纷纷编辑出来,通过引导士子研读儒典以期修道德、通经济的初衷因而大打折扣,改变俗学之弊的目标迷失了。 在北宋末期,面对与金人战事的屡屡失利,科场得人与否面临着直接的考验,经义取士的弊端全面显露。欧阳澈沉痛地指出:“至于以经义取高第而享爵禄者,反视国家之难,如越人视秦人肥瘠而不加喜戚于其中。甚者差以运漕,尚且畏惮而不前,规规为全身计,况肯当锋镝以立忠谊耶?臣以是知丑虏为害而未能风驱电扫者,虽本于脂韦辈不足以立大事,抑亦经义科非所以得豪杰之才故也。臣观祖宗朝以诗赋而取士,则士无一经之专,贯综坟典,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览,往古之存亡、用兵之得失、行事之成败,虽梦寐亦能记录。况其醖藉瑰伟,则英风锐气无施不可。”(16)经义取士的目的之一就是选择道德高尚的人才,结果这些人才在大敌当前之际的表现甚至连一介匹夫都不如,而诗赋进士之人的表现则还有一定的英风锐气。因此欧阳澈不得不反思经义取士的种种弊端及其根源:“臣尝求中程式之文而读之,其间未必皆无病也,或昧于古今而以汉为唐者,或不通经旨而误引证者,或全录前辈时文者,或使故事而误其姓名者,或以神祖而为祖考者,缀缉不根之语而不答所问者,色色有之。”(17)从中选的经义来看,居然有的文章昧于古今而以汉为唐,不通经旨而引证乖谬,甚至抄袭往届的时文,典故讹误,游谈无根。新政人物本来是想以此来突出道德选才的导向,结果却恰恰相反:“致有士人指考官受赂之污,摘举子谬中之失,而讼于有司,则上下互相掩覆,不为体究。故与其选者,人不以为荣。或素不知经而识字有数者有之,或能诵时文而不知经史者有之,或尘垢龌蹉而言语无味者有之,或屠沽博奕辈而误墨成蝇者有之。此皆缘贿赂不公,考较无术故也。”(18)不通经籍居然可以中经义之选,斗筲之人投机专营,苞苴公行,争讼不已,可谓斯文扫地。而且,这些公然专营的行为有常态化的趋势:“故凡士人将就试,则预采时文脍炙人口者,以经意分排门类,每一门撰义数道,俟其入场,即以所问之题而参合辞意相类者,依本誊录,谓之迎题。或预料有司所问之题,而撰成全篇,至有五篇皆备,略不措意者。况比革科以来,每一义题,两学前后传写,不啻数十篇者有之。其辞意不出乎此,有识之士,不欲袭蹈其迹,或穿凿而为曲说,后进无识者或全录而不更一字,有司亦不能悉究。至于糊名一判,则滥进者悉皆与榜,信乎经义不足以得人也。”(19)由于经义的范围比较小,士子完全可能在考前有所准备,或押题,或准备程文以套作,这就使得考试失去了意义。其实经义取士很容易导致“一学术”,即使不用像王安石那样通过朝廷来确立某一学问的科场权威地位,在具体的考试当中,面对经传的种种分歧,士子们也不得不揣摩有司或者朝廷的学术倾向而有所选择,因而,学术上走向专制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在巨大的利诱面前,士子们养成趋奉揣摩上峰心理的巧佞人格就在所难免。 在熙宁年间的科场讨论中,明确反对罢诗赋的是苏轼。他在熙宁四年奏上的《议学校贡举状》中力主诗赋取士,反对过分突出德行的考量:“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于此乎!”他指出科场重视德行的后果只能是煽动天下伪饰德行以博时誉。他认为从唐到宋,诗赋得人多矣,没有必要改弦更张。而明经科的考试则弊端丛生,经义取士可能重蹈其覆辙:“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20)以后的科场实践被苏轼不幸而言中,他以崇正学术作为科场发展的方向,反对杂以佛老的性命之学,这实际上是针对新学的,他或许已经感觉到王安石意欲借科场改制来推行思想专制的用意。元祐年间李常的《乞经义诗赋各设一科奏》是针对苏轼的这篇奏章的反驳,他认为那些通过诗赋进士的官员,也是因为有着深厚的儒家思想修养,才成为能臣,这并不能改变诗赋劝人是名教之罪人事实。他危言耸听地预言,诗赋取士可能导致唐末五代动荡局面的出现:“此臣等所以虑道术日衰以就废绝,将复如唐末、五代时,学子志识浅陋,此有志之士每多太息而流涕也。”(21)像李常这样言辞激烈地反对诗赋取士的,在当时是少数。朝臣们普遍倾向于诗赋与经义并用的折中方式,他们认为这样既照顾到诗赋的学殖修养,又兼顾儒家通经致用的选才根本。 元祐更化期间,诗赋部分地恢复了科场的地位,这让苏轼倍感欣慰,他作了一首《复改科赋》赞美其事,他认为诗赋取士的优势在于其可操作性强,而经义则无有定准:“探经义之渊源,是非纷若;考辞章之声律,去取昭然。”他推导辞赋之源曰:“原夫诗之作也,始于虞舜之朝;赋之兴也,本自两京之世。迤逦陈、齐之代,绵邈隋、唐之裔。故遒人徇路,为察治之本;历代用之,为取士之制。追古不易,高风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号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胜其弊。谓专门足以造圣域,谓变古足以为大儒,事吟哦者为童子,为雕篆者非壮夫。”这就为律赋嫁接上关乎治道的高贵血统,借以弥补律赋相对于经义的先天不足。他还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噫,昔元丰之《新经》未颁,临川之《字说》不作。止戈为武兮,曾试于京国。通天为王兮,必舒于禁龠。孰不能成始成终,谁不道或详或略。……三舍既兴,贿赂公行于庠序;一年为限,孤寒半老于山林。自是愤愧者莫不颦眉,公正者为之切齿。”(22)在这篇赋中,苏轼没有触及宋代律赋的局限,而只是出于攻击新法的目的,对诗赋和经义过毁过誉。 就目前所见文献来看,对科场取士看法比较理性的是毕仲游《理会科场奏状》。他认为在选才方面,诗赋明显优于经义,经义作为谋道之具,不具备衡才的功能,读经必须通过长时间甚至一生的揣摩历练,来造就耆儒硕老。可是以此来选才,则不切实际。他指出圣人之经术成为博取利禄之具,这不是对儒道的崇奉,而是亵渎。因此,他主张根据诗赋、经义的不同特征采取不同的选才办法:“然则专复诗赋以取士,设嘉祐明经之科以待不能为诗赋之人,而又诏天下求穷经谋道、不累科举者,使传道于诸生,则政有并举,才无或弃,亦可以释民疑矣。”(23)他注意到了科场取士的工具性特征,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经义取士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这也许是一种制度在建立之初难以避免的现象。元祐年间的诗赋经义取士政策还没有完全办理妥当之时,哲宗绍圣述圣,便又恢复了专以经义取士的政策。这一次,王安石的新学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经义取士所滋生的科场痼疾,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变本加厉地严重起来,其结果是造成了两宋之际人才素质的全面下滑。纵观诗赋经义取士之争,其背后是儒家保守主义与人们的习惯观念在人才观、文学观方面的较量,是儒家思想深入社会生活的深刻反映。熙宁科举新制,在制度上确立了儒家中心主义的科场文化环境,对以后的科举影响至为深远,经义在不断完善中演化出八股文,律赋也逐渐凝固为八韵,成为八股文的又一重要源头。 收稿日期:2014-12-27 注释: ①《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3页。 ②吕公著:《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奏》,《全宋文》第50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③参司马光《议学校贡举状》,《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三册,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552页。 ④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22页。 ⑤《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杨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31-3432页。 ⑥范镇:《议取士状》,《金宋文》第40册,第224页。 ⑦参看刘攽《贡举议》,《彭城集》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8-339页。 ⑧参看司马光《议学校贡举状》,《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三册,第556-557页。 ⑨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5页。 ⑩穆修:《答乔适书》,《河南穆公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1页。 (11)张方平:《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乐全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第184页。 (12)李调元:《赋话·新话》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7页。 (13)毕沅等:《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六,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96-597页。 (14)司马光:《起请科场札子》,《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15)参看李复《论取士奏》,《全宋文》第121册,第378页。 (16)欧阳澈:《上皇帝第三书》,《全宋文》第182册,第378页。 (17)欧阳澈:《上皇帝第三书》,《全宋文》第182册,第381页。 (18)欧阳澈:《上皇帝第三书》,《全宋文》第182册,第380页。 (19)欧阳澈:《上皇帝第三书》,《全宋文》第182册,第381页。 (20)《苏轼文集编年笺注》第三册,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622页。 (21)李常:《乞经义诗赋各设一科奏·一》,《全宋文》第72册,第244页。 (22)《全宋文》第85册,第160-161页。 (23)《全宋文》第110册,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