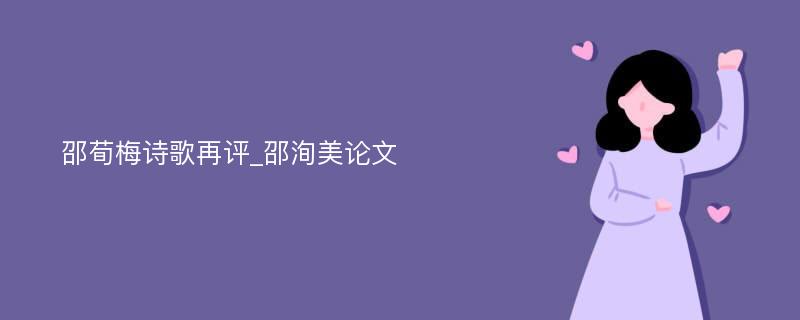
邵洵美诗的再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价论文,邵洵美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6)01—0034—04
邵洵美(1906—1968)1923年赴英留学,后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继而去法国巴黎,与徐悲鸿等同习绘画,1926年回国,1927年与表妹盛佩玉结婚。1920年左右开始诗创作,著有诗集《天堂与五月》(1927)、《花一般的罪恶》(1928)、《诗二十五首》(1936)等。
邵颇富有,乐于助人。诗的路数不同于徐志摩,但他是徐志摩的崇拜者。他在《诗二十五首·自序》[1] 中, 较为全面地谈及了自己的诗创作所受到的国内外诗家的影响和自己创作道路的变迁。他认为,新诗早期,胡适之等“他们的成就是文化上的;在文学上,他们不过尽了提示的责任”,“到徐志摩手里,才有一些眉目”。闻一多、柳无忌、朱湘“偏重在形式方面”。“孙大雨是从外国带了另一种新技巧来的人,他透彻,明显,所以效力大;《自己的写照》在《诗刊》登载出来以后,一时便来了许多青年诗人的仿制。不久戴望舒又有他巧妙的表现,立刻成了一种风气”;“孙大雨在技巧以外还有他雄朴的气概,戴望舒在技巧以外还有他深致的情绪,摹仿他们的人于是始终望尘莫及”,“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韵节,每一个时代又总有一种新诗去表现这种新的韵节。而表现这种新的韵节便是孙大雨、卞之琳等最大的成就。前者捉住了机械文明的复杂,后者看透了精神文化的寂寞:他们确定了每一个字的颜色与分量,他们发表了每一个句断的时间与距离。他们把这一个时代的相貌与声音收在诗里,同时又有活泼的生命去跟着宇宙一同滋长”。
在这里,邵洵美多少怀有用现代主义衡量中国新诗的偏颇。除徐志摩外,对闻一多评价过低,郭沫若的《女神》,更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他说从中“感觉到一种新的力量在蠕动,但是嫌他们的草率与散漫”),然而邵对新诗的形式和技巧的看法,不失为一家之言。
他自己的诗创作,起于“旧体诗翻译外国诗失败”和“常读旧式方言小说而得到了白话的启示”。但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外国诗,古希腊女诗人莎茀(Sappho,今通译萨福)以及史文朋、先拉飞派、波特莱尔、魏尔仑,都曾使他心折。据说徐志摩曾对人讲“中国有个新诗人,是一百分的凡尔仑(Paul Verlaine,通译魏尔仑,邵洵美《火与肉》中译为万蕾)”,指的就是邵洵美。邵氏自己坦承:最初是模仿,接着是追求词藻的华丽,第三段是“声调的沉醉”,1930年以前的诗,“大都是雕琢得最精致的东西”。他始终相信柯勒立治的名言:“诗是最好的字眼在最好的秩序里。”他重视“字句的排列与音韵的布置”,重视“分行与音尺”,反对平仄的束缚。“‘少壮的炫耀’,写了《洵美的梦》便尽竭了。同时我便在‘肌理’上用功夫。”这里所说的“肌理”,不是指翁方纲所倡导的以儒家经典学问入诗,而是指重视以象征主义的“义理”、“文理”入诗。但实际上仍在形式上着力,追求“形式的完美”。他认为,“在词藻上,在韵节上,在意象上,我要求能得到互相贯通的效果”。相对而言,他后来比较重视象征意象。他认为,由于“形容和譬喻是暂时的象征,象征则是永久的形容和譬喻;而凡是伟大的诗都有一种永久的象征性”。所以,诗有“曲折性”,不可能很“明显”。
邵洵美早期的诗,取材广泛。《天堂》写了天堂、人间,阴谋、暴虐的上帝,易被诈骗、诱引的奴隶,为了真爱而被罗织罪名的青年男女,罪恶的天堂,那是人间的地狱,是作品给读者的第一印象。《花姊姊》长达300多行, 实则只是表现了人生如进屠宰场的牛羊,死如一只蚂蚁;人与人之间只是杀与被杀。但诗人解不开人生的谜,企图从人性善恶抑或环境逼使找原因:他们“为了怕自己死,所以恨别人生”,最终停留在非常皮相、非常一般的层面——“自私”上。
作者的第一个诗集,在长诗艺术上几乎一无可取。《花姊姊》中重复写战场上“杀”、“死”各达百行。这里只引写“死”的一段,读者可借此一斑而窥全豹:
死死死!/你死,/他死,/我死,/死死死!
死死死!/你半死,/他半死,/我半死,/死死死!
死死死!/你也死,/他也死,/我也死,/死死死!
一个死,/两个死,/五个死,/十个死,/死死死!
死死死!/五十个死,/一百个死,/一千个死,/一万个死,/死死死!
死死死!/几万个死,/多多少少个死,/死死死!
重复堆砌的赞美,在新诗中,恐少有超过它的。短诗则大多有点诗意,如《头发》描写颇出色:
啊这北极雪山般白的颊上,
漂来一层淡红芍药色的轻浪;
那眼球眉梢及发髻,
又像水獭休息在岸旁。
线条、着色不失画家的本色。诗的最后一节,引人遐思:
啊情人的头发吓,
在情人心中打着结;
情人在这最短最快的时光吓,
分分秒秒只是去解这无穷的结吧。
可理解为,情人的头发有千千结,等待爱人去解开;或者是在相聚的不长时间里,爱人欣赏她的情意。短诗不似长诗明说,比喻也不是明喻。
《爱》共四节,每节四行,后二行四节一样,第四节写道:
海水叫月月不语,
浪儿化作点点泪;
这便是爱,
这便是爱的滋味。
是明喻又不似明喻,前二行形容爱的深,如海,爱的滋味无边。邵氏有些短诗是由一个比喻构成,如《恋歌》,第一节用天池和云荷的关系,比喻“我”和意中人的关系,略嫌单薄。
在《天堂与五月》中,有两个趋向已明显呈现。其一是格律化。《五月》编中的19首诗,都有格律可循,形体整齐。这是向新月诗派靠拢的明显标志;二是在法国波特莱尔等象征派影响下,向颓废肉感方向迈步,这是邵洵美诗被人诟病的主要原因。其实,他的诗并未流于淫,如《春》、《夏》、《颓加荡的爱》,可算是典型。
啊这时的花香总带着肉气,
不说话的雨丝也含着淫意;
沐浴恨见自己的罪的肌肤,
啊身上的绯红怎能擦掉去?
——《春》
纯白的月光调淡了深蓝色的天色,
热闷的喊叫都硬关住在喉咙里;
啊快将你情话一般温柔的舌儿,
来塞满了我这好像不透气的嘴。
——《夏》
两首诗都将大自然人性化或者说“两性化”。前一首把春当作多情的妇人来比喻、象征。花香、雨丝,正是春的表征,但在春雨连绵之后,春仍然着多种颜色,红花依然在,春的皮肤上仍有绯红。此前的诗人大多把春比作美丽的姑娘,而邵洵美却把它绘成有点淫意的妇人。这是它的新奇处,也是它的独特处。后一首深蓝天色和闷热、透不过气来,点明了夏的特征,后两行与《春》写法一样,把夏两性化了。这两首诗,有淡淡的肉感化,但还不是“黄”和“淫”品。
《五月》写在“欲情的五月”,“我”保持着冷静和清醒,感觉到生与死,极端的快乐与惶恐,对立的东西可以转化,所以不想跨进天堂,因为地狱、短夜已给了他足够的体验。
《颓加荡的爱》从一个方面表现了邵洵美诗中爱情的特征。他写的男女关系,总带有几分“颓加荡”,诗这样写“天床上的白云”:
啊和这一朵交合了,
又去和那一朵缠绵地厮混;
在这音韵的色彩里,
便如此吓消灭了他的灵魂。
在道德的层面上,诗人没有表露明显的谴责,但作者并没肯定、歌颂这种现象。从诗的最后两行中,可以觉察诗人惋惜的心情:在这多种“音韵的色彩里”,“消灭了他的灵魂”,言外之意,是太可惜。
我觉得对这一类诗,不能用中国传统的观念,不能用儒家的诗教去衡量,首先应该从世界文学中类似的现象作比较。如波特莱尔被某些人认为是“淫诗”的《恶之花》中的少数诗,和惠特曼《草叶集》中的个别篇章尽情地描写性、男女肌体及生殖器,歌颂性、性交和宇宙、大自然的一致性,裸露、任性、自由、解放、解脱、纵情、狂欢。我想只要看过《恶之花》中的《首饰》、《忘川》、《致大喜过望的少妇》、《累斯博斯》、《入地狱的女子》、《吸血鬼的化身》,和惠特曼《草叶集》中的《亚当的子孙》的人,都会有同感。这里引惠特曼仅四行的短诗《处女膜哟!有处女膜的人哟!》:
处女膜哟!有处女膜的人哟!你为何这样逗弄我?
啊!为什么只能给我一瞬间的刺激?
你为什么不能持续下去?啊!你为什么现在停止?
难道如果你超过了那一瞬间,你就一定会把我杀死?
这里,纯粹是写性爱,但是读者必须将它置于组诗和诗集的整体中去感悟,才能取得真谛。而邵洵美把宇宙、世界和各种关系两性化,大半也是作者认为两性关系较单纯,而且正如闻一多在奈尔孙的影响下所说:“严格地讲来,只有男女间恋爱底情感是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2] 1919年,鲁迅就说过:“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性欲和食欲一样,是人的本能,“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3]
《花一般的罪恶》中的《序曲》为我们读懂邵洵美的诗,提供了“导读”:
我也知道了,天地间什么都有个结束;
最后,树叶的欠伸也破了林中的寂寞。
原是和死一同睡着的;但这须臾的醒,
莫非是色的诱惑,声的怂恿,动的罪恶?
这些摧残的命运,汙浊的堕落的灵魂,
像是遗弃的尸骸乱铺在凄凉的地心;
将来溺沉在海洋里给鱼虫去咀嚼吧,
啊,不如当柴炭去燃烧那冰冷的人生。
在诗人看来,他所抒写的,这些“色的诱惑,声的怂恿,动的罪恶”,也是宇宙“须臾的醒”的短暂表现;在冰冷的人生中,不失为一刹那的火,即一瞬间生命的火;它是美丽的,但却是“花一般的罪恶”。
在《火与肉》的《贱窟与圣庙之间的圣徒》中,邵洵美承认自己欣赏享乐派的生活,赞美享乐派是“真的生活,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生活”。这种生活态度,在他诗中也有反映。从诗人的创作道路着眼,《花一般的罪恶》[2] 是预备前行的踌躇,迈开了这一步,作者再也不想收回脚步。
《诗二十五首》果然有新姿态。结束了此前“少壮的炫耀”的写法,采用较深且复杂丰富的现代主义方法。《洵美的梦》、以后的大多数诗如《声音》、《Undisputed Faith》、《牡丹》、《永远想不到的诗句》、《风吹来的声音》、《绿逃去了芭蕉》、《蛇》、《二百年的老树》等各有特色。它们中又可分几种类型。《洵美的梦》、《希望》等更多的由前期常使用明喻改为象征。意象趋于繁密化,曲折多义,往往用多个排比句或补充句暗示抒写对象。如《声音》开始写“声音”传达的不可靠,接着写道:
这时候,我说,要是有酒,酒会
使我交出一篇料不到的供状;
虽也许只是一首背熟的诗,
一个想熟的字,一张看熟的画,
可是他们他们都会像箭头瞄准了箭靶。……
事情就会闹大,眼泪会像雨,
情感会像风,自己会没有主张。
10行诗(包括未抄的两行)中,有4行7个排比句,诗中有汉语的明显特点。这首诗所写的“声音”,是幸福的使者,抑或是灾害的化身,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灵魂和肉体“各自说出各自不敢说的话”,忧愁、爱各有自己的声音;这声音不管是平凡还是奇迹,但世界少不了你;没有了你,多少事会成哑迹;而你——声音——在人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你不管怎样,如果在梦中,一个声音呼唤着你的名字的话,表明声音在靠近你。声音,是现实世界之外的一个世界,但它有神奇的魅力,像是耶稣,像是上帝。有时用有联系的两个意象,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如:
因为她能唱,唱到夜莺变哑巴;
因为她有一双看不远的眼睛
会看得孔雀羞惭地把彩屏收起。
其次,诗人在一定程度上在《春》、《夏》的诗路上前行,如《牡丹》、《我不敢上天》、《风吹来的声音》、《蛇》都是明证。《牡丹》写道:
牡丹也是会死的
但是她那童贞般的红,
淫妇般的摇动
尽够你我白日里去发疯,
黑夜里去做梦
少的是香气;
虽然她亦曾在诗句里加进些甜味,
在眼泪里和入些诈欺,
但是我总忘不了那潮润的肉,
那透红的皮,
那紧挤出来的醉意。
这专写牡丹的另一面,不长久的一面,她使人“发疯”,“做梦”;她没有香味,但一切那么逼真,那么诱人。诗写尽了牡丹——一种人的一面。《蛇》是邵洵美诗中颇受争议的一首。这里只引前二节作一点分析:
在宫殿的阶下。在宙宇的瓦上,
在垂下你最柔嫩的一段——
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裤带
在等待着男性的颤抖的勇敢。
我不懂你血红的叉分的舌尖
要刺痛我那一边的嘴唇
他们都准备着了,准备着
这同一个时辰里双倍的欢欣!
第三节写蛇的皮肤的油滑,是磨光了竹节的结果,此中有“舒服”,有“伤痛”,有冷又有热。第四节希望蛇再把剩下的一段,“来箍紧我箍不紧的身体”,到明天早晨,我将感到温暖,如同盖着稀薄的绣被。诗始终从蛇的可怕与女性诱人的矛盾特征中着笔:一方面写尽了蛇的多情与肉感;另一方面,又真实地表现了蛇的可怕,舌刺人,皮冰冷,身箍人,意象生动可感。与冯至同题诗比较,冯诗更雅,邵诗则俗,但都不失为诗美中的一个品种。都介于“似与不似之间”,既有蛇的特征和一般人对蛇的感觉,又有女性的特征(邵诗中的女性特征多了点“颓加荡”)。
对于邵洵美的诗,有关诗学和技艺上的问题并非关键,最有争议的是他诗中的“颓加荡”的因素、成分或者说色彩,是否可以作为评价邵洵美诗“一票否定”。我认为,第一,外国19世纪诗史上有过之无不及的同类的错案(《草叶集》和《恶之花》)早已改正了,我们在20、21世纪不应制造新的错案。第二,邵洵美的诗最成问题的,并非已流于“淫”。他主要是吸收法国诗的乳汁,贯穿“颓加荡”的特色,从而使自己的诗另成一格。第三,他并非全盘肯定这种“颓加荡”。他作为接受魏尔仑影响最大的诗人,作为在诗艺上有特色、艺术上较圆熟的诗人,中国新诗史是不应将他排除在外或仅仅是作为批判对象出现的诗人。
收稿日期:2005—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