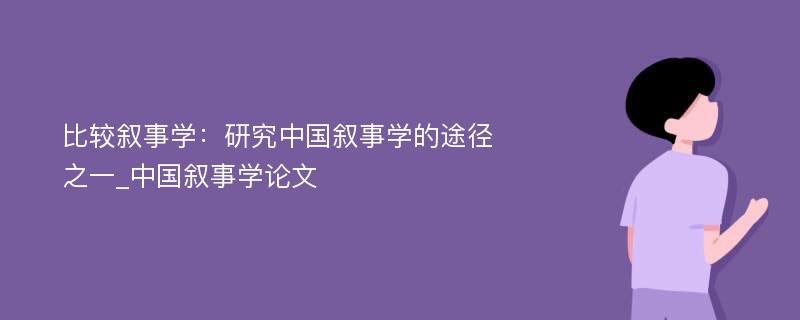
比较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之一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3-0035-06
叙事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结构主义浪潮首先在法国兴起,随后流行于欧美,并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学术领域,在中国文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不仅势头不减,而且与国际叙事学界以及国际叙事学研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2007年10月与2009年10月,在江西南昌和重庆分别召开了第一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第二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来自美国、德国、挪威等国的叙事学家分别参加了这两次国际会议。2011年10月,将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叙事学会议同样是一次国际暨全国性的会议。与此同时,少数有影响的中国学者也进入了国际叙事学研究的主流领域,发表了质量上乘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叙事学界的注意。
然而,总体上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叙事学研究中的声音还有些不足,这种现象已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近年来,在叙事学的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有关“中国叙事学”的问题展开了探讨,对中国学者如何在国际叙事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如何在叙事学这一具有广泛国际性的学科与学术研究中彰显出中国学者的研究优势,如何运用和发掘中国丰富的叙事作品和叙事理论的资源,如何从整体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进一步展开与国际叙事学界的交流,让国外的学者们更多地听到来自中国叙事学界的声音等展开了讨论。人们希望随着叙事学研究的不断加深,能够出现具有中国自身意义上的、可以在国际叙事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叙事学研究。
这种看法表现出中国叙事学者对促进国内外叙事学发展的热望以及对自身叙事学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叙事学的发展来说,从当代叙事学兴起以来,已经经历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阶段①,形成一个融合各国学者的研究、广具国际性的源源不断的叙事学之流。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人们不难辨识出各国学者为叙事学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一些有影响的成果。比如,法国学者托多罗夫、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布雷蒙等人对经典叙事学所作的贡献,他们所“创立的叙事学是整个结构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他们遵循索绪尔对‘语言’(la langue=视为系统的语言)与‘言语’(la parole=在语言系统基础上进行的个别的言说)的区分,把具体的故事看作由某种共同符号系统支持的具体叙事信息。”[1](P4)法国学者的努力,为当代叙事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后,荷兰学者米克·巴尔,美国学者普林斯、查特曼,以色列学者里蒙-凯南等人以他们的研究对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与完善作出了贡献。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外叙事学的中心自法国向美国转移,形成了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出现了一批如詹姆斯·费伦、戴维·赫尔曼、彼特J.拉比诺维奇、希利斯·米勒、苏珊·S.兰瑟等叙事学家,他们的研究使美国学者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叙事学界举足轻重。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中,人们也仍可看到各国学者所作的各有特色的研究,并形成后经典叙事学的不同分支。比如,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所提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荷兰学者米克·巴尔所进行的叙事学的文化分析研究,德国与奥地利学者如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安斯加·纽宁等所展开的文化与历史叙事学研究,美国学者彼得·布鲁克斯、罗斯·钱伯斯所进行的精神心理叙事学,多瑞特·科恩所进行的历史图像叙事学研究等。至于在叙事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就是经典叙事学之前的所谓“叙事学研究的‘古代’阶段”,各国学者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德国的形态学方法等对叙事学的影响也清晰可辨。
应该说,近20余年来,中国学者在叙事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对来自国外的这一理论,我们经历了翻译、介绍、吸取、消化、运用的过程,并且越来越意识到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分析上下工夫。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国外引入的各种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可以说很少有像叙事学这样,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并一直有学者热衷于它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同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的。与此同时,在叙事学研究的视野下,中国学者也逐渐注意对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加以梳理和总结,并以叙事学理论作为参照相互融会贯通、求同辨异,以沟通中外叙事理论,促进叙事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工作,杨义1997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可以作为其中的代表。杨义认为:“有必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地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研究其本质特征,并以西方理论作为参照,进行切切实实而又生机勃勃的中国与世界的对话。”[2](P1)赵炎秋也在1998年提出应重视对于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研究,目的之一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叙事理论。“西方叙事理论产生于西方文化的母体之中,移植到中国必然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地方……西方叙事理论进入中国,必然要做一些调整和变化。这种调整和变化的依据,首要的自然是中国当代的叙事文学实际,但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叙事理论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3]这种沟通中西叙事理论、重视对中国自身叙事理论研究的思考与取向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这样的工作,不仅中国学者在做,国外也有学者在从事此类研究,尤其是那些未受到西方充分关注的东方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印度当代久负盛名的诗人与学者阿雅帕·帕尼克于2003年出版了《印度叙事学》一书,总结了印度叙事艺术所采用的各种方式,确认了印度叙事作品中所运用的10种主要的叙事模式,并偶尔论述了它们对西方叙述者可能的影响。在该书的导论部分对印度的叙事理论与实践作了概述;在结论部分探讨了叙事文与叙事学之间的关系;附录部分则概述了亚洲的叙事传统。《印度叙事学》试图强调这样一种认识:在印度叙事作品的色彩斑斓、不断变化的一连串景象或事物中,故事讲述者构建起了十分清晰的叙事策略,而这是为印度以及国外的比较文学家所忽视的。可见,挖掘与总结自身的叙事传统,并与国外的叙事理论与实践相沟通,是各国叙事学者、尤其是东方学者所关注的。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在叙事学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如何使中国的叙事学者更好地为国际叙事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促进中国自身的叙事学研究和叙事作品分析?如何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国际叙事学领域中具有自己的特色,我想,也许“比较叙事学”可以作为构建广义的“中国叙事学”之一途,并促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国际叙事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比较”作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各个不同的学科所广泛采用。而在一些冠以“比较”的学科,如比较政治学、比较法学、比较文学等,“比较”则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它是构成该学科或学科分支的基础。既然作为比较研究,就不是对某一单一国家或单一对象的研究,它必定是涉及两个或多个对象的研究,其相互作为参照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比较叙事学”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考虑的。与一般的叙事学研究不同的是,对不同语言与文化领域的叙事作品、包括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叙事理论之间的比较与对比,对于比较叙事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并必须从总体上贯穿始终,对其从各自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做更深一步的探究。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实际上已有学者提出了“比较叙事学”的问题,并进行了与这一方向相关的研究,但这方面的工作远未形成势头,也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1998年,赵毅衡出版了《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作者在该书《自序》中指出:这本书是他在美国准备博士资格论文时所做的读书笔记,全书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来阐释:“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己。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4](PⅠ-Ⅱ)该书从叙述行为、叙述主体、叙述层次、叙述时间、叙述方位、叙述语言中的语言行为、情节、叙述形式的意义等方面,运用中外叙事作品作为例证,结合理论进行阐释,尽管其核心不在于进行比较研究,但其意义在于提出了“比较叙述学”的问题。傅修延在其1999年出版的《先秦叙事研究》中,强调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作者指出:《先秦叙事研究》“主要运用叙事理论来作透视与解剖”[5](P7),这里的叙事理论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叙事理论,也包含了西方的叙事理论。应该说,上述著作包括前面提到的杨义的《中国叙事学》都带有比较叙事学研究的性质。
在国外,也有学者提出了“比较叙事学”研究。但相较国内学者在这一方向的研究与实践来说,国外学者对此似乎不如中国学者这样明确与积极②。在谷歌网站上键入英文“comparative narratology”一词,出现的有效搜索结果相当有限。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的学者冈三郎在日本的《英文学思潮》上发表了两篇论文:《朗费罗叙事文的“比较叙事学”:费德里哥鹰物语在路边客栈 故事中的转换》与《早期英国悲剧比较叙事学研究》中,明确提出了“比较叙事学”。前述印度学者阿雅帕·帕尼克的《印度叙事学》,是在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进行的,也应该可以看作带有比较叙事学性质的研究。纽约大学斯丹姆教授与乔治城大学瑞安格博士2004年主编出版了《文学与电影指南》一书,该书共25章,其中,第5章针对20世纪以来将小说改编为电影远远超过电影改编为小说(即所谓“novelizations”)、对书写文本转换为形象的关注超过了对相反的转换的关注这一状况,探讨了小说与电影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指出:与其说它涉及的是研究影片——小说(film- novel)之间关系的问题,毋宁说是电影——文学(cinema- literature)之间的关系。它所研究的不是两类特定文本之间的关系,而是实践一种在影片与小说之间穿梭往返、以便更容易理解的一种叙事类型,这种叙事类型既可以很好地用于分析书写文本,也可以很好地分析电影叙事。在这一基础上,作者对“比较叙事学”作了这样的界定:“要而言之,它将是一个我称之为‘比较叙事学’的问题。但是,我们如何对此作出界定?简单说来,比较叙事学并不致力指明两个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似与相异,而是要展开电影—文学之间的相互融通,以熔炼出更明确与富于成效的观念。”③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所表明的比较叙事学,更多的是以探讨不同种类的文学艺术文本之间的可融性与可转换性,而非致力于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叙事理论与实践之间由于语境不同而出现的相似与相异、并由此出发进行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它与我们所提出的“比较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有所不同。
可以看出来,中国学界对比较叙事学研究方向的注意远远超过国外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外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在他们的眼中,西方的学术理论就是普世性的世界学术理论。即使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长期以来占核心地位的,依然是属于西方范围之内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鲜少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比较研究。就学者而言,在西方学界,除了少数汉学家而外,一般治叙事学的学者对中国以及东方的文学与理论均所知甚少。西方学者是从他们自身自古希腊、罗马开始的文学传统来探讨叙事学理论、实践叙事学研究的,其理论概括中绝少看到来自除西方以外的文学实践。而一般说来,中国叙事学者除了对自身的文学与理论传统非常熟悉外,对源自国外的叙事学理论以及西方的文学实践也都不生疏。这样一来,对致力于研究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叙事理论与实践之间异同与关系的比较叙事学就难于由国外、尤其是西方的叙事学者来承担了,而中国叙事学者却可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杨义坦承:他在写作《中国叙事学》一书之前,曾在英国牛津访学时,批阅了一些西方叙事学的著作,并“以中国自古及今的叙事经验,对西方叙事学进行比较性的阅读”,他说:“当看到一些西方著名学府的名教授对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曹雪芹、鲁迅一流巨人,竟然不甚了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多少有资格对西方叙事学的‘世界性’产生怀疑。在西方学者较少涉足的领域,中国学者有必要作出发现,这应该是人类发展的共同主题。”[2](P4)作为中国叙事学者,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在比较叙事学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形成中国自身的叙事学研究特色。
在比较叙事学的视野下,可以进行富有意义的研究。在进行比较叙事学研究时,如下一些方面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比较叙事学是对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所作的比较研究。它将致力于探寻存在于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之间的异同,并进而探寻造成这些异同的深层社会、心理、习俗、文化等原因。可以说,比较叙事学是比较文学透视下的叙事学研究,因而,一方面,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比较叙事学研究是适用的。比较文学“属于不同文化领域的作品之对比研究”[6](P11-12)。从总体上贯穿对不同文化领域中的叙事作品进行比较与对比研究,是比较叙事学的基础。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叙事作品,都带上了其形成的不同语言、文化与地域特色;而在这些丰富的叙事作品的基础上概括与总结出来的叙事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特色。与此同时,人类毕竟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表现在叙事作品中,也同样可以发现许多相似与一致的地方。因而,探究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的相似与相异,不仅对研究文学作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极为有益,也将对形成于不同文化系统中的作品与理论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而对沟通不同文化、促进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的人们的交流与对话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比较叙事学仍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研究,可以将比较叙事学作为叙事学研究、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分支来看待,因而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同样是比较叙事学研究的基础,在研究中应该将“叙事学之基点”[7]贯彻始终。叙事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构成叙事学的基本要素,在比较叙事学研究中,必须得到充分的体现,必须作为基本的导入点、基本的研究层面去进行。无论是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叙事理论,还是所形成的叙事作品的比较与分析,抑或是其间所形成的差异以及相互影响与融通,均需在这样的层面上来进行。
第二,比较叙事学应该在比较文学与叙事学的理论基础上,深入挖掘与探讨丰富的中国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资源,包括古代的叙事理论与现当代的叙事理论与作品资源,以与国外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实践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比较叙事学研究的基点应该放在中国的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上。中国有着几千年丰富的文学传统,有大量优秀的叙事作品,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中国自身富于特色的文学理论,包括叙事理论。对中国自身的资源挖掘越深、分析越透彻,就有可能将这样的研究做得越好。而在与国外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的比较研究中,也才会更深入地发现与分析很多富于意义的东西。比如,在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即“视点”或聚焦的研究中,热奈特首先将聚焦区分为三种形式,即零聚焦、内聚焦与外聚焦叙事。他认为:外聚焦叙事的作品在两次大战之间变得家喻户晓,应该归功于达希尔·哈梅特的小说(他的主人公就在我们眼前活动,但永远不许我们知道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和海明威的某些短篇小说,如《杀人者》,尤其是《白象似的群山》,他守口如瓶,一直发展到叫人猜谜的地步。[8](P130)这里,热奈特几乎完全未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叙事作品的实践纳入其视野内。我们对中国传统小说稍作透视,就可以看到这种只对人物的外貌、言语、行为进行描述,而几乎不进入人物内心的方式,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并不罕见,白描式的描述正是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新叙事话语》中,热奈特多少修正了他对外聚焦的某些看法,指出:“自然外聚焦不是两次大战间的美国小说的发明,它的创新只是在一般很短的叙事中从头至尾维持这个方法。”[8](P230)即便是这样,他显然也未注意到,在鲁迅早于达希尔·哈梅特、海明威的小说创作中,人们可以发现堪称经典的属于所谓外聚焦叙事的短篇小说,如《示众》与《长明灯》。这两篇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作品中出现了众多的人物,而在对人物的描述中丝毫未深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内心,只有对人物言语、外貌与行为的描述,但作品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令人震撼的效果,具有极高的艺术表现力。[9](P108-123)对中国自身的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的探讨,应该是比较叙事学的立足点,在中外比较研究中,不仅可以深入挖掘属于我们自身富于特色的东西,丰富与发展叙事理论研究与叙事作品分析,同时可以相互沟通,增进相互了解。
第三,比较叙事学研究,其对象自然应该是双方或多方的。作为比较的一方,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实践作为立足点不可或缺;同时,作为比较研究,少不了相对的一方或多方。这一方或多方如何选择呢?从叙事理论发展的历史与叙事作品的影响来看,到目前为止,无论从理论的系统性或对中国自身的影响来说,尚无超过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与叙事作品可与之相比。这种情况,在近20余年来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的表现尤为明显。因此,目前可以用西方的叙事理论作为比较叙事学研究主要参照的基础。也就是说,在目前较为可行的是开展中西比较叙事学研究。当然,在逐渐成熟的基础上,也可以逐步开展以中国作为基础的、与除西方以外的其他语言和文化系统之间的比较叙事学研究。目前已具备这方面研究条件的学者,在中国与除西方以外的语言文化中所进行的比较叙事学研究自然应该得到特别的鼓励。应该使以中国自身作为立足点的基础上开展的比较叙事学研究日益丰富,范围更为广泛,以使叙事学研究真正形成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学科。
注释:
① 英格伯格·豪斯特莉(Ingeborg Hoesterey)对叙事学的发展提出了另一种讲法,她把叙事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叙事学研究的“古代”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结构主义范式为基础的“经典”叙事学;第三个阶段是所谓的“批判”叙事学,豪斯特莉称之为“新希腊化”(new Hellenism)时期。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讲法表明叙事学仍然蒸蒸日上。(见James Phelan & Peter J.Rabinowits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3页)。
② 在美国学者普林斯2003年修订再版的《叙事学词典》中,没有“比较叙事学”的词条。在戴卫·赫尔曼、曼弗雷德·雅恩、玛瑞-劳热·瑞安2005年编辑出版的《罗特雷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中,给予了诸如“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词条以大量的篇幅,对文化与历史叙事学、历史图形叙事学、精神心理叙事学、电子网络叙事学等均有词条和论述,对叙事与电影、叙事与音乐等也都不乏论述。但书中却找不到“比较叙事学”的词条,几乎没有对它的任何论述。这说明比较叙事学研究尚未受到欧美叙事学界的注意,未进入欧美主流叙事学研究的视野。
③ Robert Stam and Alessandra Raengo(eds.),A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Film.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See http://www.blackwellrefe rence.com/public.赵毅衡在其《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说:“近年来,由于符号学家的关注,电影叙述学发展很快,但其基本模式与小说的叙述学相通。本书将偶尔用电影叙述的例子作对比性说明。”(见该书第2页)二者在此有相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