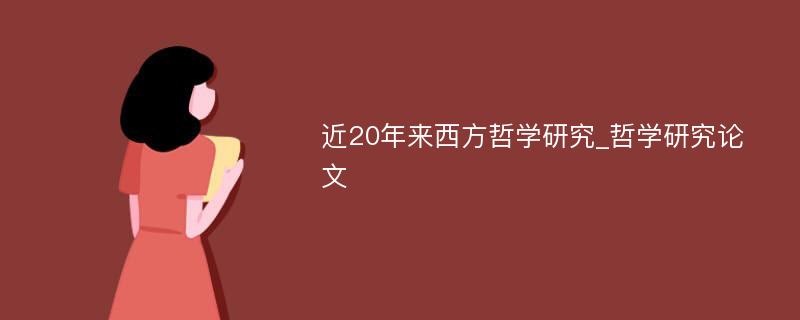
20年来西方哲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来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1999)12—0038—04
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过程中,70年代末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以来的20多年,无疑是西方哲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时期。
一般说来,可以把这一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拨乱反正,西方哲学东渐得到恢复并走上正轨的阶段;80年代后期开始,是深入发展,西方哲学东渐取得重要成果的阶段。前一阶段中有“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与“尼采热”的出现,在后一阶段中,胡塞尔现象学受到热情传播则是西方哲学东渐走向深入发展的集中体现。上述变化以及前后两个阶段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期西方哲学东渐过程中的发展趋势。下面,就这一发展趋势表现及其特点,进行具体分析。
就第一阶段而言,“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与“尼采热”的出现,充分反映了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在改革开放后对萨特、弗洛依德与尼采哲学的高度热情,也生动地体现了新时期西方哲学东渐的繁荣景象。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关这些哲学流派,特别是这几位哲学家的著作被大量地翻译过来,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中,不少著作成了当时最为畅销的书藉。
第二、发表了难以计数介绍这些学派、特别是这几位哲学家的文章,举办了大大小小关于这些学派、特别是这几位哲学家思想的专题讨论会或讲座。这些文章与活动,不但受到了社会上的热烈欢迎,而且在年青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萨特的“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成了谈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命题。尼采的“价值重估”、“意志自由”、“成为你自己”等,也都成了他们日常谈论的话题。
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学者除把一批国外学者评述这些哲学家的成果翻译过来外,还在初步研究的基础上大量撰写介绍性或评论性的著作。从它们的内容考察,虽然其中不免还有这些哲学家本来面目的阐述,但在这一方面却没有成为重点,而是主要着眼于开始全面介绍与传播。因此,这些著作都以其热情和客观的态度,深深地感染了读者。
就是因为这些“热点”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化现象,所以这些学说的大量输入和广泛传播,对于更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冲击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束缚,都产生了一定推动作用,同时这对于人们主体性的建立,无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它还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对现代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理解。
但是,还必须看到,这种积极影响又是历史的和有限的。主要是这些“热点”都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尽管表面上传播气氛热烈,论著发表数量很多,但是从总体上考察,它们多是直接的、表层的、情绪化的渲泄,真正学理上探究很少。实践表明,这样发生的社会影响是不能持久的。因此,随着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哲学东渐的发展,表面的热烈情绪便被里层的理智思考所代替。例如,不久出现的“告别萨特”、“告别存在主义”的反省,就是它的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表现。在这种反省中,他们逐渐自觉地领悟到:“萨特仅仅为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异化和战争条件下的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提出了自由、选择和创造之于人生价值的理论意义,但对于究竟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和价值,萨特存在主义就显得苍白无力,提供不了令人信服的答案。短短几年后,生活的实践使很多人从轻信中自觉过来”。(注:陈中亚.《我告别了存在主义》,《中国青年》,1982( 10,(30 —31).)事实表明,这样形成的“萨特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弗洛伊德热”与“尼采热”也是这样,它们都在一阵热浪之后便沉寂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思潮受到了中国哲学界的关注与研究。80年代的后期,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认识的深入,以及中外哲学交流的扩大与发展,胡塞尔现象学得到了热情的研究和积极的传播。现象学是本世纪西方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胡塞尔全集》的陆续出版,以及地区性和国际性现象学研究会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对其研究的广泛而深入的开展。从现代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几乎是经久不衰和无处不在的。值得提出的是,“这种影响是一种理论效应意义上的影响,它表现在:一方面,胡塞尔所使用的现象学方法不仅为欧洲大陆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现象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且它还影响了现象学运动以后的西方哲学、心理学/病理学、美学/文学/艺术论/社会哲学/法哲学、神学/宗教理论、教育学/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甚至经济学等等学科问题的提出和方法的操作。另一方面,无论赞成他还是反对他,人们都无法避免他,都必须对他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虽然认识的现象学理论始终处在胡塞尔哲学的兴趣的中心,但他在一生的哲学追求中所把握到的生活真谛远远不局限在理论理性领域。他所指出的其他各个思维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西方思想的发展,以至对胡塞尔的不理解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当代西方哲学,至少是欧洲大陆哲学的认识的狭隘性。”(注: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 三联书店1995,6、372.)因此,60年代以来, 胡塞尔现象学就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开放的国际学术领域。特别是在这临近世纪的末叶,国际哲学界已处于对以往哲学的反思、再理解和消化的阶段。所以,就国际范围来讲,现象学的研究,正在朝着既专且深的方向发展。
在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虽然有的学者早在20年代,也曾间或地提到过现象学;例如张东荪,就多少在文章中简要地谈到过胡塞尔现象学(注:如发表在《东方杂志》第19卷17号上的(1922年)《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第22卷7—8号(1928年)上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等文章,均有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介绍,文中Husserl译为呼塞尔.)。此外,还有杨人梗《现象学概论》一文发表(注:见《民铎》杂志,1929年第1卷和第10卷第1号.)。30年代, 蒋经三在《现象学派与新康德派》中把这两个学派联系起来进行了考察(注:见《学艺》杂志,1931年1 月,第11卷第1号.)。40年代,倪青原在其《现代西方哲学之趋势》里,还概括地阐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大旨及现象学运动的发展(注:见《学原》杂志,1947年第1卷第3号。文中Husserl译为虎适耳。)。 但是,与传播其他有影响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比较起来,真正全面的研究尚未进行,就是一般的介绍也极为有限。而且,在自这以后直到70年代末的一段时间内,现象学基本上排除在中国哲学界的视野之外,甚至到拨乱反正开展后“萨特热”已经出现时,胡塞尔现象学却依然是讨伐的对象(注:参见《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文章》,商务印书馆,1982.)。 只是到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与“尼采热”逐渐沉寂下来以后,才把目光转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身上。现象学研究在我国的这种落后状况,不但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对某些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还将会严重制约着我国传统哲学的变革与文化变迁的实现。因此胡塞尔现象学的全面研究与热情传播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它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认识的深化。这是西方哲学东渐在经过一段曲折之后全面走上了健康发展道路的标志。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90年代以来,胡塞尔现象学的传播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大陆和港台有关学者,共同商定成立了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创办了以专门传播现象学为目的的不定期刊物《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并由它牵头在南京、合肥、香港、上海和海口举行了现象学专题讨论会。通过这些活动,使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思潮在中国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在它的推动下,其他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其中,除翻译与出版了一批这个学派的著作与国外学者研究这个学派的成果外,中国学者撰写发表了一批论文和专著。如叶秀山的《思、史、诗——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尚杰的《语言、心灵和意义分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罗克汀的《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演变:现象学纵向研究》(广州文化出版社,1990)、涂成林的《现象学的使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倪梁康的《现象学及其效应》(三联书店,1995)、张庆熊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现象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汪堂家的《自我的觉悟——论笛卡尔与胡塞尔的自我学说》(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李幼蒸的《结构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与熊伟主编的《现象学与海德格》(远流出版公司1995)等。此外,《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先后出版了两辑。
如果把上述现象学的传播活动,特别是这些著作与前一阶段那些“热点”中的活动与著作加以比较,可以清楚地发现新时期西方哲学东渐中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
第一,在西方哲学的东渐的社会气氛上,虽然没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种热热闹闹的场面,但是,中国学者投身到这个哲学领域中来,却是经过冷静的理性思考后采取的行动。因此,他们在研究与传播胡塞尔现象学思潮时,既有独立的探索,又有通力的合作。特别可贵的是,为了使它在中国得到深入持久的传播,他们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具有耐得十年寒窗与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实践证明,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哲学研究事业,没有这种精神要想取得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成果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参与这个学派研究与传播活动的学者,也没有前面那些“热点”发生时那么广泛,而是局限在理论界。然而在这些学者中,有些多年留学西方胡塞尔研究中心,有些来自国际著名的现象学研究者门下,与西方研究现象学队伍交往密切,对国际现象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较为熟悉。特别是在研究与传播过程中,他们不但能够深入钻研,大胆探索,而且还力求把自己的研究与国际上对这个思潮的研究做到同步进行,表现出乐于与国际现象学研究接轨,勇于攀登国际现象哲学研究高峰的气概。
第三,从取得的成果数量而言,发表的论著虽然没有那些“热点”传播期间那么多,然而它们却很少“萨特热”或“尼采热”中那种情绪化的渲泄。相反,它们材料扎实,论述充分,视野开阔,有开创性,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例如,在这些论著中,既有对现象学家著作原汁原味的解读(特别在论述现象学家的学说时),又有在深入钻研基础上经过独立思考提出的富有启迪的观点。尤其在对现象学学理的探究上,更是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在这一点上,虽然有关现象学及其发展过程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论及,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都看重现象学基本精神的揭示,都关注现象学方法的阐明,都着力于现象学效应及其影响的追究,都关心引进现象学在中国的学术价值,特别是探索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变革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作用。因此,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长期以来哲学研究的政治化倾向,洗去了过去哲学研究中附加到哲学功能上的那些杂质。这是哲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良好的一种势头。
第四,在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推动下,深受其影响的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哈贝马斯的社会哲学的研究与传播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仅以海德格尔的研究来说,除有《海德格尔选集》上下卷等重要原作中译本问世外,中国学者撰写的专著即有:喻宣孟《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4)、靳希平《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书店,1995)、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1996)、《海德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和张汝伦《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等。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有这么多成果付梓问世,这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现象学等这些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虽然起步较晚,但它取得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
综合上述几点,说明西方哲学东渐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它对哲学研究事业来说,是积极的、有意义的。如果这一趋势能够健康地发展下去,特别是学者们如果能够站在当代全球化理论高度上,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古典西方哲学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同国际西方哲学学术界的平等对话,把深入的学术探讨和群众性的传播结合起来,可以预见下个世纪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将是一个大有希望的领域。
标签: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论文; 现象学论文; 萨特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胡塞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