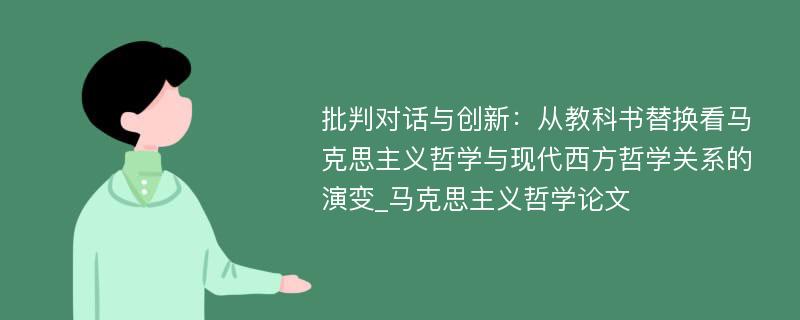
批判→对话→创新——从一本教材的版次更替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关系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本论文,版次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教材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新时期的哲学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是一对重要的互动因子 。考察二者间关系的嬗变,对于理解我国哲学的当代走向,前瞻其演进态势,具有重要的学 术意义。在此,我不拟泛论这一问题,而只想借刘放桐教授等编著的三版“现代西方哲学” 教材为一例说。
刘放桐教授等编著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已由人民出版社 于2000年6月出版。这也是刘教授等编著的同一教材的第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叫做《现代 西方哲学》,出版于1981年6月,第二个版本叫做《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出版于1990 年8月,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三个版本间隔约为10年,总跨度为20年,加上酝酿出版的 最初阶段,正好跟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相吻合。这本教材在同类教材中印数最多,影 响最大,因而实际上成了新时期中国学人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最便捷、最通行的一个“视窗 ”。透过该“视窗”的三个版本,我们所看到的现代西方哲学大异其趣,这显然不是因为对 象的自身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对象基本上还是那些对象,而是因为编著者看待对象的态 度、思考对象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亦即其头脑中用以分析现代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 身发生了变化。在该教材的第一个版本中,编著者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苏联模式的 教科书哲学,以之分析现代西方哲学,必然采取批判模式;而在该教材的最新版本中,编著 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基于实践之上的现代哲学,以之分析现代西方哲学,批判模式就转 换成了对话模式。从批判模式到对话模式,遂成为该教材版次更替的基本走势。由于该教材 是由权威出版机构印行的,因而其观念反映了同时期社会上的普遍观念,正是这一点使得该 教材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关系嬗变的缩影。
本文将首先勾勒这一缩影,以显现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关系嬗变的 基本轮廓。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探讨今后二者关系嬗变的趋向,据我所见,该趋向应是: 二者将在对话性互动中为我国哲学的理论创新积累思想。故此,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 西方哲学之关系嬗变的历程归纳为六个字:批判→对话→创新,下面次第分析。
(一)从简单否定现代西方哲学到批判地评介现代西方哲学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关系的嬗变过程,以及理解“现代西方哲学”教 材版次更替的意蕴,必须首先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是20世纪的中国史所造就的客观结果,是当代中国的任 何哲学思维活动所无法回避的一个既定事实。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整 个世界,包括现代西方哲学,是该事实的题中应有之义。20余年来中国哲学的进步,不是通 过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通过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 每变革一步,其对现代西方哲学就宽容一分;而这种宽容导致现代西方哲学影响的扩大,反 过来又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进一步变革。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大家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然而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内容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会懂得这些年人们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引进现代 西方哲学的历史意义。
在改革开放前,“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往往采取简单地否定 态度。”[1]这种态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将现代西方哲学拒之门外,表现为:在80年代初以前 ,系统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的高校凤毛麟角[2]。其所以拒斥现代西方哲学,在于那时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极端的教条主义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苏联模式教科书所表达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乃是一种自足的、完备的终极真理体系,而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的哲学更是 将该真理体系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照此推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穷尽了真理,其他 哲学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至于现代西方哲学竟然在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况下还要另 搞一套,其反动性毋庸置疑。
“文革”的结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走上了变革之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讨论、“实事求是”观点的恢复,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极左面目的另一番模样, 尽管其基本观念还是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那一套。在这种情况下,批判地研究现代西方哲 学成为可能,《现代西方哲学》教材应运而生。所谓批判地研究,在那时主要就是在介绍现 代西方哲学的流派和观点的同时,不忘给它们贴上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之类的标签,不忘给 它们戴上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之类的帽子,其典型句式如:“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影响 最大、流毒最广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之一。”[1]这样一种研究模式,就是以教科书哲学为 理所当然的批判主体、以现代西方哲学为批判对象的“批判模式”。
批判模式虽然连研究者自己也未必喜欢,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可接受状况[3]。无论如何, 从盲目排拒现代西方哲学到批判地介绍现代西方哲学,毕竟是一个难得的进步。
(二)“批判的剩余”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互动
应当说,《现代西方哲学》一书对教科书哲学的观点是十分忠实的,它的积极意义在于“ 材料大于观点”——批判活动必然产生“批判的剩余”,亦即其所介绍的现代西方哲学的理 论材料具有不能够被编著者自觉贯彻的批判意图所完全整合的剩余属性,这些剩余属性遂成 为作者和读者所共有的纯收益。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对批判的剩余而非批判本身的追求, 才使《现代西方哲学》先后印刷7次,共12万余册,而这种批判的剩余反过来又成了批判者 自我批判的推动力量。
在《现代西方哲学》畅销的同时,“大量当代西方哲学名著被翻译出版,我国学者自己撰 写的有关当代西方哲学的论著也大量问世。单是各种不同规格的本学科的教材也已出版了十 多本”[3]。这些批判性研究迅速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剩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在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直接指向苏联模式教科书哲 学的变革呼声不断高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张和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正是这种 局面使得《现代西方哲学》的作者很快就感到了书中的观点“过‘左’”,“为了不使谬种 进一步流传”,曾建议停印此书,并最终决定修订此书[3]。
《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作为80年代末期的一项研究成果,既反映了当时现代西方哲学 研究领域的新进展,更体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实效。该修订本的一个直接目 的,就是“力求突破旧的、僵化的批判模式。例如不仅仅以唯物唯心来划哲学的界限,定哲 学的成败,而尽可能真正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实事求是具体分析”[3]。这种 观点跟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超越唯物唯心的主张不无默契。不过,由于作者当时心目 中尚未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系统理解,所以修订本所确定的目的并未达到。
(三)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模式
90年代,哲学的现实关怀趋于消沉,但自我反思却更加深刻。被译介的西方哲学文献,包 括古代的、现代的和当下的,越来越多;本土思想也越来越受到学界和社会的重视;甚至马 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开始被作为纯学术对象加以考量,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无声的 变化使得哲学研究逐渐地被放置到了一个更加深厚的学术基础之上和一个更加繁复的理论结 构之中,那种惟我独真、惟我独尊的哲学意识已经明显过时。
这种情况下,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究竟应当怎样才合乎时宜,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处理才更为恰当,便成为一个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虽 然不少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在个人的专题性研究中已经不再申言其是否采取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或者说其有关研究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有一种微妙的疏离,但是 ,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教材却无法回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
本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指导应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在《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修订版)》中也是很 清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90年代以后,马克 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成了争论日益激烈的问题,继而现代西方哲学究竟具有何种性质也成 了问题。《新编现代西方哲学》明确地把二者的关系作为问题提出来,显示了我国现代西方 哲学的研究模式正在发生一种深刻变化,其关键之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作为现代西方哲 学研究的坐标的同时又成了研究的对象。用作者的原话来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 是态度来从整体上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4]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能提出这个问题,还在于作者已经有了对问题的初步解答,尤其是 有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这种新理解也正是《现代西方哲学(修订版)》不曾明确 具有的。按作者的意图,“《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将主要贯彻如下两个基本观点:西方现代 哲学取代近代哲学是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型,它使西方哲学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 阶段;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转型有着原则的区别,但在超越 西方近代哲学上二者殊途同归,二者都属现代哲学思维方式。”[4]作为现代哲学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不是以实体和本原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实践为基础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 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不是 在理性独断和心物等二分的基础上使人片面化和异化,而是回到活生生的、知情意统一的、 具体的、完整的人,并为人的自由和创造开辟广阔的道路。”[4]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显然不同于当初《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运用的那种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那种哲学是 “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传 统形而上学的水平”[4]。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情况的人都知道,《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理解,跟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多数学者的有关理解是一致的 。
用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去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值得肯定的东西就大大 增加了,其独到之处也容易彰显出来。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超越近代哲 学的意义上就有了共同性,同时相互间又有原则区别。正是这种情况,使得研究二者的关系 、比较二者的异同、促进二者的对话成为必要。如是,用对话模式取代批判模式就顺理成章 了。
对话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仍然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地位,二是构造了一个对于现 代西方哲学的尽可能开放的思维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是一种特定的哲学学派,而现代西 方哲学则是在现代西方这一时空范围内各种哲学流派的总体,二者间在逻辑上是不对称的; 单单将二者构造为对话关系这一做法,就默认了前者的优越性。虽然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指 导中国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一模式对现代西方哲学毕竟是最宽容的,至少现代西方哲学在对 话的时候可以跟马克思主义哲学平等相待,这一点就来之不易。
(四)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为21世纪中国的哲学创新积累思 想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新编现代西方哲学》所初步建构的对 话模式,只是二者关系演进到世纪交替时期所呈现的一种新形态。完全可以想见,这种模式 、这种形态不可能是恒久的和终极的。如果若干年后(比如又一个10年以后)这本教材还有修 订的机会的话,我们相信作者一定又会提出新的想法;而那些现在仍然不满意此书观点的人 ,也可寄希望于它的将来。这个将来实际上就是对话模式的运行趋向。那么,这个趋向的含 义又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也许该书的编著者有自己的考虑,我在此只想谈点个人想法。
首先是两个基本判断。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今后将长期成为我国哲学研究的一大 基本问题。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紧密关联着中国民族的现当代命运,揭示和解决其所 蕴涵和关涉的问题是我们在新世纪正确把握自身命运的一个思想前提。在今后一段时间,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展仍将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自我变革来实现。其二,现代 西方哲学的思维平台将逐渐成为我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思维平台。这话的意思是:现代西方哲 学在哲学操作的思维水准上较近代哲学已经有了整体的提升,我国哲学研究的操作平台只有 搭建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水准上,才能做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实绩。这里不是主张盲信现代西 方哲学的观点,或只了解现代西方哲学而不学习其他哲学,而是说必须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建 立在通晓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见解、精神实质和思维技艺的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现代西 方哲学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形上层面,观念地凝结着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跟中 国的问题也处在历史和现实的勾连之中,因此,只有站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平台上,我们 的哲学研究才可能在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尽量不重复西方的问题。
根据这两个判断,在中国新世纪的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仍将处于 高度相关的状态,它们之间的对话也必将在更加深广的层面上展开,对话的参与主体和操作 方式也一定会多样化。通过这些对话,中国民族以至全人类所经历和面临的许多问题必将进 一步获得哲学觉解。在此过程中,对话模式客观上将成为为新世纪的哲学创新而积累思想的 重 要机制。这也就是说,以解决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以至全球之重大问题为指归的哲学创新,将 是或应当是21世纪我国哲学研究的根本趋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对话模式只 有自觉朝着这一趋向演进,才会获得良好的前景。
有了这个从批判模式到对话模式再到哲学创新的历史维度,有了刘放桐教授等编著的“现 代西方哲学”教材之版次更替作典型例证,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关系嬗 变的脉络就一目了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