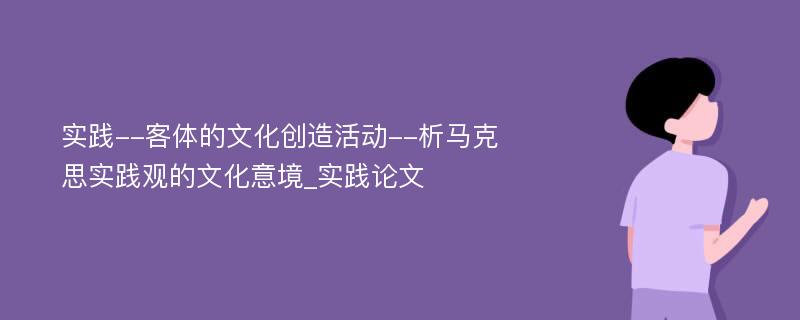
实践——对象化的文化创造活动——析马克思“实践观”的文化意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文化论文,意境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广义的“文化”概念内涵意趣深长,其定义目前约有200种左右。 因此,我们很难择定其一为万无一失的界说。但“文化意境”涵纳的自然“与社会的人化”、“人类活动与生活的文明化”,却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内容。马克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展开其理论路向的。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此处, “环境的改变”也即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2 〕“创造”的韵致标示了它并非一般的物质生活活动,而是文化创造活动——“使环境人化”的活动。“人的活动”体现着人的文明发展,也即人不断地“向文而化”,使自身不断地脱却原始性和野蛮性而向越来越高级的人性水平发展。二者的一致性表征着人的价值,而“革命的实践”又是该价值的命脉所系。由此可见,“革命的实践”就是文化创造,或者说是在一定文化意义指导下的实践。离开了文化创造就不是人的社会实践,而是动物的活动了。正是在这个视界下,我们可将马克思“实践观”的文化内涵厘定为“创造和实现人的价值的对象化活动”。把“创造”同“人的价值”关联起来,这在实际上确定了人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并为“文化”指示了一种“人为”而“为人”——亦即人的自我成全——的方向。
一、“对象性”与“对象化”
“对象性”与“对象化”范畴融通着“实践”的底蕴,因而规范着文化创造的真正旨趣。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和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种事物一样,都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棵树须以土壤、水分和阳光为存在对象;一只蜜蜂须以花和花粉为存在对象,也需要以它所属的蜂群为存在对象。人所需要的存在对象更多,他受到更多的条件制约,因此也就有更丰富的“对象性”。单就“对象性”的存在意义而言,人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对象性”是任何一种存在物在直接“生存”意义上的存在性,所以它是所有存在物的普遍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3 〕处于对象性网络中的万千事物间的相互作用,孕育并引发出千姿百态的创造性活动。其实,大自然演化万象和育生万物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创造”活动。天象的瑰丽,山川的秀美无疑是大自然的“创造”奇迹,而生生不息、新新不已的各种有生命的事物(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的发生和演变,又何尝不是一种神妙莫测的“创造”景观。但大自然同它的“创造”过程是直接同一的自然过程,它的任何一种“创造”——例如一座山的拨地而起或一种新的生物性状的产生——都不存在事先的规划,不具有社会性与精神性。而人的文化创造却不同,它不仅具有自然性(人以自然为对象), 而且具有社会性(在社会实践中创造)、 历史性(世代相续的创造过程)与精神性(在思维指导下进行)。更重要的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在还没有以成相的方式存在以前,就已经观念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就是说,人的每一次创造活动都有“内心图象”(马克思语)事先存在,这就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把人同一切非人的自然物区别开来,也把人的“创造”同大自然的所谓“创造”区别开来。
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4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对人的独特的“对象化”活动的最形象而准确的表述。人的存在的“对象性”是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而实现的,人在这种“对象化”活动中使自己的存在对象打上人的印记,这即是所谓“人化”,而人也在这种“对象化”活动中获得了内涵要比其他一切存在物丰富和生动得多的“对象性”存在。
事实上,人正是在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对象化”活动中,能动地构建了自身特有的自然性、社会性、历史性、精神性四重对象性关系,从而才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创造者主体身份的。马克思这样阐述道:首先,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5〕个人从自然生存出发, 第一个历史性的自主活动便是诉诸劳动,迫使自然承认自身价值。这样,就产生了现实个人与自然界以劳动为中介的最基础的对象性关系。其次,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现实个人改造自然的活动并非离群索居的个体单干所能奏效,只有社会性的劳动才是唯一可行的手段。于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相互需要的第二种对象性关系。在以上双重对象性关系中,个人确立了社会本质,并且他们的自主活动也被赋予了社会性质。再次,人还是历史的存在物。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的活动,都只是整个人类实践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现实的个人不仅要以他所处的现实社会为存在对象,而且要以过去各个时代的社会为存在的对象。“单是由于后来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历史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6〕最后, 人又是精神的存在物。人类的实践不可避免地与精神相依相伴。这不仅表现为人凭借思维对实践进行价值认识、评判、选择与改造;能动地导引实践活动并把经验提升为理论。更重要的是,人的意识还能以既得的理性成果和形式为对象,借助于“反思”与“反省”,不断地创发出精神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是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
综上所述,人所独具的“对象性”状况与“对象化”活动是全部问题的底蕴,实践概念的最深长的意味在这里,人类文化的最本源的起因也在这里。
二、“自然”与“自由”
“自然”与“自由”范畴是“对象性”与“对象化”范畴的必然延伸。倘若在“自己是自己的根据,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意义上确定“自由”的涵义,我们也可以说大自然(整个自然)的“创造”活动也是一种“自由”活动,因为我们无从在大自然之外为这种“创造”活动找到理由或根据。但就自然界中的任何一个或任何一种具体自然物而言,它本身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便是被大自然强制性地决定了的,因而并不能从这种必然的命运中得到“自由”。而且,即使是作为自然全体的“大自然”,其创造活动也纯粹出于“自然而然”,所以即使我们勉强说这种“创造”活动也是一种“自由”的实现时,这里的“自由”也决没有“目的”(因此也没有“价值”)贯彻其中。人却不同,人作为一种“受动——能动”的“自然”存在,同时即是一种“自由”——有别于动物的“他由”——的存在。人的“创造”活动都是“对象化”活动,它表征着人的“内心图象”在客观对象物上的实现。所以,人的创造活动,总是有目的的,亦即是体现人的某种价值追求的。人的“内心图象”是由人自己绘制的,而人在绘制这“内心图象”时,一定会依据某种价值标准,所以人在他的创造性活动中所表现的“自由”也一定具有“自觉”的性质。
“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本质属性,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8 〕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属性。而以“自由”和“自觉”来理解人的有别于动物乃至一切非人的自然存在物的生命活动的属性,“自由”和“自觉”就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仅当作最高目标追求的最后结局意义的状态,而只能被合理地看作是人的不断展开着的创造过程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实践作为人所独有的生命活动,它的每一次真实运作都显现着人的“自由”和“自觉”。因此,也可以说,“文化”植根于人的“自由”和“自觉”,倘若人的活动失去了自由的性质,文化的根蔓也就随之枯萎了。
人类文化创造的“自由自觉”性生动地体现为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过程:文化及整个文化世界的价值都是人立足于自身价值所赋予的,都是人对外部世界价值思维的肯定形式。它不仅使外部世界变成了意识到的存在,变成了人的对象世界,变成了有价值有意义的世界,也使人的本能变成了意识到的价值需要,使人的存在变成了对象世界的主体,变成了意识到的自我存在。因此,文化创造既是人的价值实现,又是人的本质实现,它既创造了一个客观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人化”世界,又创造并丰富了人及人的本质。
然而,人的“自由”与“自觉”决不能被理解为随心所欲地任意挥洒。因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9〕就“能动表现自己”而言,人的实践是“自由”的, 但这种“自由”又只能是在外在必然性制约下的“自由”。因此,作为人生命活动性质的“自由”只能被合理地诠释为:自由并不只是必然性的对立物,而更是一种被认识和超越了的必然性。在这里,“必然性”作为“自由”的媒介而存在,是自由过程中一个接一个被扬弃了的环节。而正因为人的文化创造的“自由”是一个永不间断的扬弃必然性的过程,因此,尽管在它的正向度上终始关联着人对真、善、美的价值的求取,但它同时必然蕴含着负向度——假、丑、恶,在这个向度上,有所谓“异化”的发生。“异化”不是一个自然范畴,而是一个人文范畴。马克思曾经精辟地阐述过的“劳动异化”是人的异化的中心环节,它即是在“自由”(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的负向度上展开的。在动物或其他自然物那里不存在异化问题,因为大自然的自然而然的“创造”活动即使可称之为“自由”(自作理由自作根据)的活动,那种“自由”也不带有任何价值色彩。“异化”是有价值色彩的,它只同以“自由”为生命活动的性质的人相关,所以马克思把“劳动异化”也称作人的“自我异化”。而“自由”既然意味着“自己是自己的理由,自己是自己的根据”,那末,在我们说人是“自由”的时,也就意味着人应当对自己的对象化活动的后果负责,既对实践的正向度价值负责,也对其反面负责。这样,在更宽广的意义上,人的自我异化便应当归属于“文化”范畴,正象人对异化的扬弃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一样。
但是,我们切不可把马克思关于文化创造具有两种向度的描绘看作是对未来持不可知论。事实上,马克思的原意只是为了说明:在人类创造文化并实现自由的历程中,真、善、美的价值目标只能在与假、丑、恶的冲突与转化中才能达到。人类创造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们不断追求自由、扩大自由的历史。这个过程正如马克思的“三阶段论”所概括的:最初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继而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最后才可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从而为人的更高的文化状态创造条件。这一更高的文化状态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0〕
三、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覆盖着全部人类社会的领域与历程。据此,马克思概括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1〕我们依据此意引伸,也可以说: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为人的社会生活与其价值意识不可分离,而“人化”祈向又是社会实践的必趋之势,因此,社会生活的本质与文化创造相容并摄为一个整体。事实上,人的价值意识发生之始,就是人意识到外部世界的价值及自我价值之始,也就是主体与客体分离——人的主体意识发生之始。而与此种价值意识浑然一体的实践一经开始,也就立即纳入了文化创造的趋向。
文化并不只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产品、工具、制度、运转程序)的总计,它的内在生命在于通过“创造和实现人的价值”而创造和实现人本身。人对自然的关系、人对人(社会)的关系、人对历史的关系、人对思维的关系都是人的对象性存在关系,这些关系通过实践(人的“对象化”的活动)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12〕这种历史观蕴藉着如下思想:第一,历史的主体不是现实个人之外的任何抽象物(例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费尔巴哈的“人类”等),而就是有血有肉,从事着社会文化实践的个人自身。“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13〕,因此他们的价值目标,不是指向某种“历史目的”(如“绝对精神”的目的等),而直接指向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4〕第二,有生命的现实个人就是从事社会物质生产的个人,因此个人劳动的社会形式——自主活动类型(因为社会劳动是个人自我肯定、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故称之为自主活动类型)是人类历史的基础。整个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发展史。每一时代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也许不是任何个人的最佳实践形式,但必须是当时氛围内,多数个体相对于前一时代较能发展,从而导致整个人类进步的形式(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如其不然,多数个人就会起而斗争,把它转变为另一种适合多数个人发展的新类型。所以,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为根本内容的历史,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演变史。它表现为:每一时期的交往形式,“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的历史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5〕第三,根据以上理由,人类的一切都导源于现实个人的社会活动,因此“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6〕由此出发,文化创造的价值目标指向“个人”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之事。马克思曾科学地论证了这一取向的必然性:“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当初要靠牺牲大多数个人和某些人类阶级[来进行],但终会打破这种对立,并与个人的发展归于一致;因此个人的高度发展,也只有由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来赎卖,因为种属的利益,在人类界和在动物界一样,是要由个体利益的牺牲来贯彻。”〔17〕这就是说,尽管人类在阶级社会中的演进必然带来人的自我异化,造成对个人发展的压抑;但同时,人类历史的进步又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准备了条件;因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8〕马克思曾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描述为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9〕,这不正说明他的理想社会是以“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价值尺度的么?据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文化观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价值枢纽的。
也许有人会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只是“应有的世界”的话题,而“文化”毕竟是离不开“既有的世界”的。然而,我们却可以这样推断:如果说那个“应有的世界”的目标并不纯然是幻想的产物,那么它一定会在“既有的世界”中找到其根据。事实上,人类创造文化、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就是一个不断从“既有的世界”跃向“应有的世界”的过程。文化世界是人创造的,但是,当它的价值、功能、意义一旦不能满足人的价值需要的时候,或者当文化世界的价值、意义、功能发生悖谬而阻碍人的价值实现的时候,人就要根据新价值(“应有的世界”价值)改变旧的文化世界,另外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世界以实现自身的新价值。正是在这个意境上,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一“应然”目标一定有其与“既有的世界”相通的通道。而这通道就是有着“自由、“自觉”性质的人的“对象化”活动,亦即人的“创造和实现人的价值”的实践。实践创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中的种种文化事实,并因此把这些文化事实联结成一个可理解而有活力的整体。实践又不断地调整和变更着作为整体的“既有”文化世界,使它在历史中成为一种动态的自身可以新陈代谢的存在。而文化世界的纵横交错和时空联结所以不至于流于一种机械的或生物学式的运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实践永远有着体现人的赋有价值的自由的品格。因此,我们当然可以说: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注释:
〔1〕、〔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273页。
〔2〕、〔3〕、〔7〕、〔8〕、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68、96、96、117页。
〔4〕同上书,第23卷,第201—202页。
〔5〕、〔9〕、〔11〕、〔15〕同上书,第3卷,第23、29、5、81页。
〔6〕、〔12〕同上书,第4卷,第321页。
〔10〕同上书,第46卷,上册,第10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76页。
〔14〕、〔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
〔17〕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2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