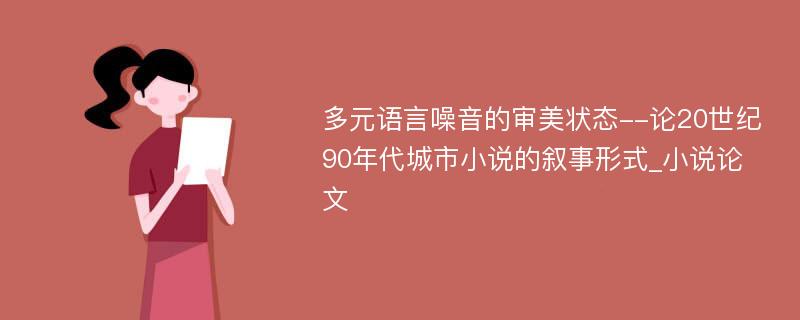
多语喧哗的审美状态——九十年代城市小说叙事形态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状态论文,城市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在工业化、商业化的背景上如同万花筒一样旋转起来,令人眼花缭乱地蜕变着,变幻出多姿多彩的景观。与此同时,一股以城市为审美表现空间、以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价值追寻为主要书写内容、以城市景观为天然叙事成分的城市文学创作潮流奔涌而来,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生长点。
书写内容的不同、审美情致的差别、叙事方式和内在文化意蕴的迥异,使九十年代的城市文学呈现出一种多语喧哗而且缺乏主调的审美状态,具体体现为叙事形态的不同。本文即试图对这一现象加以阐述并略陈己见。
一、平民生活的本真描摹
街巷、弄堂、胡同是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仍然保持着自己稳固的生存形态的传统城市民间社会,“或者说是当代都市文明与传统的农业文明相持抗衡的缓冲区域”(注:杨经建:《90年代“城市小说”:中国小说创作的新视角》,《文艺研究》2000年第4期。),虽然这里也历经时代浪潮的冲刷,但它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运行轨迹。生活在这里的平民百姓们,作为处在现代都市文明生态系统边缘的群落,默默地维持、坚韧地延续着城市文化的根系和命脉,“其日常生活每每交融在古与今、新与旧、历史和当下的混沌中”(注:杨经建:《90年代“城市小说”:中国小说创作的新视角》, 《文艺研究》2000年第4期。)。
九十年代一些城市小说就以城市民间社会为审美对象,站在民间立场上,用细致的笔法如实地描写普通百姓那种琐碎、平淡也不乏乐趣的世俗生活。因为叙事的历史时空和审美风格不同,这类小说呈现为两种叙事形态:
1.站在现在时态的民间立场上,以与日常生活同构的、朴素的话语方式描摹细碎的生活细节和平淡的日常场景。
这类小说具有新写实小说的风情遗韵,也是从日常生活的世俗性、琐碎性和庸常性着手来建构日常生活的叙事,所写的也无非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柴米油盐等等最普遍的生活内容,但是它们又明显不同于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偏重于表现平民日常生活的平庸无奈和不尽人意,日常生活在这些小说中总是表现出千篇一律的单调和乏味的面目。九十年代描写平民生活的小说则克服了这种偏颇,既写出了日常生活的庸碌、平淡,也发掘出了日常生活所包含的琐细的乐趣和平实的美感。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江汉路的那群市井平民在夏夜里有滋有地味地享受着世俗生活的乐趣:清淡可口的晚饭,眉飞色舞的闲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娶妻生子、解决住房困难、为家人排忧解难、下岗、拆迁诸种烦琐的事件构成了日常生活饱满、复杂的内涵。张大民就是在这种平淡琐碎的生活中兴头十足地生活着。范小青的《伏针》通过寻常小巷中普通百姓家庭的日常生活展现传统民间生活样态古朴安宁的诗化品性与和谐之美。针灸大夫陈先生与世无争,淡泊超然,认真行医,悉心授徒。他的子女每天按部就班去上班,回家就帮他护理病人。平静的家庭生活中偶有一些变化也很平淡,如侄子学艺不精就去开诊所,小儿子美满完婚。日常生活于平淡中显现出悠闲自在的情调。她的《城市民谣》描述江南古城一个叫钱梅子的平民女子下岗待业、开办饭店的日常生活。小说着力渲染那种与这个古老城市的韵致相一致的古朴、安宁、自在的生活情韵,失业、炒股、经商,一切喧腾的波澜都被日常生活抚平。
这些小说的叙事语言都是民间口语。我们可以从池莉和范小青的小说中各摘取一段进行简要分析。
猫子说:“个巴妈苕货,他是婊子养的你是么事?”嫂子笑着拍猫子一巴掌,说:“哪个骂人了不成?不过说了句口头语。个巴妈装得不是武汉人一样。”
——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你呀,老婆说,你这个扶不上的刘阿斗,你这个拎不清的阿木林,你这个憨进不憨出的寿头码子。我嫁了陈皮你这样的人,也算我前世没修好。
——范小青《绢扇》
上述文本所撷取的都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民间语言,没有经过刻意的雕琢和润饰,信手拈来,完全是自然形态的日常口语,具有非修饰性的世俗品格。这种民间口语虽然俚俗,却洋溢着如火如荼的生活气息,能够恰如其分地烘托、传达出民间生活闲在、随意的意趣与粗俗的格调。小说这种带有民间风味的叙事语言让普通市民感到平易和亲切。
2.回眸历史,以民间意识去烛照和重现被遮蔽的日常生活,凸显日常生活的永恒性。
民间社会是一个以物质生活做底子的恒久的世界。都市民间是一种靠物质生活来维系的精神向度。它的特征是不管社会变动、政治因素和时代精神的变化,它始终保持着它完整的生活逻辑和体系。
在九十年代,最为擅长在历史的背景上展现平民生活的恒定性的莫过于王安忆。王安忆认为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的根基。《长恨歌》凸显了日常生活不能被政治变幻切断的连续性和永恒性。以王琦瑶为代表的男女情爱、人情往来、衣食住行等民间的日常生活如长流的细水,在波澜起伏的历史潮流中绵延,并不因为历史的巨大转折和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干预而断裂。即使在文革时期,弄堂外的政治运动已经如火如荼,而讲究的饮食起居、坊间的流言、暧昧的男女私情、冬夜的围炉夜话……这些私人性的日常生活从容避开了政治风浪的侵蚀和打击,在弄堂深处委婉曲折地潜滋暗长。《文革轶事》叙述了文革中胡迪菁、赵志国、张思叶、张思蕊等几个游弋于政治旋涡之外、避居家庭的平常男女的日常生活。其中既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致和讲究,也有为了生存的相互挤兑和算计。种种微妙的家庭矛盾和隐隐约约的儿女私情在亭子间中一步一步展开。民间在漫长历史中日积月累形成的日常生活方式具有一种恒常的稳定性,文化大革命虽然以翻江倒海的气势改变了社会生活的面貌,却改变不了上海屋檐下基本的日常生活方式。无论历史如何演变,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始终按照自己的历史惯性一如既往地向前运行。
同样以芸芸众生的平庸生活为写作对象,王安忆却回避对日常生活进行平面书写,而是把平凡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用精雕细磨的笔法去描摹和铺陈那些活色生香的世俗性生活细节,比如金丝边的细瓷茶碗、切得细细的胡萝卜丝,从中发掘生活内在的殷实、朴素的美感和绵密、悠长的韵味。王安忆的叙事语言是华丽、铺张且富于阐释性的,比如“这是来自于底层的、日常的弄堂生活,充满了人气烟火,积攒的是一种城市心境,而流言的细密绵软流淌的则是生活的琐屑与本真”。
上述这两种描摹平民生活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叙事特征,那就是其叙事的中心都是平淡的生活事件和琐碎的生活细节。程青《恋爱课》以几对平凡男女的聚散离合为叙事线索,叙述的重点却落在男欢女爱、婚丧嫁娶、吃饭穿衣、婆媳妯娌之间的微妙关系等日常性的生活事件上。徐惠照的小说“过了”普通市民梁观洲一家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新婚恩爱和夫妻磨擦、育儿的辛苦与快乐,婆媳矛盾、母子关系。而《长恨歌》则是在繁复、精细的生活细节中把握和刻画日常生活的风情神韵。王安忆的笔触常常流连于那些世俗性生活细节:粉红缎子旗袍上的绣花、在里弄中传播的嘁嘁嚓嚓的流言、叫卖桂花粥的梆子声、弄堂里夹了油烟和泔水气味的风……这些繁复、密集、可感的细节是生活的“声”与“色”,是日常生活的肌理与情态,它们释放出丰富的审美信息,让人体味到日常生活的精致、富足和安闲。上海弄堂里普通百姓吃饭穿衣、接人待物的日常生活图景也就在这些世俗性细节里徐徐展开,并获得了感性的审美形态。
二、漂泊生态的寓言式写真
在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中,乡村以其安宁和淳朴而被视为心灵的家园和精神的故乡,而文明与邪恶并存、冒险与机遇同在、竞争与挑战相伴的现代都市则不具备故乡的品格,由钢筋水泥浇铸的都市日益成为一种异己化的敌对力量。城市的现代化带来的是漂泊的心灵,失落的个人。这种漂泊既是一种居无定所、四处漂流的生存形态,也是一种失去人生方向、虚无焦虑的精神形态。
生存漂泊是九十年代城市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中国的现代化背景上,城市意味着文明,意味着改变命运的机会,更意味着一种优越的生存方式和现代化的生活形态。于是,进入城市尤其是大都市,成为城市之外人们普遍性的光荣和梦想。但是,当人们满怀梦想和热情进入城市之后,却不能被城市所接纳,只能在城市中漂泊流浪。九十年代很多城市小说以这些城市淘金者或寻梦者的故事演绎着生存漂泊的主题话语。在小说文本中漂泊着一个又一个漂泊者的身影。他们是这个城市的闯入者,闯进城市却又无法融入都市,只能以异乡人的身份在城市中辗转漂泊。肖建国《闯荡都市》中的李顺祥在喧嚣嘈杂的都市几番闯荡之后,不仅没有在城市扎下根,而且失落了所有的美好幻想,最后无比凄惶地离开了城市。《别人的城市》中的殷志寄身特区五年,亲眼目睹这个“别人的城市”把许多纯真和美好的东西无情地碾为齑粉。无奈之下,他返回家乡小镇,却发现自己成了外来人,只得再次出门打工,带着人生的破碎感继续漂泊在别人的城市。《下一站》的“我”是一个孤独又自傲的打工仔,或是炒老板的鱿鱼,或是被老板辞退,在迷茫之中飘向一个又一个的“下一站”。《宁婴》中的宁婴滞留于繁华的大上海,幻想依靠城市中的男性实现进城的梦想,她从一个男人飘向另一个男人,以堕落的漂泊形式进行着无望的圆梦旅程。这篇小说与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京飘”代表的邱华栋一直非常执著地书写着漂泊一族的故事。他的《闯入者》中的主人公吕安因为无法办理调动手续而不能被城市真正接受和容纳,他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小家来安置自己疲惫的肉体、安抚孤独的心灵,但两任同居女友都离他而去,他只能带着一个女性塑料人体模特在北京城里到处漂泊。在城市,这些寻梦者永远在路上,处于无根的漂泊状态。
在这些以生存漂泊为主题话语的小说中,城市已经不仅仅是小说的叙事空间,而是被赋予了一种人格化的内涵,它在根本上是一股强大而无形的异己力量,始终与人处于紧张的对峙和冲突之中。邱华栋在他的小说比如《城市战车》、《沙盘城市》中总是无比愤恨地把城市比喻为“吃人的老虎机”、“不停旋转的沙盘”,它抗拒人的进入,无情地摧毁人在城市中安居乐业的梦想。而小说中的主人公,作为异乡人,对于城市,始终保持着一种向往的姿态,渴望融入城市,却总是被拒之门外,于是他们不断对城市进行拥抱、追问和质疑。人与城的对峙和冲突就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内在结构。
精神漂泊是九十年代城市小说的又一主题话语。相对于生存漂泊,精神漂泊是城市漂泊一族的另一种漂泊形态。城市中物欲的喧嚣和扩张、复杂多变的生活形态的诱惑往往容易使人迷失人生的方向,精神上处于没有着落的空茫和悬浮状态。西飕《青衣花旦》就描写了一群迷途的城市羔羊。两个无所事事的男人与两个舞女都倍觉空虚和迷茫,彼此之间带有情欲色彩的相互试探也无法填充精神上的虚空。于是,在小说的结尾,四人爬上楼顶去乘凉,却发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好象正在某次航行中。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茫茫大海何处,也不知道最终的目的地”。这正是对都市中人们无所皈依的精神状态的寓言式书写。“七十年代生”作家丁天在其小说中不断渲染和突出城市年轻人精神上的茫然和虚空。《饲养在城市中的我们》里,“我们”这些年轻人,在生活中除了情爱追逐之外别无目标,整天无所事事,漂浮在生活的表层,找不到一个踏实的生活目标和确定的精神寄托。《告别年代》中的“我”试图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努力探寻活着的意义,但始终找不到灵魂的栖息地,只好让精神飘着。
为了恰当地表达主题,这类小说的叙事在无聊的、平面的生存状态上滑行,并着力于呈现这种生存状态中那种百无聊赖的情绪和感觉。这种情绪和感觉在小说文本中无处不在,弥漫在每一个场景中,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或者,我们可以说,小说叙事的中心就在于对一种空无的精神状态的描绘,而不是为了提供什么情节曲折的故事或者观赏性的生活场景。对于精神漂泊状态的出色呈现让这些小说具有了某种哲学的深度和寓言的品格,能够把人引入一种哲理性的思考。
三、白领生活的诗情表达
白领是改革开放土壤所培育出的新兴都市阶层,他们文化素质较高,有着体面的职业和令平民大众羡慕的收入,他们的生活既有优雅、精致的一面,也有商场拼搏的艰辛、情感的失落和复杂的人际关系。90年代的城市小说用一种温婉诗意的笔调来描写这个阶层别具一格的生活风光。
出现在90年代城市小说中的这群白领精明能干,才华出众,完全不同于那些终日为柴米油盐奔波和操劳的底层平民,白领女性很少有传统的依附性,往往是独立自强的职业女性甚至商海成功者,而男性大多是当今传媒所宣扬的成功人士。不过,九十年代城市小说中出现最多的是白领女性。她们气质高雅,追求浪漫的小资情调,渴望纯美缠绵的爱情,但她们又具有很强的世俗精神,追求丰裕的物质生活。如张欣《如戏》中的佳希,曾经痴迷艺术家丈夫蔡丰收,但当丰收下海从商、消泯了艺术家的脱俗气质之后,她深感失望。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既向往富足的生活,又想享有艺术的优雅和浪漫的感情。当两者不可兼得时,佳希只好向另一个艺术家匡云浓那里寻求诗意和情感慰藉。再如唐颖《丽人公寓》中的宝宝,为了安逸的生活,甘愿与富商同居,但在内心里又时时渴望纯真的爱情。
与白领阶层的生活诉求相适应,描写白领阶层的小说其故事内容也无非是职业场上的拼搏和男女情爱。温馨浪漫的爱情一直是很多白领小说的故事核心。这些小说在叙事上沿袭了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故事模式,那些女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优雅纯情、缠绵又执著的白领丽人,与她们相匹配,小说中的男主角不是温文尔雅、事业有成的白领男性就是冷峻豪侠的猛男勇夫。潘向黎的《十年杯》、《无雪之冬》和《变歌》都是演绎都市男女白领之间的爱情故事,在都市背景上展开的这些现代版才子佳人故事,洋溢着浓郁的浪漫气息,带着青春的娇媚、港台的风情,如同为了让白领的情爱故事更富有可读性,张欣《伴你到黎明》把才子佳人置换为美女和黑社会的草莽英雄,《浮世缘》还把异域风光、黑社会、都市奇遇等等惊险情节镶嵌进男女爱情故事框架中,以增加故事的传奇性。另外一些白领小说不局限于男女爱情,而是把笔触伸向较为广泛的白领生活领域,设置商海打拼和情感失落两条线索,并让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和穿插,以编织耐人寻味的故事。张欣《首席》中的欧阳飘雪与梦烟在玩具界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帮助,她们尽管在事业上都属于小有成就的白领丽人,但在感情上都始终不如意。同样《掘金时代》也是以女强人穗珠在营销界的拼杀和成功以及婚变作为故事的主体。张欣认为“文学没有轻松的一面也是很可怕的”,“都市人内心的积虑、疲惫、孤独和无奈,有时真是难以排遣的,所以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为他们开一扇小小的天窗”。(注:张欣:《深陷红尘,重拾浪漫》,《岁月无敌·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秉持这种抚慰而非教化的叙述姿态,张欣的白领小说卸下了非常沉重的文化重负,有意地化解了生活中的沉重与艰辛,在叙事中,大的结构是商场拼搏,小的情节是温情,有时候小情节甚至淹没了大结构,整个叙事流溢着一种淡淡的感伤和一抹剪不断理不乱的怅惘。
不过,白领小说最吸引大众视线的是它们对于白领阶层生活情调的渲染,对白领阶层生活方式的感性化书写。全球化语境下西方中产生活方式的耳濡目染、东方及时行乐主义的浸润熏陶以及自身的生存优势,三位一体塑造了白领阶层富足体面、潇洒优雅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白领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另一种表达。这种生活方式曾经在现代化背景下被描绘了那么久,并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消费主义潮流的引导而日渐成为整个中国日常生活的想象中心。九十年代白领小说对这种生活方式的精彩表达无疑满足了大众对中产生活方式的追慕和想象。池莉的《来来往往》、张欣的《遍地罂粟》、《此情不再》、张者的《资本爱情现在时》都用一种不无欣赏的态度书写白领阶层的生活图景。在这些小说里,那些白领男女们身穿名牌,驾着豪华轿车,潇洒自如地出入于星级酒店、咖啡厅、酒吧等富有高雅情调的消费场所。这是一种让急于奔小康的普通民众羡慕不已的生活,对于大众,它是一种诱惑,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允诺。白领小说对白领生活方式的书写因为符合大众对自己未来生活的设计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广大读者在白领小说的叙述空间中在心理上得到了一种想象性的满足。
四、另类生活的商业化书写
在九十年代日益商业化的文学语境中,在传媒的精心包装和强力宣传下,一批以“七十年代生作家”命名的新一代作家浮出了水面,并以标新立异的写作迅速吸引了大众的眼球。
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物欲”中,蔑视一切传统规范,沉迷于都市的时尚之中,本身就是城市另类的代表。在写作姿态上,他们以城市另类的代言人自居,如周洁茹所说:“我的小说就是我的生活。我关注我身边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深深陷于时尚中间的年轻人。”她们的小说依托于现代都市的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以自我的生存经验作为小说的底本,改变了经典文本的背景设置、叙事方式的审美情趣,追求一种玩世不恭、狂放颓废的写作。他们将前卫的个人经验与消费社会的物质景观巧妙地缝合起来,将城市的奢华与城市的肮脏糅合在一起,从而编织成一种奇异的另类文本。
都市的另类生活是她们小说的叙事中心。都市另类们是处于城市生活边缘、在反叛传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的一个特殊群落。这个群落包括自由撰稿人、酒吧歌手、流浪艺术家等等形形色色的他们彻底地否认和抛弃公众所认可的一切价值体系,蔑视城市的一切既成秩序和生活规范,其生活是由酒吧、大麻、摇滚乐、滥交、吸毒构成的紊乱无序的世界。这种惊世骇俗的边缘化生活方式,在卫慧《上海宝贝》、《爱人的房间》、《蝴蝶的尖叫》、《欲望手枪》、棉棉《糖》、《九个目标的欲望》、金仁顺《冷气流》、周洁茹《我们干点什么吧》、安妮宝贝《午夜飞行》、《一夜》等异常尖锐和新潮的另类文本里,有力地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怪异的生活方式如何在城市现实中生长和展开。《上海宝贝》集中展示了都市另类奇异的生活景观,揭示了这个特殊群落的精神表征。那些无业游民、外国人、艺术家们浪迹于各色酒吧和舞厅之间,喝洋酒,穿名牌,甚至吸毒和纵欲。他们虽然栖居在都市的阴暗角落,但却享受着城市最为前沿的时尚生活。他们拒绝庸俗,渴望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冒险,在狂热混乱的生活和高强度的感官刺激中寻求令人晕眩的生命快感。生命的狂欢过后,他们又倍感空虚和疲倦。这是消费社会浇灌出的盛开在都市下腹部的“恶之花”。与《上海宝贝》接近,棉棉的《糖》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毫无保留地书写那些新奇乖戾的另类生活经验:自杀、酗酒、吸毒、滥交。在小说中,那些流浪艺人具有鲜明的反社会倾向,行为乖张,特立独行,他们拒绝正常人的世俗生活,他们生活在自己所命名的白天和黑夜之间,在迷乱、失控、破碎的异端生活中自我放逐。不独上述两篇小说,几乎所有的另类文本都以极端感性的笔调细致描绘怪异的另类生活场景。
作为在消费主义浪潮中涌现出来的写作群体,这些另类作家还喜欢用影象化的方式来呈现现代消费社会的景观。他们把现代大都市那些最具有消费性的空间,比如恍惚迷离的酒吧、喧嚣刺激的迪斯科舞厅作为人物的活动空间。酒吧是另类作家由衷热爱的书写空间,酒吧在他们的小说中甚至成了另类生活方式的超级象征符号。酒吧在《像卫慧那样疯狂》是一个昏暗的、感官的、疯狂的、无法自持的空间:“一律是灯红酒绿,满屋子的烟雾,香水味儿,女人的眼风,黑发红唇或红发黑唇的时髦女人,加一打或温柔如水或冷酷如铁或愚蠢得要命的男士,在黑灯瞎火里推推攘攘、拉拉扯扯、吱吱呀呀,连酒吧最角落里的老鼠都周身洋溢着颓废、糜烂的气息。”酒吧在棉棉那里呈现出另一种怪异的风格:“是大麻的气味,非洲音乐、闪着荧光的发辫,冻女人热啤酒、冻啤酒热女人。”酒吧弥漫着颓废、堕落、迷幻的气息,闪耀着古怪的光芒。除了这些消费性的物质化空间,那些修辞性很强的著名品牌作为消费社会的象征符号也频繁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上海宝贝》中点缀着七星牌香烟、吉列派剃须刀、CK香水、“三得利”派汽水、“妈妈之选”牌色拉乳等等著名品牌的生活用品。安妮宝贝的小说中也一再出现cappuciono牌咖啡、青草味香水、日本著名品牌的棉布衣服。可以说,另类作家们“制造出一套全新的消费社会的符号象征体系”(陈晓明语)。
在话语形态上,这些另类文本也叛离了传统的文学叙事方式。它们不侧重讲述完整的故事,也不注重经营明晰的情节,而是将一些缺乏内在联系的生活碎片和表象拼贴、粘连在一起。如在棉棉《糖》把吸毒、淫乱、同性恋、死亡等等耸人听闻的生活表象和事件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叙事不停地在这些生活表象之间跳跃和切换。卫慧《爱人的房间》只有模糊的生活片段、暧昧的人物形象,传统文学中的那些明确的叙事因素在这里通通消失了。这种叙事方式,一方面瓦解了叙事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使整个文本显得松散零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主题话语的杂糅和文本意义的弥散,每一种生活表象似乎都能够支撑起一种主题,但各种生活表象的拼贴就使整个文本的主题成为欲望、罪恶、时尚等多重主题的杂糅,而所谓的文本意义不过就是一系列生活碎片纠结在一起呈现出来的含混的性质。此外,另类作家们的叙事资源基本上来自于个人的生存经验。叙事资源的贫乏使得他们的写作往往陷入自我重复和彼此相仿的尴尬境地,堕落进模式化的陷阱。棉棉的《糖》、《啦啦啦》、《九个目标的欲望》基本上都是在叙述“我”和“赛宁”的大同小异的故事。在赵波《萍水相逢》、《异地之恋》讲述的都是一对邂逅的陌生男女之间发生的勾引和抗拒的故事。卫慧和棉棉的小说在人物形象、背景设置等方面具有雷同的倾向,有相互抄袭的嫌疑。
另类作家把西方以艾伦·金斯堡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当作精神教父,但是他们的写作与“垮掉的一代”有着本质的不同。“垮掉的一代”的写作“掀开了美国当时社会百般掩抑的腐烂的肮脏”,(注:黄发有:《激素催生的写作——“七十年代人”小说批判》,《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具有真正的社会文化反叛深度,而另类作家的叛逆与历史的宿命和现实的苦难无关,“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真正的反叛的锋芒和批判的力量”(注:彭卫鸿:《论新生代作家的后现代性迷失——以卫慧、棉棉的小说为例》,《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而且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和大众传媒的炒作中蜕变为一种矫揉造作的表演,一种哗众取宠的媚俗姿态。他们在传媒的暗示和名利欲望的驱使下,在写作中真真假假地暴露着个人的隐私,有意识地放大和堆积那些肉欲化、物欲化的经验,以迎合大众的阅读趣味、充分满足大众的猎奇和窥视的欲望。这样,另类生活景观成为她们文本的最大卖点。他们的小说,他们在小说中反复渲染的反主流的另类生活方式也因此而成为“当代消费社会的时尚潮流的一部分”(注:陈晓明:《无法深化的自我与现实——近期小说的审美意识流向》,《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