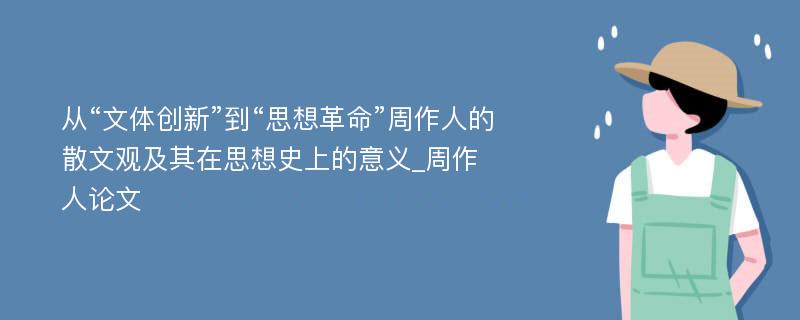
从“文体革新”到“思想革命”——周作人的小品文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品文论文,文体论文,思想史论文,观念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11-0119-08
一“传统”:一个全息的文化概念
周作人的美文写作涌动着他对现代欧美文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不满与反抗。①然而,这一文化努力在当时中国的阅读界,不但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反而存在着相当的误读——当周的批评者从他的美文中读出一种隐士的态度,因而批评其文化、政治立场的后退、落伍时;②而当他的支持者同样从这一批作品中读出一种平淡冲和的西方绅士气度时,他们就都将美文解读成了一种缺乏反抗力量的唯美的呓语。这与周这一批作品的文化指向,相距颇远。1924年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的时局更趋复杂与紧张,因此,在经历了一波高潮以后,周作人的美文写作差不多戛然而止。此后虽也仍有所作,但那都是一些零星的行为了。到1929年写三礼赞、1930年写草木虫鱼系列,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局面,就又有变化。此时周的上述散文虽仍作闲适貌,但文中已颇多讽刺之意。这折射出他对现实时事的曲折的关注与反抗,文风更接近于1921年的《碰伤》,而与1924年的那一批美文作品,显示出了相当的距离。
于是,周作人终于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反现代派”作家。对他来说,一个深刻的矛盾在于,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批评,仍在他现代性追求的整体立场之内。正是这样,当传统成为一种批判现实的构成性力量时,他事实上就处于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之中,即他一方面要在现代性追求的整体目标内对传统有所限定,从而防止某种力量——形形色色的社会“正统”思想与歧见——在现代社会“故鬼重来”;另一方面,对于那种以现代欧美国家为范型的现代化模式,他同样要区分其中非理性的部分,以防止现代中国社会进入到另一种偏枯之中。这样,在周作人,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其现代化的文化诉求之间就不是截然对立,而存在着一种相互调校的文化互动关系,即以现代化的整体立场清理传统,又以传统修正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在周作人的文化立场中,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并不表现为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混融在了一起。
这样,当周作人借助美文写作而致力于探索一种“生活的艺术”,即以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来“建造中国的新文明”时,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就既不是西方模式的简单翻版,同时也不全是中国传统的自然演进。对他来说,传统与西方,都各有其需要克服的缺陷,也都各有其值得吸纳的因素;而若从一种“大人类主义”③的立场出发加以考察,则存在于东、西方文明中的这样一种缺陷或光辉,其实又是无所谓东西的。比如对中国“正统”(作为传统的一个部分)思想的批评,在周作人,或正是其批评现实(包括以西方现代面貌出现的现实)的表达方式之一;而他赖以批评中国文化正统或西方欧美文明的思想武器——一种包括中国民俗文化在内的非正统的传统,也正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构成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周作人消除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界限。这为他后来转身传统,通过对传统的重新阐释(或梳理晚明小品散文的历史,或从中国明清时期的笔记文字中寻找自己散文的写作材料)来实现其“再造文明”的时代梦想,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
由此,1924年以后,周的美文写作虽然消沉下去,但他在美文写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立场,并没有湮没不明——借助于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周作人曲折然而持续地发表着他对现实的批评。这成为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别一种表述。即以文学而言,经由美文写作(它的题材处理、风格锻造等等),周一方面将中国现代文学的源流追溯到了明清时期的小品散文;另一方面,在这样一种史的勾勒中,他将自己的关注点从日常生活的趣味描述中转移出来,而突出强调了一种以现代个性论为基础的反抗精神及其脉络。这样一种转移内应于1927年前后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状况,它说明,在一种更为严酷的思想环境下,周作人的关注焦点,也由美文时期的现代性反思,转移到了对于中国文化道统——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道统,更是指受这一思想影响的形形色色的现实,包括以西方现代面貌出现的现实——的批评。这就是说,借助于对晚明小品散文的史的勾勒,周将文学的反抗/抒情特性,扩展到了思想的领域。正是这样,1925年以后,当周的批评者鉴于革命氛围的日益浓烈而批评他似乎更为保守的文化立场时,我们还需看到,在周作人,当他大力张扬晚明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创作时,他的思想关注其实并非是在“晚明”或“小品文”,而是要借助于这样一种史的归纳与阐释,来实现他批评现实的文化目标。
二“小品文”:从“文体”借鉴到“文学史”考察
对周作人来说,晚明小品散文最初是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出现在他的文学视野里的。当他试图以一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表述来实现其对于日益物化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时,晚明小品散文的题材处理与写作风格,就具有了借鉴的意义。周对于晚明小品文的喜好事实上很早,这从他最初的日记中就可以看出:
(戊戌年二月初五日)上午食龙须菜,京师呼豌豆苗,即蚕豆苗也,以有藤似须故名。每斤四十余钱,以炒肉丝,鲜美可啖。
(己亥年正月十五日)晴,早起……午至调马场,坐兜轿行山中,过一岭约五百级。下山行一二里,过一溪,径丈许。舁者赤足而渡,水及骱止。下有圆石,颗颗大如鹅卵,颇觉可观。再行二里始至。一路鸟语花香,山环水绕,枫叶凌霜,杉枝带雨。倘得筑以茅屋三椽,环以萝墙一带,古书千卷,同志数人,以为隐居之志意(按,“志意”二字,钟叔河校以“地”字),而吾将终老乎其间。墓前刺柏数株,子离离然,撷得六枚,擘而嗅之,香烈无比。傍晚归家,食圆子。④
这样的内容与风格,在周作人到南京读书前的日记中,是较为普遍的,其笔调明显带有晚明小品的风味。这透露出他对晚明小品文的早期接受,即对一种以生活趣味为中心的文学内容与风格的偏爱。
然而在20年代初期,当他将这样一种散文体式纳入到美文主张中来的时候,对这种散文内容与风格的强调,就已经融有他对“人类正当生活”的追求,即对于一种建立在个性与趣味基础之上的精神生活的重视。从这一点讲,周对晚明小品散文的认识,已经超越了传统名士风流的文化范型。1924年以后,当他的美文写作开始消沉,他对晚明小品散文的关注也就由一种文体上的借鉴转向文学史的考察。到这时候,周作人文学视野里的晚明小品文及其作者,相应地,也就由一种对于精神生活的强调,转而凸显“个性”对于“统制”的反抗;即其批评的重心,由现代欧美文明的制度、物化发展趋向,转向一种思想上的禁锢。在关于晚明以来小品散文的历史描述中,周作人勾勒出了两种文学力量的对抗——“言志”对于“载道”的反抗。这是个性对于统制(划一)的反抗。在这样一种描述中,周赋予一种非正统的传统以现代的意义。
不妨先来看看周氏本人在这一方面的相关言论。1926年5月5日,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周即说:“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般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⑤
将中国现代散文的源流追溯到明代公安派、竟陵派以至苏东坡的文学传统之中,周的目的并非是要从中提倡一种名士风流的习气;⑥而在于,在这样一种文学中,他看到了“言志”文学观对于“载道”文学观的反抗。在周作人,这既是作家个性的展露,同时也是作家突破礼教控制、保持一种独立姿态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与前提。由此,与此前的美文写作相比,周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考事实上就更为深入。在美文写作中,周的理想是以个体精神的自由自足来作为他“人类正当生活”的具体诉求之一;而在1925年以后中国社会局势的影响下,当他将自己的注意力日益转向对晚明小品文作史的考察时,他就更进一步地想要构建一个以原子式个体为价值核心的社会秩序,即从个体出发,来重新界定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关系。对这种关系的重新确认,当然仍在他对“人类正当生活”的思考范围之内,但无疑,随着社会局势的日趋复杂,这一思考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如果说,在此前的美文写作中,他更为关注个体内在的精神生活,那么现在,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形势下,他除了要兼顾内在的问题,更要触及个体与社会外部交往的诸多问题。更进一步说,对个体与社会外部交往原则的重新界定,或正是周作人确保其理想中“人类正当生活”的必要前提,是他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想延伸之一。
正是这样,周作人对这一文学脉络的梳理,以及对在这一文学脉络之下的作家/作品的评述,就并不完全是文学的,而更有其文化上的考量。比如苏东坡,在林语堂的眼里,这位被称之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乐天派”,其“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⑦但在周作人的论述中,苏却仍在“韩愈的系统之下,是载道派的人物”,“他的作品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模拟古人的”,只有“另外的一小部分,不是正经文章,只是他随便一写的东西,如书信题跋之类,在他本认为不甚重要,不是想要传留给后人的,因而写的时候,态度便很自然,而他所有的好文章,就全在这一部分里面”。⑧这样,周对苏的推崇,就只在其“书信题跋”一小部分的文字。在周看来,这一部分文字,一方面“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⑨;另一方面,虽有艺术的情致,却常常受到古文正统的歧视与压制,个中的原因,周氏认为“大抵总在意思的圣凡之别,为圣贤立言的一定是上品,其自己乱说的自然也就不行,有些敝帚自珍的人虽然想要保存,却也只好收到别集里去了”⑩。在这样的考察中,一种文体上的歧见与观念上的压制,联系在了一起。这里,假如我们纯从文学的角度考虑,那么,“载道”的文学当然不是每一篇都坏,而抒情的文学也未必篇篇都好;但周的关注点显然不在这里,当他从苏轼的诸多文字中特别拣出“书信题跋”的部分加以表彰,并将它与古文的流脉对照着观察时,就已经内在地包含了打破中国传统文体观念中的“上下身”(11),并借此反省造成此种文学现象的深层原因的意图。这就势必牵涉到他对中国文学道统(“为圣贤立言”)的合法性质疑,隐藏着他对思想、言说自由的维护与肯定。
对于袁宏道的看法也一样。周作人对袁中郎的表彰也有其侧重。1934年,在《重刊〈袁中郎集〉序》中,周即认为,中郎的著作“不见得样样都好,篇篇都好”;而他所以欣赏中郎者,主要在其反对模仿的文学主张,认为“中郎的诗,据我这诗的门外汉看来,只是有消极的价值,即在他的反对七子的假古董处”,“中郎反抗正统的‘赋得’文学,自是功在人间”。(12)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氏并说:“我们不能拿现在的眼光,批评他的‘优人驺从,共谈雅道’为有封建意味,那是时代使然的。他的反对模仿古人的见解实在很正确。模仿可不用思想……”(13)模仿,如果仅仅是指创作技法上的借鉴或吸收,那并不是一件坏事。然而在中国的古文传统中,模仿是和“文以载道”的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唐代的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而韩愈自己在《答刘正夫书》中也认为:“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俱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14)这样一种文学主张在明清文学中有更进一步的推演。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即引方苞“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姚鼐“不能发明经义不可轻述”的话为证,揭示了桐城派散文内在的实质与趋势,并评论说:“唐宋八大家虽主张‘文以载道’,但其着重点,犹在于古文方面,只不过想将所谓的‘道’这东西放进文章里去作为内容罢了,所以他们还只是文人。桐城派诸人则不仅是文人,而且也兼作了‘道学家’。”(15)在这样一种文学统系中,当文章仅仅是作为“贯道之器”的工具而存在,而“道”又权威并普遍地存在于古代的经典中时,学者对古圣先贤的膜拜就不可避免,由此主导下的文学主张,就内在地具有一种复古的倾向,“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类口号的提出,特其极致耳。在这样的前提下,模仿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行为,而更表现为一种思维方法与价值选择;而反对模仿,也就具备了破除这样一种思维方法与价值选择的文化功能。在周作人,当他引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中的话“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16)来批评一种因袭的流弊,说“代圣贤立言,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17)时,他所要批评的,也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上的弊端,而还直指与这种弊端紧密相连的思想上的奴隶根性。在《论八股文》中,周即敏锐地指出:“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18)在这样的观察中,文学上的模仿和思想上的奴隶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周作人所极其警惕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当他从中郎的文字中读到一种反对文学复古的言论时,他所感到戚戚者,恐是在这样一种文学状态中,作家可以从文学“道统”(奴隶性)的控制中摆脱出来,而保持个体思想的独立与自由。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周作人读出了公安派文学反抗礼教的态度。
从这样一条脉络下去,我们再来看周作人关于晚明小品散文的论述,就会发现,他的主题差不多全集中在这一文学的“反抗性”之上。在写于1926年11月5日的《〈陶庵梦忆〉序》中,周作人认为,“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19);1928年11月22日,在《〈燕知草〉跋》中,他再次强调,“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20);而在写于1930年9月21日的《近代散文抄序》中,周更直言:“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21)。在这样一些意见的基础上,1932年,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即将一部中国文学(散文)史概括为“言志”与“载道”“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的交替起伏,在社会动荡的时候,“文学上也没有统制的力量去拘束它,人人都得自由讲自己愿讲的话,各派思想都能自由发展”,所以能够酿成文学言志的潮流,而一旦社会统一稳定,“思想定于一尊,儒家的思想统治了整个的思想界,于是文学也走入了载道的路子”。(22)
这样,周作人对晚明小品散文作史的梳理的“主题化”嫌疑就很明显了,而他从事这项工作的思想意图也因此而更加清楚。在周作人,他所以花偌大力气来勾勒这样一个文学传统,其目的就不但是要将这样一种散文写作,置于“古文”的对立面来加以观察,而且更要借此提炼出一种反对文学“道统”控制的思想质素,从而维护个体自身的独立与价值。从这样一个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周作人以“抒情言志”的文学传统和“文以载道”的主张相对立,其目的就不完全在于文学本身,还牵涉到了他对中国文化与现实的批评,以及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正是这样,对于周作人的这样一种文学史架构,我们不能仅从文学本身出发加以评述,否则,我们与周从事的这项工作之间,或多或少地会存在一些隔膜。(23)朱自清在《诗言志辨》的《序》中曾委婉地批评说:“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现时却变得和‘载道’对立起来。”(24)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朱的辨析是有道理的。但周的意见其实更侧重于思想的方面,正是这样,他后来回应这种志道纠结的言论说:“我这言志载道的分派本是一时便宜的说法,但是因为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话,仿佛诗文混杂,又志与道的界限也有欠明了之处,容易引起缠夹,我曾追加地说明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25)这就是说,在“言志”与“载道”二分的文学架构中,周作人强调的是思想言说/文学表述的自主与自由,而并非纯文学地讨论“诗言志”或“文以载道”的内涵。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下,在公安派的创作中,周作人看到了“真实个性的表现”:“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个性的表现。”(26)这是周作人理解中的公安派作家及作品的现代意义。而当他将中国现代散文的源流追溯到这样一个传统中来的时候,他所要赋予中国现代散文,甚至整个现代文学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真实个性”的品性或内容。这就使他的文学史研究融入了思想的要素。
三 现实的指向:在“革命文学”的参照下
这样,在1926—1932年间,周作人之所以花这般力气来勾勒这样一条文学发展的脉络,从“言志”与“载道”的分立中强调一种“真实的个性”,并由此凸显文学的反抗力量,其背后的推动力量,大半不在他对晚明小品散文的欣赏,或者出于一种理论的兴趣,而更是基于其间中国社会政治、文学的演变,以及他对处于这一变化中的知识分子自身使命的理解。在这一立场的背后,隐含着他与“革命文学”主张的分歧。
也许并不仅仅是一个巧合,1925年以后,不但周作人的美文写作开始消沉,而且,整个中国文学界、思想界都在酝酿着一种变革。舒衡哲认为:“1925年之前,知识分子自视他们及其所从事的启蒙运动是‘时代精神’的体现。1925年以后,他们则越来越迷惘于响应‘时代的需要’。”(27)这里无论是“时代精神”或“时代的需要”,其实都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救亡的主题紧密相连:当启蒙者试图以伦理的自觉来为政治的自觉奠定一个基础时,他们收获的是对自身文化工作的一种自信;而一旦当这样一种文化逻辑在现实(如“五卅惨案”)面前遭遇挫折,对启蒙的反省也就不可避免。这就是说,“启蒙”的“救亡”不力,为“革命”方案的形成预留了空间。
这样一种变化在当时就被一些作家敏感地表达出来(28)。以茅盾为例,他的《蚀》(1927—1928年)三部曲描述了一批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者在现实面前的幻灭,而在随后的长篇小说《虹》(1929年)中,“五四”方案(婚姻自由、突破传统家庭的束缚等等)不但没有解决女主人公梅行素的个人问题,反而在她追求新思潮的过程中,见证了新思潮在日常生活中的异化。在这个作品中,作者通过对一些号称受到新思潮影响的新人物的描写,事实上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实成效作了有力的反省;而最后,只有当梅女士决心投身革命,“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并汇入到“五卅”游行群众的队伍中时,亦即只有当她从“五四”文化启蒙的方案转向革命的方案,并将她自己个人的命运融入到时代、集体的命运之中时,她自身的个人问题才得以解决。这折射出作家本人对于革命的态度与期望。(29)
从1925年开始,周作人的思想也由原先的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在这一年的《元旦试笔》一文中,周作人反省自己的思想历程,说:“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从这一点来看,周的思想似乎和当时普遍的革命热情正是相一致的,然而仔细分辨,两者之间仍有相当不同。罗志田认为,“(过去的研究)说到民族主义多想到其因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在民国之前,若不计同盟会等反满的民族主义,这大体是不错的。但民族主义从来就还有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一面”(30)。这就是说,自晚清迄20世纪20年代(实际上也可以放大到整个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直是和国家主义的立场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一种思想情形,周作人在当时显然就已经感觉到了。就在那篇《元旦试笔》的文章里,在强调了民族主义之于当时中国的意义以后,周紧接着特别分辩说:“我不相信因为是国家所以当爱,如那些宗教的爱国家所提倡,但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却是正当,而且与更‘高尚’的别的主义也不相冲突。”(31)这样,和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义不同,周提醒读者,他的民族主义仍然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
这就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更多地呈现出与“五四”思想革命相贯通的一面。对周作人来说,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像国家主义者所提倡的,将个人的命运普遍地纳入到国家的命运之下来加以考虑,从而凸显阶级、集体的力量(如茅盾在《虹》中所主张的);而仍然需要通过个体文明程度的提升,来为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基础。“五卅事件”以后,周作人写了《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开头即说:“关于这回上海英国人的行凶事件,我们十分愤慨,因为他们不拿中国人当人。”当朱自清以普泛的“他我你”来指称每一个中国人,并热血沸腾地号召未亡的中国人“起哟!起哟”时,当钱杏邨们通过“五卅运动”看到阶级觉醒的力量时,周作人所关注者,却仍然是他早年所提倡的“人”。由此,对于“五卅事件”,他的反省颇显冷静。他“一方面希望国人自省,切勿像英国那样不拿别人当人”,另一方面“又希望国人更进一步,切不可再不拿自己当人。我在路上看见学生慷慨激昂地讲演,同时却有两脚小得将要不见了的女人和从脸上可以看出他每天必要打针的男子从旁走过,我就不禁脊梁微冷。自己糟蹋到了这个地步,哪里会有力气反抗”?这样一种观察视角,无疑与他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主张具有一种连贯性。这使周作人得出不同于主流言论的结论:“我们如不将这个拿自己当奴隶,猪羊,器具看,而不当做人看的习惯改掉,休想说什么自由自主,就是存活也不容易,即使别人不来压迫我们,归根结蒂是老实不客气地自灭。”(32)三天以后,在《文明与野蛮》一文中,周更明确地说:“我希望中国人能够顿悟,忏悔,把破船古炮论斤的卖给旧货摊,然后从头的再设制造局练兵处,造成文明的器与人;从头的办学堂,养成厉害——而真是明白的国民,以改革现今的文明。”(33)
在这样的思路下,周作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事实上就仍然未能脱离他早年所倡扬的“人的文学”的主张,此时“真是明白的国民”的养成与彼时所主张的“人类正当生活”,其实仍有其内在的思想关联性,即通过个人的自觉来求得民族的自立。在周作人,被奴役的二等国民自然不能构筑起“人类正当生活”,但如何摆脱这种被奴役的二等国民的状态,其途径除了“从头的再设制造局练兵处”,还有赖于“真是明白的国民”的养成。前者属于军人,而后者却正是知识者的责任。在这样的前提下,周作人对于“国耻”的理解有异于常人:“我想国耻是可以讲的,而且也是应该讲的。但是我这所谓国耻并不专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的羞耻。这样的耻辱才真是国耻”,“我并不说不必反抗外敌,但觉得反抗自己更重要得多,因为不但这是更可耻的耻辱,而且自己不悔改也就决不能抵抗得过别人。所以中国如要好起来,第一应当觉醒”。(34)在这样一种思想关联之下,面对时代危机,他所开具的药方,其着力点就仍然落在个体文明程度的提升,即个体社会观念的现代化之上(此所谓“社会观念的现代化”,并非是说论者单向度接受某一种西方的社会观念,而是指论者思想通达;而思想上的通达与否,周氏后来又常从“人情”、“物理”两个方面来加以考量)。所谓“真是明白的国民”的养成,其途径一方面要求革除中国人中的“西崽气与家奴气”,另一方面也还“应该竭力发掘铲除自己的恶根性”。周认为,只有这样,“才有民族再生的希望”。(35)由此,与革命的价值取向不同,周作人的解决方案是:“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36)这样,绕了一个圈子,周作人的关注又回到“建造中国的新文明”这一核心上来——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应因于时代提出的问题,周作人仍然希望以“新文明”的建设,亦即中国社会的文明/现代化转型,来为汉民族的重生,提供最基本的文化养料;而这个“新文明”的建成,仍然建立在“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的基础之上。
这为1925年以后周作人观察中国社会的局势提供了一个基点。面对日益严重的外患,周的主张仍然建立在个体自我改造的基础上,并使他对一种以公众人数为政治、思想正当性之基础,即以“公意”(37)为价值取向之衡定的思想主张,持有一种警惕的心理。(38)在周看来,假如缺乏个体层面的理性自觉,即其所谓的“思想改造”方面的工作,那么,基于情感的群众运动——包括革命——将很可能演变成为一种“狂信”。这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有可能酿成一种思想上与政治上的不宽容,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压制。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周作人即明确提出了他的担忧:“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39)而要消除“狂信”,培植一种健全、理性的思想根基,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从这样一个脉络来看,在周作人,对“言志”文学观的梳理,实则隐含着他对现代知识分子自身使命的强调与认识。当他在晚明小品的梳理中突显个性对于礼教的反抗,对晚明文人与小品散文的言说,也就成为他观察社会现实的一个载体。对周作人来说,历史并不仅仅代表了过去,还表征着当下。当他觉得中国的思想问题仍然在于道统与八股时,他就愈强调论者的个性自由,反对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特殊利益之间的截然对立。在他看来,这恰是中国民族主义得以成立的一个基础,即他的民族主义立场既不表现为简单的排外主义,也不表现为文化上的复古主义,而恰恰建立在“思想革命”的基础上。由此,在周作人的文学史观中,我们读出了与20世纪中国流行的公理世界观迥然不同的文化指向与内涵。
注释:
①关于周作人美文的反抗性,笔者另有《脉络与关注:周作人的美文写作及其文化意义》一文加以阐释,此处不予展开。
②这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杰的《周作人论》(1934年)。在这篇文章里,许引周氏《乌篷船》中的文字,并也注意到周“很显然的表现出对新兴资本社会的厌恶”;但由这一个前提,他得出的结论却是周“对封建社会的恋慕的情绪”,“这种恋慕封建文化的精神,再出之以士大夫的绅士的态度,于是乎,他的趣味的主张,悠然忘我的心情等,便从此出来了”(孙郁、黄乔生编:《回望周作人:研究述评》,第8—9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③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见《艺术与生活》,第2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④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第2—3、36—38页。引文标点由引者添加,下同。按,关于周作人早期的日记,另可参阅周作人《旧日记抄》一文,收《风雨谈》,第152—16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⑤周作人:《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见《周作人书信》,第8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⑥而这,恰恰是当时评论界对于周的普遍认识。陈子展在《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一文的开头部分即说:“书架上不摆部把公安竟陵派的东西,书架好像就没有面子;文章里不说到公安竟陵,不抄点明人尺牍,文章好像就不够精彩;嘴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不读点小品散文之类,嘴巴好像就无法吐属风流;文坛上这个时髦的风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什么人开头……这才说出这一风气是从知堂老人开头的。”(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其文其书》,第21页)
⑦林语堂:《苏东坡传》,第5—8页,张振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
⑧(13)(15)(16)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21、24、40、2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⑨周作人:《周作人书信·序言》,第1页。
⑩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自序》,第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1)1925年2月,周作人曾写过一篇题为《上下身》的文章,说“人的肉体明明是一个整体”,而“吾乡的贤人必强分割之为上下身”。“上下本是方向,没有什么不对,但他们在这里又应用了大义名分的大道理,于是上下变而为尊卑,邪正,净不净之分了”(《雨天的书》,第7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中国传统的文体观似乎也存在着类似的区隔,载道的文学为上、为尊、为正、为净,而那些抒情的小品则为下、为卑、为邪、为不净。
(12)周作人:《重刊袁中郎集序》,见《苦茶随笔》,第57—5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4)李汉:《昌黎先生集序》、韩愈:《答刘正夫书》,皆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第121、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7)这是清许善长《碧声吟馆谈尘》卷四《论八股》中的话,周作人说它是“八股时文的特色”,并进一步追问:“现今有多少人不是这样的?”(周作人:《关于命运》,见《苦茶随笔》,第112页)。
(18)周作人:《论八股文》,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附录一,第63—64页。
(19)周作人:《陶庵梦忆序》,见《苦雨斋序跋文》,第115页。
(20)周作人:《〈燕知草〉跋》,见《苦雨斋序跋文》,第124页。
(21)周作人:《近代散文抄序》,见《苦雨斋序跋文》,第126页。此文原题《〈冰雪小品文〉序》,收入《苦雨斋序跋文》时改题《近代散文抄序》。
(2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18—19页。
(23)在已有的研究中,木山英雄曾注意到周氏兄弟散文的“非文学性”。在《实力与文章的关系——周氏兄弟与散文的发展》一文中,作者说:“我只想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散文的界限向广阔的非文学方面展开着;另一个是在文学内部成为各种文学样式之根底的文字语言具有最融通自在的形态。总之,大概是由于散文的这种性格,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的鲁迅和周作人的文学意识,在纯粹性和老狯性之间的振幅之大上极为出类拔萃。这里,要通过散文的问题来理解中国文学的时代与性格的某个方面,就需要尽可能自由地观察,在文学论上即使有些模糊不清也罢。”(《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70—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在讨论周作人关于“言志”与“载道”的文学史架构时,我们似乎更应注意到这种“广阔的非文学”的面向。
(24)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见《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130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2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729—730页。
(26)周作人:《〈杂拌儿〉跋》,见《苦雨斋序跋文》,第117页。更有意味的是,1935年1月15日,在《厂甸之二》中,周作人针对当时批评中郎的声音,说:“近来袁中郎又大为世诟病,有人以为还应读古文,中郎诚未足为文章模范,本来也并没有人提倡要做公安派文,但即使如此也胜于韩(按,指韩愈)文,学袁为闲散的文士,学韩则为纵横的策士,文士不过发挥乱世之音而已,策士则能造成乱世之音者也。”此更可见周对公安派文学的关注,并不仅仅在于文学本身(《苦茶随笔》,第28页)。
(27)[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177页,刘京建译,丘为君校订,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关于1925—1927年之间中国思想界的变化,这部著作的第四章《革命运动的严峻考验:1925—1927》(第169—227页)有较系统的考察,可参阅。
(28)这在当时的一些评论中已有明显的反映[钱杏邨:《〈英兰的一生〉》(载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太阳月刊》创刊号,收入《“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第70—71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原载1927年1月16日《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5期,收入《“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第16页)、郭沫若:《革命与文学》(收《“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第10页)等]。
(29)这样一种思想转变,在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朱自清身上也有体现。相关分析参阅[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171页。
(30)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自序》,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1)周作人:《元旦试笔》,见《雨天的书》,第127页。
(32)周作人:《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原载1925年6月20日《京报副刊》,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207—20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3)周作人:《文明与野蛮》,原载1925年6月23日《京报副刊》,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215页。
(34)周作人:《代快邮》,见《谈虎集》,第109—11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另外,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在这篇文章里,周讨论的“国耻”当然是中国的国耻,但若从“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的羞耻”的前提立论,那么,“像英国那样不拿别人当人”的国家,其实又何尝没有“国耻”呢!
(35)从这样的思想逻辑来看,贺凯的观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敏锐性。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贺凯认为:“‘五卅’到一九二七,中国的社会已在转变,中国的革命已在向新的方面发展,而周作人仍然肩着‘五四’时代思想革命的旗帜,钻在‘趣味’里写他的悠闲清淡的‘小品’”(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研究述评》,第25页)。1925年以后,周的思想虽然由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但支持其民族主义思想内核的,确实仍然是“思想革命”的立场,因而延续了其在“五四”时期的文化立场。在这一点上,贺的观察是敏锐的。他的问题只在于,1925年以后,周“悠闲清淡”的小品文(美文)写作事实上已经消沉下来;而即使是那一批美文作品,周也别有其文化上的批评指向,对这一基本事实的忽视,导致许多评论家对周的文化定位发生偏差。
(36)周作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见《雨天的书》,第111—112页。
(37)“公意”(general will)是卢梭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又被翻译为普遍意志、公共意志、国民总意或公同。这一概念在晚清引入中国,五四期间开始流行。相关介绍参阅许纪霖:《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政治正当性》之第四节《政治的精神:个人、良知和公意》,见《中国社会科辑刊》2009年秋季卷(总第28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8)这样一种认识也基于他对义和团运动的观察。参阅周作人:《关于〈胡进士的传单〉》(原载1927年6月4日《语丝》第134期,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114—115页)、《读〈京华碧血录〉》(原载1924年6月2日《晨报副镌》,收入《雨天的书》,第185—187页)诸文。
(39)周作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见《雨天的书》,第111页。
标签:周作人论文; 小品文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革命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美文论文; 散文论文; 思想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