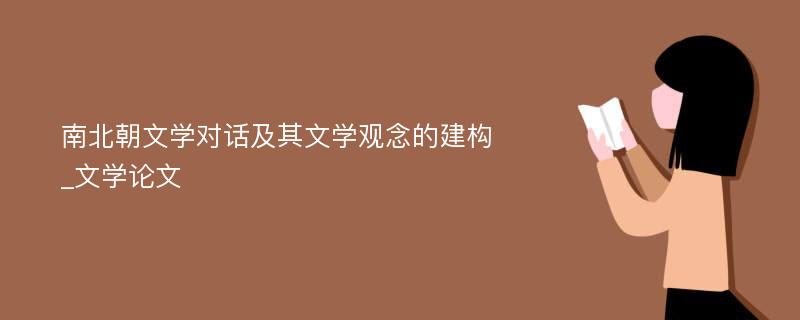
南朝与北朝的文学对话及其文学观念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朝论文,南朝论文,文学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批评史上,南北朝是一个大分裂与大融合的时期,是唐宋辉煌灿烂的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础。这个思想文化分崩离析的时代,最终通过对话与其他途径的建设,不仅在新旧之间找到契合点,而且在地域和文化的融合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境致,这是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的最大收获。南北朝的思想文化融合影响到文学批评方面,便是对文学观念作了新的调整与拓展,进而影响到唐代文学观念的构建。
南北文学首先是在中华文学传统基础之上展开和演绎的。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中分析北朝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轨迹时先叙述汉至西晋以来文学发展的盛况:
汉自孝武之后,雅尚斯文,扬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马、王、扬为之杰。东京之朝,兹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张、蔡为之雄。当涂受命,尤好虫篆。金行勃兴,无替前烈。曹、王、陈、阮负宏衍之思,挺栋干于邓林;潘、陆、张、左擅侈丽之才,饰羽仪于凤穴。斯并高视当世,连衡孔门。虽时运推移,质文屡变,譬犹六代并奏,易俗之用无爽;九源竞逐,一致之理同归。历选前英,于斯为盛。①
作者强调这种文学兴盛是中华文学传统的演变所致,对魏晋以来的文学持肯定与赞同的态度,这与北朝时苏绰与李谔等人的保守观念有所不同。作者从中原动乱引起文学分裂与变化的角度,谈到北朝文学的发展脉络,依照他的分析,北朝文学的展开与南朝的对话交流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是草创阶段。作者谈及北朝文学此阶段时,首先从中原动乱引起南北分裂始,“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指出西晋末年之后,中原板荡引起五胡乱华,战乱中,虽也有一些作者挥翰而作,“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以致“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故而在文体上重视章奏符檄一类,而体物缘情之作则无暇顾及。第二阶段为兴起阶段。及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汉化的过程才开始,南北文化的大规模融合达到新的阶段。《北史·文苑传》亦分析了这时期文学兴盛的特点: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泉源,言多胸臆,润古雕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岁年,未闻独得。既而陈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畴类,稍革其风。及明皇御历,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也?于时陈郡袁翻、翻弟跃、河东裴敬宪、弟庄伯、庄伯族弟伯茂、范阳卢观、弟仲宣、顿丘李谐、勃海高肃、河间邢臧、赵国李骞,雕琢琼瑶,刻削杞梓,并为龙光,俱称鸿翼。乐安孙彦举、济阴温子升,并自孤寒,郁然特起。咸能综采繁缛,兴属清华。比于建安之徐、陈、应、刘,元康之潘、张、左、束,各一时也。②
这里所述的洛阳是南北交通与汇集的要冲,一直是东汉至西晋的都城,是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人文渊薮,英才荟集,北方的文士在这里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学习可谓得天独厚,北来的文士自然而然率先得到汉魏以来的文化的陶染,因而有永嘉遗风。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北魏统治者的倡导,迄至北魏末期,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北方文士如温子升等人,“比于建安之徐、陈、应、刘,元康之潘、张、左、束,各一时也”。这个时期南北文化对话与交流取得最大成就,后来虽然北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但是这种南北对话的过程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特别是南朝梁代末期发生了侯景之乱,梁代趋于中衰,这时候许多著名文士如庾信、王褒等人,因为各种原因被强留北方,再加上北朝的统治者对于中原文化的倾慕,十分优容这些来自南方的著名文人,主动向他们学习文学,而这些文士也主动地以其深厚的文学修养与人格风范影响北朝,于是南北对话与融合进入了一个更深入与更繁荣的时期。后来,南方文化胜过北方文化,北人的过分学南,将南方文学中的一些末流也加以仿效,导致文风趋于华丽,改变了北方文风的自身特点,于是引起了北方一些保守派文士与帝王的不满与警惕,他们从维护统治者意识形态需要出发,批判南朝末期文风流宕不归的弊端,开始对南方文化进行狙击,甚或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北史·文苑传》评论道:“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然绰之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③而隋代帝王对于南方文风的影响北方虽有所纠偏,但并未能革除风习。
北朝与南朝的对话与交流,大体上有两条主线,其一是在传统的诗骚精神影响下进行的;其二是在不断的取长补短基础上开展的,从而兼容并包,修成正果,奠定了唐代文学精神和南北兼收并蓄、情采并重、文质彬彬的格调。南北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是中国既有的传统文化进行重组的过程。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先秦以来就形成了成熟的价值体系与包容性,同时也本着“和而不同”与阴阳发散、变动相和的精神来对待外来文化,从而不断充实与丰富自身,形成了强大的新陈代谢功能与包容万物的气度。在南北朝时代,这种文化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汉族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始与汉族中心圈文化接触、磨擦与融合的过程。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中原文化,特别是南方文化开始影响浸润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人,一些文士自觉地用中原传统的诗骚精神来从事生活体验与文学创作。比如《隋书·文学传》中记载孙万寿为隋末文士,“万寿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经,略通大义,兼博涉子史。善属文,美谈笑,博陵李德林见而奇之。在齐,年十七,奉朝请。高祖受禅,滕穆王引为文学,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军总管宇文述召典军书。万寿本自书生,从容文雅,一旦从军,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赠京邑知友。”④此诗流传至今,节选部分内容如下:
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粤余非巧宦,少小拙谋身。
欲飞无假翼,思鸣不值晨。如何载笔士,翻作负戈人!飘飘如木偶,弃置同刍狗。
失路乃西浮,非狂亦东走。晚岁出函关,方春度京口。石城临兽据,天津望牛斗。
牛斗盛妖氛,枭獍已成群。郗超初入幕,王粲始从军。裹粮楚山际,被甲吴江溃。
吴江一浩荡,楚山何纠纷。惊波上溅日,乔木下临云。击越恒资辩,喻蜀几飞文。
鲁连唯救患,吾彦不争勋。羁游岁月久,归思常搔首。非关不树萱,岂为无杯酒!⑤
郁郁不得志而写诗赠友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士兼官员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文学造诣而言,此诗并不出色,模仿汉魏以来文士的痕迹是很重的。此诗与同时期南方齐梁文士的作品相较,意境既非独辟,修辞更是平庸;与庾信在北朝所作写乡关之思作品如《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拟咏怀》相比,更是无法评骘。但其中传出的对话与交流的信息却是值得关注:第一,作者生长于北地,是在隋代统一南北后由北入南,不同于南北朝时的许多文士到了北地之后文风为之一变,他所比拟的贾谊当年也是由长安入长沙,当然那时长安是西汉王朝的首都,是汉族政权的京城所在地,而今孙万寿是由北朝的首都进入江南之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南北交流此时互位的情况;第二,作者虽为北朝文士,但是在文化前景上却完全南方化了,南方当时不仅是地理上的概念,也是中土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代名词,孙万寿在诗中的思想文化观念,比如以贾谊自比的屈骚精神,诗中追慕王粲、陆机、郗超等魏晋名士,伤叹遭遇不幸,其中的情感与思想,可以说是汉魏六朝文士的常用情辞与心态。这说明他已基本融入中华文化语境之中。传说这首诗传入长安京城后轰动一时:“此诗至京,盛为当时之所吟诵,天下好事者多书壁而玩之。”⑥这说明对于中土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倾慕乃时尚所趋与南北文士共同所好。
值得注意的是,就学术而言,虽南北有异,但南方文化传承了中原文化的主流,积累甚深。《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⑦由此可知南北学风之特点,然具体到学问的精深渊博,应当说南方依然为执牛耳者,北朝无法与之相抗。当时的学术通过南北对话与交流得以补充与拓展,《隋书·儒林传》记载:潘徽为吴郡人,“性聪敏,少受《礼》于郑灼,受《毛诗》于施公,受《书》于张冲,讲《庄》、《老》于张讥,并通大义。尤精三史。善属文,能持论。陈尚书令江总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诣总,总甚敬之。释褐新蔡王国侍郎,选为客馆令。”⑧潘徽本是经学出身,学问继承了传统的经学与小学,精于礼义之学。一次隋朝派遣使者魏澹聘于陈,二人遂展开对话与较量:
隋遣魏澹聘于陈,陈人使徽接对之。澹将返命,为启于陈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饯送。”徽以为“饯送”为重,“敬奉”为轻,却其启而不奏。澹曰:“《曲礼》云:‘主敬客。’《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孝经》:‘宗庙致敬。’又云:‘不敬其亲,谓之悖礼。’孔子敬天之怒,成汤圣敬日跻。宗庙极重,上天极高,父极尊,君极贵,四者咸同一敬,五经未有异文,不知以敬为轻,竟何所据?”
徽难之曰:“向所论敬字,本不全以为轻,但施用处殊,义成通别。《礼》主于敬,此是通言,犹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于子则有敬名之义,在夫亦有敬妻之说,此可复并谓极重乎?至若敬谢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爱,止施宾友,敬问敬报,弥见雷同,敬听敬酬,何关贵隔。当知敬之为义,虽是不轻,但敬之于语,则有时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举一隅,未为深据。”澹不能对,遂从而改焉。⑨
由这段记载可知,北朝使者的经学修养毕竟比起累年传承与发展的南方学术要差得多,无法展开较量。二人就“饯送”与“敬奉”二字何为合乎礼仪展开对话,最后隋朝使者不得不折服于陈朝的官员。因为学术的力量不是行政实力强弱所能取代的,尽管后来陈为隋所灭,但潘徽因其学术名声依然受到隋朝王公的赏识,“及陈灭,为州博士,秦孝王俊闻其名,召为学士。尝从俊朝京师,在途,令徽于马上为赋,行一驿而成,其名曰《述恩赋》。俊览而善之。复令为《万字文》,又遣撰集字书,名为《韵纂》……炀帝嗣位,徽与著作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助越公杨素撰《魏书》,会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杨玄感兄弟甚重之,数相来往。”⑩可见潘徽对于隋朝的学术文化贡献甚大。特别是北人的审美观念严重滞后,无法进入到审美的空灵境界之中,他们习惯于用经学的眼光来看待作诗。《颜氏家训·文章》中记载: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11)
王籍的这首诗显然受南方的玄学影响,追求意在言外的境界,使人在读后产生回味无穷的感受。这种美学追求在魏晋南朝时习以为常,其实早在魏正始年间的何晏、阮籍等人的诗作中即已开其端,南人以为不可复得,而北方的文坛大人物卢思道与魏收等人却不以为然,加以诋诃,可见其欣赏水平不高。当然,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北朝的温子升、邢劭等人自己也承认模仿南方的沈约与任昉的作品,但是他们毕竟是当时的北方才俊,也得到了南方的赏识。如《北史·文苑传》中记载,温子升从小在北方跟从名人学习,“子升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以夜继昼,昼夜不倦。长乃博览百家,文章清婉”(12)。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所谓南北融合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是一种回归,温子升自称是晋大将军温峤之后,祖父为避难归魏,温子升自幼就有一种南朝后裔情结,他在北地的文学创作带有很深的南方文化的印迹,这是不待言的。他在北朝的出名,除了他自身的用功与才华外,与他的家学渊源难以分开。而他的出名,又反过头来影响到南朝,《北史·文苑传》中记载:
永熙中为侍读,兼舍人、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后领本州大中正。梁使张皋写子升文笔,传于江外,梁武称之曰:“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阳夏守傅摽使吐谷浑,见其国主床头有书数卷,乃是子升文也。济阴王晖业尝云:“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13)
从这段记载可知,温子升在北朝的文名经由梁使传到梁朝,尽管梁代有如沈约与任昉等被温子升与邢劭所模仿的文士,但梁武帝读了温子升的文章后,竟赞赏有加,敬慕不已,认为是陆机、曹植在北朝的重现;北朝的王晖也夸之为可以凌超颜延之、谢灵运、沈约与任昉等人,可见南北的互动与学习,推动了南北对话与融合,虽对温子升文誉的推崇有过溢之词,但南北文人既互相较量又互相学习的事实也再次证明了对话和交流的重要性。
在南北文化对话与文艺批评的构建中,庾信的贡献较为突出,他以其独特的悲剧身世与文化积累以及入北之后的乡关之思,谱写了南北文学的最高境界之作《哀江南赋》。庾信在北朝文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文论,结合自己的身世之感,通过具体的文学创作体会,对于中国古代的“诗可以怨”与“发愤著书”的优秀传统进行了拓展,下文以庾信为中心展开相关论述。
庾信本是齐梁时著名文人,与徐陵同时,后入北朝西魏。入北后文学成就大进,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殿军人物。晚年所作,内容上起明显变化,如《哀江南赋》、《枯树赋》等,自伤遭遇,并对社会动乱有所反映,风格转为萧瑟苍凉,为杜甫等所推崇。庾信的文学理论,近似于陆机的《文赋》,是结合自己的创作而感发出来,并且本身就是在文学形式中宣示出来的,不同于《诗品》和《文心雕龙》,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现的,这就造成了他的文论感受性强,针对性强,但是散见于诗赋的序文与书札之中,通过收集整理,可以开掘出其中的许多精彩思想,呈现出理论著作不曾有的亮点。
庾信的诗赋所以能够凌超众作,融合南北,一个是由于他的悲剧身世,另一个则是由于他早年的文化积累与家学渊源。如果从融合南北的角度来看,他主要是以自己的身世与所秉承的文化传统来推动这种融合与对话。在庾信入北的诗作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情结,就是自己的家族情结。庾信出身儒学世家,父子在梁代受到重用,文才享有盛名,为时人所仿效。在入北后,这成为他的优越感,一如陆机入洛后的家族荣耀感。北朝的文化对于他的影响主要在于地理风习的影响上,而在正统的文学修养方面,主要还是来自于他早年的文化修养与家学背景。我们看到,庾信入北后,这种家族与文化优越感从来就没有消除过,反而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支撑着他在北朝的心理平衡。如果没有早年的精神优越感,庾信的精神可能就面临着崩溃。在《哀江南赋序》中,庾信继承了屈原《离骚》以家族为荣的写作精神,首先仿效汉魏名士的风格,感叹: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举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唯以悲哀为主。(14)
这段序文的家族意识是何等强烈。这说明庾信入北之后,非但没有放弃自己的家族荣誉感,相反家族荣誉成为他在异域羁旅的精神寄托。“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之所以成为庾信自觉仿效的楷模,是因为他有着与他们大体上相当的遭遇与才名,这种家族荣誉感,有着儒学精神的传承在里面。庾信的祖先庾易为齐征士即高士,享有盛名,是庾信心中的偶像。庾信在进入北朝后,一直以自己的儒学信仰与家族荣誉拷问灵魂,著名的《小园赋》其实是庾信在北朝心灵忏悔与痛苦中寻求精神栖居的心态表现。这篇抒情小赋开始即抒发了自己寻求精神家园的心态,当时庾信在北地虽然位望通显,但是内心却陷入了巨大的痛楚之中,无法摆脱屈仕北朝的屈辱与心灵的分裂,他愧对先人与自己的精神信仰,正是这种忏悔意识,使他晚年的诗赋作品有一种深层的类似宗教救赎的精神在内。在《小园赋》中,庾信将小园作为自己意欲引退的心愿,小园与诗赋一样,被赋予精神家园的意义。赋中写到“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引用潘岳的典故,表达了自己倦于朝政,身心俱疲,寻找栖所的悲苦心态。赋中所写小园闲适美丽的景致,表面看来可以安慰自己的心境:“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然而在赋尾却情不自禁地吟哦自己的悲凉与凄苦:
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百灵兮倏忽,光华兮已晚。不雪雁门之踦,先念鸿陆之远。非淮海兮可变,非金丹兮能转。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谅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浑浑!(15)
庾信的悲凉与凄苦是永远不能解除的,因为它并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整一个时代投射在自身的烙印,从而具有巨大的典型意义。赋尾以苏武与李陵的别诗譬喻自己的遭际,暗示自己的悲苦,唯有用李陵、苏武那样的别离之诗才能表达出来。庾信晚年的辞赋与诗文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苏武、李陵之别的典故,不仅是以苏李故事自比,更是用来自我解脱与慰藉。庾信晚期文章所以被称作“老更成”,是因为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自己独特的身世遭遇。而这种历史文化传统,盖源于他早期所受的儒学教育。儒家的廉耻观念以及士大夫的自尊观念,使他陷入巨大的精神耻辱,不能自已,晚期庾信始终被这种耻辱感所折磨,这一点也是他不同于王褒的地方。王褒入北后虽然产生了羁旅愁思,也写过一些乡思之作,但是始终看不到庾信那种发自内心的巨大的忏悔意识与耻辱观,更看不到他的赎罪意识。《周书·王褒庾信传》中记载:
初,褒与梁处士汝南周弘让相善。及弘让兄弘正自陈来聘,高祖许褒等通亲知音问。褒赠弘让诗,并致书曰:“嗣宗穷途,杨朱歧路。征蓬长逝,流水不归。舒惨殊方,炎凉异节,木皮春厚,桂树冬荣。想摄卫惟宜,动静多豫。贤兄入关,敬承款曲。犹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阳之田,铲迹幽蹊,销声穹谷。何期愉乐,幸甚!幸甚!”
弟昔因多疾,亟览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怀五岳之举。同夫关令,物色异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经说道,屡听玄牝之谈;中药养神,每禀丹沙之说。顷年事遒尽,容发衰谢,芸其黄矣,零落无时。还念生涯,繁忧总集。视阴愒日,犹赵孟之徂年;负杖行吟,同刘琨之积惨。河阳北临,空思巩县;霸陵南望,还见长安。所冀书生之魂,来依旧壤;射声之鬼,无恨他乡。白云在天,长离别矣,会见之期,邈无日矣。援笔揽纸,龙钟横集。(16)
这封信中王褒以阮籍穷途之恸自比,与庾信晚期的诗赋常以阮籍自比倒是有几分相似。其中写乡关之思很凄恻感人,但是看不出被留仕北朝后的耻辱感。所以《周书·王褒庾信传》中称他:“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其羁旅焉。”(17)可见他的忏悔意识无法与庾信相比,传说庾信入北后,开始一些北方文士并不服气,庾信将《枯树赋》示给他们看后,无人再言。(18)那些北朝的文士所以叹服庾信的《枯树赋》,首先是其中所坦露的精神魅力与文化传统,其中用典的恰切与深意,修辞的工丽而自然,显示出庾信晚期之作纯熟的艺术功底。这则故事一方面说明庾信的文才不凡,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北方文士的见贤思齐,正是这种胸怀,使得他们虚心向南方文士学习,加速了南北融合的步伐,尽管后来出现了过犹不及的情况。
庾信入北后的诗赋等作,通过自己的身世激活了儒学中的人文精神,使得他的作品从早期的吟风弄月变得雄浑苍茫、悲慨深挚,这当然与北地独特的人文地理与风俗人情有关,庾信早期生活在秀丽温暖的江南,那里的风土人情与文化传统,自古以来就产生了《吴歌》、《西曲》那样的作品,但是更主要的是庾信通过自己的悲剧身世,使得儒学的忧患意识与耻辱精神得到释放。在他的晚期诗赋中,这种文化反思意识与追寻精神是十分强烈的,反映在写作手法上是用典很多,文化蕴涵加浓加深,比如《竹杖赋》、《邛竹杖赋》、《伤心赋》、《小园赋》、《哀江南赋》等都是如此。庾信的诗赋叙说了自己创作缘于表达痛苦,感于人生的特点,并且往往引用古人的范例来加以说明。在梁太清二年(548),庾信遭受侯景之乱,有二男一女相继亡殁。羁留北朝后,又有一女和一外孙夭折。公元557年,陈武帝即位,梁亡,时庾信已在北周,创作了《伤心赋》以表达内心的哀伤。六朝时代,人们可以大胆而直率地抒发对于亲人亡殁的感伤哀悼之情,不必再拘于两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格套。并且可以上援古人,《世说新语》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成了堂而皇之的事。在这篇赋序中,庾信写到:
予五福无征,三灵有谴,至于继体,多从夭折。二男一女,并得胜衣,金陵丧乱,相守亡殁。羁旅关河,倏然白首,苗而不秀,频有所悲。一女成人,一外孙孩稚,奄然玄壤,何痛如之,既伤即事,追悼前亡,唯觉伤心,遂以《伤心》为赋。若夫入室生光,非复企及,夹河为郡,前途逾远。婕妤有自伤之赋,扬雄有哀祭之文,王正长有北郭之悲,谢安石有东山之恨,岂既然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傅长虞、应德琏、刘韬之母、任诞之亲,书翰伤切,千悲万恨,何可胜言?龙门之桐,其枝已折;卷葹之草,其心实伤。呜呼哀哉!(19)
透过这一段浸透着庾信身家伤痛的感言,可以看到庾信发自内心的创作叙说,是来源于对于亲人的情不能遏的抒发需要。而且这一段作为正文前面的序文,情辞并茂,由于是从内心自然宣发的感喟,更能引起人们对于诗可以怨、发愤著书观念的接受与信服。它不是从理念推导出来的,而是从感情生发出来的,此种文论,突出了中国古代文论重感受、重直觉的文化特点。庾信在此段文字中,不仅是局限于个体的感受,而是善于通过这种感受,将其上升到历史传统的深处,与古人相对应。他认为班婕妤、扬雄、曹植、王粲、谢安等人缘于伤逝而自然感伤的哀辞,“书翰伤切,千悲万恨,何可胜言”,凝结为至美的文学作品。
庾信与北朝的文学对话,首先借助其深厚的儒学修养与文学成就,又融合自己独特的悲剧身世,引领北朝的文学与文化。这种对话已经超越了具体的说教与辩论,而进入言传身教的境界。正因为这样,那些北朝的王公贵族才对这位来自于敌国的大臣那么优礼有加,倾心感佩。如果庾信一味巴结讨好北朝贵族,反会被他们所鄙视。《周书·王褒庾信传》中记载:“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20)这种周旋的过程,也就是对话与交流以及互相影响的过程,从现在看到的庾信的作品,早年作为宫廷文士的积习是难改的,那些宫廷生活与应景之作对于他来说轻车熟路。但他更多的是以其思想来影响北朝有志文学的王公贵族,比如他在《赵国公集序》中就提出:
窃闻平阳击石,山谷为之调,大禹吹笛,风云为之动。与夫含吐性灵,抑扬词气,曲变阳春,光回白日,岂得同年而语哉?柱国赵国公,发言为论,下笔成章,逸态横生,新情振起,风雨争飞,鱼龙各变。方之圭璧,涂山之会万重;譬似云霞,赤城之岩千丈。文参历象,即入天官之书;韵涉丝桐,咸归总章之观。论其壮也,则鹏起半天;语其细也,则鹪巢蚊睫。岂直熊熊旦上,增城扎日月之光;焰焰宵飞,南斗触蛟龙之气。
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颂》,谐和律吕,若使言乖节目,则曲台不顾;声止操缦,则成均无取。遂得栋梁文囿,冠冕词林,《大雅》扶轮,小山承盖。(21)
庾信在这里开始盛赞宇文招的诗作富于文采,富于变化,这里面固然有许多溢美之词,但接着笔锋一转,从历史传统中追溯宇文招诗作的价值。庾信认为屈原宋玉与李陵苏武之诗所以为美,是由于不幸的身世所造成的,而建安、太康以来的文学创作,丧失了风骨气质,变成了雕虫篆刻,不足以道。这里实际上是借题发挥,通过对于宇文招诗歌的评论引发自己对于文学发展精神构评价。庾信晚年超越了他早期的文学审美趣尚,而回归了诗骚精神、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杜甫《戏为六绝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咏怀古迹五首》言“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可谓深中腠理。庾信晚期文风的悲凉苍劲,也是这种诗骚精神与汉魏风骨的实践产物。
这种创作思想,在庾信的《哀江南赋》中达到极致。这是一篇用赋体写的梁代兴亡史和作者自传。赋的名称当从《九歌·招魂》中“魂兮归来哀江南”演变而来,从这篇赋中,可以看出他对梁代的覆亡充满了悲悼和依恋之情。文中用了一系列典故,自伤身世,“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诸句。庾信在文中明确提出自己的创作惟以悲哀为主,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诗可以怨”思想的发展。庾信以自己的创作体会,论证了钟嵘《诗品序》中提出的“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22)的论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赋序的最后,庾信呼吁:
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23)
赋中用陆机与张衡的典故引作自己的知音,说明自己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心声。“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两句说尽了中国古代文论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关于文学产生的最深层的动因说,即文学缘于个体的感受与激活。钱钟书《谈艺录》云:“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若《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皆居南朝所为。及夫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惟《象戏》、《马射》两篇,尚仍旧贯。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而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24)
南北朝时代的南北对话,对于初唐文艺观念的构建起到了直接推动的作用。初唐时期兴起了编修史书的热潮。初唐官修史书对六朝文学的总结以及对文学基本观念的重新界定,是其着彩处。史书中大都斥责六朝末期文学的淫靡,认为淫靡的文学对六朝的衰亡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从而提醒后代对亡国之音要保持警醒。同时,初唐史家倡言政教亦不废除对文学的审美与抒情功能的肯定。初唐史家适应大唐帝国一统天下的需要,提出融合南北文风的主张。魏征在《隋书·文学传论》中指出: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25)
以魏征代表的初唐史家认为,南方文风受老庄玄学与人文地理的影响与浸染,文辞清丽,情感绮靡;北方文风受北地风土人情与两汉儒学余风影响,文辞厚重,情感刚健。这两种文风可以取长补短,兼收并融。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政教功能是可以兼融的,理想的文艺应该是集政教与审美为一体,从而“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汉魏六朝的一些文人往往顾此失彼,造成政教至上或审美至上,唐代帝国作为气魄恢宏的封建王朝,应当吸取汉代与六朝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创造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初唐史家的观点顺应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潮流,早在南北朝后期,一些有识见的文人如庾信与王褒等,已有意识地将南方清丽细巧的情辞风格与北方豪放质朴的文风相结合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至唐,南北统一,南北文风的融合更有了实践的可能,也正式摆到了文人们的文化视野内。从思想对话的角度去看,这段引文透出的信息是,南北文学与文学批评经历了漫长的对话与演变过程,才形成了各有所长、各有千秋的境地,经由对话与交流,特别是一些优秀人物如庾信等人的理论与实践,才完成了这一过程。这些对话与交流,奠定了大唐帝国恢宏博大、多元并存的文学基础,沾溉后世,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后期的风范气度。
注释:
①②③⑧⑨⑩(12)(13)[唐]李延寿:《北史》卷八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78、2778、2781、2814、2814~2815、2815、2785、2784页。
④⑤⑥(25)魏征等:《隋书》卷七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5、1735、1736、1729~1730页。
⑦刘义庆编、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3页。
(11)颜之推:《颜氏家训》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
(14)(15)(19)(21)(23)严可均:《全后周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5~186、85、186、191、209页。
(16)(17)(20)令狐德棻:《周书》卷四一,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731~732、731、734页。
(18)张鷟《朝野佥载》:“梁庾信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予后无敢言者。”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0页。
(22)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总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24)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9页。
标签:文学论文; 南方与北方论文; 南北朝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哀江南赋论文; 枯树赋论文; 庾信论文; 温子升论文; 小园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