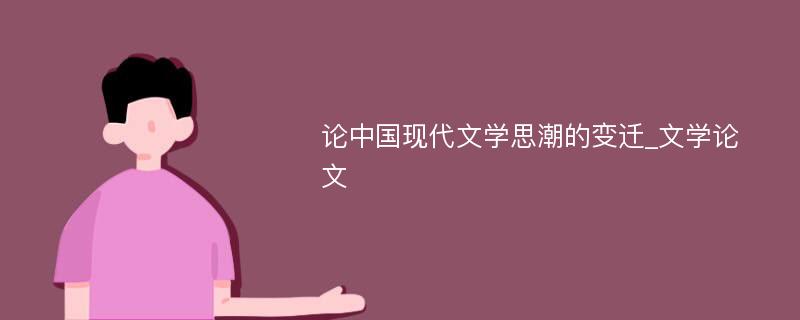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流变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旋多重变奏:从表现人生到政治认同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交织于东西文化双重网络系统里,接受着历史的庄严选择,步履维艰地前进在坎坷的道路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作家们,用“民主”与“科学”这一撬动世界旋转的杠杆,试图将文学从封建的“道”和“载道”中解放出来。《新青年》是当时影响最大、倡导最强的前驱,它震撼了万千读者枯寂的心灵和死水一样平静的文学界。而人的觉醒也就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在多元追求中“表现人生”。
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上人的空前觉醒。近代洋务派“船坚炮利”政策的破产、辛亥革命半途夭折的教训,给“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以巨大的刺激。他们醒悟到,仅凭物质技术和政治体制的变革都不足以救中国,欲砸碎“巨人身上的镣铐”,最要紧的是“立人”,造就出现代国民。于是,他们上承梁启超的“新民”说,仿效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主义运动,把自己的“兴奋点”由政治革命转向思想革命。随着人的觉醒的时代主题的确立,文学亦觉醒起来,作家们维护文学的尊严,追求文学的“全”与“美”。不过,严酷的中国现实不可能给文学留下多少独立的时间和空间。此时的文学家不能置涂炭的人生于不顾,因而,“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是当时一切有着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学理想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是这样,倡导过“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同人亦如此大谈文学的社会使命和功利价值,以至迈出“象牙之塔”,走上风雨飘摇的“十字街头”。从整体上看,“五四”时期似乎存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大文学思潮,而雄居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实则是“表现人生”。在“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中,不同的作家对现实人生有着各自的视角与阐释方式。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多从人道主义出发来反映人生、探讨人生、指导人生,他们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与小知识分子灰色的人生,笔端渗透着深切的同情与怜悯。创造社的作家则从个性主义入手,不重视客观描绘和细节真实,宣泄主观情感,诉说性的苦闷、生的穷愁和时代的悲哀,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个人的尊严、价值及欲望的追求。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不难找到他们自身的影子。他们当时表现的是“整个的人生”和“社会——民族的人生”,对“人生”的理解比较宽泛。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作家对多种文学观念作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那么,这一切全是缘于此时尚未出现一种完整、一致而富有权威性的文学观念。他们在强调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时,其实也注意到了文学自身的规律,在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层面的同时亦没忽略文学的审美价值层面,因而,实际上绝少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也很难寻到纯粹的“载道”、“训世”的文学。
“五四”时期作家们的现代文化意识、思想启蒙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被浓缩、凝聚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政治热潮。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前后,不少作家出于对思想启蒙的失望,更出于对政治革命能改变一切的热切而天真的期待,因而都对文学表现出某种鄙屑。鲁迅先生当时说过:“文学,是最不中用的”,“中国现在的社会状况,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1〕。所以,许多作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 而大革命失败把作家们又抛回文学领域,他们一改“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主张,而使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正式实现从“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到“表现政治”的文学思潮转换的,是1928年“革命文学”口号的论争。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救亡的旗帜下,现代中国作家自觉地把创作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他们积极响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宣言:“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呼吁“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他们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和民主根据地,像艾青、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李广田这样一些曾一度热衷于抒写个人纤细的情感、流露出唯美倾向的作家,亦陆续地投入到政治潮流中,开始为战斗而歌唱,为革命而歌唱。如果说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著名命题是对30、40年代普遍存在的“为政治”的文学观念的一个理论概括和总结,那么,以后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则是《讲话》影响作用的发展和强化。诚然,“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在30、40年代还存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涌现出了巴金、老舍、曹禺等一批优秀的民主主义作家,不过,比之于整个政治化的左翼文学思潮,民主主义作家的声热和影响则显得微弱得多。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实在无法给“为艺术”的文学提供一个适宜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尽管“为艺术”的文学思潮也曾有过热闹的“家史”,产生了新感觉派小说、现代派诗歌、何其芳等人的散文以及朱光潜的美学理论,并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但它们生不逢时,很快便归于沉寂。
如果说“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富有生命力是艺术的真实性,那么,“为政治”的文学思潮强盛的生命力则全赖于艺术的政治性。政治本位强化了30、40年代文学的阶级意识和群体意识。“五四”时期作家们主要关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形成了真诚地看待人生、如实地表现人生的共同创作准则。强调“真”是文学研究会作家与创造社作家共同的着眼点。前者倾斜于再现生活的“真相”,后者突出表现内心的“真情”。30、40年代的作家才更重视文学的政治性和革命性,其时,他们心目中的文学已是“革命的前驱”〔2〕, 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3〕,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最后把文学概括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至此,文学由介入政治逐渐转换为政治认同,于是就有了评判作品成败的第一标准,它是区别是否是革命作家的分水岭。 文学观念上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30、40年代文学思潮的全貌。 如果说“我首先是一个人”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最强音,那么,30、40年代文学的最强音则是“我首先是一个革命人”,对人物进行哲学、历史、宗教、伦理、心理的多维思考亦随之被阶级分析所取代。对此,我们可以从茅盾的《虹》经“革命加恋爱”作品的发展,到后来沙汀的《闯关》、艾青的《火把》中见到一斑。阶级意识的强化,使作家们逐渐丢开自己熟悉的生活,而以饱满的热情去选择和表现劳动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与斗争。
众所周知,从2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即逐渐与中国传统的群众本位观念相融合,这种融合对中国作家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他们逐渐放弃曾热烈追求、心向往之的个性意识。当丁玲突然在《在医院中的时候》重新提出个性要求,描写个性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尖锐冲突时,她弹出的确实是一个与周围环境、时代氛围极不谐调的音调,因而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为政治”文学思潮的某些缺陷,使“为政治”文学思潮自身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以致于它最终没能产生与鲁迅先生及其他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相媲美的艺术杰作。但是不能否认,“为政治”的文学思潮也曾给中国文学带来了虎虎生气和勃勃生机,她能永彪史册并为后人所景仰的那种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那种慷慨悲歌与壮怀激烈的政治热情,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鼓动性和感召力,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融汇与转换:民族民间文学复归的价值取向
近代中国在军事上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两难的抉择:一方面要借助西方先进文化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实现又必须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一方面要用西方文化来改造我们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在这种“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中我们又必须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中西文化的这种强烈冲突在文学中的投影是:既要迅速与世界融汇并保持同步,又要坚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要提高普通民众的审美水平和审美能力,又要适应普通民众的审美要求和审美习惯。面对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问题,“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潮与30、40年代的文学思潮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新文学的雏形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建构起来的。在西方文学的镜子折射下,中国传统文学全是“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都是在落后的封建宗法制度意识形态上产生的“死文学”和“非人的文学”。因而,出现在更高层社会形态中的近现代西方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标志着先进与落后的进化概念和价值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以极大的热情肯定和颂扬西方文明,胡适的《建设的革命文学论》呼吁:“赶紧多多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要以“庄严灿烂的欧洲”作为中国文学革命的样板。当时,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一批卓有成就的作家,都是在西方文学影响下开始写作的。正是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广泛借鉴,才使中国文学以一种“偏激”和“片面”的方式迅速挣脱了几千年中国古代文学的重重桎梏,建构起了一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充满自由精神和襟怀宽广的现代文学雏形,才使中国新文学站到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新起点上,初步完成了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整体转换。
然而,到了30年代,一大批作家开始尝试把“欧化”的形式与中国的现代生活内容融合起来,创造出真正的现代的民族文学。从30年代初到40年代,围绕着文学的民族化问题,革命文艺界进行了多次关于大众化、民族形式和普及与提高等问题的讨论,批判了“五四”文学的欧化倾向。后来,毛泽东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了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于是,在30、40年代,“五四”时期作家那种与世界文学融汇的急切要求被向民族民间文学复归的迫切要求所代替,无论是在小说、戏剧,还是在诗歌、散文中,都渗透了民族文艺尤其是民间市民文艺的广泛影响,洋溢着浓厚的民族气息。然而,人们在强调文学的民族性的同时,又忽略了对民族文学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改造,轻视了前一时期文学所积累的积极成果。表面看来,它们似乎是对“五四”的否定之否定,但实质上并没有完成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这导致了“五四”时期文学思潮与30、40年代文学思潮之间出现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断裂。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是感情解放的浪漫时期,我以为,这一时期也是理性解放的启蒙时期。因为,这一时期许多作家都摆脱了儒道思想的束缚,借助西方的各种主义和学说去思考宇宙、社会和人生,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辩色彩,问题小说、哲理小说、散文、格言式的小诗十分繁荣。冰心恬静地描画着冰清玉洁般的“爱”的哲学,许地山从容地思考着空山灵雨式的宗教哲学,而庐隐则徘徊于她那悲观的生命哲学之中。这种带着个人智慧和体验的哲理色彩,在30、40年代文学中是很难见到的。原因是此时作家们所热心的是宣传与演绎某种理论、思想,而不是探索与思考。这种倾向,在30年代初期蒋光慈的作品、华汉的《地泉三部曲》等作品中就已初露端倪。尽管当时左翼文艺界批评了这些作品的概念化倾向,而且在后来的创作中这种倾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但他们所代表的特点依然存在。无论是洪深的“农村三部曲”或是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或是以后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它们采用的都是寓意性创作手法,力图通过讲故事来说明一个先验存在的观念、道德,以此来教导读者。这与中国古代“重教化”的传统和通俗文学中“劝善惩恶”的传统有密切关系,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民间文学对30、40年代文学的影响。此外,文学在30、 40年代迫切要求高度集中、统一、一体化, 这是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需要。其带来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复活了古典文学那种用普遍伦理节制个人情感的规范性的特点,使“五四”文学那种独具个性的创作越来越少,作品在题旨、取材、风格、意象、深层结构、形式安排等方面相似的作品越来越多,表现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作品多于饱含个人辛酸、哀乐和创意的作品。这与“五四”时期千姿百态的文学形成鲜明对照。
“五四”时期的文学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注重呈现方式,不再把情节视为作品的核心,也不再把行动当作人物的核心,而是淡化情节,强化细节,向人物心理开掘,细致地揭示、描写人物活动和事件发展的过程,常常采用辐射式的横向结构,等等。30、40年代文学在许多方面摈弃了所谓欧化的形式和技巧,自觉地向民间叙事文学学习,用叙述性代替呈现性,用情节代替描写,用平面展开代替内在挖掘,作品大多采用单线或双线纵向推进结构,等等。而对人物形象作类型化的处理,强调故事性和传奇性等特点,在解放区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30、40年代文学在民族化的努力中适应了工农读者的文化心理和审美经验,使民族民间文学的许多优秀遗产重新得以发掘,不但纠正了文学发展中某些片面“西化”的偏颇,而且大大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和技巧,富有成效地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从这一意义上看,30、40年代文学思潮是“五四”时期文学的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其发展的本身所带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幼稚与狂热:悲凉沉郁中折射亢奋激越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近百年饱尝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与辛酸,并从沉睡中惊醒,努力去抗争。这种历史进程使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在审美特征上呈现出从悲凉沉郁到亢奋激越的演变历程。
当我们翻开“五四”时期文学作品时,我们往往会感觉到其时代的苦闷感。其间有“生的苦闷”,如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郁达夫的《还乡记》,而王以仁的《流浪》则写尽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穷愁潦倒。其间有“性的苦闷”,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以及叶灵凤等人的作品大胆地描写了人的自然情欲,宣泄出“向善的焦躁与惩恶的苦闷”,将青春时期的本能欲望与传统道德的伦理之间的冲突写得惊心动魄。其间有“爱的苦闷”,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几乎全是那么纯真与圣洁,她们所吟咏的对爱情的渴望,是爱情追求中的痛苦,是爱情无法实现的悲伤。其间亦有“玄思的苦闷”,这一时期的作家充满着探索人生根本的哲学热情,在问题小说和哲理小诗中,投射的是他们苦苦思考着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意义以及宇宙的奥妙的影子。简而言之,“五四”时期的苦闷感已经渗透了人生的各个层面。
除苦闷情绪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更有一种不知如何摆脱苦闷的迷惘感。鲁迅的涓生不知怎样跨出那第一步,而“过客”虽然执拗地向前走去,却不知等待他的是鲜花、荆棘还是坟墓;许地山则用充满佛教色彩的语言喟叹:“我们都从渺茫中来,在渺茫中往,往渺茫中去”;庐隐更是悲愤痛彻地呼喊:“哪里有彼岸?哪里有花园的主人?哪里有秋天的女神?哪里有自然的使者?”有时候,这种迷惘感甚至变成绝望感、荒谬感和无可依归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作家才如此热衷于自杀的描写,就连相信进化论的鲁迅先生也曾把希望与绝望联在一起,以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作家们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失望和对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怀疑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榜样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日趋胜利的现实,使知识分子逐渐看到了民族和国家以及个人的前途,热烈地憧憬着光明的新中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远看着东方已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4〕”这种乐观精神不仅存在于党的领袖之中, 也存在于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中。它十分深刻地影响到文学,使30、40年代的文学思潮一反“五四”时期文学思潮的悲凉沉郁,变得亢奋激越,热情奔放。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必胜、正义必胜的乐观意识。“五四”时期常见的悲剧性结局几乎全部消失,而“五四”时期几乎看不到的“大团圆”结构方式则比比皆是。这一倾向在30年代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和“革命加恋爱”的作品中已初露端倪,到了40年代更成了普遍现象。诸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以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等作品,尽管它们也展现了严酷、复杂、甚至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实,但最后总是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英雄的牺牲必然换来革命的胜利,因而,我们从中体验到的与其说是悲,毋宁说是壮。
悲秋、残春、孤鸿、衰草、夕阳,是“五四”时期作家大量运用的意象和意境,它们溶入了作家凄绝哀伤的主观感受。而我们在30、40年代作品中看到的则是太阳、黎明、春天、红旗、火把、军号,它们是作家对革命的讴歌,对未来的向往。然而,正是这种乐观的、理想主义的意识,反映出了这个时期作家的单纯和盲目。他们低估了阻碍人类进步、个性发展的一切落后势力,对革命进程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虽然在气势和力度上比“五四”时期的更强,但却少了几分清醒和深邃。就拿塑造农民形象来说,“五四”时期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是凝重、麻木与萎缩的,而30、40年代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则是觉悟、坚强与勇敢的——它充分发掘了中国农民革命性的一面。这无疑是对“五四”时期农民形象塑造的重大发展和补充。但这个时期在对革命者形象塑造上的理想化倾向也是明显的。从《倪焕之》中的王乐山、《虹》中的梁刚夫、《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的林希坚,到《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章品以及《暴骤风雨》中的肖祥等等,面对严酷的现实和恶劣的环境,他们总是那样冷静刚毅,甚至一出现,再复杂的矛盾也都迎刃而解了。他们被描写得太完美了,人们根本看不到他们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听不到他们真诚深刻的自我反省。诚然,处于艰苦卓绝斗争中的人们需要受到鼓舞,需要一种理想人格作为自己的榜样,这种理想色彩在当时确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全球意识:文学思潮历史的坐标确立
文学介入政治,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西方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如启蒙主义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与俄国革命、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与二次大战等等,都是较为突出的例子。而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充溢着怀疑和批判精神,是它们共同的特点。在中国,造成文学与政治完全认同的原因,与其说是政治本身对文学的独立性尊重不够,倒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心理素质上形成了对政治过分的依附感和认同感。当文学介入政治时,既要坚持政治功利本位的价值标准,亦要尊重真实本位和艺术本位的价值标准,在维系它们之间关系“平衡”的同时,要允许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形成不同的层次,保持必要的张力,以达到促进文学多元发展之目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正是在这一点上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才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于世界意识中追求民族性,于民族意识中追求世界性,这是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所应有的表现。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要意识到“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 〕”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现代文学,我们必须要具有强烈的“世界意识”,必须彻底消除民族性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清除掉那些与整个人类发展和进步不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艺术形式,特别是对于现代中国这个在社会形态上落后于西方、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的国家,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和魄力。如果有人认为这样将会丧失掉自己的传统文化,泯灭民族的个性,实为杞人忧天。因为,传统的河流是川流不息、无法断裂的,新的潮流的引入,只能使传统的河流更加波澜壮阔,更加充满活力。“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那就必须促使这一文化去同其它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T·S·艾略特如是说于我们是有所启迪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学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风貌和魅力,才能为世界文学作出独特的贡献。唯其如此,它才不至于被世界文学淹没,才可能在世界文学大家庭中占有一席地位。我们应该在世界意识中追求民族性——摆脱了片面性与局限性的民族性,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保持一致的民族性,尤其是可以丰富国人对世界、人类和宇宙以及本民族特性的认识,丰富人们的审美感受的民族性。
总之,历史是一次性的,它一经过去便永不再现。中国文学的前景既不是也不可能是传统文学的复归,或者传统文学的中断;既不是也不可能是以中国文学为主体吃掉西方文学,或者以西方文学为体、为质,以中国文学为用、为形。中西文学的融合已经并且必将是充满矛盾纠葛、历时颇为久远,不断重新理解和发现对方的新的价值、并加以吸纳融汇。80年代,中国人民开始以健康的文化心态在改革开放中作出自己的选择,摸索、确认出一条既不脱离人类文明大道,又不脱离民族文化传统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之路,从而,在中外文化多向融合的基础上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新的价值系统和民族精神。
〔1〕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
〔2〕郭沫若《革命与文学》。
〔3〕鲁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