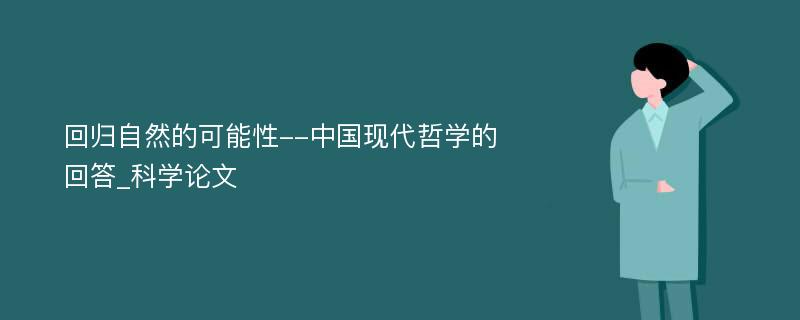
回归自然何以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回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回归自然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天人合一,或人与自然合一,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随着异质的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念逐渐被改变、被“现代化”、被“科学化”。人们在观念上将自然视作认识的对象与征服的对象,在情感上不信任自然、疏远自然。原本作为人生意义重要来源的自然仅仅被当作物质能量的提供者,而不是继续为人生提供意义,人生意义因此出现许多问题。出于对科学文化造成的人与自然疏离的警惕与担忧,许多中国现代哲学家通过各种方式重建回归自然的道路。他们一方面以强烈的现实关怀积极回应科学文化;另一方面又积极面对传统,表现出较健全的理论视野。
一、科学时代的自然问题
中西古今的碰撞促使哲学家们不断深入地反思不同文化中的自然范畴。方东美先生曾对西方文化史上的“自然”观念作过清晰、精辟的梳理:“1.自然是指在后期希腊哲学中所谓的,一个没有价值意义,或否定价值意义的‘物质的素材’。2.希伯来宗教思想认为一个堕落的人受虚荣的欲望,自私的恶念和虚伪的知识等愚妄所迷惑,而一任罪恶所摆布,这就叫自然。3.自然是指整个宇宙的机械秩序,这种秩序依近代科学来说,即是遵从数学物理定律支配的数量化世界,是纯然中性而无任何真善美或神圣价值的意义。4.自然是指一切可认识现象的总和。严格遵守先验自我所规定的普遍和必然的法则。这和康德本体是一个显明的对照。5.大诗人们常把自然当作拟人化的母亲。6.斯宾诺莎所谓的‘活的自然’是指具有无限力量的无限本质。在它之下,都充满了创造的性能。”第三个自然观念就是我们熟悉的科学文化中的自然,不过,在西方文化中,它与第一、第二、第四个观念却是密切相关的。
金岳霖先生曾通过区分“自然”与“纯粹的自然”揭示人疏离自然的状况。他所说的“自然”指通常意义上的自然与自然神;“纯粹的自然”则指经过科学化、知识化的“主体的领域和客体的领域的自然”。对于前者来说,人类归属于它,对于后者来说,人类与它相离,在它之外。对于前者来说,自然律也是行为律,对于后者来说,自然律仅仅是存在于物质之间不变的关系,是对相互分离的客体事物变化与运动的描述。金岳霖认为,后者是人类中心论自然观,即使客体自然屈从于内心的纯粹的自然,其极致是“客体自然几乎正在消失”,是失掉“自然的自然性”。由此“客体自然几乎正在消失,而且,知识的力量、工业的力量和社会组织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二、回归自然的努力
金岳霖先生这样问道:“为什么自然与人应该合一呢?难道它们还未合一?如果它们能够合一,为什么它们还没有合一呢?如果它们不能够合一,为什么要提倡它们的合一?而且所谓的合一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提出合一这一问题。”上述追问差不多囊括了科学时代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所有问题,而“必须提出合一这一问题”也代表了背负天人合一传统的中国思想家对此问题的态度。人只有回到高明博厚的自然,才能获得安身立命的根本。这里的自然包括外在的自然界,也包括内在的自然(本然的性情)。超越科学、回到自然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家普遍的追求。
方东美在细致地分析了西方自然观念之后,也对中国哲学中的自然范畴给予本体论、宇宙论、价值论的定位。他说:“自然,顾名思义是指宇宙的一切。就本体论来说,它是绝对的存有,为一切万象的根本。它是最原始的,是一切存在之所从出。就宇宙论来看,自然是天地相交,万物生成变化的温床。从价值论来看,自然是一切创造历程递嬗之迹,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层级。”自然不是西方文化中的无价值的事实、现象、质料,它既然在本体论、宇宙论、价值论上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那么,人就应该尊重自然:“个人就应以忠恕体物,深觉我之与人,人之与我,一体俱化。我、人、物三者,在思想、情分及行为上都可以成就相似的价值尊严”。自然有价值意味,因此可以吸引人来体物,善待物,人在情感上也向往自然就合情合理了。
相较于方东美对自然质性的规定,贺麟对自然与人的看法则彰显了两者辩证的历程。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贺麟区分了几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一种认为自然是人生的工具或材料;第二种认为自然是人生的反映;第三种认为自然是人生的本源;第四种认为自然为人生的对象,人生为自然的主体。后两种看法主张回到自然,而且把自然看作人生本源还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自然是一个无尽藏,可以提供各种意义;二是自然代表人生的本然或本性,回到自然就是恢复本性,或保全本性。
贺麟本人倾向第四种看法。他认为,人生与自然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逻辑发展的过程。在第一个阶段主客混一;第二个阶段主客分离;第三个阶段主客合一。在他看来,主客分离是走向主客合一的必要前提。主客分离过程是人主动创造的分离,目的在于征服对象以求得自身的发展。结果就造成“自然成为精神化的自然,人生成为自然化的人生。自然建筑在人生上,人生包蕴在自然里。人成为最能了解自然的知己,人成为最能发挥自然意蕴的代言人。”强调自然的精神化就是强调自然的人文化,即“以天合人”,这正是传统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特征。贺麟本人对此亦有高度的自觉,他说自己所讲的回到自然是儒家式的,而不同于道家的回到自然。
冯契在理论上自觉把“事实”充实进去,并把自然原则贯彻于天道、自由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承续了道家命脉。冯契对于自然的秩序的看法可以归结为:自然=本然+实然+或然+当然。具体来说:“从对象说,是自在之物不断化为为我之物,进入为人所知的领域;从主体说,是精神由自在而自为,使得自然赋予的天性逐渐发展成为自由的德性。在没有能所、主客的对立时,自然界是未曾剖析的混沌,‘强为之名’,我们称之为自在之物或本然界。人类由无知到知,以得自经验者还治经验,本然界就转化为事实界。事实界是自然界之进入经验、被人理解的领域……可以思议的领域称为可能界……价值界是人化的自然。”万物有本然之性,本然之性是事实之性、可能之性、价值之性的根据,但通过人的实践与认识,本然之性可以化为事实之性、可能之性、价值之性。在冯契看来,西方传入的科学与常识一样,把本然化为事实。事实是自然演化历程的一种形态,但不是其唯一形态或终极形态,在事实基础之上可以生成无数种可能。
自然必然性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和人的需要相结合,使自然人化,就创造了价值。价值界是人化自然,是贯穿着人的目的的自然。冯契认为,人化的自然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价值虽贯穿着人的目的,但就自然的必然性来说,它也是“合于”自然的,是合乎万物性分(本然之性)的,人化自然的过程是自然历史的过程。人化自然既有自然的必然性,也有其对人的当然性。
自然界演化过程属于外在的自然,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则属于内在的自然。与自然界演化秩序相一致,人类自身也相应的经历了一个由自在到自为,由天性到德性的发展过程。在冯契看来,德性在双重意义上与自然相关:它既出于自然,也归于自然。德性培养过程离不开自然,尤其离不开外在的自然。因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必须在与自然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发展自己,只有达到与自然为一才会感到自由”。就过程而言,德性培养要展开于与自然交互作用过程中;就结果来说,达到与自然为一才会有自由。不过,在如何达到与自然为一的问题上,冯契认为,单靠个人的自然禀赋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社会关系才能实现与自然为一。天性是德性的基础与根据,但自然禀赋不能作为自由的界限。撇开社会人伦,仅仅追求率性自得意义上的自然,最终只能是一种乌托邦。
三、困境与出路
从贺麟、方东美、金岳霖及冯契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回到自然的愿望与努力。按照他们的思路似乎可以乐观地说,即使在科学的时代,人们仍可以回到自然,居于自然之中,仍然能够过自然的生活。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身在科学中,安得返自然?以智慧来吸收、改造科学及其物化形态的努力尽管值得钦佩,但这能够改变科学主体的眼界吗?
从科学在欧洲的历史,以及它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看,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纯粹中性的知识经验,它还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科学对自然、人曾经、现在都在实施“祛魅”,即祛除其中的神性、巫性,祛除自然的价值维度,使自然成为光秃秃的事实。神性、价值乃是自然之“神”、自然之“灵魂”,也是自然对于人最亲切、最能吸引人的核心维度。按照金岳霖的说法,科学祛魅即是祛除“自然神”或“自然的自然性”。如果自然之神性,或自然之自然性无法确立,自然就不能召唤人,就不可能吸引人去与之合一。自然律及由此造成的事实使自然更加可信,但失去价值的自然却不再可爱,也使人不可能再去信任、信赖、信仰它,更不愿意回归这样的自然。
问题是如何重建对于人与自然的理性的信仰?冯契主张在实践基础上把性与天道交互作用理解为价值的源泉,确立自然的多重向度,将价值界理解为自然界的有机维度,进而确立了自然的“价值性”、“意味性”。不过,冯契在本体论上重建自然的意味性过程,似乎并没有关注这样的问题:即使自然是有意味的,如果科学不断对之祛魅,不断祛除其中的意味,我们该怎么办?
牟宗三在《现象与物自身》一书中将“物自身”确立为“具有价值意味的概念”:“如说‘本来面目’,亦不是所知的对象之‘事实上的原样’,而乃是一个高度的价值意味的原样,如禅家之说‘本来面目’是。如果‘物自身’之概念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事实概念,则现象与物自身之分是超越的,乃始能稳定得住”。牟宗三极力论证“物自身”具有价值意味,不过,他所说的“物自身”并不是客观的自然。“物自身”是形上本心的创造,自然界本身并不存在这样有价值意味的“物自身”。具体说来,“物自身”是“无限心”、“智的直觉”、“本心仁体”这些形上心灵的创造,它既由之生,也只能由之呈现。没有“智的直觉”,万物就没有任何价值意味。比如,现象界就没有价值意味。在牟宗三看来,现象是感触直觉所对,是认知心所生成的东西。“自然就是现象之总集。我们所谓自然界,所谓研究自然科学之自然,那个自然界只是一大堆现象……不是天造地设的”。自然是现象,是识心之执所对的,因此,它属于“价值中立”的范畴。既然只有“智的直觉”才能创造、呈现有价值意味的“物自身”,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先立乎大者”,确立本心仁体。以本心仁体、智的直觉来控制、支配精神,以保障世界不受科学世界观的支配。相反,如果能够以本心仁体控制科学世界观,这个世界的意味就不至于被褫夺——祛魅,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就表达了这样的立场。所以,自然界本身是无意味的,意味只存在于形上本心那里,是纯粹主观的东西。牟宗三以思辨的形式突出了意味的主体性质,这种努力无疑对抑制科学世界观有其作用。但否定价值意味的客观性会造成以下结果:人与自然的亲近成为对自身的欣赏,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欺骗。这其实以另一种方式褫夺了自然本身的魅——神性。
冯契与牟宗三的理论展示了现代中国情境下回归自然的困境:科学可以创造价值,因而其自身有价值,而且,现代情境下自然价值意味的确立又绕不开科学。从方法论上看,科学方法不能发现、也无法证明自然有价值意味,人文精神、人文境界可以呈现价值意味,但它不是唯一的创造源。不过,这种困境同时也昭示了摆脱困境的出路。冯契的“四个世界”理论重新确立了自然本身的价值意味,这可以说奠定了回归自然的本体论基石;牟宗三的“智的直觉”理论、“良知坎陷”理论则为我们展示了回归自然的方法论依据。是否可以把本体与方法统一起来,确立一个在本体论上保证自然有意味,在方法论上又使我们能够抑制科学世界观、体味自然的理论。基于此,人们既愿意回归有意味的自然,也能够体味、把握、创造有意味的自然?这恐怕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或出路。
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07.4.4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