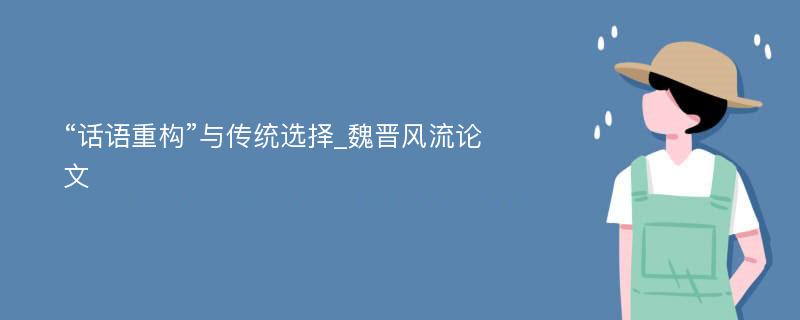
“话语重建”与传统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中国古代文论:语境缺失或“知识型”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并且也是博大精深的,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西方文论的许多范畴在中国的古代文论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形态(注:如《文学评论》1993年第2 期龙协涛《中西读解理论的历史嬗变与特点》一文,提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读解理论非常发达,“接受美学阐述过的一些重大问题它似乎都涉及到了”。另,张少康先生在《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对“直觉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和作用,也许比西方强调直觉还要早些”。(《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第46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古代文论之所以在当代失去了“中心”地位,并非仅因为年轻人追求时髦,或者有些研究者盲目崇拜西方,而是确有其内在的原因。本文认为,除了已被许多人谈论过的,如中国的古代文论发展的断续性、概念随意性等(注:这方面可参见《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陈洪、 沈立岩《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文学评论》1997年第5 期蔡钟翔《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古代文论生成的历史语境今天已经缺失。
那么,如何来看中国古代文论生成的语境呢?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论发展史上,文论赖以存在的语境是在不断变化着的。然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来考察。魏晋以前是中国文论的孕育期,而魏晋作为文学的“自觉”时期,正是中国文论的生成期(注: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基本上采用了张少康先生的观点。张先生认为,先秦是中国文论的“萌芽产生期”,汉魏六朝是“发展成熟期”。(见《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不过笔者认为,汉代仍是中国文论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的准备期,这一时期文论的审美主导倾向在魏晋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故而笔者把魏晋时期看作中国文论话语生成的典型语境。叶朗先生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自觉的时代”(第183页), 而“汉代美学是从先秦美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美学的过渡环节”(第159页), 可作参考。)。因此,可以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文论生成的典型语境。一种话语的语境所涵盖的有话语主体的生存状态、作为话语的逻辑出发点的主流哲学、政治经济状况等主要因素。我们先来看魏晋时期文论话语主体的生存状态。士人是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言说者。在先秦时期士人甚至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言说者,在政治系统中,士人并没有处于边缘化状态。而到了魏晋时期,士人阶层逐渐退出政治中心地带,仅以谈玄的方式保持着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对话。有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蜕变”说,认为先秦士人的思想代表多为布衣之士,在政治上没有稳固地位,在经济上无固定收入(这也许正是他们对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原因);而魏晋士人则呈现出贵族化倾向,他们大多出身豪门,家资巨万,与势力集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先秦士人低下的政治经济地位刺激起他们重新安排社会的主体意识;魏晋士人的社会地位则使他们失去了对社会状况的深切关怀”(注:李春青《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0页。)。其次,至魏晋时期,中国的主流哲学由汉代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代之而为老庄哲学的兴盛。可以说,玄学的兴起与当时士人的生存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客观上“出世”的条件使崇尚“自然”、“逍遥”的老庄思想得以确立哲学话语的中心地位。闻一多先生在论及庄子崛起于魏晋的问题时指出:“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化,——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注:《古典新义·庄子》,见《闻一多全集》第二卷,三联书店,1982年,第279—280页。)此外,佛教精神在这一时期也渗入世俗哲学的领域,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李泽厚在他的《美学历程》中对这一现象做了较详细的论述,他说:“从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辩到南朝佛学形神之争,佛教以其细致思辨来俘虏门阀贵族这个当时中国文化的代表阶级,使他们愈钻愈深,乐而忘返。哲理的思辨竟在宗教的信仰中找到了丰富的课题,魏晋以来人生悲歌逐渐减少,代之以陶醉在这思辨与信仰相结合的独特意味之中,‘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魏书·释老志》)”(注:见李泽厚十年集《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20页。) 这是中国主流哲学的变化。另外,汉末以降,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折,数百年强大的统一政权沦为混乱的“军阀割据”、战事频仍的牺牲品,黄巾起义、三国纷争、八王之乱,等等,这也是造成士人阶层退出社会政治领域、遁隐于精神世界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其一,是人格与文品的贯通。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即把作为人的道德属性的“气”导入文学范畴,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点,从此人之气与文之气成为一对互相依存的概念。刘勰在《文心雕龙》的《体性》篇中则着重阐述了“性”与“体”的关系:“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我们尽可以说这些观点源出于“诗言志”说,但必须看到这一点:在当时的语境之中,士人对政治生活的失望导致他们对个体人格的完满境界的追求,而这种完满人格境界的表现形式便是文学。反过来说,对文学的评价便首先成为对人格的评价。其二,讲求体悟,不重分析。老子曾提出“涤除玄鉴”的概念,就是讲以虚静之态与“玄”相镜映,即“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庄子更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提出“心斋”、“坐忘”之说,即在观照世界的过程中达到“心与物化”,所谓“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万物之所造”,就是达到互为主客的浑融境界,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庄周梦为蝴蝶’,这是站在庄周的立场说的;站在蝴蝶的立场,也可以说‘蝴蝶梦为庄周’。”(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这样的哲学思想, 不仅导致了创作论上的体悟说,如陆机的“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刘勰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等,而且也影响到直觉式批评方法的形式。中国古代文论早已有着方法的自觉,《文心雕龙》中就有“六观”之说,但有了方法的自觉并不等于会去自觉地运用方法,由老庄哲学所提供的思维方式,使得魏晋以后的文学批评无法为我们提供分析型的足够例证。其三,规范化,繁琐化。当文学成为士人阶层的乌托邦时,他们也便殚精竭虑来营构这座精神家园,力求完备、雅致、细腻。仅从文体分类来看,曹丕概括为四科,陆机举为十类,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仅在篇名标出的文体就有三十三类,《昭明文选》列出了三十九类,而赋一类又列子目十五种、诗类列子目二十二种(注:参见童庆炳先生著《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17页。)。不仅如此,他们还要为各种文体做出风格上的规范,曹丕强调:“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即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哗而谲诳”。《文心雕龙》之《定势》篇也有同样的论述。在这里,我们既应肯定其文论自律化倾向,同时,也可以见出文人雅士在这个乌托邦中精雕细琢的悠闲自得。有论者将这种现象称为“雅化追求”,并认为,隋唐以后,“魏晋士族贵族化的精神追求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传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故而隋唐直至清代的士人在学术观念与审美趣味上都带上了浓厚的精神贵族味道”(注:李春青《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第4页。)。
特定的话语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存在的。在建立当代文论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文论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众所周知,古代文论研究有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现象,即同一个范畴会引发多种解释,各执一辞,自说自话。如对“风骨”概念的理解,主要观点竟达十余种之多。这种现象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是我们对古代文论研究不够深入所致。如果说黄侃、范文澜、刘永济、宗白华等对“风骨”提出不同解释的先生还“研究不够深入”,只怕是无法说得过去。我认为,这里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已处在不同的语境。与刘勰处在同一语境中的人,听到“风骨”二字,无须解释,已能心领神会;而在我们听来,则无异天籁。再如,中国的“诗话”、“词话”一类批评文体,提供给现代人的大多是一种印象,而不是清晰的理路。正像季羡林先生说的,“大家常说杜甫‘沉郁顿挫’,李白‘飘逸豪放’,还有什么‘郊寒岛瘦’一类的说法。可是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文学家把这种风格说清楚的”(注:见《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回顾》一文,《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第4页。)。这并不是说当时的人也不清楚,只是我们不清楚而已。 简而言之,我们所面对的是另一种语言。对这种语言的解释几乎已成为许多综艺节目里“猜猜看”的游戏,因为它既可能猜对,也可能猜错,所以会吸引人们加入到这个游戏中来。这正符合当今大众文化的特征:事情很有意思,但未必有意义。
法国思想家福柯曾经提出“知识型”(episteme)概念,所谓知识型,“是决定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所使用的基本范畴的认识论的结构型式,是某一时代配置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的根本性的形成规则,是制约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的深层隐蔽的知识密码。”(注:《求真意志》译者序,阿兰·谢里登著,尚志英、许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页 。)因此也可以说,特定的话语都是在特定的知识型框架中被谈论和理解的。知识型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其基本道理也可以用来说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曾做过这样的论述:“其时之思想中心不在社会而在个人,不在环境而在内心,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于是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 我们把魏晋当时之“新型”拿到今天来加以思考比较就可以看出,也许今日之“新型”还没有确定,但其基本取向与魏晋之“新型”是背道而驰的,其追求者为“入世之理想,物质之境界,资生之绝对,玄远之相对”。那么,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之中,我们可以去“原汁原味”地理解甚至使用生成于魏晋的文论话语吗?李春青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也许是不无道理:“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的贵族化倾向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大众化、通俗化趋势是格格不入的。”(注:李春青《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页。)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在今天看来,只能作为一种背景的理论模式或研究对象存在,而将其运用于当代文学的批评,则正如两种编码系统无法兼容一样,不可在同一界面上操作。有人试用之进行批评,如黄维梁先生《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作用——用〈文心雕龙〉“六观”法评析白先勇先生的〈骨灰〉》,证明是失败的(注:见《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需要指出的是,黄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理论与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沟通工作,还曾以西方的当代文论方法来评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春的悦豫和秋的阴沉——试用佛菜〈基型论〉观点析杜甫的〈客至〉与〈登高〉》(见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比较文学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而这篇文章写得极为出色,反过来证明,用当代的批评方法可以解读古代的作品。对这种现象的解析应当是阐释学的任务。但尝记得赵鑫珊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类知识的进化是迅速的,而人性的进化则极为缓慢;文学作品是人性之流露,故而如生命之树一样常青。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按赵先生的观点,灰色的理论只有不断更新才可保持其相对的生命力。)。曹顺庆先生也认为完全可以用“虚实相生”这一“中国传统话语”去解释荷马史诗中那一段著名的对海伦的侧面描写,这样做可以“进一步检验中国文论话语的有效性、普遍适用性及其独特性”。曹先生的分析是这样的:史诗中“写海伦登上城墙观战,没有一个字描写她的美貌,而是从特洛伊王公贵族们的轻声赞叹中,烘托出她那倾国倾城的绝色。这就是以虚求实,‘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注: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第152页。)恕我鄙陋,没有看到曹先生的专文分析, 但我想,既是解释,大概总不能只是得出一个“以虚求实,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结论便罢,而必须解释为什么以虚求实就能够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也就是说,应当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做出分析,才能满足现代人的阐释需求。但中国古代那种非理性的、概括式的、象喻式的批评理论虽然能够对文学现象做出评述,但却无法进入学理层面的分析,而没有分析的文字在今天也许只有领导干部的训话可以被认可,作为批评文章它将不会适应当代的审美趣味。而从根本上来说,是语境(或“知识型”)发生了更替。
中国古代文学生成的语境已经缺失,然而,中国的文化是不失缺失的,它一直为我们的言说提供着文化的乳汁。第四节将谈到这一点。
2、20世纪中国文论:两种误读与再度失语
关于20世纪的中国文论,也许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过这种话语权力的控制。可以说,一种话语就是一个家园,在这个家园中,我们都曾感到怡然自适。然而,今天我们也都或多或少感受到了失语的痛苦。我们摆脱了它的控制,也失去了自己言说的家园。根本原因是我们解构了这种话语赖以存在的语境。
中国20世纪文论形成的语境,有一个总的背景——救亡。可以说,救亡的背景制约着这样文论话语的言说者存在的状态、对话语方式的选择等,换句话说,中国20世纪文论形成的语境,就是一个“救亡”语境。首先,救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解构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语境。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知识分子们超然物外的心态被严酷的现实所打破,他们力求保持的贵族式雅化处境在鸦片战争之后已不复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注:《中国记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 第545页。)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已不是入世还是出世的问题,不是能否保持完满人格的问题,而是能否继续做一个拥用说话权利的人的问题(注: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明末清初之时已经存在过,但为时不久即告消解。因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即使在满州人的统治下仍得以保留下来。党锢之祸尽管有过,但在文学领域,传统的言说方式仍然存在。)。从此老庄哲学真正告退,文学终于从空中落到地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文学理论患了第一次失语症。民族的危机使得知识分子阶层面对着政府的腐败,面对民族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陶曾佑的观点可谓当时的代表,他认为“经史子集”均不足为训,“考诸吾国,自鸿荒洎夫中古,经则详于私德,略于公益,为个人主义之伥;史则重于君统,轻于民权,开奴隶舞台之幕;子则鄙夷浅显,注重高深,耗学者之心思脑力;集则记载简单,篇章骈俪,种文坛之夸大浮华”(注:《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见《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 第249页。)。从清末直到民初,从太平天国捣毁孔圣人的牌位到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曾经发生过多次尊孔与反孔的论争,就是这种虚无观的体现。尽管在国难当头之时不免有人试图标举国粹以振国民之心,但更多的人在数百年闭关自守之后,一旦被打开门户,那一股强大的意欲革新自我的逆反心理,使得整个社会的目光绝不会转向过去。因此,从第二个方面来说,救亡使得中国的文人在失语之时自然承继了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将选择的意愿投向西方。梁启超大力提倡译印日本的政治小说,王国维则对德国美学情有独钟。此二人的做法为中国人在失语之后建立新的文论话语开辟了新路。此后的中国文学理论,几乎无一人不是在研读某种甚或数种西方文论的基础上说话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则有更多的人将目光转向俄苏文学。这一事件的意义之大,除了它给救亡图存的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道路之外,从我们的角度说,它是将两种重要的原素带入了中国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救亡影响到中国20世纪文论话语形成的第三个方面,是它决定了中国人在重建文论话语时的价值取向——为人生。而这种价值取向也决定着对外来事物接受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20世纪文学所受俄国文学影响最大,由受俄国19世纪文学的影响而至于在俄苏文论的基础上建成中国20世纪文论的话论形态。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国文学对俄苏文学的长达数十年的接受过程中,由接受语境所致,最起码存在着两度的误读。
鲁迅的观点也许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注:《〈竖琴〉前记》,见《鲁迅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页。)但我认为,误读也正在此时发生。 鲁迅以果戈理小说同名创作的《狂人日记》,即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实绩,标明了这种误读的总体倾向。果戈理的“妈妈,可怜可怜你的孩子”的呼唤浸透着强烈的自我救赎感,而鲁迅的“救救孩子们”则无疑是“治国化民”的意识图式的体现(注:参见拙文《果戈理与中国》,见《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5—40页。)。俄国文学的为人生,其终极指向是个人的救赎,这可以用托尔斯泰的“天国就在你们心中”一言蔽之,恕不在此详述。而中国人理解的为人生,有着极为广泛的含义,它指向着贫困的消除、政治的变革、以及民族的解放,等等。梁启超“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而陶曾佑的说法更是将文学之为人生夸大到极致:“欲扩张政治,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注:《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中国近代文论选》第253页。) 这种理解看上去是很宽泛的,但从文学本体的层面上来看,它却只强调了文学的功利性(注:此观点可参见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章第四节。),这为后来中国的文论生成“政治——社会批评话语”提供了基础。这是在救亡语境中中国文论对外来影响的第一次误读,用布鲁姆的话说,这是不可或缺的“创造性曲解”。
第二次误读发生在中国文论中马克思主义内容生成的过程中。从我们早期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文学理论著作来看,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二手货。如鲁迅所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冯雪峰所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沃罗夫斯基的《社会的作家论》,等等(注:参见程正民先生《中国现代诗学与俄苏诗学》文,见黄药眠、童庆炳先生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50年代甚至日丹诺夫的种种讲话也成为我们校正自己理论方向的指南< % 近日读到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新序”,其中说到:“列宁早就说:‘现代哲学是有党派性的,正如两千年前的哲学一样是有党派性的。虽然用假冒博学的新名词或极其愚笨的非党派性掩盖起来,而在实质上,互相斗争的党派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结论》)我在二十年前却没有认识到列宁这个指示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深刻意义。直到解放以后,阅读了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才比较充分地认识了哲学史的科学定义。”可见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二手货的虔敬,以及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的。)。我们就是这样,将被苏联人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作真理恭迎进来,并且借助热情洋溢的政治气候,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机械反映论,将政治——社会学的文学理论范式发展到庸俗的极致。这一误读尽管也存在着“创造性曲解”,但很明显,它与我们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主流哲学思想是相背离的,而且其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看到,这第二次误读与第一次误读的共同之处是,它仍发生在“救亡”的语境之中。尽管在冷战时期中国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但中国高层领导人却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救亡意识,因为他们相信,中国的主要危险来自于内部的“和平演变”,并且这种“危险”在60年代达于“危机”状态,从而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这样的主导意识支配之下,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成为“亡”的危险区域,也就是救亡的前线。因而文学负载上沉重的责任,甚至文学本身被压垮,只剩下“责任”在行走。
直至文革结束,人们的所有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急剧的转折。人们从对“国家危亡”的焦虑转向对濒临崩溃的经济的关注,并且随着精神产品的市场化趋势的生成,艺术创作带有越来越明显的消费色彩。“救亡”语境终于被解构。作为在这个语境中生成的“政治——社会批评话语”成为无处存身的漂泊者。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学理论的再度失语。
有人认为,新时期以来,仍有人“固守原有的范式”,并“力图重新解释或修补原范式的部分内涵,以扩大适用域”(注:金元浦《论我国当代文艺学范式的转换》,《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 这个观点所表述的内容是可以理解的。但姚斯借用库恩的理论所提出的文艺学“范式”(paradigm)的概念不等同于“方式”,它应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制约话语形态的东西,或者是相当于福柯所说的“知识型”,是一种关系的综合体。因而它是人所无法“固守”的,可以说,人们所能固守的只是在某个范式下的言说方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范式”是可以“固守”的,则它就是可以选择的或保留的;而在我看来,在语境缺失之后,范式发生转换,它将永远成为过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社会的批评”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保留,而作为在特定语境中生成的话语,它已无法为我们所选择。
我们一度陷入了本土传统的虚无状态,失语的痛苦折磨着从压抑之中解放出来的、急于言说的每一个人。似乎我们又回到了本世纪初的情境之中。这时,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曾经带给我们数十年说话权利的西方。
3、现代西方文论:“快捷方式”与达成对话
如今,西方文论大量进入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甚至整个西方文化也以高涨的热情突袭而来,近来已有不少人在谈“殖民文化”的问题了。我想,这个问题留待专家们去争论。我们还是冷静地看一下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是怎样进入中国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文学理论“平面轰炸”式地进入中国。有人认为这是缺少历时感的进入。但我想,这种说法在80年代还可适用,但90年以后来,我们已做了大量的梳理、阐释工作,各种理论思潮的来龙去脉在大家心中已并不陌生。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另一种观念,认为西方20世纪以来短短几十年竟有多种文学理论模式相更替,因此说明它们都是短命的,所谓“各领风骚三五年”而已。甚至有人以在美国有人听到“decon”(解构)一词便嗤之以鼻为由, 来说明解构主义已经在西方“臭了街”。当然,也有人以嘲讽的口吻预言了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可能有的人会痛苦地面对从西方照抄搬来的‘新的批评话语’那昙花一现的生命,但现实是无情的,把已经被中国的现实否定了的东西作为‘趋同’的对象,这恐怕只能是一种情感寄托的方式吧!”(注:马龙潜《对文艺学的性质和发展趋势的认识》,《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我认为,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作为思潮的西方文论确是在本世纪发生过急剧的变更,批评由外部进入内部,再由内部走向更广阔的外部,或者说不断地结构,再不断地解构。但是,作为方法(言说方式)的西方当代文论却的确是以“平面”的方式存在的。如出现于本世纪初的精神分析批评,作为由弗洛依德、容格等人标举的一种思潮早已结束,但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它却保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因为无论怎样高喊“作者已死”,作品的作者维度是永远不能消失的,即使是在有人预测的“电脑复制”时代也是如此。同样,结构主义早已被解构,但由结构主义而生成的叙事理论,将为我们理解本文提供长期有效的工具。至于解构主义,虽然有人以为至今已觉不新鲜,但它所建立起来的富有创新意义的思维方式不仅在逐渐渗入西方的许多研究领域,并且也为我们今天的话语选择提供着一种哲学的方法论。比如法国批评家罗杰·马约尔谈及“结构主义变色龙”罗兰·巴特时所说:“主流已不复存在,但罗兰·巴特对今后的影响还是巨大的。”(注:参见怀宇译《罗兰·巴特随笔选》译后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第374页。)如果说“昙花一现”,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是“昙花一现”,但作为方法的浪漫主义并不是昙花一现的。也就是说,由某种思潮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往往会淅出某种创作或批评模式(不是范式)。当思潮过后,这种模式会沉淀下来,供后人选择。
于是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西方文学理论在20世纪会呈现出一种加速度的流派频仍的态势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比如人文及自然各学科急剧拓进的影响等,恕不详论。但这里不妨谈谈与本文相关的原因。在古典的西方文学观念中,文学具有神圣的意味,柏拉图曾认为诗人是代神立言的。黑格尔将“理念”引入艺术发生理论也给艺术加上了神秘的色彩。现代艺术理论也确认了艺术与巫术及宗教的密切关系。但在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艺术逐渐被纳入生产领域,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物质产品的生产,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和劳动时间。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4—165页。)。艺术在这种物质化的过程中,神圣的意味即告消解。用本雅明的观点来说明这个问题也许是最合适不过了。他认为,人类进入20世纪之后,机械复制的巨大影响使得艺术失去了它的“时空存在”性和“唯一无二”的真确性,他将这些失去的东西称作艺术的“韵味”(注:赵一凡据英文“Aura”译作“光晕”,似更可见出其神圣意味。见《欧美新学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62—163页。)。艺术既然起源于宗教,因而“与其韵味有关的艺术品的存在,从来就不能完全与其仪式的功能分开”,或者说,艺术首先具有与其仪式功能相关的“崇拜价值”,而文艺复兴后,“随着艺术的俗用化,真确性取代了作品的崇拜价值”。接下来,机械复制时代到来,真确性消解,艺术品被赋予了巨大的“展示价值”,也就是说,与古典时代的情形相反,艺术最重要的不是“它存在着”,而是“它被观照着”(注:参见王齐建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一、二、三、四节,《文学理论译丛》(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王才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五节,《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一旦艺术从圣坛上走下来,它便成为批评家们肆虐的乐园。首先,作者的意识被精神分析学者加以解剖,而后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家们则将作者抛开,开始了肢解共时文本的运作,而结构主义者再竖起来探寻作者与文本的历时原型,解构主义大师们似乎还不尽兴,便赋予读者以充分的“阅读的快乐”的权力。总之,作品成为被观照的,那么如何观照就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20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频繁更迭的一个原因,就是要解决如何观照的问题。罗兰·巴特曾在《阅读的快乐》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要是您把一根钉子钉入木头,木头会根据你钉的位置而有区别地进行抗衡:因此,有人说木头不是各处匀质反应的。文本也不是各处匀质反应的:边缘、断节,是难以预见的。……没有任何对象与快乐处于一种常在的关系之中。”(注:《阅读的快乐》,参见怀宇译《罗兰·巴特随笔选》译后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211页。)巴特的例子是说明符号学如何应付文本的,而此处用来说明我们的问题亦无不可:木头既有非匀质反应,便会有不同的钉入方法;艺术既已像后工业时代的所有事物一样被文本化,并且又有着不同的抗衡构造,也便就有了种种区别解读的手段。我的观点是,这些解读手段为我们迅速接近文本创建了快捷方式,或者说,为我们掌握言说的权利提供了武器。
我并不认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历史语境与西方后工业时代的语境已经达到契合。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两种语境的交叉之处。西方现代文论的繁盛,其背景是在“上帝之死”的口号之下对文学神圣意味的破除。文学理论,尤其是批评化的文学理论,越来越带有科学色彩,并且成为极力跳出意识形态统治而充分自律的学科门类。而中国新时期的文学是在破除“政治神话”的语境中生成的,文学逐渐成为消散了“政治韵味”的伊甸园。而西方当代文论进入中国,从一个方面说,正是基于这样的语境交叉。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基于确立言说方式的需求。在我们的文论再度失语亟需恢复言说的时候,西方当代文论则以其“快捷方式”捷足先登。当我们的救亡语境消解后,经济热潮同样带来了大量令人关切的问题,文学创作迅速作出反应,其创作量之大,内容之丰富,声音之繁杂,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然而这也使理论家和批评者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着大量急需解读的文本,他们找不到言说的方式。也就是说,此时的“失语”并不是不知说什么,而是不知怎样说。最初我们以为是视野出了问题,便去求助于自然科学理论,后来发现“三论”中只有系统论庶几可做一点文章,其余并不相通;于是发起“主体”论争,意在为个体争取言说权利,但个体的膨胀在中国的主流文化压力之下是行不通的。因此,寻找言说方式成了许多论者的共识。李泽厚在《美学译文丛书·序》中的话正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想法:“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著作翻译过来。我认为这对于彻底改善我们目前的美学研究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有价值的翻译工作比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用处大得多。”正是在这种寻找“用处”的理论背景下,我们开始了令人应接不暇的对西方当代文论的引进工作,而它也正以其前所未有的方法论的优势激活了我们新语境下的言说。正是在我们恢复言说的起步阶段,“失语”这个名词却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称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西方化”倾向(注:“失语”作为心理学概念,既指言说障碍,也指不解意义下的言说。)。
我认为,与其说我们已被这种话语的权力所征服,不如说我们对这种话语接受得还不够。所说“够”,不是说要学得像,而是要学通,从而摆脱倾听者的身份,而与之建立起真正的对话关系,立足于中国的本土文化,最终化为己有,生成中国自己新的文论话语。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丧失信心。人人都知道“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那么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土壤上,也必将形成为我所用的新的形态,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正如佛教从汉魏时期传入中国,至隋唐前后有禅一宗化为中国特有的一样。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禅宗的成形距佛教传入有数百年之久,即是说,将外来之物化为己有需要一个过程。而西方的现代文论成规模进入中国文坛还不过十几年时间,这时便大声疾呼,我们已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了,毋乃太过杞人忧天。
美籍学者成中英在论述本世纪中国哲学转化复苏的三个阶段时认为,第一代学者创建了新的体系,但缺少对传统的批判和对西方精密的了解,第二代的一批海外学子,他们“无不以其半生之力专志于西方哲学的理解和诠释工作”,然而,“就他们对西方传统凝注成的理想范型的理解来看,仍系传统的护教者。”而至今日第三代哲学家已“主动与当代西方哲学产生的问题觌面,实际上已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注:《论中西哲学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297—298页。)。这一观点也可用于我们所谈的文学理论。今天,需要的是“主动觌面”。所谓觌面,即是对话。只有达成对话,才能获得言说的权利。关在屋内寻章雕句只是独白,现在屋子已经没了,如果我们不将目光投向广阔的世界,我们就将继续停留在失语状态。
4、话语重建:回归家园与期待自由
我前面说过,中国文论语境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的缺失。我们不仅无法逃出文化的制约,而且我们真正的言说自由,也即话语的确立,必然要在文化的家园内实现。
郑敏先生在《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一文中阐述德里达的理论时将“书”与“书写”视为传统与创新的符号,二者是分而不合、合而又分的关系,“创新的过程必然是传统出走,但也必然又对传统多次回归,……但创新的回归只是片刻的轨迹运动,很快又会离开传统,再度自由地进行无形的‘踪迹’运动。”“任何创新必有反抗传统的一面,因而出走去探险,寻找新的途径,但又必然在得到自由后又会渴望回到传统再汲取母乳,因为:‘它的回归运动旨在重新振兴源头的激情’”(注:见《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第55—56页。 并可参见德里达《书写与歧异》英文本,阿兰·巴斯译,伦敦,1978年。)。我想,这一论述对我们是有启示的。无论一种创新如何“自由地进行无形的踪迹运动”,它也无法与传统割裂开来。在我们的论题中,这种传统就是中国的文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中国文化这种唯一在世界上存续了数千年的古老文化的生命力。它对我们的言说方式来说,是一种永久的制约。我们不一定再用古代文论的范畴来规范我们今天的话语,但古代文论所栖居的文化家园将永远是我们的母体,是我们汲取母乳的源头。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成熟的批评家们在出走之际从不忘再度回归。比如,上海的当代文学批评家王晓明从8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系统阅读(注:参见《追问录》,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文学理论工作者意识到古代文化的深厚内涵。然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从一个缺失的语境中寻找新的言说权利,而是为了在汲取文化母乳的基础上丰富言说的底蕴,将其转化为新时期知识型的构成部分。
甚至我们已可以在某些论者的文章中感受到“回归”对文论话语的成型所产生的作用。如上海英年早逝的批评家胡河清。他的当代文学评论大多采用精神分析、比较文学、甚至原型批评的方法,从他的行文中,我们可以见出他谙熟于西方当代的批评话语,但他却是立足于中国深厚的文化根基,将方法化为个人独到的言说方式,故而给当代文论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郜元宝在《悼胡河清》一文中说:“他对当代作家的揣摩固是精熟,对据以考察这些作家的传统文化背景,至少他经常谈论的那些方面,我们相信他确实浸淫很深,身在其中了,所以他也不引经,也不据典,随手拈来,点到为止,把传统意识真正化为运思作文的一线神脉”(注:见《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15页。胡河清文章亦见其评论集《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5年。)。一个读过大量西方哲学文学著作的年轻学者,并不因而被某种外来的话语权力所征服,原因就是他在不断地“出走”,又不断地回归。在胡河清看来,中国的文化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家园,走得越远,思之越切。他说:“进入成熟时代的作家,有在高深的层次上重新认同文化传统的必要。‘认同’不等于无批判、无反省,而是一种智慧者的沉潜,既保持着现代作家的理性批判意识,又力求对独特的民族文化之精要产生深邃的感悟。”(注:《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传统》,见《胡河清文存》第94页。)
所谓“进入成熟时代”与德里达的“得到自由”恰相契合。以我们对西方当代文学传统的接受来说,这就是我们创新的出走,而在出走与获得自由之间存在着一个过程。那些已经得到自由的便必然渴望再度回到久别的家园汲取乳汁,而在创新之中尚未得到自由的便会继续其无形的踪迹运动。我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我们目前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接受正处于这个“无形的踪迹运动”阶段。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自由阶段,继而返回传统。但如詹姆逊所说,“返回历史并不是回到旧的历史去,而是要求创造某种新的形式的历史,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表达这些内容的形式方式都要求创造一种新的历史。”(注:《德国批评的传统》,见《比较文学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4页。)也就是说,一旦自由到来之时,我们将在自身的文化土壤中种植出自己的新时代文论话语之树。
我们期待着这个自由阶段的早日到来。
标签:魏晋风流论文; 文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读书论文; 魏晋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