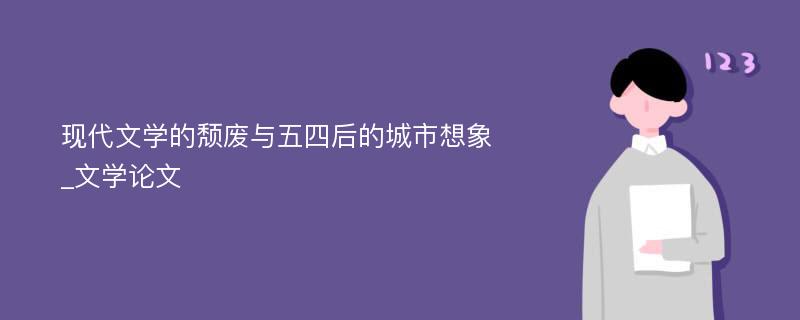
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与后五四时代的都市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颓废论文,都市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带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唯美—颓废文学”而言,虽然如李欧梵指出,中国的现代前卫作家在新文学运动中引荐了许多西方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不过我们很难在这些中国作家本人的创作中找到标志明显的现代主义特色。①然而,作为现代性问题的知识产品,现代主义的引进在中国也并非是一个全然的伪问题。公平地说,当“现代化”(modernization)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话语时,不同的文化主体面对不同的历史境遇时必然会产生出独特的现代性方案。本文着力探究的是,在当代表五四精神的启蒙现代性占据主流地位之际,一批接受了西方和日本前卫文化熏陶的作者是如何敏锐地捕捉到了都市生活的变化在个体心理上留下的跃动形象,以自己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美学认知方式加入了中国“现代性”的实践。
列文森(J.R.Levenson)这样描述上海:“到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在上海,出现了一条世界主义的花边。”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作家试验性写作的含混和困惑与上海这个通商口岸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既充当物质和文化层面的现代文明范本,又被视为帝国主义入侵的桥头堡而遭受猛烈批判这一处境有着密切联系。
对上海通商和租界情况做的研究表明,虽然上海居民对19世纪中叶涌入中国的西方物质文明一开始持怀疑态度,但很快,租界内完善的公共设施和井然有序的管理方式就征服了本地人。较之残破、丢脸的广大中国内地,租界确实提供了一扇中国人可以借之感受“先进文明”的窗口。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无论租界和华界,上海的城市发展都达到一个新高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塔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些殖民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仍远远落后于上海。”③上海时尚生活的步伐紧跟伦敦、巴黎和纽约,确乎成为破烂的中国衣裳上的一条世界主义花边。
这个时代的上海以它无可争议的物质现实说明,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向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成为了一种现实。上海的世界性魅力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迅速将对“现代”的礼仪式崇拜转化到生活的各部分。
那些由新造的摩天大厦、百货大楼、电影院、咖啡馆和舞厅所构成的城市景观成了培植都市颓废文人想象力的场所,如作为消费社会典型场所的咖啡馆。咖啡馆对上海唯美—颓废文人的重要性在于它代表了成熟、优雅和精细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从乱糟糟的第三世界街头进入其中相当于一次内外场景的转换。张若谷的一篇散文《俄商复兴馆》曾这样描述了咖啡馆的氛围:
坐咖啡里的确是都会摩登生活的一种象征,单就我们的上海而言,有几位作家们,不是常在提供“咖啡座谈”生活吗?大家一到黄昏,便会不约而同踏进他们走惯的几家咖啡馆。这里的“俄商复兴馆”和那边的“小沙利文”,是他们足迹常到的所在,他们一壁慢吞吞的呷着浓厚香淳亚拉伯人发明的刺激液质;一壁倾泻出各人心坎里积蓄着的甜蜜,彼此交换快乐的印象,有时在灯红酒绿之下,对面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向他们细细地追诉伊的已往的浪漫事迹;轻听一句两句从钢琴和提琴上发出来的旋律……④
但与此同时,外来文化的殖民身份又不可忽略,如魏菲德(Fredric Wakeman)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每天都体验着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和对外国入侵的愤恨。在上海,矗立于外滩的风格迥异的西洋建筑注解着中国不只受到了一个宗主国入侵的事实。这里既有新古典风格的英属大厦: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海关大厦、大英银行和汇中饭店等,也有代表新兴殖民势力的美国现代建筑:国际饭店、沙逊大厦和四行储蓄会,它们在高度上已经超越了英属建筑。当然,也不能忽略有着漂亮大理石门面的日本台湾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意大利邮船公司,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一个具有民族自尊心的激进中国知识分子眼中,帝国主义的物质在场是一个无法抹去的威胁。据阿克巴·阿巴斯(Ackbar Abbas)的理论,从建筑角度来看,摩天大楼对这个城市的俯瞰象征着赤裸裸的殖民欲望,摩天大厦以它坚不可摧的主体性使自身变成需要保持距离来被凝视的对象,“于是建筑具有了潜在的危险性,它把我们所有人的目光——无论是本地人还是观光客——都转化为一种游人对一个稳定的和纪念碑式的意象的注视”。⑤由于摩天大楼鼓励仰视和充满崇拜感的视觉方式,它的存在时刻提醒着殖民势力的物质实在性。
尽管殖民主义是这个城市生存现实的一部分,但20世纪20、30年代集中于上海的有关民族主义文学与西方“优等”文明的压迫之间却并未形成我们期望中的对立。我认为,这与在中国的殖民势力所采取的特殊统治形式——通商口岸制度有关。
中国通商口岸发展出来的贸易管理和文化交往制度与其他直接或间接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有着巨大差别。简单地说,由于殖民者没有在中国建立完善和全面的殖民统治结构,所以即便西方人的权威在租界里被明文确认,但中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却可以对此不予理会,如白鲁恂(Lucian W.Pye)所说:
在其他国家,殖民统治包含很复杂的人际互动,推动现代化的当地人与殖民国家之间,有着直接和强烈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一般中国人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交往:对他们来说,所谓外国渗透的威胁和“不平等条约”的恶行,只是没有体验的抽象概念。⑥
殖民者形象虚化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作家可以不去注意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按李欧梵的说法,中国作家对自己的身份有着充分的信心,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中国的现代作家并不使用任何外国语写作,而是持续地使用中文,将它视为唯一的语言。”⑦因此,“尽管……上海作家带着喧哗的西化色彩,但他们从不曾把自己想象为,或被认为是因太‘洋化’而成了洋奴,从他们的作品里,我得出了这个明显的结论,即虽然上海有西方殖民存在,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却从不曾出过问题”。⑧正是由于通商口岸独特的殖民体制,中国知识分子尽可一意拥抱西方的现代“先进”文化,并以此置换“黑暗”“落后”的中国旧观念,而不必在反抗/通敌的黑白二元间做出选择。实际上,在上海现代作家笔下,外国殖民者的形象几乎是缺席的。相反,他们的叙述往往预设一个理想化的西方来置换现实存在的殖民主义。
20世纪20、30年代,如施蛰存所说:“在上海新文学史上,算是活动过一个短时期的唯美派、颓废派”⑨。像波德莱尔、王尔德、邓南遮、史文朋等带有浓重颓废色彩的西方现代作家,被当时文化界视为代表了世界文学的最新潮流。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上海出现一批在以后的正统文学史上将被称为“颓废”、“病态”的作家,他们充满兴味地注视着这个城市的霓虹魅影并把新兴的城市生活形态转化为新的文学想象力。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的现代文学史被“重写”的呼声淹没时,这批作家的身影重新进入了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他们之中既有大革命后在左翼的激进前线与都市文化的颓废之间徘徊的准革命文学家(叶灵凤、田汉、陶晶孙),又有邵洵美、腾固这样政治态度不明,耽溺于唯美想象的颓废作家。正是在这众多的文人文本中,作为现代性实践一部分的“颓废”的面孔渐渐浮现出来,但却是以与西方不同的面孔浮现的。
卡林尼斯库认为,西方文学中唯美—颓废思潮的产生与基督教的末世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线性进步的世俗化时间观愈来愈成为主宰性的话语,然而进步的尽头是不可避免的末日审判,人们与时间的联系越强,越会感到天启灾难的迫在眉睫。虽然进步这一事实不可否认,但人们体验进步的结果时却带着失落与疏离的焦灼感。⑩正如魏尔仑(Paul Verlaine)在十四行诗《忧郁》里宣告的:“我是处于衰败之末的帝国”。在现代艺术家眼里,资产阶级建立的进步与民主的社会充满了腐败和危机,正无可挽回地走向末日,于是,“进步即是颓废,反过来,颓废即是进步”。(11)源自1850年代的法国的欧洲颓废精神正是在对资产阶级文明——连同它标榜的进步、理性、人道主义等等——感到厌倦后,转向了精微的精神领域和感觉世界,他们表面上的冷淡和孤立,其实蕴育着反现代文明的英雄气概。沙尔·克罗斯(Charles Cros)写道:“在经历了使我们孤立并使我们不同于过去的如此重大的灾难后,正是我们一直相信着艺术、相信着精神的王国。”(12)资产阶级用理论和制度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的真实“历史”在颓废者眼中终将成为断瓦颓垣,只有超时间的梦境和精致的激情可以恒久存在下去。
与欧洲现代艺术家反庸俗的布尔乔亚现代性的精神性态度相比,中国现代作家的唯美—颓废文学带有深深的通商口岸的物质烙印。中国现代作家的颓废气质的作品既不超现实也不能在资产阶级的文明秩序之外发现任何东西。一个例子是,“颓废主义”在中国作家的描述中往往和物质感官上的“享乐主义”相连接。黄忏华就把“官能底交错”作为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颓废派这一派底人……他们以为现代底社会是没有趣味,丑恶得难堪,不愉快之极底,所以不得已光是自己底快乐,也就满足。这个最后一段,就是享乐主义者底心情;他底所谓快乐也只是肉体上就是官能上底快乐。他们实在是官能万能底人。”(13)对中国作家而言,“颓废”很难称得上是一种对文明秩序的追问,更多的是一种个体感性存在的确立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上的自以为是。通过考察一些西方唯美主义文本如《莎乐美》、《道连·格雷的画像》、《死城》等在中国的流布可发现,上海唯美作家对文本美学上的内在严密性几乎漠不关心,但唯美主义文本中显现的惊世骇俗的感官意象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海派唯美—颓废作家在留学和都市文化生活中培养出的西方化趣味,使其可以把这些作品反常、堕落和偏执狂的主题当作有魅力的风格,借之震撼麻木和保守的现存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一向与民族主义、革命、无产阶级这些充满历史意识的集体主义名词相关联。乔治·卢卡契(George Lukacs)在其著作《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中论述道,以前的现实主义小说描写的个人首先作为个体存在,具有先验的、不受社会历史束缚的性质,而与各国民族意识的复兴俱来的是“现代性”的历史观,个人感觉到自己生活在共同的时代氛围里,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对个人意识的作用越来越强烈。这一体认一方面增强了人们的历史主体意识,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民族历史是与世界历史的整体运动密切关联的,历史发展的趋势必然要走向黑格尔式的“世界精神”,即现代理性价值的全面实现。(14)作为历史进化论的鼓吹者,卢卡奇的《历史小说》本身便隐含了西方理性精神运动的普遍性契机对人类最终解放的承诺。从这个角度看,上海唯美—颓废作家的生活体验和创作实践,可以说表明了一种试图从历史限定论的教条主义中脱离出来的企图。虽然在中国其他地区居民眼中看来,他们文本中的物质色彩代表着下流、腐朽的外国生活方式。
从一开始,唯美—颓废文学就和抽象的历史—社会意识相混杂。然而,20、30年代的唯美主义文学的实践者越来越发现美学的虚妄性与现实社会斗争的脱节。于是才有了徘徊于“象牙之塔”和“十字街头”之间的苦闷青年。因此,如果说在上海唯美—颓废作家那里有什么对立的话(相应于西方颓废精神中蕴含的美学超验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对立),那也是植根于都市文化氛围的“天才”人物与从第三世界的殖民情境中生发出来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要求之间的矛盾。换言之,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对“提前现代化”了的都市空间的沉溺,与启蒙现代性蕴涵的个人与民族意识的结合这两类处于不同场所的“现代”,在同一空间被强行整合时形成了内在紧张感。如周全平在《幻洲》里声称要在繁华都市生活的“沙漠”中创造一个充满“咖啡,葡萄酒,香水,红艳的肉,颤动着,娇喘着……”的“空幻的世界”。在此,个体在都市生活中的苦闷和对社会的叛逆是可以互训的,“自从这娇艳的五月把成熟的春意带到荒凉的沙漠中以后,烦闷益发象毒蛇一样把这水平线下的爵士们纠缠住了,死了的热情在这媚人的五月中又醒了转来。桃色的悲哀,咖啡店的春梦,黄金的诱惑,啊啊,家国的悲戚,民族的痛苦”。(15)
也就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现代唯美作家具有了一点“颓废”色彩,尽管他们的审美方式是彻底世俗化的,尽管他们的写作无论怎么看都在历史之内。但阴差阳错的是,历史本身在此出现了混乱,上海“十里洋场”的资本主义文明(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说叫做“畸形繁荣”)虽然给城市居民带来了抑制不住的世界主义兴奋,但它和现实中国的隔离使其难以被放到历史时代的大框架中。中国现代作家越是沉迷于它的物质表象,越会感到自己坠入想象性的虚幻世界。虽然这一虚幻世界既缺乏超验的美学深度,更谈不上欧洲现代主义式的否弃资本主义文明价值,但它所营造的幻觉气氛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大叙事而言仍可称得上“颓废”。
当上海现代唯美—颓废作家向这个城市移情时,在他们眼中,具有异域风情的都市新异景观仅是作为“美”的象征物出现的,对上海的审美迷恋,只可能存在于把上海视为一座超越现代中国的混乱和邋遢的文化纪念碑的膜拜心态中。海派文人自己必须先被城市世界性所表现出来的神秘力量所俘获,才可能把它笼罩着神秘光环的“气息”(aura)传达给读者。
那么,这一具有崇拜价值的“气息”的来源何在?我认为,正是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的特殊殖民性和海派文人远离生产的旁观者身份,共同造就了海派唯美—颓废作家的审美恋物症。
如前所述,由于通商口岸的特殊体制,压迫性的殖民当局在城市居民生活中实际上是缺席的,这使得中国现代作家得以不必担心自己的本土身份而狂热拥抱西方;同时,尽管海派文人的创作常被正统的京派知识分指斥为“商业竞卖”,(16)但在文艺品市场上,比起真正迎合市民口味的“鸳鸯蝴蝶派”来,唯美—颓废作家通常占据的位置并不醒目。即使像邵洵美这样家业较殷实的文人也几乎完全不谙生意之道。在陶晶孙的《毕竟是个小荒唐》中,当舞女弥吉林看到主人公递给别人的名片上印着Prof·Dr的头衔时,立刻讥笑道:“你又在发挥Petit Bourgeois的根性了。你晓得什么Dr·什么Prof·有什么用途呢?在这儿,只有金钱是第一,无论你是什么大博士,一文价值都没有,用不着说的事体原来就用不着说,你说一句你是你便好了。你在大学里还不能用Dr·来吓学生,难道在饭店里跳舞厅里会适用Dr·呢?我们不是金钱便是性。性同金钱以外不应该有什么。”(17)
在此意义上,虽然唯美—颓废作家热烈地歌颂这个城市物质化外观,但被亚当·斯密(Adam Smith)揭示的资本运作的秘密对他们几乎毫无意义。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文人,他们一方面和贫穷的中国保持着舒适的距离,另一方面又与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发生疏离,这就使他们成为这个城市的旁观者——城市是作为审美对象和宗教式的庆典仪式而被呈现的。
在这方面,我们来看叶灵凤的小说《禁地》里对主人公室内装饰物的描写:
当中的一方人造象牙镶边的面镜、边上雕刻着很精细的近代风的花纹。镜子的左方排着五个参差的香水瓶。三瓶的牌号是Houbigant.。颜色两瓶是浅黄,一瓶是纯白。每一只瓶的下方贴着关于瓶内的香水用途的注明。我们可以看出浅黄色的两瓶上是Lotion和Perfume,那白色的一瓶上是Toilet.。其余两瓶的瓶式都很精巧,一个表形的牌号是Piver,一个尖长形淡绿色的牌号是Cappi。(18)
这个化妆室的使用者显然是个时髦人物,他身上所有一切都是由一系列的国际消费文化符号堆积起来的。我们看到,一种异己的、西方化的、先进的文化形象点据了小说的中心位置,海派唯美—颓废文人所追求的“摩登”的结构成分已转移到别处,越过他们自己所属的国家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经验,转移到了宗主国的世界性资产阶级消费文化市场中。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物”的审美崇拜身份不可忽略。一个社会化的、生存在严密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熟练操作者,决不会忽略物品的交换和牟利的本质。但从文人的视角看,对商品的占有固然有着物质性的一面,可是更重要的则是从商品中升腾起来的异域“气息”,它代表了一种精神补偿力量——是现实的中国生活中缺失的、不受限制的和刺激感官的存在。
以审美幻想抽干资本的本质,以第一世界的绚烂外表取代第三世界的现实存在,这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唯美—颓废作家的表述策略。这种置换产生了明显的后果:资本主义文明那些消费性质的表征层面从整体中被切割出来,成为单独的、静止的被体味的对象,而资本主义作为整体系统的运作方式却与个人的经验相隔离。于是唯美—颓废作家对商品的凝视变成了一种暴力行为,把对象抽象化和客体化,祛除了所有参与性的深度体验。这一凝视过程本身形成了一项新的美学内容,最好地体现了通商口岸城市在美学层面上的自我异化。
在唯美—颓废作家的创作中,除了商品以外,另一个层次的都市魅惑来自女性,她们以传统中国文学中从未有过的官能性和符号性颠覆了传统叙事框架中具有稳定身份架构的形象。而在文化形式上,她们与商品一样,充当了男性作家想象现代生活的欲望载体。如叶灵凤在小说《流行性感冒》里所描述的一位时髦女子:
她,像一辆一九三三型的新车,在五月橙色的空气里,沥青的街道上,鳗一样的在人从中滑动着……迎着风,雕出了一九三三型的健美姿态:V型水箱,半球型的两只车灯,爱莎多娜·邓肯式的向后飞扬的短发。(19)
在这个时代,时髦女郎很快成为上海的都市传奇,象征着城市可以自我提升,达到超越历史的高度。这些女性通常缺少丰满的性格。她们形迹可疑、举止神秘,我们无从知道她们的过去和未来,但她们的身体却极度开放,具有触摸感和曲线美,身上各个装饰部分都说明着自己和世界时尚潮流的同步。尤其重要的则是她们的不贞。不贞的现代女性令海派文人如此着迷的原因在于,她们混乱的国际身份及模糊的价值观念带有虚幻的“异”的色彩,其飞扬、不羁的特征是对传统性道德的反叛。通过对她们身体的盗用,不贞女性被转化为隐形的西方“他者”的象征符号。请看邵洵美的《蛇》:
在宫殿的阶下,在庙宇的瓦上,
你垂下最柔嫩的一段
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裤带
在等待着男性的颤抖的勇敢
我不懂你血红的叉分的舌尖
要刺痛我哪一边的嘴唇?
他们都准备着了,准备着
这同一个时辰里双倍的欢欣!(20)
在诗中,邵洵美不仅把蛇和女性的身体作了错综的处理,而且还要在对象的身上做爱。虽然表面上并没有点出对方的都市身份,但“蛇”的比喻(暗示着放荡、危险和身体的质感)以及对感官快乐的极致追求(据亚里斯多德的说法,蛇分叉的舌尖有利于它双倍地享受美味),显然表明这是一个不贞的女体。她是男性叙述者储存跨身份、跨地区的国际想象的容器,透过她的身体,主体实现了摆脱阴暗的现实束缚的愿望,直接进入了一个散发着异质文化“气息”的美感世界。而审美感的产生又与主体把破碎的都市空间对人感官上的刺激色情化息息相关。在邵洵美眼中,与都市放荡女子的交合就意味着主体一次短暂的升华——在象征性的仪式过程中克服了主体心理空间内残存的第三世界狭隘性而引发了一阵探询都市秘密的神奇快感。
毋宁说,摆脱了生产和交换范畴的商品和水性杨花的不贞女性,是上海的异国风味造就的奇幻境界的寓言性表征。当主体不能确定自己的稳定身份时,对她们“窥淫癖”(Voyeurism)似的凝视和变态的占有起到了填补心理空虚的作用。实际上,不贞女性五色令人目盲的身体语言和商品的意象符号在逻辑上是同质的,它们都唤起一种脱离自身实质的审美感受,而且相互融会。在“通感”的氛围中两股气息交汇了,都指向一个虽然在中国留下了足迹,却还根本没有实现的第一世界的奇域。在此意义上,唯美—颓废作家真正成为了城市梦游者。
注释:
①Leo ou-fan lee,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The Cultural Agenda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载《学人》第4辑,第511页。
②Joseph R Levenson,'The Past and Future of Nationalism in China',in Joseph R Levenson(eds.)Modern China:An Interpretive Anthology,London:Collirer-Macmillan limited,1970.p.11.
③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二十一世纪》第9期,第18页。
④张若谷:《俄商复兴馆》,转引自《上海文学》2001年第2期。
⑤Ackbar Abbas,Building on Disappearance,in Simon During(eds.),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9,p.148.
⑥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二十一世纪》第9期,第16~17页。
⑦⑧李欧梵:《上海的世界主义》,《二十一世纪》第54期,第44、45页。
⑨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⑩Matei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155-156。
(11)Ibid.,p.155.
(12)皮埃尔·布吕奈尔:《19世纪法国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9~300页。
(13)黄忏华:《近代文学思潮》,商务印书馆1924版,第120页。
(14)George Lukacs,The Historical Novel,Boston:Beach Press,1963,p.23-25.
(15)骆驼《周全平》:《我们的幻洲》,1926年6月12日《幻洲》周刊第1期,第153页。
(16)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1933年10月天津《大公报》第8期。
(17)陶晶孙:《毕竟是个小荒唐了》,《陶晶孙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
(18)叶灵凤:《禁地》,《灵凤小说集》第427页,上海现代书局1934年版。
(19)叶灵凤:《流行性感冒》,《叶灵凤小说全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345页。
(20)邵洵美:《蛇》,《诗二十五首》第55页,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版。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二十一世纪论文; 历史论文; 邵洵美论文; 作家论文; 上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