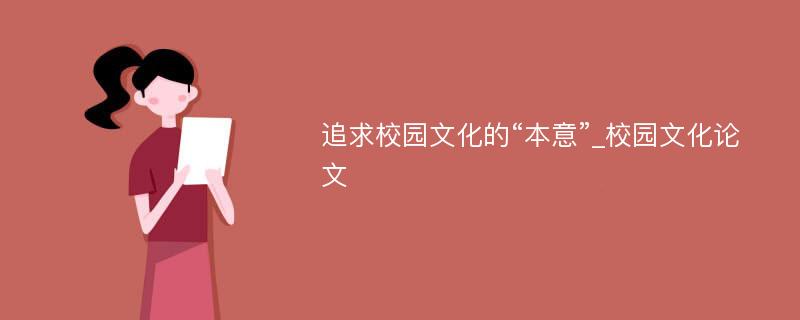
追寻校园文化的“原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意论文,校园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校园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但是在教育研究中又无法回避,并且历久弥新的课题。通常而言,校园文化是人们从事学校教育活动时所创造的物质、精神成果及其过程,一般地在层次上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种分析由末到本、由表及里、由目至纲,因此对校园文化进行如此的概念界定和结构划分,在理论上无可厚非,然而在实践当中,我们却难免深感在这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面前身陷尴尬。有的学者提出,校园文化的形成要注重校园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建设[11,然而这种影响表现在何处、程度有多深,我们无从考证。有的学者提出校训校风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各个学校的校训校风都是在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个性,以展示其独特的校园文化风格”[2],然而我们发现连最传统、最广泛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种号召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生的笑话之中,被当作戏谑的对象,何来校园文化之有呢?还有的学者提出,要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进而建设校园文化[3],然而比比皆是的第二课堂素质课、形形色色的社团活动到头来却被学生嗤之以鼻,诸如此类的活动在怨声四起中,非但没有促进良好校园文化的形成,反而助长了形式主义之风。我们不禁开始反思:是不是学校里面多种植被,学生就能被熏陶出环保的意识?是不是每个教室中都贴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标语,就能陶冶出学生勤奋刻苦的良好学风?是不是多组织几次以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冠名的活动,就能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学生内心?本文试图以解释学为理论依据,揭示“理解”在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理解”与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虽然研究理解的哲学不仅仅只有解释学,但不可否认解释学是专门研究理解的学问。从整个解释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大致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理解观,一种是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的“意义复原观”,另一种则是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意义生成观”。前者认为意义是客观的,表现为作者对文本所表达的“原意”,拒绝读者个人观念的解读;后者认为意义是在对话中创生的,表现为读者与作者的“视界融合”,意味着新的意义的生成,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交融,最终达到价值认同。由此可见,“意义复原观”是实证主义的,其目的是为了理解作者赋予文本的客观意义,但我们既不能保证可以真切地获得作者的原意,也不能保证心服口服地接受作者预设的内涵,因而一味地卑躬屈膝于作者的“原意”前,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如果一种解释学把理解当作是原意的重建,那它无异于恢复了一种僵死的意义”[4]。因此,只有通过主体间性的对话,包括读者与作者的对话以及读者之间的对话,才能达到对意义的真正理解,才能形成真正的价值共同体,因而这种意义对于理解者来说才是生动、有用的。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实际上是解释学中从“意义复原观”到“意义生成观”的过渡。在海德格尔之前的解释学传统中,理解一直当作是一种理论意义层面的“理解”,它试图通过一种理性的方式去认识和解释有意义的东西,而与之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所谓的理解首先自己剥夺了它的纯‘认识的’性质,他认为那种认识论的理解是次要的,是从一个更普遍的解释学的理解中派生出来的[5]”。因此认识不同于理解:认识追求主客体的相互吻合,认识者处于被动的地位;而理解追求的则是意义的生成,理解者处于主动的地位。
校园文化中的教育内涵不是通过认识的方式为学生所获得的,学生是存在于文化中的主体,是以一种主动的方式理解建构文化现象背后的教育意义的。因此,学生必须通过自身对文化现象的亲历与感悟,理解蕴含于其中的教育内涵,理解这种文化现象与自身存在的关系,并在这种意识上的理解之后,才能够更好地养成自己的灵魂与行为。可以说文化育人重在受教主体对于文化现象的理解,它是一种“慢教育”的形式,是一种循循善诱的“软教育”,而不是强硬的规训手段。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对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的期待却有一种急功近利、甚至是将其神话化倾向。文化现象往往被当作是刻板的教科书,我们要求它的教育功能立竿见影,要求它能够像戒尺一样,时刻督促着学生,但却忽视了学生对校园文化中教育内涵的真正理解。
二、校园文化的育人过程拒斥“理解”
我们呼吁对校园文化进行理解,倒不一定是说我们曾经没有进行理解,而是我们的理解往往没有实现真实意义的生成。
一方面表现为我们将理解等同于学生对文化现象中预设意义的“认知”,学生不是基于自身所处的真实情景,没有结合个人的“前结构”或者说是“偏见”进行理解。在伽达默尔看来,人总是在历史中理解历史,总是带着个人的偏见进行理解。“一个个别主体与其生活世界交互作用的成果,即是意义的来源”[6],因此生成性理解一定要基于学生的生活世界才能够进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我们将理解等同于学生自说自话的私人话语,学生没有机会在自我与文本、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对话中进行理解,更谈不上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达到“融合视界”这一“更高形式的普遍性”。即便是强调个体的生活世界,反对追求原始的本意,但生成性理解也绝不是要让学生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理解乃是越出个体的有限视域,勾勒出各种意义路线”[7],对话过程中的每个参与者都是平等的,可以相互质疑、相互挑战,最终的目的是达到一个理解的“融合视界”。因此,生成性的理解既有个人的特殊性,又有不同个体间相互交融的普遍性。
实际上,我们对校园文化教育功能的实现抱有理想化的态度,两者在不证自明中被想当然地联系在了一起,仿佛校园文化一经出现,教育目的便水到渠成。校园文化成了一种封闭性的自娱自乐,只有空洞的概念躯壳,而丧失了真正的意义灵魂;文化育人的理念也异化成为工具理性的驯化与操控,讲求效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对文化意义的体验,无丝毫人文关怀可言:这是校园文化存在性的危机与教育价值的危机。校园文化好像是飘在天上的浮云,是学校教育的空中楼阁;我们虽然在现实中往往打着校园文化的旗号,义正辞严地强调陶冶和感染的文而化之,但对校园文化却真的只是在雾里看花。显然,校园文化与生活情境和学生主体相互分离,是我们过分功利性质的教育造成的结果。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先预设出一个意义,然后机械地构造我们一厢情愿的文化氛围,但却往往忽视了学生这一最主要的参与者,忽视了他们身处的真实情景,并且试图“防止”他们对自己“遭遇”的文化环境进行生成性理解,因此我们有理由呼吁对校园文化“失落的意义”进行重新理解,让“生成性理解”成为校园文化、教育意义以及学生主体之间得以相互沟通的桥梁。
三、校园文化的“原意”追寻之路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校园文化的“原意”的理解应当是在真实生活情境中通过对话的方式而创生的,是通过生成性理解而获得的。我们对校园文化之“意”进行“追寻”和“拯救”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校园文化的意义何以可能的追问,这一问题涉及校园文化意义本身,是对校园文化意义的存在性的拷问,校园文化现象所负载的意义从何而来,这种意义是如何发生的;同时,也在实践中为校园文化的建设和优化提供了根本性的参考和建议。
1.让校园文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校园中的文化情境是“制作”出来的而不是“营造”出来的,因此学生对待文化情景的态度往往就是将其当作任务来“应付”,而不是当作生活去“体验”。看起来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实际上对于学生来说只是空洞和抽象的形式,只有让校园文化成为学生生活必要的一部分,才能够使得“理解”成为可能。很多被设计出的文化情境脱离学生的生活,导致学生“被束缚在一架由异在的意志所支配的机器中,他顺从地做着那指派给他的工作”[8],学生从主体异化为了客体,对周围的情景逐渐变得冷漠与迟钝。比如时下流行的红歌进校园活动,很多学校试图通过组织全校范围内的红歌大赛来创设校园红色文化,以此为契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乍看起来,唱红歌与爱国教育确实有着深刻的联系,但现实的效果却只是对设计者一厢情愿的尴尬讽刺。这倒不是说不应该鼓励学生学红歌、唱红歌,而是要求我们对红歌文化于当代学生的教育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由于当代学生对于革命年代不甚了解、更谈不上亲身经历,红色经典也难以引起他们心中的共鸣,红歌对于学生来说可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因此学生很难理解红歌的文化内涵。
2.重视学生在理解校园文化过程中的“参与性思维”
学生的参与性思维在理解校园文化过程中的体现就在于对文化情境进行自主的理解,进而剔除虚假的意义,同时构建真实的意义。现实中校园文化“意义的失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假定每种文化现象所负载的意义是既定的,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只能被认识的实体,因此我们顺理成章地将现象与意义公式化地一一对应起来,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映射关系能够并且必须为所有学生所接受。可见,我们剥夺了学生对校园文化现象进行理解的权利,将这种理解降格为一种对象化的认识过程。这样学生就不免感觉到,文化现象与意义是可以斩断的,意义可以脱离现象而存在。我们说,这种文化现象只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独白,表现为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它模糊了意义产生的过程,而是将所谓的文化意义“还原为一种中央集权式的正统,或独白式的语言”,[9]它拒绝个人理解的挑战,拒绝多元理解的存在。因此,学生对于文化场景的理解永远不是“我”在说,而是替“他”说。所以说从校园文化的建设到教育意义的呈现,都不是设计者闭门造车的事情,而是要倾听学生对于不同文化现象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确文化情境对于学生的真实意义,从而进一步改善校园文化。
3.尊重不同学生对于文化意义的多元理解
工具理性、效率至上,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教育愿景,往往会忽略甚至是扼杀不同学生对于文化情境多元化的解读。即便是再丰富的文化现象,也无法掩盖刻板规范之下单调的教育意图,反而只能导致华丽的外表显得更加的苍白无力。学生置身于这种“霸权”面前不得已而失语了,个人的观点得不到应有的表达。特别是当自己的观点与那种预设的文化意义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的时候,矛盾也得不到很好的和解;当自己对所谓的意义产生怀疑时,也由于受到一个假想的“大众观念”的恐吓,内心真实的意见也消解了。所谓标准化的意义反而成了学生价值观养成、主体意识培养的枷锁,异化了原本应当是多彩的意义世界。然而每个学生都有着不同的阅历,因而有着多元的经验世界,对于同一事物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的。对于文化的理解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哲学解释学“恢复了‘成见’在理解中的‘合法’地位,主张在不同视界的融合中,可以通过对话,达到相对的、多元化的意义生成,强调理解的过程是消解对立、彼此融合合理因素的过程”[10],对于不同的理解我们要采取协调和包容的态度,文化背后的意义也只有在对话的过程中才能够变得丰富多彩、更富有生命力。因此,我们必须让学生成为对校园文化进行理解的主体,构建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意义世界。但是,这也不是要让学生在校园文化意义的理解中坠入相对主义的陷阱,而是要让学生在个人与文化环境、我与他人相互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将校园文化的意义不断扩大和丰富。由于“教育意义既不是完全属于个体主观性观念的赋予,也不是教育本身的‘原义’,它是学生的精神世界与教育的意义形式融合后的产物,是一个‘第三者’”[11]。所以,校园文化的意义也是一个“视界融合”的产物,是多元主体相互对话的产物。
标签:校园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