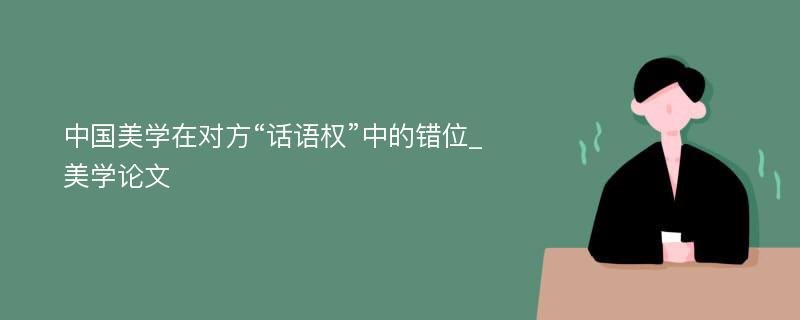
中国美学在他者“话语权势”中的错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他论文,权势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美学在这里指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的美学,它从先秦时代一直绵延到清末时期。这样来界定,并不是说现代以来的中国没有美学,而是表明,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的美学是有别于西方的,也是有别于现代以来中国国内的主流美学思想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在现代以来已失去了它在艺术话语领域中的主流地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曲解,或受到了漠视。
应该承认,在当代的美学研究中,如采用传统的中国美学体系已不能适应新的艺术和新的艺术意识的需要,并且由于借鉴和移用了西方美学体系,也使得当代的中国美学研究比起古代来就有了新的范畴系统和思维方式,这可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正像当代的生物工程技术一样,在改良生物品种的同时,尽可能地使生物基因保持多样化,是未来发展的可靠保证,在人文学科中保持和重新发掘古代的思想传统,也是学科建设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可靠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探讨中国美学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错位问题,便是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针对性的一个研究课题。
一、从话语权势到“东方主义”:错位效果理论探源
话语权势,也可称之为话语权力(the power of discourse)。将话语同权势、权力结合起来看待,这始于法国的解构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科。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包括《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论知识的颠覆》、《监督与惩罚》,以及3卷本的《性史》等书中, 都涉及到一个主题:话语的权势问题。
福科的理论带有一般解构主义的共性。他认为,所谓真实性并不是对象的一种属性,而是在特定理论框架中体现的属性,假使某种理论宣称它已发现了久久求索的真理,那么该真理也不过是该理论系统内部的逻辑产物,譬如中医的“气血”概念找不到在西医中的相应词汇来传迻,甚至也没有解剖学上的依据, 但它在中医的望闻听切的手段中有所体现,并且根据气血方面的病理学辩证施治,也确可达到治病救人的功效。这样一种非本质主义的真理观算是解构主义者的共同观点,再进一步,福科有他个人的见解。
其他解构主义者,如德里达认为,话语并不反映现实,话语只是反映了话语体系的内部关系,可是福科还是看到了话语同话语之外的世界的联系。福科认为,话语是从一定角度来表述的,话语也往往包含了一种评价,另外话语的表述有自己一套约定俗成的惯例,这样,话语就体现了一种权势,在话语中描述的客体是被话语权势所支配的,话语的受话者受到话语的指令,再有一点则是话语还提供了话语主体以合法性的地位。如“老鼠是一种有害动物”是一段话语,在该话语中,老鼠生存的合法性就被剥夺了。本来从纯生物学的意义上看,老鼠即使不比人更有价值,那它也和猫、松鼠等动物一样是生物进化史上的一件珍贵作品,可在该话语中,对受话者也有须以鼠为敌的诉求,否则就有敌我不分之嫌;再者则是这一表述就使人有一种价值评判原点的作用,所谓有害、有益,都只是以人的利益为价值尺度,当对人有益时,砍伐森林不算错,而对人不利时,一只虫子吃了一片林中树叶也算罪过。
福科的理论对于话语权力有较多的论述。他在3 卷本的《性史》中,认为“应当建立一门不再把法律当做模式的规则的权力分析学”,对他来说,权力的根源不是指国家机器和官员的权位,“权力不是制度、结构、力量……而是在一社会中用于指复杂战略分析情境的名称”。〔1〕在福科看来,话语体现了权势,而权势又可以提供话语, 如各门学科或专门话语累积起来,组成公共机构,包括高校、研究院、法院等,反过来,这些公共机构又生产出新的话语,如教学讲义、研究报告和法院文告等。
福科的话语理论发表后,很快地在文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以及政治学等层面都产生了影响。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实际上是在福科话语权势的理论下,写出了他的《东方主义》(1978)和《文化帝国主义》(1993)两本书。他认为,虽然话语都可能体现了某种权势,但不同话语的权势是不等值的,有强势话语和弱势话语之分。如课堂师生问答中,一般地说教师一方代表了知识的发布者和学生成绩评定者,所以他的话语是从强势立场发表的,学生则处于弱势话语的地位。在《东方主义》中,赛义德指出,在西方文化界,西方学者凭着自己的强势话语,对于东方社会和文化常有严重曲解和歧视,为西方凌驾于东方提供了一种道义上的合法性依据。如哥伦布到达美洲被说成是“发现”美洲,其实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上千年就有印第安人在那里生活了。这种“发现”就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来作为评价世界史的尺度。非洲一位学者也曾以泰国“人妖”现象为例来提出了类似见解。泰国是一个佛教的国度,该国文化主要就在这一框架下定位,但是,当年的欧洲殖民者是从猎奇角度看到了泰国的去势男性——人妖,他们是一种下等的从艺者和从事色情行业的人——于是就以人妖文化来作为泰国文学的代表,而这一明显的误解又由于泰国旅游业为了招徕海外游客,也就以此作为该国文化的表征。可以说,早期殖民者是以武力为后盾来发表强势话语,而在当代则是以西方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强势来作为话语权势的后盾的,它使第三世界的文化“心甘情愿”地处在被人命名的弱势话语的地位。
应该说,“话语理论”的火药味是很浓的,它的激进色彩使其在言说中常有过激之处,可是它也确有一些真知睿见的成分。在美学领域,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今就可能面临被强势话语误指的状况。
二、艺术本质观方面:艺术是什么对艺术如何是的错位
每种文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艺术,同时也就伴随有自己的艺术观,这些艺术观可以有相似之处,也可以极不相似,根本就不是对同一问题言说的状况。譬如,佛教文化中的艺术推崇“象教”的威力,认为造型艺术可以把观念性的东西用具象来表达,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教喻效果。佛教的门廊,竖立着横眉怒眼、虎视眈眈的四大金刚,它们注视着入庙的来人,仿佛稍有对佛的不恭就会受到金刚们的惩戒。在庙内的大殿里,则是佛的慈悲、宽容、祥和的容貌呈现在眼前,使人能有一种真正觅得安全的感觉。如果说金刚的伎俩是逼人就范,那么佛的所为就是诱人信服,这种软硬兼施的象教确实是可以起到作用的,至少是可以影响到人的无意识的,而伊斯兰教则认为对任何形象的膜拜都可能导致偶像崇拜,而真神安拉是一种精神,他可以化为各种形象呈现,但形象本身并没有神力。如果说伊斯兰教也有“象教”的话,那么它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如清真寺的圆型屋顶有象征性的意义,屋顶下俨然是人间的乐土,因为它自诩自己才是真正有真理的宗教,而其他宗教则是邪恶的。
在中西艺术观上也是与此理相通的。两者有许多相似的成分,如古希腊学者和中国先秦思想家都标举诗的教化作用,孔子告诫其子孔鲤是“不学《诗》,毋以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诗人下了驱逐令,但也还给唱颂诗的存在留下了一块生存空间。至于亚里斯多德则是完全肯定了诗的积极意义,在西方柏拉图讲诗人创作的“灵感”,中国古代诗论中也讲创作时“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创作冲动。在中西古典美学中,都以诗美作为艺术美的最高体现方式,其他文学体裁乃至包括音乐、绘画等艺术的更大范围,其美学价值都是以包含了多少诗美要素作为衡定标准的。但是,在这些相同点之外却有一个不同点,那就是二者对于艺术有一个不同的基本假定。在西方关于文艺的本质观中,它是力图追问艺术是什么?而在中国则是询问艺术如何是?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所列举的日本和英国两种文化对花朵的态度来看,他以日本17世纪著名诗人芭蕉的一首俳句为例:
当我细细看,
荠花正吐艳盛开,
倚在篱笆旁!另一首是英国19世纪诗人丹尼斯的诗:
墙缝里的花儿,
我把你从缝中拔出;
连根带花,都握在我的手中,
小小的花儿,倘若我能理解
你是什么,——连根带花,一切的一切,
我就应该知道上帝与人类是什么。这两首诗都是以花为描写对象,但它们的风格是很不同的。铃木大拙指出,芭蕉只是在看花,在感受一种由花引来的难以言传的体验,充满了诗人的深厚感情,“而丹尼斯则是主动的与分析的。首先,他把花从生长着的地方拔出,使花儿与其相属的地面分离开来。与东方诗人完全不同,他没有让花儿单独地留在那里,他一定要把它从墙缝中拔出来,‘连根带花’,这意味着植物必然死亡。显然,他并不介意花儿的命运,他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像某些医学科学家那样,他要解剖花。而芭蕉却连碰都没碰一下荠花……”〔2〕这两种态度在艺术观上是不同的。 日本人的思维同中国的相似,这种东方式的思维是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人不是将对象置于客体地位再作认识,而是人将自己置于对象的立场去体会对象,如看梅花傲雪,就感受了梅的孤傲;看竹的挺拔,就体会到竹的气节。而西方人的思维是以“我”为认识的主体,对象都被置于客体的地位,客体的意义是在主体的认识中体现的,或者说是要由认识才能发现的,它倚重的是理性。
这一点体现在艺术本质观上,就是西方文论要去追问艺术是什么,对此的回答往往就成为某些文论系统的标志,柏拉图认为是神灵凭附产生文艺,他又认为文艺同现实隔了三层;黑格尔认为美和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等等,这些对艺术本质的厘定也成为评价文学的基本准则。而在中国文化中,文学是人的精神的表达,而人的精神同宇宙的精神是相通的,即“天人合一”,因此不是人创作出什么艺术,而是人如何去发现生活中的艺术性,如何使生活中的事物显示其艺术性。
试以中国文学中对于宇宙的俯仰观照来说,可以拈来这些诗句为例:
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汉·苏武)
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魏·曹丕)
仰视乔木杪,俯聆大壑淙。(晋·谢灵运)
山光悦鸟性(仰),潭影空人心(俯)(唐·常建)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唐·李白)其实,俯仰天地,观照万物,这对于各国艺术来说都是共通的,但在西方俯仰是主体站在此处,远眺那地平线之外的无穷远处,它是一种追询,一种冒险。而在中国则是俯仰都落实到内心,主体在此处看四方,再将四方的景物收罗于胸中,由内心出发再返归内心。既然内心是世界的“家”,因此世界的本性也就不是向外部求索,不是问它是什么,而是向内心自省,问世界如何是。世界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内心去安置它。贾岛有首诗写:“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是问答,但答而非答,师即山中不远,但又“云深”渺然,不知所之,从具体的知其形迹来说没有答案,但从抽象意义上看,这岂非正是山中高人德行的表征?
中国古代文艺学不关心艺术是什么,就在于艺术可以是你所想是的东西,什么也都可以作为艺术,但如何是艺术却值得考究,这从王羲之论书法的一段文字可以见出,他指出:
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尔。〔3〕在中国字的手书中,可以是艺术,也可以不是艺术,在这里二者都是写字,其区别就在于作为艺术的书法是在操作中有一套它如何成为艺术的方法。王羲之的这段题字可以说是道出了中国的艺术本质论的实质!
三、艺术创作论方面:艺术表达对无言之美的错位
在艺术创作论上,东西方的艺术观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西方的艺术观是假定,艺术家或艺术品要传达出一个什么,而这个所传达的东西在创作之前是不存在的。在古希腊的摹仿说中,虽讲艺术是对生活的摹仿,但艺术描写的素材仍然不同于生活的原始材料。亚里斯多德就说,艺术比历史更真实,按他的逻辑,也可以说,艺术比生活更真实,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偶然性和枝节问题,而艺术还体现了生活的必然方面。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则说过,在诗人吟咏伦敦雾之前,伦敦雾并不存在。其实单从反映论上讲,王尔德是颠倒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但从审美角度来讲,他又道出了几分真实,那就是,伦敦雾虽然先于艺术描写就存在了,但伦敦雾作为一个审美的对象,则是由诗人、艺术家来创造的。进一步,是由于诗人的这种描写,人们才学会了用艺术的眼光来看伦敦雾。这就像夏夜星空的图景是先于人的感知的,但是因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才使得旧历七月初七的银河有鹊桥相会的诗意。总的来说,在西方的文艺学中,艺术创作处在能动的位置,它是一种能动的活动。
贺拉斯在《诗艺》中说:“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容,同样,你自己得哭,才能在别人脸上引起哭的反应。”〔4〕在这段话中,可以见出读者是被动的, 得先要有诗人在诗中所表达的喜怒哀乐,然后才有读者心理上的喜怒哀乐。诗人充当了一个设计出某种阅读心理旨向的角色。艺术传达说到底是要将自己的所思所感传达给别人,让别人也有诗人在作文时所体验到的那份情怀。这一认识是假定传达行为在发生前与发生后有不同状况,信息走向是一条“作者——作品——读者”的路径。而在中国文化中,假定信息是弥漫在全部空间的,因此并不注重艺术传达的行为,在它的体系内,由创作通向阅读,只是阅读者将早先已有的感受悟解出来,而并不是把新的信息传达给读者,而是由作品的述说点化了读者,使他能从以前的遮蔽状态中得到“澄明”。对此,我们可从东晋顾恺之论画的两则记录来看:
1.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郎有识具,此正是共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
2.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5〕从这两则记述可以看出,顾恺之的观点是并不追求绘画酷肖原物,“益三毛”本来照着人物画写生也可以画出来,但顾恺之要在对人物的描绘中寻找到能传达出人物神韵的东西,那么“益三毛”(即在人物脸上添三根发须)正是这一思路的结果,它可能是写实的,也可能只是一种想象,譬如脸上有一撮毛,而画上只描出三根之类。至于点“目精”经年踌躇,则更是体现出了绘画中的意会性质,它不是要告诉欣赏者画上写的什么,而是要求应怎样来看,而这一看的角度可使创作与欣赏的双方达到一种情感交流上的共鸣效果。
这种共鸣效果同中国文化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音希声”等等对于表达功效的怀疑是有关的。如叶燮在论文时说到理、事、情三者关系,对于理、事方面的表达他又说:
然子但知可言、可执之理之为理,而抑知名言所绝之理之为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为事,而抑知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6〕这就是说,有些事、理是语言难尽其妙的,同时人们可通过感悟的方式体会到它的存在,语言(或其它传达媒介)不是表达它,而是暗示出至理的存在,并唤起人的感悟。所以,语言的传达作用并不是像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传达信息的作用,它只是在低级的艺术中才是如此,它只有形模而缺乏神韵。真正优秀的创作中,其语言媒介则是指向言外之意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假定必然导致在艺术领域内的非写实追求,并且对传达的意义提出了怀疑。
在《坛经》中记录了一则六祖慧能向弟子说法的事,他问弟子们什么是无名无字、无内无外、非有非无,非因非果?众弟子面面相觑。内中一个只有13岁的小和尚说是佛性。慧能诘问,在前面说了它是无名无字的,而你却说佛性,怎么是有名字的?小和尚回答:佛性本来是无名字的,但为了解说它就安了一个“佛性”作为名字,而这个词在“正名字时,却无名字”,就是说,要理解佛性的含义,不能只从语言上来看它,恰恰应从语言不能表达它的内涵上来体会它。这则公案阐述的是禅宗道理,然而,其实质上同中国文化的语言怀疑论倾向是类通的。这一认识在清人郑板桥的创作体会中也有过表述,他说: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7〕眼中之竹,胸中之竹,一个是客体事物的映像,一个是主体对这映像的感悟,而这两者都不是形诸笔端的手中之竹,手中之竹无法曲尽其妙地表达出眼中与胸中之竹,然而,手中之竹又可以暗示出折射出眼中和胸中之竹的状况,手中之竹的价值不在于“反映”了客体,也不在于“表现”了主体,这种以表现说、反映说来对艺术的界定是西方的逻各斯理性对艺术的概括,用于西方的艺术倒是适应的,但对于中国的美学来说就成了一种扭曲。
这种不去反映或表现的艺术信条也贯穿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如陶渊明的《饮酒》(其五)写道: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全诗10句,前面的8句像是在描写或表达什么, 但诗人的意图却是超越了这些描写的,他感到有某种“真意”,但欲辨却忘言。其实这言说似乎已没有多大意义了,就在前8句的描写中,那种闲适、 隐逸的乐趣岂是用言语所能道出?只有在这隐于市嚣的生活的经历中,诗人才体悟到,并且读者也可以感悟到隐居者拥有自己人生的真实意义。
可以说,中国美学中的艺术创作论所推崇的无言之美,同西方美学摹仿说所推崇的真实、表现说标举的想象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无言之美从退的方面说是认为言不及意,从进的方面说是认为应得意忘言。它不仅在艺术观念上,也在艺术实践尤其是中国的诗、画艺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甚至就在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说书艺术中也可以窥见其形迹,下面以记叙说书人吴天绪当年讲《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文字来看:
吴天绪效张翼德距水断桥,先作欲叱咤之状,众倾耳听之,则唯张口怒目,以手作势,不出一声,而满室中如雷霆喧于耳矣。其谓人曰:“桓候之声,讵我辈之所能效?状其意,使声不出于我口,而出众人之心,斯可效矣。”〔8〕张飞在长坂桥对隔岸的曹军怒叱,吓死了曹军中的夏侯杰,也吓退了曹军。其声壮如雷,可想而知。说书人在仿效张飞当时其声其貌时,是学不到张飞的声威的,即或学到了,吓死了吓跑了台下的听众也不妥帖,吴天绪巧妙地采用了虚拟性的表达,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这段描写显示出了中国美学关于艺术创作的理想形态,即创作的东西不是靠作者去传达什么,而是启示读者去悟解出来。
四、艺术的文化位置方面:艺术观照对万物一体的错位
艺术不只是一个美学的事实,它还是一个文化的事实。在对艺术加以考察的过程中, 西方美学是将它作为一种生活之外的他者( the other)来看待的。所谓他者,就是外在于“我”的事物和事实。那么,什么是处在“我”之外的呢?每个人都有日常起居的活动,都有具体功利目的的行为,如生产行为是期盼获得生产的结果等等,这些构成了人的生活的基本内容,它们不是属于人之外的活动。所谓人之外的活动包括:作为对人的精神加以反思的哲学,它是在生活之外的一种理性;历史,它代表了人类的记忆,是将过去与现实联接的思想上的纽带;以及艺术,它可以使人以一种超越性的眼光来看待日常生活中已熟悉了的生活,等等。
但是,这种将艺术视为在人之外的观念,实际上是源于西方文化中主客体分裂的文化现实。在这种文化中,人是作为主体去观照、改变作为客体的现实,现实本身是一种外在的力量。至于人所创造的文化,它们本身是人造的领域,带有人为的痕迹,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具有人的主体的因素的,但这些产品一经问世,就有了自身独立的命运,不再被其创作者所左右,如制定篮球规则的人也可能犯规,可能负于对手。这里有一个区别在于,大自然是单纯的,它只是人去认识的客体,而人的作品则是体现了对人生活的认识(广义上的认识),然而它也毕竟是在人之外的。黑格尔是率先把实践观点引入到艺术领域中的,实践是联系主客体的桥梁,但他也有将艺术视为外在于人的观点,他说的一则例子就显示了这一倾向:
例如一个小男孩把石头抛在河水里,以惊奇的神色去看水中所现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个作品,在这作品中他看出自己活动的结果。这种需要贯串在各种各样的现象里,一直到艺术作品里的那种样式里的在外在事物中进行自我创造(或创作自己)。〔9〕在这一事例中,投石入水是实践,从水中圆圈看到自己活动的结果是观照,这就是说,人的活动被艺术所观照,然后人又在艺术中观照被艺术观照着的自己,艺术在这整个过程和环节中,俨然是一面镜子,它本身是什么无从了解,要了解的话已是从中反观到的了解者自身。
将艺术定位在观照上是西方文化观推导出来的一种必然态度,但在东方思想中却没有这一文化渊源,因此它的艺术的文化位置也就有所不同。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朱熹的一段对话看出端倪:
问:“《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有一太极。’如此,则是太极有分裂乎?”
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10〕这里月亮“散在江湖”是一个绝妙的回答,月亮只有一个,但各处的水面都可映出一个。就象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天上月杯中月都有明澈宁静的形象,但不能说月已分成了两个。由这一观照来看,具体人生也好,艺术对人生的描摹也罢,说到底都是对世界的理、性、命的分写,就其用为二,就其体则一。艺术与生活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将这种观念比照柏拉图的文艺观则更可见出中西观念的差异。柏拉图也是认为有一个作为万物本源的“理”,即理式(Idea),理式是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本源、本性,具体的事物是分享了理式的部分,如人间有多种床,包括竹床、棕床、铁床、双人床、单人床等等,这些具体的床在样式、材料、质量上都可能有很大差异,但它们都是床,原因就在于它们都分沾了一部分床的理式,是床的理式的摹本。艺术再来对床加以摹写,则艺术描写的床与现实的床又有差异,如没有实用价值之类,则艺术又是摹本的摹本,与理式的真理“隔了三层”。西方的思想是要将原物与艺术的描写分离为二,中国的思想则是万物一体,认为它们都是理的具体体现。
万物一体的思想承认艺术描写生活的同时,它也就在生活中,与生活融为一体。这一认识是否会混淆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呢?这确实是有可能的。前文曾引述顾恺之绘画“数年不点目精”,这可以看作艺术上的严谨,就像当年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为塑造犹太形象而苦苦觅求一样。那么,顾恺之的另一则轶闻就不能只以创作严谨来说了。《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引沈约的《俗说》说,顾氏“为人画扇,作嵇(康)、阮(籍)、而都不点目睛。或问之,顾答曰:‘哪可点睛,点睛即语’。”在这一表述中,可以见出艺术与生活、艺术形象与生活原型之间的界限是消解了的。其实,单从艺术描写的形似状况来看的话,中国画是不讲究透视、不讲究人体解剖学比例的,它并不能达到模写人物时的以假乱真的程度,以为人物“点睛即语”,实有赖于文化上的假定。
对于万物一体、万物一理观念导致的艺术上可能出现的雷同化倾向,中国古代思想也自有一套理论来解说。在以“气”来论创作的文论体系中,气是一,每个人都是由自己的气来统率创作,但可以因气的阴阳、清浊上的配搭不同,结果同秉一气,但又各禀其气。从根本上讲,所有创作都是气的体现,但所体现的毕竟有所不同。另外,也可以从接受的差异角度来理解,这在朱熹的解说中可以见出: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具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11〕同一“理”,在不同身分的人就有仁、敬、孝、慈的不同作用。那么,以此来推导艺术创作,创作都是一气贯通,但气的体现所处位置不同,则其具体体现也就有异了。
在艺术的文化位置上,中国美学是将艺术与人生同一,并不是作为一个人与世界之外的第三方来看待。也正由于这一假定,所以,作为人生修养的“心斋”,“坐忘”,也用于对艺术构思的说明中。正是根据同样道理,才会有中国美学的以禅论画,以禅喻诗,等等。
五、余论:中国传统美学话语系统的译解问题
在符号学领域中有符号系统的观念,即符号的意义不只是符号本义就会充分显示的,它还需依赖其符号系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黑、白、红等都是表示颜色的形容词,而它们之间的反义词状况如何,就有赖于符号系统的俗成惯例的规定了。在“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的成语中,红与黑是反义词。而在“一阴一阳之谓道”中,阴阳之道的最直接的表征是白天/黑夜的交替和互生,那么黑与白就是反义词。 在中国围棋中,黑白二色棋子就是阴阳之道的最初的具象化的表达,因为据考证,围棋是起源于由太极图而推衍的占筮活动的。再如结合到英国历史上的红白玫瑰战争,前苏联在建国之初时的红军与白军之间的战争,则红与白是反义词,并且中国民间是红白喜事对举,是红白也有互为反义词的性质。
那么,在符号系统的转换中,符号转换就是不充分的。美国逻辑学家蒯因在《词与物》(1960 )中曾提出了“译不准原理”(Interminacy of Radical Translation),按此原理,一种语言在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可以有多种译本,它们都可以是“忠实”译解原文的,但它们之间就具有差异甚至相互对立。举一例子来说,汉语“叔叔”译成英语是“Uncle”,再将其转译成汉语时也可译为“舅舅”, 这是因为英语只有一个Uncle来表示父辈的叔、伯、舅等, 而汉语中一定要作出区分,它划开了同姓与不同姓的关系,而这与宗族社会对于宗嗣关系的强调是相关的。由此就可以见出词汇在语言系统中已不只是指称对象,而且还表达了人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倾向。蒯因后来在所指与意义上一致的理论中还进一步发展了译不准原理,就以金星这一既叫启明星(晨),也叫长庚星(暮)的词汇来说,“所指可能是暮星,因而也可能是晨星,后者与前者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暮星’可能是一个好的译名,而‘晨星’则可能是一个坏的译名”。〔12〕如果说在这种词汇的转译中存在着“译不准”的状况的话,那么,在一种理论系统转译到另一种理论系统时,这种译不准的状况也是同样存在的。
从艺术的文化位置上看,西方美学将艺术看成人与对象之外的第三者,它反映了人在世界上的处境和人的感受,但它又不同于人在现实中对自身状况的自省,这种差异表述出来就是艺术反映生活的必然性,艺术比实际生活更典型,艺术中的思想体现了超乎个人的一种普遍的人性述求,艺术描写教人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平日已熟视无睹的周遭生活,等等。而在中国的美学中,艺术就融入到生活之中,这从对美术作品的态度上也可见出。西方美术是以跻身于卢浮宫一类博物馆展出为荣,在这展示中它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一个间隔。而中国的书画是挂在家居的厅室,书画的名气可以提挈主人的名望,而主人的名望也可以使他收藏的艺术品提高身价。装裱后挂出的字画同主人的生活联接为一个整体,字面所体现的旨趣成为主人生活情趣的一个部分。西方美术作品作为第三者(人和自然之外),它是以其不同于他物的特殊点来标明它的价值的,而中国的美术品就置于生活之中,因此它并不张扬特性而只注重旨趣,在旨趣的体现中就自然地体现出特性。在此可以从钟繇学习书法的例子来看:
昔钟繇与胡昭俱能为行狎书,繇初师刘德升,后传蔡邕笔法,由是学之致妙。繇临终于囊中出授子会曰:“吾精思三十余载,行坐未敢忘此。常读他书未能终尽,惟其学字,每见万类,悉书象之。若止息一处,则画其地,周广数步;若在寝息,则画其被,皆为之穿。”其用功若此。〔13〕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是以临摹作为学习的基本前提,并且也要求习字者对生活中的各种形象,如崖上顽石、林中枯藤、山中猛虎、云中白鹤等等形象进行揣摸,在写字时也就是表达这些生活中所见意象的情趣,所谓大师的书法就是对这些情趣逼近的书法,因此,临摹大师作品与直接揣摸生活中的意象是殊途同归的。而在西方美术中,这种临摹则只是今后创作所需的基本功的训练,而创作是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的,如果在新作中可以窥见以往杰作的痕迹,便有抄袭、剽窃之嫌。但在中国书法中,既然大师们可以取法于自然,而人的作品与自然是类通的,则临摹他人的嫌疑并不构成致命的缺点,倒是临得不象,未达到原作的水平才更是致命的缺点。
又从艺术创作论来看,西方美术是要求作品表达一个什么,而且要有新意,中国美学并不认为艺术非要表达什么。唐代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的“含蓄”中写“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精神”中写“生气远出,不著死灰”,都是这种不用表达而读者自会体味到内容的一种描述。从心理学上讲,它属于暗示,但暗示时是施动一方将意图传达给受动者,故在中国的诗歌美学中似乎更提倡自由联想。在这里可以从晋初阮籍的一则经历见出。阮籍驾一车漫游,信马前行,到了路的尽头,就穷途而返,再向另一方向信马前行。再到路的尽头,又调转车向。一次,阮籍到了苏门山,山中有隐者人称苏门先生,传闻他是真正得道高人,于是阮籍上山拜访,书中有这一段记载:
籍闻而从之。谈太古无为之道,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先生倏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长啸,韵响寥亮,苏门先生悠尔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啸,有如凤音。〔14〕这一段文字是说阮籍上了苏门山后,找苏门先生谈及哲学和历史的问题,而先生不但未回应,甚至没有正眼看他一下。阮籍心知与高人的交晤也许得用另一种方式,他发出“长啸”,啸是一种没有歌词的歌,是靠曲调节奏表达啸者的思想感情,这一超越了语言的表达方式真正打动了苏门先生,他由不正眼看阮籍转变为向他微笑。阮籍下山时,苏门先生用啸声为阮籍送行,阮籍从这啸声中领悟到,这是先生对自己所提的哲学和历史问题的解答,顿有茅塞顿开之感,阮籍回家后写出《大人先生传》,讲述自己悟解到的道理。正是由于这无言之美、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美学假定,中国艺术讲究的是一种由尽量少的表达而暗示出尽可能多的意蕴的境界,这在诗歌中的“欲辨已忘言”,在音乐中的“弦外之音”,在美术中的“计白当黑”等都可以具体体现出来。本来,纸张是白色的,中国画又不像油画那样先在画面铺上底彩,因此画中白色就是纸张原色,它本是无所表现的,但在“计白当黑”的假定中,是将整幅画面看做一个整体,本无表现性的白色就作为空气、作为石头的阳面、作为云、作为天、作为烟雾等等的表现。无言之美的意义在这一状况中也就可以得到解释。
再说艺术本质观,中国的思想从关于“气”的论说就可以见出,它同庄子齐物的思想是相通的。庄子曾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为始。”〔15〕这一思想从先秦萌始,到宋明时期的理学将其推到极致,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北宋时的周敦颐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16〕这一段话是对阴阳互反,万物一体思想的集中表述,既然万物一体,那么,讲艺术是什么就同讲非艺术是什么或讲艺术不是什么都没有大的差别,将它们推向极致,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阴阳、太极、无极。在这一思想的背景下,艺术是什么不可能作为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命题提出来,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操作上的问题。某人的创作是艺术,而另一人的只是涂鸦之作,这里的差异不在于前者“是”,后者“不是”艺术,而是前者“如何是”的,后者缺乏了这个转化媒介的“如何”才导致它“不是”。由于对形而上世界的思考已被哲学、尤其是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所左右,所以在美学和文艺学的世界中,中国艺术观里的本质论与创作论就大体是相通的,基本上都是关注艺术如何是艺术的问题。
总的来看,中国美学体现的是另一种文化精神,另一种理论系统,以今人所熟悉的、实际上是浸润了西方学科思想的观点来看这一美学形态,那就只能是看到有别于它的本来面目的状貌。这样的一种认识维度固然也可解释中国美学,固然也可用于对具体的艺术问题的说明,固然也可以在行文时引述一段它的有关论述,但这样做实际上是有缺陷的。当年,胡适在解释实用主义的精神时曾作了一个譬喻,100个小钱, 你可以分成两堆50个小钱,也可以分为各25个小钱的四堆,还可分成10个钱一堆的10堆,等等,它贯彻的都是均分原则,但所分的状况有很大不同。在这些分法中没有哪种比另一种更对的问题,关键是看哪一种分法更有实效。在这个意义上说,将中国美学在西方他者的话语中编码也无不可,只要它说得出一些道道,能给学习者有所教益就行了。但是,这种实用性是非历史性的,它同人们求真的欲望不合。并且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有不可通约处,完全通约起来就不会贯彻“均分”原则,势必是用西方的话语来解说中国的内容。同时,人类的文化是多样性的,人类社会未来的健康发展有赖于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如当今人们已意识到保护生态的多样性是必要的,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也同样是必要的,只有在多样化的文化中,人的思想才不至于凝固和僵化,才有着一种批判和参照某一特定文化的思维支点。在当今,在面临社会转型包括其伴生的文艺转型,以及在文艺学中大量借鉴西方话语的状况下,一些学者感受到了文艺学话语爆炸的威胁,我们实际上正面临着失语的窘迫,在对文艺论说时,那喋喋不休的讲述常常只起到录音机的作用。在他者话语权势造成的失误状态下,重新回到自己母语文化的话语中,汲取它的思想营养,又参照他者话语的表述,或许可以为自己营造出一个新的话语空间。
注释:
〔1〕转引自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5—676页。
〔2〕铃木大拙、弗洛姆、德马蒂诺《禅宗与精神分析》, 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3〕《王右军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4〕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第118节。
〔5〕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
〔6〕清·叶燮《原诗·内篇》
〔7〕《郑板桥集·题画》
〔8〕《扬州画舫录》
〔9〕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页。
〔10〕〔11〕《朱子语类》卷九四、卷十八。
〔12〕蒯囚《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第58页。
〔13〕唐·蔡希综《法书论》
〔14〕《世说新语·栖逸》
〔15〕《庄子·达生》
〔16〕《周子全书·太极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