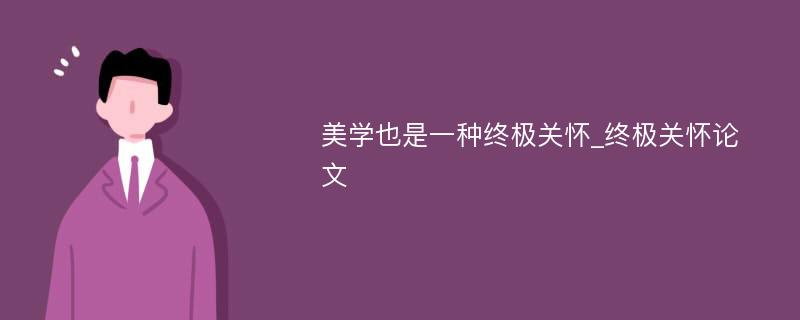
审美也是一种终极关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明的人不仅需要肉体的温饱,而且需要精神的慰藉,其慰藉的最终指向便是一种终极关怀。大致说来,人类的终极关怀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给多样的现实世界以统一之本体存在的哲学承诺;一种是给有限的个体生命以无限之价值意义的宗教承诺;一种是给异化的现实人生以情感之审美观照的艺术承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哲学之本体论和宗教之形而上学纷纷面临着学理上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之文化形式需要自觉地承担起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历史使命。
一
在西方哲学史上,终极关怀的问题最初是以“形而上学”的命题出现的。因此,研究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知道“形而上学”是怎么回事。在西方,这个词最早是一部著作的名字。亚里士多德过世后,安德罗尼柯承担起为其整理和编纂遗著的工作。在编完了《物理学》一书之后,他遇到了一个难题:下一部的著作无以命名,因为它探讨的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宇宙本体,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超验领域。为了慎重起见,安德罗尼柯便将其命名为ta meta ta physica,意为“物理学之后”,译为拉丁文便是metaphysica。再后来,这个词被传入中国,翻译家根据《易传·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而将其译为“形而上学”。
在我们所知的一切物种中,人是最为聪明的,也是最为贪婪的。人不仅要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来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而且要创造出大量的精神财富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聪明使人意识到,他的存在是有限的;贪婪使人不满于如此短暂的有限生命,而要追求无限的存在。不幸的是,肉体生命只能延长,不能永驻。因此,人们不得不在肉体之外寻找精神的寄托,这也便是“爱智慧”的动因所在。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之所以不满足于对现实世界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而要超出自然科学的领域去探讨超验而永恒的宇宙本体,与其说是为了给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不如说是为了给人类的存在寻找一个更为永恒的家园——终极关怀的存在依据。这便是形而上学,或曰“本体论”研究的意义所在。
围绕着纷纭复杂的客观世界统一为何物的问题,古希腊的哲学家形成了判然有别的两大阵营。其中的一派企图从某种物质质料入手,将这种特殊的质料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另一派则坚持从某种物质形式入手,企图从对象的形式中抽象出一种外在于客观世界的形而上本体。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前一派叫做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后一派叫做唯心主义的哲学路线。其实,把世界的本质说成是“水”并不见得比将其说成是“数”更为高明,二者都不过是古代人对宇宙本原的一种素朴的猜想而已。这种猜想的方式本身就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因而不可能超出内容和形式这两个方面。
在上述哲学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自己著名的“四因说”(质料、形式、动力、目的)。在“四因”中,他特别重视“质料”和“形式”两大因素的地位,认为前者是事物的原料,后者是事物的本质,二者相加便构成了具体的个别事物,因而它们共同构成了世界的本原。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只是对上述两大派别的综合而已。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出现,使得以后的经院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建树,而只不过是割裂开来的亚氏哲学:唯名论者坚持并强化其“质料”的部分;实在论者坚持并强化其“形式”的部分。
到了近代以后,由于本体论的研究长期得不到深入,哲学家们便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认识论。因为只有解决了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才能够对世界的本原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回答。而围绕着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近代哲学家分成了英国经验派和大陆理性派两大阵营。从表面上看,这两派哲学家一类重质料、一类重形式,仍然是古代两条哲学路线的延续。然而不同的是,经验论者从近代自然科学中吸收了归纳法,唯理论者从近代数学中汲取了演绎法,使得这种延续获得了新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与前提。然而,单靠经验归纳,虽然可以使我们获得新的知识,但却难以保证这种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因为归纳的材料总是有限的,其结果只能是或然而非必然的;反之,单靠逻辑演绎,虽然可以保证推论结果的严密可靠,但却无法产生新的知识,因为逻辑演绎所依据的最初前提并不是演绎自身所能提供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康德融感性和理性、归纳和演绎、经验材料和先验形式于一体的二元论出现了。
康德之后,以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虽然企图从人类主体的意志、欲望、本能入手,寻找到一条窥视宇宙本体的独特门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工具,却只能使这种研究停留在体悟和推测的基础上。与之相反,以经验批判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则主张将世界的本质这类形而上学命题视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假命题”排除在哲学研究的大门之外,从而使本体论的研究再次被悬置了起来——终极关怀没有了着落。
二
在人类的文化行为中,不仅哲学具有本体论的内容,而且宗教也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与哲学不同的是,宗教不是以理性的方式来探讨宇宙的本体,而是以信仰的方式来追随世界的主宰。与哲学不同的是,宗教不是将宇宙的本体抽象化,而是将世界的主宰人格化。然而,无论是哲学的“爱智慧”,还是宗教的“爱神祇”,其内在的原因是共同的,其至深的动力都是要为有限的人类寻找一种无限的寄托和依据:终极关怀。
正像费尔巴哈所指出的那样,“宗教是人类精神之梦”。人的本质在宗教的对象化过程中受到了异化:神越是被人类塑造得完美,就越反衬出人类的软弱和无能;神越是被人类捧得高高在上,就越反衬出人类的卑贱低俗;人越是肯定神,就越是否定自身……以至于神成了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而人类反倒成了罪孽深重的奴隶。而事实上,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
正像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力图论证本体存在的科学性一样,历史上的宗教家们也在不断地论证其神祇存在的合法性,这种论证的重要工具便是“目的论”。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的存在都不是任意的、偶然的,而是这个宇宙的主宰、至高无上的神有意安排的。问题在于,随着人类文明的深化,以目的论为主要工具的神学和以机械论为主要工具的科学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哥白尼、布鲁诺的“日心说”告诉人们: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太阳系的一颗行星,这便使上帝为人类创造世界的理论难以自圆其说了。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告诉人们:自然界的发展本无什么既定的目的,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只不过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这便使上帝缔造人类的学说显得有些荒诞不经了……
从学理上讲,由于宗教家所憧憬的天国不是经验的此岸世界,而是超验的彼岸世界,它无法为我们的感官提供任何确切的经验材料,因而是无法认识的。用康德的理论来说,它可以构成信仰的实体,但却无法成为知识的对象。换言之,信奉哪路神仙完全是信仰者自己的事情。他可以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为之献身,但却没有权力将这种信仰说成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让他人也来信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尼采才说出了那句惊世骇俗而又颇为无奈的话,“上帝死了!”
麻烦还不限于此,正像不同的哲学家所构造的宇宙本体不同一样,不同的人创造的神也是不同的,犹太教徒创造了耶和华,基督教徒神话了耶稣、基督,佛教徒尊崇释迦牟尼,穆斯林则独信真主安拉……这些由不同教派所尊崇的宇宙主宰不仅莫衷一是,而且彼此对立。从“十字军东征”到“9·11事件”,不同的宗教极端势力试图运用武力来征服乃至摧毁异教徒。但是,要建立一种普世认同的宗教就像建立一种普世认同的哲学一样,至今还只是一种梦想。这样一来,正像哲学本体论的建立渺渺无期一样,宗教形而上学的努力也似乎变成了泡影——人类的终极关怀又一次落空了。
三
人类还有什么办法来完成对自身的终极关怀呢?或许,最后的希望应寄托于艺术。
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艺术的功能主要是用来摹仿或再现客观的现实世界。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艺术的功能主要是用来规范和诱导人们的社会行为。
显然,作为不同人类群体共有的文化现象,艺术的出现应有其更为深刻、更为独到的功能。在我看来,艺术作品中虽然包含着认识内容,但认识内容的多少不是艺术价值的关键所在。否则,徐悲鸿笔下那幅不太合乎解剖学规范的《奔马》便不会价值连城了。在我看来,艺术实践中尽管包含着教化的成分,但教化成分的强弱也不是艺术价值的关键所在。否则,贝多芬谱写的那首不含道德内容的《月光》便不会被千古称颂了。在我看来,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不在于认识,不在于教化,而在于给人以情感的慰藉。这种慰藉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但都是对遭受异化痛苦的人们所进行的精神关怀,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分为初级关怀和终极关怀。所谓初级关怀,是对人们生活情绪的放松、抚慰、宣泄,并通过这种形式使其恢复到健康状态。所谓终极关怀,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感悟、理解、追问,并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对于不同层次、不同状态、不同境遇中的欣赏者来说,这两种艺术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就艺术自身的价值而言,后者显然要比前者更有意义。这也正是《三字经》比不上《古诗十九首》、《金瓶梅》比不上《红楼梦》的原因所在。
一部优秀的艺术品,哪怕是写平平常常的生活琐事,也总能上升到终极关怀的高度来加以理解。从《俄狄浦斯王》绝望的挣扎,到《浮士德》顽强的探索;从《哈姆雷特》沉痛的反思,到《等待戈多》麻木的期待;从《离骚》的上下求索,到《归去来兮》的古今游荡;从《牡丹亭》的生死之恋,到《红楼梦》的色空之迷……古今中外,凡是超越民族和地域从而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品,无不具有形而上的终极关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艺术作品的终极关怀,既不像哲学那样诉诸人的理智,也不像宗教那样诉诸人的意志,而是以诉诸人的情感为主要特征的。因此,这种终极关怀并不是要给多样的现实世界提供某种统一的存在本体,也不是要给有限的个体生命寻找某种无限的灵魂归宿,而是要给异化的现实人生呈现某种审美的情感慰藉。由于这种慰藉能够将有限的生活境遇指向无限的生命意义,因而便有了足以同哲学和宗教相媲美的价值与功能。
在西方的历史上,不少思想家早已看到了艺术所具有的这种终极关怀的价值与功能,并将其作为反抗异化现实的有力武器。卢梭认为,人类越发展,道德越堕落,理性并不能给人类自身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因而祈灵于浪漫主义的艺术活动。康德认为,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判断力可以使人的想像力和知性得以协调,从而将分裂的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知、情、意相统一的整体。席勒认为,只有艺术所创造的“活动形象”,才能重塑现实生活中支离破碎的人格,以进入一种审美的乌托邦。黑格尔认为,艺术和宗教、哲学一样,是“绝对精神”自我回归的必由之路。叔本华认为,艺术可以使走火入魔的“意志”得到暂时的麻痹,从而使骚动不安的主体获得片刻的安宁。尼采认为,真理是丑恶的,宗教是虚伪的,只有艺术能够给人的生命以积极的力量。弗洛伊德认为,同宗教与科学一样,艺术可以将被文明所压抑的“本我”解放出来,将其“升华”为审美的情感。韦伯认为,在宗教的救赎失去作用的情况下,艺术的救赎便成为抵御文明异化的有效途径。海德格尔认为,诗歌可以使被异化的语言得以复归,艺术可以使被遮蔽的存在重新澄明……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的哲学本体论并不发达,宗教也并不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因而古人的终极关怀往往是通过艺术的审美观照而加以实现的。这种文化的“代偿功能”是中国古典艺术特别发达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文明的人类之所以陷入异化的痛苦,乃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利刃斩断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原始纽带。因此,作为治疗异化痛苦的古典艺术,最常用的方式是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断痕重新修复起来,从而将短暂的现实人生与永恒的自然存在联系起来,将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族类生活联系起来。换言之,无论是思乡还是怀旧,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如果我们沿着这种世俗情感的延长线不断追索的话,便总能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衔接处找到一种指向无限的生命意义。这一意义也许永远也不能完全揭晓或彻底实现,但这种追索本身已具有了终极关怀的功能与价值。
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艺术的终极关怀有着尤为突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西方传统的哲学与宗教渐渐式微;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原始联系也渐遭破坏。随着世俗化、商业化、现代化生活的到来,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孤独。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认识功能、政治导向在下降,艺术之终极关怀的人类学意义在上升。在一个商业化、信息化、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里,艺术的这种功能使其有望成为超越哲学观念、宗教信仰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打破国界、种族的坚硬壁垒,实现人类精神的重新整合。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蔡元培有关“以美育代宗教”的深刻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