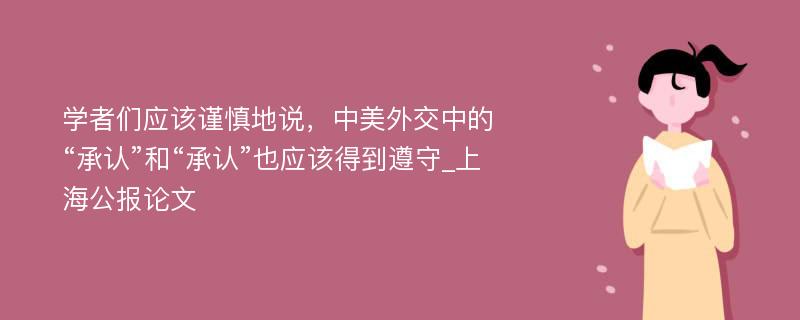
学者立言宜谨慎——也说中美外交中的“承认”与“认识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认识到论文,也说论文,外交论文,谨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读到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的大作《是“承认”还是“认识到”?——评人教社历史教材对外交原则问题的歪曲》(《学术界》2001年第6期),文章指责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教材《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第102-103页)中关于“在中美发表的上海公报中,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句是对美国或中国外交原则的歪曲,因为黄先生查对了“中美上海公报”的中文原文,其措词是:美国“认识到”中方的立场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认为,“认识到”不能等同于“承认”,尤其在外交文件里是如此。
黄先生强调,“外交文件中措词的表述,是不容随意解释的原则问题。对于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来说,更是关系中华民族整体素质提高的大事,也是关系尊重历史事实和准确解释历史事件的问题”,故“这是任何一位严肃的史学工作者、学术研究者、教材编写者和中学教师们应当明辨的原则问题”。作为一个史学从业人员,我相当赞同对基础教育历史教材予以关注。从黄先生的文章中看到,这是一个已经争论两年的问题了。黄先生自己在1999年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后有政协委员在2001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正式提案质询,教育部也有正式的答复。
教育部的答复说:“为了避免理解上的偏差,人教社还特别核对了1972年上海公报的英文版,发现与该公报中文版中‘认识到’一词相对应的英文单词'acknowledge'”在一些英汉词典中的第一个释义都是“承认”,则“‘认识到’与‘承认’两个词实际上并无本质差别”。这样,该“教材的叙述似乎也没有错”(此答复文字转引自黄先生文,下同)。在黄先生看来,问题已上升到“外交文件中'acknowledge'和'recognize'两词在中文究竟怎样表述确切”这一关键的“语言学”问题。他为此“仔细查阅了40部以上”的各国词典,引用了15种英汉或汉英辞典,并请教了语言学、美国史和中美关系方面的数位专家,用了一万多字的篇幅“向读者提供必要的权威资料”,并确定“在外交文件中把'acknowledge'解释成‘承认’显然是理解上的错误”。
不过,语言学上的研讨与“基础教育历史课程”这一黄先生最初提出的问题有些距离,还是应当回到他所强调的主张,即“尊重历史事实”并按外交文件的“愿意表述”。黄先生反复引用了1972年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及1978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皆中文本)关于中国立场的类似表述,前者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后者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认为美国的立场从1972年的“认识到”到1978年的“承认”,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在外交辞令上是不能含糊的。历史教材在这个问题恰恰是弄错了”。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恰恰弄错了”的是黄先生自己。理由很简单,在两份官方文件的英文本中,“认识到”与“承认”都是同一个词,即"acknowledge"。换言之,美国政府两次都"acknowledged"中国政府的立场,而1978年的中国外交部(代表着中国政府)或认为中文表述中“承认”比“认识到”更能充分表述美方的立场,或即像教育部一样根本认为“两个词实际上并无本质差别”,所以改变了中文用语。由于这是正式外交文件,两次中文表述应皆得到美方的认可。且外交文件用语的修改应非随意,常规情形下经修正的后一次表述应更得双方的认可。
黄先生问道:历史教材“究竟是以史实为依据还是以编者自己的个人看法为准?究竟是遵循中美两国共同认可的正式外交文件呢,还是可以自己随意解释”?答案当然是以史实为依据、以文件为标准。按照这一答案来看,如果确有所谓语言学“理解上的错误”,犯“错误”的就是中美两国政府。倘若中美两国政府没有“理解上的错误”,那就只能是黄先生“理解”有错。我想,在外交文件的用语方面,实际运用者的理解恐怕更为“正确”,而且他们在确定用语方面的严谨和认真决不让一般学术评论者,因为这里牵涉到各自的国家利益!
陈寅恪说过,“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在历史研究中应遵循陈先生提出的这一准则,我个人至为赞同。不过中学教材是否也必须如此,还可以商讨。可以说,在用中文表述上海公报时用“认识到”更切近当时的历史,但若为避免造成英文不甚佳的中学生出现与黄先生相类的误解,改为“承认”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毕竟是中美两国政府同意了同一英文词汇的两种不同中文表述,且应更倾向于认可后一次表述,则更晚出的中学教科书在并非直接引语的情形下采用后一表述,应可接受。教育部的“答复”说教材关于上海公报的概括“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切合问题本质的”,并无太多可以挑剔之处。
黄先生试图提高中学教材准确性的用心至可感,他说该教材的表述“在学术上是很不妥的”,可能是将大学里历史研究的标准运用到中学教学之中了(其实也仅略有“不妥”,尚未到“很”的程度)。但他进而责备该教材的表述“在政治上也是不严肃的,在效果上是非常有害的”,并正式断定为“明显的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错误”,多少有点让人回忆起“无限上纲”的时代,不太像学术争鸣的口气。不论这一教材在其他方面有无史实问题或有多少问题,关于中美公报这一条基本不存在学术问题,尤其不曾“歪曲”不论美国还是中国的外交原则。窃以为学者立言宜谨慎,最好将讨论限制在“学术”的范围之内,不妨将“政治错误”留给更专业的人处理。
在学术范围内,黄先生自己反更适用于“在学术上是很不妥的”这一判断。因为他不仅对外交文件的“理解”不够正确,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尝试了他所说的“解释历史事件”的工作,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美国政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上海公报中美国的‘认识到’和建交公报中美国的‘承认’是有区别的”。美国政府的英文措辞既然未变,仅据中文文本的词汇改变从语言学角度考证出美国政策的“变化”和“区别”,这一结论恐怕不立,反更接近黄先生所说的“随意解释”。
本来只要稍费力核对一下中美公报的英文本,就不致得出这样的结论。且1978年中美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之英文本并不稀见,在任何大学图书馆都应有的《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当年第51期(1978年12月22日)上即可查到。论者或曰:黄先生毕竟阅读了中文本。信然。可是在讨论以英文为官方语言的美国政策转变并涉及中英“语言学”时,顺便也浏览一下英文本,似更严谨。就其所强调的“史实”而言,文件原文的可据性显然大于不论数量多少的辞典。黄先生费了如许力气旁征博引,却恰恰不去核对引起争议的文件本身,这在平时治学已不甚妥,在试图纠正他人错误时就更不合适了。
而且,真要研究和探讨“外交文件中'acknowledge'和'recognize'两词在中文究竟怎样表述确切”这一“语言学”问题,正应该多引用“外交文件”本身,也只有“外交文件”才是所谓“权威资料”,才能解决黄先生提出的问题。既不核对引起争议的文件,也不引用一项其他的外交文件,却希望从众多的英汉辞典里求解答,不是有些南辕北辙吗?
近年史学界少数人为了提高表述的“理论性”,无意中常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黄先生将一个到图书馆30分钟内即可解决的史实问题上升到语言学高度进行探讨,为此“仔细查阅了40部以上”的各国词典,便相当能体现这一倾向。注重“小学”是中国学术的传统(清儒尤擅长之),跨学科研究是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早就提出的目标,后来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特别提倡史学和语言学的结合,但似尚未见有人主张研究历史问题可以不顾历史本事的考证而移位到语言学中去找答案。
至于有著名语言学专家在“查阅了多本国外和国内出版的词典”后告诉黄先生,他“认为在外交文件中把'acknowledge'解释为‘承认’是错误的”,我颇怀疑这是否黄先生引述有误。因为事实很明确:中美两国的外交家恰将此二词作为对应词使用,且包括这一用法的相关文件公布了20多年,迄今未闻两国的职业外交家和外交学者提出异议。常规的语言学专家不一定就认为自己是外交领域里用语的专家,能“著名”者尤其不至于如此轻率地跨学科下判断。
从黄先生论述的理路看,更可能是他先转换了问题再请教专家(即增加了原不存在的"recognize"一词然后对比之),从而导致专家的答复虽支持他的论点,却未必符合事实。此虽非有意为之,等于陷这些专家于信口开河之窘境。如果黄先生坚持就本事论本事的史学常规,不转换其请教的问题,相信他所请教的专家都不致做出支持他判断的答复,因为这些专家都具有读英文的能力,而且以治学严谨著称,不会不看原始材料就“随意”下判断。
黄先生也引用了“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苏格教授”的著作《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来支持他的论断,但他若不是没看明白苏教授的中文表述,就是引申了苏教授的观点而误用之。黄先生引用的苏著原文是:“从中美建交公报可以看出,其重申了《上海公报》中确立的原则,但又比《上海公报》向前迈进了一步。《上海公报》中美方仅仅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并不等于美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中美建交公报》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很明显,这里所说的“迈进的一步”是指上海公报中没有的内容,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外交政策的“迈进”当然与先前美国“认识到”的那一部分相关,但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根本是两个分开表述的部分,这在中文本里也非常清楚,常人皆不致混淆。美国先前“认识到”的内容也就是“《上海公报》中确立的原则”,对此苏教授使用的词汇是“重申”。这一段陈述直接明晰,要想误解本来甚难;只有根本未曾通读过本来不长的中美建交公报全文,也不注意苏教授所说的“重申”,才可能产生误解。无论如何,苏教授所论与“外交文件中'acknowledge'和'recognize'两词在中文究竟怎样表述确切”这一“语言学”问题完全无关,也不支持黄先生提出的美国政策“变化”论(美国的总体对华政策确有变化,但苏、黄两人所说的却是不同的“变化”;美国的具体政策表述也有变化,即将“认识到”或“承认”的主张之载体由“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的立场”,可惜这不是黄先生关注的“变化”)。黄先生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把一个历史事实的具体问题变成了语言学的大问题,所有他请教的专家都是——也只能是——在“语言学”上支持他的见解,他所引用的所有语言学和非语言学文献也没有一处可以支持他所谓的美国政策“变化”说。
我宁愿相信黄先生不是故意转换教科书的问题,他也未必是有意曲解苏格先生的陈述,很可能因为这是一个长达两年的争议,在此期间积累了一些情绪性的因素,使黄先生多少带有胡适所谓“正义的火气”,稍偏离了学者的冷静。“三人成虎”的古训其实也适用于说虎者自己,第一次未查核相关的原始资料或只是个初步的失误,长期重复后自己也弄假成真,导致问题的转换;为证明这一新“问题”而扩展到旁征博引的“随意解释”(用中文文件的词汇差异去证明以英文为官方语言的美国政策的转变,便很能体现其随意性),无意中反日益远离了本题。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黄先生提出的问题本身也未必成立——所谓“把'acknowledge'解释成‘承认’”这一被攻击的目标本身并不存在,它根本是黄先生的创造。在类似中美公报这样的双边外交文件中,只要没有正式确认某一文字的文本为正本,一个词义的两种文字表述是并立的。所谓“把'acknowledge'解释成‘承认’”,无形中等于确认中美公报的英文本为正本,中文本不过是英文本的“翻译”,这恐怕并非中美两国政府的原意。再退一步言,即使按黄先生所“理解”的将英文本作为正本,这里也只有“翻译”而没有什么“解释”;若说中美公报的中文本不过在“解释”其英文本,似又等而下之了。
黄先生近年比较热衷于“学术打假”,此文也是他的“打假”系列论文之一。然其热情有时似乎太过洋溢,他所提出的“歪曲”若真成立,也只是“歪曲”了美国的外交原则;美国政府当时不觉以“承认”作为"acknowledge"的中文对应语有何不妥,事后也未闻其提出修改的要求,似乎提示着他们并不认为这里存在什么对外交原则的“歪曲”。何劳黄先生代打抱不平呢?如果黄先生的确认为有“歪曲”存在,并且本着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宽阔关怀,有意代美国政府“讨个说法”,不也应该先向中美两国政府提出商榷,然后再据以纠正中学教科书的错误吗?至于以“无限上纲”的手法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干预,更已逾越出常规的“学术”范围,多少提示出某些“打假”者非“学术”的心态。
在我看来,比较正常的学术批评是“批评者在自己从事研究的领域内说话”。这一点我近来已说过不止一次,仍愿再次提请注意。黄先生驰骋美国史领域已数十年,但中美关系似乎并非他的强项;越界立论,又要避免给人以“外行”的感觉,就更宜遵循史学最基本的规则——尽量多查阅第一手资料。可惜黄先生热情有余而严谨不足,选择了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取向,在自己不熟悉的历史领域尝试自己没受过训练的语言学探索,复受情绪性因素的影响,终走上“随意解释”的不归路。
“学术打假”实非易事,特别需要“打假”者自身在学术上立足稳固。如果以维护学术的热情代替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核查具体文件中特定的文字表述就上升到语言学上进行悬空泛论,等于是自己制造一个本不存在的问题然后进行辩驳,正是典型的“自立自破”。这与“打假”的初衷实相违背,倒与“打假”的目标更为接近。司马迁曾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句老话非常值得我们治史学者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