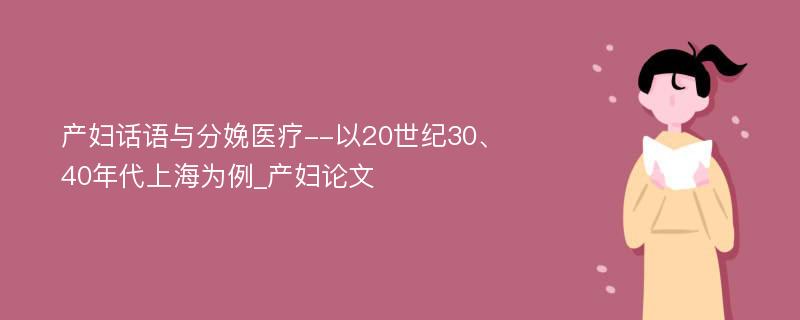
母性话语与分娩医疗化——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母性论文,上海论文,四十年论文,话语论文,医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R173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10)04-0058-06
在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中,女性是颇受关注的群体,是各种话语争相表述的对象。其中,生育话语与富国强种这一目标之间的关联十分密切。因此,分娩卫生成为号召国家、社会与妇女采取集体行动保持种族生命延续的一种动员策略以及政府卫生行政的重要纲领。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剖析母性话语对女性身体的新诉求,以及分娩医疗化对女性身体的宰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女性卫生问题。
一
中国的婴儿与产妇死亡率问题是民国以后较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有人指出中国婴儿死亡率颇高,平均约166‰,与先进国家相比竟高出数倍。[1]产妇的死亡率也高得惊人,与婴儿死亡率不相上下。由于健康母体产生健康婴儿、健康婴儿代表未来强大种族的逻辑,母性的保护作为一项国家与社会的事业被提了出来。同时,分娩卫生被视为妇女为履行对整个民族的母性职责而应该自觉掌握的常识。
公共卫生学家胡定安在“国家与社会之妇女卫生问题”一文中探讨了妇女卫生的“一般”问题。他指出,尽管妇女运动蓬蓬勃勃开展,但是妇女卫生问题尚未被给予充分认识。因此,他撰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要唤醒女子开展一场妇女卫生运动,国家与社会对妇女的生活负起监视与保护的责任。因为从公众卫生角度来说,妇女与未来的国民有密切关系,所以妇女卫生是一般的,不是个人的。就国家卫生行政而言,就是要“使一般妇女们免受胎产的痛苦和一切生命上的危险疾病,及免除有影响及于小儿的疾病,使妇女们对于子女,可全力负担母亲的责任,国家可以得到由健全母亲养育出来的健全国民”。从这个意义来说,国家为谋强种起见,应防治性病、设立收容生产(即分娩)之公立机关、立法保护妇女等,各公立医院产科部应通过免费讲解、展览会等形式指导初产妇“养成一正式母亲”。[2]
胡定安的建议代表了一种趋势:在富国强种的话语中,妇女卫生问题由私领域到公领域的转变,亦即由“个别的”到“一般的”的转变。同时,妇女卫生也应被纳入卫生行政范围,从而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所应采取的手段。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民族危机恶化,国内局势动荡,内外交困的国民党试图以复兴民族的姿态与作为使自己摆脱窘境,母性则成为可利用的重要资源。① 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7月31日被确定为“全国儿童年”,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此“唤起全国民众注意儿童教育,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及图谋儿童福利,以完成儿童之肉体、精神及社会的能力”。[3]母性保护问题成为焦点:“母性保护就是保护有孕的妇人及产妇。因为胎儿的安产不仅是做父母的人所希望的,也是全社会所希望的,故社会当然应尽保全儿童生命的义务。但照统计看来,儿童出生时往往发生障碍,考其原因所在,不外对于母性保护事业尚未能充分的顾及,对于母性的教育未能彻底之故。所以母性保护是儿童保护上不可忽视的。”[4]在这里,“保护母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妊娠卫生与分娩卫生的代名词。按照富国强种的逻辑,产生健康儿童的母体应该得到保护。因此,分娩卫生作为号召国家与社会乃至妇女自身保护母性的一种动员策略而存在。新法助产、妇婴保健等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二
事实上,母性保护的一个基本立场在于对贫穷母亲的扶持。时人观察到,以上海一般劳动者的家庭情况来说,妇女肩负沉重的劳动负担,且囿于经济拮据,是绝对谈不到胎儿的保护与卫生的,可以说,儿童“只有被生的义务而无受教养的权利”。中国一般贫民妇女处置婴儿的方法,“非但不足以养护,简直把中国整个民族的生命断送了”。[5]对劳动阶层妇女而言,工作与履行母职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矛盾的。既然母性对于富国强种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自然不可偏废。因此,在职业与母性之间找到平衡就变得十分紧要,“妇女就职,妇女最要注意母性勿使有所妨碍就是!”[6]妇女不仅要学习母性与儿童保护的科学知识,也要尽量避免恶劣的劳动条件对母性机能(主要是生育能力)的伤害。[7]
时人建议,为了保护母性,让贫穷妇女更好地履行母职,国家应大量在农村与都市中建立免费的卫生顾问所、孕妇免费收容所、分娩所;迅速建立贫穷产妇的津贴制、产前产后休息制;对于非堕胎不可的孕妇,应予以公开就医、施行手术的免费服务,并应严厉禁止无科学常识的秘密堕胎等危险行为。[8]通过建立免费医疗机构以及立法,南京国民政府欲表明解决贫困、堕胎等社会问题的态度。30年代初,宪法草案中的“人民权利问题”有关母性保护的内容体现了这种态度。例如第二十三条“为母者有受国家保护及扶助之权”,补充第一条“妇女在生产前后及哺乳期间依法受国家特别保护及扶助”,第二十四条“非婚生子应受国家之保护”等。[9]
此外,由于“母性保护就是保护有孕的妇人及产妇”,因此妇婴保健机构作为母性保护的机关应普遍设立:“最近上海市有妇婴检查机关的设立,此外,托儿所也有几处在试办,我们除希望它们更多的设立以外,更盼舆论机关,多方来鼓吹并督促批评,务使这种机关能普遍的施行,愈办愈进步。”[10]
此类机关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较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观念,即“儿童公育”。这一观念表面上与妇女解放的目标有关。要使男女达到真正完全的平等,必须使妇女从一切生活的琐碎事务中解放出来,把吃、穿、住和育儿等家事交给社会管理,以便自己去从事其他独立的生产职业。这种被称为“家事社会化”的做法以前苏联为典型。其中,育儿社会化亦即“儿童公育”,“国家将负起全责,替做父母的担任儿童的教育、训练和医药卫生等等事务”;“关于育儿方面,欧美各国近年来公共医院增多,妇女分娩差不多都是在医院中进行的,比较贫苦的也可以得到免费住院的待遇。”[11]
谢一鸣在《儿童公育研究》一书中论述了欧美国家“儿童公育”制度产生的原因:一方面,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造成许多“私育的儿童”惨黯的命运,堕胎、溺儿、弃儿等现代工业的“罪恶”陡增;另一方面,妇女解放运动浪潮过后,抚育儿童变成唯一束缚妇女身体自由的因素。[12](P17-20)尽管“儿童公育”旨在解放妇女身体,然而吊诡的是,在谢一鸣所列举的巡回助产妇、妊娠妇商谈所、乳幼儿健康观察员、母亲学校、产科医院等欧美国家的“儿童公育”制度中,妇女的身体乃是作为“产生第二代国民的母亲”的身体——而不是解放了的妇女的身体——受到“无微不至”的保护的。[12](P19-14)即使儿童被视为是国家和社会公有的,而非父母私有的,但是产生儿童的身体却是母性独有的,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母性的身体无法获得解放。
谢一鸣警告母亲们“切勿盲从儿童公育”,因为它并非解决就职与履行母职之间矛盾的根本方法。他建议,妇女在20岁至40岁之间应专心生育和抚育子女,40岁以后可以外出工作。[12](P147)欧美经验之所以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或许正是在于近代中国的富国强种话语。归根结底,儿童的健康才是“富国强种的最大资产”。[13]因此,“儿童公育”强调的分娩卫生仍是出于健全母体产生健全儿童的需要,以及国家与社会在现时政治、经济情形下所应采取的慈善行为。
既然妊娠与分娩是妇女担负着的与富国强种密切相关的重任,是生育健康国民的第一个步骤,那么妇女理应以认真的态度、科学的观念来对待:“妊娠乃为人应尽的义务,但是却不该漫然的、不用意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不论妊娠也好,分娩也好,都要有一种确实的、预定的观念。‘又有喜了’、‘又有孕了’是不行的,非有‘生产优良的孩童’、‘制造健全的国民’这种信念不行。”[14]
与此相应,妊娠卫生与分娩卫生也是妇女必须自觉学习与掌握的常识。当时上海很多报纸、杂志上都会刊载以“孕妇卫生”、“分娩卫生”等为标题的文章,一些卫生书籍也专门介绍妊娠与分娩的生理常识与处置方法,如妊娠各月胎儿的变化、母体的生理变化、妊娠中的摄生、产期预算方法、分娩的顺序、产室与分娩器具的准备以及婴儿处置法,等等。[15][16]
虽然怀孕与分娩是生理过程,但也存在转为病理的危险,如妊娠中毒、流产、难产和产褥热等。尽管无知产婆被认为是导致难产的罪魁祸首,然而产妇缺乏产科知识也被认为是一大原因:“欧美各国,鲜闻有因难产而致命者,推原其故,当由于产科知识普及所致。是以欧美妇女,自受孕以至临盆,莫不遵守医师之检验;即有难产现象,医师既可矫正于未产之先,亦可挽救于产生之际;不致临时仓皇,措置失当。反观吾国,孕妇均以受诊为耻,非至难产临危时期,绝不仰求于医者之门;医师虽能,究乏起死回生之术,焉有不束手待毙者乎?”[17]
为了减少分娩危险,孕妇要适当运动以增强体质,合理饮食,还要定期到医生处进行产前检查,遵从医生与助产士的嘱咐,对于分娩疾病要早察觉、早防范。分娩时,应延请有名医生,或前往医院,不可妄招鲁莽产婆。妇女接受这些基于西医产科知识的建议,就是在保护自己的母性身体,也就是在保护未来国民。这也就是所谓母职训练的基本内涵。
以上我们看到分娩卫生是如何参与建构富国强种话语,以及这一话语是如何塑造女性身体角色的。“国家兴亡匹妇有责”、“新贤妻良母”都是借用传统资源重新在母性与民族之间建立关联。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帝国主义这个值得效仿但同时也必须对抗的因素。分娩卫生成为具体的动员策略,使国家、社会与妇女围绕诞育健康国民这一目标而共同行动,从而普及西医产科知识,推广新式助产,设立妇婴医疗机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妇女的身体与健康只有在作为母性的一种具体表现时才有意义。
三
所谓“分娩医疗化”,可以理解为西方18世纪以后新的助产术通过新式助产者应用于分娩领域的过程;与此同时,大量新医院尤其是世俗医院的出现为临床医学的诞生提供了场所,产科也与这种医学的整体转向相一致。此外,人口统计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技术使得分娩被纳入国家的总体规划,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分娩的医疗化与国家化进程。[18]
对一个生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产妇而言,分娩方式有多种选择。如果她是个新派女性且家境殷实,或许会选择私立产科医院住在头等病房里分娩,由知名的产科医生来接生。如果她是穷困人家出身,雇用产婆到家里接生可能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或者她受到分娩卫生宣传的影响,希望尝试新法接生,她可以通过某种途径获得某私立产科医院的“免费接生券”,进入那里的三等病房待产,并在产后免费住上几日。当30年代中期各区卫生事务所增设妇婴卫生事务后,她也可以预约所在区卫生事务所的助产士来家里接生,当然,产前检查是必要的前提条件。如果她实在贫困而付不起过多的接生费,尤其是那些额外的药费如催生针、强心剂等,则可以申请有限的免费接生名额。不论怎样,随着分娩卫生的逐渐推行,分娩行为的医疗化亦在逐步形成。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分娩的医疗化同时也是女性的身体及生活医疗化的过程。女性所面对的不仅是分娩场所的改变,还有新的医疗空间中所蕴藏的新的知识权威与医患关系。对产妇及产家而言,选择医疗化的分娩行为也并不总是安全而愉快的经历。那些讲述产院中分娩体验的妇女告诉人们,与可置产妇于死地的稳婆之手相比,产科医院临产室的象征意义也绝不会令人感到舒服。
一个名为振华的产妇在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分娩。在经过初诊后,医生确定她即将分娩,于是让她搬到临产室。在这个密闭空间内,家人被隔离在外,振华感到自己如同身处刑场一般:“这室面积很大,设备也颇完备,不过在产妇的眼中看来,无异是一个刑场。那高高的产床,也就是一座刑台。一人上了这个刑台呀,生死存亡是没有把握的,也许可以说他就是生与死的交界线吧?……军士们上战场杀敌,是为国家流血,我们妇女生产,不也是为国家流血吗?这产科医院不也是女子们的战场吗?我们妇女牺牲在这生产的战场上的,一年之中不知有多多少少呢!……”[19]尽管费尽气力,振华最终还是顺利产下婴儿。在完成个体分娩行为的同时,她明显感到亦完成了女性身体所承担的富国强种任务。临产室就是或生或死的战场。而在胜利之后,大多数产妇还须面对十几日寂寞而单调的住院生活。(头等、二等病房的产妇可能不必经历这种寂寞,因为这里允许家人陪护。)
有时,对临产室的恐惧与对医生的不信任交织在一起。一个名为冬莹的年轻初产妇产前在“古庙似的”医院里住了9天,这让她感到窒息与苦闷。当她被抬进临产室后,她似乎做好了当个“产死鬼”的准备。而当她看到难产器具,明白自己可能难产时,逃离出去就是唯一的想法。经过麻醉手术后,她被转到病房,并开始出现高热症状。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医生也不能确定。于是,她在心里痛骂医生,把她的性命当儿戏。医生对她进行检查时,她感到疼痛难忍,“终不懂西医为什么会如此不温柔,令人厌恶”。产后十日,不但病情没有好转,甚至都没有见到自己产下的婴儿。最终,她决定离开医院这座“鬼牢”,就算死也要死在家里。[20]
振华与冬莹对于出院回家感到如同久离家园的游子回到故乡,然而在产院的经历让她们仍旧心有余悸。病人的呻吟、护士的忙乱、难闻的气味,通常是产妇初入院时的不快体验。对密闭的临产室恐怖情景的想像加剧了分娩体验的痛苦。而医生在施行体检甚至手术时的冷漠更增加了医病关系的紧张。与冬莹一样,一个叫君平的产妇初次分娩就选择入院,她的恐慌主要源自两方面:怕医生动手术以及在病房里独处。她后来写到:“虽然我的家里没有这病室一样干净、漂亮,但是总有些不习惯。”[21]在产妇们看来,舆论所描绘的干净而明亮的产院病房不会是“卫生”的表现,而是生疏感的来源;至于降低产妇、婴儿死亡率的新法接生,也绝非是造福母婴的代名词,而是充满不快与恐慌的分娩体验。人口统计的宏观效果对个体而言失去了意义,分娩始终极有可能是“一脚棺材里,一脚棺材外”的生死界限。
我们尚不能确定究竟哪些产妇会选择在医院分娩,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她们住在几等病房,至少只有中产阶级的家庭才能负担起住院分娩的费用。此外,能够将自己的分娩经历写成稿件发表在杂志上的妇女(或其丈夫),应该受过教育并且很有可能接受了分娩卫生观念。相比之下,对大部分下层妇女而言,或许从未想过住院分娩,即使请助产士到家里来接生也是万不得已的选择。
如何解决贫苦产妇的分娩卫生问题,是医疗体系以外的政府应当考虑的。作为富国强种诉求之一的分娩卫生,在经过若干年的舆论渲染之后,政府究竟给予了多大推行力度遭到怀疑。有人感慨1947年上海市立妇婴保健院的设立,认为即使40张床位无法满足上海众多贫民的需求,但政府此举“究竟比那些捉拿小贩、登记娼妓之类”要高明得多,希望政府“在人口密集的都市设立规模较大、设备较完善、名副其实真能解决部分妇女与婴儿的保健问题的医院”。[22]而一些私立医院却毫无仁心。有一个产妇难产一天一夜,产婆束手无策,于是丈夫将其送到医院。按照丈夫的说法,他明知道医院里分娩是最妥当不过,然而由于在工厂做工收入有限,无法支付入院分娩的费用。医院的主任医生却以无可奈何的声调回答,私人医院无法做善事,按照产妇情形须施行剖腹手术,照医院规定,手术前需预付若干手术费。当丈夫到工厂借钱回到医院后,产妇却因施救过晚而死亡。[23]
分娩医疗化给出了一个安全分娩的承诺,然而在现实中穷人却很难享受。有人指出,分娩卫生的推进并非单纯的医疗问题:“(产妇的牺牲)仅是产科技术上的预防、医疗,能解决了问题吗?我们不是看到许多产妇在产后不满三日就操作家务,而留下了疾病的可能性,许多孕妇因劳动过度而成了难产吗?这是医疗的问题吗?”[24]还有人明确指出,那些以利润为根本前提的产科医生或医院,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罪恶表现,“制度上未有根本的改革,这种现象是无法避免的。而这种局部制度的改革,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全盘改革又有相连的关系,不是枝枝节节的办法所能有效的”。[25]正因如此,战后分娩卫生成为公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让市民享受到免费的分娩医疗服务,尽管当时公医制度的推行存在诸多困难。
综上所论,民国时期“保护母性”的口号表面上直指对女性健康的关注,然而在富国强种的话语下,女性的身体与健康只有在作为母性的一种具体表现时才有意义。由于女性自身担负着诞育健康后代的生理机能,因此她们被要求自觉地采取科学的分娩技术与行为方式。分娩医疗化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以降低产妇、婴儿死亡率为标榜的西方产科学技术并不能够使女性摆脱经历生死界限的恐慌感,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女性在选择分娩医疗化的同时,体验到的是身体所遭受的宰制。医院临产室的冰冷氛围,医生与助产士的熟视无睹与粗劣手法,这些是母性神话未曾提及的。而现实制度的缺陷使得分娩医疗化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对下层妇女而言,她们很难享有分娩医疗化的福利,亦无从履行科学育儿的使命。
在分娩医疗化已基本普及的今天,一些医生与学者反思分娩方式,从历史汲取灵感,倡导居家分娩、采用抱腰蹲踞产位等,同时强调对分娩产妇的精神支持,而非助产技术本身。这并非否定近代以来的分娩行为与技术变革在保障人口数量以及健康方面的有效性,而是基于人性化的立场重新思考女性身体与医疗化问题。
注释:
① 近代中国的“母性”话语是较为复杂的一个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要求。20世纪20年代瑞典教育理论家、妇女运动家爱伦·凯(Ellen Key)的“母性保护论”被介绍到中国后,“母性”(Motherhood)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爱伦·凯认为女性最重要的天职就是“母职”,母性是提高种族品质、民族进化的关键,因而反对“儿童公育”、女子独身、妇女参政等这些阻碍母性发展、破坏母性神圣性的主张。这种带有贤妻良母主义色彩的观念在中国被男性知识分子利用作为修正妇女解放运动的依据,让“出走的娜拉”回家。他们呼吁母性对家庭、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尤其在养育下一代方面要履行“科学化”的母职。而当时“母性自决”、“摆脱母性”的呼声则戳穿了男性主流话语建构的“母性虚像”。俞莲实认为母性神话与妇女的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是节育运动的一个推动因素。参见俞莲实:《民国时期城市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以北京、上海、南京为重点》,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3月,未刊稿,第137-1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