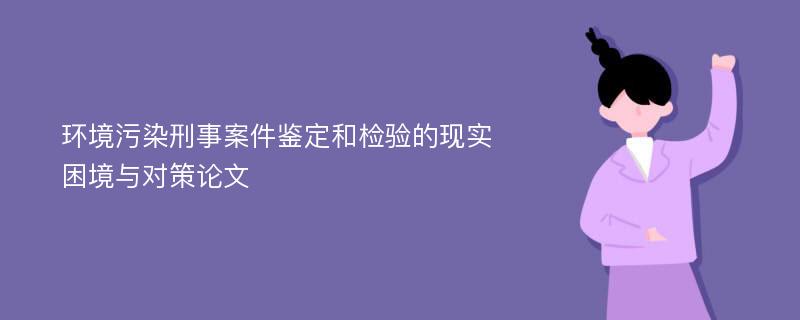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鉴定和检验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陈嘉一,胡 佳
(四川大学法学院,成都 610000)
摘要: 2016年第29号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可借助于鉴定意见或检验报告认定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基本确立我国环境污染犯罪鉴定和检验制度。鉴定检验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统一化。然而,司法实践中出现司法鉴定主体混乱、鉴定意见采纳难、检验报告法律地位不明和跨学科知识人才储备不足问题。法律与部门规章的割裂,落后的评估技术、尚待完善的配套制度、模糊的鉴定事项和因果关系鉴定作用不明,以及鉴定制度发展的历史因素是导致现实困境的根源。应从统一立法规范、完善机构目录和鉴定事项内容、明确检验报告的鉴定意见、法律地位,着手完善环境污染犯罪鉴定和检验制度,为正确办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统一环境污染执法司法尺度提供技术保障。
关键词: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鉴定;检验报告
当前,我国正经历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实质化改革,准确认定证据属性、适用配套的证据认定规则及实现证据调查实质化是重点改革内容。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呈现井喷式增长趋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①。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深刻阐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2019年2月,两高三部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下文简称“纪要”),要求各部门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刑法,统一环境污染执法司法尺度,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惩治力度。妥善办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成为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因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专业性强,涉及环境法、环境科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知识,在鉴定和检验方面问题突出。为此,2016年《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6年司法解释”)第14条确立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鉴定和检验“两条腿走路”方式②。本文拟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鉴定和检验的现实困境入手,反思问题根源并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以期为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谏言献策。
一、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鉴定和检验制度的现实困境
(一)司法鉴定主体混乱
2015年12月,司法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笼统地对鉴定机构设置发展规划进行了整体构想。随后在2016年,环保部公布了第二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但并未规定环境污染鉴定主体问题。
查阅第一批、第二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以下分别简称第一批《名录》与第二批《名录》),细读其相关问题说明并对比表格发现,第一批《名录》和第二批《名录》分别列明了12 家和17家机构及协作单位,级别为国家或省级,其中有监测站、研究院、鉴定中心。此两批《名录》上的监测站和研究院的单位性质均为国家或省级直属事业单位(如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名录中的鉴定评估中心有非营利社团组织(如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心),有事业单位(如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也有隶属于司法机关内部设置的鉴定机构(如昆明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同时,第二批《名录》中的协作单位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绍兴市环保科技服务中心分别属于独立的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和企业。
推荐机构名录是环保行政部门的内部文件,旨在为机关内部办理此类案件提供指导参考作用,抬头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各派出机构、直属单位”。附在第一批名录后的问题说明,强调名录仅具有推荐性质,供需要鉴定评估机构有关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参考,亦不属于行政许可,不具备强制力。但这并没有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笔者发现:一,该文件仅针对环境行政机关,效力不涉及司法机关办理的环境刑事案件;二,推荐机构既有国家级也有省级,未说明其他省的省级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在本省内是否有效;三,既然推荐名录不具备强制力,若委托《名录》之外的机构进行鉴定,得出的鉴定意见效力如何认定;四,名录上的机构性质多为事业单位,这样的“出身”难以确保鉴定的中立性。
2018年6月14日,司法部出台《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此规范性文件规定了鉴定机构的资质认定和审核登记的要求,说明立法者已意识到规范鉴定主体和鉴定人资质的重要性,但同时应当看到,规范鉴定主体只是鉴定和检验制度的第一步。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统一鉴定主体资质认定及其鉴定意见的效力需要梳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程。
推进各地区鉴定机构的建设,严格鉴定标准,以解决目前鉴定机构资质混乱、标准落后的问题。虽然我国环境污染司法鉴定机构数量较五年前已经有大幅增长,但仍有部分省份缺少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已有准入环境司法鉴定机构的省份,也应当丰富鉴定的类别,吸纳高等院校、社会机构等科研力量,优化鉴定队伍。其次,做好申请准入环境司法鉴定机构的专家评审工作,组建专家评审团对环境污染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专业能力、硬件设施等进行评审,严格坚持“凡登记必评审”原则,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准入登记提供可靠依据和参考。最后,应当加强已登记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常规管理和考核评估。包括加强对拟从事环境污染司法鉴定业务的人员和已登记准入的鉴定人的执业培训和考核,注重加强执业人员的执业水平和能力。实现对环境污染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动态管理,完善投诉和退出机制,依法惩处违法违规的执业行为,确保鉴定工作规范化进行。每年,还应依据各地管理规定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执业条件等重新核定业务范围。
(二)因果关系、损失评估,鉴定意见采纳三大难
环境损害具有周期长、因素多、不明显的特点,所以因果关系判断较难。首先,环境损害周期长表现为损害结果要通过一定周期才显现出来。其次,在环境损害鉴定中,导致损害产生的原因是许多污染因子复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污染因子处于自然环境的融合之中,很难或无法区分具体污染因子是导致损害发生的主要成分。多种因素交叉影响下很难判断具体引起某种疾病或身体健康的真正原因。[1]最后,许多环境损害并不能直观感受,需要专业鉴定,比如土地污染不一定能通过视觉和嗅觉发现。
汤甲真14岁时,得知伯父送儿子到离家10多里的一所小学寄宿读高小。他羡慕极了,再三请求祖父也送他上学。得到同意后,他满心欢喜地在开学过了20多天后入校。“当时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开始接受爱国抗日的思想教育,激起了为抗日救国而读书的极大热情。”他说。
在民法领域,立法者考虑到一般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会明显导致不公正,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规则来解决因果关系证明难题,减轻当事人(主要针对污染受害者)的证明难度,以有效地获得诉讼救济,实现实体正义。这样的处置方式仍然引起了较大争论,一些国家认为证明责任倒置只适用于几种类型的案件,而环境侵权案件不在其中③,最高院终审的“污染致蝌蚪死亡案”也没有完全按照举证责任倒置④。
不同于民法领域的优势证据规则,刑事诉讼法坚持的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如现在普遍推广的疫学因果关系认定,其方法为病情的发展满足时序的逻辑要求,原因一定出现在结果之前,满足量与作用的关系,用以证明原因和损害具有统计学上的关联,检验病因的方法和结论与临床学和病理学不相矛盾反映了生物学规律的符合性,保证结论与现有的科学原理不相违背。[2]从本质上讲,此种因果关系鉴定的证明仍然采用的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既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既定的事实,应当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该如何与鉴定衔接。同时,大自然具有一定限度的自净能力,污染潜伏和不断累积,达到一定的程度,超过了其自净能力,才会以明显的损害方式浮现。环境污染还具有隐蔽性,如果某些污染的污染因子多、发现较晚,会导致鉴定周期长,大自然的自净能力也会发挥作用,一些污染因子会转移稀释或者挥发,此时取样检测进行损害评估,其结论的证明力往往不准确。
朋友来,必定会跑去看。前,后,左,右,上,下——有人甚至端过头顶,连下面也不放过。不过,最后还是迷茫地问我:你养的鱼呢?鱼缸里怎么什么都没有!
“既然你要儿子,我也不跟你争,但我每月要看他一次,抚养费由我来出,房子就留给儿子。我什么都不要,明天走人!”
(三)检验报告地位不明
2012年刑诉法解释第 87 条⑤和 2016年司法解释第14条⑥将非法定鉴定机构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意见称为“检验报告”,发挥法官定罪量刑的参考作用,并应参照刑诉法解释中鉴定意见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认定。具体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检验报告的适用条件仅限于有鉴定需要,但无法定司法鉴定机构,且属可以检验之事项。适用方式是由国务院环保部或公安部指定;二是检验报告只“可以”发挥“参考”作用,从严格解释上不是证据;三是与鉴定人一样,检验人员承担着出庭义务。经通知后拒不出庭的,检验报告不能发挥“参考”作用。总体来看,立法对环境污染检验报告的态度十分“暧昧”,一方面宽松的对待检验资质,另一方面又严格要求对其按鉴定意见进行审查认定。相关司法解释也未阐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检验报告究竟具有何种法律地位?检验机构及检验人需要满足何种条件?如何在庭审中合法运用?怎样发挥“参考”作用等系列问题,不仅如此,这还导致辩护人无法就检验报告之检验机构资格或检验人资质提出辩护意见,实际上是对辩护权的忽视和侵犯。
“定罪量刑的参考”的表述在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并不陌生,常见的还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报告”。⑯正如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关注,学界对检验报告之法律属性亦探讨热烈。龙宗智教授和孙末非教授认为,检验报告属于证据,并应当通过扩充“证人”之内涵,使检验人这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作为专家证人身份出庭参与诉讼,其出具的检验报告则视为证人证言,适用证人证言的证据规则。但需注意的是由于检验人是根据自身专业技术知识而对专门性事项出具报告,故不能证人证言审查规则中的意见证据排除规则[8]。两位教授还对法律未变更前更为适宜的审查方法进行设想。他们认为,基于检验报告的书面性,可以暂时将其作为书证并参照鉴定意见的标准进行审查,“对于检验条件完备、论证过程充分、结论足以让人信服的、符合法定要求的检验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予以采信”。[8]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专家可以作为鉴定人或证人参与案件审理,前者以出具鉴定意见的形式提供对专门性问题的意见,后者则以出庭提供证言的方式提供意见或对鉴定报告发表意见。还有一种情况是专家作为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但这与前两者截然不同,因为此处专家的功能并非给法官定罪量刑提供依据或参考,而是作为合议庭成员,直接认定案件事实问题。照此理解,检验人承担与鉴定人相同的诉讼功能,但并不具有鉴定人资质,又因其并不对鉴定意见提出意见,也并非出庭提供证言,无法划入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其他类型[4]。
(四)跨学科知识人才储备不足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是环境科学、鉴定学、诉讼法、证据法学四门学科知识的交叉地带。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对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损害范围、程度等进行合理鉴定、测算,出具鉴定意见和评估报告,鉴定人需要有跨学科的视野和丰富的知识储备。
当今世界,多种检测环境变化的物理、化学、生物指标不断被科学家发现,环境污染鉴定研究取得较大发展,人类主动应对环境变化的灵敏性、主动性越来越强,土地、空气、海洋三种污染形式各有不同的鉴定手段,新技术不断出现,鉴定环境污染的手段趋于多样,并逐步探索、验证最精确的鉴定方式。从诉讼法、证据法学角度来说,目前我国对环境刑事案件的研究集中于鉴定主体资格,鉴定意见的可采性及诉讼操作,多集中于理论方面的研究,不足之处是对上述实践性极强的问题的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法学学者与环境学、鉴定学学者分属于文科、理科,“隔行如隔山”,不了解跨学科知识导致制定的处理方式顾此失彼。
环境污染案件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量逐年增长,明显的趋势是行政处罚的适用率远远高于刑事处罚,在公安机关受理的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未进入审判环节,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跨学科知识的制约。在犯罪侦查环节牵扯到环境科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病理学、毒理学等学科,在案件侦查、起诉、审判环节又需要追求专业知识和司法审判的整合,同时具备以上几种知识的审判人员可谓凤毛麟角,除了寻求一种统一的认定标准之外,还需要法院和法官增强学习能力。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Industrial Robot Simulation Technology Training” based on Robot Studio
二、现实困境之原因分析
(一)立法和部门规章缺乏统一规范
如上文所述,我国的环境立法大多为倡导性规制,在我国《环境保护法》等基本法有关鉴定问题出现空白的前提下,运用下位法和行政法规对此问题进行构造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首先是立法的效力问题,下位法和行政法规进行的规制是否会违反基本法的立法原则。在我国,有关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法律有《水污染防治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农业法》《矿产资源法》等,有关同一种污染问题可能在多部法律中都有规定,如有关水资源污染,在《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分别规定了罚款⑦和责令停止排放⑧的不同手段。我国的立法存在着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规章的效力位阶是既定的事实,究其原因是利益冲突,由于不同层级的行政机构拥有自己的立法资源,所以政府部门主导订立的行政法规,以达到某种行政目作为出发点,同时与政府利益、部门利益紧密关联,产生抵触和冲突是不可避免。在环保立法上显著表现有:一、规章超出基本法、上位法授权的范围进行处罚;二、上位法作了规定或进行了修改,下位法与之不符,却没有及时修改或废止。如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法规颁布后,原先制定的相关法规或规章的部分条款未及时修改或废止,个别地方依然依据这些条款制定新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来维护或扩大本不应存在的权力和利益[5]。
目前,中央和各地有关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浩如烟海,地方立法者不愿梳理、废止冲突、无效法规,反而重视新规章制度的出台,鲜少考虑与法律及上位法规是否一致的问题,此类“省事”的做法是一种“懒政”,扩张了行政权力、忽视公共利益,群众、企业救济无门,不仅导致个体权利受到侵犯,影响经济发展,更损害了作为百年基业的生态环境。
(二)评估技术落后,配套制度欠缺
2011年5月环境保护部出台的《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在附件列出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版)》(后文简称《推荐方法》),随后在2014年10月24 印发了第II 版。其中规定了五大类污染损害范围:人身损失、财产损失、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应急处置费用、事务性费用。财产损失中,《推荐方法》对固定资产损失、流动资产损失、林业损失和农产品损失规定了不同的计算方式,固定资产损失、流动资产损失的计算方式为数学公式⑨,农产品损失的计算方式是准用性规定⑩,而林业损失的评估方法参见农产品财产损失的计算方法,配套制度的短板体现在计算方式上。林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职责不同,农业生产的目的在于产出农产品,而发展林业的目的在于保护生态资源,农业、林业受到环境污染的原因和危害后果也不相同,农产品受到污染对人民健康的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林业损害对人的影响是间接的、不明显的,两类损失运用同一个标准进行计算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外,农产品财产损失参照的《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于2008年提出,已无法满足目前实践需要,只规定了要对因污染而死亡的渔业资源及因污染而导致品质下降的渔业资源进行赔补偿,但未给出因污染而导致水产品品质下降损失的评估方法,同时,有关农产品有毒有害物质的积累影响食用安全的内容始终是空白。
另外,有关环境污染的监测标准配套制度也不完善,如1990年3月1日批准实施的《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不包含国家对渔业生态环境水质监测的氮、磷指标,在鉴定的标准上已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发展。本来专业性极强的各类环境标准就让审判中的法官如堕云雾,而配套制度不完善、标准落后的问题更让司法实践荆棘丛生。
图1示,PLAGL2主要表达于阳性细胞核与胞质中,PCa中PLAGL2阳性表达率(80.6%,83/103)高于良性前列腺增生(22.0%,11/50),其中在PCa组织中弱阳性26例,阳性28例,强阳性29例,在良性前列腺增生组织中弱阳性7例,阳性4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003,P<0.001。
(三)鉴定事项模糊,因果关系鉴定的作用不明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2 条将鉴定事项进行了四大分类:(一)法医类鉴定;(二)物证类鉴定;(三)声像资料鉴定;(四)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没有将环境污染鉴定单独归类,有关环境污染的笼统归于其他类统一管理。2015年12月21日,司法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列举了七种环境污染的鉴定领域,但并没有具体规定某种污染需要鉴定的事项。同时,各鉴定机构对于同种损害的鉴定名称不一,对于环境污染损害财物损失的数量化鉴定,林业方面有“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鉴定”“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司法鉴定”⑪“森林灾害损害鉴定”⑫。水资源方面有“海洋污染损害鉴定”“海洋与渔业损失污染评估鉴定、近海海洋与海岸带环境损害鉴定⑬。对于同一种污染损失的鉴定有多种名称类似的鉴定项目,且其名称为专业术语,非专业人员难以理解其内涵与外延,更不用说选择其中最具参考标准的项目了,法院选定鉴定机构以及认定损失范围非常困难。
未来对于鉴定机构管理化管理的展望是形成全国统一的鉴定机构名录,该名录既包含了依法成立并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又规定了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进入名录的条件。各行政单位将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及其鉴定范围在互联网上公开,地方保护壁垒逐步消除,跨行政区域的鉴定效力问题得到解决,环境案件“三审合一”的配套措施臻于完善。
(四)历史因素制约检验报告作用的发挥
司法解释把检验报告界定为定罪量刑的参考,并采取含混不清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审判需要。不同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会遇上关于环境法或相关生态科学的各类专业问题,法官对此很难进行准确判断,审判中对鉴定意见的依赖性大。但我国司法鉴定整体发展较晚,且环境污染司法鉴定属于三类传统司法鉴定外的其他鉴定事项,发展极不健全。具有环境污染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较少,费用高昂,难以满足办案实践的需求,故司法解释规定可以指定不具有环境污染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以作为鉴定意见的补充,也代表着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从多元化局面向规范管理的过渡阶段。[6]此外,由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行政从属性,案件办理机制及行刑证据转化规则不断细化完善,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更强调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法院的通力合作,将环保部门及公安部门确立为指定机构进行检验的主体,既是必要,也为可行;另一方面是受我国审判的习惯思维的影响。我国刑事审判追求“实体真实”,检验报告既能证明案件专门性问题,使用门槛又“较低”,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了便利。检验报告“可以”发挥定罪量刑“参考”作用,又给予法官较为宽松的自由裁量权和高度的适用灵活性,使得法官“可以用”“愿意用”。
三、完善对策
(一)消除行政立法冲突,统一鉴定主体资质
《名录》反映出鉴定主体缺乏统一规范的问题需要出台强制力的法律法规来解决。法律、行政法规应当做好对鉴定主体资质的原则性规定,下位法在遵循上位法精神的前提下再对本行政区划的鉴定主体资质进行规定。同时在梳理行政立法时尤其应当协调好辖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目前国家规范鉴定机构的立法出台之前,各省级行政单位的司法局应当做好本辖区内环境刑事案件鉴定机构及鉴定人资质的审查和认定。另外,法院需要明确其他省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在本省是否有效力,法院可通过庭前会议等前置程序对此进行过滤,在征求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之后,检查鉴定程序启动是否合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选定是否科学,及是否需要鉴定人出庭,以达到繁简分流的目的。
(二)严格评审流程,完善机构名录
基于前文四个时段内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在SPASS软件中分别拟合回归方程,预测该区域2020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承载力值,推算2020年生态盈余与生态压力指数,以此判断未来2020年公园的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大陆法系把鉴定人定位为法官的辅助人,要求法官“不应下意识地接受鉴定,而是竭力形成自己的意见”,即使鉴定报告中对因果关系已经作出了认定,法官在审判中必须独立作出判断。然而法律对于鉴定报告到底是事实认定还是法律判断并无明确规定,导致法院判决依赖鉴定报告,将鉴定报告中的因果关系作为自己的法律判断来使用,缺乏对鉴定意见的独立审查。
(三)完善鉴定事项内容,明确因果关系鉴定的作用
环境污染损害鉴定包括人身损害。受害方根据《民法》《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律解决赔偿问题,人身损害亦需要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在当前环境污染“三审合一”模式改革背景下,一并进行人身损害鉴定有利于统一执法尺度,节约司法资源。但在环境污染中进行人身损害鉴定需要注意,环境污染司法鉴定与其他司法鉴定并列且独立,故对环境污染人身损害鉴定时应配备专业临床医学等人员,建议由省级卫计委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专门的环境污染人身损害的人员队伍进行规范管理,并应注意编制人身损害的疾病目录等。
目前我国空气污染司法鉴定有国家标准17项⑭,海域污染司法鉴定领域内共有国家标准77项,行业标准225项⑮,环境污染鉴定参考的国家标准内容相互引用的情形很多,为避免同一种污染采取不同的鉴定方式,检察院,法院应当科学选取鉴定标准。首先应当确定污染区域,如水污染要考虑到是渔业水质污染还是自然保护区水质污染,再考虑鉴定的标准问题。另外,对于同一污染指标的鉴定或者是对于污染损失评估,不同国家标准可能存在不同的取样和操作方式,法院在审判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污染类型、地区差异、案件性质等不同情况进行判断。
德国的目的论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产生,该流派强调翻译所要达到的效果,主要代表人物是卡特琳娜·赖斯、汉斯·弗米尔、贾斯塔·霍茨—曼塔里和克里斯汀娜·诺德。目的论的关注点不是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完全意义上的转换,而是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译者是否能根据译文的意图选择最合适的表达方法[1]。
要明确鉴定机构对因果关系的鉴定并非是对因果关系盖棺定论,而是作为科学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增强法官心证,并未侵犯法官独立的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权。要厘清因果关系鉴定的证明力问题,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和新兴的疫学因果关系等理论,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低于刑事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一方面,立法者需要考虑在环境污染案件中构建刑事、民事证明标准的衔接。另一方面,公害犯罪性质上和公害侵权并无本质区别,仅是危害程度不同和责任后果不同而已。[7]因果关系的鉴定也影响到被告人罪与非罪的认定,因此,法院在审判时不能仅仅根据鉴定意见对因果关系进行认定,应当综合整个案件和所有证据。
第一,准备阶段。针对学生能力的差别进行均衡分组,确保组间竞争的公平性。为每个分组任命小组长,确保小组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明确分组考核规则,确保每个小组能够按照学习目标进行组织活动。
(四)明确检验报告的证据地位
此外,立法之所以纳入检验报告这一“折衷”“中庸”的类型,实际上是在无法开展司法鉴定时,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备用”手段。然而,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刑事检验报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检验报告之形式,既逃脱了严格的刑事鉴定资质要求,又在实际案例中发挥定案根据作用。[4]可见,检验报告这一类材料已被司法实务所依赖,并存在一定程度的滥用。随着我国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深入和环境污染案件办理“三审合一”模式的推进,厘清检验报告之法律地位、准确适用审查认定规则已经迫在眉睫。
就笔者看来,检验报告除检验机构和检验人不具有法定资质外,与鉴定意见基本相同。且检验报告出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专门解释中,是源自司法鉴定机构的缺乏及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要求。2018年9月,司法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准入登记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截至2018年9月,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中专门从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业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共78 家,遍及17 个省。随着环保部门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的不断发布,司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的数量逐步增多。检验报告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司法产物,不再适应当前发展现状。随着庭审实质化的不断深入和行政机关取证合法规范化,证据调查成为法庭审理的重中之重,检验报告对定罪量刑产生了重要影响,实现检验报告规范化势在必行。由此,笔者认为,与其建立一套新的检验报告制度约束机制,不如将检验报告直接纳入司法鉴定制度中,去除“检验报告”这一证据种类,统称为“鉴定意见”,适用鉴定意见的审查认定机制。对于环保部门指定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在证据转化时应当作为稳定性较强的证据进行形式审查,重点审查其资质及鉴定程序的合法性,再辅之以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意见的科学客观性。
注释:
①2017年以来,四川省公安机关共办理污染环境刑事案件131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02人。
②第14条规定:“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公安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③在德国,证明责任倒置目前仅适用于证明妨碍、严重违反职业义务、产品责任、违反阐明义务和咨询义务,而不适用环境侵权领域。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依德国法院判例及《水资源法》《环境责任法》的规定,采用因果关系推定。
④浙江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与嘉兴市步云染化厂等五单位水污染损害赔偿案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法告申民再抗字第17号判决认为:根据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受损人需举证证明被告的污染特定物质排放的事实及自身因该物质遭受损害的事实,且在一般情况下这类污染环境的行为能够造成这种损害。本案养殖场所举证据虽然可以证实被告的污染环境行为及可能引起渔业损害两个事实,但由于养殖场所养殖青蛙蝌蚪的死因不明,故不能证明系被何特定物质所致,故养殖场所举证据未能达到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前提。
⑤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但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或者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以进行检验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
⑥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1)怠速模式必须在信息娱乐系统中激活;(2)必须选择D挡或高效模式;(3)车速在55~160km/h 之间;(4)断油滑行模式(不踩下油门踏板);
鉴定环节是刑事案件中重要的一部分,除了环境污染损害的鉴定,常见的还有对人身损害、血迹、弹道、痕迹等多种类型的鉴定。在许多领域凭借人的感官很难直接判断,需要专业人员通过专业的技术和仪器作出认定。在知识交叉领域,审判人员由于知识面的局限性,只能通过第三方提供的鉴定意见来推断该结论是否具有证明力。鉴定环境损害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和科学方法的可靠性决定了鉴定意见是否具备证据的可采性。目前审判的重点是追求程序正义的实现,法官对鉴定意见本身的科学性既不懂也不重视,“以鉴代审”现象频发。[3]
⑦水法第67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取水许可证:(一)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二)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
作品的主人公盖茨比是来自西部农村,出身卑微,服过兵役,退伍后来到东部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他的初衷是在充满金钱与机会的“人间天堂”般的大城市实现财富梦、爱情梦,成为出人头地的上层人。然而,不谙世事的他,由于缺乏对世事险恶的判断与预测,在“金钱至上”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腐败生活方式的熏染下,干起了贩卖私酒的买卖,虽然一夜暴富,最后却落得个被人谋害惨死的结局,作为理想主义化身的传奇英雄却成了“黄粱美梦”的实践者,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笑柄。
⑧水污染防治法第69条:饮用水水源受到污染可能威胁供水安全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采取停止排放水污染物等措施,并通报饮用水供水单位和供水、卫生、水行政等部门;跨行政区域的,还应当通报相关地方人民政府。
⑨固定资产损失=重置完全价值(元)×(1-年平均折旧率%×已使用年限)×损坏率(%),其中:年平均折旧率=(1-预计净残值率)×100%/折旧年限,流动资产损失=流动资产数量×购置时价格-残值。
本届黄河国际论坛的主题是“流域可持续发展及河流用水权保障”,论坛围绕主题设立流域综合管理、健康河流与环境流量、应对气候变化、流域管理工作和新技术、水管理与公众参与等五大分论坛,同时召开了12个政府间合作及国际组织相关专题会议。国际水利相关新技术、新成果、新设备展览在论坛期间并行举办。
⑩按照《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SF/ZJD0601001)、《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GB/T 21678)和《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价技术导则》(NY/T 1263)计算。
⑪例如四川星辉林业司法鉴定中心承接此项业务。
以汉诗英译为例看译者伦理博弈 ………………………………………………………… 姚婷婷 张 杰(1.70)
⑫例如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承接此项业务。
⑬例如山东海事司法鉴定中心承接此项业务。
⑭详见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⑮详见国家海洋局公报2015年第2号。
⑯刑诉法解释第484条规定:对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的调查报告,以及辩护人提交的有关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的书面材料,法庭应当审查并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上述报告和材料可以作为法庭教育和量刑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庄琳.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若干思考[J].环境保护,2018(17):30-34.
[2]焦艳玲.环境公害诉讼不确定因果关系之解决——以疫学方法为视角[J].河北法学.2017(11):117-125.
[3]程鑫,陈敬根.海洋环境污染案件中的司法鉴定认证问题研究——以海事诉讼“抽象心证”之滥用为视角[J].河北法学,2018(2):98-109.
[4]涂舜,陈如超.刑事检验报告制度的实证研究——评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87条[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3):100-114.
[5]杨银平.地方行政立法规范冲突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6.
[6]胡云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环境污染刑事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
[7]蒋兰香.日本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环境刑事司法的借鉴[J].刑法论丛,2010(1):255-273.
[8]龙宗智,孙末非.非鉴定专家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完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1):102-111.
Actual Difficulties with Determin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Criminal Case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CHEN Jiayi,HU Jia
(School of Law,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00,China)
Abstract: Article 14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No.29 of 2016 stipulates that,in the criminal case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special fact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n be established by means of appraisal opinions or examination reports, thus the determination and examination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s in China is basically established.The determination and examination work has gradually been standardized and unified.However, in judicial practices,there arise the following problems:the subject for judicial appraisal is confusing,the appraisal opinions are difficult to adopt,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examination report is unclear, and the number of talents with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is insufficient.The separation of laws and departmental regulations, the backward evaluation techniques, the supporting systems yet to be perfected, the uncertain items for determination,the unknown role of causal determin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termination system are the root causes for the real dilemma.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determination and examination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s by unifying legislative norms,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catalogue and determination items and contents,and clarifying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determination opinions of the examination report,so that the technical guarantee for correctly handl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cases and for unifying judicial scale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aw enforcement can be offered.
Keywords: criminal cas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judicial testimony;examination report
中图分类号: D9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19)03-0065-07
doi: 10.16104/j.issn.1673-1883.2019.03.012
收稿日期: 2019-04-11
作者简介: 陈嘉一(1993— ),男,四川平武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司法制度。
标签: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论文; 司法鉴定论文; 检验报告论文; 四川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