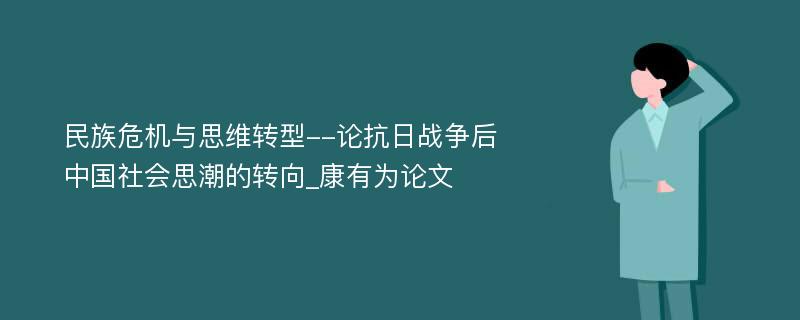
民族危机与思维转型——论甲午战后中国社会思潮的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论文,思潮论文,战后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往往要经历巨大的危机和灾难,并以此为契机,开始新的转机和生机。正如恩格斯在甲午战争前一年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是活动方式改变了,就让命运来实现吧!”[1]中日甲午战争,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耻辱,同时也促成了全民族的觉醒,导致了近代思潮的巨变,引发了传统思维的转型。
一、民族危机意识的深化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传统的中夏外夷的民族意识被注入了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新内容,在思想界逐渐复苏和强化。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就已经感到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自己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过去的“边患”,而是一个十分强大且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于是练海军、办工厂,“自强”、“求富”,发起了洋务运动。但是,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洋务事业,却在甲午之战中毁于一旦,而且败的是那样的惨,条约定的是如此的苛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波,强烈地震撼了国人的心灵,使蔓延已久的“变局”观念扩大为普遍的全民族的危机意识。
最先感到这种危机的是一批思想敏锐的有识之士。文廷式目睹现实,忧心忡忡,引用外国人的话告诫国人:“中国若再不改行新政,吾数年复来,不见此国矣。”“中国人心至是纷纷欲旧邦新命矣。”[2]梁启超说:“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伸,实自此始。”所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3]著名经学大师皮锡瑞说:“自甲午战败,各国对我态度顿变。……外患日亟,国势危弱,朝野咸主变法自强。”[4]著名诗人兼政治家黄遵宪,当时正在湖北办理教案,在与友人游览黄鹤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来,黄遵宪更是痛心疾首。他在给好友建侯的信中说:“新约既定,天旋地转”。这个条约不仅把“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拱手而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产”。他发出了“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5]的深沉叹息。
戊戌维新的杰出代表康有为,也正是在这时崭露头角的。他目睹和约签定后“举国哗然”的社会现实,毅然挺身而出,发起“公车上书”,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痛切地揭示当时普遍存在的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生存危机,以“四邻交逼,不能立国”,“瓜分豆剖,渐露机牙”这样险象环生、朝不保夕的严峻态势,来刺激统治者麻木的神经,唤醒昏睡百年的国人,促使全社会和全民族的觉醒。在民族存亡千钧一发的情势下,无论怎样深刻而精辟的理论说教,也比不上“危机!危机!危机!”的强烈呐喊。在以后的几次上书中,康有为依然是反复陈述这种危机,旨在长鸣警钟,唤醒国人。
民族危机意识成为具有不同政治倾向、政治观点的思想者选择中国出路的共同的基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这场巨大的危机刺激下,彻底放弃了改良政治的希望,进而举起了反清革命的大旗。“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兴中会宣言》的中心思想,就是唤醒全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挽救危机。这正是革命志士和爱国侨胞危机意识的强烈流露。
华侨革命家谢瓒泰,感慨风云,悲愤时事,特意绘制了《东亚时局形势图》。他在这张《时局图》中,以熊代表俄国,以犬代表英国,以蛙代表法国,以鹰代表美国,以太阳代表日本,以肠代表德国。将这些代号放置到中国地图上,形象地揭示了列强瓜分中国之意。他在图边题诗:“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警告国人速起救亡。
甲午战争之后,高涨的民族意识,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社会覆盖面较以往更为广泛。丧师失权、割地赔款的深创巨痛,震惊朝野,在社会的表层和中层,人心激愤,“士气大昌”,形成了“慷慨爱国之士渐起”,关心国事、忧患时局者“在所多有”、“遍地皆是”的态势[6]。即使是平时相对远离政治中心的社会底层,也是“人心愤激久矣,每言及中东一役,愚父老莫不怆然泪下[7]。素朴的乡村民族意识,逐渐地在酝酿,在扩散。二是人们对民族命运的自我体认比以往远为深刻。这种体认,是以对世界大势较为深切的把握为基础的。资本帝国主义势力逼在眉睫的威胁,造成了思想界空前的屈辱感。中外政治、经济格局的强烈反差,导致了人们深切的落伍感。这种心理情结同中华民族悠久、光荣的历史传统相撞击,又激发了国人不甘于沉沦的自尊心。这样,普遍的屈辱感,就成为民族意识高涨的心理基础;痛切的落伍感,迫使人们在面临外部挑战时做出民族生存的抉择。民族自尊则导致了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的走向和归宿,将人们的愿望和信念集中在一点——倡扬民族意识,争取民族自存,从而迈出了自我改革的艰难一步。可以这样说,耻辱激成了自尊,危机蕴含着转机。
二、新文化运动的巨澜
民族危机意识催化了以振兴民族为目标的文化更新。如果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出发,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应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新旧转换的分水岭。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认同西学,成为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甲午战争惨败的严酷事实,迫使更多的人不得不去了解“近日列国情事”,从而以广阔的视野,去注视那纷彩异呈的外部世界,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肯定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谭嗣同的经历很具有典型性。他早年是一个沉溺于旧学的官宦子弟,“何尝不随波逐流,弹诋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8]“三十年之后,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9]。谭嗣同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痛巨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10]。“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11]。1895年,他邀集有志变法的同人,率先在家乡浏阳设立学会,讲求新学,又设立了算学格致馆,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严复从此决定“以西学为要图”,“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从此开始了他那系统翻译介绍西方学术名著的文化输入工程。
同时,在一些随笔作品和小说散文中,也时常流露出学习西方的要求,反映了普通民众和下层士大夫的文化追求。例如在黄庆澄的《榴觞醉语》中有一段话:“中国欲自强,必讲西学;欲讲西学,比先立议院,上下通情,而后可祛蒙蔽诸弊”[12]。小说《中东大战演义》中,作者用抗日名将刘永福教训儿子的话,道出了他的文化倾向。他说:“宦海风涛,升沉无定,以后不必再习武事,以求仕进。凡有余力,可讲求西学,以为立身之基”[13]。晚清著名作家李伯元创作《官场现形记》,也是渊源于甲午战争的刺激。他的族弟李锡奇说:“伯元愤于满清政治腐败,戊戌变法未成,甲午惨败之后,国家瓜分之祸迫在眉睫,非大声疾呼,不能促使全国上下觉悟”[14]。《孽海花》一书的作者曾朴,也是受了甲午丧师割地的刺激,“觉悟到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更新的大变革,更看透了故步自封的不足以救国,而研究西洋文化实为匡时治国的要图”[15]。遂于1895年进入总理衙门开办了北京同文馆特班学习法语,而且开始与康、梁等维新人士有所交往,思想深处已发生变化。这些动向,构成了“自是人士渐渐倾向西人学说矣”的思潮主潮。
第二,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初步反思。仁人志士通过探讨中国败于日本的原因,对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在康有为等人看来,中国败于日本,固然有武器陈旧、枢臣主和、战将贪懦、士兵怯弱、调度无方等因素,但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在政治制度的陈旧和腐败。“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16],可谓一语中的。而日本恰恰是通过明治维新,用君主立宪取代了君主专制政体,才“有今日之强而胜我也”。他们还进而指出,君主立宪政体的日本战胜君主专制政体的中国,是历史之必然,因为日本“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矣”[17]。墨守成规,不知变革;上下不通,君主孤立;对内镇压,对外屈服,都是专制主义所酿成的弊端。
在这种腐败丛生的政治体制下,即使搞枝节性、边缘性的改革决难成功。康有为等人站在改革现行政治体制的认识高度,既肯定了风行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具有某种近代化的先驱作用,又对其严重局限性提出了批评。谭嗣同说:“中国数十年来,何尝有洋务哉?抑岂有一士大夫能讲者!能讲洋务,即无今日之事。足下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耳,电线已耳,火车已耳,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耳。”而这些“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于其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18]。康有为也批评洋务派的活动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19],结果,“变其甲而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无其本源,失其辅佐,牵连并败,必至无功”[20]。严复更痛斥洋务派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21]。他一反洋务派所津津乐道的“中体西用”的文化主张,大胆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新见解,从而给中国政治文化思想注入了新的内涵。
以儒学为主干的正统文化是专制政治的理论基石,也是洋务思潮的主要依据。因此,剖析当朝政治,反思洋务运动,必然要引发到对中国正统文化的重新评估上。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以先知者和开拓者的勇气和锐气,批判旧学,弘扬新学,成为向封建文化勇猛挑战的时代先锋。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22]。他认为如果不改弦易张,除旧布新,依然故步自封,死守旧学,其结果将使“中国所谓道德文章、学问经济、至贤名士,一齐化为洋奴而已矣”[23]。两千年来,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道,被尊为万代不易的封建旧学的英灵,在谭的眼里已成为粪土,这无疑是刺向专制文化的一把利剑。
至于接触西学比较早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此时更以他们的中西文化功底,通过初步的文化比较和类比,批判旧学,反思中学,推崇西学。康有为在1898年6月的上皇帝书中,把中国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两个不同时代,他称中国传统社会为“一统之世”,以“静”、“隔”、“散”、“防弊”为统治思想和社会特征,使上下隔绝,人群之间“不相往来”,人民“不识不知”,无为寡欲,终至国弱民贫。而西方当代是“竞长之世”,以“动”、“通”、“聚”、“兴利”为思想导向和社会特征。使上下相通,人群之间团结协作,“民心发扬,争新竞智”,而成人才济济、国家兴旺之局。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不言而喻。与康有为相比,深通西学的严复将中西文化的优劣分析得更加细微和明确。他在著名的政论《论世变之亟》中,列举了中国和西方在伦理、政治、经济、学术和风习等方面的十二项差异,以“重三纲、明平等;亲亲、尚贤;尊主、隆民;夸多识、尊新知;委天数、恃人力”,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不同的价值观。尽管这仍是平面的罗列,而严复又自称“未敢遽分其优拙”,但读者还是可以深深感到他那种强烈的新学优于旧学的文化意识和倾向。
三、救国思潮的昂扬
恩格斯曾经指出:“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了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24]。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意识和文化更新要求,逻辑地导向爱国主义思潮的涌动和昂扬。
19世纪的最后几年,爱国救亡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关心国事、参与政治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组织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个世纪下半期在思想界逐渐形成的“变局”意识和主权观念,经受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迸发为振动人心的救亡呼声。深刻地表现了近代历史主题“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救国营垒中的各个阶级、阶层用类似的语言呼喊出来的。前面提到的孙中山在海外组织的兴中会,从团体名称到章程内容都鲜明地反映了爱国救亡的时代主题,并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随后,康有为等维新志士于1888年4月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大声疾呼亡国在即,“惟有合群以救亡,惟有激耻以振之”。一时间,“国民”、“国地”、“国教”、“国耻”成为流行性的政治概念;“立国自强”成为思想界共同的认识。而几乎就在康有为在京师发表保国会演说的同一个月,地处偏僻的冀鲁交界地区,以乡野民众为主干的义和拳(人称义民会)也发出第一批传单,召示“各省爱国志士”行动起来,用暴力驱逐蹂躏自己故土的征服者[25]。此后诸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捉拿洋教,振兴中国”的宣传,连续出现在拳民运动的揭贴传单里。兴中会、保国会和义民会,各自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从思想到组织上不存在任何联系,他们的救亡思路和政治实践,也有许多互相抵牾,甚至格格不入之处。但是,这几个团体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都相继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聚集起斗争的人群。这足以说明救亡图存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救国呼声并不仅仅只反映在为时人和后人所关注的革命思潮、维新思潮和“灭洋”浪潮里,而是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覆盖面。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的诸如尚力思潮、实业救国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几乎都是这时萌生和出现的,它们从不同的棱面反映了国人救亡图存的种种思路和努力。以张謇为代表的“实业救国”思潮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蔷庵,江苏南通人,出身于一个富农兼商人的家庭。甲午之前,他一直过着科举、说客兼幕僚的生活。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当他实现了一个旧式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标之后,目睹的却是清朝中枢的专制和腐败。一次慈禧太后在大雨滂沱中从颐和园返回宫禁,张謇杂于迎驾群僚之间,匍匐泥泞,状若伏犬,全身沾濡,而轿里的慈禧却对他们不屑一顾。科举制度培养奴性,封建等级摧残人格,三十年寒窗落此结局,使张謇发出了深深的感叹:“读圣贤书,志气何在?”
紧接而来的是甲午战败和瓜分狂潮,“看看中国国势,一天比一天危迫下去,朝局用人政事,也是一天比一天的紊乱黑暗;就想到日本是一个小国,何以反走到中国前面去了?它怎样强的?怎样救贫救弱的?因此就想到要中国不贫不弱,救醒它起来,除掉振兴工商业,决没有第二个办法”[26]。对官场的厌倦,对国事的焦虑,促使他投身于为封建士大夫一向贱视的工商实业,提出了“实业救国”的设想。
张謇以“救醒”中国为目标,解释了经济、军事和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若鹜其花与果之灿烂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与果将何附而何自生”[27]。在他看来,只有具备强大的以近代化工业实业为标志的经济实力,中国的自强即迎刃而解,“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能”,“救贫之法惟实业,致富之法亦惟实业”,这一套论述,构成了当时“实业救国”论的理论基础。
张謇运用自己优越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从1895年起陆续创办或参与投资了包括工、农、牧、垦、交通等在内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形成了大生资产集团。这一事件在近代经济史上表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而在思想文化史上,则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一批封建士大夫的自救意识与价值观念的转型。
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生长的士大夫阶层,一直奉行耕读结合、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念,封闭的、宗法的、耕读结合的精神体系和生活方式所支配的士绅阶层,一向以内圣功夫、外王事业为最高的奋斗目标。内圣是最高的独善和自修,外王是最高的兼善和他修,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内圣外王的最佳注解;圣人风范和君子气度,是儒者理想的自我形象。《大学》所说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内圣外王法则的一套由内到外、由己到人的修炼方法。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在面向社会现实并积极为皇权政治服务的人文精神,士或“君子”则是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因为人文精神是全幅的展现,“君子”也就必须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全才,“一物不知,儒者之痴”,就是很好的说明。而仅具一技一艺之能的专才,特别是以功利为目标的专才,一向为儒家所不为。孔子所强调的“君子不器”,就是让读书人纯粹成为一个读书人,并不是为了训练专才。所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反职业主义”的文化,孔子教育是一种“反职业的经典主义”,缺少一种“理性的专业化”心理,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张謇放弃仕途,投资近代工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向传统价值观念挑战的代表性。他如状元出身的孙家鼐、陆润庠,也在甲午后投资办厂。随后许多具有功名地位的士人纷纷投身于工商业。这反映了一批旧式士大夫在时代刺激下对人生理想的新的选择,也是对儒家救世精神的重新解释。实业救国虽然当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方案,但作为革命思潮、维新思潮的补充,反映的是救国思潮的广泛性和多样性。祖国的危急状态,促使中华民族中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在不同程度上调整着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组织阵容。这标志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开始由旧向新的转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9页。
[2]《闻尘偶记》,《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1期,第2页。
[3]《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13页。
[4]皮名振《皮锡瑞年谱》,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5]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6]《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页。
[7]《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8页。
[8]《谭嗣同全集》,第220页。
[9]《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4期,第124页。
[10]《谭嗣同全集》,第160页。
[11]《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4期,第124页。
[12]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449页。
[13]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221页。
[14]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第37页。
[15]魏绍昌《孽海花资料》,第158页。
[16]《康有为政论集》上,第219页。
[17]《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6页。
[18]《谭嗣同全集》第202页。
[19]《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7页。
[20]《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7页
[21]《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
[22]《谭嗣同全集》,第337页。
[23]《谭嗣同全集》,第22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2页。
[25]吴宣易节译《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第8页。
[26]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355页。
[2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355页。
标签:康有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谭嗣同全集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实业救国论文; 谭嗣同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甲午年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 张謇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思想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