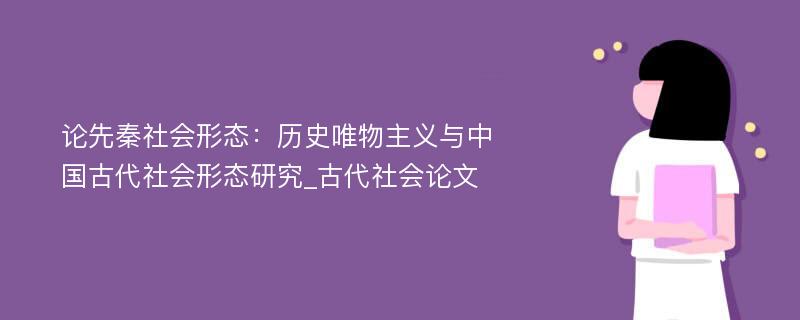
“先秦社会形态”笔谈——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形态论文,唯物史观论文,笔谈论文,先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形态研究,不仅是一个实证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历史学发展方向的理论问题。社会形态理论对于史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意义十分重大,直接关涉到我们怎样认识和撰写一部人类历史。上个世纪初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我国早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便开始自觉地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我国的历史和社会形态进行研究,并逐步建立起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此后,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和争论便一直是我国史学界的一个焦点课题。
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又称“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人类社会时所创立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就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认识,并认为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唯物史观以后,就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对唯物史观进行检验,并进一步发展了唯物史观。恩格斯于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一部以唯物史观观察和阐述古代社会形态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书提示了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历史进程,论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进一步丰富和证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在中国最早传播唯物史观的是李大钊。1919至1920年间,李大钊在《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介绍、阐释、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此后他又于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论》,运用唯物史观对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和历史观作了科学的论述。
在李大钊的倡导下,最先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是郭沫若。此前,他在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就接受了唯物史观。郭沫若从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写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第5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文章,后于1930年3月汇集成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是我国最早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一部学术著作,可以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在这部著作中,郭沫若首次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提出的关于国家和社会形态的理论对我国古代社会形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殷代为我国原始公社制的末期,西周的社会形态是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度相当的奴隶社会,东周以后为封建社会。(后来于1954年再版时又将殷代改划为奴隶社会,并在《奴隶制时代》中将我国奴隶制的下限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从此,揭开了中国古史分期(实即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大论战的序幕。
在郭沫若的带动下,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相继应用唯物史观来系统地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并提出了与郭沫若的古史分期有所不同的见解。1934年7月,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41年,吕振羽、范文澜分别在重庆和延安出版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撰写的《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和《中国通史简编》上册;1943年,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55年重版时改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各领风骚的著作,系统地探讨和阐述了我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并作出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分期,对我国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史学发展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中确立了领导地位,唯物史观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我国史学界深受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普遍接受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社会发展理论,确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虽然当时也有学者对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提出了怀疑,但很快被当时通行的政治化的学术批评压制下去。如雷海宗于50年代提出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奴隶社会阶段的观点。他认为由原始社会末期到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存在着奴隶制,并举例称雅典、罗马的短期奴隶制发展,只能看成是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而北美新大陆的黑奴制也是这个变种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复活。雷海宗还根据他所主张的“工具发展理论”,认为原始社会之后,人类社会依次为部民社会、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而后二者实际上都是封建社会,只是稍微有所不同。[1]这一观点在当时被当做大逆不道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受到了猛烈批判。此后,此类怀疑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学术观点便销声匿迹,大家便都在普遍肯定中国古代出现过奴隶社会的前提下,汲汲于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和讨论——主要是研究和讨论中国古代何时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学术空气趋于活跃,有关我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探讨重新活跃起来。与此同时,西方许多不同流派的学术思想不断地传入我国,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种影响亦波及到了中国史学界,我国史学界长期坚持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断受到冲击。广大史学工作者对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有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古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反思、质疑、研究和论争。经过多年的反思和探讨,虽然史学界对于我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依然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普遍认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学说并非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奴隶社会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我国古代也不曾存在过奴隶社会这一社会形态。由于过去我国史学界普遍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社会发展理论当做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于是有学者便由否认我国存在过奴隶社会进而怀疑甚至否认唯物史观的真理性,怀疑、否认唯物史观对于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进行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还要不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如何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成为我国古史研究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正确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澄清我们在以往的社会形态研究中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和误释。
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是很严重的偏差,将马列主义一些经典著作中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论述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甚至将阶级斗争当做唯物史观的核心,将学术研究政治化,在史学研究中出现了公式化、教条化的倾向。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这些公式化、教条化倾向,是对唯物史观不正确的运用造成的,而不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本身存在的缺陷。我们要在思想上区分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实践、社会结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原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比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人类社会是由无等级、无分层的平等社会向有阶级社会发展,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血缘组织的瓦解、地缘组织的出现、人群利益的重新分配导致国家的产生等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迄今仍然有着其他理论无法替代的价值,对于我们正确进行社会形态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在今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中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当然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更应该正本清源,澄清以往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和误释,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100多年前对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论述全当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公理”,亦即不能把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应该自觉地解放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应该认识到我国史学界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并非唯物史观,并不符合人类历史的实际。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在一些经典著作中论述过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序列,但那只是针对西欧的历史而言,而并非对整个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概括。例如中世纪时,阿拉伯、斯拉夫等许多民族,并末经过奴隶制社会。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当年郭沫若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适用性出发,论证中国与西欧同样经历了由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将“奴隶社会”引入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对此,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异议。不仅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以为然,而且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认为中国古代不曾有过奴隶社会。如陈独秀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于《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七号上发表《实庵字说》,通过论证商周时期的“臣、民、氓、奴、婢、隶、仆、童、妾”只是服贱役的家内奴隶,而并非当时主要部门的生产劳动者,从而否定中国古代曾经经历过奴隶社会。陈氏还进一步认为,与希腊、罗马由奴隶制而入封建制不同,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原始公社的废墟上直接建立起来的。[2]当时陈氏在共产党内已被作为托派而受到批判,因而他否认中国存在过“奴隶社会”的观点也被当做“托派”观点加以批判。现在看来,陈氏的见解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无论是作为商代主要劳动生产者的众人,还是作为西周春秋主要劳动者的庶人,都不是什么奴隶;至于战国秦汉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为国家提供租赋徭役的自耕小农,这也是越来越清楚的史实。”[3]我们不应该因为陈氏在政治上属于“托派”,而否定其符合历史实际的学术观点。
至于我们今后究竟应该怎样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加以注意,这就是我们应该正确理解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探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不可否认,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有共性,但各个民族又有其特殊性。这是任何从宏观上研究探讨我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学者所必须考虑到的。既要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又要在这一大背景中看到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特殊性。我国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中的偏差之一,就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强调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共性,而忽视了我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特殊性。如郭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说:“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4](P6)显然郭老过分强调了人类发展的共性,而忽视了中国社会形态的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性。
近年来,在关于我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根据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放弃了以前被奉为圭臬的五种社会形态旧说,另辟蹊径,对我国古代社会形态作出了新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如晁福林先生以秦的统一为界将我国原始社会野蛮时代以后的古代社会(夏——清)划分为“氏族时代”和“编户齐民时代”这样两个历史阶段。又按照社会性质,将夏商划为“氏族封建制社会”,将周代划为“宗法封建制社会”,将秦汉以降划为地主封建制社会。[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力主“战国封建说”的田昌五先生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之外构筑了一套新的中国古代史体系,他把五帝和夏商周(即以前所谓的奴隶社会)称为“族邦时代”,战国直至清朝灭亡(大致相当于以前所谓的封建社会)为“封建帝制时代”。[6]严文明先生则提出了“龙山时代——古国,夏商周——王国,从秦到清——帝国”的国家形态三段说。[7]而在编的《中国大通史》(商传、王和、赵世瑜、曹大为等学者主持编写)也不再沿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把夏商周三代称作“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把秦汉至清中期称作“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8]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兹不赘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传统的观点一直恪守从氏族、部落到国家的理论模式,都把夏朝看做中国国家的起点和文明的开端。可是近年的考古发现的新资料表明,在夏王朝诞生之前的1000年间已经出现了介于氏族部落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应该怎样认识和界定这些介于氏族部落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呢?谢维扬先生即根据塞维斯等人建构的“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模式,对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进程进行了新的诠释。[9]
毋庸置疑,上述诸位学者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及与之相关的文明和国家的起源问题的探讨,都有着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虽然目前大家对这些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远未达成共识,但是我们相信,在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下,实事求是地正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充分吸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中积极的可取成果,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们有能力建立起一套既能较客观地反映我国历史实际,又能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理论框架。
标签:古代社会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封建社会论文; 郭沫若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