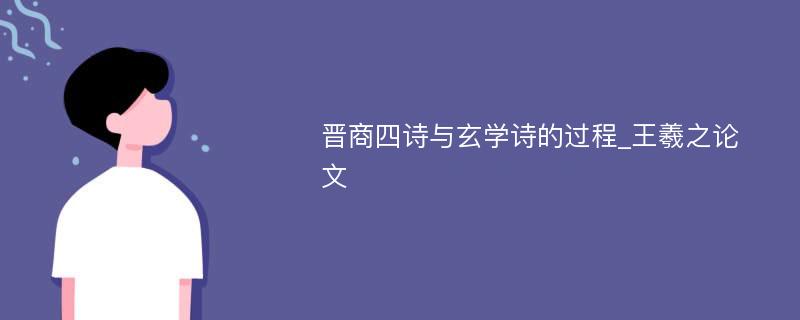
晋人上巳诗文与玄言诗的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文论文,进程论文,晋人上巳论文,玄言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会发现其中有不少篇章涉及节日民俗,它们不仅常常反映了社会风俗习惯,也常常折射出当时的文学艺术特征,而这往往被忽略,从而造成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本文试图以晋人上巳诗文为中心,考察晋代文学尤其是玄言诗的一些特征及其进程。
上巳起源与活动:趋向欢乐与文雅
在晋代,上巳是一个隆重的节日(注:《宋书·礼志》:三月上巳,“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本文仍统一使用上巳的称呼。)。当时,既没有正月十五的火树银花,也没有八月中秋的月下团圆,端午的龙舟竞渡也还没有多么大的声势。晋人把无限的欢欣和热情以及审美的眼光和玄远的遐思投向了三月的上巳。
上巳节日自东汉开始流行。《后汉书·礼仪志》曰: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絜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絜之矣。
张衡《南都赋》曰:
于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濒。
蔡邕《祓禊文》曰:
洋洋暮春,厥月除巳。尊卑烟骛,惟女与士。自求百福,在洛之涘。
东汉时上巳之盛况可以想见。至于上巳的起源,却众说不一,不妨略举汉人之说。韩婴《韩诗》曰:
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
《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
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
蔡邕《月令章句》曰:
《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滨,盖出于此。
根据上引文献,我们可以知道,水边祓禊,除灾求福,这种风俗至迟在春秋时期的郑国已经形成。起初,祓禊并不限于三月,更不拘于上巳,故有《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之说。东汉末刘桢《鲁都赋》曰:“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除,国子水嬉。”这是秋禊在汉代仍有遗存的实例。但春禊终究盛行于世,“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絜買之矣”,这应是最重要的原因。人们在冬季多居于室内,生活不免单调乏味,彼时又严寒不便沐浴,当春日和暖,正是走向户外并在流水中“去宿垢疢”的好时辰。“临川挹盥,濯故洁新”(晋闾丘冲《三月三日应诏诗》),人们在清洁身躯的同时,当然也希望弃旧图新,远离不祥,于是有了祓禊的仪式。除灾求福的仪式,渐渐演变为大众欢腾的聚会,起初的敬畏心理日趋淡薄,三月上巳也渐成春游佳日,这早在《诗经·郑风·溱洧》篇中就得到了反映,那士女相谑的欢乐景象和气氛如在目前。到了汉代,上巳祓禊大抵已徒具形式,节日气氛更为浓厚,从至今可见有关的少数几篇文学作品中尚可略见一斑。
对于上巳,晋代人为我们留下了相当多的文学作品,使我们有可能得到比较全面的了解。在这一天,人们出行水边,宴饮游乐,曲水流觞,弦歌吟咏,射猎垂钓,等等。
曲水流觞是上巳的代表性重要活动,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这一活动在汉代还没有广泛流行。沈约《宋书·礼志》曰:“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燕群臣。”在时间上来说这应是比较早的活动。而在西晋初,这种活动已很普遍,但是人们并不太清楚其起源。梁吴均《续齐谐记》曰:
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曰:“三日曲水,其义何指?”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之义起于此。”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好事。”尚书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祠。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
这个故事反映出对民俗解释的不同观点。挚虞叙述之事荒诞而朴鄙,标志着一部分士人对民间习俗的认同。束皙之说也无据可凭,却得到晋武帝的赞同,想来一方面满足了晋武帝对君主权力神秘化的心理需求,一方面也符合统治阶层将民间习俗文雅化合理化而纳入轨范的历史常规。而对所谓周公“羽觞随波”场景的想象,或许更能激发文士们文酒风流的情愫。于是,对上巳民俗活动的文雅化合理化就含蕴了激发高雅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因素。
洛水祓禊:士人的审美享受
在西晋,皇都洛阳显然是上巳节日活动的中心。这里有皇帝召集的华林园宴会,也有公卿庶民杂糅的洛水祓禊。
华林园在洛阳城内东北隅,本名芳林园,魏帝曹芳改为华林园。晋平定吴国后,上巳日曾宴于华林园,群臣赋诗,今存程咸、王济《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荀勗有《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闾丘冲有《三月三日应诏诗》,都作于华林园,可知上巳日于华林园举行宴会是常事,而赋诗是当日一项重要活动。当然,在这种特定环境中,诗作的基本内容不外乎歌功颂德,没有多少文学意味。不过,皇帝提倡臣下作诗,应当对诗歌创作的开展有积极作用。举例来说,《文选》载应贞《华林园集诗》,李善注云:“干宝《晋纪》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孙盛《晋阳秋》曰:‘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从应贞诗受到称赞而言,这一次集会赋诗带有评比性质,那么,历次华林园集会包括上巳集会也有可能间或举行类似的赋诗评比活动,这无疑具有促进作用。应该指出,尽管上巳宫苑宴会间赋诗所产生的作品本身不足以受到过多的关注,但这一活动对节日活动已形成的游乐性质却具有文化提高意义,上行下效,这也会在士人群中产生影响。
洛水祓禊的盛况远远超出宫廷的华林园集会,这从现存成公绥《洛禊赋》、张协《洛禊赋》、褚爽《禊赋》、夏侯湛《禊赋》、阮瞻《上巳会赋》诸赋的残片中得到反映。在有关倾城而出、宴饮游乐的描写叙述之外,我们或许更应注意那些浸染士人雅致的事情。张协赋曰:
于是缙绅先生,啸俦命友,携朋接党,冠童八九。主希孔墨,宾慕颜柳。临涯咏吟,濯足挥手。
类似的情景在东汉杜笃《祓禊赋》中曾经出现:
若乃隐逸未用,鸿生俊儒,冠高冕,曳长裾,坐沙渚,谈诗书,咏伊吕,歌唐虞。
将这两段加以对比,见微知著,可以察觉出时代风气的不同,文人士大夫精神面貌的差异。东汉人以儒家经学为本,关心时势、学术,颜之推曰:“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入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颜氏家训·勉学》)此言与杜笃赋中所述正可相印证,故“隐逸未用,鸿生俊儒”皆怀用世之心。晋人则思想自由通达,多几分潇洒超脱。《世说新语·言语》记载洛下名士祓禊事: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注: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有“王济诸人尝至洛水解禊事”云云。则《世说新语》所记“戏”字当为“禊”字。)
洛下名士将上巳出游视为雅集乐事,进行清谈,显示其高远情趣、思辨才能、谈说技巧,即使尚论古史古人,也洋溢着他们自身的情趣与智慧。因此,对谈者听者来说,都是惬意的审美享受。以集会的品格而言,著名的兰亭雅集应与此有潜在的渊源关系。从清谈的雅致到玄言诗的玄远,其间的过渡并不存在困难。这也表示出,士人在参加民俗活动时,既有随俗的一面,也有追求脱俗的一面。
如果说士人群体通过上巳的清谈吟咏等获得文化的审美享受,水边自然景致也常融进他们的雅兴之中,从而获得对自然界的审美享受。这在现存西晋人赋作中有所表现,如褚爽赋曰:
川回澜以澄映,岭插崿以霏烟。轻霞舒于翠崖,白云映乎青天。
阮瞻赋曰:
临清川而嘉燕,聊假日以游娱。荫朝云而为盖,托茂树以为庐。好修林之蓊郁,乐草莽之扶疏。列四筵而设席,祈吉祥于斯途。酌羽觞而交酬,献遐寿之无疆。同欢情而悦豫,欣斯乐之恺慷。发中怀而弦歌,托情志于宫商。
他们已超脱世俗喧腾而注意到山水自然之美,爱好修林草莽之清幽,列席交酬,弦歌以寄托情志。此情志固然不能断定是由山水而发,但其间存在的联系却是难以否认的。
古代山水文学自东晋始盛,人们对山水有了自觉的审美意识,而这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文心雕龙·明诗》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钱钟书先生引东汉末荀爽《贻李膺书》与仲长统《乐志论》,认为:“山水方滋,当在汉季。荀以‘悦山乐水’,缘‘不容于时’;统以‘背山临流’,换‘不受时责’。又可窥山水之好,初不尽出于逸兴野趣,远致闲情,而为不得已之慰藉。达官失意,穷士失职,乃倡幽寻胜赏,聊用乱思遗老,遂开风气耳。”(注:《管锥编》第3册,第103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西晋左思不得志于时,作《招隐诗》二首,歌颂于山水美景中悠闲自得的隐逸生活,高咏“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已不尽属“不得已之慰藉”,而明确表达出对山水的审美要求,这正是时代风尚的具体表现,上引赋作也是例证。
在西晋人上巳诗中,值得注意的有阮修《上巳会诗》:
三春之季,岁惟嘉时。灵雨既零,风以散之。英华扇耀,翔鸟群嬉。澄澄绿水,澹澹其波。修岸逶迤,长川相对。聊且逍遥,其乐如何。坐此修筵,临波素流。嘉肴既设,举爵献酬。弹筝弄琴,新声上浮。水有七德,知者所娱。清濑瀺灂,菱葭芬敷。沉此芳钩,引彼潜鱼。委饵芳美,君子戒诸。
诗中有对水边景致的审美享受,有“知者乐水”的道德体会,有对人生处世的理性领悟。这是山水与玄言的初步结合,是喜好哲学思考的魏晋人尚老庄倡自然说在文学方面的反映。在山水这天地自然的一部分中优游,寻求精神上的自然,获得对自然之道的领悟,这应是当时一些士人的追求。将此诗放到玄言诗发展的进程中作衡量,它或许可以说是比较早的重要作品,唯其早,也就有其不自觉性,即尚未像后来者那样将山水作为体道的对象,而它偏重于逍遥娱情,道则偶然得之。
总之,上巳节日民俗为西晋士人提供了聚会高谈吟咏的好时机,洛水祓禊尤其重要,于是他们在欢欣的气氛中进行文化交流,领略自然风光之美,触发思辨体悟,这就为山水与玄言相结合而进入文学创作开通了一条渠道——人们迄今似未足够注意的渠道。而对于东晋士人的创作来说,这还只是开端。
兰亭雅集:自山水体道的范例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玄言文学盛行于东晋,但东晋初期时局未稳,人心不定,又加以对西晋清谈废事的痛心反思,故玄风不畅,直到中期政局平稳,偏安已成,玄风方炽。同时,南方山水之秀丽也使流连山水成为风气。以玄言诗著称的孙绰,“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乃作《遂初赋》以致其意。”(《晋书·孙绰传》)士人自山水中体悟玄理,“固以玄对山水”(孙绰《太尉庾亮碑》),山水与玄理的自觉结合促成了玄言文学的兴盛。自魏正始以来兴起的自然说,使人们摆脱了汉代“天人感应”神学观的束缚,逐步深入地意识到自然之理独立存在。当东晋士人面对山水时,这山水是自然中的独立存在物,也是自然之理的体现者,他们以玄远之心静观山水,激发出自觉的审美意识,最终以体悟道理获得精神愉悦。
在“固以玄对山水”的文学创作中,不能不提及著名的兰亭雅集,由于发生在上巳这特定场合,更值得我们细心体味。这一次集会,留下了三十七首诗和两篇序。作为主人的会稽内史王羲之作《临河叙》: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注:此文原见《世说新语·企羡》刘孝标注引,与世传王羲之《兰亭集序》文字不同。学术界对《兰亭集序》真伪有争论,故本文不引用,尽管后人往往是首先通过《兰亭集序》而认识兰亭集会。)
文中简洁地描写了山水风光,道出“修禊事”形式下的实际内容是“娱目骋怀”与“畅叙幽情”。孙绰序曰: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耶?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仰瞻羲唐,邈已远矣;近咏台尚,顾深增怀。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为壮矣。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物同荣,资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泱然兀矣,焉复觉鹏鷃之二物哉!
临水而悟理,因时序而思古人,这是此地此日应有的感发。水停则清,处林野则心志旷远,故“借山水以化其郁结”,安定情感,使一心虚静。由此而静观山水之美,体悟万物齐一和同之理。理既通而心畅,于是人与自然相融合,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文中反映了当时士人自山水体道、以理化情的风尚,对心“畅”的追求。这在数十篇兰亭诗中有着更清晰的反映。
兰亭诗表现出对时间的敏感与超脱。上巳日的来临,标志着时间循环的又一新开端,从而引起对时间流逝的感想,“代谢鳞次,忽焉以周”(王羲之诗),“时来谁不怀”(曹茂之诗)。临水的诗人们不会不想起孔夫子“逝者如斯夫”的名言,然而他们无一人提及,只因他们没有孔子那般积极用世精神,没有那般紧迫感。在他们看来,“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王羲之诗),宇宙永远在运行,自然无为,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人只需顺从自然,心安理得。因此,当时序更替,辞旧迎新之际,他们不恋旧,不感伤,不慷慨激昂,以基于平静心的喜悦迎新,进入新的时间与空间,“适我无非新”(王羲之诗)。《庄子·秋水》郭象注曰:“明终始之日新也,则知故之不可执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惊,死生之化若一。”郭象语正可移用于此处。他们从时间流逝这一永恒现象得出的是理性观念,即故与新只是相对而言,新不停出现,而转瞬又已为故,诚如王羲之所表达:“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也正因为以理性观念看待新化为故,以达观处之,不致动情伤感,“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谢安诗)。这却也适应了民俗的节日欢乐气氛,而从根本上说是受到民俗的潜在规范,这一天不是哀伤的日子。
由于时间的相对性观念,视千年如今日,兰亭诗缩短了与古人的时间距离。诗人们想到上巳的起源,倾向于《论语·先进》“浴乎沂”的萧散情调,纷纷歌咏:“咏彼舞雩,异世同流。”(王羲之诗)“宣尼遨沂津,萧然心神王。”(桓伟诗)“古人咏舞雩,今也同斯叹。”(袁峤之诗)孔子“吾与点也”的态度,包含丰富的内蕴,而其中对人与自然和谐的向往,显然得到兰亭诗人的认同,这同时也流露出他们对隐逸生活的追求。《晋书·王羲之传》曰:“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晋书·谢安传》也有类似记载:“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兰亭雅集具有这样的背景,兰亭诗中自然就常常怀想古之达人高士,愿与同游:“望岩怀逸许,临流想奇庄。”(孙嗣诗)“遐想逸民轨,遗音良可玩。”(袁峤之诗)“庄浪濠津,巢步颍滨。冥心真寄,千载同归。”(王凝之诗)“愿与达人游,解结遨濠梁。”(曹华诗)在他们看来,身处即是箕山、颍水、濠上,可与许由、巢父、庄子等人携手同游,高隐世外。晋简文帝入华林园曾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见《世说新语·言语》)身处宫廷园林,尚且有濠濮间想,更何况身临佳山水间呢!《庄子·秋水》记庄子于濠梁观鱼,知鱼之乐,起初应是静观,偏于理性,体察鱼之情态,渐渐沉浸于审美观照之中,物我两忘。唐成玄英疏曰:“夫物性不同,水陆殊致,而达其理者体其情,是以濠上彷徨,知鱼之适乐。”成玄英对此中达理与体情的关系说得是比较恰当的。濠梁观鱼的从容自得,受到兰亭诗人的歆羡,而庄子对自然物的观照方式,又何尝不深深影响他们呢!由此可以论及兰亭诗人对山水的观照。
兰亭诗人观照山水,首先想到的是从中悟道,心境玄远,终而顺乎自然,物我两忘,与山水相融合。王羲之诗曰: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诗人所见无非是理,然而这理强寻不得,需待其“自陈”。这就要“寄畅”于山水自然,与之相处相融,同时保持一种互不役使的关系。《庄子·知北游》曰:“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兰亭诗人当然深明庄子意旨,因此会产生王羲之“适我无非新”这般感受。诗人静观中“理自陈”,这理是与山水自然共存而不可单独存在的理。宗白华先生说得好:“‘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他又说:“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注:见《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载《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可以说,“虚”与“玄”是东晋人观照山水时的基本特性。说到此,我们不免想起西晋陆机所说的“伫中区以玄览”(《文赋》),“玄览”出自《老子》,意谓深入静观,本意应着重于知理,而陆机意在观察万物情状,不在体悟事理,因此眼中纯是实境。兰亭诗人则心境幽远,超入玄境。庾友诗曰:
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
这体现出观照山水时心境空灵高远,以此与无限的宇宙融会,极其自然地体悟道理。这与王羲之所说“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同样概括性地道出他们观照山水的特点。更值得注意的是“理感则一”之语(注:关于“理感”,可参看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第382~3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它透露了兰亭诗人体悟道理的方式,即以伴随形象的感性去体悟生动世界所包蕴的道理。因此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而山水也决不只是充塞义理的理窟,它既有义理的内在美,也有声色的外在美。兰亭诗人对山水的审美是对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观照。
基于兰亭诗人观照山水的玄远,他们的笔下对山水景色常作空灵的鉴赏,很少作细致的描写,有些诗中描写山水景色的诗句比较多,也仍然不偏离其共同特征。试看孙绰诗: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诗前四句描写景色,“莺语”、“游鳞”二句细致生动,但到此为止,以下转入对集会中赋诗、谈玄、听乐等活动的叙述。从全篇结构来看,景色描写起铺垫作用,引出后半的集会乐趣。然而景色描写又不仅仅起铺垫作用,诗人身处山水之中,应有对山水“自来亲人”的由衷欣喜,但他并不以山水美为最终追求,我们从中似能感觉诗人体悟宇宙生机的玄远意趣。在兰亭诗之外,同时的庾阐有《三月三日临曲水诗》、《三月三日诗》,景色描写更胜于孙绰此诗,而同样能从中感受到其深处蕴含的玄远意趣。
兰亭诗人“固以玄对山水”,将山水视为以理化情而获得逍遥的寄托对象。正如孙绰序中所说“借山水以化其郁结”,兰亭诗中有很多类似的表达:“散怀一丘”,“寄畅在所因”(王羲之诗),“寄散山林间”(曹茂之诗),“愠情亦暂畅”(桓伟诗),“豁尔累心散”(袁峤之诗),“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王玄之诗),“豁尔畅心神”(王肃之诗),“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徽之诗),“散豁情志畅”(王蕴之诗),“寄畅须臾欢”(虞说诗)。通过“散怀”、“寄畅”、“寄散”等词语,表现出他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矛盾的回避,对人间哀乐之情的消释,将身心寄托于山水以达理求畅而物我两忘的欣然。
在解读兰亭诗之后,我们可以说这是玄言诗的一次有积极意义的发展,因为是自山水体道,就与自然美紧密联系,具有形象性,不像直接阐发玄理那样常常过于抽象生涩。同时,这也是后来山水诗发展的一次准备,其中一些诗有对山水自然景色的描写,其高远清新的特色无疑为后人所学习。兰亭诗可以作为东晋中期玄言诗的代表,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其一定的作用。由此不免想到历来几乎一致的对玄言诗“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的评价,是不是过于简单化呢?
兰亭诗产生于节日聚会上,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节日民俗的影响。那弃旧迎新的喜悦,那曲水流觞的仪式,从外表上看都与民众没有什么区别,但其本质上与民众有雅俗之分,特别表现为对山水美的鉴赏和哲理性玄思,而这又是以上巳节日风俗为广阔背景的。如果这次聚会不是在这特定的场合举行,那么诗人们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必然会有所变化,也或许会因节日民俗背景潜在影响的缺失而稍减生趣,这又是兰亭诗于玄言诗中的独特性之所在。
南北朝时期,朝野官民对上巳节日的热情似乎不减晋人,但如果从文学角度考察节日创作,却不见有什么可以多说几句的作品,尽管《文选》收入了颜延之的《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与《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而且王融之作“文藻富丽,当世称之”(《南齐书·王融传》),但从内容而言那毕竟只是单调的歌功颂德夸饰之作。而晋人的上巳作品传扬一代风流,兰亭盛会更是空前绝后。唐代白居易有诗曰“共道升平乐,元和胜永和”(《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殊不知“共道升平乐”何及兰亭诗人“寓目理自陈”的意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