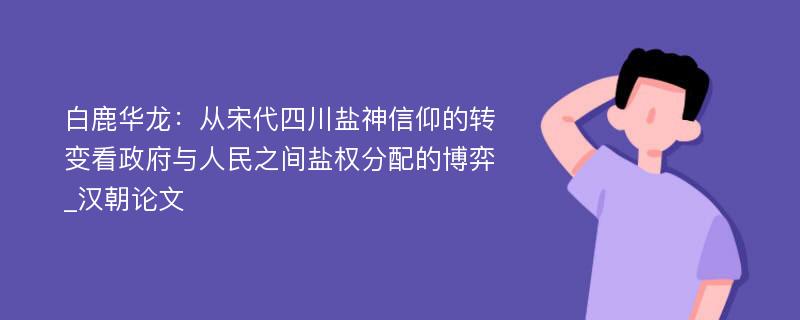
白鹿化龙:从宋代四川盐神信仰变化看官民盐权分配的博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鹿论文,看官论文,宋代论文,分配论文,四川盐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4)05-0164-07 通过地方信仰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向为学界所重视,相继产生了诸如杜赞奇“权力文化网络”、武雅士“民间象征分析”、杨庆堃“宗教功能”、王斯福“宗教隐喻”等研究范式①。这些研究主要采用“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通过地方信仰的功能来分析其对民间社会的影响。目前在研究地方资源社会中,通过引入民间信仰来解析资源背后所折射的社会互动关系以及相关秩序的构建与维持,也已成为学界的重要视角选择。宋代四川作为全国最重要的井盐产区,所谓“鬻井为盐,曰:‘益、梓、夔、利’,凡四路”[1]4472,因盐利税入丰厚,“川峡四路盐课,县官之所仰给”[2]3827。为控制财利之源,官方在信仰塑造中塑造出诸多官方盐神作为食盐发现者或权威符号,意图在意识形态中强化食盐垄断的合理性。而食盐作为“食用之品,无论贫富在所必需,人人皆当食盐”[3]卷一,也成为民间利益诉求的重要内容,由此民间自造一批平民盐神用以证明平民同样拥有盐权的合理性。围绕盐神的塑造,四川官民在意识形态展开了博弈,对当地盐权分配秩序的均衡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以往的研究对此较为忽视,故为本文试予探讨②。 一 四川官方盐权控制下的信仰垄断 宋代四川施行食盐官营政策,“川峡承旧制,官自鬻盐”,官府掌握当地盐权分配权,民间仅在官府允许下有条件(需交纳盐课)地分得少量盐权。在四川官方盐权的垄断下,形成“大为监,小为井,监则官掌,井则土民干鬻,如其数输课”[1]4472的盐权分配格局。这种盐权分配秩序完全是官府主导的产物,官方在利用权力加强垄断的外在表现下,另需在意识形态通过盐神的塑造完成盐权垄断的舆论合理性建构。 (一)帝王将相为原型的盐神塑造 杜赞奇认为,中国许多宗教信仰的源泉主要源于天人合一的官僚体系,“神位如同官位,只是由那些已故去的文臣武将充任而已”[4]124。宋代四川官方在塑造盐神时,即通过代表自身利益化身的前朝或本朝帝王将相为原型,将其创造成当地食盐的发现者③。 宋代官方盐神塑造的首选往往是政府控制的产盐重区。官方通过对其盐神的塑造,造成自身占有的事实合理化,民间再进行盐权争夺就丧失了理论依据,而官方则由此造成在当地盐权分配中占有绝对主导权,并实现对食盐的垄断。 如云安军(治今重庆云阳县),宋代以盛产“伞子盐”而闻名,西汉大将樊哙被塑为当地盐神。据传,汉高祖刘邦由将军樊哙陪同,从东乡(今四川宣汉县东北)入朐忍县(今重庆云阳县西南)募兵招贤,哙在云安射猎,见一白兔,跟踪发现卤水,高祖即令当地隐士扶嘉开掘汲卤煮盐[5]309。樊哙借由云安食盐发现始祖的身份而被祀奉;隐士扶嘉则因开井采盐,后官至廷尉,也被塑为盐神。此外,扶氏还预言了当地盐脉,“高祖以嘉志在扶翼,赐姓扶氏,为廷尉,食邑朐□县,嘉临终有言曰:‘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6]5281,因扶氏“既神悟前知,能晓地理,脉水泉”,死后“盐井溢焉,故盐监人相传嘉为井神”[7]卷二十四。徽宗崇宁三年(1104),朝廷为扶氏神庙赐额“丰利”,政和六年(1116)再封为“昭利侯”[8]礼20之146,后又加封为“昭利广济王”[9]246。而樊、扶二人的共主汉高祖,也因“开井利民”,同升为盐神[9]64。 忠州(治今重庆忠县)盐井,在“监、凃二溪,一郡所仰”,汉代荆州刺史杨震被塑为盐神。杨震,字伯起,人称“关西夫子”,“神尝刺史荆州,溯江至此,憩于南城寺,谓人曰:‘江北二三里间安得有宝气耶?’……至凃山,见白鹿饮泉,曰:‘宝气在此矣。’土人从所指处凿磐石,而得盐泉”[10]卷十九。杨氏因发现盐泉而被祀为盐神。 绍庆府彭水县(今重庆彭水县)伏牛山“左右有盐井”,官府在“盐泉有左、右监官收其课”[11]1055。盐神为东汉大将马援,“昔马援讨平武陵蛮,驻师于伏牛山下,山之左右有盐井四区,莫知所创始,故老相传,自唐宋以来设盐课司,以征井之课税”,后“吏以故事请祀于井”[12]528。因马援“征五溪蛮,常驻师于此”,被祀为当地盐神[12]42。 由此可见,官方对蜀中盐神的塑造是通过以帝王将相为原型的事迹附会来实现。虽然这些神祇与产盐区的关系是否成立尚待商榷,但他们无一不是作为官方代表而出现的,并以此体现出官府对当地盐权支配的权威性。 (二)帝国象征为符号的盐神塑造 在宋代四川盐区,官方为规避赤裸裸的利益表白,还采取了另一类策略化的方法,即将帝国象征的符号塑为盐神,以隐喻食盐占有的合理性,这主要通过龙和道教首领人物来表现。 “龙”在宋代是帝国的象征,它处于一个由国家承认的权威体系当中,代表着帝国利益的在场。盐卤与水有关,而水在传说中又归龙管,如此官方便顺利地将盐神与龙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体现自身利益的隐喻。官方通过营造“龙”在四川盐区的出现,使得“自然的卤水经历了文化化的过程,这表明帝国的进入对当地来说意味着一套隐喻帝国等级秩序的象征符号的进入”[13]252。官方通过将龙与自身的权力等同起来,以此完成对当地盐权垄断的“合法化”程序。 如云安盐场除祀扶嘉等官员为盐神,又以龙的显现来加强官方垄断。据称:“汉扶嘉生一女,一日游于溪畔,恍惚有娠,年余产一物,无手足耳目,嘉怒,劈为九段,投之溪中,须臾化为九龙。”[9]246在这里,扶嘉因九龙的启示寻找到云安盐水的位置,其女“依其嘱掘井至九口”[5]309,可以说九龙正是云安盐场九井的隐喻。因此,九龙也一并得到祭祀,宋代“又锡九龙以王号,今为九井之神”[9]246。 大宁监(治今重庆巫溪县)是宋代川东最著名的产盐区,“大宁之井咸泉出于山窦间,有如垂瀑”[14]300,成为官方符号介入的重点区域。五代时,大宁便被渲染为“盐井水中往往有龙,或白或黄,鳞鬛光明”[15]168,宋代仍然加以崇祀。太宗淳化间在盐泉出口嵌以铁龙头,龙口下有池,曰“龙池”,旁塑“龙君庙”,庙内奉祀三位龙神[16]204。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三龙神一并封王,分别称“普济”王、“善利”王、“广惠”王,号“涌盐源盐井三神祠”;徽宗政和五年(1115),又御赐庙额“宝源”[8]礼20之126。 达州(治今四川达州市)因盐被誉为“在诸郡为最优”[11]1041,其产盐重区通明县(今四川万源县东南)宣汉井场祀奉“盐井龙王”,官方在此建“宣汉盐井龙王祠”,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赐庙额“惠济”,孝宗乾道二年(1166)加封为“显应侯”[8]礼20之81。 长宁军(治今四川珙县东)为川西最著名的盐产地,境有淯井,“其井不凿而自成”,成为官方掌控的著名大井。官方以淯井盐泉有雌雄二水,虚构有雌雄二龙护佑,于监中奉祀“雌雄龙君”为盐神,“取雌雄之义”[6]5021,5025。 宋代官方盐神的塑造,除“龙”符号外,道教的象征亦与之同。如索安士(A.K.Seidel)所言:“自汉末道教产生伊始,帝国权威的神化与象征便是其核心,鬼神与世俗官府平行,实则统一在同一个结构中。”[17]48帝国凭借道教为喉舌获得“君权神授”的舆论,反过来道教获得官方的授权肯定,道教首领人物受到帝国敕封,本身就隐含了帝国权力的渗透。受到敕封的道教人物(如张道陵被封为“天师”等),同样代表了帝国的利益,他们的活动同样具有官方权力在场的暗示。官方将敕封的道教首领人物塑为盐神,更隐喻地体现官方对地方资源的垄断。因道教在民间的信仰基础更广,更能为官方起到政策宣传和民心教化(宣传并承认食盐官有)的作用。 如隆州(治今四川仁寿县)境有陵井,“纵广三十丈,深八十丈,益部产盐甚多,此井最大”[6]4473。陵井的开凿相传与道教始祖张道陵有关。“汉时有山神,号‘十二玉女’,为道人张道陵指陵上开盐井,因此陵上有井,名陵井”,因张道陵“开凿盐井,人得其利,故为立祠”,被官方祀为盐神。为强调道教的神异色彩,以突出帝国的权威象征,张氏开井被渲染为:“天师以后汉建武十年生于吴之天目山,天师平西蜀,妖鬼不复为人害。永寿中,老君下降,涌出玉局为天师重演正一明威之旨,过阳山见白气属天,指其下有盐泉。”陵井开凿后,朝廷专置陵井监管理。神宗时,郡守文同“奏易州名以避真人(道陵)之讳”,又改为仙井监,无不体现官方之色彩[6]4487。 二 四川民间食盐诉求下的信仰自救 宋代在官府食盐垄断下,四川民间诉求很难得到解决,民众除在行为层面上(如偷开私井、贩卖私盐等)与官府展开盐权争夺外,同样通过塑造平民盐神与官方展开意识形态的博弈。王斯福认为:“地方性崇拜的庙宇和节庆就是一种自我组织以及庇护的混合体……感谢地方性保护神将‘灵验’赐予地方,由此而保护了地方以及他们自己的‘福气’。”[18]233宋代四川民间塑造的盐神与官方的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不同,神祇生前并未出将入相,只因代表了民众利益而受到祠祀。 宋代四川盐井的开采多由刑徒充任,他们做为民间人物,是食盐的直接生产者,被塑为盐神可更直白表达民间获取盐权的渴望。如隆州陵井,“以大牛皮囊盛水引出之,役作甚苦,以刑徒充役”[6]4473。陵井被官方定为张道陵所开,“古老传云‘十二玉女’尝与张道陵指地开井,遂奉以为神”[19]3206。民间却因“玉女”帮助天师开井奉其为盐神,在陵井旁建“玉女庙”[6]4481。因宋代四川开凿盐井的刑徒中,女刑占有相当比重,如潼川府盐亭县有女徒山,“故老相传昔有女徒千人于通泉县康督井(盐井)配役,遇贼于此”[10]卷六十六,可知隆州民间所祀的“十二玉女”实际正是女刑的化身。 邛州蒲江县(今四川蒲江县)盐井,乃祥符中县民王鸾所开,“利入至厚”[11]995。为保障民间盐权的拥有,当地同样以盐工为原型塑造出三位女性盐神,称“三夫人祠”[8]礼20之59。 富顺监(治今四川富顺县)“以其井出盐最多,人获厚利,故云富世”,因盐井“皆妇人推车汲水”,民间亦崇祀“玉女”盐神,并以神名命泉,“井深二百五十尺以达盐泉,俗呼‘玉女泉’”[6]5052[10]卷六十六。此外,富顺另有金川神和梅泽神。金川神“盖盐井神也”,百姓在监郭下井为其塑“金川庙”供奉。梅泽神,“井主姓梅,梅本夷人,在晋太康元年因猎,见石上有泉,饮之而咸,遂凿石至三百尺,盐泉涌出,煎之成盐,居人赖焉”[6]5052。 简州(治今四川简阳市)号称“简之郡,产盐惟最”[6]4297。民间盐神主要有艾、谭、惠、孟氏四神庙,“皆戎装,盐商共祀之”,相传“其地旧无盐井,有四人来教民辨土色度深浅,授以凿井之术,盐利遂兴,因德而祀焉”[20]卷三十三,四人因在当地发现盐泉,为百姓带来衣食之源,而被奉为盐神。 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县)境“有盐井、铜山之富”,被誉为“剑外一都会”。相传该地“旧无盐井,唐时一新罗僧游蜀至此,指其地凿之,盐泉涌出,因置寺,有塔,奉其遗躯,百姓为纪念新罗僧的贡献,将其祀为盐神,为凸显其灵验性,称:“每岁暮春,鹦鹉群飞塔上,至今犹然。”[6]4637 大宁监“溪南山岭峭峻之中咸泉涌出,土人以竹引泉置镬煮盐”,官方遂于开宝六年(973)置监以收课利,垄断了当地盐权。民间为表达盐权抗争,塑造土著猎人袁氏为盐神,以隐喻官方垄断的不合理性。当地最大盐产地宝山,“在监北十七里,半山有穴如瀑泉,即咸泉也”,袁姓猎人即被认定在此发现盐泉,“古老相传云宝山盐泉,其地初属袁氏,一日出猎,见白鹿往来于上下,猎者逐之,鹿入洞不复见,因酌泉知味,意白鹿者,山灵发祥以示人也”[6]5265。为纪念猎人发现盐泉的功绩,民间造“猎神庙”加以崇祀,以表达民间的利益诉求。 绍庆府彭水县伏牛山有老郁井,为当地最大盐井,民间盐神同为土著猎人。“相传有人在附近猎白鹿,鹿受伤后奔至此倒伏而发现盐泉,成井后呼为‘倒鹿井’,后人以地名谐音改称‘老郁井’”[21]254。 达州有通明盐场,场内有“斑鸠井”,所祀盐神为陈、罗二猎人。据载:“斑鸠井在八保明通井岩畔,其卤源自穴中流出,相传有陈、罗二人捕猎至此,见白斑鸠飞入岩穴,白水流出,尝之味咸,遂煎成盐,至今尚有陈、罗二人遗像。”[22]24 通过比较可知,宋代四川民间盐神的塑造基本以盐工或猎人为重要原型,通过盐工产盐或猎人寻盐的叙事结构制造民间盐权的享有,这正是民众与官方在盐神信仰的博弈中所通常采用的策略。 三 四川官方对民间盐神信仰的改造与容纳 四川民间盐神作为官方利益的对立面出现后,官方为了维护食盐支配权、争夺盐利,需要通过权力对其进行改造。在官民盐神信仰的博弈中,官方始终占据主动,但为了稳定当地统治秩序,官方又不得不对民间利益和信仰给予容纳。诚如韩森在研究宋代民间信仰中认为:“地方官需要依靠地方精英征集赋税、安定地方,也可能会支持同一个神祇,以便构成合作。”[23]92然而,官方对民间神祇的承认,并非不加辨别的全盘接受,因为“神祇是官僚还是个人化的保护者,一直取决于信仰者、陈述者在何种语境以及出于何种目的”[17]1,官方只是在符合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对民间盐神通过赐封、转变、转换等方式予以改造和承认。 如隆州盐场,同一地区存在官民两种盐神信仰,各自表述着对当地盐权的拥有。对此,官方通过贬斥民间盐神,然后再赐予封号加以“收编”,将其纳入官方控制之下。在民间,“玉女”盐神一直是赐福的美好象征,如丽甘井的得名:“昔有‘十二玉女’于此山服盐泉,‘玉女’美丽,盐亦甘好,因名。”[6]4481但官方却将其斥为“淫祠”,并营造一种恐怖气氛,以示对民间信仰“非法”的蔑视,“(百姓)祀‘玉女’于井内,‘玉女’无夫,后每年取一少年掷盐井中,若不送,水即竭”[24]1693,如此官方的介入便顺理成章。天师井的创开过程便体现了这种控制思想。据称:“天师井,本狼毒井,东汉张道陵所开,有毒龙藏井中,及盐神‘玉女’十二为祟,天师以道力驱出毒龙,禁‘玉女’于井下,然后人获咸泉之利。”[6]4497为求当地盐权秩序的稳定,官方亦不能无视民间的利益表达,因此对“玉女”亦未完全否定。“玉女”被“天师”控制,暗示着民间盐神沦为官方的附庸,然后经官方的改造,封为“灵真夫人”[25]873。“玉女祠”建于“天师庙”侧,得到官方承认并与官方盐神并列,实际也是一种官方对民间盐权利益的妥协。最终官民通过盐神博弈,在实际的盐权分配中也求得了秩序的认同:“置灶煮盐,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19]3206 另如邛州蒲江县盐井供奉的平民神袛“三夫人”,先被官方改造为“圣姑”,绍兴三十一年(1161)赐庙额“博济”,以此纳入官方供奉体系;乾道八年(1172)又分别加封为“灵惠”、“协惠”、“赞惠”三夫人[8]礼20之59。 官方对待民间盐神的另一方式是不加改造,直接授予封号,使其转变为官方认可的盐神。对官方而言,“不论动机如何,封赐神祇做为朝廷最初进入该领域的一种路径,被认为在地方社会是强有力的”[17]201。如富顺监民间盐神为王、梅二人,王氏在后蜀时被官方封为“金川王”,建“金川庙”加以崇祀;梅氏因猎发现盐泉,“梅死官为立祠”;宋淳熙中,“封金川庙为永利侯,梅泽神为通利侯”[6]5052,反映官方对其认可的程度已经很高,使其脱离了平民神祇的色彩。官方加赐平民神祇封号的原因,“与其说是人与神之间的合作,倒不如相信他们所说的,是为了官府的利益而控制神祇威灵的一种努力”[23]92,最终还是为了官府自身利益。 官方对待民间盐神的第三种方式是对民间象征符号的转换。如宋代川东盐区,在民间看来多是猎人通过“白鹿引泉”而发现盐井。而“鹿”正是民间的象征,代表了民众的祈福心理。尤其“白鹿”作为一种瑞兽④,被视作平民神祇发现盐泉的引导者,表达了民间对其灵异性的肯定和盐权享有的心理寄托。官方对民间发现盐泉的使者“白鹿”进行的改造,主要是将其转化为官方符号“龙”,即所谓的“白鹿化龙”。首先,龙是官方认可的帝国权威符号的象征,而龙形象中就有鹿角,另外,龙本身也是“与鹿有关的吉祥神兽或原始图腾神灵的变体”[26],这为两者的转换提供了可能,而不至于牵强附会。如大宁监民间宣称盐神因追逐白鹿而发现盐泉,官方遂将白鹿改造为龙,建“龙君庙”以崇祀,使其完成了由民间走向官方的过程。同时,官方亦对其平民神祇做了妥协,认可民间设立“猎神庙”,与“龙君庙”并列。嘉定中,大宁知监孔嗣宗建宝源寺,“以祀井神”,共奉龙君和猎神[27]卷一。这恰是官民盐神博弈的结果呈现,对官民盐权分配秩序的均衡具有积极意义。 四 四川民间对官方盐权分配的信仰认同 宋代四川盐神信仰的博弈中,呈现出官方主导和控制的特点,官方在自造盐神和控制平民神祇的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动,民间则处于类似“冲击—回应”的反馈模式。因囿于史料或官方修史的背景,目前能够得见的记载主要是民众对官方盐权分配的认同以及在信仰中所表达的“感激之情”,这明显缘于民众自身的弱势地位所决定。当然,如果官方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又会对民间食盐信仰诉求给予一定满足,则双方的信仰博弈会呈现更加和谐的格局。 民间信仰认同的主要表达是对采取各种措施缓和官民盐权冲突的地方官予以“准盐神”的待遇加以祭祀,甚而从祀盐神庙直接享受与盐神同等礼遇。如太祖建隆中,贾琰通判陵州(隆州),因盐井阻塞严重,“不复开浚,民食大艰”,贾氏“专干浚井,琰至井,斋戒虔祝,引锸徒数百人祝其井曰:‘圣主临御,深念远民,井果有灵,随浚而通’”,并亲自执锸率盐工下井淘采,“数旬始见泉眼,初炼数百斤,日稍增至数千斤”,郡人感其德,“绘琰像,祀于井旁”[28]27。 孝宗淳熙初,李繁任四川总领,时邛州蒲江盐井“岁欠课百三十余万”,当地郡守“增发盐课以供少府私用,致灶民负担沉重”,李氏“谴官查核,又请宣抚司更法平价,减邛州蒲江盐额十万八千余斤”,因李氏较好处理民间盐权纠纷,“蜀人绘像以祀”[9]232。淳熙中,胡元质制置四川,因蜀中盐井所纳虚额严重,尤以简州“虚额尤多”,胡氏代为上奏,“每岁计豁除折估钱五万四千九百五十余道”,简州民众为其立生祠加以祭祀[6]4297。 宁宗时,遂宁知府许奕将官方盐利分予地方办学,“复盐策之利以养士”,“民德之,画像祠于学”[1]12271。开禧间,吴猎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见蜀民盐课负担严重,“奏请将四川盐课等税由原来的四百万缗减为二百万缗”,蜀人“思其政,画像祀之”[9]255。嘉定中,大宁监盐权冲突严重,“人户汲泉,强弱相凌,多抵于讼”,朝廷“乃遣荣州资官令孔嗣宗措置,有不便于民者,悉除去”,孔氏“止存垅户租盐三色,除去四色,民以为便至”,又规定“今凡盐出津四分,官取其一,谓之抽分,尚孔长官三七分之除意也”,民众感其德,“多为立祠,号孔长官祠”[6]5268。因孔氏合理解决官民盐权冲突,重建利益分配秩序,因此得到民间“准盐神”的最高待遇而“从祀宝源庙”[29]204。 理宗宝庆中,赵希益担任富顺监学教授,见当地盐权秩序紊乱,弊端众多,上奏使“井灶盐弊一切罢除”,去任之日,“士民绘像以祀”[30]卷三。 民间信仰认同的另一方式是承认官方所祀盐神,将其与自造神祇共同祭祀。如前述官方所祀盐神后来普遍得到民间认同,其影响甚而至于晚近。如云安盐场、大宁盐场、明通盐场均建有“井祖庙”或“龙君庙”,祭祀龙君的日子和仪式称为龙君会;云安盐场建有“高祖庙”,祭祀刘邦、樊哙、扶嘉等[22]25。 民间信仰认同的最积极表现是民众发现盐泉后主动告官,对将盐权利益主动让与官府的发现者,官府不仅不予贬斥,反而祀为盐神。如长宁军原为宋泸州(治今四川泸州市)羁縻属地,因其“深介夷腹,初人未知有井”,后有二人因放牧而辨其咸,“告之有司,乃置监鬻盐”;在监城北井之上又有盐井,“古老相传以为井初隶夷之罗氏,汉人黄姓者与议,刻竹为牌,浮大溪流约得之者以井归之,汉人得牌闻于官,井遂为汉有,今监中立庙祀之”[6]5021。长宁军两处盐井皆是百姓先发现或得到盐泉,然后再报于官府,以此而得到民间祭祀。从百姓得泉先告官府的举动来看,他们内心已经具有“食盐官有”的认同意识,而民间对他们予以祭祀,则是民众在盐神信仰中对官府具有盐业主导权的承认。 上述民间对官方信仰认同的表达,前提都是建立在官民盐权分配得到较好处理的基础下。如果官民盐权冲突较为剧烈,官方对地区盐权的分配处理失当,则各自的盐神博弈最终会走向对立的两极。在民间看来,官民盐权分配的秩序应是和谐而又有序的,符合官民双方的共同利益。如大宁监定期举办的“绞篊节”,便因代表了这种民众期许而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蕴。绞篊本为当地运盐设备,“篊在盐井,引泉踏溪,每一笕用一篊,其笕与篊经一年,十月旦日以新易陈”。绞篊因用竹篾制成,不能耐久,必经一年一换。因当地盐权分配得到较好处理,每年十月一日为绞篊更换之日,便为官民双方共同信奉之节日,“郡守作乐以临之,井民歌舞相庆”,形成官民同庆的场面[2]5265。实际上,这正表达了民众对官方盐权分配合理的一贯夙愿以及与官方共享地区盐权的要求。 综上所述,在宋代四川盐区,作为一种典型的资源导向型社会,其盐神信仰作为官民争夺食盐资源在意识形态的博弈,实际表达的是官民之间追求当地盐权和分配秩序的利益诉求,而非单纯体现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的功能呈现。四川盐神信仰作为官民盐权博弈的表达,为双方共同利益所服务,它并非仅仅表现为地方之整合、国家—社会之关系的处理工具,它更多表达的是一种资源在地方社会所触发的各群体间的互动过程以及各方围绕这种资源的博弈所呈现的纷争与妥协;它既体现了官方的盐权垄断思想,也反映了民间盐权的自救,在信仰中通过官方的盐神改造和民间的认同得以表达,最终官民双方围绕食盐资源的博弈中寻求到一种合理的盐权分配秩序,完成井盐社会利益和信仰秩序的有序、和谐与稳定。 注释: ①较有影响的著作有:〔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美〕韩森著、包伟明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美〕武雅士主编《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美〕韩明士著、皮庆生译《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英〕王斯福著、赵旭东译《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这些研究多以信仰本身为视角,重在分析信仰的功能及意义的表达,成为解构“国家—社会”的重要模式。 ②目前涉及宋代四川盐神信仰的研究不多,且多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重在对信仰内容的描述和官民节日欢庆场面的渲染。主要论著有:王仁湘、张征雁《中国滋味:盐与文明》(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张银河《中国盐文化史》(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宋良曦、林建宇等《中国盐业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李绍明《少数民族对开发盐源盐业的贡献》(彭久松、陈然编《四川井盐史论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刘卫国《渝东盐场的民俗节》(曾凡英编《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宋良曦《中国盐业的行业偶像和神祇》和《中国盐业与地方会节》(宋良曦编《盐史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通过将盐神信仰作为官民食盐博弈的一种方式,分析其背后所折射的社会关系互动,这类研究成果目前为止仍较为少见。 ③宋代四川官方盐神信仰中有些为前朝人物,其信仰源自何代已不可考,但在宋代方志中多次出现,可以肯定其信仰在宋代仍然延续了下来。因此,文中对宋代盐神的阐述,除本朝人物塑为盐神的时间加以说明外,其余不再赘述。 ④关于“白鹿”为瑞兽的解释,见《抱朴子·玉册篇》:“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参见:〔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九○六《兽部十八·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