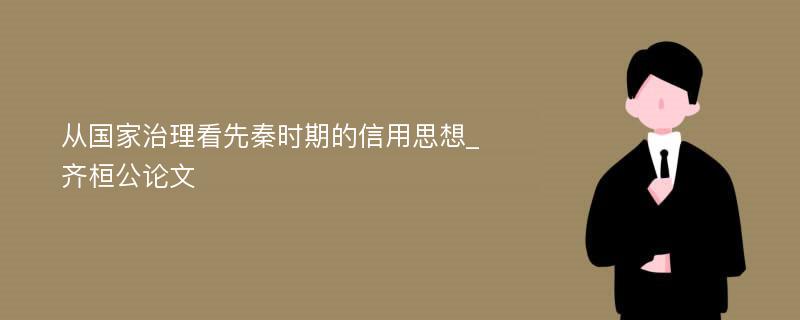
先秦时期信用思想探析:国家治理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先秦论文,视角论文,时期论文,信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用”近年来被学界广泛关注,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信用是“二元主体或多元主体之间,以某种需要为目的,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心理承诺及约期实践。”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信用是一种“贷和借的运动”,是“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行为。“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只是有条件让渡的独特形式的运动。”②考诸先秦史籍和出土文献可以发现,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与现代信用相类似的概念。近年来,学界对先秦信用的探讨多集中在信用观念的产生以及对借贷的描述,而对于信用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理解仍显不足。因此,本文主要利用先秦典籍的相关记载,结合先秦时代政治局势发展的过程,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就信用在先秦时期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及演变作出初步探讨。 一、先秦时期信用观念的出现 “信用”这一概念出现很早。从传世文献看,《尚书·康王之诰》载:“信用昭明于天下”;③《周礼》载:“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④但在先秦典籍中,“信用”一词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一般用“信”来表达“信用”的概念。据学者统计,《左传》中“信”字共出现216次。⑤“信”的概念多与各国间订立盟约、盟誓及“质”有关。 关于“信”字的起源,有的学者认为在商、西周时期还未出现“信”字,直至战国时期的古文字中才有此字,如:“商周文字中不见信字,战国文字中才有”。⑥宋镇豪认为甲骨文中已有“信”字,不过出现频率很低。⑦冯时根据对出土甲骨文的研究,认为“商人对于神的敬畏使他们不能不怀有诚信之心,而这种心理不仅孕育了真诚待神的朴素诚信观念,而且直接发展出具有人本思想的信。”⑧结合传世文献分析,冯时的推测基本成立。《礼记·祭统》载:“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唯贤者能备,能备然后能祭。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之以时。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为。此孝子之心也。”⑨此即强调对待鬼神必诚必信的重要性,通过对天神所表现的诚信,阐明信用的核心内涵在于人对待鬼神态度的思想。后世的“歃血为盟”“折箭为誓”“啮臂盟”“信誓旦旦”“指天为誓”等都保留了记录人对天神诚信的信息。 关于经济信用的发展。它是伴随着货币的出现而发展的。殷商时期的贝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货币。王国维认为:“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商书·盘庚》曰:“‘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⑩王毓铨认为:“在古代中国境内,最初的货币大概可以说是贝。”(11)春秋战国时期,货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诸侯国所使用的货币并不统一。各国货币在形制、材质上各不相同对商业经济造成了很大阻碍,也影响了信用在经济领域内的传播。货币的出现使得信用思想在经济领域得到重要体现。因为有了货币这一信用媒介,商品交易变得更加顺利。 借贷行为的出现。早在西周时期,社会上就已经存在民间借贷行为,而且这种行为需要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明证,并按照法定的利息支付,违者要处以刑罚。“凡民同贷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法之”,(12)记载的就是民间信用。《周礼》记载“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13)这里的“赊贷”,指的是国家信用。当时的泉府负责各种征课、稳定物价和办理赊贷,泉府的这种“赊贷”,可谓中国最早的政府信用。 商业信用的出现。西周时期,政府重视市场建设和市场管理,王都及各诸侯国都城,均设置用以贸易的“市”。《逸周书·作雒》载:“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14)可见,地处“天下之中”的雒邑,在其营建之初即已设“市”,并对从事活动的“工贾”进行单独管理。西周官府对市场的管理,主要是针对国家控制的较大市场,至于农村中小市场上民众间的交易,则不在管理范围之内。(15)西周中后期,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和私商数量的增加,官府对商业和市场的管理有所加强。王畿各城市及各诸侯国都设有专门的市场管理机构。《兮甲盘》铭所说“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的“次”,就是指市场管理机构。(16)根据《周礼》记载,管理市场的职官有司市、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虣、司稽、胥、肆长、泉府。司市为“市官之长”,管理的内容有:不得以次充好,欺瞒消费者,“使贾人不得杂乱以欺人”。实行“质剂”之法,由市官“质人”掌管、执行。凡货物买卖,以官府制作的交易符券为凭证,书两札,买卖双方各执其一。长券曰“质”,短券曰“剂”。“大市,人民、牛马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17)质人划一度量,随时巡查稽考,对不合规定者“举而罚之”。总体来说,“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以量度成价而征犊,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18)司市的职责就是保证市场交易中的信用原则,防止货物以次充好、货物价格与规定不符,并负责处理交易双方间的各项纠纷。正是在官府的强力引导之下,商业交易中的公平信用原则得以贯彻与执行。 关于政治信用的雏形。国家治理层面对“信用”观念的实践可追溯到商、西周,甚至更早。《尚书》中的誓与诰,为统治者与治下将士百姓的约誓,反映了早期的政治信用关系。《尚书》卷7《甘誓》载:“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正义引《曲礼》云:‘约信曰誓’”(19),约信与誓互训。《说文》曰:“约束也,从言折声。”(20)可知,所谓誓,即以言辞定约束,通过约信或誓来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甘誓》是夏启与有扈氏在战前而做的战争总动员。其文曰:“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书·汤誓》,为商汤伐夏之前所作。其文曰:“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王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泰誓》,为周武王伐纣前所作,其文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21)这三誓分别是夏、商、周开国前为战争动员所做的誓戒,性质相同。其一,立誓约的双方分别为君主与将士,其誓约为由上到下的约束;其二,公布被讨伐者之罪,以使师出有名;其三,将赏罚原则公之于众。其核心是与将士设约,示赏罚之信。又如《尚书·盘庚》,虽然篇名不用“誓”,其实质也是约誓。按照现代政治学对于政府信用的界定,“个体、组织,甚或国家的履约意志与能力,这个‘约’既可以是无形的口头承诺,也可以是有形的文字协约。”(22) 这种由上而下的盟誓形式,如起誓的仪式、记载誓辞的文书、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履约的预期和奖惩,虽然方式古朴,但基本上具备了政治信用的构成要素。可见,誓是早期政治信用的表现形式。 二、春秋时期的国家信用与霸主政治 (一)信用作为一种政治道德得到普遍尊重 信用在春秋时期作为一种政治道德受到了普遍的尊重,被称为“信,国之宝也”(23),“信,德之固也”(24)。春秋时期,王权衰落,政治结构多元化,权力分散于各个诸侯国,并以霸主政治的形态重建了国家秩序。霸主通过会盟来明确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建立各国间的利益交换和平衡机制。霸主通常也是盟主,甚至新君即位亦经常与他国会盟确定地位。政治信用是维持会盟的重要政治原则,正如《国语·鲁语》所载:“夫盟,信之要也”;“晋为盟主,是主信”。(25) 信用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极强的约束,即使贵为一国国君也不能失信。《史记》卷42《郑世家》记载了郑庄公为了兑现承诺不得不与母亲穿泉相见的史实。郑庄公的母亲宠爱庄公的弟弟段,段与庄公的母亲武姜图谋作乱,“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作为叛乱的主谋,庄公的母亲武姜被迁于城颍,庄公发誓曰:“不至黄泉,毋相见也”。可见,这个誓言虽然并不是正式的誓约,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这样的誓言郑庄公也不敢违反。一年后,庄公对自己的过激行为有所追悔,欲与母亲相见,却又不得不顾及到自己的诺言,“我甚思母,恶负盟,奈何?”郑国大臣颍谷之考叔献策曰:“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26)郑庄公于是穿地至泉出而见母。郑国君臣用这种变通的方式,表现了对重诺守信的尊重。 治理国家也要遵约守信、兑现政治承诺,否则极可能引起政治危机,甚至引起国家动乱。《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载,齐襄公命其大臣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并约定戍守期限为一年,但到期时襄公却拒绝履约,“往戍一岁,卒瓜时而公弗为发代”;“或为请代,公弗许”。(27)因而,连称、管至父以齐襄公不遵守事前约定为由,联合公孙无知发动叛乱。 (二)国家信用与齐国霸业 1.齐桓公霸业中的“礼”与“信”。齐桓公开创了霸主政治的先河,一方面用强大的国力做后盾;另一方面,倡导德和礼,用“礼与信属诸侯”。(28)齐桓公和管仲遵行政治信用,信守盟约的行为,在齐与鲁的“柯之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齐桓公五年(前681),齐国与鲁国交战,鲁国战败,鲁庄公献遂邑求和,齐鲁两国在柯地会盟。在会盟中,鲁国曹沬以匕首劫持桓公于会盟坛上,要求齐国退还占领鲁国的土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齐桓公屈就了鲁国的要求,两国订立了盟约。如何对待鲁国这样一个战败的弱国?如何对待在被劫持状态下签订的盟约?齐桓公的想法符合正常的逻辑,“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但管仲的看法却高出一筹,认为“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杀曹沬事小,但毁约则会失信于天下,于是齐国退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此举,齐桓公树立了讲信义守盟约,不以大欺小、倚强凌弱的形象。此后,“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29)齐桓公成为事实上的霸主是在鲁僖公九年(前660)的葵丘之会。该会盟的核心是“诸侯无相害也”。“诸侯无相害”是周成王之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30)桓公纠合诸侯,希望继承和发挥诸侯子孙“世世无相害”的传统。由于东周以后周天子权威不再,周成王“无相害”的盟誓只能由霸主在盟会上申明,但齐桓公没有僭越,其既要维护周天子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地位,又要以盟会为武器把持天下的权力。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以尊王为号召,即尊重君臣之礼,重建以霸主为核心的列国秩序。如果齐桓公不遵守礼的规定,使周天子不尊,诸侯就可以效尤,则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就无所依据,天下就会陷于动荡之中。因此,管仲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31)桓公的霸政是以尊礼守信为核心的,所谓“盟以信礼也”“信以守礼”“忠信,礼之器也”,深刻地说明了礼与信之间的关系。(32) 2.齐桓公霸政对经济信用的规范。葵丘之会强调了与盟国共同遵守的五条原则:“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33)其中,前两条关键的条款都与经济信用有关。就“毋雍泉”而言,那时诸侯国的国家面积都不大,一条河流可能流经数国,上游国家截断水流,下游国家便有断绝水源的危险。由此可见,“毋雍泉”是保证各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信用原则。 “毋讫籴”,是指各国不能囤积居奇、不救别国粮荒。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较小,遇到灾荒非求助于邻国不可,倘若邻国不救灾荒,则会有举国断炊的危机。因此,那时的列国都将诸国之间的借贷,尤其是粮食的借贷视为非常重要的国家信用,所谓“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34)如鲁国遭遇灾荒向邻国齐国求救,得到了齐国的救助,“鲁饥……文仲以鬯圭与玉磬如齐告籴……齐人归其玉而予之籴。”(35)又如晋国遭遇饥荒向邻国秦国求救,得到了秦国的救济,“晋饥,乞籴于秦。缪公问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国家代有,救菑恤邻,国之道也。与之’……卒与粟,自雍属绛”。其后,秦国有灾而晋国不救,两国为此爆发了战争,“惠公用虢射谋,不与秦粟,而发兵且伐秦,秦大怒,亦发兵伐晋。”(36)可见,“毋雍泉”“毋讫籴”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基本要政,也彰显出国家信用的重要作用。 为了维护列国间的正常贸易往来,在齐桓公召集的各次盟会上,都曾把维护正常商业交往,作为重要的内容写入盟约。如僖公九年,葵丘之盟有“毋忘宾旅”的内容。(37)即要保护客商,不得阻碍粮食的流通。为了繁荣经济,促进商品流通,齐桓公采取了减轻关税负担,维护交通畅通等政策,“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38)齐桓公的这些做法,类似于当前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同盟体。如果没有信用做基础,当时的商业交往、商品流通以及减轻关税这些盟约是难于顺利施行的。 为了管理民间借贷,齐桓公派人深入民间调查借贷事件。“鲍叔驰而西,反报曰:‘西方之氓者,带济负河,菹泽之萌也。渔猎取薪蒸而为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钟,少者六、七百钟。其出之,钟也一钟。其受息之萌九百余家’,宾胥无驰而南。反报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处,登降之萌也。上斫轮轴,下采杼栗,田猎而为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余家。’”(39)当时已经出现了实物借贷与货币借贷的形式,其额度由粟数十钟到数百钟,钱六七百万到上千万不等,借贷利率从二分到十分,相差甚为悬殊。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经济信用原则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借贷活动中。 (三)国家信用与晋国霸业 1.晋文公霸政精神的变化。作为春秋时期的另一位霸主,晋文公开创的晋国霸业持续了100多年。晋文公在政治信用方面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方面,高度重视取信于民的政治信用;另一方面,对于维系诸国关系的“外交信用”则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晋文公君臣以诚信为立国之本,充分体现在“箕郑对文公问”中。“饥,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对曰:‘信。’公曰:‘安信?’对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则若何?’对曰:‘信于君心,则美恶不踰。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于是乎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匮之有?’公使为箕。及清原之搜,使佐新上军。”(40)由此可见,箕郑对晋文公系统讲述了如何使用信义解救百姓的饥荒,也即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如何以诚信立国、取得民众信任的问题。晋文公不仅采纳了箕郑的建议,而且命他担任要职,足见其对信用思想以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的高度重视。 关于晋文公重视取信于民的政治信用,还有一事可佐证。《国语·文公伐原》记载,晋文公攻打原城时,与将士约定以七天为攻期。过了七天原城仍不投降,晋文公命令撤军原城。尽管原城已经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但文公说:“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41) 晋文公高度重视列国关系中的政治信用,“退避三舍”的故事实际上也反映了遵守政治誓约的思想。晋退避三舍后,晋楚两国大战于城濮,晋军战胜,晋主导缔结了践土之盟,晋文公开创的晋国霸业就此揭开帷幕。不过,与“存邢救卫”“分沟礼燕”的齐桓公不同,晋文公的霸政精神已经发生了变化。列国关系中的政治信用逐渐成为一种斗争的手段,而不再是与周礼等同的价值观念。《左传》载“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42)周天子也参加了这次盟会,与践土之盟中周襄王主动参加不同,“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43)本来应该由诸侯到京师去朝见周王,晋文公却以诸侯的身份召周王前来相见,严重地违背了周礼。孔子读到《春秋》上这段文字时,本着为“尊者讳”“且明德也”的原则做了修改,“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44)自晋文公称霸起,尊王的政治号召越来越成为一种表面上的形式,靠实力说话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旋律。在晋国霸业兴盛的一百多年间,由其主持的较大盟会见于记载的有38次。在《春秋》中,鲁国的国君去洛阳见周王只有1次,还未行朝见之礼,而去晋国朝见多达21次,由此足以说明霸主最终取代周王成为了真正的天下共主。 2.晋国霸政中的经济信用。晋国霸政同样重视维护列国间的正常商业交往。在晋楚于宋国西门之外的盟约中,对各国间借贷、救灾、维护道路畅通、保证正常商业往来都做了详细规定。《左传》载:“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45) 晋国作为霸主国,对小国还有贡赋之征。晋文公、襄公时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46)大体说来,其时,诸侯对晋的负担相对轻些。而此后日益加重,使各国疲于奔命,“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47) 三、战国时期的政治信用 战国时,列国关系中的政治信用遭到严重破坏,“信义外交”逐步让位于“权谋外交”。 秦国商鞅曾经借盟会之机,扣押了魏国主将公子卬。《史记》卷68《商君列传》载:“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48)秦国还在盟会中扣押了楚国的君主楚怀王。《史记》卷40《楚世家》载其事甚详,秦昭王先以叙旧为由邀请楚怀王盟会,“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也”,“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楚怀王到武关后,秦昭王却“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49)秦国的行径已经远远背离了春秋时列国盟会的原则——“盟,信之要也”。 由于列国关系中的政治信用屡屡遭到破坏,战国时期各国不得不采取交换质子的办法来保证盟约的履行。秦昭襄王为质于燕,韩太子苍为质于秦,秦庄襄王为质子于赵,楚顷襄王质于齐。正如阎步克所言:“盟约”到“人质”恰好标志着“信”之发展的两个阶段。(50) 虽然战国时期列国关系中的政治信用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仍然保持着道义上的力量。被扣为人质的楚怀王得到了极大的同情,以至于秦末反秦军都以楚怀王的旗帜为政治号召。在列国外交中最不讲信义的秦国,竟然也以“信义”为武器,指责他国失信。秦始皇将六国中四国的灭亡原因都归结为其背约负盟。《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51) 与当时列国外交信用遭到破坏相对应,作为取信于民的政治信用却高度发达起来。战国时期,周王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诸侯国君。各诸侯国君相继称王,既没有周天子的管束,也没有霸主的制衡。各国之间的战争已发展成惨烈的兼并战争。在这种氛围中,富国强兵成为各诸侯国的共同诉求。从战国初期开始,各国纷纷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在各国变法运动中,取信于民的政治信用被作为推动变法的武器,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商鞅在秦国推动的变法。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打击宗法贵族,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并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一统帝国的根本原因。(52)商鞅的变法涉及四个方面:第一,奖励耕战;第二,建立法制;第三,打破宗法贵族制度,建立新型官僚制国家;第四,移风易俗,改变秦戎狄之风。其中,打破宗法制度影响到旧贵族的利益,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商鞅变法必须树立取信于民、令行禁止的政府权威。商鞅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并没有立即公布。为了向国民表明变法的决心和信用,商鞅采取了“徙木立信”的方式作为推动变法的先声。《史记》卷68《商君列传》载其事曰:“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53) 对于取信于民与变法成功的关系,北宋司马光的观点很清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54) 战国政治信用的发展出现了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列国间的政治信用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正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所言,“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55)另一方面,各国取信于民的政治信用则得到了强化。 四、战国时期的经济信用 (一)货币的发展及流通 战国初期,货币在各国的使用相当广泛,各国政府都采取措施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在民间,不允许私自铸钱,对民间私铸货币的打击是维护国家信用的重要举措。在战国时期,除黄金作为各国的通行货币外,各诸侯国均使用以黄铜制造的、固定形态的货币,如齐国的刀币、三晋的布币、周的泉币。而秦国拥有固定形态的货币则出现于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初行钱”。(56)由于各国自行铸造货币,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别的货币体系和流通地域。但是,这些货币区并不是孤立隔绝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军事形势的变化,列国之间的货币形成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复杂局面。战国末年,货币在秦国的使用相当广泛,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秦国对盗窃判刑的轻重,是以物品价值多少来定罪的。《秦律》规定:“盗采桑叶不盈一钱,赀徭三旬。甲盗不盈一钱,乙知而不捕,赀一盾。”(57)对盗窃物都折算成钱,从而判罪,说明货币在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另外,钱还可以用来赎罪。《秦律》规定:判流放的罪人,可赎免,谓之“赎迁”;判黥刑或耐刑的人,也可赎,谓之“赎耐”“赎黥”。(58)赎即指用金钱货币办理。 随着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渐趋重要,民间私铸等新问题随之出现。秦简《封诊式》有这样的案例:“某里士伍甲、乙缚诣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熔)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熔),来诣之。”(59)这是一个典型的盗铸货币的案例,它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秦国货币铸造权由政府掌握,民间不得私铸,否则要绳之以法;二是秦国的货币铸造权虽然受到法律保护,但民间私铸货币仍大量存在,禁而不止。 (二)金钱借贷行为的普遍出现 春秋时期,“家累千金”的富商大贾并不多见,见于记载的只有范蠡、子贡等。战国时代,在农业、手工业和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富商大贾活跃在商品流通领域,独立的商业资本也得到了发展。随着商品买卖的进一步繁荣,借贷资本,即通过贷放货币获取高额利息的资本也随之发展起来,国家对借贷资本进行了相应的规范和管理。 关于借贷,战国以前就存在,但那时主要是实物借贷。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贷粟”已颇常见,这在前文已有所述。战国时期既包括实物借贷,也包括金钱借贷,并以金钱借贷为主。放贷者(债权人)有贵族、官僚、商贾、地主,还有国家政府。从出土的《秦律》中可见,不仅存在民间的借贷关系,秦国政府与百姓之间也有借贷关系。《法律答问》云:“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法”。(60)府中的资金本是官府放贷用的,不允许官吏私自借用,私自贷用者与盗窃同罪。 借贷同商品交易一样,以竹木制的券为凭证,先把借据写在上面,然后剖分为二,由债权人执右券,债务人执左券。借债到期,债权人“操右券以责(债)”,(61)命债务人前来合券并偿还欠债和利息。(62)此种债券称为“傅别”,“傅”指合券,“别”指个别的右券或左券。如果因债务问题发生纠纷,官府则依据“傅别”断案,所谓“听称责(债)以傅别”。(63) 官府有追债的职能,如追债不得,还要代为偿还债务。“百姓……有责(债)未赏(偿)……而弗收责(债)……令其官啬夫及吏主者代赏(偿)之。”(64)百姓欠官府债未还,其人死亡,则令该官府啬夫和主管其事的吏代为偿还。 (三)战国时期对商业贸易的规范和管理 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时期各城邑都划出一定的地段和范围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市里分成若干列,即出售货物的“市肆”。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区四周布“市门”出入,市设置“市吏”管理,(65)市中经商的人均有“市籍”。从出土的《秦律》看,有涉及市场管理、商贩组织形式及对违法者的处罚规定等,如“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人,不从令者赀一甲。”(66) 在商鞅的法令中,“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67)这体现出变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即重农抑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业贸易信用的发展。但其变法法令中“平斗桶权衡丈尺”,即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使秦国各地的贸易往来更加通畅和频繁,与重农抑商的措施相反,对当时秦国商业贸易信用的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总之,战国时期各国加强商业管理的做法,维护了国家信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贸易信用的发展。 五、先秦诸子对信用观念的论述 信用观念起源很早,在春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受到了广泛的推崇和重视,信用被称为“言之瑞也,善之主也”(68)“礼之器也”(69)“战之器也”(70)。先秦时期,与信用有关的“会”“盟”“誓”“质”之类的行为在列国之间极为普遍。《春秋》所叙的242年间,列国军事行动凡483次,朝觐盟会凡450次。(71)信用思想的演进引起了先秦诸子的注意,其中重要的思想家都对信用观念进行了论述,尤其是关于信用思想在国家治理层面的重要作用。 孔子把信用看作是个人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标。如孔子答子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72)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把“信”当成是人人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73)孔子答子张:“主忠信,徒义”,(74)充分体现其崇德思想。孔子还认为,信是君子首先需要具备的品行,“君子不重则不危,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75) 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对于国家信用,尤其是取信于民的政治信用,孔子给予了高度重视,将其看作为超乎生死之上的重要信条,做出了许多重要论述。就治理国家而言,孔子认为“信”是最重要的准则。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76)“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77)孔子从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了信用的政治意义。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信用思想,并有所创新。孟子将“朋友有信”视为儒家的五伦之一。如“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78)由此将“信用”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一起,从个人内在的道德规范变成了整个社会必须依从的五种基本伦理关系之一。在孟子看来,信用是朋友之间相互交往的基本道德前提。孟子的五伦说,从理论高度上阐释了信用的重要性,一直为后代统治者所遵循,影响深远。孟子的信用思想还体现在其政治主张上。孟子一贯主张取信于民,并提出了“制民之产”的富民主张,认为只有让百姓富裕,并教化他们知仁义、讲孝悌,则百姓自然而然地就会懂得信用的道理,国家也就会因此而变得容易治理。同时,“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79)这里记载了当时贫苦农民借高利贷来纳税的情形,可见高利贷的猖獗。“称贷而益之”,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孟子已经涉及消费借贷的范畴。 墨家解释“兼爱”之人的重要特征是“言必行,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80)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必须符合自己的言语,个人的任何言论都必须表现出一定的实践行动。墨家坚持把“信”作为评价人们道德规范的一项重要标准。墨子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81)这意味着只有言而有信的人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在墨子眼里,“夫尚贤者,政之本也”,(82)而选拔贤者的标准则在于其是否忠诚守信,墨子为此曾说:“忠信之士,我将尚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83)只有讲信用的人才能得到墨家的赞许,而那些背信弃义的人则被墨家视为低贱。在墨子看来,只有具备信用这种品德的人,才有能力做到“兼爱”天下之人,才有资格为万民“兴利除害”。此外,墨子还认为统治阶级也必须遵守信用,在政治上做到“赏罚有信”,墨子坚持“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84)“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曰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85)因此,墨子认为统治阶级以信用的原则治理国家是国家大治的一个重要前提。 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世间的一切皆由“道”所产生,而道又“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情”“其中有信”。(86)这即是说“信”与“物”“象”“情”一样,都存在于“道”之中,是构成“道”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在这一理论逻辑下,人们必须讲信用、重诚信。由此,老子提出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认为人只有做到“言善信”,才能跟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此外,老子还将信用当作是人生行为的重要规范。对于士大夫来说,“信用”是其必须遵循的最基本准则之一,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由其贵言也”;“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87)即重诺言、讲信用必须成为人们共同遵循的人生准则。 庄子虽历来被认为是超然物外、不媚世俗的典型,但也极其重视信用。庄子认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88)庄子不仅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哲学概念,而且与老子一样均认为“信”存在于“道”中,即“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惟有天地,自古以固存。”(89)即讲信用是顺应“道”的自然行为,是一种“自古以固存”的内在要求。《庄子·外物》载:“庄周家贫,往贷于盐河侯,盐河侯曰:‘诺,我得邑金,将贷子三百,可乎?’”(90)这里记载了关于货币的借贷。 《管子》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包含先秦许多流派的思想,但又不能算是杂家。在《管子》一书中,从官民互信、邻国互信等方面论述了政治信用的重要作用。 臣不亲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乱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于邻国,国有患则莫之忧也,有难则莫之救也;外内皆失,孤特而无党,故国弱而主辱;故曰:“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言之不可复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贼暴也;故言而不信,则民不附;行而贼暴,则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灭亡之所从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复,行之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91) “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92)《管子》提出储藏粮食和货币以备贷放,希望以政府放贷的方式来消除高利贷对贫苦百姓的豪夺,使百姓得以安居而不误本业,国家的利益也能得到保障。 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从令行禁止、明赏罚、君臣互信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信用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93)“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94)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针对各国君主强化军事力量、比拼国力、兼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列国间政治信用遭到破坏的现象,提出了“义为本,信次之”和“义立而王,信立而霸”的论点:“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彊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95)“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96) 《吕氏春秋》产生于秦统一六国前夕,借《晋文公攻原》一事,阐述了对信用观念的评判,坚持强调“必以诚信得之”,(97)表明“信用”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已经对先秦时期的政治生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六、总结 “信用”观念在中国起源很早。最初从人对鬼神的态度发展起来,随后从人对鬼神的诚信发展为人对人、国对国的诚信。商、西周时期的盟誓是君主与治下臣民订立的协约,是其后“取信于民”“明赏罚”“令行禁止”的国内信用的早期形态。春秋时期开始盛行的盟会,订约的各方均为平等的主体,是“外交信用”的早期形态。对先秦时期经济领域中信用思想的萌芽和发展的研判不能简单地以现代经济思维去看待,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与经济背景,客观地对这一时期经济领域的信用表现进行分析。先秦时期,人们不仅认识到“信用”在借贷、商业贸易等经济领域产生的影响,而且更加重视其在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诸子几乎都对“信用”观念做了论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均在国家治理层面对“信用”进行了阐述,其中孔子已经将“信用”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先秦以后,儒家思想长期占有重要地位,“信用”观念被列入“三纲五常”进入儒家学说的核心,并对先秦以后历朝历代的国家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注释: ①句华:《政治学视野中的政府信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②《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页。 ③[清]孙星衍著,陈抗、贺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25《周书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08页。 ④[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17《春官宗伯第三下·诅祝》,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61页。 ⑤刘驰:《中国古代的信用与“信”》,中华文史论丛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论丛》第8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页。 ⑥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⑦转引自刘驰《中国古代的信用与“信”》,中华文史论丛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论丛》第88辑,329页。 ⑧冯时:《儒家道德思想渊源考》,《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⑨[清]朱彬:《礼记训纂》卷25《祭统第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22页。 ⑩王国维:《观堂集林》卷3《说珏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6-77页。 (11)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 (12)孙诒让:《周礼正义》卷68《秋官司寇第五上·朝士》,第2828页。 (13)孙诒让:《周礼正义》卷15《地官司徒第二下·泉府》,第1095-1098页。 (14)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4页。 (15)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1册,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16)李学勤:《兮甲盘与驹父盨》,人文杂志编辑部编印:《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西周史研究》,1984年印刷,第244-273页。 (17)孙诒让:《周礼正义》卷15《地官司徒第二下·泉府》,第1095-1098页。 (18)孙诒让:《周礼正义》卷15《地官司徒第二下·司市》,第1054-1059页。 (19)李学勤主编:《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20)[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7页。 (21)分别参见李学勤主编《尚书正义》,第173、189-191、267页。 (22)句华:《政治学视野中的政府信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23)[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8《僖公二·二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4页。 (24)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9《文公·元年》,第352页。 (25)[清]徐元诰:《国语集解·鲁语下第五》,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9页。 (26)第1759页。 (27)第1484页。 (28)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7《僖公七年》,第283页。 (29)《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第1487页。 (30)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40页。 (31)黄永堂译注:《国语全译》卷6《齐语》,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32)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566、873、1229页。 (33)[清]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卷10《僖公九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3页。 (34)徐元诰:《国语集解·鲁语上第四》,第148页。 (35)徐元诰:《国语集解·鲁语上第四》,第149页。 (36)《史记》卷39《晋世家》,第1653页。 (37)[清]焦循:《孟子正义》卷25《告子章句下·七章》,北京:中华书局1987版,第843页。 (38)徐元诰:《国语集解·齐语第六》,第240页。 (39)[清]黎翔凤:《管子校注》卷24《轻重丁第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74页。 (40)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四第十》,第357页。 (41)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四第十》,第353页。 (42)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2《春秋经二·僖公二十八年》,第63页。 (43)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8《传·僖公二十八年》,第337页。 (44)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8《传·僖公二十八年》,第337页。 (45)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11《传·成公十二年》,第465页。 (46)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15《传·昭公三年》,第649页。 (47)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14《传·襄公二十九年》,第609页。 (48)第2232-2233页。 (49)第1727页。 (50)阎步克:《春秋战国时期“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51)第235页。 (52)[英]汤因比著,林绿译:《历史研究》第6部《一统国家》,香港: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8年版,第550页。 (53)第2231页。 (54)《资治通鉴》卷2《周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7页。 (55)[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 (56)《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89页。 (57)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58)《秦简·法律答问》中有“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刑以上,令赎”。参见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第24页。 (5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6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01页。 (61)《史记》卷76《平原君列传》,第2370页。 (62)《史记》卷75《孟尝君列传》,第2360-2361页。 (63)孙诒让:《周礼正义》卷5《天官冢宰第一上·小宰》,第167页。 (64)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第181页。 (65)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7页。 (66)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第172页。 (67)《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2230页。 (68)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九年》,第971页。 (69)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年》,第1229页。 (70)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成公十六年》,第880页。 (7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9页。 (72)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卷10《公冶下》,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53页。 (73)程树德:《论语集释》卷4《为政下》,第126页。 (74)程树德:《论语集释》卷2《学而下》,第34页。 (75)程树德:《论语集释》卷2《学而下》,第36页。 (76)程树德:《论语集释》卷1《学而上》,第21页。 (77)程树德:《论语集释》卷24《颜渊上》,第837页。 (78)焦循:《孟子正义》卷11《滕文公章句上·四章》,第386页。 (79)焦循:《孟子正义》卷11《滕文公章句上·四章》,第386页。 (80)[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卷4《兼爱下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16页。 (81)孙诒让:《墨子间诂》卷1《修身第二》,第10页。 (82)孙诒让:《墨子间诂》卷2《尚贤上第八》,第49页。 (83)孙诒让:《墨子间诂》卷2《尚贤下第十》,第65页。 (84)孙诒让:《墨子间诂》卷3《尚同中第十二》,第79页。 (85)孙诒让:《墨子间诂》卷4《尚同下第十三》,第96页。 (86)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页。 (87)朱谦之:《老子校释》,第31-32、70、152页。 (88)[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渔父第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32页。 (89)郭庆藩:《庄子集释·大宗师第六》,第246页。 (90)钱穆:《庄子纂笺》,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221页。 (91)黎翔凤:《管子校注·形势解第六十四》,第1183-1184页。 (92)黎翔凤:《管子校注·揆度第七十八》,第1388页。 (93)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3《修权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页。 (94)[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11《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65页。 (95)[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7《王霸篇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2页。 (96)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1《强国篇第十六》,第305页。 (97)[秦]吕不韦撰,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集释》卷19《离俗览第七·为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4-5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