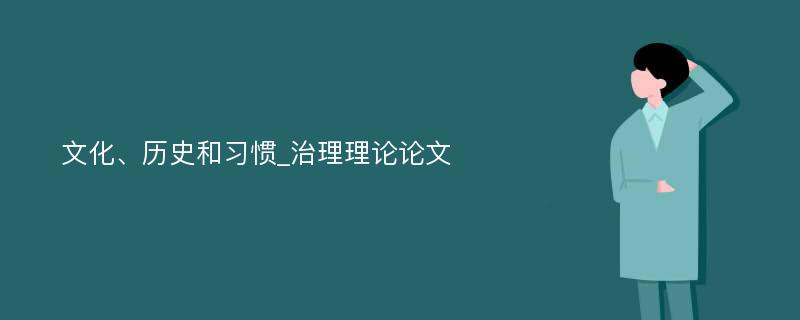
文化、历史与习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习性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在评论社会学文献的去习俗化时指出,“尽管习性①概念对于这种学科缔造者的概念纲要和理论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但令人费解的是,迄今为止,它一直没有得到社会学学者的重视。”[1](p.159)他可能也会同意,习性对于文化社会科学方面的一系列现代学科的基本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它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在把社会心理学既从心理学又从社会学区分开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也是一个贯穿现代美学史(从美学的市民人文主义起源开始一直到后现代表述)的概念。不过大量迹象表明,习性问题在近10年左右受到更为批评性的关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关于重复和差异的论述在这方面已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复活了柏格森(Bergson)曾区分过的习性与记忆的术语,努力构建一种关于独特性重复(repetition of singularities)的学说,这种独特性重复不同于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重复机械形式,他认为后者是由习性形成的。②在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的著述中表现出来的对这种术语复活的兴趣也有类似指向,因为他在对建议(suggestion)与模仿二者的关系在社会性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论述时,给予重复性实践重要地位。
后福柯主义关于自由治理的文献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特别注意作为一种机制的习性,因为它能够区分,一是应该在何处实行通过个体的自由渴望实现对个体统治的构想,二是,相反,应该在何处实行更为直截了当的统治形式。他们把习性对行为的控制看得非常重要,认为人格的决定层面完全干涉了能够进行自由实行和反思性判断的能力,而在强调习性成为自我统治的自动化形式的机制方面,也可以看出这种快照(shutters)已经注意到自由统治策略。③
鉴于这些考虑,我在这篇论文中意欲表明,与充斥在自由治理文献之中的假说相反,习性在人格建构中(或在与不同统治形式相应的统治个人的手段之中)并非总是占据同样的位置。我并没有把“人格结构”看做永久不变的心理结构,而是看做(用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的话说)一系列随着历史变化的“空间、洞穴(cavities)、关系与分隔(divisions)”,这是由于造成自我分裂的不同力量各种方式,与对这些碎片施加影响的各种方式相互叠合、相互作用而形成的。[2](p.301)我将审视后达尔文主义在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是如何改变习性在人格结构之中的地位(它们割裂了习性最初与习俗观念的联系,而将其与对本能的新理解联系起来),来展示这些问题,审视其后果。
首先,我将参照关于自由治理的讨论,因为这些讨论给予成为一系列社会文化学科的通货的习性足够关注,来更为充分地勾勒习性的地位。然后,我将审视皮特·里弗斯(Henry Pitt Rivers)将习性与本能相互区分开来的术语,并考虑他用以解释习性与本能的相互关系的方法,是如何与澳大利亚殖民统治实践牵连在一块的。最后,作为总结,我要讨论后达尔文主义对习性与本能的关系建构的替代选择,并讨论将习性与本能纠缠在一块,是如何有利于达成更为历史化的巧妙的自由治理实践的目的的。
习性与自由治理
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论述性格在19世纪中期的自由治理观念中所起的作用时,注意到关于习性观念的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就是,习性观念在调节欲望与冲动时发挥了作用,这种调节把主体形塑为静止而又变化的中心:“习性就深深地印在天性之中,但并非不能被意志力所动摇”[3](p.118)。他可能是在谈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例子,在穆勒《论自由》的文章中,自我观念是依据遗传的习俗分量和意志力的反对力量之间的对立而组织起来的,这种对立成为他在有历史社会和无历史社会之间所作的区分的基础,这种有历史社会是在柯施莱克(Koselleck)所用术语的意义上来谈的:即期望未来与现在和过去不同,这是主体行为迟早会引起变化的结果。就是在这种新暂存性与它所引起的对未来一定不同于过去(这是因为人的能动性在不断革新)的期望之中,习性成为须以新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在穆勒那里,这种须解决的问题是以下面二者之间对立的形式而呈现出来的:一方面是在自由民主中所发现的对自由和革新的激励,一方面是亚细亚社会和原始社会。穆勒把前者解释为通过改善与“东方专制主义”相应的习俗,从而已经超越了曾经的历史的社会(过去曾经在历史上非常活跃),相反,把原始社会解释为由于持续不断重复的半自然形式的力量,因而仍然没有进入历史的社会,这是因为它仍然逗留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难以察觉的过渡区的原始位置。
乔伊斯并不是唯一意识到习性对于自由治理问题的重要性的学者。玛丽安娜·瓦尔德(Mariana Valverde)也讨论过习性与专制倾向的密切联系,而专制倾向经常可以在自由治理之中看到。这一点也可以从对被殖民者的行为习惯模式的改善中看出来,那些统治者认为被殖民者缺乏意志力可以实行的自我结构。玛丽·普维(Mary Poovey)也说明了类似观念如何充斥在19世纪对缺乏技术的部分工人阶级进行治理的观点之中,这些工人被认为缺乏那些镜子似的道德形式,要依照斯密斯的著名的“意志人(man within)”④的模子而形塑,而如果习性对行为的控制,要通过使其面对反思性审视来松动的话,这种形塑是需要的。
就是通过这些方式,习性观念成为自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格结构的组成部分,这样就将个性纳入轨道之中,并将习性置于自我重新构形过程的中心,通过这种典型运作,自由治理的目标开始运转了。习性之所以位于这种过程的中心,正是因为,如果要摧毁习性的力量,只能(如乔伊斯指出的)用一系列其他习性替代它。如他指出的,“习性必定遭遇习性”[3](p.120),因为意志的实行必须既挑战习性,又努力输入一系列调节行为的新习性,如果不断自我革新的人格(人格能使自身保持稳定⑤)的理想要实现的话,这样通过主体的自由活动,社会可以继续得到进步。然而,如果习性在自由治理的话语与实践之中继续运转,它就很难以同一方式继续发挥作用。乔伊斯实际上谈到了这一点,他曾指出,在19世纪晚期,习性以新方式被观念化了,正如性格逐渐被观念化为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术语,而不是道德术语。例如,威廉斯·詹姆斯(Williams James)曾谈到,在1890年前后,习性已经成为一种“物质性法则”,刻记在大脑生理机能的运行之中。然而,在相关的变化之中,对于像穆勒那样的作家来说,习性常常等同于那些与习俗观念相联系的重复形式,而在生命科学的后达尔文主义发展那里所创立的自然/文化关系的新概念之中,(对于劳埃德·摩根[Lloyd Morgan]来说,)更多地成为要依据本能来考虑的事物,成了一种连接进神经系统之中的重复形式。
更多的是因为穆勒,在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处理习性的手段之中也充斥着类似的区分,他也把习性看做需要改变的障碍。涂尔干把社会行为划分成两极对立——一种是在习性影响下的重复行为形式,一种是自觉反思控制下的行为,对于他来说,重大挑战是当将社会行为带入自觉意识的控制之下时,要面对习性的力量。因为把习性看做自然的强大力量,要通过社会学对道德文明教育的影响来克服,所以社会学实践的社会作用是要使习性屈服于意志力与意识力量的调节作用。这并非如查尔斯·卡米克(Charles Camic)所强调的,是用无习性甚至新习性形成来替换习性的问题。所谓新习性,就是在自我控制意识的最佳形式影响下行动的习性,来取代本能的或机械的习性,而这种自我控制意识是在讨论过程中形成的。然而,涂尔干的习性实践使命实现的代价是将其排斥在社会学理论区域之外。他把习性接纳进心理学学科之中,以便于研究植根于人类动物性的生理结构之中的行为形式,卡米克指出,涂尔干标出了社会学学科化、自主化的要求,只关注道德因素和观念因素(即意识)在社会行为组织化之中的作用。⑥
韦伯的著述尽管与卡米克的截然不同,但也有类似指向。他认识到习性力量是传统形式的社会组织化的钝性资源,在其“习惯”(habitus)概念中,他揭示了习惯(它完全是由传统形成的)和习惯的某种动态形式之间的差异。习惯的动态形式是在日常生活的静态习性中形成的,从而推动习惯步入那种动态过程,这是终结历史必需的(在Kosselek的意义上)。而且,韦伯也显示类似于涂尔干所关切的,努力为社会学在德国高校系统中获得一种特殊位置,他强调了文化在构成有意义行为场域方面的作用,将其作为社会学的真正问题,这样就把真正习性引入心理学之中,而习性行为尚未受到表征、意识和意志力调节的影响。
卡米克继续指明帕森斯(Parsons)对习性的论述在美国社会学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他也指出,他在欧洲社会学中并非那么重要。这里最明显的例外是皮埃尔·布尔迪厄,他的关于习惯的论述吸取了胡塞尔和梅洛·庞蒂所倡导的尽管是现象学传统但也可以是哲学社会学的表述,当然还有莫斯(Mauss)的遗产,继续在韦伯著述的轨道上将习俗机制与习性机制区分开来。布尔迪厄在回溯性表述之中,坚持“在古代社会和现在社会,社会代理人并非像时钟一样遵循他们并不理解的规则,被自动地调节”[4](p.9),他们将习惯融入通过经验获得并重塑的倾向性能力。在据说可能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论述习惯的著作《区分》中,习惯的这种特点并没有平均分布,一些习惯(如他归之于工人阶级的显著习惯),就具有植根于必要选择的习性的所有特点。⑦习性也在日常生活社会学的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从乔治·卢卡奇开始到亨利·列斐伏尔,不过在这方面,它被看做对立形式之中的负面因素,即一方面是社会行为完全规则化的、非反思性的重复形式,另一方面,是授予一些团体洞穿日常生活的物化表面而获得超常卓异的非凡因素的能力,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社会革命行动的自觉代理人。
这种文献与平行发展的(将感知和注意的自动形式陌生化或去习惯化的)现代主义美学对习性的否定性编码之间也有着重要联系。显而易见,这也适用于俄国形式主义将感知的习惯模式陌生化或去习惯化在革新文学系统之中的作用的论述。不过,这也同样适用于现代主义的先锋派对陌生化或去习惯化的作用的构想,他们的第一代在19世纪晚期法国的已经自动化的文学艺术场中,运用了一系列陌生化手段,打破了早期惯例化的文学形式,在布尔迪厄对他们的论述中,去习惯化机制占有重要地位。
我出于两个原因注意到现代美学与日常生活社会学对习性的理解的联系。第一,它是一条非常有用的途径,来强调在现代美学和现代社会理论的漫长历史中,习性得以表征的术语之间的紧密联系。第二,它提供了一种手段,便于回到我刚才关于习性与自由治理的话语实践之间关系的评论。鉴于现代美学与自由治理的问题式的早期表述的关系,所以现代美学成了一个平台,使习性本身(即习性被理解为无思想重复而不是任何特殊习性)第一次出现并成为一个问题。这里重要的人物是沙夫兹伯里(Shaftesbury),因为他的关于美丽的礼貌话语给政治权威奠定了基础,这种政治权威既不依赖神圣权利,也不依赖霍布斯式的强权,而且其目标更多的是,为了治理成所有人都分享(尽管相互之间保持相当距离)他们自己的政府。关于品味与判断力问题的礼貌话语要通过自我表面分裂转换成自我治理的内部机制,沙夫兹伯里实现的手段是将社交谈话的对话层面转换成一种手段,这样,自我和自己对话(或自我调节),从而使许多部分达成和谐。⑧
然而,在许多其他限制当中,这种经由自我多重组织化达到自我治理的能力,在其社会分布状况中也受到限制。沙夫兹伯里(作为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已经指出的一个话语范例)在从马克思到布尔迪厄的现代社会政治思想的随后发展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排斥了“乡巴佬”、朴实的手艺人和底层民众[5](p.7)以及更为普遍的机械师,理由是,他们的职业规则和习性本质耽搁了他们发展成这种多重自我。这样,市民人文主义的审美政治话语就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造成了一种对立,那些统治者有资格参加集体自我统治政党,因为他们能够反思性监控和调节自己的行为,而那些被统治者囿于习性,注定遭到更会反思的统治者的统治。
这使我不得不在此更为详细地说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的现代自我范式构建中,是如何尽力把市民人文主义范畴转变为他所给予审美判断的角色。⑨但是,在康德看来,习性和文化对于他所心仪的自我特殊层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文化,才能生产出无论选择什么,都没有倾向性的理性存在,才能生产出那种心仪存在自由的倾向性”[6](p.389)。同样,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指出,文化的对立面是习性:
然而,习性是一种身体内部的被迫性,使人以同一方式行进(迄今为止人们一直以这种方式行进)。它甚至剥夺了人们的可贵道德的良好行动,因为它削弱了心灵的自由,而且导致了不假思索的完全相同行为(单调)的重复,因此显得荒唐可笑……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有另类习性激起丑恶欲望,那是因为,人的动物性跳出来太多了,其行为是由习性规则导致的本能行为,完全像另一种自然(非人)一样,因此就会有完全堕入兽类之虞。[7](p.40)
习性在这里就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敏感区运转,被安置在自然/动物与文化/人二者之间对立的交界点之处,这在拉图尔(Latour)对现代社区的论述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从这种非常简要的勾勒中,也可以看出习性在现代社会理论、政治理论、美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而且不止如此,它一直横跨了这些不同的理论体系,成了一个重要的连接性术语,从而使它们对治理实践和手段的关注聚集起来,凝聚成一系列对立:自然/文化,必然性/自由,这样就将包含自由治理与排斥自由治理二者组织起来了。而且,也有大量迹象表明,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正如利萨·阿德金斯(Lisa Adkins)和贝弗·斯基茨(Bev Skeggs)二人已经指出的,关于反思性自我的叠合组织化(乌尔里希·贝克[Ulrick 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将其视为“高级现代性”的特征)的论述,对于现在的当代阶层化话语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运转侮辱了那些所谓的缺乏这种叠层化自我所需的反思性自我调控能力的阶层。更概括地说,这种观点只不过是罗斯所概括的社会学的基础性的“历史虚构”重新表演而已,在由一条长期单一线路所支配的只能如此的故事中,行为模式被束缚于传统和共同体的力量,屈服于个体性和自治的现代实践,这条单一线路尽管或发达或滞后,却都是从固定性发展到不稳定性,从习性发展到反思性,横跨了所有的生存与经验的领域[2](p.304)。
然而,我在这里更为注意的是,习性思想通过标出如下二者之间的对立,来确定自己在时间关系的差异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能够自由地自我构建的社会,另一方面,是注定以过去/现在的区分形式无休止地重复的社会,它形成了扁平、简单和机械的个性的“古老”或“原始”形式的重复结构。我在这里主要想表明,必须密切注意这种过去/现在区分得以表达的不同方式,这种表达依据的是给予习性在个性结构之中位置的变动结构。
习性、本能与竞争存活(survivals)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现在让我转到英国人类学中的达尔文主义与后达尔文主义的争论之中的习性与本能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主要参照19世纪晚期的进化人类学的问题式之中的适者生存法则来探讨习性与本能所起的作用,尽管我也会叙述在政治理论与生命科学之中的相关争论。不过,我要从一系列出版于1844年的《关于土著与澳大利亚殖民的文件》的英国议会文件开始。我引用的文件来自洛德·史坦利(Lord Stanley[他是殖民办公室的政府首脑])写给新南威尔士殖民总督乔治·吉普斯爵士(Sir George Gipps)的信件,是关于吉普斯转交的格雷上尉报告的信件,格雷在报告中,讲述了他作为探险队队长在澳大利亚内陆的经验,讲述了试图将土著文明化的徒劳行动,强调了这种企图是毫无希望的。史坦利评论道:
我极为认真地拜读了这些快报,为那些让人沉重压抑的经历深表遗憾。考虑到这种使命所面临的匪夷所思的困难,似乎难以否认,迄今为止所做的文明化土著的努力一直是徒劳无功的,仍然没有实现实质性的进步,也没有合乎理智的理由期望他们在未来获得更大成功。阁下一定会理解我是多么痛苦、多么不情愿地得出这个观点,但是我不能对议员们必然会对您给我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作出的结论装作不知。[8](p.120)
但是,他又继续表示,尽管非常勉强,但保留土著还是可以改善的希望要比另一种选择,即已经广为讨论的观点更好:
我还是更愿意相信,可以做一点事情;我并不认为给他们一点关怀,基督教义就一定不会生效,我也不认为,文明化的益处是不可交流的。我并不能在理论上默许:他们是不能改善提高的,在白人殖民者的先进发达面前,他们的灭亡是必然的,是不可控制的。[8](pp.120-121)
凯·安德森(Kay Anderson)在《种族与人文主义危机》中,把这些文件视作对18世纪四五十年代这段时期的表征。在这段时期,殖民话语在两方面之间维持着平衡,一方面,是18世纪基督救世主义话语的遗产和启蒙运动阶段理论的现世改良主义,它们相信,尽管采用不同手段,澳大利亚土著是可以改善提高的。另一方面,是19世纪晚期的更为典型的种族话语。这些种族话语坚信种族特征根深蒂固地植根于身体之中,它们将土著从基督救世时代和文明化的进步时代迁移出来,认为土著是劣等种族,在生存竞争中无可避免地会走向灭亡,从而将其置于灭绝的死亡时代。然而,对于安德森来说,这里更为危险的是一系列具体殖民实践。她是从后人类视角来写作的,这种视角是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其他人在挑战那些将人与自然世界区分开来的二元本体论的著述中提出来的。安德森指出,澳大利亚土著引发了一种表征危机,搞乱了这种本体论术语。她将美洲野蛮人被启蒙运动的推测性的、阶段性的历史所同化的方式与突如其来的挑战进行了比较与对照,这种突如其来的挑战就是,18世纪晚期太平洋航海家和随后的澳大利亚殖民者提出的这种历史,他们发现了一类显然难以改善(正如经验所表明的)和难以提高的人,他们似乎如此稳定地徘徊在自然/文化的分界线的入口处,这就冲击和置疑了原来的二元本体论。
安德森指出,这种紊乱紧张得以解决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把种族差异自然化。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这种方式最初采取了多基因发展学说的形式,这种学说将种族差异解释成不同发展线路的结果,这对基督教和启蒙运动的人类整体论构成了挑战。安德森表明,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开拓了一个空间,可以通过否认种族差异是天生的、不可逾越的方式,把土著放在文明化工程之中,但是,人类学的随后发展依然将土著置于这种工程所能触及之外,将他们划拨到史前史范畴所表征的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新历史过渡区。作为过去在目前的存活(survivals),土著面对的困难不是被认为天生不同,而是被认为太落后于时代,仍然位于从自然进入文化的入口处,他们表征了人类进化的零度发展,这意味着他们远远没有达到穿越进化时代的漫长时期,这将他们与殖民者所处的正确历史时代分离开来,而种族竞争的必要性就导致了他们的灭绝。
现在看来,一切都合乎逻辑,然而,我想指出,要充分理解在这里运转的独特动力,就需要理解,这种把土著视为残存(survivals)的构建,是如何成为对早期关于习性与本能的关系更为公允论述的重构的。因为如果将这两种构建相互分离,适者生存法则就把个性置于人格构形的完全不同的辩证过程之中,这种辩证过程就是从那种康德之后发展起来的习性与本能倾向缠绕成一对的人格,到文化力量(被视为自由地自我形塑的能力,可以推动历史的发展)所坚决反对的人格。桑克·穆图(Sankar Muthu)指责康德道:“他所构建的阻挠人性的动物性,实际上是由本能驱动的。从动物性到人性的运动是一种通向自由与文化的运动”[9](p.128)。正是这种对立为文化制度行动奠定了人格的动力,而文化制度在其经典的19世纪形式中,被塑造为削弱习性对人类行为影响的实践。传统、习俗、习性习惯,这些在后康德主义的文化观念中,都是“能够实现我们的充分人性之前要去克服的对手”[10](p.16)。这样,文化就发动了一种审视过程,使个人将他们自己从沦陷于前反思或不思考的行为习性模式中解救出来,而发动自由自我的构建过程。
在维多利亚晚期的人类学中所说的人格结构,与此截然不同。第一,它把人格设想为一系列历史化的渐变阶段(即,不是对立形式而是上升形式);第二,它不是把本能解释为与文化对立的纯自然,而是作为自觉行动的储存库,它通过习性的调节作用而步入本能的自动化形式。对于土著来说,其后果是一种矛盾悖论,一方面,认为他们没有丰厚的可以文明化的本能储存。另一方面,认为土著处在从自然过渡到文化的入口处,所以其行为是由一系列原始本能引导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本能作为从未完成的自然向文化过渡的残存,在千年的干预中一直重复着,因此其力量得到了加强,这样它们现在多多少少有点像钢铁一样控制、束缚着行为。这种逻辑在皮特·里弗斯关于人类学收藏原因的论述中是显而易见的。他遵循着达尔文对习性和精神性力量在人与低等动物中所起作用的论述,将动物与人类身上的习性与本能的关系视为本质上受到同一原则支配。就像动物要么通过豢养要么通过经验理性形成本能习性并遗传给下一代一样,类似过程也发生在“智性思维”和“自动思维”在调节人类行为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之间的关系之中。
我们知道智性思维可以对不熟悉的情况作出理性反应,而自动思维可以直觉地对特定情况作出反应,不需要意志和意识的努力。然而我们也知道,习性通过有意识理性的运行而获得,而不变的习性就成了自动化,那么就不再需要开动意识理性指导行动,就像它们最初所做的那样……[11](p.296)
皮特·里弗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每个由本能引发的行动,在一些物种历史上的先前阶段都是自觉经验的结果”[11](p.298)。这种观念成了(动物和人的)发展机制的组成部分,认为更多的源于经验的简单思想被传递形成本能的自动化形式,就可以更自由地对新的和复杂的思想作出反应。⑩在这种机制中关键点就是习性,皮特·里弗斯将其视做一种包含了智性思维有意识理解的形式,但是,它由于通过重复而成为惯例了。就是通过习性,经验教训由于一种储存逻辑被转变成本能,这种储存逻辑是,由习性到本能的循环完成之后就为另一种循环敞开了空间,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逐渐成熟的本能反应,构成了自动思维。同样,习性控制着行为,如穆勒所说的习俗控制着行为一样,尽管这种抑制力量得以运行的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对于穆勒以至于康德而言,本能等同于人的自然性的动物成分,这种力量可以既在人又在豢养动物身上得到校正,但并非社会行为的先前学习形式积累形成的倾向性。[12](p.561)
殖民圈套在论证结尾大煞风景地出现了,皮特·里弗斯指出,“自动化倾向根据任何既定系列观念来行动的能力,必定与个体祖先为了那些具体观念而进行思维的时代长度是相应的”[11](p.299)。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低等动物要比高等动物更倾向于自动化的行为形式;因为其本能还没有纠正到与那些高等动物相同的程度,所以它们实践着同一套自动反应的时间就会更长,相应地,本能对行为的控制就增长了。土著的位置大体而言是相同的,因为把他们永远定位在自然/文化对立的入口处,所以他们就从不会超越简单模仿自然的形式,不会出于一定目的调整这些行为(皮特·里弗斯用这些术语论述石器工具的发展),这些行为一直重复沿袭了好多代。因此,“与这种观念联合持续存在于这种生物(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人)的连续数代的头脑中的时代长度相应,总会有一部分后裔倾向于继续选择使用这些特定形式,这多多少少出于本能——事实上,不是出于那种永恒本能(它是由于动物内部机能为了更好地适应外部条件而逐渐形成的),而是出于纠正过的本能,这种本能呈现了一种永不变更的保守僵硬形式”[11](p.300)。对于未开化人尤其是(以皮特·里弗斯的野蛮人范畴而言)土著来说,问题在于,习性机制不能以充分活力来构建“纠正过的本能”的储存库,它仍然非常微弱稀薄,只能达到对行为的格外束缚与控制,这是数千年来的无休止重复造成的。
作为坐在摇椅里的人类学家,尽管皮特·里弗斯的写作与殖民统治的即时性还保持着一段距离,但显而易见,这些表述在19世纪晚期的澳大利亚引起反响。帕特里克·沃尔弗(Patrick Wolfe)在其关于殖民主义逻辑的精彩的探索性著述中提醒我们,最好把这种逻辑看做一种结构而不是一个事件,这种结构在不同历史时刻采取了不同形式。因为殖民主义的主要目标不是剥夺土著的劳动剩余产品,而是占有土著的土地,因此其逻辑就是灭绝土著人口。沃尔弗指出,就澳大利亚而言,这种结构呈现了三种不同形式:边界冲突形式目标在于灭绝殖民人口;通过进化规则和不可避免屈服于优等民族的监禁形式的手段而推迟土著的灭绝;通过管理方案的传播和与白人的文化合并而将其融化吸收。不难理解皮特·里弗斯关于习性在土著人身上所发挥的作用的论述如何与第二种灭绝策略相关,第二种灭绝策略在19世纪末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也波及了20世纪初期。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它也渐渐让位于当时语境下的融化策略,那时民族政府工程得到发展,蒂姆·洛斯(Tim Rowse)称之为“土著领地”(其目标在于将土著人口合并于国家之中)的联盟形态得到了发展。(11)
更为深入的分析
在后达尔文主义的人类学与生物学之中,有许多其他模式显示了进化观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体现在当代的关于不同人性级别之间关系的争论之中。一些是在类似于皮特·里弗斯所论述的相同领域之中,另一些情况在其表述中要更为简约。哈登(Alfred Court Haddon)利用了他在Torres Strait岛所做的田野调查,费尽心思讲述了一个完全以达尔文主义术语编织的进化故事,并认为这是物竞天择所调节的没有计划的竞化结果。这样,就把他所设计的品质进化看成令人失望的习性结果(菲利浦·斯蒂德曼[Philip Steadman]称之为“不精确复制”),这样就可以将其描述为“就人类整体智力而言,它是完全没有引导的操作”[13](p.318)。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关于“文明化连接问题”的论述,在穆勒对习俗控制的论述和达尔文著述之间铸造一种联系方面也产生了同样影响。对于白芝浩来说,习性获得是通过社会训练、通过达尔文式的变化机制的运行,有选择地遗传给下一代的“遗传技艺形式”,并以某种方式嵌入神经系统,成为能力的储存库,使其有可能推动社会进化。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什么原因,如果这种情况并不发生,社会就不能生成变化,因而就不能提供一系列进化选择,不能挑选性地从一代遗传到下一代。白芝浩在此接着穆勒表明,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社会处在专制主义控制之下,因为专制主义摧毁了讨论的民主原则,而这种民主原则是变化得以导成一种政体的主要机制。这些关注所引起的回响可以在鲍德温·斯潘塞(Baldwin Spencer)所使用的术语中听到(他是一位曼彻斯特自由家庭的儿子,并不墨守成规),他在古典自由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思想方面都受过很好训练,他用这些术语描绘他在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居民阿兰达人(12)中间的遭遇:
如在所有的未开化部落一样,澳大利亚土著的习俗注定了他们只能使用手和脚。他必须做父辈在他之前所做的事情。如果在一场仪式表演中,其先辈在前额上涂了一条白线,那么他必须涂一条白线。在一定范围内,任何对习俗的违背,肯定都会遭到经常是严厉的惩罚。然而,尽管土著非常苛严保守固执,仍然有可能将变化引入。[14]
斯潘塞为了说明这种变化如何到来,他引用了讨论原则,不过他是以一种既解释变化如何能够发生(它是由对不同的地方性集群相遇时发生的不同行事方式的讨论激发的)又解释同时这种变化是有限的(在穆勒和白芝浩所倡导的作为促进变化的必要条件的风尚之后,这些讨论并不是平等的自由讨论,而是由男性长者权威支配的,结果是,变化只有在那些长者认可的保守有限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方式做到的。
论述也无疑吸收了罗马尼斯(Romanes)—赫胥黎(Huxley)的传统,这种传统偏离了新拉马克主义(neo-Lamarckian)关于习得特征遗传的论述,也偏离了达尔文自己关于泛生论机制的晦涩说明,并将文化发展机制与自然进化机制脱离开来。这种习性进化观和习性与本能的关系在劳埃德·摩根(Lloyd Morgan)的《习性与本能》这个文本中得到严格贯彻。摩根依据达尔文把本能和习性解释为既是人又是动物的行为要素,把本能界定为“人的并非有意识推理过程形成的性格和行为的组成部分”[15](p.2),把习性界定为“多多少少是既定的程序或行为模式,它通过重复由个体获得,可以说已经成为惯例”[15](p.1)。他所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习性的第二次自动作用是否由遗传传递,以至于导致了本能的最初自动作用”[15](p.325)。但是与皮特·里弗斯和白芝浩不同,摩根否认它们之间存在什么联系。他指出,“种族进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进化已经从机体转移到环境。作为进化的必要条件的增长物,通过在社会环境之中储存而出现,因此,每一个新一代以跨代增长的形式调整着自身,但是并不需要任何增强的作为本能的天生适应能力:
在书写记录中,在社会传统中,在各种各样使科学和工业进步成为可能的发明中,在艺术品中,在所记录的高贵生活的典范之中,我们拥有一个环境,它同时也是智力进化的产物,并提供了目前的每个个体心灵发展的条件。[15](p.340)
就行为调节而言,这种情况的主要后果是,将注意力从白芝浩和皮特·里弗斯所关注的习性/本能的关系,转向取而代之的文化(已经储存在社会环境之中)与习性的联系。那么,这里又要回到康德所提出的文化与习俗之间对立的术语,这种回归在赫胥黎的《进化与道德》中是明确的,尽管这种回归仍然深深打上进化论思想所塑形的进化人格新历史深度的烙印。这种在对竞争和殖民的反对中(摩根将这种反对作为其论说的一般逻辑)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它最后与其立场的后果相对时,他又回避接受,出生在文明化国度的孩子与出生在野蛮或未开化国度的孩子之间的唯一不同,是储存在社会环境之间的精神氛围,而不是任何遗传的自然习性。在这种“局限情况”之中,依然存在种族差异,植根于仍然进行的物竞天择过程之中,在野蛮人可以进入真正的智性和文化进化的阶段之前,物竞天择仍旧必然折腾消耗他们。
然而,我在这里不只是把上述内容标成需要更加深入研究的问题。我的更为普遍的目的一直是要建议一些研究途径,使“文化、历史与习性”和自由治理实践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敞开,以便于进行更加多样的历史分析。我特别主张,尤其是当把上述二者的关系与瓦尔德(Valverde)的习俗与专制主义的关系进行比较时(专制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被引用来作为自由治理的替代物),要特别重视研究把不同人格结构中的习性操作成治理行为目标的多种手段。如果说,在穆勒的分析中,对亚细亚社会的静止状态的论说是依据习俗的丰厚度来进行的,那么,皮特·里弗斯引用的说明“原始”社会惰性的就是本能的浅薄度。因为依赖于习性如何依据习俗或本能来定位,依赖于习性即习俗或习性即本能如何依据文化来定位,所以,不同类型的人格就被以不同方式向治理干预敞开。
①在英语原文中有三个相近的单词:habit,habitus和custom。考察托尼在文章中的用法,habit偏重于个体的心理结构,暂译为习性,而habitus偏重于个体的无意识的自动化行为,暂译为习惯,而custom偏重于社会意义上的习惯规则,暂译为习俗。——译者注
②Bergson distinguishes two kinds of memory,one of which,purely automatic,carried in the motor mechanisms of the body,"has all the marks of a habit" while the second,formed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conscious representation,"has none of the marks of a habit".(Bergson,2004:89-90)The first,as Bergson further glosses this distinction,"follows the direction of nature",while the second "would rather go the contrary way".(102)
③For an extremely useful introduction to these concerns,see the special issue of Economy and Society(36[4],2007)on the work of Tarde edited by Andrew Barry and Nigel Thrift.
④This concept is elaborated in Smith's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Smith,2002).See,as well as Poovey,Brown(1994,1997)for a discussion of the operation of this concept in Smith's work.
⑤This concern with the rote of habit in stabilising the person is particular clear in Mill's account of ethology; see Mill(1967).
⑥This is also,for Geras(1976),the move that most distinguishes classical sociology from Marxism.
⑦See Bennett(2007)for a discussion of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this occasions.
⑧I draw here on the discussions of Shaftesbury and the more general formulations of civic humanist aesthetics in Barrell(1986),Paulson(1996),and Poovey(1994,1994a,1998).
⑨But see,for two of the most pointed engagements with these issues,Caygil(1989)and Deleuze(1984).
⑩A similar account had been proposed by Felix Ravaisson(2008)earli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With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at Ravaisson did not historicise or racialis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s possessing thick or thin stocks of instinct in the manner proposed by Pitt-Rivers.
(11)See Bennett(2004)for a fuller discussion of these questions.
(12)I follow convention here in using Spencer's spelling rather than using the corrected form of the Arrernte,since my concern is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is category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centric discour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