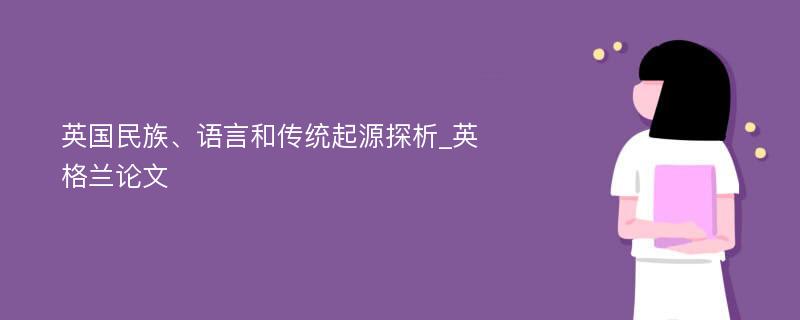
英格兰的种族、语言和传统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格兰论文,种族论文,传统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伦三岛面积仅24万平方公里,却曾占据比其本土大150 倍的殖民地,它是上个世纪的世界中心,从工业革命到足球,英国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尽管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英国国力相对收缩,但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在世界史学界,人们对英格兰——这个被称为原生型的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研究,抱有经久不衰的热情。就中关于英格兰的种族、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起源问题,即是英国史中令人感兴趣的议题之一,本文试图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师长与同仁。
一 英国人的最早祖先
关于英格兰的种族来源,很久以来就存在着争议,这种争议最早可追溯到罗马帝国征服高卢、继而征服不列颠时期。
罗马人入侵不列颠岛后,遭到当地岛民的顽强抵抗,岛民在战场上森然可怖的外表,给凯撒军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佩带克尔特人的长剑,并不穿护身的盔甲,凯撒讲述到,“所有布立吞人都用一种蓝色的大青涂染身体,……他们蓄长发,除了头和上唇之外,他们把全身上下都剃刮干净”。据载,凯撒军队还遭遇过当地妇女率领部落军队的抵抗,显然,在公共生活中一些妇女是很杰出的人物,然而在家庭生活中,一夫一妻制似乎还没有形成,凯撒写道,妻子们通常由10至12个一群的男人所共有,包括由父辈与子辈所共有。罗马人所遭遇的不列颠人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究竟是不是该岛上的最早的居民?凯撒提出质疑,却没有结论。
一个世纪以后出生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此仍持怀疑态度:“谁是不列颠的最早居民?他们是土著人民还是移民?这始终不清楚。”接着,他又以一种高傲的口吻补充说:“必须记住,我们正在跟野蛮人打交道。”〔1〕
后来的人们,主要是近代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英国的祖先最早来自欧洲大陆。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的动力要么来自人群的移动,要么来自艺术和技术转移,即不同文化的接触。由于不列颠是个岛,它早期历史的动力必定是迁徙。迁徙带来文明,也确定了不列颠最早的主人。例如,戈登·蔡尔德在《不列颠群岛的史前社会》(1940年出版)一书中认为,新石器时代不列颠地区家畜和庄稼的出现,肯定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曾发生“入侵”的结果。按他的说法,野蛮欧洲的开化是被“东方文明”启动的,虽然不列颠处于文明开化过程的边缘地带,但由于拥有出海口和半岛,对于外地人进入是有吸引力的,于是,文明通过欧洲大陆传入不列颠。
“迁徙说”一度具有广泛的影响,但随着考古学家对越来越多来自不列颠材料的系统研究,通过一个一个遗址、一个一个地区的实地勘查,人们对不列颠最早的居民有了新的看法。
1935年,在离伦敦20英里、泰晤士河南岸的斯旺斯孔布村的茅坑中,发现一个20—25岁的女性头骨化石。这是已知的英国最早的人骨化石,据信属于25万年前结束的霍克斯尼安冰河期。斯旺斯孔布人的脑容量为1275—1325c·c,属于现代人脑容量范围。其脑壁比北京猿人要薄,从印在顶骨内壁中部脑膜脉管的类型看,比北京猿人复杂,所以比北京猿人的年代要晚,大约属于直立猿人到早期智人的过渡阶段。这次考古发掘中,还发现被火烧过的燧石和一些木炭,以及一根用火烧制成的木矛,这是已知欧洲最早的用火证据。以后,类似的遗址和旧石器晚期以及中石器时期的遗址不断发掘出来,这些发现,把不列颠居民远古时期的信史大大提前了。
需要指出的是,不列颠最早居民的历史,与欧洲大陆不断移民并不断与之融合的历史很难分开。在第四纪冰期以前,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本是联在一块的,当时就有成群结队的猎人为了追逐猎物而跨过当时尚未沉入水中的大陆架地带,来到水草茂盛的如今称之为英格兰的地方。迁徙,以及移民与土著的融合,往往以战争和征服为先导,所以,远古时代照样存在暴力。在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西南部一个长长的坟堆里,发现一具成年人的骷髅,在他的一侧,有一枚树叶形状的燧石箭头。在科茨沃尔兹边境上的维奇伍德森林中,有一座长房子样子的坟墓,其中一个埋葬者是被箭射死的,箭头从下方穿透右肋,嵌在脊骨中。〔2〕可见,石器不仅用于劳动,也用于征服。这种迁徙与征服的过程,延绵不绝,但由于年代久远,面目模糊,我们所知甚少,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来临,人们才获得更为可靠的线索。
不列颠的新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伊比利亚人的迁入。在许多教科书里,伊比利亚人被认为是不列颠群岛的最早居民,其血统是构成该岛现有居民的一个重要成分,在爱尔兰、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尤其如此。这批来自地中海的拓荒者,是一种身材短小、皮肤稍黑、头颅狭长的人种,他们可能来自克里特岛。当第一批地中海移民横渡狭窄的海峡登陆后,立即发现这里和他们刚刚离开的欧洲大陆并无两样。那时,不列颠低地大都长满了潮湿的橡树林——橡树、榛树和多刺的小树,到处都是荆棘。卑湿的山谷往往被水浸没。大部分较为干燥的地区也都长着高大的橡树、槐树、山毛榉、赤杨和扁柏,这一切都难以用石斧来消除。伊比利亚人所以大多定居在该岛南端的丘陵岗地上,并非因为那里最为富饶,而是因为白垩质丘原上林木比较稀疏,就其运用的开垦工具而言,这是他们所能选择的最佳之地。
按照经济史学家的意见,伊比利亚人的开拓业绩,“带来了所谓新石器时代的经济革命”〔3〕,除了武器和工具有所变化外,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至今屹立在英格兰南部萨尔斯巴利平原上的巨大石柱群(Stone henge,又可音译为“斯通亨治”)。这种石柱群已发现80处以上,多数建在低地靠近河水的地方,考古学家称之为“巨石文化” ( Big Stone Civilization),他们通过这些大石块建成的纪念物,追溯这种文化的内涵和传播情形。例如,G·S·霍金斯的《巨石群谜解》一书,对某个遗址的布局和方位进行仔细研究,而后提出:它的建造者的实际兴趣,显然在于测量时间和预测季节的转换。〔4〕
二 从克尔特人到诺曼征服
然而,给古代英国打上更深烙印的是来自欧洲西部的有着高身材、金头发的克尔特人。公元前700年以后, 克尔特人各部落分三批先后移入不列颠,其中一支称“不列吞”部,不列颠这个名称大约即来源于此。克尔特人开始使用铁器,并且使用耕牛。虽然不很普遍,却使他们有能力开始砍伐森林,疏干池沼,经营粗陋的农业。在克尔特时期末叶,出现了由4头或8头牛组成的犁队。〔5〕虽则潮湿的橡树林仍未开辟, 然而居住区移向河谷的运动却始于此时。克尔特征服者在不同的区域,与先来的伊比利亚人有不同程度的混合。西部的主要种族仍是伊比利亚人,不过克尔特人已能强迫不列颠岛的大部分地区接受他们的部落组织,其政治和文化影响达于全境。
在克尔特人统治全岛若干世纪后,公元43—407年期间, 发生了罗马人的入侵和征服。表面上,不列颠被划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直接受罗马总督统治;实际上,由于克尔特人的抵抗,罗马人始终未能控制全境,特别是北部高地地区。为了阻止不列颠人南下袭击,罗马于公元2世纪初年修筑了一条从西海岸的卡莱尔到东海岸的泰恩河口的城墙,共118公里。因当时正是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统治时代, 故称这道长城为哈德良长城,又名罗马长城。为了便于统治和军事行动,罗马人在岛的南部建筑了许多大道,把他们居住的城市和别墅联结沟通。长城以北,罗马人的占领是间或的,偶然的;长城以南情形就不同了,罗马风俗和拉丁语言对这一地区有相当的影响,特别在罗马大道上兴起的城市里,尤为明显。文学、法学以及军队和后来教会所用的语言都是拉丁文,市民多能用拉丁文读或写,当时留下的金石铭文全都是拉丁文。不列颠的上层社会已近完全罗马化,从克尔特的部落酋长变为罗马地主和官吏。当然,罗马人最大的影响是基督教的输入,3 世纪时基督教在英国已形成一定力量,其势力范围不仅局限于罗马统治区。总起来看,罗马对不列颠的影响,从区域上主要在长城以南,尤其在城市地区;从形式上主要表现在文化和语言上,而非血缘上,虽然作为统治者的罗马军人也有娶不列颠人为妻的,但那只是局部甚或个别现象。
英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与罗马人遭遇的那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后来被概称为克尔特文化。克尔特文化及克尔特语言对英国有很深的影响。16和17世纪,学者们推断出:威尔士语源于曾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定居的古代克尔特人的语言。 而威尔士语直至20世纪仍在威尔士一些地区流行。实际上, 今天英国的许多河流都是以克尔特语命名的,诸如艾尔河、阿冯河、迪河、德尔文特河、默西河、塞文河和泰晤士河。还有像撒奈特、克拉文和怀特岛这些地方,其名称也都源于克尔特语。利兹是用克尔特语命名的最大的英国城市。不过克尔特语进入英语的词汇如“ass”(驴子)等,却寥寥无几。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在英国的传统中具有一种古老的克尔特情调,如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A·L·罗斯即指出:“19世纪的史学家们惯于把我们看作盎格鲁——撒克逊人,其实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盎格鲁——克尔特人。”
现代英国人的直接祖先,主要是来自西欧大陆的日耳曼人,其中大部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时间大概在公元5世纪中叶, 当时罗马人已撤离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则是当时欧洲民族大迁徙运动的一部分。登上不列颠岛的新的入侵者,大部分来自日耳曼最落后、最原始的部落,原住在易北河口临近海岸的地区和丹麦南部地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本是不同的部落,但都使用英吉利文,风俗上也极相似,两部落之间是否有真正的区别,现在还是疑问。他们远离罗马文明,野蛮好斗,而且装备不错,所谓“撒克逊人”通俗的含义大概就是“佩带长刀的人”;他们携带的其他器具和船只也比较充分。另一支进入不列颠岛的日耳曼人,来自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部落,被称为朱特人。他们在不列颠岛南部肯特郡登陆,肯特实为朱特的变音。朱特人以前曾和罗马文明有过接触,这是肯特郡在整个中世纪都保持与英国其他地区不同特征的原因之一。肯特郡与英格兰其他地区确有不同的社会史,那里不少社区是由小规模的个体农业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农业的。
由于不列颠人的抵抗,日耳曼人的征服过程大约持续了150年。 英国全境惨遭蹂躏,一切残余的罗马文明都遭受毁灭性打击(当然,不能说拉丁文化的影响完全突然泯灭,借以珍藏这种文化的基督教亦是如此)。不列颠人不是被杀戮,就是沦为奴隶,或者被挤到北部、西部山区。但是,大部分不列颠人还是同入侵者融合,形成后来的英格兰人, England一词原意就是盎格鲁人居住的地方。经过长期争霸战争,到公元7世纪初,入侵者建立起7个王国,史称“七国时代”。不久,又出现了北欧人的入侵。为了抵御这种新的进犯,827年, 形成了统一的英格兰王国。
来自北欧的这种新的入侵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8—9世纪丹麦人的入侵,二是11世纪中叶的“诺曼征服”。丹麦的入侵,特别是诺曼人征服,使英格兰民族发生了一次迄今为止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与种族融合。现代英国历史学家塞拉斯和耶特曼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说:“诺曼征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从此以后英格兰不再受到征服,并因此而成为鼎盛国家。”〔6〕
人们,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在内,常常对入侵的北欧人不加区分。诺曼(Norman)按其字义就是北方人,所以在英国史上既有特定涵义,又泛指整个北欧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之间极相近似,他们的行动又相关联,所以常常不能确定所叙述的究竟是哪种人。大致说来,8 世纪入侵英格兰的是丹麦人,入侵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是挪威人,两种人当时又都被称为“维金人”(Vikings)。维金人不一定处处都比英格兰人开化 ,可由于他们发展出某些特殊技能,如丹麦的利剑和快船,因而成为最厉害的敌人。自8世纪始,维金人几度侵扰英国, 曾长期在英国东北部建立“丹麦区”,并袭击和占领了包括伦敦在内的许多重要城镇和地区。9 世纪下半叶,英王将泰晤士河口到提兹河的大部分盎格利亚地区割让给丹麦人,才取得了暂时的妥协。进入10世纪以后,逐渐统一和强大起来的英国,开始收复“丹麦区”。结果,这些地区承认了英王的最高权力,不过仍然保持了许多斯堪的纳维亚的特性。由于这两个民族在语言和社会制度上比较接近,所以他们相处起来并不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差别在慢慢地消失。
1066年来自法国诺曼底公爵的“诺曼征服”,则以最后征服而告终。9—10世纪之交,北欧人尽管在英格兰割地称雄, 却已无力进一步扩张,于是10世纪逐渐移师法兰克北部,寻求新的突破点。最后定居诺曼底,建立起诺曼底公国。当然,来自海峡对岸的威廉公爵入主英格兰,并不完全凭借武力,而是如他自己所说,也是“捍卫权利”,坚持他是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7〕(1066年1月,英王爱德华去世,幼子埃德加年幼,而且无人扶助。从王室世系上说,距离最近的是诺曼公爵威廉,但他是个私生子,被贤人会议拒绝,而推举爱德华临终时推荐的哈罗德为国王。这样就成为威廉入侵英国的借口)。征服的成功,使少数北欧血统的诺曼底人建立了对操撒克逊语的英吉利人的统治。同时,诺曼贵族继续在海峡另一侧拥有地产和领主权,他们甚至以英国为基地来扩充其在法国的领土。从一定观点来看,这是个有多重民族性的统治阶级。
一直到13世纪末,虽然诺曼统治者将法语以及拉丁语都规定为法律用语、宫廷用语和学校用语,但是英语方言始终很流行。学徒拜师宣誓时,法语和英语两种语言通用,因为第3代或第4代诺曼移民通常能说两种语言。理查德·菲茨尼在写于12世纪的一部著作中指出:“随着英格兰和诺曼人之间的杂居和通婚,这两部分居民已经融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在今天几乎区分不出谁是英格兰血统,谁是诺曼血统,这当然仅就自由人而言。”亨利三世1258年关于《牛津条例》的文告是以英文发布的。但标志英格兰民族语言的最后形成,则是乔叟在1380年用英文写成的头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名著《坎特伯雷故事集》,自此英语终于跻身为上流社会的语言。15世纪中叶,英格兰中部偏东的地方方言作为标准的书面语被政府文件的起草者所采用。赞颂西门德·孟福特的《刘易斯战歌》,宣称“为求得自由,英格兰再次呼号”,大概还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但是,英格兰人已经用英文唱起了:“夏天正在到来。”〔8 〕
诺曼人的成功统治被接受,诺曼人和英吉利人也逐渐由对立走向融合。不过,对诺曼统治者的谴责之声,几乎从未停止过。其中最严厉的批评者认为,诺曼征服是外国人将专制暴政强加给英吉利民族,并以后者失去自由为代价。关于在诺曼人到来之前存在过一段黄金时期的神话一直在流传。马卡姆夫人于1823年出版的畅销书《英格兰历史》中,甚至有这样的描述:一位母亲提醒她的两个正在阅读撒克逊时代英格兰人历史的孩子,“由于诺曼征服以后撒克逊人仍然繁衍在这片国土之上,而且在人数上大大超过诺曼人移民,所以几乎每一人基本上都是萨克逊人的后裔,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许多习惯和风俗都足以表明我们的血统。”〔9〕
三 马尔克制度
不论5世纪迁徙至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朱特人, 还是后来的诺曼人,都曾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他们和其他日耳曼部落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有着相同的传统、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其中最典型的是日耳曼人通行的马尔克公社制度。马尔克制度,在古代日耳曼部落里,几乎是唯一的制度。这种制度,在日耳曼人的全部生活里已经扎下了深根,今天虽然只剩下了很少的残迹,“但在整个中世纪里,它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典范。它浸透了全部的公共生活,不仅在德意志,而且在法兰西北部,在英格兰和斯堪的那维亚”〔10〕。马尔克制度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注定成为不列颠和西欧大陆新兴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
按公元前后的凯撒和塔西佗的记载看,土地公有和以家庭为单位个体耕作制度是马尔克的重要特征。当时马尔克和公地相互可以通称,部落的、村镇的或村庄的共同财产,不仅包括荒地、沼泽、牧场和森林,同时还包括草地和耕地。马尔克村民有使用和管理土地的平等权利,并且通过协商的办法共同决定土地的处理。在森林、荒地、沼泽和牧场,人们都可以砍柴、打猎、取蜜和在公共牧人的照顾下放牧自己的牲畜。每个人都可以让他的母牛或雌马与公共的公牛或雄马交配。耕地统一分割成价值相等的条田(gewanne),村民家庭用抽签方法分得份地, 每年更换,而公共的土地,则保留不动。在凯撒时代,他们的田地还是共同耕作的,但至少到塔西佗时(凯撒之后150 年)已知道由各个家庭独立耕种土地。〔11〕他们没有种植果园的技术,也不懂得灌溉,对于土地只要求生产谷物。他们对于冬、春、夏三季有具体的观念,并且在他们的语言中分别有特别名称,但无秋的名称,也不知秋的恩赐。从塔西佗的描写看,他们主要还是一个畜牧民族,他们常常以牲口的数量来估计财富。
部落的主要权力来自于自由民大会。一切重大事情,包括罪犯的审判,都由自由民大会集体决定。如果有“王”的话,“王”也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的产生亦是如此。塔西佗指出,他们选举“王”或酋长时,要考虑宗族,通常根据继承权选举“王”,但选择将领时,则依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能力。青年人总是喜欢追随着那些雄武有力,富有战斗经验的人。假若他精力充沛,勇敢善战,身先士卒,他便受到尊敬,受到服从。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刃剑,多用于砍杀,而不是刺杀。青年人经过正式仪式,获得佩剑的权利,这是一个青年接受的第一次荣誉;中世纪由扈从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就起源于此。被一大群出类拔萃的青年卫护着,不仅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力量。这些青年平时拥护首领的地位,战时保卫首领的安全;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以及一份战利品。这种制度有助于后来西欧封建制的形成,因为这种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附庸对封建领主的忠诚和后者提供土地和保护的基础之上的。国王并没有无限的或专制的权力,如同将领的领导多是靠着自身的魅力,而非专靠权威一样。 〔12〕
只有巫师才能申斥人,监禁人,甚至鞭打人。这种责罚并非受到将领的指使,而是被认为出于神的命令,因为神是被相信能够鼓舞士气的。这表明日耳曼人的行政权和教化权很早就是相分离的。从记载上看,凯撒也特别注意到了不列颠岛上类似于巫师或占星术士的“僧侣”,被称为督伊德教徒,他们除了教导年轻人外,还应召对成年人之间的纠纷作出仲裁,因此充当一种为公众服务的角色,并接受金钱与实物的馈赠作为报酬。凯撒认为督伊德起源于不列颠,月亮与树是他们的崇拜物,而荒野中的“橡树林”则是他们的神殿。他们根据月亮的盈亏计算日期,他们的计时单位——两星期——一直流传到今天。
塔西佗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写成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赌棍,另一方面又盛赞他们高尚的道德标准,并将这些道德标准奉为罗马人的典范。例如,他们认为婚姻是一种严肃、神圣的事情,除少数酋长外,大多数男人都实行并满足于只有一个妻子。新郎送给新娘的全部礼物只是几头牛、一匹装备齐全的马、一个盾牌、一把利剑。新娘也给新郎一些武器。交换礼物之后,婚姻便缔结了。塔西佗说:“这样的婚礼意在告诫新娘,她的责任是作为丈夫在劳动中和危险时的伴侣,战时同冒危险,平时同甘共苦;使她知道在严格的道德的制裁下,在劳苦的工作中,女性并不能自居例外。”
此外,在日耳曼人的道德风俗方面,还值得一提的是对待妇女的态度。他们认为,妇女具有神秘的意义,能预见未来。他们很重视妇女的意见,遇事就和她们商量。他们作战的时候,亲属紧紧站在旁边,成为其勇往无前的最热烈的鼓舞者。归来后,战士将自己的剑伤显示给自己的母亲或妻子,她们亲自历数伤痕。据说,有些濒于溃败的战局,经妇女们的鼓励,常常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她们不断地祈祷,并将胸部敞开,大声喊泣,使男人们明了被奴役的危险就在眼前。在日耳曼人看来,使自己的妇女受到奴役,是不可忍受的耻辱。他们这种对待妇女的态度,使人联想到流行于中世纪上层社会中崇拜高贵女性的“骑士爱情”。日耳曼人严冬时节喜欢成群结队地挨家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食物为止,此种习俗,也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情景:作为封建权益的一部分,国王或贵族连续许多天应邀参加为他及其随从举行的宴会。〔13〕
注释:
〔1〕〔2〕〔4〕〔8〕参见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第34—35页;第17页;第29页;第92页。
〔3〕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年版,第7页。
〔5〕E·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1卷,伦敦1947年英文版, 第52页。
〔6〕W·C·塞拉斯和R·G·耶特曼:《1066年及其他》, 伦敦1930年英文版,第83页。
〔7〕A·哈里森:《普通的人们——从诺曼征服到现在的历史》,方塔那1984年英文版,第2页。
〔9〕马卡姆:《英格兰历史》,伦敦1823年英文版,第85页。
〔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6页,第360页;355页。
〔12〕参阅马克直:《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有关章节。
〔13〕见塔西佗:《日耳曼志》,纽约1932年英文版;参阅齐思和等主编《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