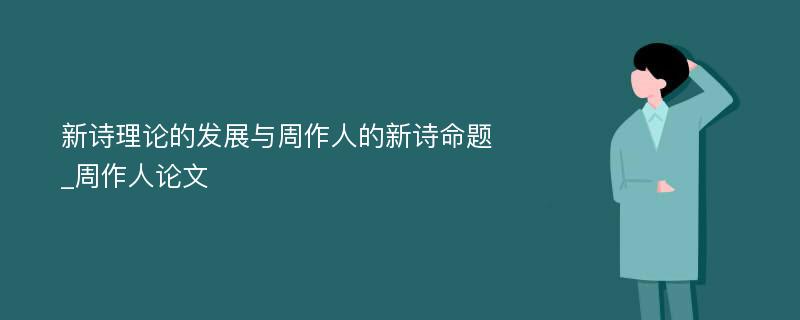
新诗理论的开拓和周作人的新诗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理论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2)04-0071-11
周作人是我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开拓者之一,他虽然并不以诗名世,但在新诗开拓者中 却是资格较老的比较成熟的作者。在最初一批新诗出版物中,《分类白话诗选》(1920.8)和《雪朝》(1922.6)两部新诗选集都有他的作品,后来还单独出版了他自己的一部《 过去的生命》(1929.11.出版),收入他创作的新诗共27题37首。王哲甫评他的诗:风格 “冲淡自然,很能表现出委婉的情意,颇近于古代诗人陶渊明”[1]。他的著名长诗《 小河》在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2号上发表后,曾被胡适誉为新诗中的“第一 首杰作”,虽不免有偏嗜、过誉之嫌,但其象征性的含蓄的意蕴,回荡的情思,自然的 音节,和完全散文化的质朴委婉的语言,在早期白话诗创作中确属罕见。与此同时,他 作为一位在初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出过不少力的新文学理论批评家,在他的文艺论著中也 有许多涉及诗歌方面的理论、主张和见解,在新诗理论的开拓中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和 包容性的特点,是很值得我们回过头来重视和研究的。
一、早期新诗理论开拓的历史回顾
在20年代初期中国新诗草创阶段,新诗理论还相当贫乏的时候,许多新诗开创者(诗人 和理论批评家)对于新诗的见解和主张,固难免于偏激或浮浅。
被茅盾誉为新诗创作初期的“一根大柱”[2],同时被朱自清推崇为新诗理论的“金科 玉律”[3]的胡适的《谈新诗》[4],仅以文学进化论的观点倡言“诗体解放”及其带来 的表现新的时代内容的无限可能性罢了,却缺乏对新诗所应有的理论规范,其浮浅自不 待言。
俞平伯在肯定了“白话诗”的前提下,提出白话新诗的“三大条件”:遣词须有“美 感”,“音节务求谐适”,情理还须“简括、深切”,即要求体现“诗质”与“诗形” [5]。但这不过是对诗的最一般的要求,还谈不上新诗的理论建设。
宗白华的《新诗略谈》[6]从对诗的“形”(“有音律的绘画的文字”)与“质”(“人 的情绪中的意境”)的理解出发,对新诗的创作问题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意见:一是从学 习音乐、绘画和造型艺术入手,“作诗的艺术的训练”;二是通过哲理研究和对大自然 的观察感受与参加社会活动,“做诗人人格的涵养”。这是对于初期白话诗论的一个较 大的突破,涉及了新诗创作带根本性的问题,在胡适、俞平伯等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 一步;可惜在理论阐述上,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只初步涉及了诗的本体论(较笼统)和创 作论(偏于创作修方面),还并未突出新诗的特点和要求,也还未涉及新诗的鉴赏和批评 问题,所以仍然是不够完整、深入的。
康白情的《新诗之我见》[7]是“五四”新诗创作中很值得重视的一篇新诗理论文章, 其对诗的本质、特点、新诗与旧诗的区别及其与散文的区分,都有明确的认定;对于新 诗的要素——形式方面的“自然的音节”、“刻绘的作用”,内容方面的“情绪”的表 现和“丰富的想象”(意境),以及对于新诗的创作过程——“选意”、“布局”、“环 境化”、“随心写”和最后的“读与改”——都有简略的论述。特别强调“诗是主情的 文学,诗人就是宇宙的诗人”,必须“善养情”;强调“诗源于自己的表现的艺术冲动 ”,要把“最高尚的人格表现于最高雅的风格里”,就要加强诗人的“人格修养”、“ 知识修养”和“艺术修养”;强调“新诗的精神在创造”,“做一首诗就要让这首诗有 独具的人格”。可以说,康白情这篇《新诗之我见》对于新诗的本体论和创作论都作了 较为切实的论述,无论对“五四”写实派或浪漫派都具有指导意义,在胡适、俞平伯、 宗白华等人的诗论的基础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李思纯的《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8]则针对“五四”新诗创作的实际,专门提 出新诗的形式问题加以批评和探讨,不能不说是一篇旨在“纠偏引路”的及对贤文。他 同意宗白华《新诗略谈》关于诗的定义,认为:“诗的本体,不外是两方面:一面是属 于思想的,所谓文学的内容,一面是属于艺术的,所谓文学的外象。内容方面,是诗的 精神;外象方面,是诗的形式。”但自胡适首倡“诗体解放”以来,关于新诗的讨论只 “偏重于诗的作用价值及诗人的修养”,形式方面虽有涉及,却“大概存而不论”,两 三年来新诗创作的现状除郭沫若《凤凰涅槃》等少数作品外是很不令人满意的 :一是在事象表现上“太单调了”,二是形式上“太幼稚了”,三是“太漠视音节了” ,这“都是属于艺术上的缺点”。由于这“许多缺点”的普遍存在,新诗“是否已具有 代替旧诗的能力,自然还是疑问”。他认为“诗的形式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与诗的 艺术有甚深的关系”,因而他主张“今后的要务”一是“多译欧诗,输入范本”,二是 “融化旧诗及词曲之艺术”,“以创造新诗”。李文的价值虽不在新诗建设上,但它及 时提出了在“诗体解放”的新诗创作中被忽略了的艺术形式问题,有助于启发人们对新 诗的艺术的探讨。
郭沫若《致宗白华》的两篇诗论[9],从他的浪漫主义诗歌观和泛神论的宇宙观出发, 则强调诗“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的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 上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他说:“诗人的心境 譬如一湾澄清的海水……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 起来,宇宙万汇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 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的本 体,只要把它写了出来,它就体相兼备。”与其充满浪漫精神的诗意表现相联系,在诗 的形式方面,则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认为他人已成的形式是不可因袭的 东西,他人“只是自己的监狱”。“诗的生成如像自然物的生成一般”,因而诗的文字 应“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然于自然流露之中,也自有它自然的谐乐,自然的画意 存在,因为情绪自身本具有音乐与绘画二作用故,情绪的律吕、情绪的色彩便是诗,诗 的文字便是情绪自身的表现。”这就把浪漫主义诗歌的本体观和创作观大致表现得十分 明确了。
到了20年代中期,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10]、《<女神>之地方特色》[11] 和《诗的格律》[12]等著名诗歌批评与理论主张的发表,则把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推向 了一个自觉的阶段。闻一多鲜明地提出“新诗”的概念:“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 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新诗应该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11]。他并不反 对诗人的个性表现,但却明确地反对为个人渺小的休戚而歌唱(见诗作《静夜》);他称 赞郭沫若不愧是“时代的肖子”,首先称赞的就是“《女神》之时代精神”,即大破大 立的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个性解放、觉醒意识、忏悔意识的表现[10]。同时,他也明 确地指出《女神》和“当今诗坛之名将莫不皆然”的创作中过于“西化”而“薄于东方 色彩”的重大缺憾,强调说:“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的纬线所编织成 的一匹锦,因为艺术不管是生活的批评也好,是生命的批评也好,总是从生命产生出来 的,而生命又不过时间与空间两个东西的势力所遗下的脚印罢了。”因此,我们做中国 新诗不仅要具备新诗的“时代精神”(包括时代感受、时代情绪),还要“时时刻刻想着 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一句话,就是要“时时不忘我们的‘ 今时’同我们的‘此地’,我们自会有了自创力,我们的作品自然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 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然后才是我们翘望默祷的新艺术了!”[11]闻一 多能够站在诗歌艺术的本位,民族的本位和中外诗歌交互影响与艺术发展的高度,来看 待中国新诗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在环顾人类艺术史和“五四”新诗创作实际的基础上, 较为全面地提出了中国新诗所应该具备的20世纪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地方特色 即民族特色)的双重品格。并且,他还在探索中国新诗的形式方面,提出了建设“新格 律诗”的理论主张(即“三美”主张)[12],作为对“五四”自由诗日益严重的散文化“ 非诗倾向”的有力反拨,由此形成了对中国新诗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新月诗派”即 新格律诗派。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和新诗创作,都被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差不多在闻一多、徐志摩提倡建设“新格律诗”的同时,穆木天、王独清在其发表于 《创造月刊》的通信文字中,则提出了要创造“纯粹诗歌”(实则是象征主义诗歌)的主 张。穆木天认为:“诗是在先验的世界……一个有统一性的心情的反映,是内生活的真 实象征”;“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它“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 深处”。他认为:“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波,浓 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不动的淡淡的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 的情肠,才是诗的世界”。要言之,诗的世界便是“最纤细的潜在意识”、“最深邃的 最远的不死而远的音乐”,即“内在生命反射”,“一般人找不着、不可知的远的世界 ,深的大的最高的生命。”[13]他主张一首诗必须具备思想内容上的“统一性”和心情 流动的“持续性”,否则便会令人难以理解[13]。对于诗的艺术表现,则强调诗要有大 的暗示能,强调“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 说明哲学”,“用有限的律动的字句启示出无限的世界,是诗的本能。”[13]
王独清的《再谈诗——寄木天、伯奇》明确宣称要“努力于艺术的完成”,“做唯美 的诗人”。他说他“很想学法国象征派诗人,把‘色’与‘音’放在文字里”,并着重 从自己创作经验中,谈如何造成“纯粹的诗”的“音”、“色”之美。他把“理想中最 完美的‘诗’”,归结为一个公式:“(情与力) + (音与色) = 诗”[14]。穆、王及其 诗友们这一“纯诗”的艺术追求的结果,便是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派在诗坛的形 成。
至此,有了“象征诗派”和“新月诗派”的出现及其理论探讨,中国新诗便确已进入 一个由“破”到“立”的检阅、思索与理论建设的阶段了。但是在这一过程的叙述中, 我们的新诗理论批评史研究家们,却往往忽略了一位起着桥梁作用的重要人物——著名 文学理论批评家兼中国新诗开拓者之一的周作人。
周作人不仅在“五四”新文学团体中,最先提出“个性的文学”主张[15],而与后来 的“创造社”有着思想上的沟通,也不仅在20年代中期,直接地支持、推荐了李金发寄 自柏林的象征主义诗集《微雨》和《食客与凶年》的出版(注:1923年6月周作人收到李 金发从柏林寄来的两部诗稿《微雨》、《食客与凶年》后,即复信李金发,称赞这种诗 是国内所无,另开生面的作品,编入“新潮社丛书”,推荐给北新书局出版。(见李金 发《仰天堂随笔·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收入李金发《异国情调》一书。)), 使国内诗坛骤然掀起一场“微雨冲击波”;而且在新诗最初兴起的一段时间里,他不但 与鲁迅同时发表了具有象征意蕴的体例独特的诗作(注:如鲁迅《梦》、《桃花》,周 作人《小河》《秋风》等。)而令其名声大噪,他还在并不惹眼的一系列诗歌评论和文 艺杂谈中,表明了他对中国新诗的理论主张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包容的气度与理论的 深度——从诗的本质、特点,到诗的地方色彩、民族特色与个性表现的关系,诗的内容 与形式的关系,诗歌创作对于想象、梦想和诗歌语言的简炼、含蓄的基本要求,新诗人 对于继承中国古代诗歌优秀的抒情传统和表现方法同时学习借鉴外国现代诗歌的艺术精 神与表现技巧,而将二者融合沁透加以创新的正确态度,以及对于中国现代诗歌发展道 路的多元化思考,一直到怎样进行诗歌批评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完整、系统而周密的 论述。尤其可贵的,是所有这些见解和主张,都不是囿于一己所好和一党一派的偏嗜, 而是体现着思想解放的时代特点和诗歌本体的特点,闪烁着一种求实的、辩证的、智慧 的光辉,表现出一种博大精深的包容气度和历史的眼光。这是当时一般诗论者很难达到 的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
二、关于诗歌的本质、特点与诗歌创作
周作人在为汪静之《蕙的风》而写的一篇评论中说:“诗是人情迸发的声音”。情诗 在诗中“占着极大的地位”[16],就是有力的证明。这是周作人对诗的本质的最基本的 认识。
因此,他特别看重诗歌的感情的“真实”。他要求诗人在创作时,“必须用自己的话 来写自己的情思。”[17]他这样表述说:“世人的心与口如不尽被虚伪所封锁,我愿意 倾听‘愚民’的自诉的衷曲,当能得到如大艺术家所能给予的同样的慰安。我是文艺爱 好者,我想在文艺里面理解到别人的心情,在文艺里面找出自己的心情被别人理解的愉 快。在这一点上,如能得到满足,我是感谢的……”[18]他这一段话讲得十分坦诚。这 虽然不是专门对诗歌讲的,但作为“人情迸发的声音”的诗歌,其所表达的感情尤须真 挚动人,是自不待言的。然而作为特殊文学形式的诗歌来说,感情的“所谓真实,并不 单是非虚伪,还须有迫切的情思才行,否则只是谈话而非诗歌了”[17]。这是周作人十 分强调的诗的特点,他用了一个很生动的譬喻来予以说明:
譬如一颗星,燃烧至某一程度才能发出光焰,人的情思必须燃烧至某一程度,才能成 为诗料[17]。
这样,周作人便主张:写诗的“第一条件是须表现实感”,而且这“实感”还须达到 “迫切而不能忍欲言”的炽热程度!第二条件是还要“有恰好的句调,可以尽量表现这 种心情,此外没有第二种说法。那末这在作者就是真正的诗,他的生活之一片;他就可 以自信地将它发表出去了”[17]。
其次,与要求诗歌表现生活所孕育的迫切的真情相联系,周作人还特别强调诗歌对于 诗人的个性的表现和创作的自由。这是周作人的诗歌主张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他说 :
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的时候可以大胆地说出来 ,因为文章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 的话要诚实得多了[19]。
他还说,“五四”后“几年来中国新文艺渐渐发达,各种创作也都有相当的成绩,但 我们觉得还有一点不足:这便是因为太抽象化了,执着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写出预定 的概念,却没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一个单调”[19]。因而 ,他表示“我希望于摆脱这些自加的枷锁,自由地发表从土里生长出来的个性”[19]; 并要求给予诗歌作者以充分表现自己真实的个性(生活、情思、语言)为前提的最大的“ 创作自由”:
我的意见,以为最好任各人自由地去做他们自己的诗,做好了,由个人的诗而成为国 民的诗,由一时的诗人而成为永久的诗人,固然是最所希望的;即使不然,让各人发抒 情思,满足自己的要求,也是很好的事情[17]。
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无论人家文章怎样的庄严,思 想怎样的乐观,怎样讲爱国报恩,但是我要做风流飘逸或讽刺谴责的文学,也是我的自 由,而且无论说是隐逸或是反抗,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只要不 是成见的、执着主张派别等意见而有意造成的,也都有发表的权利与价值。这样的作品 自然具有它应有的特性[19]。
总之,周作人从诗的本质和特点出发,主张做诗的人要做什么诗,“什么形式,什么 内容,什么方法,只能听他自己完全的自由。但有一个限制的条件:便是须用自己的话 ,写自己的情思。”这便是周作人具有现代意识的诗歌创作主张。这种主张,不仅对新 诗创作,而且对于整个“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都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正因为这样 ,他便十分看重诗的新颖和独创,他引用福禄特尔的话说:“第一个把女子比作花的人 是天才,第二个这样说的便是呆子了。”[17]周作人的诗歌创作主张,至今还是值得我 们的诗人们时常深思的。
三、关于诗的地方性、民族性与个性的关系
同强调诗人的个性表现相联系,周作人非常重视文艺作品(包括诗歌在内)的地方特色 与民族风格,并把这三者统一起来的有机结合,看作是诗和整个文艺的“生命”。他认 为:“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 了地域(的不同)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19]。他举出法国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同 北法兰西的文人作品的差异,做为一个鲜明的例子,并由此推论说:在中国这样辽阔的 土地上,“当然更是如此”[19]。他指出:
我们说到地方,并不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地之力。 ……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开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 人生的正当的道路[19]。
由此,他尖锐地批评和忠告某些诗人、作家说:
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地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 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 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文艺都是 如此[19]。
周作人在这里讲了这样三重意思:第一重,批评某些文艺家脱离生活现实,只沉醉于 空虚的理论、观念;第二重,说明怎样才是真实的思想和文艺;第三重,指出一切文艺 都是这样,概莫能外。紧接着,他还引用了尼采的诗句作为对诗人、作家的一种号召: “……我恳请你们,我的兄弟们,忠于地!”[20]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周作人十分强调文艺的“地方特色”、“地方趣味”,不 仅仅是把它同“培养个性”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把它同文艺的走向世界联系在一起。 这里绝对没有狭隘地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之嫌。他说,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现在 固未必执守乡曲之见去做批评,但觉得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其重大的”,因为“强烈 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 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否则‘拔起了树木’,不但不能排到 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枯槁了。”[21]他说他自己“常怀着这种私见去看诗人,知道的, 因风土以考察著作,不知道的,就著作以推想风土;虽然倘若固执己见,过事穿凿,当 然也有弊病,但我觉得有相当的意义”[21]。他批评“现时”新文艺家的一般倾向,指 出:“不过我们这时代的人,因为对于褊狭的国家主义的反动,大抵养成一种‘世界民 ’(Kosmoholites)的态度,容易减少乡土趣味……我仍然不愿取消‘世界民’的态度, 但觉得因此更须感到‘地方民’的资格,因为这二者本是相关的,正如我们是个人,所 以是‘人类的一分子’(Homarano)一般。”[21]这样,他就把文艺的“个性”、“地方 性”(民族性)和人类共通性(世界性)这三者高度地统一起来了。
正因为这样,他在为刘大白出版的诗集《旧梦》所写的感想式的文字中,就批评刘大 白这部诗集中的作品没有“多大的乡土趣味”,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而表示遗憾;希 望大白今后“更多地写出真的今昔梦影,更明白地写出平水(注:平水,即刘大白的家 乡浙江省平水县。)的山光,白马湖的水色,以及大路的市声”[21]。这一批评,对于 我们今天的相当一部分忽视文艺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年轻一辈诗人、作家,绝不是 没有教益的。
总之,周作人是把“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起来的个性”,“摆脱了一切束缚,任 情地歌唱”,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看成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三者统一起来的 文艺,认为这乃是诗和文艺的“生命”[19]。这是怎样精辟,怎样发人深思的见解!现 今那些一心想离开现实,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而沉于梦幻或醉心虚无的诗人们,难道不 可以深长思之么?
四、关于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周作人主张诗歌形式一定要适合内容的需要,形式绝不是一种孤立的追求,而是与一 定的内容相适应的;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形式支配内容或脱离开诗的内容——变为 形式主义。这就是周作人的内容与形式统一观。
他举出“小诗”做例子说:“如果我们‘怀着爱惜在这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复 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想将它表现出来,那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 ”何以这样说呢?因为“思想和形式之间有重大的相互关系,不能勉强牵就。我们固然 不能将简洁含蓄的意思拉成一篇长篇,适当的方法唯有为内容去定外形;在这时候,那 抒情的小诗应了需要而兴起,正是当然的事情了。”[17]
对于诗歌的内容方面,除了前面强调的个性的表现,真情的抒发和地方性、民族性与 个性的统一之外,他还要求“感人为善”,即要求思想和情调的健康。他在《答芸深先 生》(1927.10)的信中说:
我不相信诗人应当是“先知”,拿着十字架在荒野上大叫。但有健全思想的诗人,总 是更令我喜欢。郭沫若先生在若干年前所说“诗人须通晓人学”这句话,我至今还觉得 很对。
周作人的这一思想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诗歌的创作与发表总是相联系着的,创作尽可 以不顾一切地抒发自己的感情,然而发表出去,让广大读者去领受,影响、撩拨读者的 感情,诗人就不能不有一种社会责任心:注意到是否能起到积极、健康的作用,至少不 要起消极、有害作用。这是聪明的、善良的诗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
不过,话再说回来,具有一种开放意识的周作人,懂得诗人往往具有一种“超前的” 、高远的思想,并不去对他们作普遍一律的要求。他只是要求最起码的情感的健康而已 。他甚至对于平庸思想的作品也十分宽容,只要它在艺术表现上确有可取之处。例如, 他一面指出苏曼殊的诗作“思想平庸”,“不大高明”,“逃不出旧道德的樊篱”;一 面却又肯定其诗歌里的“真气与风致”,称赞苏曼殊“在宣统、洪武之间的文学潮流中 ”,“毕竟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答芸深先生》)。周作人这种不把文学视为狭隘 “工具”的宽容精神,同样是值得今天的文艺研究家、批评家和诗人们注意的。
五、关于诗人的梦想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
对于诗歌创作,周作人还十分重视诗人的梦想的素质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这也 是诗歌创作能否成功的必要前提。
他认为,诗人大都是富于“梦想”的。他借了科伦的一句话,说:“这世界在歌者看 来,是为了梦想而设的”[22]。他对诗人的“梦想”,作了这样的解释:
梦想是永远不死的。这梦想既非科学,又非迷信,实不过是一种表示感情和愿望的“ 创作力的活动”[22]。
周作人的这一解释,非常精辟地道出了诗人“梦想”的本质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意义 。非真诗人,难得有这样真切的体验和这样深刻的理解。
那么,诗人为什么耽于梦想呢?周作人回答说:因为“对于现在,大家总有点不满足… …所以多有逃避现世的倾向,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23]。用“逃避 说”来概括诗人之耽于梦想或沉入回忆,固然是以偏概全,不尽科学;但对其根源—— 源于对现状的“不满”——的分析,却是正确的。这就基本上把诗歌中常多梦想或回忆 这一现象解释明白了。因为:大凡诗人,无一不是理想主义者,对于现实的感受和不满 就特别地强烈,因而在诗中表现着梦想与往昔的回忆就尤为常见。
关于诗的语言,周作人认为,诗的语言“非真实、简炼不可”,对于只有数行的小诗 ,这“简炼”的功夫就“尤为紧要”[17]。如何才能做到简炼呢?那就要在构思和剪裁 上、在字句的锤炼上用心了。然而又要不失其自然的风韵,这就很不容易。他自己做的 诗,如《歧路》、《高楼》、《秋风》等看似那么平淡、简短的几句,却都是很下了一 点功夫的,所以才那般清隽自然,耐人咀嚼。
与此同时,他又要求诗的语言必须“含蓄”,有“一点儿朦胧”的意味,而不能太浅 露直白。他批评“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一个玻璃球,晶莹 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就少了一种余香和回味”。而要使诗的语言叫 人读了之后,能够有“一种余香和回味”,这就要求诗歌表现上的含蓄,学习、借鉴一 些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他主张为了含蓄,诗要多用“暗示”和“象征”,并且“带一 点浪漫蒂克的意味”;他认为“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 之’,我们上观国风,下察民谣,便可以知道”。这是同诗是以抒情为主这一本质特征 相适应的,抒情自然要讲究艺术,尽可能避免“浅露的直白”。他之所以不太满意刘大 白的诗歌,主要就在它们的“浅露的直白”,“使诗味未免清淡一点”[24]。
周作人自己的诗歌,虽然数量不多,大多能以简练、含蓄的语言表现出“委婉的情意 ”,并且显示出一种“冲淡意远”的独特风格,除了《小河》而外,《秋风》、《高楼 》、《画家》、《两个扫雪的人》等都是为人称道的名篇。
六、关于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外国诗歌的态度
周作人不像一般“五四”新诗人那般全盘否定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与经验。他对富有 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古代诗文,是采取一种有分析的“扬弃”态度,即否定和抛弃其中 陈腐的名教思想和束缚人的个性表现的过于死板的格律、笔法,同时却重视继承发扬中 国古代诗歌和古代散文优美的抒情传统与表现手法。
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表明对古代文学态度的论文《古文学》,提出“研究古文学”是 国民的一种权利而非义务。他说:对于一个文艺家来说,“艺术上的造诣,本来要有天 才做基础,但是思想与技术的涵养也很重要,前人的经验与积累,便是他必要的材料。 ”他借了京西一个朋友的信中的话说,“蔑视经验,是我们的愚陋,抹杀前人,是我们 的罪过”。并进一步指出:“这前人的经验与积累当然不限于本国,只是在研究的便利 上,外国的文学因为言语及资料的关系,直接的研究较为困难,所以利用了自己的国语 的知识去研究古代的文学,涵养创作力或鉴赏文艺的趣味,是最上算的事,这是国民所 享的一种权利了。”他分析说,“虽然现在的诗文著作都用语体文(即白话),异于所谓 古文了,但终是同一来源——即中国的社会的生活”,“其表现的优劣在根本上总是一
致,所以就古文学里去考察前人的经验,在创作的体裁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帮助。”[25]
他还提醒在对于古代诗文的学习、鉴赏中,须力戒穿凿附会:一是不可脱离作品产生 的时代环境去妄加“现代化”的解释,如胡适解说《诗经》所犯的错误[26]。二是更须 注意剔除在古代诗文的诠释上外加的那“一层纲常名教的涂饰”,切不可“中传统之毒 ”,把古代诗歌甚至《国风》民歌都看成是“虚矫的‘为名教的艺术’”。他指出:“ 这个主张倘不先行打破,冒冒失失地研究古代文学,非但得不到好处,而且还要上当, 走入迷途。”他举出生动的例子说:“关于《睢鸠》原是好好的一首恋歌,却说是‘后 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南有松木》本是结婚歌,却说是‘ 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也’。经了这样的一番解说,那儒业者所崇拜的多 妻主义似乎得到了一重拥护,但是已经把诗的真意完全抹杀……我们若将《诗经》旧说 改正,把《国风》当作一部古代民歌去读,于现在的歌谣研究或新诗创作上一定很有效 用,这是可以断言的。中国历代的诗未尝不受《诗经》的影响,只因有传统关系,仍旧 囚在‘美剌’的束缚里,那正与小说的讲劝惩相同,完全成了名教的奴隶了。”[25]他 还举了将《古诗十九首》妄解为“思君之作”的典型例子,指出:“这自然都是假的” 。诚然,“世上有君主叫臣下替他尽忠的事实,但在文艺上讲来,那些忠爱的诗文,倘 若不是故意的欺人,便是非意识的自欺,不能说是真的文艺”[25]。这是我们在阅读、 鉴赏古代作品时,应区别清楚的。
此外,他还谈了读诗的方法。他认为,对于某些只是表现情绪的作品,阅读时“可以 不求甚解”,勿须“篇篇咬定这是讲什么”,因为事情本身对于诗人并不重要,所以在 诗里被“隐”去了,他所要表达的只是一种情绪;我们读它时,也只要感受到那么一种 氛围,就可以了,诗人抒情的目的就达到了[26]。古代诗歌的某些作品尚须加此,更勿 须说现代诗歌了。这正是善读诗、解诗之一法,是真的“懂家”之谈,而至今却还有许 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和方法。
对于外国诗歌,周作人主张:第一是学习、借鉴西方诗歌的创作精神和表现技巧;第 二是反对奴隶主义地全盘西化。对于欧洲的近代诗歌,出于“五四”文学革命的需要, 他自然是主张要积极地学习、借鉴的,希望外国近代诗诗歌的精神、气度能对中国新诗 的创作发挥有益的影响。在给《扬鞭集》写《序》时,他就指出:“不瞒大家说,新诗 本来是从模仿(外国诗)来的,它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这就是我所谓融化 ……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愈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 。”但是,他却坚决反对丧失掉民族特色和诗人个性的生硬的模仿,他说:
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 管去,就替代血液之用[27]。
这比喻非常精辟。他认为,不管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或外国文学,“模仿都是奴隶,但 影响却是可以的。国粹只是趣味的遗传(即民族性的遗传——笔者),无所用其模仿;欧 化是一种外缘,可以尽量容受它的影响,当然不以模仿了事”[27]。
如何将发扬中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和接受外国近代诗歌的有益影响,两个方面结合 起来?他主张:“以遗传的‘国民性’为素池,尽它本质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 影响,使其融合沁透,合为一体……,造成一个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正如人之遗传逐 代增入异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27]。这样,他就把继承、发扬民族文学传统和吸 收外来影响的关系和目的,都一并说清楚了。周作人正是用了这样的观点,具体而正确 地分析、论述了“五四”小诗的兴起。
这里,还须着重强调:周作人对古代诗歌和外国诗歌的态度,是同他尊重个性表现的 创作主张相一致的。他一再声明说:“我平素主张无论对什么流派,都可以受影响”, 但却“不可以模仿”。“我们反对模仿,并不是有中外古今的区别与成见”[27],因为 “假的,模仿的,不自然的著作,无论是旧、是新都一样无价值,这便是因为它没有真 实的个性”[15]。他把反对“模仿”,终究归结到文艺表现个性的本质上来,这是周作 人“现代意识”的一个突出的表现。他在《个性的文学》一篇著名论文中,特地举出印 度那图夫人(S·Nadu)模仿英诗创作受到戈斯的尖锐批评,以及她后来“再放开手去做 真正自己的诗”所取得成功的例子,然后加以评论说:
戈斯并不是说印度人不应该写英国式的诗,不过因为这些思想及句调实在已经习见, 不必劳她来复述一遍;她要做诗,应该做自己的诗才是。但她是印度人,所以她的生命 所寄的诗里,自然有一种印度的情调,为非印度人所不能感到,然而又是大家所能理解 者:这正是她的诗歌的真价值之所在。正确地说来,不但当然与非印度人不同,便是与 其他印度人也当然不同;倘若她的诗模仿泰戈尔,也讲什么‘生之实现’,那又是假的 ,没有什么价值了……[15]
80年前周作人的这些意见,不是依然还值得我们当今诗坛的一些诗人们,认真地思考 一番么?
七、关于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问题
周作人研究了“五四”以后几年中白话新诗发展的情况后,当时就认为“新诗的道路 不止一条”[17]。他指出,白话新诗中既有“有韵新诗”,也有“不叶韵的”;而“有 韵新诗”,有的是“白话唐诗”,有的是“词曲”,有的是“小调”,而且那旧诗里最 不幸的“挂脚病”与“趁韵”也常常出现了。他认为那些不叶韵的,虽然也有种种缺点 ,倒还不失为一种新体——有新生活的诗,因为它只重自然的音节,所以能够写得较为 真切。由此,他便“悟出白话诗的两条路:一是不必叶韵的新体诗,一是叶韵的‘白话 唐诗’,以至‘小调’”。
他说这自然只是“一般的说法”;而“至于有大才力能够做有韵新诗的人,当然可以 自由去做,但不要像‘白话唐诗’以至‘小调’为条件。有才力做旧诗的人,我以为也 可以自由去做,但也仍以不要像李、杜、苏、黄或任何人为条件”[25]。其基本主张是 :一面强调文学的继承关系——包括中、外文学遗产中一切优良的有价值的东西;一面 又强调文学的创新——自己的个性的表现,并要将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
前面说过,他不像一般“五四”新文学运动者那样全盘否定旧诗的传统,而是主张“ 扬弃”,并且预言:注意到“国语中字义、声音两重对偶的可能性”,觉得“国语文学 的趋势虽然向着自由的发展”,却也有可能“炼成音乐与色彩的语言”——“只要不以 词害意就好”[25],这在力求破除旧诗格律的当时,不啻是很有见地的一种预言。周作 人当时就预见到自由诗和新格律诗这两种新诗形式发展的可能性,并根据汉语的特点, 特别指出“炼成音乐与色彩的语言”是可行的——新诗人应该在追求新诗的语言美和形 式美方面作出努力。
总之,在周作人看来,文学本来是“情绪的作品”,诗人要怎样做诗,做什么诗,只 能听其抒情的完全自由。诗歌的道路原本是八面畅通的,“只有一个限制的条件,便是 须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情思”[17]——写得像诗。尽管限于当时远未成熟的条件,尚 未对白话新诗的发展道路问题作更深入的论述,而其开放的精神、乐观的态度,却是十 分鲜明、强烈的。
八、怎样进行诗歌批评
周作人既然主张诗歌精神的解放,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各方面都应尊重那“从土里 生长起来的个性”,那么,在诗歌批评上,他自然主张和提倡“宽容”的精神。他鲜明 地表示说:“文艺以自己的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 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的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各人的个性是各 各不同的,“现在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要去强迫统一,即使这不可能的事实居然实现 了,这样的文艺已经失了他唯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所以宽容是文艺发 达的必要条件”[28]。
但是,尊重诗人、作家、艺术家的“自己表现”即个性,这还不是文艺批评必须“宽 容”的唯一原因,此外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一,是批评家和诗人之间艺术趣味上的差距问题,亦即批评家艺术趣味(艺术批评标 准)的时、空局限性问题。他指出:
我们常人的趣味,大多是‘去年’的,至抵也是‘当日’的罢了。而‘精神贵族’的 诗人,他们的思想感情可以说多是‘明天’的。因此,两者之间常保持若干的距离,不 易接触[29]。
他联系欧洲文学史上的教训,举出例子说:
现在大家都知道称赞英国济慈的诗了,然而他在生前却为‘批评家’所骂倒。为什么 现在的任何人都能赏识济慈的诗,那时的堂堂《勃拉克乌特杂志》的记者却会如此浅陋 ,不特不能赏识,而且还要痛骂呢?难道那时文艺批评家的见识,真是连此刻的商人还 不如么?……这个缘故,是那时的趣味是十八世纪的,现在的趣味却是济慈以后的十九 世纪的了[29]。
然后,他还联系诗坛现实的情景,感慨说:“现在的批评家笑着《勃拉克乌特》记者 的无识,一面却凭着文学之名,尽在那里痛骂趣味的新‘济慈’”[29]。周作人指出: 读者或批评家的艺术趣味落后于诗人、落后于时代“这种事情是常有的”,这是因为“ 我们在学校、社会、教育各方面,无形中养成一种趣味,为一生言行的指针,原没有什 么稀奇,所可惜者,这种趣味往往以‘去年’为截止期,不肯容受‘今天’的事物,而 且又不承认这是近代一时的趣味,却要当他作永久不变的正道,拿去判断一切,于是济 慈事件在文艺史上不绝于书了”。就以诗的客观效用之一——“感人为善”的标准—— 来说吧,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游移不定”、与时推移的;世界上本来就“无恒善 ”,怎么可以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评判它呢[29]?
其二,是批评本身的主观性问题。他认为,“个人的鉴赏的标准,多是主观的,不免 为性情及境遇所限,未必能体会变化无穷的情境”[17]。他说:“我们绝不能脱去我们 自己”,“我们关闭在自己的人格里,正如在永久的监狱里一般”。因此,“真的文艺 批评,应该是一篇文艺作品;里面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对象的真象,无宁说是自己的反映 。”他指出:“客观的批评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29]。
其三,是“诗的效用……是难以计算的”[31],我们很难用一篇批评文章和一种批评 尺度,穷尽它的价值。他认为,文艺之作为“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自然不能与人生 分离,它的表现人生与“感人为善”的客观效用是不应被忽视的,这仅仅是一个方面; 但还有另一个方面,文艺之作为文艺而不是别的东西,还有它的独特性即本体性,而不 能被视为狭义的“工具”,这便是有它的“独立的艺术美和无形的功利”。所以,“为 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并不是文艺的“唯一职务”[30],我们的批评就不能只从单方 面去看。换句话说,“文艺问题固然可以用了社会学的眼光去研究,但不能以此作为唯 一的定论”[31];诗歌作为最高层次的艺术,就更是如此。这就是说,诗歌批评固然可 以、而且应该以社会学的眼光去进行分析、评论,但却不能作为诗歌唯一的价值取向; 诗歌还可以从灵感、个性结构学等种种方面,去进行考察和评论。因此,他认为,要欣 赏诗歌艺术,是需要有“相当的一番训练”的[31]。
其四,他还从诗歌“生产”的特殊性,主张对诗人创作的要求不宜过高、过急。“在 批评家,希望得见永久价值的一篇作品,这原是当然的;但这种佳作是数年中难得一见 的,现在想每天每月中遇到,岂不是过高的要求么?”[17]因此,他便主张:“做诗的 只要有一种强烈的感兴,觉得不能不说出来,而且有恰好的句调,可以尽量表现这种心 情,此外没有第二样说法,那么这在作者就是真的诗,他的生活之一片,他就可以自信 地将它发表出去了。有没有永久的价值,在当时实在没有计较的工夫与余地。”[17]
那末,诗歌还可以不可以“批评”呢?答复是肯定的。诗歌批评的“宽容”,并不是取 消“批评”。在周作人看来,“批评”本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趣味的事体 ,于诗人作家和读者双方都是有益的;关键是在于做“批评”的态度和方式。周作人主 张诗歌批评应该采取一种鉴赏的方式,才能有效地体现批评的“宽容”态度和求实精神 。他觉得文艺批评都应取一种“鉴赏”的方式,“谈自己的感受”,而不要对别人的作 品去进行法官式的“判决”。他说:“我相信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察,是 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摘”[32]。对于诗歌作品来说,“我们见了这些诗,觉得那 几首好,那几首不好,可以当个人的意见去发表,但读者要承认这并没有在法律上裁判 力。”[17]他特别提醒诗歌批评家要有一种自知之明,要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艺术趣味 和诗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因而在发表对于诗人诗作的批评意见时更须特别谨慎:
我们鉴于文艺史上的事件,学了乖巧,不肯用了去年的头脑去呵斥明天的思想,只好 直抒所感地表白一番。但是到了真是距离太远的地方,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在这时 候,便不得不等真的批评家出现,给我们以帮助[29]。
他非常不赞成那种把批评当做对别人作品进行“判决”的做法,指出:“许多司法派 的批评家,硬想依了条文下一个确定的判决,便错在相信有永久不易的条文可以作评定 文艺好坏的标项目,经过多数的附和,于是成为权威罢了。这种趣味当初尽有绝大的价 值,但一经固定,便如化石美人只有冷而沉重的美,或者不如说只有冷而沉重的压迫一 切强使屈服而已”[29]。因而,他自己在进行诗歌批评的时候,总是尽量取一种谈感受 的方式,如对汪静之的情诗《蕙的风》,对刘大白的《旧梦》,对刘半农的《扬鞭集》 等诗人、诗作的批评,都是一种鉴赏的态度,平易近人,体现着文风的坦诚与谦逊。
总之,他主张做批评的人“只要表现自己而批评,并无别的意思,那便也无妨碍,而 且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29]。难怪,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周作 人的那些批评文字,也都可以当作清新可喜的散文来读,并不像现今批评家大多板起面 孔在那里说话。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新诗主张,在早期新诗理论开拓者中,的确具有完 整性、系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尤其是在关于诗的本质和特点,诗的地方性、 民族性和个性的关系,新诗人同中国古代诗歌和外国诗歌的关系,以及怎样进行诗歌批 评等问题上,其见解尤为深刻。这些新诗主张,不仅对于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建设具有 较全面的开拓性意义,其某些精辟的见解就是今天看来,还依然切中肯綮,无论对当今 的诗歌创作或诗歌批评都仍有启发意义。“五四”时期的周作人,的确算得是中国现代 诗歌的一位难得的知音了。
正因为他对“五四”新文学理论建设的多方面的贡献,所以我们对于他在30年代的“ 落荒”和抗战以后的变节,才倍感痛惜与愤恨。对于他在“五四”新文学建设中曾经起 过的作用,我们所持的态度,便是鲁迅先生《忆刘半农君》所表明的对于刘半农的态度 ,这便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收稿日期:2001-07-18
标签:周作人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秋风论文; 文艺论文; 个性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