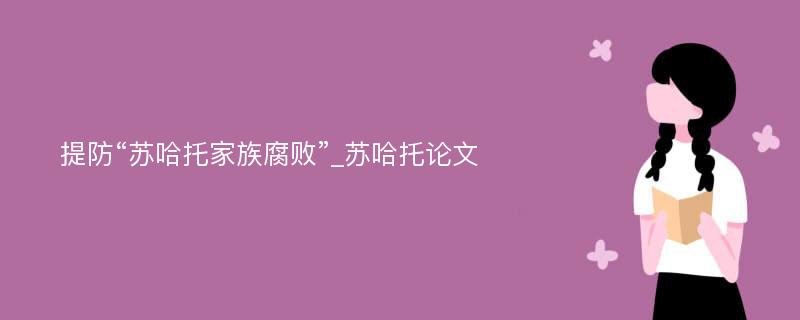
警惕“苏哈托家族式的腐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腐败论文,家族式论文,苏哈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族式腐败是当今社会腐败的新的发展趋势
在最近十年,湖南省共查处了厅级以上的巨贪12人。这12名巨贪中,竟有5人是与其子女一起联手索贿受贿的。这5人是:湖南省机械厅原厅长林国悌、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张德元、湖南省物资厅原厅长谭照华、湖南省建材工业集团原副总经理王德元、湖南省交通厅原厅长马其伟。
《中国青年》1998年12期刊登了一篇《“九爷”炒地记——中国第一大非法炒地案内幕》,文章写的是一位曾因“借债市长”之名而誉满南粤、被人称做“九爷”的原官拜广东省常务副省长、人大副主任的于飞,怎样与其两个女儿、一个女婿相勾结,利用手中执掌的大权,软硬兼施,从买地到卖地,轻而易举地(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获得了1.66亿元的“巨额利润”,使原本赤条条的于家小姐魔术般地变成了亿万富婆……这一案件,确实发人深省。
那么,这类腐败案件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腐败案件呢?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苏哈托家族式(‘一家两制’)的腐败”案件。即父辈们利用手中掌握之权力,通过炒地皮、炒批文、炒基建、炒银行信贷、炒合资(假合资)等方式,不断地、急速地将国有资产向其家族(首先是子女类的直系亲属)转移(向港澳转移,向外国转移)。这儿的所谓“一家两制”,指的是父辈们从政,子女辈从商——国营的、集体的、私营的、合资的等都有。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权钱交易家庭化”,即因为“一个人只要在社会结构中拥有一定的权力,他所在的家庭就可能共同享用权力带来的成果”,于是,“掌握者提供权力,家庭成员收取费用”。为何权力者本人不直接“收取费用”呢?邓伟志先生的解释是:“掌握权力的人的公职身份妨碍他进行交易。”
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和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女婿,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和他的儿子陈小同,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兼东莞市委书记欧阳德和他的儿子、女婿们,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与他的女儿、女婿,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鸿运和他的儿子,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和他的女儿褚映群,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阎健宏和她的儿子刘博,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同庆及其儿子陈励生,广州市公用事业局原局长丁振武和原副局长崔鸿聚及其子女,沈阳大案中的慕绥新及其前妻、女儿、女婿(在沈阳市先后注册了十几家公司)……这些腐败案件,实际上都是“苏哈托家族式(‘一家两制’)腐败”的翻版。
家族式腐败的特点
这种“苏哈托家族式腐败”有哪些特点?
第一,掠夺财富的疯狂性。“苏哈托家族式腐败”侵吞国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而且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大量案件表明,这类家族式腐败所侵吞的国家资财,不是几万、十几万,而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是成亿的,因而对国家经济的危害特别巨大。
靠着在首钢拥有绝对权力的父亲上台的那个花花公子周北方,仅在香港和内地就有6套豪宅(香港的一套竟花费了2800多万港币,相当于一个效益好的分厂的全年利润);生活上也极度奢侈腐化,1994年7月至1995年2月在东湖宾馆住宿五次,共22天,竟花费50多万元。在对外交往中,因为他的无能、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使首钢损失了十几亿元人民币。他本人也是贪得无厌,在1993年6月至1994年4月之间,先后在经济交往中以生活资助费、中介费等名义收受贿赂928.2万港元。
那个云南烟草大王“褚时健家族”,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港元、30万美元,褚时健的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那个“欧阳德家族”,“大公子”在去港前担任欧阳德领导下的东莞市某区区长。1992年他拉来了一个外商合作经营住宅小区,并以区政府名义担保贷款5000万元用于住宅小区建设。1993年1月,“大公子”去了香港。时隔两月回到东莞,摇身一变成了“港商”,区政府将住宅小区50%的股份转让给这个“港商”,他从这个项目上捞钱达数千万元之巨。同时,这位“大公子”又与区政府合资开办了一家夜总会,他一人占有70%的股份,投入的资金全部从开发住宅小区时由政府担保贷到的5000万元之中支付(名副其实的“空手倒”)。“二公子”见此法来钱容易,照样仿效,去港转了一圈儿回东莞后也变成了“港商”。这位“港商”借用东莞市一建筑公司工程队的牌子,把凤岗海关的2000万元推土工程强夺到手。仅此一项他就获利700万元。陈柱豪是欧阳德的二女婿,本来只是市政府车队的一名司机,在“调”到市公安局任车管科的副科长之后,独揽汽车牌照发放大权。几年时间,他竟受贿28.5万元港币,通过炒卖地皮又获取非法收入150多万元。
震惊中外的湛江走私案中的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同庆除了自己拼命敛财之外,上任第一天,他就带着老婆、弟弟、儿子、女儿,一一和当地领导见面。他的弟弟陈捷庆很快就开始承担工程赚大钱;陈同庆还玩命似的鼓励、怂恿、包庇他的那位被人称为“走私汽车大王”的儿子陈励生走私。陈励生在198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凭借其父陈同庆的权力和影响,先搞假手续派驻香港,成为香港居民后返回湛江成立假合资公司。其父陈同庆为了让儿子有足够的走私资金,亲自出面,让市政府出面担保境外银行给陈励生的公司贷款400万元港币,疯狂走私。从1996年初到1998年9月,陈励生共走私汽车1900多辆,柴油43000多吨,偷逃税款1.9亿元人民币,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
……
在这里,仅仅是举了几个“腐败家族”的案例,其腐败数额之大,给国家造成损失之大,实在惊人。因为资本外逃是一种不容易受到惩罚、风险较小的腐败方式,所以那些大大小小的“苏哈托家族”——就像于飞父女一样,将用权炒来的资本迅速地转到香港——只要有可能,尽量将腐败来的资本转移到境外,这已是造成我国国有资产向境外、国外大量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一些经济学家研究,“我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的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而且进入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而在这类国有资产流失中,家族式腐败就占有相当的比重。据国有资产管理局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抽样调查和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得出的基本判断是:从1982年到1992年,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损失高达5000多亿元。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199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量26000多亿元的1/5,比1992年财政总收入4188亿元还多800多亿元。即便按这个据说是“比较保守”的数据计算,我国目前平均每年流失、损失的国有资产也达500多亿元。这就意味着我国每天流失国有资产达1.3亿元以上。
第二,“苏哈托家族式腐败”的廉价性。这种形式的腐败“成本”特别低,其腐败的动力特别充足,而且又是在腐败者权力管辖之内,所以特别容易实施。
“苏哈托家族式腐败”的“成本”特别低廉,它无需经济上的投资,也无需技术上的准备,它需要的只是父辈手中的大权,因而经常是“空手套白狼”,“无本万利”,再加上它所得来的利益完全由家族内部“独占”,所以家族腐败者的腐败动机就“特别充足”,腐败的动力就特别巨大。他们会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后果(甚至自己的脑袋都不惜)进行腐败。
因为这种腐败是在自己权力系统下进行的,所以这种腐败最容易得逞。就拿于飞来说,他明明知道有一个凡“用地1000亩以上须经国务院批准”的政策,但是,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他在自己的权力系统中抛出了两招。第一招:“居高临下、大政府对小政府”。于飞为了利于理直气壮地要地,于1992年5月,背着省领导,提出要在大亚湾规划区划一万亩土地由省政府组织省内公司开发,并在惠州市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踏看和选定了开发前景较好的樟树埔地段。于飞对在场的惠州市和大亚湾的领导拍着胸脯说:“省经协办要在这里搞成片开发,为熊猫汽车和壳牌石化企业配套,待壳牌石化企业上马后,副产品加工能赚很多钱,赚了钱之后,也可分点给你们。将来你们也可以向惠州方面发展,需资金,我可以帮助你们组织几十个亿来开发。”第二招是:“抛砖引玉,打上取下”。1992年6月,于飞和省经协办一位副主任及随行人员,约惠州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广州谈购地签约事宜。在这次谈话中,于飞授意省经协办要地6000亩,价格要极低。惠州方面一听这回事,一股被“策划”的羞辱感涌向心头,但又不好“抗旨”。于是,6000亩地一分为二,2500亩是省经协办的,3500亩就是德成公司的。过了一段时间,惠州方面推说没有6000亩地。于飞又说先给香港德成公司吧,外商嘛,弄不好就会告状,省经协办的地就放一放吧。就这样,于飞通过弄权,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女儿的“香港公司”弄到了一般人搞不到的3500亩地。
第三,“苏哈托家族式腐败”败露的艰难性。因为“苏哈托家族式腐败”是“血缘型”的,是“家族型”的,很少会发生一般腐败案件那种“狗咬狗”式的“内讧”。一般来说,侦破这种家族式腐败是极其艰难的。在印尼,若苏哈托政权不垮台,其家族腐败之黑幕就不会暴露;在中国,若陈希同不被揪出,也很难将其缺德少能的儿子陈小同送上审判台。在“台上”腐败了的父辈们总是会千方百计、不惜手段地利用自己手中之权力去保护自己腐败家族的利益的。譬如那个无德无能的周北方。在1991年春天,首钢的两位党委副书记曾商量设法让周北方离开首钢,并请北京市委组织部领导做了妥善安排。一次,他们趁首钢主要负责人非常高兴之机,婉转地建议让周北方离开首钢,到北京市管理好、水平高的外贸部门工作,谁知这位“第一把手”听后勃然大怒:“我就一个儿子在首钢,你们都容不下,我退休以后,你们还让不让我回首钢!”由于父辈的包庇纵容,周北方越来越有恃无恐,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总之,只要父辈们的权力不倒,他们子女及亲属的腐败就会永远继续下去。
第四,“苏哈托家族式腐败”危害的严重性。“苏哈托家族式腐败”至少有以下三个危害。
一是它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由于存在大大小小的“苏哈托家族式腐败”,社会资金越来越向少数有权人和有钱人手里集中,因而迅速形成了一个“一夜之间”就暴富起来的阶层,于是社会中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少数人”以非法手段占有了“多数人”的财富,加大了社会两极分化的速度。譬如,全国居民存款高达54万亿,而在这54万亿存款中,有10%的储户占有80%的份额,高达432万亿,其中不乏那些通过“苏哈托家族式腐败”的腐败者。
二是它使国民心态严重失衡。他们牟取的暴利可谓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因而挥金如土,生活糜烂,腐化堕落,从而使国民心态严重失衡。譬如,那个花花公子周北方就是这样,他一家在香港和国内总共占用六套住房,在香港的三套分布在三个不同地区,其中在香港的半山富人区购置的一套公寓,花费高达2000多万港元;境内的三套住房为珠海一套四居室、北京二套二居室。他一人还占用了奔驰、宝马、奥斯莫比尔等五辆豪华型轿车。周北方还利用职权把其妻调入海外总部,不上班照领工资,还配了专车。他还利用关系,为其妻子、女儿办理了长住香港的“绿卡”。周北方在国外期间,更是大肆挥霍,进行猖狂的违法犯罪活动。他行踪不定,今天在新加坡,明天飞到马来西亚,后天又到了秘鲁,海外媒体称他为“小旋风”。周在海外吃住要高档宾馆,泡妞要美貌小姐。其挥金如土的手段,连许多西方的资本家都瞠目结舌,自叹弗如。像这样的生活方式怎能不引起人民的愤慨?!
三是它会毒化社会的氛围。家族式腐败者为了掩盖腐败行为,拿出腐败得来的一小部分钱财去贿赂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从而加速了对权力系统的“精神污染”。譬如,就于飞及其女儿的那个案子来说,于大小姐顷刻之间就变成了“亿万富婆”,她惟恐夜长梦多,急于要将这些非法所得转到香港,为了漏报增值税,利用“银弹”向有关人员进攻,行贿金额达数百万元,致使一批干部被击中落马,同样成为“阶下囚”。
总之,由于“苏哈托家族式腐败”的存在,社会矛盾和剧,降低了民众对社会的信任,导致民心丧失,社会凝聚力下降。所以说,它是社会转型时期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对这种“苏哈托家族式腐败”应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第一,要加深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的认识。我认为,在“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堡垒”中,“苏哈托家族式腐败”是“堡垒”中的“堡垒”。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哈托政权的垮台,就是被他自己所构筑的“家族式腐败堡垒”攻破的(印尼现任总统瓦希德认定,苏哈托家族贪污的赃款高达450亿美元),是苏哈托家族集团腐败毁掉了苏哈托政权。历史发展证明,全世界像苏哈托政权那样因为家族腐败而垮台的例子是很多很多的。
如,1986年,从政40多年、担任20年菲律宾总统的马科斯因腐败引起民众反抗而被推翻。在执政的40多年中,马科斯利用公共权力受佣金,拿回扣,吃党费,无所不为,为自己聚敛了大量财富,仅在瑞士已查明的私人存款就高达10亿美元(有人估计为30~50亿美元)。1984年世界银行的一个秘密报告说,1978-1982年共贷给菲律宾137亿美元。其中31亿美元用途不明,多数被马科斯夫妇化公为私,存入自己银行的账户。在他的领导下,相当长的时期里,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的40%被各级政府官员贪污。
还有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及其家族营私案。当全斗焕依靠“肃军政变”爬上总统宝座之后,全斗焕家族就开始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并依仗权势进行疯狂的贪污受贿。其胞弟全敬焕担任全国“新村运动”中央本部事务总长之后,贪污受贿金额达78亿韩元(约1080万美元)之巨;其胞兄全基焕从一个普通警察迅速爬上“泛韩旅行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贪污公款27亿韩元;他的堂兄全淳焕原是经营水产的一个小批发商,一跃成为大田市水产市场株式会社总经理,受贿两亿韩元……据统计,全斗焕倒台后被揭出的家族腐败有十余人之多,其胞兄、胞弟、堂兄、妻弟等七名皇亲国戚被韩国司法当局分别判处十个月至七年的有期徒刑,罚款66.4亿韩元,退赔7.98亿韩元。
前苏联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的“驸马爷”丘尔巴诺夫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官,当上“驸马爷”之后竟迅速地被提升为中将,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自此之后,他专横跋扈、排除异己,生活上腐化堕落,并大肆贪污受贿,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共受贿654200卢布(约合105万美元),最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当然,根据有的学者对苏哈托政权式腐败问题的研究和分类,我们国家的腐败类型与上述国家不同,属于发展中国家腐败的第二种类型,即这类腐败大量产生于中层和下层政府官员中间,最高层腐败的程度低。所以,我们应该吸取苏哈托政权垮台的严重教训。
在当前反腐败的斗争中,我们队伍中还有不少人不愿意承认(有的人则是认识不到)在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大大小小“苏哈托家族式腐败”,不愿意看到这种腐败的危害性。这是最最危险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凸显出来。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指出:“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所谓“苏哈托家族式腐败”,就是高级干部与其家属、子女一起搞特殊化,一起搞腐败,不同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搞特殊化、搞腐败的形式更高明、更现代了。所以问题不是你“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客观本身就存在。
第二,中央纪委有明文规定:“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但是,我们的社会有这样一个毛病:只是习惯于发批示、发文件,至于指示、文件下达后的执行就另是一回事了。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会出现大大小小的“苏哈托家族式腐败”案件?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些“高级干部”根本不将中央的指示、文件放在眼里,轻的是眼开眼闭,重的仍是我行我素(或是采取变通的办法,我在我的权力管辖内安排你的子女,你在你的管辖权内安排我的子女,来一个“等价交换”)。所以在发完指示、文件之后更重要的是检查。在这类检查中,首先高级干部要自查:作为高级干部有义务将自己亲属、子女的工作情况向同级党委进行汇报,接受同级党委的监督。此外,光是自查还不行,还要“纪委检查”和“交叉检查”,将“一般检查”与“重点检查”结合起来。为使这类检查不走过场,将有问题而检查不出来的作为渎职、失职来处理。只有加大平时的“检查力度”才能将“苏哈托家族式腐败”避免于萌芽之中。
第三,认真清查过去炒地皮、炒批文、炒基建、炒银行信贷、炒合资(假合资)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尤其是要认真清查过去在这类非法操作过程中暴富起来的高级干部及其亲属、子女。认真执行高级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鉴于当今暴露出来的“苏哈托家族式腐败”的高级干部及其亲属、子女拥有大量的财产不明来历案件的发生(譬如,陈希同就在大庭广众中申报过自己的家庭财产,一点问题都没有),建议对这方面的制度进行认真修订,堵塞漏洞,以进行更好的监督。与此同时,要完善我国的金融体制,防止腐败资金大量地外流。
第四,要重视对“苏哈托家族式腐败”类型案件的举报工作,建议实施“有奖举报制度”,对凡是提供有关“苏哈托家族式腐败”重大案件线索并能为国家挽回重大损失的人,应该给予重奖。与此同时,要采取得力措施保护那些坚决抵制“苏哈托家族式腐败”的干部,对那些挟私打击报复者要严肃查处。惟有这样才能鼓励广大干部与群众与“苏哈托家族式腐败”斗争的积极性。
第五,要放手发动舆论监督功能。“苏哈托家族式腐败”并不怕党内监督,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和贪来的钱)去对付、化解这方面的监督。他们最怕的是舆论监督,最怕的是舆论曝光,最怕的是舆论的穷追猛打。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怕乱思想,要给予舆论监督部门“穷追猛打”的权利。只有将这些案件彻底大白于天下,彻底曝了光,才会使一些执法者不会“手下留情”,才会真正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总之,鉴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如法制的不健全、家长制的残余、封建皇权思想的余毒等等),在当今反腐败斗争中,对大大小小“苏哈托家族式腐败”斗争是最具风险性的,最为艰难的,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是最大的,如果我们不采取严厉的措施,那么一定会遗患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