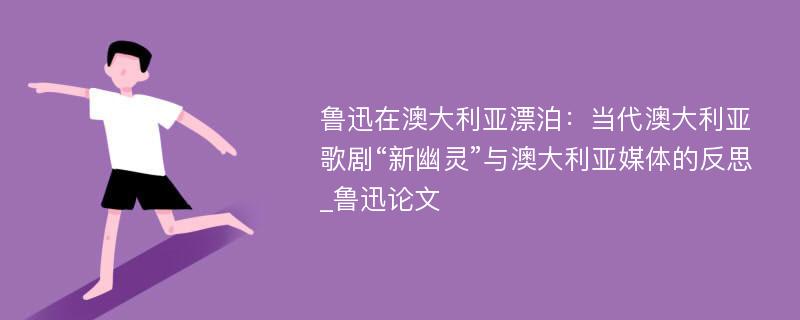
跟鲁迅徘徊在澳洲:当代澳洲歌剧《新鬼》及澳洲媒体的反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洲论文,鲁迅论文,歌剧论文,当代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9月,我在浙江绍兴举办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递交了一份讨论鲁迅小说英文译本的论文。记得事后一些当地的记者问我们这些西方学者,为什么会对鲁迅及其作品感兴趣。尽管我们给出了各种理由,但当地的记者似乎只认可这样一点理由:阅读鲁迅的小说可以找到一条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捷径。这使我想起了我在澳大利亚所讲授的课程——“想象中、认知中的中国”(China Imagined and Perceived),此课实质上是观照中西方差异下有关文学作品中东方主义形象的一种“展开”。课上我让学生读几段亚瑟·史密斯(Arthur Smith)189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的篇章。这本书的流行并不是由于它公正地描述了中国人,而是由于若干读者以为它可以为西方人(实际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在中国的商人)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提供一条捷径。如此说来,我这篇文章将要讨论的歌剧也可以看作是澳大利亚观众(或至少那些做出回应的批评家)想象中可以理解当代中国的一条途径,另外如果说艺术的隐喻暗含真相,那或许更加确切些。
一个澳大利亚现代歌剧,取用一个不寻常的剧名叫《新鬼》(Fresh Ghosts),于1997年11月27日在戏剧院首演,地点位于墨尔本圣科达(St Kilda)区前卫的“非百老汇”类型的场馆。这个海滩区以“非主流”文化中心而著称。歌剧《新鬼》在墨尔本和悉尼(舞台在悉尼新城区音乐剧院)两地上演,演出票每晚都销售一空。剧中演员大多数为中国人,用英文来演唱,但在舞台旁边配有明显的中文字幕。观众里中国人不少,但大多数还是白人。歌剧节目单的“卖点”即为整体的汉字:顶端用中文写“根据鲁迅的短篇小说《药》改编”,“新鬼”两个汉字在中部(一张图片上叠加一个六七岁小男孩的图片,他目光低垂,手里抓着正在安慰他的看似年轻母亲的手),封面底端的文字是“英文演唱,配中文字幕”。歌剧配乐由著名作曲家于京君(1957年生于北京)创作,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1970年代末)和东京音乐大学(1980-1983)①,并于1988年夏天在美国马萨诸塞西部的探戈伍德音乐中心(Tanglewood Music Center)师从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汉斯·维尔纳·亨策(Hans Werner Henze)和奥利维·纳森(Oliver Knussen)。1984年他和一名来华学习中国音乐和语言的澳大利亚女孩结婚,这促使他移民澳大利亚②。
在“新鬼”开演之际,于京君已经“在日本、意大利、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他的第二故乡),获得了二十多个作曲奖项”③。然而这不单单是一个中国人的“离散作品”,源文本系“格伦·佩里(Glen Perry)改编自鲁迅小说《药》”,《药》首次刊登于1919年5月的《新青年》上。《新青年》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杂志④。这个小说被选编到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中,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篇著名的核心文本并被编入中国高中的语文教科书中。这是格伦·佩里的第一个剧本。舞台导演是道格拉斯·霍顿(Douglas Horton),音乐总监是马克·萨默贝尔(Mark Summerbell),舞台设计师是黛尔·弗格森(Dale Fergus on),灯光师是艾弗特利·索罗博斯(Efteri Soropos)。一名来自墨巴音乐学院(Melba Conservatorium)的学生许英(音译)作为女中音饰演华大妈。胡海珊(音译)作为女高音饰演倩影(音译)(革命家夏瑜的情人),那时她刚刚毕业于墨尔本维多利亚艺术学院歌剧工作室。谢琨饰演革命家夏瑜,他生于扬州,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然后在墨尔本大学维多利亚艺术学院学习,并且成为广受人们欢迎的“(旅澳)三大中国男高音”之一。男低音蓝晓明饰演刘氏,他曾在四川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男中音格雷·罗利(Gary Rowley)饰演了双角色(康氏和医生),他是全剧中唯一的成年非中国人演唱者,之前曾在塔斯马尼亚学习和演出,于1990年加入维多利亚州立歌剧院。10岁的单大卫(音译)与马修·德盆哈(Matthew de Pehnha)共同饰演了华小栓这一角色。我们后来得知,单大卫“现年十岁,才18个月前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他的祖父母在他4-6岁时教他弹钢琴,目前他在韦弗利山小学合唱团演唱。”⑤
小说中的一段情节发生在传统的绍兴茶馆里,但是剧中这个场景却转移到了香港或者海外某个有小推车的中国粤式茶餐厅里。全体演员和乐队都穿着制服、黑色裤子,红棕色上装的翻领口袋上戴有易于识别的白色星星徽章(让我想起了银桃子和“银柿子”徽章,鲁迅小说中阿Q的自我革命和纳粹让犹太人所戴的“羞耻的徽章”⑥)和领带(这就让我们想起旧中国长辫子,也许是暗指革命成功以后中国人剪辫子了⑦)。
这幕歌剧的名字是戏剧的关键(至少海外的中国观众是如此理解的)。“新鬼”取自鲁迅的一首旧体诗。此首写于1931年2月末的诗是用来纪念他的朋友柔石和其他年轻左翼作家的,他们于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对英语使用者来说,诗中的暗示并不明显,除非对193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上海有详细的了解。但是“鬼”这一字至少暗示了一种令人心神不安或给人强烈感受的死亡形式,而“新”字则表明了“刚刚被杀”。鲁迅很可能在刚刚得知柔石和其他左翼作家牺牲的当晚写下了这首诗,这些牺牲者后来被合称为“左联五烈士”。两年后,鲁迅在一篇悼念他们不幸牺牲的著名散文《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情感,他得知了他们被处决后:“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⑧
这首诗原本没有标题,但是中国有人用《为了忘却的记念》为其标题,或是用由诗歌前四字组成的名称《惯于长夜》来命名。1934年12月20日,鲁迅在写给编辑杨霁云的信中,提到过这首诗是《悼柔石》⑨。这首诗的格式是七言律诗。我将诗原文复制如下,后附上我自己参看《鲁迅诗集》而翻译的英文版本⑩: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To long and sleepless night I've grown
accustomed in the spring;
Fled with a wife and babe in arms,
my temples are graying.
Mid dream there comes an image faint-
a loving mother' s tear;(11)
On city walls the overlords'(12)
e'er-changing banners rear.(13)
I can but stand by looking on
As friends become new ghosts,(14)
In anger face bayonet thickets(15)
And search for verse ripostes.
The poem intoned,my gaze turns low-
one cannot write such down.(16)
Moonlight shiners with watery sheen
upon my jet-black gown.
此处我将新鬼翻译成“new ghosts”而不是“fresh ghosts”是为了避免在澳大利亚英语中“fresh”词义的诙谐意味。可是澳大利亚批评家特雷弗·海(Trevor Hay)发现标题中使用“fresh”一词“比汉语中与‘新’字对应的‘new’更容易唤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可以联想到鲁迅关于1931年“左联五烈士”痛苦哀悼的那首诗:“忍看朋辈成新鬼……”(17),具有文学渲染色彩。这里我的推断是特雷弗·海显然是已经读过了我书中翻译的诗文(他引用一句I can but stand by looking on,as friends become new ghosts于此,但未加标注)。
在回答澳大利亚采访者提出标题的意思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于京君说:“这是中国的意象,意思为刚死的人,出自鲁迅1918年所写的短篇小说《药》。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为著名的作家之一。在汉语文学世界中,他的知名度相当于布莱希特(Brecht)和乔伊斯(Joyce)在西方文学界的地位。”(18)他继续解释剧中的台词道:“小说讲述了两个中国女性深爱自己所爱之人,也彼此爱护的故事。一个女性是因为谋杀政府官员而被行刑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恋人;另一个女性是儿子因致命疾病即将死去的母亲,心神错乱的母亲被迫接受可怕的用人血治病的方法。”(19)
这里我们有两处有意思的转换性词语:一处使用了“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另一个词就是“恋人”——剧中引入了一个新角色,一个年轻的女性名叫倩影,她是革命者夏瑜烈士的恋人。这可能是为了符合以恋人为中心的西方歌剧传统,但也可能是为了以悲剧为中心。刽子手的角色康氏(《药》中是康大叔,前文提到的是康氏,下文按康氏翻译)(20)和医生两个角色是由唯一的西方演员格雷·罗利扮演。剧中小栓的角色由两个男孩单大卫与马修·德盆哈共同出演。单大卫那时只有十岁,依我看(我两次看过他们的演出),小栓在夏瑜被行刑后,就在他自己也死于肺痨前,唱到The Rains Will Come(“大雨将至”),是全剧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咏叹调:它以男孩清澈的高音预言性地进行宣告,那声音紧紧萦绕在人们心头而久久无法消散。的确,这个男孩用他地道的英语演唱给澳大利亚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克莱夫·欧康纳(Clive O’Connell),这位平时非常苛刻的批评家评论道:
用双语字幕的原因是不明确的。一个可能就是普通话(即中文字幕)可以照顾来看演出的中国观众。英文演唱的作品出现字幕并不是新鲜事,正如我们在布里顿(Britten)的澳大利亚歌剧作品中看到的一样。事实上有些演员有着很重的口音,然而,10岁的单大卫却没有。他到澳大利亚仅有18个月,口音就和你听到的校园里回荡的当地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小孩儿乡音一样。为了配合整体效果并且合拍,他的角色要求很高。单大卫处理得相当好,展现了他既精通旋律又能够掌控沉重道具的才华。(21)
节目单的第一版告诉观众:“《新鬼》改编自写于1919年的《药》。故事发生在清朝末期,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剧情如下:
第一幕:华大妈的茶馆
一位医生在给华大妈的儿子,得了肺痨的小栓检查。医生提供了奇怪的“治疗”方法,说如果这也不见效的话,就没希望了。稍后,倩影进来了,她问华大妈是否有办法为他的朋友夏瑜治病,夏瑜好像因为得了什么病在发烧,很痛苦。小栓神志不清地昏睡着,他出了很多的汗,并在噩梦中发出喃喃的梦话声。
第二幕:小城另一处房间
倩影回到夏瑜身边,夏瑜是激进分子,认为中国的病态社会急需治疗。墙上传来砰砰声,夏瑜为此大叫起来,倩影用华大妈的治疗办法,使他平静下来,这让他陷入了昏睡状态,但是并没有消除他的气愤。
第三幕:隔壁康氏房间
我们看到了康氏,一个刽子手,用力地敲墙,诅咒他的邻居。刘氏,一个政府官员,进来告诉康氏有关本省下一次行刑的细节。刘氏得了头痛病,康氏向他推荐了华大妈的茶馆。
第四幕:茶馆
华大妈给发脾气的小栓准备一种治病药方。刘氏进来说他的头痛得厉害。华大妈一边准备药方,一边说出了医生的诊断,小栓的肺痨无药可医。刘氏告诉华大妈他知道一个可靠的药方,说让华大妈明早在古轩亭口见他。
第五幕:华大妈的白日梦
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行刑的场景。华大妈清醒过来想起了该做的事情。她一直走到十字路口。刘氏走到她面前给了她一包东西,华大妈拿出一包钱来交换这包“药”。
第六幕:茶馆
华大妈边给小栓服药,边哼唱摇篮曲,好像在等待药方发挥魔力。华大妈看见一只黑乌鸦便去赶它离开,以免给她的儿子带来厄运,因为今天是神奇的一天。倩影进来说夏瑜不见了,她怀疑他因为批评皇权而被当局带走了。华大妈试图去安慰她,但是她却是在批评夏瑜。倩影开始发怒并激烈地为夏瑜进行辩护,说他是出于对同胞的真正热爱才会这么做的。康氏和刘氏进了茶馆开始谈论一个名叫夏瑜的罪犯已被执行了死刑。倩影怀着恐惧踉跄着去袭击刘氏但是却被康氏控制住了。刘氏警告倩影说,她如果知道夏瑜的话,最好永远别再提他的名字,否则她也会消失。倩影挣脱了康氏的控制逃跑了。刘氏才解开给华大妈的药方的秘密。
第七幕:墓地
我们看到了两个坟墓。夏瑜的坟墓被一圈白花包围,分外明显。华大妈进来,随后是倩影,她看到花后满脸疑惑。她无法相信是家人或朋友送来的花,因为他们都怕因夏瑜而受牵连。同时,华大妈看见一只黑乌鸦,她去驱赶它。处于危险中的倩影开始和墓中的夏瑜谈话:“夏瑜,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叫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乌鸦没动。他们一起哀悼,然后华大妈引导着倩影离开了坟地。
对我来说,前两幕对夏瑜的描述使我想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中那些领导者的老故事,凭借其最初的火热和幻觉而引发了一场以宗教为旗号的运动来摆脱中国的噩梦。这是以洪秀全为原型的,而不是徐锡麟和秋瑾,给海外华侨重温了一些历史的记忆,非常像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书在海外的影响一样(22)。但至少一个澳大利亚批评家说剧中的象征使用的太过分:
傻子都知道让情节简化,可这个作品中的象征手法用的太多了,有一处重要的象征手法使用不当之处在于最后两幕华大妈用大声喊叫要驱赶的黑乌鸦。它出现在小栓吃人血馒头之后并再次出现在墓地中,预示着死亡和阴暗。使用乌鸦的意图并不是原创,它并没有给作品本身增加生气,我想可能是因为剧本中或演出中没有把乌鸦表现得很清楚。此外,这一策略已经被试过了,并且做的更加令人信服——像《波基与贝丝》(Porgy and Bess,译者注: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乞丐与荡妇》,音乐家周小燕怒斥,如此修改是媚俗,并阻止使用此名)中的《贪婪之歌》(buzzard song),布里顿的《麻鹬河》(Britten’s Curlew Rwer),还有《狂情露西亚》(Mad Lucia)……
先将误解放在一边,在这个时尚的室内剧中,作品中有几处确实让人难以理解。演出空间后墙上的一组屏幕有时候看起来像X光的屏幕,一排排的人物照片叠加起来好像都是中国人,在布局中不时露出裂缝。这可能是在表明满清王朝政权的本性,他们给每个人都“立了案”。这些裂缝代表着直言不讳的死者,如夏瑜。或许如此,但是屏幕太远了而无法明确其意义。当歌剧开始时,大卫·山被一盏持续升起到他够不着然后又降下来的中式灯笼戏弄了,之后又引诱他去摸/抓它。这是在象征自由?生命?希望?还是一个活泼的灯光师?
在墓地那幕剧中,水浇到了门楣上,通往剧场之外,有一种声音效果,像下雨一样。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又说明了什么呢?是眼泪?还是悲伤?
我想这些使人分心的戏剧动作与剧情之间并没有多大关系,除了于京君的这个作品比较简单之外。他在剧中的演出丝毫不做作,甚至在最赤裸的时刻,也不让人觉得它自高自大。
但强加一种深不可测的效果只会给观众的理解增添麻烦。
《新鬼》和最近的一场室内剧演出《梦回藻海》(Wide Sargasso Sea)形成极大的反差。前者努力使剧情紧凑,但剧情大过了音乐,正是因为《新鬼》出色的演唱和简练的表演才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掌声。(23)
我发现第一场开场时,在茶馆里有明显的“后现代”场景。演唱者背后屏幕上有咖啡杯碟在叮叮当当地摇动、灯具的投影,母亲和医生两人穿着红色西装夹克和黑色裤子,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香港茶餐厅里的服务员。这样的时间框架对观众来说非常不和谐,因为他们刚被节目单告知故事发生在满清王朝最后时光里的1911年。剧中的故事环境设置,将我们所处年代和晚清年代场景安排得几乎一样多。而且演唱的歌曲多数是高分贝的,这引起了至少一位批评家(克莱夫·欧康纳)的抱怨:“于京君教人演唱的风格引发了许多大声争论,尽管在某些方面让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如此……”(24)他继续说到:“如果排演中可以找到共同点的话,那就是这些歌唱演员已经接受了西方音乐观念,看起来指挥是聚光点,作品显得有些自负。谢和蓝演唱的声音处处都很大,尽管这样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但效果最终令人感到疲倦。”(25)这很有趣,因为西方观众眼里对中国歌剧的期望是一种优美雅致轻柔的形式,或者有起伏的技巧。关于“大声争论者”的抱怨提醒了我,鲁迅在《社戏》中写道他自己不喜欢京剧,当然鲁迅是在谈论那些华而不实的形式和吵闹的表演。这里,澳大利亚的批评家也许在暗示着用“分贝”来替代更直接的批评。
澳大利亚媒体代表在首演后试图直接采访我,我拒绝了他们。原因很简单:我第一次看此剧主要是想找出故事情节和鲁迅原著短篇小说的差别(如上文提到的,是有相当大的差别)。这不是说与原著不同是件坏事,因为二者根本就不是同一种艺术形式。再说华人观众都认为此歌剧有影射,而我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不愿意扯那么远。澳大利亚批评家特雷弗·海(Trevor Hay)这样评论道:
一家茶馆的经营者不顾一切地想要找到一个治疗她儿子肺痨的药方(鲁迅的父亲是肺痨患者也是庸医的受害者),被一个阴险的政府官员说服,她只需在清晨和他在十字路口见面——按中国的民间风俗,充满了悲惨的恶魔、邪恶和早夭的地方——给他一定的费用换取“灵丹妙药”。她见到了官员,付了钱,拿回了一个装着药的神秘包裹。通过茶馆里一段对话可表明(英文唱词,中英文字幕显示,回想起中国歌剧的唱词通常是伴随有演员克服方言的问题),我们知道当这个交易进行时,一个来自鲁迅家乡的年轻女性在1907年被公开行刑,当时鲁迅在日本学医。那时发生了母亲给儿子的灵丹妙药事实上就是一个沾了死刑犯的人血馒头的事件。(26)
海先生的分析有着耐人寻味的意味。华大妈最初并没有意识到“灵丹妙药”到底是怎么来的,或是什么东西,他们(普通的中国人)在迷信或不人道的行径中得到豁免——将谴责直接归罪于不法的政府官员。这是一种批判,而它事实上更加“政治”。并且与鲁迅对社会的理解相比而言,把迷信当作检测人性的工具进行拷问,还显得不够深入。不论剧本是否故意提起这些问题,它们是受过教育的澳大利亚人会联想到的。公平来说该剧至少“暗示”了观众的视听。
与克莱夫·欧康纳不同,特雷弗·海指出了乌鸦的象征意义。看来他是做过了认真的外部研究的,他在评论中写道:
这是《新鬼》作为歌剧来表现的主要困难。我怀疑只有那些真正读过小说的人才能意识到最后一幕剧中乌鸦振翅飞翔承载着什么含义。关于它的含义,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大量的讨论,最终归结出一个理念,乌鸦并不是迷信而是一个迁移了的灵魂,它飞出了一段令人生畏的距离,而不是真正以革命为目的地。第七幕和最后一幕的剧情告诉我们:“当它们离开的时候就听到振翅,他们仰望头上盘桓的乌鸦,并肩走向地平线。”(笔者注:第一版的剧情没有这个细节)。鲁迅写的最后一句话中有乌鸦飞起来“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这样的表达,当他松开箭杆的时候,可怕的现实随之消失,找寻遥远的和可能毫无希望的革命理想主义。很奇怪,该剧将可怕的现实处理的非常之好,此刻还加入了一点浪漫主义——就是这个要素可能在歌剧中看起来最为正常不过的——翻译很脆弱无力。没有鲁迅的铁笔做指引,乌鸦无路可寻。
然而,这个令人敬佩的充满想象力的作品的主要成功之处在于重塑了小说的精华——舞台是鲁迅最伟大的著作所固有的,在这里可以感觉到鲁迅的存在就像一个掌控舞台的导演一样。如同在京剧中,情节最小化,套路多余且多功能化……服装程式化……而于京君混合着西方歌剧风格的唱腔,带有张力的“高音”效果令人陶醉,舞台上一小组混合的管弦乐队伴奏就像传统的京剧一样,二胡令人回想起鲁迅出生地的音乐,那令人心酸的韵律支配着演出的进行。我想鲁迅本人也会惬意地惊讶,中澳灵感的共鸣是多么真实,多么脍炙人口!(27)
显然,节目的改编版本是为了回应欧康纳(无疑还有其他观众)的几点评论。原来的第七幕情节结束得非常突然:“华大妈看见黑乌鸦就去赶它走。在她处于疯狂的时候,倩影开始在墓碑前和夏瑜说话:‘瑜儿,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乌鸦没动。他们一起哀悼,然后华大妈引导着倩影离开了墓地。”特雷弗·海对乌鸦和它飞走的象征做了大量的分析。作为一名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他很审慎地对待这一问题。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吸引过不少读者的注意,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甚至还选了一幅画有乌鸦的传统水彩画作为他的书脊(28)。尽管如此,可能是由于没有仔细阅读文本,夏志清的分析还不够准确。他说:
这个萧瑟的场景,母亲的哭泣,从她的绝望中挤出了相信老天是公平的信念,变成了对于意义和革命未来的象征性疑问,对于中国现代小说这是想象力的高度的问题之一,强烈的以乌鸦为讽刺,呆着那里一动不动,像狮身人面像一样沉默,完全不顾母亲的哭泣。(29)
我在想这可能导致了澳大利亚批评家的误解。捷克学者米莱娜·多莱热罗娃—韦林格洛娃(Milena Dolezelova)通过猜测乌鸦是“令人恐惧而宣泄的代表革命的象征”(a frightening but cathartic symbol of revolution),得出了小说的传奇性结构分析(30)。这种解释说不定源自中国。如果真的如此,她没有做出标注,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她自己的想法。然而我会说我们在短篇小说(31)或剧本文本中没有找到那样的证据。我想的是文本(和叙事)证明了乌鸦起飞作为象征的另一个方面,即转变旧观念(如迷信、封建思想等)。中国(和世界)将从另一个方向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正如乌鸦并没有飞回坟墓。
关于鲁迅本人,澳洲观众得了些什么信息呢?节目单给出了一段作家简历:
鲁迅,作家、散文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翻译家,于1881年生于中国浙江绍兴。父亲因患肺结核病,鲁迅的家庭状况沦为贫困状态。
两年后,鲁迅放弃学医,他开始认为“医学毕竟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自从我发现文学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佳手段时,我决定推进文学运动。”
随后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变得非常积极,在大学和学校里教书,并声援进步的中国学生。他被迫间歇性的躲藏,最终到1927年蒋介石夺取政权,放弃了抗议政治活动。此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小说、散文诗、散文、翻译和学者的创作中去,包括《中国小说史略》。
他的小说传达出了他自己在“没有希望的绝望”和敦促自己去相信“未来有希望”之中的挣扎。他的小说有着断断续续的现实、强烈的情感、激昂的氛围,通常在悲剧的震惊或绝望的尖叫中达到高潮。
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和肺结核抗争的三年里使他越加衰弱。弥留之际他写下了:“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32)
鲁迅在写小说时使用白话文是一场革命,他在白话文写作中也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他的文学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并将中国文学引入世界。所以他被称为现代中国文学之父。
当然,这段关于鲁迅的简历实际上是有错误的。把鲁迅家的衰败归咎于他父亲的疾病,是从《呐喊》作者序言中总结出来的,并没提到他祖父卷入的科场舞弊案。他的短篇小说和学术文章被误解为1927年后所写,那时他没有避开政治(事实上变成了反对派的领导者)。强调鲁迅内心的绝望与希望之挣扎也许折射出汪晖的《反抗绝望》(也许是对于京君或其他中国演员的影响)或更早的可能是李欧梵相关论文的影响。有关他小说的结构的描述是独特的:“他小说有着断断续续的现实、强烈的情感、激发的氛围,通常在悲剧的震惊或绝望的尖叫中达到高潮。”还有结论:“他的文学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并将中国文学引入世界……”这是鲁迅研究学者近些年来才注意到的。
十多年后的现在,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可以确切地说该剧是讽喻性的,在提及更多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时,中国的旅澳观众与澳大利亚的批评家二者的感想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这部作品以生动的创新加上鲁迅作品与现在的联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文学上的曲笔和象征,比如乌鸦,起初可能让人难以理解,但是激发了澳洲人的讨论和研究。最后,鲁迅作品在后现代的包装中变得新鲜并让人可以理解,它提到了很多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首要考虑的事情,正如小说《药》在1920年代的中国让读者认同它对社会不人道的批判。这是“光明正大”的改编了——歌剧、诗歌和题目中的暗喻。用特雷弗·海的话来总结:“我想作者本人(鲁迅)也会惬意地惊讶,中澳灵感的共鸣是多么真实,多么脍炙人口!”(33)这真是很独特而难得的含意深远的国际歌剧。
①该剧目给出的作者简历如下:“于京君(作曲家)于1957年生于北京,1980年代初在东京音乐大学学习作曲,师从汤浅让二。1985年定居澳大利亚,三年后成为美国探戈伍德作曲研究员,师从伦纳德·伯恩斯坦、亨策和奥利维·纳森。于京君的音乐获得了许多国际奖项(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和澳大利亚)。1991-1994年间他获得了就职岗位和保罗洛·洛恩管弦乐作曲第二名,这是澳大利亚的最高作曲奖项。他的音乐被很多管弦乐队和乐团演奏,包括伦敦交响乐团、BBC交响乐团、现代乐集、探戈伍德音乐中心管弦乐团。于京君的作品也被选入当代音乐节,包括慕尼黑双年展和哈德斯菲尔德音乐节。”(《新鬼》,第二页,原节目单)
②见文章《获奖作曲家的第一部歌剧》,帕梅拉·拉斯金(Pamela Ruskin)著,澳大利亚杂志Opera-Opera,第240期,1997年12月,第5页。
③出自于南墨尔本的室内音乐剧的档案网站,进入11/10/11。
④见《新青年》,第六卷,1919年5月第五号。
⑤这条信息以节目的第一版为基础,见《新鬼》第3-4页。
⑥以这种方式,即鲁迅的方式,演员变得既是迫害者又是受害者,正如阿Q一样最终具有双重角色。
⑦见文章Simplicity,Intensity in Yu Ghosts:Simplicity Can Do Well Without Extra Frills,克莱夫·欧康纳(Clive O’Connell)著,Opera-Opera,第241期,1998年1月,第19-20页。
⑧《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四卷,第374页。此散文的英文译文是我自己的翻译,见英文《鲁迅选集》(外文出版社,1956-1960),第三卷,第202-213页。杨宪益和戴乃迭的1980年校订本以《为了忘却的记念》为题,《鲁迅选集》(Lu Xun,Selected Works,1980),第三卷,第234-246页。
⑨《鲁迅全集》(1961),第十卷,第224页。
⑩见寇志明《The Lyrical Lu Xun:A Study of His Classical-style Verse》(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6),第149页。
(11)母亲也许是鲁迅的母亲,由于得知儿子被捕可能会死的消息,为他的命运而焦虑生病,或者为柔石的双目失明的母亲,鲁迅写道:“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地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柯勒惠支(Kae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鲁迅选集》,1961年,第四卷,374页。)
(12)词语“大王”在历史中指匪盗的首领。讽刺、押韵,由汉字“大”和“王”组成。一个评论家认为其特指蒋介石;见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香港:雅典美术印制公司,1972),第五卷,第102页。
(13)周扬时期(1950年代)的解释(《鲁迅全集》1961,第四卷,第555页)有这样一句话:“提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各种地方军阀势力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了武装冲突的爆发。”可以说鲁迅对此一定会愤怒,但我没看出这武装冲突与国民党加强自己在上海的专政统治有什么关系或国民党如何镇压、逮捕和杀戮上海左翼作家。我倾向于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香港:雅典美术印制公司,1972,第五卷,第103页)的解释,他认为“旗”是指口号和宣传反映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变化无常的政治,从刚刚开始鼓吹“法制”到第二天就变成了“训政”的教条。如此武断的指令反映了政治变化在公民权上很可能会影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大都市中的安全(他们在当时在中央政府当局管辖下的城区内还很活跃)。国民党政府处决“五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在文章《五烈士之谜》(论文集《黑暗的闸门:中国现代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8,第163-233页)中,已故批评家夏济安暗示,那五个年轻作家之死可能是因为上海共产党内部两个派系内讧而致。根据夏济安的叙述,1931年1月17日,上海巡捕突然闯入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筹备会议,逮捕柔石和其他几位“反对派“。人们猜测“五烈士”可能被党内的人出卖了。如此考虑,解释这首诗的时候可能会牵扯进来更多的暗示,因为鲁迅不是不可能发现了这种两面派的行径。此外,事实上这些作家是由外国租界宪兵队移交过来,被国民党当局处决的,在鲁迅看来,始终是国民政府应承担这些罪名。
(14)“忍看”这里的意思是“要忍受着看见”(一些丑恶的或无法忍受的东西)。“忍”在这里不必当“岂忍”“怎么忍受……?”来解释。原版诗文记录在鲁迅1932年7月11日的日记里。他写的那一幅给Yamamoto Hatsue(山本初枝)在忍看的地方写作“眼看”(可以解释为“就在眼前发生”,“无助的看着”或“被动的看……”)。尽管后来校订是鲁迅自己的,与不同版本的文本相比,原来的意思更加明确。人刚被屠杀后会变成“新鬼”在唐代诗人杜甫(712-770)的一首反对战争的诗《对雪》中出现过:战哭多新鬼……“新鬼”这个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左传》的一处记载: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左传》,文公二年)。
(15)“刀丛”(直译“刀的丛林”)让人想起佛教地狱中刀林剑树,在这了用来象征敌人的武装镇压或痛苦的折磨。
(16)因政府审查此行诗很重要,没机会写首这样的诗(或其他流露出这种悲伤和气愤的),鲁迅自己解释到:“中国那时候不允许出版这样的诗文。我们被封闭的比一个罐子还严密。”《鲁迅全集》(1961),第四卷,第374页。
(17)特雷弗·海(Trevor Hay)的评论文章《室内歌剧的交感魔力》见Real Time(澳大利亚音乐中心出版),第23期,1998年2月-3月,第40页。我在墨尔本大学教书时,墨尔本大学的图书馆和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可以找到《鲁迅诗集》的影印本。
(18)(19)帕梅拉·拉斯金(Pamela Ruskin),《获奖作曲家的第一部歌剧》,澳大利亚杂志Opera-Opera,第240期,1997年12月,第5页。
(20)这是对小说的普遍误解——在鲁迅原著中康氏不是刽子手,只不过是茶馆里的一个大嘴巴顾客,他说他自己是华大妈的恩人,是他提议弄来沾了死刑犯人血的馒头。
(21)(23)(25)克莱夫·欧康纳,第20、19、19页。
(22)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纽约:诺顿出版社,1996)。
(24)Simplicity,Intensity in Yu Ghosts:Simplicity Can Do Well Without Extra Frills,克莱夫·欧康纳,Opera-Opera,第241期,1998年1月,第20页。
(26)特雷弗·海,第40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批评家(特雷弗·海)确实做了很多的研究,不仅是在鲁迅的旧体诗上,还有对他的小说(注意其提到了《呐喊》)以及有关若干学术评论(他的一些看法让人想起了王德威关于鲁迅著作中“吃人”的主题)。
(27)(33)特雷弗·海(Trevor Hay)的评论文章《室内歌剧的交感魔力》,见Real Time(澳大利亚音乐中心出版),第23期,1998年2月-3月,第40页。
(28)在1971年平装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中。
(2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版,(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9),第35-36页。这一版(遗憾地)删除了书脊上的乌鸦水彩画。
(30)米莱娜·多莱热罗娃—韦林格洛娃,《鲁迅的药》,默尔·高曼编《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第231页。
(31)短篇小说的结尾:“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鲁迅《药》)They had not gone thirty paces when they heard a loud caw behind them.Startled,they looked round and saw the crow stretch its wings,brace itself to take off,then fly like an arrow towards the far horizon.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文,见双语Call to Arms《呐喊》(外文出版社,2002),第96-97页。
(32)《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上海重排第1版,第6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