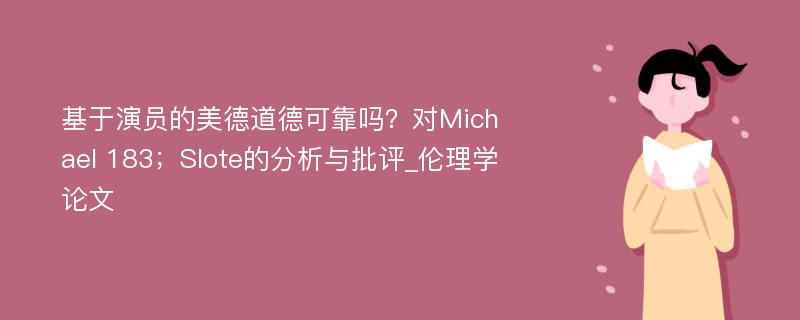
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可靠吗?——对迈克尔#183;斯洛特的分析与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迈克尔论文,美德论文,可靠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界的重要思想者,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试图建构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新框架,即“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agent-based virtue ethics),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当代美德伦理学的深度与范围。在他看来,“一种后维多利亚时代甚或后基督教时代的美德伦理学,不可能简单地回到亚里士多德。因为他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大相径庭。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把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的东西,用来创造一种独具现代形式的美德伦理学”。(Slote,1994,p.719;下引Slote文献仅标年份和页码)
关于斯洛特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背后所蕴涵的思想预设和知识观念,以及其对于我们可能具有的启示性价值,笔者已在《斯洛特的美德伦理学及其心理学预设》一文中有所讨论。(李义天,2009年b)同时,笔者在那篇文章中也提到,斯洛特的独特思路容易招致怀疑,因为他为了追求理论的纯粹性和极至性,似乎不惜沾染主观主义的弊病。(同上,第88页)因此,我们对于这位依然活跃的当代学者,需要保持冷静的批评眼光。本文将借鉴学术界的相关批评,对斯洛特美德伦理学的上述问题予以剖析,指出其可能存在的局限。
一、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斯洛特的理论特色
就整体而言,斯洛特对美德伦理学的理解是恰当的。他清楚地意识到,“美德伦理学在其描述中主要采用美德论术语,它要么把义务论术语当作是从美德论中派生出来的,要么完全不使用它们。因此,一种美德伦理学主要思考何为高贵或卑污、何为令人赞赏或令人叹息、何为好或坏,总而言之,它的焦点在于行为者(的内在品质)。……这已经足够接近地说明了美德伦理学的特征及其各种形式的共性:既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古代美德伦理,也包括现代的美德伦理学,比如19世纪英国伦理学家詹姆斯·马蒂奴(James Martineau)”。换言之,“令美德伦理学同其他思路区分开的首要之处在于,它以行为者为焦点(agent-focused)”,它将自己的理论重心置于“有美德的个体以及使其成为美德之人的内在品质、倾向和动机”。(1997,p.177)
然而,斯洛特也注意到,虽然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学同样注重行为者的品质和动机,同样“从关于品质特征和动机的(美德论)评价中引申出关于行为的评价”,但是,它“关于品质和动机的评价,却建立在有关人类福祉或繁荣的伦理事实的基础上,而没有把这种评价看作是根基性的、无需更深伦理基石的东西”。(ibid,p.207)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目的论框架中,配称“美德”的优良品质和动机并非自身即善,而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实现道德行为者的人生幸福或繁荣;那些被称作“美德之人”的行为者,也是因为他们能以.“幸福”为大前提进行目的论的实践推理,并能发现具体情境中的适度之处而做出正确的选择。对此,斯洛特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有美德的个人被描述为这样一个人,即他能够看出或识别出,在一定情况下什么是好的、正确的或恰当的事情。而这种说法清楚地表明,有美德的人做出光荣的或有美德的行为,乃是因为这件事是光荣的,而不是因为有美德的人选择了做这件事才使之获得了光荣的状态。因此,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行为的伦理状态并不是完全从品质特征、动机或个人这里引申出来的。(1992,p.89)
这样,亚里士多德主义就将“正确”或“善”的标准置于行为者之外,行为的评价尺度最终绕过“美德”而挂靠在“幸福”上。但是,“幸福”是关于行为者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内在品质的概念,因此,评价行为的最终标准便成为内在品质之外的某种东西。不仅如此,就连内在品质本身的伦理属性也需要通过“是否有助于实现行为者个人的幸福”这种后果论命题得到说明(1997,pp.207-209);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学很难摆脱“后果论”以及“伦理利己主义”的指责。
面对亚氏美德伦理学的上述困境,为了实现一种更纯粹的美德伦理学,斯洛特完全从行为者的内在品质出发,以行为者为基础来建构理论框架。在他眼里,“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就是把道德行动或伦理行动的状态当作完全从独立而根基性的动机、品质特征或个体的美德品质中推衍出来的东西。像这种基于行为者的思路,至少在关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标准解释中是找不到的”(2003,p.203),它“明确地代表了一种极至或激进的美德伦理学类型”(ibid,p.204)。自此以后,斯洛特在1997年与马西亚·拜容(Marcia Baron)、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合著的《三种伦理学方法:一场辩论》以及2001年出版的《源自动机的道德》等作品中,日益强调“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的内涵及其合理性。(cf.1997,2001)
根据这条思路,一个正确的行为既不是由于行为者依赖有效的外在规则,也不是由于行为者顾及令人满意的结果或目的,甚至不是由于行为者发现了当前情境中的适度之处,而是因为它源自行为者的某些优秀品质和动机。不仅如此,这些品质之所以“优秀”并配称“美德”,也不是因为它们像亚里士多德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有助于实现幸福的人生目的,或者像康德主义所想象的那样能够实施道德立法,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合乎直觉地令人钦佩(admirable):
如果有理论声称,某些总体动机本身在直觉上就是道德善的、值得赞赏的,而与其结果无关,也无需将其建立在特定的规则或原则上,那么,它对动机的强调便是根基性的。每种伦理理论都必须有个出发点,而基于行为者的道德理论则想说,对他人给予仁慈或关怀的道德之善,在直觉上就是如此显见,而无需更进一步的道德基础。(2001,p.18)
就此而言,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的最大特征,并不在于它根据动机和品质去评价行为的正确性,而在于它把这些动机和品质视作最根本的东西。斯洛特明确指出, “以行为者为基础的观点不讨论‘什么构成了人的幸福或福祉’这类问题,从而将有关内在品质的美德之善确立为根基”。(1997,pp.209-210)根据那些内在品质的细微差别,斯洛特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作为内在力量的道德,作为普遍仁慈的道德,以及作为关怀的道德。在斯洛特看来,这三种动机或品质都无需考虑或引入“幸福”、“功利”和“规则”,便能呈现为善,并促使行为者采取正确的道德行为。
二、思想洁癖与主观主义:斯洛特的缺陷
然而,被称为“美德”的内在品质和动机凭什么是善的?依据何在?对此,斯洛特并没有提供说明,因为他已经把这些品质和动机定义为“不假外求的/独立的”(independent)和“根基性的”(fundamental)。(2003,p.203)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论证方式在古典时代和启蒙时代有可能行得通,因为当时的人们仍相信,如果一物无法得到其它东西的说明,则意味着该物“本身”处于极至的位置;然而在现代社会和学术界中,这种论证方式却是十分乏力的:因为,除非获得经验的证明或群体的承认,否则现代人认为没有理由相信某个事物或概念的真实性。当斯洛特把美德品质说成“独立的”、“根基性的”时候,他实际上切断了作为内在品质的美德与外在世界的各种关系及其可能性。
其实,斯洛特也曾表明,被称作美德的品质和动机之所以令人钦佩,是因为受其支配的行为者可以实现关怀自我与关怀他人的对称。(1997,p.186)不过,囿于“最纯粹的美德伦理学”的标签,囿于自己曾声称美德是“独立而根本性”的善,斯洛特始终不愿意张扬作为内在品质的美德与外在世界的这层关系。
对于这方面的批评,斯洛特自己也有所觉察。他说:“(有人认为,在基于行为者的理论中)道德生活就是捍卫好动机并依此行动,而不管究竟什么才是外部世界所需要的。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基于行为者的理论将会导致一种孤闭症,与世界相隔离,而这会使人怀疑,像这样的伦理学怎么可能充分有效。”(2001,p.17)但是,他却认为这种指责并不恰当,因为基于行为者的美德理论容许行为者通过美德动机而探求事实、理解事实。斯洛特以“仁慈”为例说道:“如果一个人是真的仁慈或是想对社会有用,那么,他就不能把好东西仅仅放在身边,或者只给予他目力所及的人。比如说,除非一个人在意到底是谁亟需帮助以及他们有多么需要帮助,并且,这种在意反过来确实使他想要知道相关事实或者使他能尽力得到相关事实,以便于他的仁慈可以真正发挥作用,否则他的仁慈就不是最充分意义上的仁慈。因此,根据这种动机行动的人必须对其周遭世界保持开放,与之谋求联系并受之影响——他的决定不应当是在与我们大多数人都视作道德相关事实的东西相隔巨大的情况下做出的。因而,对基于行为者的观点来说,一个动机的道德价值,比如仁慈,并不是游移不定的(free-floating),而是依赖于它所属的那种内在状态,尤其依赖于它面对世界时所拥有的目标和期望以及它所付出的努力。”(ibid,pp.17-18)
然而,斯洛特的辩护却给人这样的印象,即他不得不承认世界上存在与经验事实相关联、并通过这些经验事实而论证自身合理性的内在品质。通过上引斯洛特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斯洛特其实很清楚:仁慈是不是“真的”仁慈,完全跟行为者在具体情境中的状况,以及该行为者采取何种策略应对当时的局面有关。而既然连仁慈都还需要通过包含具体内容的考虑来展现自身,那么作为美德的内在品质怎能被断言为“根基性的”或“不假外求的”呢?反之,如果斯洛特不接受这种推论,那么他就得承认有两种仁慈:一种是纯粹的仁慈本身,另一种则是具体的仁慈;前者是独立的、本身就令人钦佩的,而后者则是“本身令人钦佩”的东西添加了事实内容后的具体表现。然而,这种二分法能够成立吗?此外,即使不深究这种二分法的辩护方案是否合理,也仍有一个疑问悬而未决:究竟什么是“就其本身”(by itself)?这种说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在道德哲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为了证明其思想体系中的某个环节绝对合理或正确,喜欢采用这种“纯粹式的”论证策略:彷佛只要将某个对象的合理性归诸“就其本身”,便能“不证自明”而让自己和听众心满意足。可是,“不证自明”恰恰意味着“尚未证明”!或许以前的人们还可以通过诉诸“上帝”的万能或“理性”的可靠,为其思维体系的阿基米德点予以“不证自明”的证明,但是,现代社会已浸润过足够的世俗性,现代的思想也已经受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冲击或洗礼,而随着上帝的死亡和理性的衰变,各种宏大叙事已无力再为这种论证策略提供资源了。况且,当现代道德哲学中的诸多理论体系都把自己的起点标榜成“就其本身即是正确”的时候,这种理论上的自负却因为内容上的相互抵触而演变成无休止的相互指责,结果导致整个现代道德哲学遭遇信任危机。(参见麦金太尔,第8-9页)因此,试图通过“就其本身”等说辞来证明某个思想环节的合法性,这种做法与其说是达到了思想的极点,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思想洁癖或理屈词穷的表现。
退一步说,就算我们在哲学语境中承认“就其本身”的说服力,也承认这些内在品质本身即善,可是我们又如何保证它们能导致正确的行为呢?无论仁慈或关怀,都只表明行为者性格中的某种善意的倾向,而并不代表行为者的决断及其具体行为必定恰到好处。比如,一个仁慈的行为者可能会对不该仁慈以待的对象依然表现仁慈(如东郭先生对待狼),或者,一个行为者的仁慈可能不被对方所接受,反被视为对其的轻视甚至侮辱(如向某些自尊意识很强的残障人士提供帮助)。这些例子都说明,诸如仁慈和关怀等内在的心理倾向,对于实现美好的生活状态并非充分条件。与之相比,对当下境况的准确判断、对具体行为方案的恰当选择等实践判断,也十分重要:当一个行为者试图展现自己的仁慈品质时,他应该对相关对象的处境、身份和需要,以及自己的能力与行动选项予以深思熟虑,否则就可能“好心办坏事”。换言之,美德伦理学需要“好心眼”和“热心肠”,但也需要一种“好心不办坏事”的审慎态度。所以,当基于行为者的理论把行为的正确性全然挂靠在动机的正确性上,而断言好的动机必然带来正确的行为时,这种看法不可避免地有过于乐观甚至主观之嫌。
面对以上质疑,斯洛特通过引入“总体动机”(overall or total motivation)概念,将总体动机与具体动机(particular motivation)区分开来,为自己的美德理论加以辩护。。
斯洛特的“总体动机”概念并不严格:他有时把“总体动机”理解为“考虑更大范围的道德对象”,有时又说“总体动机指人的一般秉性”。(2001,p.33)由于前者会使“总体动机”呈现功利主义色彩,因此斯洛特更多的是在后一意义上阐述“总体动机”。
在斯洛特看来,作为内在品质和动机的美德应被理解为总体的道德倾向,而不是某个具体、单一的行为动机。一方面,如果行为者的总体动机是好的,并且其具体动机合乎总体动机,那么他就能采取正确的行为。即便“一个满怀仁慈或关怀动机的人没能阻止伤害,或没能帮助他所希望帮助的人们,他的行为也不能被算作道德错误”。(ibid,p.34)因为斯洛特相信:“如果一个人的每次努力都是为了发现相关事实,并且在行动时十分细心,那么,无论有多么糟糕的事情发生,我认为他也不能被批评为行为错误。……如果这些坏结果是由于他缺乏理智或是缺乏学习而导致的认知缺陷,那么,我们对他的表现只能予以认识上的批评,而不能予以道德上的批评。”(ibid)可见,斯洛特的看法是,以美德为总体动机的行为者必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其行为不能被接受,也只是证明行为者的具体动机或具体判断有缺陷,而不是总体动机出了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行为者的总体动机没有反映美德的诉求,那么即使他的具体行为产生了好后果,也不能称为正确;即使他的具体动机偶然合乎了美德的要求,也依然不值得称道。从这个角度讲,斯洛特实际上取消了“本身正确的行为”和“因动机正确而正确的行为”之间的区别。因为在他看来,那些被人们认为“本身正确的行为”,其实是受到正确动机支配的行为;而那些出于不良动机的行为(比如为了扳倒政敌而检举腐败官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本身正确”的事情,因为该行为者的总体动机是坏的。(2003,pp.205-206)所以有学者认为,斯洛特的美德理论具有整体主义的(holistic)特征(Copp and Sobel,p.548);但这种特征却是以混淆上述二者的伦理区别为代价的(达斯,第17页)。
“总体动机”的辩护看似为斯洛特的美德理论提供了一个更深层的基础,但它实际上只是在解释上构造了一层新的理论维度。由于缺乏现代心理学的经验证实,这个关于心理取向的概念更多的是反映了斯洛特在道德心理结构上的理论设计,或是他对人性的理解,而非反映了真实的经验事实。况且,即便一个人具有这种总体动机,也不必然保证他能始终遵循该动机行动,而不受到主观或客观条件的阻碍。斯洛特看重行为者内在品质的伦理意义,固然是对行为者的信任和尊重,但是,这种信任却很难说服现代人:因为现代社会对“人”的设想已经改变了很多;现代人更倾向于认为,把道德对错的确认方式置于行为者的“内在品质”,这是不慎重地将之托付给私人意见,必然陷入不可靠的主观主义。
三、内外之别:斯洛特为什么会犯错?
将判断行为的尺度完全挂靠于行为者的内在品质,这种做法在当代美德伦理学中并不鲜见。(cf.Brandt; Wallace)由于斯洛特在这方面讨论很多,表现突出,因而可作为该类型的代表。这类美德伦理学有一个预设,即将“内在性”视为美德伦理学的最大特征,或者将美德伦理学与规则伦理学之间的最大差异看作一种“内外之别”。用斯洛特自己的话来讲,“基于行为者的观点,明确地允许行为者受制于那些控制他们行为的道德要求或约束。但是,那些要求、标准和约束都是从内部(from within)开始起作用。”(2003,p.208)
但是,笔者认为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包括规则伦理学在内的任何伦理学都必然提供相应的道德心理说明。规则伦理学也一直试图从行为者的内在本性或心理结构中寻找可以充当行为规则之基础的内在要素。无论是康德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它们之所以赞赏某些行为,也是由于这些行为是被行为者凭借某种规范心理而自觉选择的。在此意义上,规则伦理学并不认为自己仅关心外在的行为;它同样需要内在于行为者的某些态度和观念作为支撑物。(Conly,p.85)尤其对康德主义而言,内在动机至关重要。可见,树立外在的行为规则这种做法与行为者的内在因素并非不相容。反过来,美德伦理学其实也一样关注外在行为。仅就斯洛特而言,虽然他反复强调要把美德伦理学完全基于行为者,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理论主旨恰好是为了梳理和澄清行为的根据。这意味着,他是在“行为如何正确”这一层面上展开运思的。
斯洛特之所以会有不准确的理解,部分原因在于,当代美德伦理学是通过批判规则伦理学而兴起的,这一背景决定了它更多的是通过与后者相异乃至相反的特征来确认自身。(Louden,p.202)既然规则伦理学的焦点是行为者的外在行为及其规则,那么美德伦理学自然就要考虑与“外在行为及其规则”相对立的方面:于是,从“行为”到“行为者”、从“外在”到“内在”的迁移,就很容易被看作美德伦理学的最鲜明特征。然而,这样做将导致两个问题:
其一,在“内在-外在”的维度上,将美德伦理学的任务局限于至多只是论证其聚焦点在内在因素而非外在因素,至于内在因素的结构和属性如何则未被视为必需的解释任务。这种理解势必削弱美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即“美德”的丰富性和说服力,因为究其本质而言,美德是行为者针对伦理生活的不同情境而做出的恰当的心灵反应。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具体的美德都有各自的适用性,背后隐藏着各自的判断和预设。斯托克尔(Michael Stocker)认为,与其像斯洛特那样泛泛地理解“美德”的内在性,不如去关注和辨析每个美德的各自特点,尤其是关注它们各自所揭示的心理学内涵。 (Stocker,p.693)在此意义上,美德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通过“考察品质和美德的‘内在运作’(inner workings)”而理解行为者的本性与道德心理,而不是像斯洛特那样“外在地对待美德,仅仅反复地告诉我们,美德是令人钦佩的品质”。(ibid,p.694)
斯洛特对“美德”的理解不但比较笼统,其更大的问题在于,他只是在“性格品质”或“性情特征”(character)的层面上而非实践理智的层面上理解“美德”。斯洛特说:“纵观西方伦理学史,大多数道德哲学家都把美德看作是理性的形式。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我们的理性是人类最独特之处,并且作为实践存在者,我们正是通过拥有并运作实践理性来实现和展示我们的卓越性的。……不过,有些我们通常一直认为是美德的品质特征,却不能完全被理解为实践理性的某种形式。……它们与其说是一种理性反应,不如说是行为者个人的心灵力量(strength of mind)。”(1997,p.203)这样,“美德”概念主要意味着某种性格趋向和心理机制,而非实践推理的模式。
但是,将“美德”仅理解为好品质或好秉性(disposition)对于美德伦理学而言是不够的。因为美德伦理学最大的合法性及其意义,并不在于它对行为者优良品质的倡导,而在于它能给出一套优越的道德推理方案,使得行为者能够将其内在品质真正地呈现为优良的状态。假如像斯洛特这样,把“仁慈”和“关怀”列入基本美德的清单,却又对于它们如何恰当地发挥作用以指导行为者的实践运思过程语焉不详,那么,这种理论在操作性和指导性方面就很缺乏了。事实上,真正令人困惑而需要美德伦理学解答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应该表现出仁慈或关怀”,而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因此,美德伦理学除了强调优良的内在品质外,更关键的是要告诉人们如何践行那些优良的内在品质,使之表现为“真正的”优良品质。
其二,上述“内外之别”只不过表明美德伦理学“由外至内”进行“翻转”,诉诸内在于行为者的因素来说明问题,却并没有证明这种“翻转”是可行的。然而,假如令人钦佩的品质并无其他因素作为依据,怎能保证一个拥有如此品质的人不会在主观上犯错误呢?达斯(Ramon Das)深刻地指出,“按照斯洛特的观点,行动的评价应该完全从动机的评价中推导出来”,但是,“做正确的事情和出于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情之间的区别的实践的重要意义,不折不扣地在于它将对行动的评价和对动机的评价区别开来。因此,任何试图将前者还原为后者的企图都不能抓住这一区别的实践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理由,斯洛特试图将这一区别的重要意义搪塞过去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达斯,第17页)
在达斯等批评者看来,如果“将正确性定义为一个有美德的人在此情此景下的所作所为而没有加以任何限制,它似乎就允许这样的可能性:一个有美德的行为者有时也许会采取一些我们在直觉上就会认为是错误的行动。”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中,即使一个有美德的人也可能会故意地、在完全意识到相关事实的情况下采取错误的行动。有人或许认为这在心理上或概念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种看法似乎没什么根据。常识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承认美德之人的错误行动不仅可能,而且经常发生”。(同上,第19页)概言之,假如作为内在品质和动机的美德缺乏稳固的经验依据,同时又不能说明自己的内在结构与正确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那么,这种私人化的“动机”就会堕落为主观化的“玄机”。它非但不能保证正确行为的发生,而且无法传达,让人捉摸不透、不可仿效。(Louden,p.206)
或许在某些领域比如宗教中,从行为者的“内在”生发的东西是可信或可接受的。但在伦理问题上,完全诉诸行为者的个人因素则被视作不可靠的主张,毕竟伦理问题不是单独一个人的问题。尽管一个人可以独立地作判断,但判断是否恰当或准确却需要凭借外在于行为者的规定性或框架来衡量和说明。伦理学相较于其他学科固然更注重行为者的内在品质和主观态度,但是,像斯洛特那样把关于道德实践的规范意义和标准尺度从外在彻底地“翻转”到内在,并且排他式地凭借行为者的内在因素来说明道德推断的合法性和行为的正确性,却是漏洞诸多。斯洛特的美德伦理学之所以容易被指责为主观主义,不是因为它看重行为者的内在因素,而是因为它太过纯粹甚至固执地看重这些因素。
四、结语:回到亚里士多德主义
其实,斯洛特很早就注意到,把行动的评价标准置于行为者的品质是一种极端的看法。(1992,p.92)在《源自动机的道德》中,他也明确承认,“一种观点可以是基于行为者的,但又不会仅因行为是由一个美德之人或一个具有善的内在状态(inner state)的人所做,就把它们当作正确或令人钦佩的。以行为者为基础的理论也不一定认为……如果一个美德之人有所行动,该行为就会因为是他做的而自动地属于好事或令人钦佩之事”(2001,p.16)。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必然”的情况,至少存在两种原因:
第一,道德行为者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自由意志的存在令道德行为者不会像机器一样完全合乎因果律地展现其内在状态。因此,斯洛特似乎很谨慎地表示:“(基于行为者的)这种观点并未断言,具有令人钦佩的内在状态的美德个体在其能力范围内一定会选择他所喜爱的那种行为……因为,考虑到自由意志中相容论(free-will compatibilism)的几种合理形式,一个仁慈之人完全能够选择一些并不表现或展现其仁慈(的内在状态)的行为。因此,如果一个人是完全仁慈的,并且看到另一个人需要帮助,那么他大概会施以援手,并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展现其内在的仁慈。但是,拒绝施以援手,同样也在此人的行动能力范围之内。如果他确实拒绝了,那么此人的行动也就没有展现仁慈,因而……大概也就不那么令人钦佩。”(ibid)然而,斯洛特的这种辩解非但没有回应批评者的质疑,反而代表着一种无奈的理论退让:因为这种言辞明白不过地揭示出,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其实无法证明有美德的行为者必定做正确的事情。
第二,从理论诉求和设计框架上讲,斯洛特的美德理论强调人们应通过“动机”而不是“结果、原则或目的”来判断行为。因此,这种理论就是一种关于行为判断标准的学说。它当然会把合乎其标准的行为视为正确,但是,“合乎该学说的判断标准”并不等于“合乎伦理生活的标准”。斯洛特自己也意识到,“如果基于行为者的理论把我们从直觉上(intuitively)就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某些行为予以较高的评价,如果它告诉我们的许多所谓正确的事情看上去(seem)是很糟糕的,那么,这种基于行为者的观点就至少值得质疑,我们有理由怀疑它所说的‘有些特定动机在根本上就令人钦佩’这种说法是否准确。”(ibid,p.18)然而,既然斯洛特已经断言对行为的评价完全是从对动机的评价中引出的,那么他又凭什么断言某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或“很糟糕的”呢?按照上述引文的说法,这种断言是从直觉上作出的。但是,这不就意味着,在动机之外其实还有“直觉”在充当行为的标准吗?不仅如此,“直觉”标准似乎更优先于“动机”——因为根据直觉所做出的评价能够用来矫正根据动机所做出的评价。就此而言,斯洛特的辩解不但无法自圆其说,而且会由于“直觉”等极具主观性的概念而愈发陷入被质疑之中。
其实,重视行为者的主观心理、强调行为者的动机在道德行为中的意义,这种做法本身是合理的:在当代伦理学语境中,这种策略也确实是美德伦理学确证自身的有效途径之一。斯洛特的问题乃是在于,为了强化内在动机的重要性,为了保证美德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切断了行为者对任何外在规则的依赖,不允许行为者的动机中包含针对任何目的的企盼,从而使内在动机变成了空洞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东西。因为我们无法在头脑中形成“无内容”或“无指向”的动机。“动机”虽是一种主观之物,但它必须包含具体的事实内容。不妨说,“动机”是行为者根据相关的道德传统和立场,对具体情境中的道德事实进行识别和判断的一种“思虑”:有的人喜欢以目的论的模式来思虑,有的人倾向于采用道义论或功利论的思虑框架,有的人则更加率性地诉诸“情感”或“直觉”;但无论哪种形式的思虑,都包含或指向着某些生活事实。斯洛特的“动机”却不是这样:它们仅仅表现为一种意愿、冲动和心理倾向,只是一些道德心理的形式规定,而未涉及行为者心理活动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模式。在这种被阉割了的动机概念中,生活的幸福和人生中的各种善是找不到位置的。尽管这种动机可能更加纯粹,但同时也显得更加“干瘪”——尤其是相比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学而言。因为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动机是通过对完整的美好生活(即“幸福”)有所向往、对当下的事实情境有所感知而构成的。亚氏美德伦理学虽然也把行为的正确性挂靠于行为者令人钦佩的品质,但它同时又让这些品质进一步地以“幸福”为旨归。也就是说,任何优良品质或心理倾向(美德)都是由于有助人生的完善和生活的美好才富有价值,而不是“凭其自身”就莫名奇妙地令人钦佩。不仅如此,在亚氏美德伦理学的语境中,“幸福”的具体内容是由生活共同体所决定的。因此,与斯洛特的观点相比,亚氏美德伦理学淡化了行为者自身的道德分量,而突出了人们对共同生活情境的依赖和理解。如果说这是理论上的“退却”,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这种“退却”是值得的,因为这种“退却”为内在品质和动机(美德)提供了一种更易理解的生活框架,它更合乎人们伦理交往的事实。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发现,斯洛特的美德伦理学与亚氏美德伦理学对“美德”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只是把“美德”理解为一种合乎生活直觉或常理的(甚至是带有情感特征的)心理倾向,而后者则是把“美德”理解为一种关于实践事务的理智运作方案。在后者看来,单纯地把“美德”理解为优良品性或心理趋向是不够的,因为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是什么使这些品性成为“美德”,怎样才能确保在行为过程中展现这些品性。阿默里·罗蒂(Amelie Rorty)指出,各个具体美德的确是人的品质,但是,“当一组品质成为一个美德时,那些居于该美德核心部分的想法与范畴上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形成针对具体情境的阐释;它们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并且通过把其他的关切放到背景的地位上而界定什么是最值得注意的东西。要做得好,并且做得让人放心,一个人就必须恰当地设想并阐释各个具体情境,并且把这件事办得可靠。而如果缺少恰当的认知结构……那么好的意愿也就成了空洞的。那些部分地构成了各种美德的认知秉性总是有其向度(tropic)或指向的(magnetizing):对情境的感知和阐释可以推导出那些恰好适于它们的反应。”(Rorty,p.137)就此而言,美德伦理学的关键任务在于,揭示并论证这种恰当的认知结构和运思方案的特征及其优势。换言之,作为一种伦理学方案,美德伦理学不能停留在对好品性、好心肠的层面上,它还需要给出能够支撑这类“品质”的理智框架——正是这种与众不同又特别卓越的理智取径,使得道德行为者表现出具体的美德言行。在亚氏美德伦理学的术语中,它被称作“实践智慧”(phronēsis)。(参见李义天,2009年a,第58-59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能把“美德”理解为优良品性或心理趋向,而是说,这些内在因素需要受到一种实践理智方案的支配与调度。诚如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所指出的:“美德是一种关于行动、欲求和感受的内在化倾向。但它是一种理智倾向。它涉及到行为者对判断或者实践理性的运用,因而它不仅仅是一种习惯。”(Williams,p.36)类似地,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也认为,尽管“美德”一般是以品质的方式来塑造人们的实践推理能力,但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理性的方式,亦即“使我们能够正确地将对象看作善、看作某种我们有理由去做的事情的方式。”(Hursthouse,p.222)在亚氏美德伦理学的语境中,美德虽然仍是一种内在的因素,但是,通过把“美德”理解为一种目的论的实践理智方案,并且让其中的事实判断与生活共同体的伦理习俗和诉求关联在一起,这种美德伦理学比斯洛特的美德伦理学更为务实可靠,在实践推理的层面也更加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