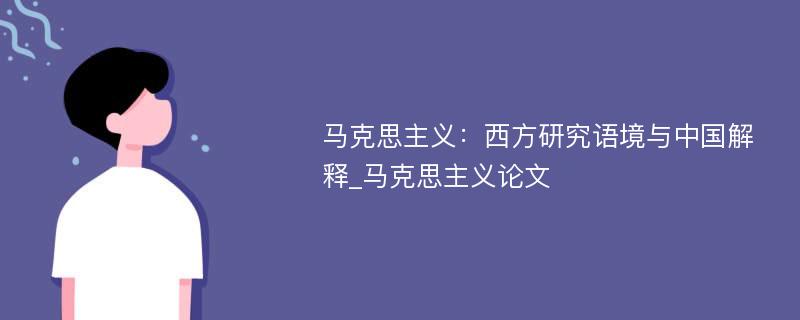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西学语境与中国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语境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田辰山先生嘱我给他的英文著作《中国的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文翻译把把关。说实话,当初读田先生的文章,是想了解中国思想的英文表达,尤其是涉及中国哲学思想(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的话)的英文表达。此前通过阅读张东荪先生40年代的哲学著作、叶秀山先生的篇章和当代中青年学人方朝晖先生的著述,以及美籍华裔学者刘禾教授的《语际书写》等资料,已感觉到许多现代中国所随意使用的哲学大词,诸如“本体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等与英文“ontology”、“dialectic”和“metaphysics”等,并不能简单地构成直接的对应关系。而这种语言和思维上的“非对称”现象,不仅渊源于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而且也由于两种差异的认知结构。在严格的意义上,我认同这样的一种判断,即中—西两种思想系统(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虽然是可以相互欣赏和彼此分享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部分地被通分,但其各自深层的核心理念则是“不可翻译的”,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也。
这里就举田先生的《中国的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书的第一章“导论”之第一自然段的中文译稿内容来说明。这段英文的原文是:
“Marxism is perhaps the most significant element in Western thought that has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a conversation with its Chinese counterpart.And,in this conversation,a Chinese version of Marxism has developed which comes to fruition in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This conversation incorporates a striking feature of ‘dialectics,’ or bianzhengfa,which not only pervades philosophical levels of dialectics in China,but also the thinking and speech of ordinary persons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However,I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dialectics,wherever one finds it in the West is different from what appears to be the Chinese analogue.Marxian dialectics in China is not the same as the inherited legacy of Marxian dialectics in Europe.What is this form of ‘Marxian dialectics’ in China,then?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form and the original Western form? 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directly the important questions of how and why Marxism has assumed the form it has taken in China.”
而原译草稿的表述则是:
也许西方思想中,唯一比较好地提供与中国哲学传统对话机会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对话过程中,毛泽东和一些共产党人理论家最后将马克思主义成熟地发展成了一种非常中国化的体系。其具有突出色彩的部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它不仅贯穿在哲学层次对话当中,也贯穿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思维和言论当中。
现在,我们发现凡西方人讲的“dialectics”与中国讲的“辩证法”,其涵义大相径庭。这就有了一个需要提出的问题:中国讲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什么呢?中国讲的与原西方讲的区别在哪里呢?它还是从欧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那里所继承下来的遗产吗?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全然可以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去理解呢?本研究课题目的在于探讨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和为什么会发展成中国这种形式的。
乍看起来,这段译文完全符合中文的句法结构,确实会让中国读者感觉到一种通顺流畅,语义清晰的文风。但我考虑,译者面对的文本不是小说,也不同于以西方思想传统为基础的“…ology”学说体系,而恰恰是用西方语言(拼音语言系统)论证中国思想(象形语言系统)的作品,既然我们承认中—西语言和思维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差异,那么,对于一部哲学著作来说,原原本本地体现出原文的语法结构则是一个不可省略的必要工作,否则对于普通读者乃至专业哲学学者来说,很可能因语言上的转换而产生习惯上的联想性误读。
在笔者看来,如果不阅读英文原著而径直地阅读上面的那段译文时,不仅英文中隐含着的语义重心暗示和“逻辑”秩序安排,都会被消解得无影无踪。更有甚者,由于上面那段文字的译文草稿不仅没有区分“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学术意义上的“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The Mao Zedong Thought”(官方定义的“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凭想象地把“in this conversation,a Chinese version of Marxism has developed which comes to fruition in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译成了“毛泽东和一些共产党人理论家最后将马克思主义成熟地发展成了一种非常中国化的体系”,这样,原来非常引人入胜的“惊奇之语”(也可以把这表达为“问题之思”),经过这样的一种语言转化,不仅变成了“老生常谈”(也可以把这表达为“教化之用”),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正是在这里,学术问题不自觉地被意识形态化了。
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在对那份中译草稿进行“校译”时,我立求尽可能地复原其英文的原始语境。我的译文如下:
或许,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中提供与中国哲学传统相应部分之对话机会的最为重要的要素。在这一对话过程中,发展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本,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达到了成熟。在这其中具有突出特色的部分就是有关“dialectics”或辩证法的解读。现在中国流行的哲学术语“辩证唯物主义”,不仅贯穿于哲学层次的对话之中,而且也已成为普通人生活言说和思维习惯中的日常用语了。
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西方人所讲的“dialectics”与在汉语中呈现出来的对应词“辩证法”,其涵义并不相同。中国人所说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与作为欧洲文化遗产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所指涉的并不是同样的一种内涵。这样就出现了一些需要解释的问题:中国式(form)的辩证法究竟是什么?这种中国式的辩证法与西方原初形式的辩证法其区别究竟何在?
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旨在探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中国式“辩证法”的这样一种形式。
我不能保证这样的译文就是适当的和准确的,但为趋向这样的目标,我还是做出了若干有意识的尝试和努力。
二
通过这样的一种学习实践,我个人体会,田先生的这部著作可能会给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专题研究,带来至少两方面的启示:
其一、田先生的这部著作提醒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研究领域中,语言及修辞分析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作为用西方语言所写出的、旨在用西方思维方式解释世界的思想体系,必定带有西方思维的深刻烙印。而当把这样一种西化思想体系转化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认知常识的过程中,“原典的马克思主义”最早受到日本维新思潮(带有明显的德国思想痕迹)的影响,后来又经过俄罗斯激进思潮(沾染了法国大革命罗伯斯比尔思想基因的新形态)的再次过滤,特别是这些“舶来品”最后必定要经过长期受到自身思维方式之根深蒂固制约的中国人深层意识的诠释,这样,经过多层过滤和数次演变后,“原典的马克思主义”就最终积淀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本”。显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本”,一方面,不同于“原典的马克思思想”,另一方面,它也同站在西学语境之内诠释原典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明显的差别。换言之,当西方人熟知的“马克思主义”被镶嵌进中国语境之后,按照西方“正统”或“经典”的准则衡量,它们之间的结合所产生的新的思想形式,就可能被视为一个“另类”,一种异化,甚至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悖论”。西方思想的这一理解路径,是需要中国学者认真体会的。否则,我们就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思想地图中,给出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清晰定位。
田先生在书中说:“‘辩证法’是中国现代哲学传统中的强大部分,它经历了时间和历史的洗礼。我的这一研究试图告诉读者:西方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一般都包括着明显的误解。从恩格斯那里继承下来的西方主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中国哲学传统,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辩证法也是从恩格斯那里继承而来,但是它实际是一种不同的特殊解读。当以恩格斯思想为源头的辩证法,被融入中国哲学传统的独特‘通变’(作者给出的‘通变’一词的英文释义是:‘continuity though change’。—引注)思维之后,就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第三道路。”我以为这个断语是中肯的。就像在异质语言的翻译转换中,似乎越是接近信、雅、达,而离原初的语境和语义可能就越远一样,“思想体系”的翻译和转换似乎也存在这种“距离越远越会走样”的情况。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程,其本身无疑是一种创造,同时也可能是一个悖论。毛泽东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批评教条主义时比喻说:根据当年苏联某项关于鸡蛋和鸡汤对人体不利的研究,“后来又说可以吃了,……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同月22日他说:“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同年5月8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又说:“譬如说怕马克思,他住在高高的楼上,要搭好几层梯子才能爬上去,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马克思也是人,他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脑袋,跟我们差不多。不过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东西就够了。……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正是这种“创造性悖论”的体现。
其二、“辩证法”(dialectics)这一关键词,本来是一个像“范式”(paradigm)、“话语”(discourse)和“问题意识”(problematic)一样的、具有深厚内涵的外来词汇,但在传统的教科书体系中所使用的“辩证唯物论”中的“辩证法”却被解释得“泛化”和“庸俗化”了,以至于人们把这种“辩证法”戏称为“变戏法”。究其原因或许与按政治权威对政治现实的需要去重建和解释历史的叙事方式(即先设定结论再粘贴资料的倒果为因的叙事方式)大为相关。干巴巴的剩下的只有几项一劳永逸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即对深刻的现实困境于事无补,又对知识的增长无甚贡献,更以严重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替代了艰苦的文献梳理和细腻的推导论证,从而与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南辕北辙。田先生把其研究集中到了“辩证法”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之“中国化”的焦点上,按照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逐一对观念的内涵和变化进行梳理。最终在中—西比较文化的框架下,给出自己的结论。虽然学术界可能未必完全赞同这些结论,但它却给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论题感兴趣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值得付出精力继续讨论的路径和空间。因此,尽管将来对田先生的这部著作或许会有若干争论,但我仍然认为,这部著作已经超越了国内目前许多已有的相关著述的水准,是一部以“辩证法”这一西方观念在中国思想历史中之具体演化为案例的、在比较文化研究高度上展开的优秀作品。
当然,在编译过程中我也常想,如果不是完全从某一脉络的哲学史角度考察,而是进入更为全面的具体思想史脉络,那么,随着有关文献的积累和考证的精致化,在“辩证法之中国版本”的研究中,还有十分宽绰的挖掘余地和论述空间。例如,像张东荪先生曾反复对西方“辩证法”学理所做出的深刻阐述,以及罗隆基先生1930年3月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评论马克思之“辩证法”问题的著名文章等,完全可以说基本上已形成了另外一路关于现代中国“辩证法”理论的诠释。如果削减了这些关于“辩证法”探索的内容,无论如何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情,尽管这些论题并非田先生此一论著所要展开的研究重点。
本文是田辰山《中国的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译本的“编译琐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