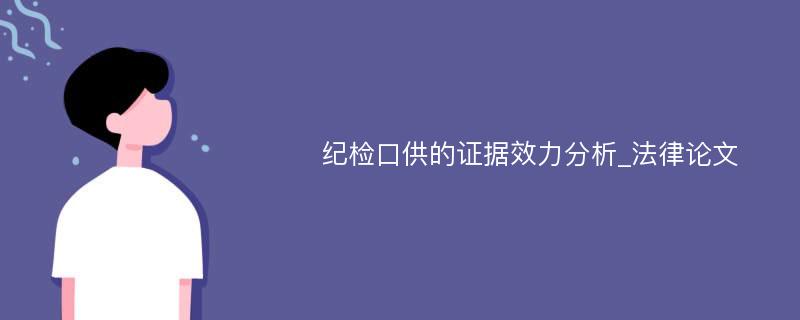
试析纪检口供的证据效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口供论文,效力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称纪检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纪案件过程中,向纪检监察人员所做的关于自己犯罪事实的供述和辩解。这种口供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做出明文规定,法学理论界对此问题也鲜有论述。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一贯做法是将纪检部门移送的材料作为线索材料,按照诉讼程序重新调查取证,然后根据自己调查的材料提起诉讼。通俗地讲,就是对纪检部门收集的涉嫌犯罪材料实行证据转换,以转换后的材料提起诉讼。一般不将纪检部门移送的材料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从我国目前公布的判例看,尚未发现将纪检材料不经证据转换而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的情况。但是,笔者最近办理的一起受贿案件,因被告人在纪检部门移送案件后全部翻供,主要证人(被告人之妻)也完全改变证言,检察机关就将被告人及其妻在纪检部门的口供和证言作为控诉证据提起了公诉。因此,纪检口供的证据效力问题,是司法实践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上述案件中,对纪检口供的证据效力之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纪检口供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二是在纪检口供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的情况下,如纪检口供与诉讼口供存在矛盾,到底应当以何为准。前者涉及的是纪检口供的证据能力问题,后者涉及的是纪检口供的证明力问题。对上述问题,控、辩、审三方的意见大相径庭。控方认为: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明文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纪检口供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因而也是刑事诉讼的证据。纪检口供的证据资格毋庸置疑。纪检口供比诉讼口供形成时间早,是原始口供,二者如有矛盾,应以纪检口供为准。此意见肯定纪检口供的证据能力,并认为其证明力优于诉讼口供,可称之为“肯定说”。辩方认为:纪检口供不属法定的证据形式,因而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由于诉讼程序比纪检调查程序更为严格,诉讼口供的效力高于纪检口供。此意见否定纪检口供的证据能力,认为其证明力低于诉讼口供,可称之为“否定说”。法院认为,对纪检口供应该区分是亲笔口供,还是笔录口供,是被告人主动交代的还是被动承认的。对亲笔口供和主动交代的事实,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在纪检口供与诉讼口供相矛盾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讲以谁为准,而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此意见对纪检口供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采取折中立场,可称之为“折中说”。上述三种观点主要是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所做的分析,各有其道理。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应用证据法理论进行剖析。
二、关于纪检口供的证据能力
证据学上的证据能力,又称证据资格或证据的适格性,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某一材料成为诉讼证据所必需的资格或条件。在英美法系中,称之为证据的可采性。我国也称之为证据的采用标准[1]。很显然,证据能力中的“能力”,如同民事权利能力中的“能力”,是一种法律上的资格或条件,是证据可否采用的标准。理论上一般认为,证据采用的基本标准包括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项标准[1]。即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客观联系,证据的形式和取得程序必须合法。其中证据的合法性具体包括:1.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2.提供、收集证据的主体必须合法;3.证据的内容必须合法;4.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2]。综观我国三大诉讼法,虽没有使用证据能力的概念,但却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立法规定,结合证据法理,我们不难得出纪检口供不具有刑事诉讼证据能力的结论。
首先,从形式上看,纪检口供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形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之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七种形式。在这七种法定证据中,并不包括纪检口供。当然,该条规定的证据形式中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一证据形式,但这一证据形式显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向司法人员所做的供述和辩解,因为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就不能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简言之,纪检口供是违纪人供述和辩解,而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其次,从主体上看,纪检口供不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人员收集的。
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一种行使侦查权的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权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行使,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根据这一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只能由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收集,其他任何机关和人员都无权行使此权利。在我国,党的纪检机关享有检查权,行政监察机关享有监察权,但根据《纪检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第2条及行政监察法第18条的规定,这种检查权、监察权是指对违反党纪、政纪案件的调查处理权,并不是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对涉嫌犯罪的,《纪检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37条及行政监察法第43条均规定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因此,纪检机关收集的违纪人员口供及其他材料只能作为案件线索,而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否则,则无异让纪检机关代行侦查权,有违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再次,从程序上看,纪检口供不是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程序收集的。
纪检部门在查处违纪案件时,是依据纪检部门的办案条例调查取证,而不是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因此,纪检口供的收集程序不可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纪检口供及纪检部门所收集的材料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
从体制上看,纪检部门办案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程序。纪检部门在查处违纪案件时发现涉嫌犯罪的,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由司法机关按诉讼程序重新调查取证。纪检部门的移送行为只是启动诉讼程序的一个原因。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需经过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基本程序。纪检部门移送案件后,还必须经过侦查程序。如果将纪检部门收集的口供及其他材料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那么,侦查程序就形同虚设。
基于以上三点,笔者认为在纪检口供的证据能力问题上,“否定说”是正确的,即纪检口供是纪检部门查处违纪案件的依据,它只能作为刑事案件的线索材料,而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
但是,“肯定说”从法律规定入手,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为大前提,以“纪检口供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为小前提,得出“纪检口供也是刑事诉讼证据”的结论。其推理过程也是无懈可击。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证据”一词的多义性。对“证据”一词,我们至少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其一指证据材料,即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所有事实材料;其二指定案依据,即定案证据[3]。“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中的“证据”应理解为证据材料,而不应理解为定案依据。否则,我们会得出“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因而也是定案依据”的错误结论。因此,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关于“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的规定,只是对定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要件所做的规定,并不是全部要件。根据本条第二款关于“证据有下列七种……”及下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等规定可以看出,定案证据还必须具备合法性要件。“肯定说”仅依据法律的部分条款进行推论,其结论未免武断。
至于“折中说”,其将纪检口供分为亲笔口供和记录口供而区别对待,确有其合理性。因为亲笔口供的可信度比记录口供要高。但是,这里讨论的是证据能力问题而不是证明力问题。在证据能力上,亲笔口供和记录口供均不具备诉讼证据的合法性要件,因而都不能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同理,被告人主动交代的口供虽比被动承认口供的可信度高,但也不能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法院在认定自首时,往往将被告人在纪检部门的主动供述作为证据加以采用,这是否意味着纪检口供具有证据能力,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呢?笔者认为不能。因为被告人在纪检部门主动供述的事实,必须经过司法机关查证属实,才能认定该事实存在。而只有在犯罪事实存在的前提下,才能认定是否存在自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之规定,对“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情形视为被告人自动投案。如果被告人在纪检部门主动供述的事实经查证确实存在,那么其在纪检部门的主动供述的情节就可以作为自动投案的情节加以认定。在司法实践中,纪检部门往往向司法机关出具被告人主动供述的书面证明,并将被告人在纪检部门的供述材料作为附件移交法院。在此种情况下,被告人在纪检部门的供述材料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书证在使用,并不是作为言词证据在使用。
三、关于纪检口供的证明力
证明力(weight)是指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对案件证明程度的大小。证明力越大,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越大,反之就越小。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两个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一个证据必须先有证据能力,尔后才谈得上证明力问题。即“证据必须先有证据能力即须先为适格之证据,或可受容许之证据,而后始生证据力之问题”[4]。二者的区别在于:证据能力是一个法律问题,证明力是一个事实问题;证据能力涉及的问题是以法律真实为前提,而证明力是以客观真实为前提;证据能力的判断规则主要是考虑证据的合法性,而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判断规则,主要是考虑证据对于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有关司法解释确立的证明力判断规则主要有:(1)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2)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3)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4)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5)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由于纪检口供没有证据能力,因此也就谈不上有证明力问题。但毕竟纪检口供有无证据能力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为了深入探讨其证据效力,我们不妨假设其有证据能力,以比较其与诉讼口供证明力的高低。
在纪检口供的证明力问题上,“肯定说”的基本理由是纪检口供比诉讼口供形成时间早,是原始口供,因此应以纪检口供为准。在证明力判断规则上,确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之说。但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区分标准不是根据证据的形成时间,而是根据证据的来源[5]。其中,原始证据是指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原始出处的证据,传来证据是指不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原始出处,而是从间接的非第一来源获得的证据材料。可见,纪检口供与诉讼口供不是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关系,不能以此为由比较其优劣。纪检口供的形成时间的确比诉讼口供早,但无论根据证据规则还是司法实践经验,均没有先形成的证据优于后形成的证据之说。因此,“肯定说”的理由难于成立。
“否定说”认为诉讼口供的效力高于纪检口供的基本理由是诉讼取证程序比纪检调查程序严格。这一理由同样是经验之谈,有关法律及证据学理论并无此规则。但是,证据学理论及有关司法解释均有“物证、历史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的证明力一般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判断规则,这一规则对历史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及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的优先效力的规定皆是因为其证据形成的程序更为严格。证据的证明力主要是一个经验判断问题。根据司法经验和社会一般常识,证据的可靠性与其形成程序的严密性往往成正比。由于诉讼程序比纪检调查程序更为严密,因此,诉讼口供的可靠性应高于纪检口供。在纪检口供与诉讼口供相矛盾的情况下,应以诉讼口供为准。从立法角度考量,《纪检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第46条规定对已经司法机关处理的移送纪检机关的案件,由审理室直接受理,不再履行立案调查手续,即诉讼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处理违纪案件的依据。但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却未规定纪检证据可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因此,诉讼证据的效力高于纪检证据也是立法者的立场。
在纪检口供与诉讼口供相矛盾的情况下,“折中说”认为不能简单地讲以谁为准,而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这一观点颇有新意。但仔细研究,此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这里讲的“以谁为准”,实际指的是谁的效力更高,谁的证明力更强。即是讨论单个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而不是证据的综合认定问题。从司法实践来看,证明力强的证据不一定是法院最终采信的证据,其所证明的事实不一定是案件的真实情况。比如,关于被告人的年龄,户籍档案的证明力高于证人证言,但如果多个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证实的年龄与户籍档案不一致,则要采信证人证言。这就是说,多个证明力较低的证据相结合,可以推翻证明力较高的证据。但就单个证据而言,证明力较高的证据要优于证明力较低的证据。因此,单个证据的证明力与证据的最终采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综上,在肯定纪检口供证据能力的情况下,诉讼口供的证明力必然高于纪检口供,但采信何者为定案的最终依据则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也就是说,证据的证明力应单个甄别,而不应综合认定。
需要说明的是,证据的证明力的判定方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影响案件事实的最终认定。在上述案件中,行贿人始终承认行贿,如采取综合认定的方法认定证明力,因纪检口供与行贿人证言相互印证,则必然得出纪检口供的证明力大于诉讼口供的结论,最终会采信纪检口供,认定被告人有罪;如采取个别认定的方法认定证明力,因诉讼口供的证明力高于纪检口供,则会采信诉讼口供,这样案件事实就形成证据“一对一”的局面,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先比较纪检口供与诉讼口供的证明力强弱,然后再与行贿人证言结合认定案件事实;而不应先根据行贿人证言辨别纪检口供与诉讼口供孰是孰非,然后再认定案件事实。
四、建议与对策
笔者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反腐体制不顺。我国现行的反腐机关有纪检、监察、检察三家。三者分属党委、政府和司法三个不同系列。这就难于避免在配合上出现问题,在衔接上出现矛盾,在资源上造成浪费。针对此问题,我国自1993年起将纪律检查与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从而使纪检监察机关的资源得到整合,工作效能得到提高,反腐力度得到加强。但是,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配合仍然存在问题,工作效能仍然不高。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借鉴我国香港等地区设立廉正公署的经验,将纪检监察及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进行整合,建立统一的反腐机构。整合后,纪检监察部门专司查处违法违纪案件职能,案件一旦涉嫌犯罪,立即交统一的反腐机构来查办,而不是等自己调查完后再移送。这样既可以节省办案资源,提高办案效率,又可克服证据转换不能的弊端。同时,在自侦部门分离后,检察机关也可专司法律监督职能,解决自侦案件监督不力的问题。
在统一的反腐机构未建立之前,对纪检监察部门查办的涉嫌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应该提前介入,联合办案。此举既可革除现行体制之流弊,也可使办案机关互相监督,解决监督者无人监督问题,有效防止办案人员徇情枉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