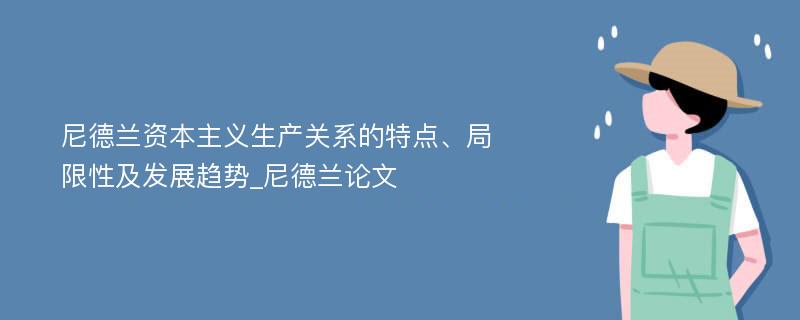
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局限性及其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关系论文,局限性论文,发展趋势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德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诚然,正如许多论著所指出的那样,高度发展的商业资本主义是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商业资本主义与18世纪尼德兰国力的式微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从根本上说,商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之既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也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般情况下,此两者总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因此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商业资本主义无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也都取得了相应的发展,有的国家,如英国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水平毫不逊色于尼德兰。导致尼德兰经济地位巨大变化的根源不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而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尼德兰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其他西欧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过,但在尼德兰表现得尤为典型、尤为突出。
17世纪中叶以前,尼德兰得益于自身的地理优势,先是在北欧,后来又在整个欧洲和世界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布鲁日、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等中心城市更是相继成为地区或全球贸易的中枢。早在13、14世纪时,布鲁日已是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区的中心城市,至少开辟了四条直通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商路,许多国家把自己的商品运往布鲁日,既有基督教国家,也有伊斯兰教国家。14世纪下半叶,安特卫普开始与布鲁日形成竞争之势。16世纪自由贸易制度的实施不仅在安特卫普营造了一个相对优越的商贸环境,而且也使安特卫普成为竞争的胜利者。由此该城从一个不甚重要的定期市集所在地转变为永久性的商业都市,从一个转运贸易港口转变为全欧商业和金融中心之一,各国商人蜂拥前来。安特卫普交易所里每天总有5000商人在这里进行交易,港口里经常停泊着2500艘船,每天进出的船只达500艘左右(注:摩特莱:《荷兰共和国的兴起》,伦敦1907年版,第1卷,第85页。)。1531年安特卫普新盖了一座交易所,欧洲所有的大城市都派代表进驻交易所,年交易总额最高曾达4000万杜卡特(注:梅默:《比利时史》,伦敦1962年版,第159页。),16世纪四五十年代,安特卫普的贸易额已占全尼德兰对外贸易总额的70~80%(注:《新编剑桥近代史》,剑桥1958年版,第2卷,第59页。)。
阿姆斯特丹是在17世纪开始成为真正的世界市场的中心,它将美洲和欧洲连成一体,同时亦把全尼德兰几乎所有的原材料和手工业产品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使之融入世界商业体系。阿姆斯特丹贸易品种的结构也大为改观,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赶上或超过了传统的地区性产品,“新”、“旧”两个世界都可在这里找到所需的原材料和消费品。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自1585年起定期出版的价格公报,在全欧洲广为流传,各地的商品价格均受其支配。这份价格公报1634年时包括359种商品,1686年便增加到550种(注:奇波拉:《产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和经济,1000-1700》,伦敦1981年版,第268页。)。阿姆斯特丹的少数大商人几乎垄断了大宗商品的交易,许多重要商品的价格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意志。
在高度发展繁荣的背后,尼德兰商业活动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大量商业资本掌握在外国商人之手、对海外市场的过分依赖和投机活动猖獗是最主要的问题。早在14世纪下半叶,由于佛兰德议会向外国商人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布鲁日对欧洲各国商人的吸引力大增,一度离去的德国商人重新在该城设立了商站,条顿骑士团在这里开设了固定的银行,重要的交易活动都在这里进行(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53页。)。来自德国南部和意大利等地的商行和银行则在安特卫普的商贸金融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安特卫普鼎鼎大名的富商几乎都是外国人(注: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93-394页。),外国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涌入,一方面推动了尼德兰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大量商业利润流向域外。在一段时间内,布鲁日是尼德兰的商贸中心,由于该城的船只、商人、贵重商品、货币和信贷等主要来自位于尼德兰南方的各个国家,专营信贷的亦大多为意大利人,所以直到15世纪末,甚至更晚的时候,尼德兰的贸易结算始终对南方客商有利(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54页。)。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不利于尼德兰整体实力的增长,也阻碍了本地商人的发展和壮大。
在尼德兰的商业活动中,海外贸易,尤其是中介贸易,明显居于主导地位,内部贸易所占的比例甚小。1317年以后,布鲁日和威尼斯建立了经常的商务联系,从此意大利商人开始运来香料和东方的手工业产品,同时汉萨同盟的船只也从德国、俄国和瑞典等国运来建筑木材、小麦、熏鱼、金属和毛皮等货物,所以14世纪时航行于兹维恩河上的几乎都是外国商船。除少数品种外,当时的尼德兰对外来商品并没有如此大的需求,众多舶来品涌入布鲁日主要是利用这里作为中转站,再销往周边国家和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布鲁日商人的作用只不过是充当欧洲各国商人的中介人而已,有的历史学家因此将这一时期的布鲁日称为“欧洲最大的中介人”(注: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0页。)。胡椒批发贸易是安特卫普兴旺繁荣的基础之一,曾经垄断该项贸易的葡萄牙王国从印度运出的胡椒几乎全部经由安特卫普售出,原因主要有二,一则这里交通便利,商贩集中;二则当地从事胡椒贸易的商业公司在尚未收到货物时,就已经向葡萄牙国王预支了部分货款,对于经常处于财政危机中的葡萄牙国王来说,这一点十分重要。德国也把安特卫普作为自己的贸易窗口,在一段时间内德国与西班牙贸易的六分之五,与美洲殖民地贸易的十分之九都在安特卫普进行。16世纪时英国呢绒织造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呢绒产品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16世纪中叶年平均出口量达到13万匹(注: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9页。)。令人感兴趣的是,当时英国的呢绒贸易合同都是在安特卫普签定的,由此可见安特卫普在这一时期欧洲贸易中的中介作用。联省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但商贸的根本格局未见变化。18世纪初叶以前联省共和国的商人始终在英国进出口贸易中扮演重要的中介人角色,他们运进英国的商品主要有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毛皮、皮革、柏油、琥珀和在联省共和国漂白的德国细麻布,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拍卖的大部分殖民地商品的得标者也均为联省共和国的商人。他们还大量购买呢绒、烟叶、食糖,有时还包括小麦和锡等商品,储存于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的仓库中,然后转运其他国家,主要是德国。中介贸易的高度发展,使得尼德兰各主要商业城市都将目光投向海外,与本地区的经济联系则显得相对薄弱,这是影响尼德兰统一市场形成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尼德兰最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亦与之有着一定的关系。
新航路开辟以后,随着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的转移,商业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欧各国投机活动大为活跃,尼德兰尤甚,这与其商业的高度繁荣不无关系。在16世纪的商品市场上,海洋天气、海盗活动、政治气候、经营手段及其他一些难以预测的因素都会引起价格的巨大波动,因此许多人便以此为主要内容开展投机活动。当时云集安特卫普的各国商人都是根据陈列于交易所里的货物样品而签定商业合同的,签约人往往不等货物运到,便伺机买空卖空。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不同时间的价格差异上,有人突然暴富,有人顷刻破产,商业形同赌博。阿姆斯特丹的投机活动极其猖狂,香料、谷物、鱼类,乃至城市房地产、公共资产和东印度公司的股票等都已成为投机对象,社会各阶层几乎无一能置身事外,各种现代的投机手段在彼时彼地亦俯拾皆是。一个犹太股票投机商曾直言不讳地说,假如在阿姆斯特丹公布消息前的五六个小时获悉命在旦夕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死讯,那么他就能在当天赚取10万埃居(注: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卷,第145~146页。)。16、17世纪是香料贸易的鼎盛时期,来自东方的胡椒是其中数量最大、价格最高的商品之一,因此成为那个时代令人如痴如醉的投机对象,当时一些最大的商人和资本家亦涉足其中。例如17世纪40年代末,欧洲市场胡椒严重短缺,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有关的各种谣传更是不径而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63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收到大量的胡椒定单,总需求量高达3.8亿荷兰磅左右,而该公司所能提供的胡椒仅为240万荷兰磅,数量相差极其悬殊。消息一经传出,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每100荷兰磅胡椒的价格即由60佛罗林左右狂升至175佛罗林。其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大量增加进口,致使欧洲市场上胡椒充斥,荷兰东印度公司即使三年内不再购买胡椒,亦无缺货之虞,由此导致1652年每100荷兰磅胡椒仅售38佛罗林左右(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卷,第87页。),跌幅之大令人瞠目结舌。18世纪时投机范围进一步扩大,国外的股票和政府债券等亦成为投机活动的对象。投机活动的盛行极大地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消极影响十分明显,许多人漠视客观的经济规律,盲目听凭幕后消息,甚至谣传来支配自己的行动,结果大多数人都难逃厄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局限性是尼德兰商业资本主义高度繁荣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孪生物,商业资本的控制权、海外市场的地位和投机活动的规模无不受制于尼德兰商业的基本大环境。客观地说,在尼德兰资本主义商业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些局限性的弊端并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相反它们还似乎在相当程度上活跃了尼德兰的商业活动,但尼德兰最终必须承受这些历史局限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尼德兰商业的停滞不前和整体经济实力的下降皆与之密切相关。
二
就经济结构而言,尼德兰个别经济领域,特别是呢绒业和航海业(包括相关的造船业)的高度发展,构成了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第二个明显特征。
呢绒织造业一直是尼德兰的支柱产业,其渊源可上溯至罗马帝国时代。10~11世纪时已形成了一批以呢绒织造业为主要产业的城市,如根特、伊普尔和杜埃等。得益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14世纪这批城市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呢绒产品在欧洲各地都十分畅销,伊普尔的产品在法国图卢兹呢绒市场上所占的销售份额,1379年为72%,次年即上升为81%,1398年更猛增至90%(注:奥顿:《剑桥中世纪史简编》,剑桥1953年版,第2卷,第1035页。)。呢绒织造及其相关的行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就业者,他们在城市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3世纪的根特和14世纪的布鲁日都达到了60%,伊普尔即使在呢绒业开始衰败的14世纪中叶,纺织品交易仍占贸易总量的51.6%(注:图马:《欧洲经济史。10世纪至今经济变化的历史与理论》,纽约1971年版,第99页。),这样的比例在其他欧洲国家是很难想象的。14世纪佛兰德各主要城市就是基于呢绒织造业的高度发展而盛极一时,其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和生产规模在欧洲都首屈一指。
尼德兰濒临北海,海岸线漫长,港湾众多,具有发展海运业的良好条件,以荷兰和泽兰为首的尼德兰北部地区就是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大力发展海上运输及相关的造船行业,从而在世界舞台上称雄一时。15世纪荷兰、泽兰的航运业初露锋芒,几乎垄断了波罗的海地区和佛兰德之间的海运业务,对汉萨同盟构成了不小的威胁。17世纪末尼德兰北方船只的载重量也越来越大。据统计,驶抵柯尼斯堡的尼德兰北方船只,1547年平均载重量为70吨位,1623年为144吨位;通过松德海峡的荷兰船只中,1557年只有30%的船只载重量超过200吨位,162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0%,1640年更是高达90%(注: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剑桥1977年版,第5卷,第530页。)。由于不断采用先进的设计和技术,一直到1800年尼德兰北方在200~500吨的商船制造方面始终居于欧洲领先地位。这一切都使得尼德兰北方制造的船只在欧洲具有相当的竞争力,颇受各国欢迎,1680年左右英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商船是从国外购买的,其中大部分来自荷兰(注: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卷,第358页。)。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也都要依靠荷兰造船厂提供部分船舶。
造船业的迅速发展,导致航运业的突飞猛进。就载重量而言,1500~1700年期间,尼德兰北方船舶的总吨位增加了10倍,到1700年联省共和国的商船队已远远超过了50万吨,其吨位相当于竞争对手英国商船队的三倍,而且可能比其他欧洲国家商船队的总和还要多(注: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9页。)。就数量而言,17世纪中叶欧洲各国总共拥有船只20000艘左右,其中约有75%,即15000~16000艘属联省共和国所有(注: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9页。)。为了维持这支庞大的船队,联省共和国广泛招募水手,据1614年的统计,其数量要超过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水手的总和(注: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自16世纪末叶起,联省共和国开始越出欧洲的界限,集资筹划开辟东方航线。1621年垄断西非和美洲贸易的西印度公司宣告成立,从此联省共和国的商船遍航世界各地,被誉为“海上马车夫”正是依靠这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联省共和国的经济活动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商业繁荣自不待言。也正是依靠这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联省共和国自恃有力量与当时的两大殖民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一争高下,遂大肆向外扩张,角逐商业霸权。一直到17世纪70年代以前,联省共和国在世界商贸、殖民领域中确实可谓称雄一时。
呢绒业、造船业和航海业的高度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尼德兰经济的整体腾飞,但另一方面也无可否认,这些行业也都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主要表现为极度依赖海外的原材料,这一点在呢绒织造业中尤为明显。虽然尼德兰呢绒织造业在中世纪的欧洲久负盛名,但受制于地理环境,本地产的羊毛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难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当佛兰德城市呢绒织造业形成较大生产规模以后,尤其是高档呢绒生产发展起来以后,这一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进口羊毛遂成为支撑佛兰德毛纺织业的关键商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隔海相望的英格兰是佛兰德的主要羊毛供应地,12世纪初佛兰德商人就已经几乎走遍整个英格兰,用现金收购羊毛。还有一些商人则居留于多佛和伦敦,为佛兰德各城市采购羊毛。为了保证关税收入,自13世纪下半叶开始英格兰政府规定,羊毛等产品必须由赫尔、伦敦等规定口岸输出,然后运往欧洲大陆单一的集散地,即所谓的羊毛中心站。羊毛中心站最早设于多尔德雷赫特,后迁往安特卫普、布鲁日和圣奥梅尔,1390年最终迁至加来,此羊毛中心站成为佛兰德输入英格兰羊毛的主渠道。
异地购买原材料使佛兰德呢绒织造业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在卢万城的呢绒生产成本中,购买英国羊毛的费用始终占了很大的比例,1434年为62.5%,1442年为55.1%(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61页。)。其结果是生产成本难以降低,特别是高级呢绒更是售价惊人,本地居民鲜有问津者,所以高级呢绒几乎全部销往海外市场,买主都是各级教俗贵族。这种原料、交换和消费都脱离本地市场的生产,实际上只是一种基础不甚牢固的加工工业。
其他行业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对海外原材料的高度依赖,不仅使尼德兰在经济上受制于人,一旦原材料供应渠道不畅,后果将难以想象,而且在政治上也必须仰人鼻息。百年战争前夕,佛兰德伯爵倒向法国一边,1336年英国便以禁止羊毛输出作为惩罚手段,佛兰德各城市的毛纺织业为此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商人、工匠无不忧心忡忡。迫于生计的巨大压力,愤怒的市民遂迁怒于法国封建主,所以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佛兰德各城市基本上都站在英国一方。
三
当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时,尼德兰凭借自身的地理条件和传统优势,将工农业和商业推向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较早进入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在这历史大转折的过程中,尼德兰曾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其经济活动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自身疆域的范围。但当周边国家的民族经济迅速发展,开始与尼德兰抗衡时,尼德兰经济活动中一度被掩盖的弱点和局限性便日益暴露无余,并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尼德兰手工业发展水平一度居于西欧前列,然而受制于自身的局限性,大多数行业波动颇大,呢绒织造业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呢绒织造业是尼德兰的骄傲,也是尼德兰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部门之一,但由于原材料供应等问题,自14世纪末叶起尼德兰的毛纺织业开始出现动荡。英国曾经是尼德兰主要的羊毛供应地,14世纪下半叶随着本地毛纺织业的迅速崛起,羊毛出口量急剧减少。14世纪中叶以前,英国每年运往尼德兰的羊毛达33000~35000包,15世纪中叶减至每年7500包,1532年仅为1168包(注:图马:《欧洲经济史。10世纪至今经济变化的历史与理论》,纽约1971年版,第80页。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55页。)。西班牙为了发展自己的呢绒织造业,同样也采取措施限制羊毛出口,1462年西班牙政府规定从此以后羊毛出口量不得超过羊毛总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与此同时,英国呢绒产品的出口数量也呈上升趋势,15世纪时最高年输出量可能已近6万匹。这一数字虽然不算很大,但仍对尼德兰呢绒生产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一些汉萨同盟和其他地区的商人开始前往英国港口购买呢绒。市场的巨大变化给尼德兰各地的毛纺织业先后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冲击,其中佛兰德这个尼德兰呢绒织造业最早繁荣的地区也最早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生产几近崩溃,颓势难以挽回。伊普尔是佛兰德呢绒生产的最大中心,如前所述该城14世纪初呢绒年产量就超过9万匹左右,但到14世纪最后30年间年平均产量已不足2.5万匹(注:米斯基明:《中世纪城市》,耶鲁大学1977年版,第256页,表格13·4。)。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跌幅超过70%,真可谓一泻千里。
15~16世纪情况进一步恶化,到17世纪时,面对英国呢绒产品的激烈竞争,联省共和国的毛纺织业节节败退,各种类型呢绒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陷入了困境。其他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荷兰的亚麻布加工业曾经居于欧洲领先地位,周边不少国家都将亚麻布运往荷兰进行漂白加工,18世纪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英国亚麻布加工业的崛起,荷兰亚麻布加工业遭受重创,出口萎缩,主要加工中心哈勒姆的亚麻布漂白数量锐减50%以上,亚麻布漂白加工厂亦由20家减少至8家(注:威尔逊:《18世纪英国和荷兰的商业和金融》,伦敦1937年版,第61页。)。
城市和手工业的动荡也影响了农业生产。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非农业人口的粮食需要,尼德兰西南部农村地区主要以谷物种植为主。当城市人口和呢绒生产都处于持续增长时期,强劲的市场需求有力地推动了谷物的扩大再生产。但到15世纪,尼德兰南部城市的衰败和呢绒行业的萎缩,严重冲击了以谷物为主的农业生产,更兼大量城市工匠无以为生,无奈之下只得转向农村寻找生计,致使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土地被迫再次进行分割,人均占有土地数量遂明显下降,15世纪末、16世纪初埃诺地区的封地和地产登记资料汇编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此外,由于农业生产结构已经定型,改变生产方向困难重重,所以尼德兰西南部地区的农业生产自15世纪末起长期停滞不前。较之西南部地区,尼德兰中部,尤其是布拉邦特地区的农业生产明显有了长足的进步,具体表现为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农业产值的增长。但是布拉邦特农产品的商品化渠道还比较单一,主要以安特卫普为中心进行交易,因此安特卫普的衰败和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城乡统一市场的削弱,不可避免地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更兼兵燹之灾,布拉邦特的农业生产自17世纪开始止步不前,甚至有所下降,人们不再重视农耕,许多土地弃耕荒芜,变成了鸟类的天堂(注: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剑桥1977年版,第4卷,第45页。)。
与此同时,尼德兰的商业和金融业也由南向北依次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衰败,那些一度作为波罗的海或欧洲,甚至世界贸易中心的城市纷纷步入多事之秋,处境艰难。商业箫条固然与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状况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受制于尼德兰商业活动自身的局限性,即前述大量商业资本集中于外国商人之手和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这就使得尼德兰商业活动的主动权和控制权都掌握在外人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尼德兰只不过是为外国商人和外国商品提供了一个活动舞台而已,一旦他们(它们)不再需要这个舞台时,或外部形势急剧动荡时,尼德兰自身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继续维持昔日的繁荣,后果不难想象。
布鲁日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商港之一。佛兰德的呢绒织造业在推动布鲁日壮大的同时,也限制了该城商业活动的内容,使之主要局限在进口羊毛和出口呢绒方面。这两项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布鲁日繁荣的基础,遗憾的是它们都掌握在外商之手。布鲁日商人并非不了解羊毛进口贸易的重要性及其经济意义,而且也曾一度主动前往羊毛产地英格兰,千方百计地组织货源,力争掌握主动权,但当英国商人逐渐壮大起来以后,布鲁日和佛兰德其他城市的羊毛商人无不铩羽而归。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和汉萨同盟的商人先后撤离布鲁日,随后西班牙商人亦效法之。由于本地商人尚无力填补空白,布鲁日的商业活动顿呈颓势。
布鲁日的银行业也曾因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而兴旺一时,阿维农之囚期间(1308~1378年),天主教会将整个北欧地区的什一税款都存放于布鲁日的银行里(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64页。),这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意大利银行亦在布鲁日设有分支机构,但从14世纪末叶开始,布鲁日银行业厄运不断。天主教会大分裂时期(1378~1417年),先是出现两个,继而又是三个相互竞争的教皇,各方都有自己的教廷、税吏、并得到一部分西欧君主的支持,闹得不亦乐乎,布鲁日银行业大受其害,教会的存款数额由此大幅度减少。后来教会又将在布鲁日的存款全部取出,转移到佛罗伦萨和罗马,对于布鲁日银行业来说这无疑是釜底抽薪(注: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务书1992年版,第464页。)。1478年,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关闭了其在布鲁日的银行,此举更是敲响了布鲁日银行业的丧钟。在这多重打击之下,布鲁日终于一蹶不振。安特卫普的商业和金融业也因16世纪西班牙经济的破产而遭到重创。
尼德兰西南部和中部地区相继式微之后,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北部地区,即联省共和国成为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最后辉煌。从总体上来说,尼德兰北方的商业活动、经济结构和运行情况都相对比较合理,但仍没能从根本上摆脱前述局限性。联省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亦未见改变,更兼代表大商人利益的寡头政治集团执掌大权,在各个领域都推行不彻底的折中政策,由此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税收政策方面,联省共和国为了保护商人,特别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的利益,将商业税和航海税定得很低,对下层民众却横征暴敛。较之16世纪,农民在17世纪交纳的赋税数量和种类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上扬,不动产税和间接税也相当惊人,鱼类产品在端上餐桌前就要支付30%的间接税。高税收导致工业品价格上升,17世纪联省共和国的许多同类产品要比法国的贵10%,唯利是图的商人亦因此而拒绝外销本国商品(注:萨哈贝尔:《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纽约1964年版,第181页。),这是阻碍联省共和国手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联省共和国商人在北欧谷物贸易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大量进口谷物,然后再向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所以阿姆斯特丹的仓库约有75%以上都被用来储存谷物,联省共和国亦将谷物贸易视为国家“一切贸易的根源”(注: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卷,第399页,第392页。)。鉴于这一情况,联省共和国海关对大部分将转卖到他国去的进口粮食都征收低关税,而对本土输出的农产品却课以高额关税,这一高一低严重打击了联省共和国的农业生产。
17世纪中叶,联省共和国的经济进入了全盛时期,海外贸易仍然是其繁荣的基础,贸易额每年高达7500万盾至1亿盾(注:萨哈贝尔:《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纽约1964年版,第182页。),在欧洲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然而由于手工业没有获得相应的发展,农业生产亦相对落后,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结构失调,这是联省共和国经济的最大隐患。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英国正是看到了这一薄弱环节,遂以打击其航海业为突破口,以削弱其海外贸易为最终目的,开始与联省共和国争夺商业霸权。165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航海条例》,该条例规定凡从欧洲输入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舶或商品原产地的船舶承运;凡从亚洲、非洲或美洲输入英国、爱尔兰和英国各殖民地的货物,只能由英国船舶或有关的殖民地船舶承运;鱼类产品的进出口及英国的沿海贸易,也都必须使用英国船舶。1660年,重新颁布的《航海条例》又规定,殖民地的某些商品,如食糖、靛青和烟草等(18世纪又包括大米和糖浆),只能直接运往英国、爱尔兰或其他英国殖民地,非规定范围内的产品则必须由英国船舶从其殖民地直接运往外国港口。自1664年起,英国禁止其殖民地直接从欧洲各国进口必需的商品,这些商品必须通过英格兰转口。为了抗衡英国这一强劲的竞争对手,也为了保住自身商业霸主的地位,联省共和国不惜与英国兵戎相见。1652年双方爆发了第一次商业战争。英国的综合实力和海军力量显然强于对手,因此能承受战争所带来的暂时损失,联省共和国则不然,1653年被迫求和。1654年4月双方签订停战和约,联省共和国不得不承认《航海条例》。其后在1665~1667、1672~1674、1780~1784年间双方又三次走向战场,结果以联省共和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由于这一系列战争,联省共和国不仅失地赔款,国力和威信都下降到最低点,而且还被迫拱手交出商业霸权,从而降格为一个二流国家。
在尼德兰各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和商业始终是两大相辅相成、兴衰与共的行业,联省共和国亦不例外,随着商业霸权的丧失,其金融业也备受冲击。长期以来,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巨头逐渐形成了一个对外封闭的放款人集团,他们在有可靠担保的前提下,以很高的利息将巨款借贷给政府,由此既可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又可获得政府的保护,所以17世纪中叶仅荷兰一省的公债就高达1亿5000万盾的天文数字(注:萨哈贝尔:《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纽约1964年版,第164页。)。除此之外,他们还把巨额金钱投向海外金融市场,在整个18世纪他们大量认购英国国债,还就印度公司、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活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萨克森选侯、巴伐利亚选侯、丹麦国王、瑞典国王、俄国女皇、法兰西国王和正在进行独立战争的美国起义军等都是他们的债务人,18世纪下半叶仅丹麦王室的债务就多达1200万佛罗林。据估计,联省共和国1782年共有资本10亿佛罗林,其中向外国贷款3.35亿佛罗林,殖民地贷款1.4亿佛罗林(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卷,第298页。),占总资本的50%弱。与商业活动高度依赖海外市场一样,资金大量外流一方面使可观的利润滚滚而来,另一方面也使金融业自身危机四伏,事实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第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于1763年。时值七年战争(1756~1763年)期间,由于欧洲各主要国家都被卷入了战争,处于中立地位的联省共和国乘机加强商业活动,一度几乎全部包揽了对法贸易,及与非洲和美洲的贸易,后两者的数额极其巨大,利润往往高达100%,乃至200%。这一暂时的现象使联省共和国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恢复往昔商业繁荣的时机来临了,为了支持日趋庞大的商贸交往,遂大肆发展信贷业务。各种名目的信贷导致证券大量流通,据有人估计其数量之多,竟超过联省共和国现金拥有量的15倍,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当贴现银行因无力贴现而突然拒绝接受期票贴现时,厄运便降临了,企业纷纷倒闭,商行接连破产,至1763年8月19日阿姆斯特丹已有42家商行宣布倒闭。一些人试图从海外抽回资金以救燃眉之急,但远水难解近渴,即使从英国回抽资金,当时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一切皆属徒劳。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由此陷于瘫痪,“交易所的一切活动全告停顿……不再开展贴现和汇兑业务,甚至没有行市,猜疑情绪十分普遍”(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卷,第300~301页。)。1772年,当克利福特商行因疯狂投机英国东印度公司股票失利而倒闭时,危机又一次袭来,受其牵连许多小商行亦纷纷破产。其后阿姆斯特丹又数度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信誉下降,实力大跌,18世纪末叶最终不得不将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让给英国的伦敦。
回顾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较快,一度显示出勃勃生机,但就总体而言,由于缺乏坚实的手工业基础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紧密的经济联系,缺乏整体的激励因素,缺乏持久的活力,因此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在辉煌一时之后,接下来便是难以逆转的衰微,尤其当世界经济被纳入产业革命的轨道时,尼德兰更显得力不从心,后劲不足,昔日的优势逐渐消失,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其他西欧国家在快速变化的经济大环境中一展身手,后来居上。这一结局绝非偶然,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
